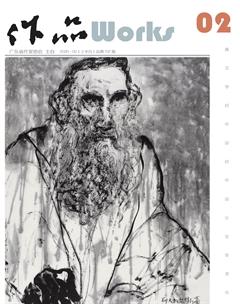刺客聂隐娘的不可思议妄想症候群(短篇小说)
王明辉
推荐语:朱振武(上海师范大学)
王明辉于2017年以优异成绩考入上海师范大学,成为我的学生,攻读国家重点学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已有三年。三年来,他在上海师范大学接受了严格的学术训练,尤其是在英语文学的赏析和研究上表现出色。
创作和研究,本就是并蒂之花。在王明辉的这篇小说中,我们能清晰地看到外国文学对他的显著影响,以及他对西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技巧的熟练运用。这同他几年来认真的学术训练是分不开的。
一对青年男女,街头偶遇,一见钟情,这样类似的情节,无论是在文学经典,还是流行文化中,都已经是屡见不鲜了。因此,要出奇、出新,才有文学价值。《聂》这篇小说,在内容上,广泛使用了“戏仿”的后现代手法。大量流行文化的运用,也使小说有了“拼贴”之感。小说虽写的是现代都市男女的恋爱故事,却使用了唐传奇与侯孝贤电影《刺客聂隐娘》的故事结构,人物名称亦一一对应。这是对经典作品的戏仿,形成了一种互文关系,也是对经典的现代阐释。小说标题,是对日本流行轻小说的戏仿。小说的第一句话,则是对夏目漱石的小说《我是猫》的戏仿。王家卫式的台词,动作电影的场景,这些流行文化符号也都成为小说的有机组成部分。但小说最重要的艺术形式,则是改变了现实主义的平铺直叙,在结构上采用的“独白”形式。几段由不同人物组成的“独白”,彼此错落有致地组合,忽而彼此独立,忽而彼此对话,使小说拥有了近似戏剧表演般的感觉。这些“独白”的文风、腔调,也各有不同。聂隐娘少女的娇憨单纯,田季安成年男人的沉稳和“做作”腔调,都各有不同。而“磨镜男”这一角色,则更像是作者的介入。在米兰·昆德拉的小说中,我们就可以看到这种写作技巧。作者以自己随时插入的议论、哲思,将小说中的人物像提线木偶一样操纵、讽喻,表达自己的想法。当然,这种“独白”式的戏剧技巧,也可以看到布莱希特“间离”戏剧风格的影子。
当然,如果只是纯粹“炫技”,小说就成了空洞的皮囊,缺乏骨架。在这部小说中,我们还是能看到作者的一些自己的思考。恋爱与被爱,在小说中被化为刺杀与被杀。男女之间的接触、彼此试探、你进我退,被化为惊心动魄的“战斗”。而“磨镜男”又代作者发声,如他所说,“太多的男男女女,不过都是一面被打碎的镜子,折射出的无穷多的镜像罢了”,这也使小说的意义不再是塑造单一人物,而是在这种人物关系中试图呈现更为普遍性的意义。这种关系的理解是否合情合理,当然见仁见智,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隐秘处,确实呈现出种种不同的可能性。因此,在许多已经被认为“司空见惯”的文学主题中,写作者仍然是大有可为的。
聂隐娘
我叫聂隐娘,男朋友嘛……还没有。
该怎么介绍我自己呢,对于像我这样的女孩子,好像不是一个容易完成的任务啊。身高,体重,星座,血型,爱好……
——好吧,认真地说,我是一个杀手。
当然,杀手这一行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性感,需要熬夜,没有社保……没有养老金。
——嗯,好像,熬夜对女孩子的皮肤是不好的呀。
嗯,还是介绍一下我的爱好吧!我喜欢枪(女孩子喜欢枪有什么大不了的!),我的第一把枪,AWP,英国国际精密仪器公司制造,口径0.243英寸,枪长1124毫米,枪重7.5千克,采用7.62mm步枪弹,优美无比的右旋膛线,有效射程600米,威慑距离1200米。
也就是说,600米开外,我就可以用这把枪,打爆你的脑袋!
“男人没一个好东西!”这是师父常常挂在嘴边的口头禅。
假如按照那些脑袋将会被我打爆的男人作为标准,这句话好像也没什么问题。
不过,有时候我也会感到疑惑:要是男人都不是好东西,那我是从哪儿来的?
田季安
他们都叫我田季安,当然,我也可以叫别的名字。这不重要。
名字只是一个符号,他们时常用它来掩饰许多东西。
比如,当你走在街上,你会本能地避开那些动作流里流气,身着奇装异服,满口污言秽语的男女,尽可能使自己的行走路径接近那些衣着平庸,眼神木讷,动作规整的人群。你感到安全。
你不能不通过符号来认识世界。即使是静卧身边,睡姿安详的爱人,他脖子上的一缕长发,忽然间就会向你出卖许多秘密。
就像你无法预料,向你走来的那个貌不惊人的女孩,會不会在下一秒就向你掏出手枪。
当然,我无法告诉他们的是,每个星期天的晚上,我都会来到我所在郊区的工厂,视察自己有条不紊的生意。四十五个熟练工人,借助夜幕的掩护,帮助我提炼出纯度最高的海洛因,然后,那些海洛因会被分装进大小不一的塑料袋里,通过飞机、轮船、汽车、毒贩的口腔和肠道,运往世界各地。
磨镜男
我是磨镜男。
你是否还记得第一次在镜子里见到自己的情景?我想你大概忘了,如同你忘了的第一个梦,忘了你是如何第一次坠入那诗意的漩涡。
你被吸入这漩涡中,然后你浮上来,你看见自己。
在镜子里的自己,你是否尝试过去抚摸它?直到你的手指触碰到冰冷的镜面,你恍如从梦境中醒来,一瞬间你明悟你所看见的并非真实。
与水中的倒影不同,镜像不会被打碎,你打碎镜子,每一片镜子上都会有一个你,你只是以另一种更琐碎的方式注视自己。
就像记忆不会因死亡而消失,你的记忆被保存在他人的记忆之中,呵护,传播,你的形象变得琐碎,被扭曲,但这不是记忆的错。
如同你不能因为自己的丑陋而去怪罪镜子。
日复一日,我重复着打磨镜子的手艺,在透明的玻璃上浇上一层薄薄的水银,玻璃的光明与纯洁在这一面消失,在另一面,则被加倍地保留下来。
聂隐娘
“十八岁,你可以去杀人了!”
那天,当我看到第一个猎物的照片时,我告诉自己,他长得很好看。
师父像是猜着了我的心思——她每次都能猜着我的心思——于是她一把夺过我手中的照片,用不容置喙的语气说:“看一遍就够了!”
当然,她没忘了自己的口头禅:
“男人没一个好东西!”
二十八岁,男,毒贩。我不需要了解更多,我的臂弯和手指已经在轻声呼唤武器的重量,然后,亲眼看着他的脑袋在我的瞄准镜里爆炸!
我注意到天空正在变得阴沉,一个杀人的好天气。
于是我把嘴里嚼得快没味的口香糖吐在地上,然后大摇大摆地走进一家五金店。
众所周知,杀手路过的五金店,招牌永远只是为了掩人耳目。事实上,店里的老板每一次都会为我提供工作需要的武器,价格公道,童叟无欺。
当然,一切都会按照规矩行事,比如,当我告诉老板今天需要的钉子的尺寸时,经过挑选的子弹正被有条不紊地嵌入弹夹,而在说明了要求的螺丝刀的模样之后,一把特殊型号的枪就会从仓库里重见天日。
我知道我的枪和它腹中的子弹都在召唤我。
可是……嗯,要是就这样把那个男人的脑袋打爆了……呃,为什么我好像有点舍不得的样子?
田季安
每天早上,我和每一个遇见我的人微笑。
为什么不呢?无非是面部肌肉短暂地拉扯,使嘴角上升到恰如其分的位置。一个微笑,消耗不了多少能量。我只是让他们看到他们想看到的,他们自然而然地就会认同他们所认同的。
虽然,他们未必理解他们所理解的。
地下室里,组织的叛徒正在哀号着,遍体鳞伤的男人被我们捆绑在椅子上,一桶水被浇在他的头上,他的表情皱缩了一下,几条伤口在脸上上下蠕动着。
对一切精致、准确的事物,我本能地怀抱着热情。比如,衡量一下施虐和痛苦之间的兑换比例。
另外,我还有一个很私人的爱好,做木工。
我只喜欢那些未经修整的原生木料,多刺而粗糙,我用我的双手,一点一点地把它们抚平,用温柔来代替野蛮,让手中其貌不扬的木头变得规整而美丽。
当我完成我的艺术品,短暂地欣赏以后,我会把它们付之一炬,美只有在瞬间才得以保留。
隔几个月我就会选择一家五金店,挑選修整木材的工具。现在,我翻动着柜台上的锯子、螺丝刀、砂纸……
这时,我看见那个女孩走进店中。
磨镜男
短暂地注视,对方的身影进入彼此的眼睛,他们就这样初次相遇。
人的眼睛的构架比任何一面镜子都要复杂。但镜子却是纯粹、安静的。它不希求窥见对方内在的思想和情感。它看见的只是裸呈于镜子前的唯一物,你的容貌,身体,表情。
也许镜子才是最适宜象征一见钟情的符号。它不照见本质,只照见存在。
聂隐娘
他长得高高的,很瘦,腋下夹着一把黑色的雨伞。土黄色的外套,但是干干净净的,像他额上的头发,柔软,妥帖。
(有些人,你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就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他那样。)
他细心挑选着货架上的商品,一件件地拿起,观察,比对,又一件件地放下。我留意到他抚摸工具的手异常温柔,细腻,让人出神。
我突然产生了一个古怪的念头:如果现在在他手下的不是那些钉子和铁锤,而是我的身体,那会怎么样呢?
(我好像脸红了……?)
田季安
我很久没有看见这样的女孩了,因此我很早就注意到了那个女孩,注意到了她青春的身体,注意到了她搭配混乱的衣着,注意到了她躲躲闪闪的目光。她小心翼翼的眼神,时不时用眼角向我窥视,然后装模作样地拿起一把螺丝刀放在手中把玩,煞有介事地研究上面的纹路。
但我发现了她握住螺丝刀的手异常有力,在我听到雨声的时候。
几秒钟,几分钟,几个小时后……同样一只手握住的手枪,扣动扳机后,子弹会飞向我。
磨镜男
把艺术当作生活是愚蠢的,那么,反之,把生活演绎成艺术又该如何呢?
影视剧中的爱情,无一不发展得十分迅捷、简短、利落。一见钟情的桥段永远被各种艺术家烂熟于心,然而……
然而,尽管可以斥之为荒谬,但是其中关于爱情的论述却显得言之凿凿——
诚然,一见钟情近于荒谬,然而若非钟情于一见,则必定永不钟情。
聂隐娘
那天下着雨,我走进一家五金店。我发现自己没有带伞。
于是我的注意力不由得被那把黑伞所吸引。那把收束的黑伞,像一只安静的猫,带着诱惑,被他安静地收在腋下。
我当然讨厌下雨了,即便可以把扣动扳机的动作做到足够潇洒,但是脑袋上湿漉漉的头发,总是会在一瞬间败坏我的形象。
田季安
我已经习惯了带伞出门,因此避免了那些雨点沾湿我的肩膀。
如同我在折磨那些囚徒时会自动穿上雨衣。我讨厌那些血迹溅上我的衣服,玷污我的躯体。
(难道坏人也会害怕肮脏吗?)
天空仿佛就在一瞬间暗下,然后转瞬之间雷霆震动。尽管我已经训练自己去保持对世界足够的漠然,但我仍不由得被倾盆的暴雨所吸引。当我向外面的世界望去,一瞬间,我的眼神同那个女孩交错、碰撞。
聂隐娘
那一天的乌云遮天蔽日,黑色装束包裹我的全身,一场大雨,足够湮灭一切屠杀的痕迹。迷人的AWP,1124毫米的修长枪管,冰冷的,而且瞬间就会变得滚烫的枪管,像一条温顺的蟒蛇,蛰伏于我的怀中。
一千米,一辆军用吉普滚滚而来,泥水在身后扬长而去。四周护卫的车辆被我忽略,二十八岁的毒贩,正坐在右边靠后的位置,一件土黄色的外套,貌不惊人,右手上把玩着几枚钉子。
大雨倾盆,如同无形的罗网,渐渐收束,消灭里面一切的呼吸。
我的嘴角扬起一抹微笑。
枪响,然后时间像是变得缓慢,一枚枚钉子,渐次坠地。
田季安
海洛因,提炼自罂粟花的果实。美丽的植物,夏季开花,秋季落叶,花瓣脱落,捡起那迷人的罂粟果实,把玩它,杀死它,你能看见那惨白的汁液缓缓流出。
这些汁液变成白色的粉末,我捧起它,静静等待着它从我的手指间滑落。
我只是一个商人,我只是满足了他们的欲望。
就像他们满足我的欲念那样。虽然有时候,我也会回忆起自己曾经屈服于欲念的时刻。
磨镜男
他们说自己屈服于爱,然后他们又说自己屈服于欲念。
爱不过是欲念中的一种。
丢开它,握紧它,兜兜转转。明智的人清醒地衡量二者,隔绝欲念,拆分爱。
或者是,对于更多的人而言,他们忽而愚蠢,忽而明智,或者是长时间昏头昏脑地愚蠢之后,又变成了大彻大悟的愚蠢——他们一遍一遍地擦亮镜子,好像这样他们镜子中的形象就会变得好看一点。
他们一下子认定了清心寡欲的正确性,如同一下子认定了愚蠢的正确性那样。
不过,要是人生没有欲念,那该是多么无聊的一件事。
聂隐娘
小时候,我喜欢笑。
偶然路过街头的野猫,摇摇欲坠的叶子,巷子里亲吻的男女,突如其来的大雨。
我忘了我是什么时候开始这笑,我忘了我是什么时候结束了这笑。
就像我忘了这场大雨是在什么时候开始,也不知这场大雨会在什么时候结束。
田季安
就像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子弹被放入弹夹,什么时候子弹冲出枪膛,什么时候子弹没入你的身体。
磨镜男
就像你清楚地知道自己爱上了一个人,但你却忘了自己是什么时候爱上了她,也会忘了什么时候你已不再爱她。
聂隐娘
枪、杀手、子弹都是一个。
田季安
杀手与猎物都是一个。
磨镜男
爱者、被爱者与爱都是一个。
田季安
那天一个杀手来到我的面前,她告诉我她需要杀了我。她的勃朗宁在幽暗的室内闪着寒光。窗外大雨倾盆,好似一切摇摇欲坠,仿佛整个世界被洪潮般的暴雨撕成碎片。她额首的头发不停地淌落雨水,滴落在地,紧握着手枪的手笔直地指向我,与她瘦削的身体构成了一个完美的九十度角。闪电劈过,房间一刹那间被照亮,我看见她的脸庞。她凝固的姿态犹如雕塑。
我平静地坐在写字桌后,平静地翻动着桌面上一本关于木刻艺术的著作。书本最后停留在第二百七十页,木匠的丑脸在纸张上栩栩如生。
我看了看她,淡淡地一笑。
“为什么不把湿掉的头发先擦一擦?”
她怔怔地看着我,很显然,她没有意识到会有这种形式的临终遗言。
又是一道闪电,我看见了她躲躲闪闪的目光,小心翼翼的眼神,时不时用眼角向我窥视。
“你是第一次杀人吗?”
“要你管!”她恶狠狠地说着,同时恐吓似的用拇指打开了手枪保险,这一举动充满了孩子气的天真。
我笑了:“难道杀手出门就不带伞吗?”
聂隐娘
在任何一个季节里,都会有一场场暴雨,把我们一次次浇湿。
师父一次一次地喃喃自语:“男人没一个好东西!”
也许,在很多很多年以前,她曾经被一场大雨浇湿,只因那个撑伞的人没有出现。
田季安
一个人不是生来就习惯带伞的,直到他一次次地被大雨浇湿。
那天晚上,她的枪口对准我,幽暗如同冰冷的井水,微微喘息。我看到她纤长的手指缓缓地放在了扳机上。即便我看不见,但她鼓起的脸颊暗示着她已经咬紧了牙关。
我说:“不要紧张。”
她不耐烦地说:“你闭嘴!”
我慢条斯理地吐出我的措辞:“杀人并不困难,你杀了第一个人,很快你就会习惯杀第二个人、第三个人……直到你淡忘这一切……”
我看了看她:“你要不要先把头发擦一擦?”
她骄傲地说:“死亡不等人啊!”
我“砰”的一声合上书本,然后将身体倒向椅背,选择一个更舒适的角度坐下,然后,平静地凝视着她。
聂隐娘
那天下着大雨,我走入一家五金店。在那家五金店的屋檐下,那个男人平静地看到了我,同时也看到了我瞳孔中所映照出的,他的倒影。
他长得高高的,很瘦,土黄色的外套,但是干干净净的,像他额上的头发,柔软,妥帖。
他用心挑选着一件件工具,他抚摸它们的动作多情而温柔。我留意到了他腋下的黑伞,犹如一只黑猫寄居在他的怀中。
那天我十八岁,那天我第一次走入这家五金店,那天我第一次遭遇一场大雨,那天我没有带伞。
那天他看了一眼我,然后好像自言自语地说:
“雨是不会停的。”
那天大雨,我和那个男人相遇在那家五金店。
田季安
在被雨水浇湿过很多次以后,我开始习惯带伞出门。
从那以后,我忘记了雨水浇湿身体的感觉——衣服浸透了雨水而沉重、冰冷,紧紧包裹着我。而现在,雨伞保护着我,同时我也拒绝了世界。
我会羡慕吗?我看见那些在雨中奔跑的孩子,纵情享受被雨淋湿的快乐,欢笑,舞蹈,挥动手臂。
很多年前我也是这么一个孩子,像鸽子一样在雨中玩耍,毫无顾忌地让衣服沾上雨水和肮脏,即便现在的我每次洗手都要重复三遍。只因为那时的我完全明白,即使在一次次纵情玩乐之后,那个撑伞的人都会出现,为我擦干潮湿的头发。
直到她消失。
那一天,我走进一家五金店。外面下著大雨,我看到一个女孩正站在屋檐下,我知道她没有带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