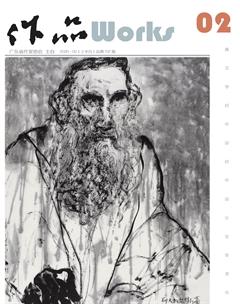福报(短篇小说)
谈洐良
推荐语:金理(复旦大學)
谈衍良身在上海写作,他将为“文学上海”增添什么样的可能性?近年来,这条道路上的先行者大致表现有三点:靠着对酒吧、咖啡厅、摩天高楼等组成的时尚地标进行精致的消费生活展演,为中产阶级勾勒迷人而夸饰的都会神话。或者以“沪漂”身份赓续司汤达笔下于连式、巴尔扎克笔下拉斯蒂涅式的形象:当庞大的都市在面前展开时,外省青年内心充满野心与狂想,既要拼命融入,又总是感觉到处处排挤和累累伤痕。或者自居贵族、“老灵魂”而指斥前述两者的虚妄,以继承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风华为傲……文学如何选择地理空间,现实中的城市如何被写入文学中的城市,当然不是简单的反映论问题,背后联系着深广的社会思潮和意识形态,以及个人视野与才思。与文学前辈相比,谈衍良与城市之间的关系更为松弛,他给了我们一双看待上海的、与此前不同的眼睛。《福报》所书写的社区,不是“文学上海”传统内的中心地带,谈衍良却写出了这一社区以及生活其间的人们内在的尊严、活力与丰富性。
我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出生,不免将谈衍良与我这一代的写作者初登文坛时的情形相比较。一种对“80后”的惯常看法是,这代人的写作往往沉迷于“独语”,沉迷于对个人经验的反复书写。略显悖谬的是,锁闭在个人经验的迷恋中,未必能敞开自我的深刻与复杂,反而显得单薄,当然这一“单薄”也是历史性的“单薄”,伴随着所谓“总体性社会”的解体。在当下世俗生活中,人不仅在精神世界中与过往的有生机、有意义的价值世界割裂,而且在现实世界中也与各种公共生活和文化社群割裂,在外部一个以利益为核心的市场世界面前被暴露为孤零零的个人。谈衍良的写作似乎有所不同,《福报》中的汪嘉康兴许与作者年龄最为接近,除了接受这个时代中青年人共享的新知之外,谈衍良将其置于一组一组的关系中:家族、社区、地方小传统……这样的关系在谈衍良笔下显得生机勃发。在小说集《乌鸦妖怪与随机数侦探》中,有更加众多的人物携带着各自鲜活的声口、性情、气质而兴致勃勃地登场。谈衍良在关系中写作,让人物在八面来风中自由呼吸……
《福报》的艺术风格是老实而低调的,却透露出基本功。不妨引入鲁迅的意见做个参证。鲁迅具备极高的美术鉴赏力,尤其对木刻艺术的见解往往度越流俗,曾在书信中委婉批评当时的一批青年美术家:“好大喜功,喜看‘未来派‘立方派作品,而不肯作正正经经的画,刻苦用功。人面必歪,脸色多绿,然不能作一不歪之人面,……譬之孩子,就是只能翻筋斗而不能跨正步。”可与此番见解相沟通的是,徐悲鸿有一段话阐明艺术精进之过程,发人深省:“二十岁至三十岁,为吾人凭全副精力观察种种物象之期,三十以后,精力不甚健全,斯时之创作全恃经验记忆及一时之感觉,故须在三十以前养成一种至熟至准确之力量,而后制作可以自由。”一生成败端赖二三十岁时的刻苦用功,将来方可成其大、成其艺术自由。从谈衍良的写作中能够感受到他对生活世界的热爱与沉浸,在热爱与沉浸中“分析精密之物象,涵养素描功夫”。话说回来,这种老实的专业精神并不意味着平庸乏味的现实主义,比如《福报》中飞机阿姊与刘轰隔着炸锅的几番对话,充满着谐趣与“文学的余裕”。
我从以上三方面来把握谈衍良写作的意义,当然这只是对起跑线上出发姿态的观察。如此年轻的一位写作者,我们理当期待他未来的文学世界更为摇曳多姿。
一
罗斌杰今天上午到永寿寺里请了一炷十块钱的香,站在香炉面前立了二十分钟,出门之后,又在庙门前的大轰哥炸鸡店买了一包十二块钱的香酥鸡。现在他该回去了,阿姊要是想见到他的话,下个礼拜六至少得早晨十点以前就到庙里来——客堂间的桂师傅告诉飞机阿姊,飞机阿姊又把这事儿告诉了坐在庙门口折锡箔的顾阿姨,顾阿姨说:“我不晓得什么罗斌杰,我只晓得今天早上来上香的人有五个,五个都是穿了跑鞋。”
从仲凯南路学府街公交站——八个月以前正式改名叫易购广场公交站——往东走一百米,穿过门厅,穿过香炉,进大殿拜上一圈,点一炷香。飞机阿姊是这样做的,她相信罗斌杰也是这样做的。据飞机阿姊从大轰哥炸鸡店的老板刘轰那儿听来的消息,罗斌杰是复旦大学佛学院的博士。没有人会通过“复旦大学佛学院的博士”联想起一个穿跑鞋的男人,所以飞机阿姊又跑出庙门去问刘轰:罗斌杰今天是不是穿了跑鞋?刘轰的两个炸锅都热烈地沸腾着,手上还在用菜刀斩着一块裹了面包糠的鸡肉,发出钝器撞击的重响。于是飞机阿姊又大声地问:罗斌杰今天是不是穿了跑鞋?
刘轰的腮帮子近乎咆哮,但他的声音还是只能当作沸油的陪衬,他说:“你站那儿能看见我穿啥鞋吗!”
飞机阿姊还真看不到刘轰穿着什么鞋,她只能看见自己穿了一双女式尖头黑皮鞋。康康在他六岁的时候就教会了飞机阿姊“光沿直线传播”的道理,也就是说,飞机阿姊看不见刘轰的鞋,刘轰也就看不见飞机阿姊的鞋。要是罗斌杰买香酥鸡的时候站在飞机阿姊现在站着的位置,刘轰也就看不见罗斌杰是不是穿着跑鞋。飞机阿姊说:“那就谢谢你,他下一趟来你就帮我看一下。”
飞机阿姊也不知道是刘轰没有回答她,还是她没听见刘轰回答了她。她转身钻进大轰哥炸鸡店边上的敬文香烛店,问:“陆老师,你晓得那个每个礼拜都要来拜佛的罗斌杰吗?是个大学生,我还从来都没见过每个礼拜都会到庙里来的大学生。”
陆老师说:“我不认识罗斌杰,我只晓得机电三班有个叫刘斌杰的。我也没看见刘斌杰来过庙里,不过他可能是来易购广场买衣服的,顺道就来庙门口看一看。你搞清楚你要找罗斌杰还是刘斌杰了吗?”
飞机阿姊说:“我搞清楚了,要寻的是复旦大学佛学院的罗斌杰,不是你们机电三班的刘斌杰。”
陆老师放下手里的两沓纸钱,从柜台下面掏出一捆线香:“现在线香价钱涨了,十五块。阿姊还是老样子?”
飞机阿姊摸出一张棕色的二十块:“老样子,现在啥物什都涨价了,陆老师到底是个老师,涨价也涨得是最晚的。下趟礼拜六的时候你帮我看看,有没有一个到庙里来的小伙子,穿跑鞋来的,名字叫罗斌杰。”
陆老师把二十块钱放进长满锈斑的铜皮盒子里,推了一下他那张倒大脸上的金丝眼镜,然后他嘴巴一咧,笑出了森林大风的声音:
“罗斌杰,我想起来啦,飞机阿姊找这个人已经找了三个礼拜了。我还晓得阿姊是没有那么容易寻着他的,阿姊,你晓得这是为什么吗?”
飞机阿姊用手指在自己的嘴巴前面摇了一下,陆老师立刻就笑着闭上了嘴。飞机阿姊知道陆老师要说什么,这个词可还是飞机阿姊教给他的。
“现世报”这个词,飞机阿姊是从她的奶奶那儿学来的。飞机阿姊的奶奶曾因为每天给她卧病在床的男人烧一炷香而被镇上人称作“心肠最好的女人”。飞机阿姊身为汪嘉康的奶奶,尽管尚未在永寿寺建立起名声,也成功地让他在两岁零三个月的时候就学会了“现世报”的用法。它通常以一个感叹词的形式出现,例如,在汪嘉康奔跑而摔倒,或者摔了碗盘筷子和他的模型车的时候,“现世报”可以用于取代“哎哟喂”的位置。
如果汪嘉康把别的孩子推倒,或者砸了别人的模型车,“现世报”三个字就不足够了。飞机阿姊会说这是汪嘉康他姆妈的现世报,或者汪嘉康他奶奶,也就是飞机阿姊自己的现世报。对于飞机阿姊从她奶奶那儿学来的用词,汪嘉康的推论是:一个人活得越久,积累的罪业就越多,“现世报”也就越重。飞机阿姊赞成他的观点,但现世报也有善恶之分,飞机阿姊足够虔诚,所以她养出了两个当飞行员的儿子;在永寿寺边上开购物中心则是亵渎,所以整个易购广场的三十八家店铺里倒闭了三十六家,剩下的只有一间麦当劳和一间没招牌的成衣批发店。
汪嘉康通常会在这时候开始笑,从而展示他也不是一个虔诚的人。
飞机阿姊说:“康康,笑话观音菩萨,还是在笑话我?”
汪嘉康笑着回答:“没有,我谁也没有笑话。我是觉得你讲得对才笑的,这就叫会心一笑,心如明镜台。”
鬼才相信汪嘉康这是会心一笑,汪嘉康一次都没给菩萨磕过头,一次都没给佛祖烧过香,他还在永寿寺门前吃香酥鸡,吃炸香菇,他说:“我在庙门口吃炸香菇,就等于是请佛祖吃炸香菇了。真正的佛祖是什么都吃的,百无禁忌,没有你们这些瞎讲究。”
大轰哥炸鸡店里一共就只有两个炸锅,一个是炸香酥鸡用的,一个是炸鸡腿用的,炸香菇用的大都是炸香酥鸡用的炸锅,因为炸香酥鸡的温度比炸鸡腿稍微高一点儿。南无阿弥陀佛,汪嘉康还是个孩子,他没有对菩萨不敬的意思。
从法律的角度看,汪嘉康还要过两年才会脱离“孩子”这个群体。观音菩萨兴许不太在乎现在的法律,飞机阿姊只指望菩萨能听自己一句话。飞机阿姊的心最诚,每天都到庙里来,她不怕菩萨不理会自己,怕的是两年以后,汪嘉康从智华中学一毕业,成了一个大学生,他就不再是孩子了。
飞机阿姊是不说谎的,一旦她觉得汪嘉康不是个孩子,她就不能对菩薩说汪嘉康是个孩子了。南无阿弥陀佛,汪嘉康虽然不是一个孩子,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她会原谅汪嘉康的,看在飞机阿姊的面子上。
二
飞机阿姊一个人住在仲凯二村四十六号四○二的二室一厅已经一年零四个月了。一年零四个月以前,飞机阿姊的老公——也就是飞机爷叔——被送进医院以后,这一间七十五平方米的屋子里就只剩下飞机阿姊一个人。
其实飞机爷叔住院以前的几年里,这间屋子也都是飞机阿姊一个人安排的,飞机阿姊亲自在阳台上搭了棚,在厨房的窗外头拉了铁栏杆。飞机爷叔进了医院以后,飞机阿姊又在阳台上的塑料棚里给瓷雕菩萨搭了一个屋子。有菩萨就得有蜡烛,但是汪嘉康不喜欢蜡烛,他说点燃的蜡烛有股脚臊臭。菩萨的面前哪能没有蜡烛呢?于是汪嘉康帮飞机阿姊在网上买了两支二十八块九毛八的节能灯假蜡烛,三十一厘米的假蜡烛,是菩萨的两倍高。
飞机阿姊刚给菩萨安了家的第一个晚上,她的第一个儿子阿大就回来了。飞机阿姊说:“你回到家里来,晚上的飞机谁来开呢?”
阿大检视了仲凯二村四十六号四○二的每一个角落,他说飞机阿姊的床垫该换了,脱排油烟机的滤网也该换了;阳台上的塑料棚在下雨的时候声音肯定比锣鼓还响,飞机阿姊的听力一直不错,窗外有两只鸟叫就会睡不着;阿大还说:“这两支蜡烛也太高了,长得像菩萨家里的廊柱。”
阿大在家里住了一夜,第二天一早,飞机阿姊的第二个儿子阿二也回来了,她第一次发现阿二的头顶心是秃的。飞机阿姊说:“你回到家里来,部队里谁来管呢?”
阿二从飞机阿姊卧室的电视机前走到小卧室里堆满饼干罐子的柜子边上,从堆满饼干罐子的柜子边上走到新换了滤网的脱排油烟机下边,从脱排油烟机下边走到了阳台上的菩萨面前。阿二说:“换了新房子以后,在厅里放一个大一点的,差不多可以到腰那么高。”
晚上,飞机阿姊的第三个儿子阿华带着汪嘉康回来了。阿华说:“小萍今天夜里要帮学生补课,就不过来了。我们到爸的医院里去看一眼,然后再去吃个饭。五个人,开车正好。”
阿华驾着他三成新的越野车从仲凯二村开到永寿寺,从永寿寺开到街道卫生服务中心。飞机阿姊坐在汪嘉康的边上,汪嘉康坐在阿大的边上。满街的车走走停停,仲凯街道的灯火早就今非昔比。卫生服务中心前的五岔路口,易购中心灰暗的霓虹灯管底下,阿华为一个九十九秒的红灯熄了火。飞机阿姊说:“我以后每天都可以坐960路公交车去看一趟老头子,看完老头子之后,我就走到永寿寺。你们还记得顾桂花吗?就是张志利的姆妈,她每天都在永寿寺门口折锡箔纸。还有桂新盛,就是那个桂光头,他在客堂间里冒充和尚,收香烛铜钿。拜完菩萨之后,永寿寺门口有一部1208路公交车,我就坐1208路公交车回家,它有一站是停在铁路边上的,就是仲凯二村的后门外面。”
躺在床上的飞机爷叔已经是个傻人了,他不会说话,也没人知道他能不能听懂别人说话,所以他的三个儿子就没有和他说话。飞机阿姊坐在床边长叹:这就叫现世报,老头子年轻的时候把永寿寺里唯一的一座木头佛像给拆了,锯成自家的椅子,报应来得晚,但是也来得厉害。这把椅子飞机阿姊是没有坐过的,她也从来不让阿大、阿二和阿华坐。汪嘉康三岁的时候被飞机爷叔撺掇着爬到这把椅子的椅背上,飞机阿姊第二天就偷偷把椅子给扔到了铁路边上的垃圾回收站里。佛像是不该进入垃圾回收站的,但焚毁总好过受辱,佛陀理应原谅飞机阿姊的罪过。
汪嘉康说:“那我也算是往佛像的头上坐过一次了,照你这么说,现世报是不是也该落在我的身上?”
没什么好担心的,这已经是十五年前的事情,该发生的报应也早该发生了——飞机阿姊本该这么说的,可惜她几分钟前才说了一句“报应来得晚,但是也来得厉害”,那可是飞机爷叔四十年前造下的孽。
飞机阿姊早在八年前就已经辩不过汪嘉康了,那一年他学了解方程,学了写八百字的作文,他还看了一本《一本书带你读懂周易》,从书里学会用抛硬币的方法帮人算命。
病床顶上的红外灯光闪烁,飞机阿姊用整间六人病房都能清楚听见的声音说:“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
飞机阿姊的虔诚有了回报,那就是她对于虔诚的延续。在她给菩萨点了LED蜡烛的第一个夜里,她对着那间浅米色塑料板搭成的小庙念了二十分钟。这二十分钟里,她根本就没有想到要阿大或者阿二回来,她从不祈祷她的儿子回到她的身边,也不祈祷她的儿子不回来。
她的阿大陪了她三天,阿二陪了她两天,阿华终于没有说要把飞机阿姊接去凯辉天锦园九号楼1501的新房子里住。从凯辉天锦园去到永寿寺得换三趟公交车,或者走路一个半钟头,飞机阿姊觉得这就是汪嘉康从来没进过去永寿寺的原因——飞机爷叔刚进公交公司上班的时候,凯辉天锦园是一片荒地,现在它在公交地图上依然是一片荒地。
现世报啊!飞机爷叔在公交公司当了十五年的调度员,排了十五年的线路表和时刻表,结果他的孙子想要去一趟永寿寺都没公交车可坐。飞机阿姊慨然长叹,她没能想起——或者只是暫时没去想起汪嘉康每个假期都会到仲凯二村里住上两个星期,而从仲凯二村到永寿寺只要坐一部1208路公交车,再走两分钟的路。
第二天一早,阿华送阿二去了机场。阿大说他也跟着一起去送阿二,然后在机场坐地铁二号线直接到火车站。飞机阿姊喊汪嘉康跟大伯、二伯说再会,阿二说:别叫醒他,让他好好睡吧,我们走了。
飞机阿姊知道汪嘉康已经醒了,阿二可能也知道。她看见她的三个儿子——三个已经长成老头儿样子的儿子,从咯吱响的绿色防盗门里走出去,然后她走进汪嘉康的房间,汪嘉康说:“你等一会儿,我把这张卷子写完。”
飞机阿姊倒退着走出房间,她决定等汪嘉康写完卷子之后就带他去永寿寺。她也知道汪嘉康是不会去的,汪嘉康会说:“到庙里去拜佛既是对我的羞辱,也是对佛的羞辱。”
三
飞机爷叔住进卫生服务中心已经一年零四个月了。这一年零四个月间,一成不变的飞机阿姊成了到访卫生服务中心频率最高的家属,成了到访永寿寺频率最高的香客。
礼拜五,飞机阿姊照例先去街道卫生服务中心给飞机爷叔喂了一个生梨。阿华硬要她出门带把阳伞,所以她就在正午十二点的太阳底下撑着黑阳伞走到永寿寺的门口。这一早上,顾阿姨已经折了五捆五十个的锡箔元宝,也就是两百五十个锡箔元宝。她刚巧在吃饭,咸菜毛豆子炒笋丝,五捆锡箔元宝就横躺在竹篮子里。
飞机阿姊一走进门堂,顾阿姨就立马放下了她的饭盒子,说:“今天早上有一个小伙子来过了,他穿的不是跑鞋,也不是皮鞋,我讲不清楚那是什么鞋子,不过它是黄色的。”
飞机阿姊每天中午都来一趟永寿寺,从来就没有见过什么小伙子。罗斌杰是唯一一个会到永寿寺来的小伙子了,但他每次都是礼拜六早上来的,大概十点到十二点。他大多时候是烧一炷香,偶尔是两炷,二十分钟,或者四十分钟。这比飞机阿姊烧一次香的时间要久一点儿,但还没有久到足以发生一场偶遇,每次他一走,飞机阿姊就到了。
飞机阿姊早就想好了,今晚汪嘉康会住在飞机阿姊的家里,第二天一早,他们就一块儿先坐1208路公交车去永寿寺,然后再去看飞机爷叔。汪嘉康不乐意去永寿寺,但探望一个神志不清的爷爷是他理应做的。飞机爷叔年轻的时候喜欢嘲笑一切虔诚的信徒,他衰老的躯壳却为汪嘉康的虔诚做出了贡献,是他让汪嘉康在这一年零四个月里四次经过永寿寺的门口,吃了四次大轰哥的香酥鸡和炸香菇。
明天一早,大概是八点半的时候,飞机阿姊就会喊汪嘉康起床,然后说:我们先去庙里,然后中午再到医院去,这两天天气热了,我想看看他们每天中午都喂你爷爷吃什么。汪嘉康当然是会同意的,他会和飞机阿姊一起在早上十点到达永寿寺,会在庙门前的小石佛边遇见罗斌杰,会和罗斌杰一起买香酥鸡,会跟着罗斌杰进到庙里,拜菩萨,烧香,在香炉边上立二十分钟。但现在不会了,罗斌杰今天已经来过了。
顾阿姨说:“你急什么呢?我只记得他的鞋子,又不记得他的人。你最好是先去问一问桂师傅,那个穿黄鞋子的小伙子到底是不是罗斌杰。”
桂师傅说他打了一早上的算盘,客堂间外面的事情一桩都没看见。飞机阿姊又去问刘轰,刘轰照着飞机阿姊吼叫了一通,说他没工夫看人的鞋子。陆老师从香烛店里跑出来喊:“阿姊,今朝进货来的锡箔纸比以前的要厚,要买几沓回去吗?”
飞机阿姊跟着陆老师进到香烛店里头。正午的阳光是正直的,它照不到屋子里,整爿店就只靠一个二十瓦的白炽灯泡照亮。陆老师把飞机阿姊拉进两排不锈钢货架当中,说:“今朝早上,我看见刘斌杰了。”
昏暗的屋子里流动着窸窣的电流声,还有电风扇转动的声音。飞机阿姊把耳朵贴得离陆老师的倒大脸更近了一点儿,陆老师深重的叹息全都叹到了飞机阿姊的耳郭里。陆老师说:“娘希匹的刘忠志,有干部不当,跑到外国去寻屁吃。他不当这个副校长,肯定就得让我来当这个副校长了。我左想想,右想想,当了副校长以后,还开一爿香烛店,就落人话柄了。但是我又不好不当这个副校长——”
飞机阿姊不认得刘忠志,也不知道这事儿和她、和罗斌杰有什么关系。陆老师喊了一声“哎呀”,又把飞机阿姊往货架深处拉了几步,“刘斌杰是刘忠志的儿子呀,也是我们机电三班的班长。我今朝早上去刘忠志的家里了,刘忠志跟我讲,我把香烛店盘给别人,我就当一个董事长,也是蛮好的。”
飞机阿姊往后退了一步,看着陆老师蹙紧的眉头,她搞不清楚陆老师是真傻还是装傻,飞机阿姊只好说:“现世报啊!你连刘斌杰跟罗斌杰都分不清楚,还神秘兮兮跟我讲什么呢?”
飞机阿姊回到家的时候,汪嘉康正躺在床上看一本《未来简史》,汪嘉康喊飞机阿姊不要睬陆老师,他光看面相就不像是个好人。飞机阿姊已经七十一岁了,陆老师大概五十岁上下,正是最会骗人的时候,他颠来倒去地说些故事,目的无非就是要让飞机阿姊接手他的香烛店。汪嘉康倒是不知道如今什么生意能赚到钱,什么生意只能亏本,但光看陆老师那双小眼睛和宽下巴,汪嘉康就能猜到他是一定不肯让自己少赚一分钱的。汪嘉康合上书,假咳了一声,“总而言之,奶奶下趟就不要去他的店里了,香烛在网上也是可以买到的。”
飞机阿姊说:“你不要假装咳嗽,你爷爷就是天天干咳,天天干咳,咳到最后就咳成肺炎了。”
按照飞机爷叔的讲法,他是从小闻香烛的味道才把呼吸道闻坏了。飞机爷叔在永寿寺正门对面——也就是如今易购中心麦当劳的位置——住了三十五年,从一岁一直住到三十六岁,他的确是闻了半辈子的香烛味道,但是哪里有人会闻香烛闻出肺炎的呢?
飞机爷叔六十七岁那年,也就是三年以前,他急性肺炎大病初愈的时候,在病床上做过一次辩解。他的这段辩解是讲给汪嘉康听的,汪嘉康告诉飞机阿姊:“爷爷说,他把佛头锯成凳子也属因果轮回的一环。永寿寺的佛每天都接受香火供养,这些香火却伤到了小时候的爷爷,让他落下了肺炎的隐疾;爷爷成年以后趁着时势毁坏了佛像,只是践行了佛陀本身应当遭受的业报。”
飞机爷叔是不会说“因果轮回”“香火”“业报”这种词的,躺在病床上的飞机爷叔当然就更不会。飞机阿姊不知道汪嘉康是听飞机爷叔咕哝了几个词还是骂了几句娘,竟然给他归纳出逻辑这么严密的一套叛逆言辞,说的还是字正腔圆的普通话。幸亏汪嘉康讲完以后补了一句:“他砍人家佛头的时候没有得肺炎,怎么能说他是为了报复呢?他的时间顺序就有逻辑漏洞。”飞机阿姊也就当他是站在佛陀这一边的。
汪嘉康第一次讲这段故事的时候,飞机阿姊本想和他辩驳两句,她打算告诉汪嘉康:这就是飞机爷叔自己的现世报。幸亏她那时候没这么说,肺炎治愈之后一年多一点儿,飞机爷叔就变成了一个傻子。成为傻子显然比一场得到治愈的肺炎更适合成为亵渎佛陀的现世报应。
汪嘉康重新翻开了他的《未来简史》。飞机阿姊瞟了一眼《未来简史》的封面,星云飘浮在纯净的黑色中央,“明朝早上我先去庙里,然后再去看你爷爷。你跟我一道去吧。”
四
上午九点三十分,飞机阿姊果然没能见到罗斌杰。汪嘉康在陆老师的店里坐了半个钟头,但汪嘉康没能见到罗斌杰。汪嘉康当然是不知道罗斌杰这个人的,但他也一定知道飞机阿姊试图把他引见给某人。汪嘉康六岁的时候,飞机阿姊用烤猪肉脯把隔壁家的阿生哥哥诱到自家来,是为了让汪嘉康交上第一个朋友;汪嘉康八岁的时候,飞机阿姊把阿大的老婆的弟弟的儿子接到仲凯一村来和汪嘉康一起住了个把月,是为了让汪嘉康好好学数学。
从结果上看,飞机阿姊的行动颇有成效,汪嘉康在那之后三个月就得了幼儿园奥数比赛第一名。可事实上,虽然阿大说他老婆的弟弟的儿子的数学成绩不错,但这个数学成绩不错的十二岁男孩只是在飞机阿姊的家里玩了一个月的电脑游戏而已。依照汪嘉康的理论,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证明这个没用的奥数比赛第一名与阿大的老婆的弟弟的儿子有关。
汪嘉康当然也不会认为他信不信佛能和一个素未谋面的复旦大学佛学院博士生——或者和任何人有关。他只是一个一炷香能烧二十分钟的陌生人,和一个一顿饭能吃五斤饭的陌生人没有什么差别。没人会因为一个能吃五斤饭的陌生人而尝试去吃五斤饭,但飞机阿姊相信汪嘉康是有信佛的潜质的。相比飞机爷叔,汪嘉康显然长得更像飞机阿姊一点儿,握筷子的手势也更像飞机阿姊一点儿。飞机阿姊二三十岁的时候也不信佛,汪嘉康现在还不到十七岁。
飞机阿姊从庙里走出来,看见十七岁的汪嘉康坐在四十七岁的陆老师的香烛店里。陆老师说:“你晓得这么一个小庙每年能赚多少铜钿吗?嘿,你不晓得的呀。你看看马路对面的易购中心,想要借永寿寺的光,结果倒是永寿寺把它们的光给吸光了。”
飞机阿姊走到陆老师背后往他的肩膀上打了一记:“你跟康康瞎三话四什么呢?”陆老师却没有停嘴的意思,他说永寿寺赚的钱越来越多了,永寿寺外面的香烛店反倒是越来越赚不到钱了。过两天,易购中心的广场中间要办一个什么世界美食什么展览的,声势很大,旁边几个小区里广告都打满了,但是现在谁还会去什么美食展览呢?都是骗人的东西。
飞机阿姊这几天看着太阳伞和塑料桌子一个个在广场中央支起来,泡沫塑料盒子从路边的小卡车上往下搬。飞机阿姊现在知道了,那些盒子里装的都是些烤肉串、鸡翅膀。南无阿弥陀佛,谁不知道易购中心开在永寿寺对面就是犯了忌讳呢?飞机阿姊喊汪嘉康准备走了,陆老师两只手撑着桌子从柜台里站起来,“还没有等到刘斌杰,怎么就要走了?”
飞机阿姊的脑子里闪过一句“佛曰”,然后闪过一句“不该说出来的事情就不要多嘴”。这句话不是佛说的,而是飞机阿姊自己说的,飞机阿姊不能替佛发言,单一句“不要多嘴”又显得有点儿无力,于是飞机阿姊说:“现世报啊!”
飞机阿姊每次喊“现世报”,陆老师都是一副无动于衷的样子。他装作是在推鼻梁上的金丝眼镜,其实就是什么也不想说。陆老师在工业学校除了每周上十节体育课,就是坐在办公室里和打了架、犯了错的学生谈话。陆老师告诉飞机阿姊,他的绝招就是每当学生试图辩解的时候,他就只管推眼镜,一点儿声音也不出。坏学生各有各的壞处,陆老师这招就叫作以不变应万变。
陆老师靠着他这招以不变应万变从德育处副主任做到德育处主任,然后又连着做了九年半的德育处主任。飞机阿姊不知道陆老师怎么能够同时是德育处主任和香烛店老板。她被汪嘉康搀着往卫生中心走,在卫生服务中心和永寿寺中间的一座桥头前,飞机阿姊说:“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善报,卖香烛锡箔是好的。”
飞机阿姊和汪嘉康上桥,然后下桥,走进卫生服务中心的大门。飞机阿姊扭头看了一眼汪嘉康无动于衷的脸:“我晓得了,你今天跟陆老师说了那么久的话,就是学了一招以不变应万变。”
汪嘉康说:“也不光是学了这一招。刘斌杰是什么人呢?”
太阳越来越高,卫生服务中心楼外的空地地面开始发烫。汪嘉康在空地中央停着的一辆黑色轿车边上站定,飞机阿姊也在他边上站定:“刘斌杰是陆老师他们工业学校机电三班的,也是他们教务处主任刘忠志的儿子。我晓得他跟你讲的是罗斌杰,陆老师记名字就没记对过,前段时间还老是把你叫成王嘉杰——三个字只说对了一个。罗斌杰是复旦大学佛学院的博士生,每个礼拜都来庙里拜一次佛。复旦大学离这里要坐四十分钟的公交车呢。他每个礼拜都要烧香,每次烧香都要静静看它烧完,不多不少,每一炷都是二十分钟。”
汪嘉康拉着飞机阿姊绕过停满车的空地,走进卫生服务中心空无一人的大厅。汪嘉康瘫坐到等待挂号用的椅子上,喊飞机阿姊快去看飞机爷叔吧,他要先买一个痤疮膏。
飞机阿姊说:“那我等你买好再过去。”
汪嘉康喊醒挂号处的护士,然后喊醒取药处的护士。汪嘉康说:“我知道你要喊那个罗什么的来带我一起去庙里。我说了多少次了,这种形式主义的东西是没有用的。你想想,为什么你找了他那么多次就是没有找到?”
飞机阿姊推了一下她的老花眼镜。
汪嘉康拆开药盒子,拧开药膏的盖子,涂在自己的嘴角。飞机阿姊这时候才发现汪嘉康的嘴角上长了一个包,他歪着脸,咧着嘴:“你想找到罗斌杰,我不想让你找到罗斌杰,结果你没有找到,如了我的愿。你觉得,这能不能算是一种现世报呢?或者说,这是因为我的福报高过了你的福报?”
五
飞机阿姊没有答应替陆老师接手他的这爿香烛店以后,陆老师像是下定决心要停了他的生意,安心做他的副校长了。顾阿姨说,陆老师开了这么些年的店,钱已经赚得够用,孩子也快大学毕业,准备从新西兰回来了。陆老师还不到五十岁,今天当上副校长的话,还有升任正校长的机会——在工业学校当校长是难了点儿,但是被调去当旅游中专的校长还是有可能的,旅游中专现在的校长已经六十岁了,两个副校长都只有三十来岁。陆老师对来卖香烛的每一个客人说:“我不是因为怕被查才不开这家店了,我是想要专心投身于教育事业之中。我前几年一边开店一边当老师都能当上副校长,你想想——”
“对啊,你要是认真当老师,那现在就得是教育局局长了,”客堂间的桂师傅说。
飞机阿姊猜想陆老师是有可能成为教育局局长的,但她还是觉得桂师傅是在笑话陆老师。飞机阿姊第一次跟陆老师说“现世报”这个词的时候,他还不知道“现世报”的意思。香烛店老板怎么能没听过“现世报”这个词呢?飞机阿姊告诉陆老师因果轮回的道理,陆老师一边点着手里的钞票一边说:“那不就是‘遭报应了嘛,我懂了,‘现世报就是‘遭报应了的意思。飞机阿姊脸上长麻子了,真是现世报啊——我用得对不对?”
一个礼拜以前,陆老师说飞机阿姊见不到罗斌杰是因为现世报;昨天,汪嘉康说飞机阿姊找不到罗斌杰是因为现世报。飞机阿姊一共也就教会过这两个人“现世报”的用法。飞机阿姊点香的时候烫了一下右手的无名指,线香的味道残留在她的关节上。她想着她每天烧香拜佛,给菩萨磕头;她想着她每天去看卧病在床的傻老头子,给他洗屁股,还给他削生梨吃。
飞机阿姊记得她的爷爷在她四岁的时候生了肝病。据说他生了肝病以后,脸黄得像是一个广柑一样,但飞机阿姊没这个印象,她对那个老头儿的所有认知都來自赞美,对她那个忍辱负重的奶奶的赞美。
她喂那个老头儿吃粥,每一顿都喂,每天都用热水给他擦脸,还给他烧香。那时候的永寿寺还只有一个主殿,殿里的和尚都认得她,说她是镇上心肠最好的女人,她的名声一直流传到一公里以外,一直流传到六十年后。顾阿姨第一次在永寿寺见到飞机阿姊的时候,她说:“你就是好阿婆家里的大女儿吧?”
汪嘉康第一次听“好阿婆”的故事的时候,慨叹了一声“现世报”。飞机阿姊告诉他:“‘现世报不是这么用的,我平时喊‘现世报的时候,那都是在骂人。”
这时候汪嘉康十一岁。汪嘉康说:“现世报不光是指恶报,也可以指福报。这样吧,‘现世报这个词你们听不顺耳,那我以后就直接喊,‘福报啊!福报!”
飞机阿姊点上一支香,就坐在庙门口和顾阿姨一起折锡箔,她说,“顾阿姨今朝夜里要不要买点毛豆子回去”,“我不光喊不动汪嘉康,他还说我是现世报”。她看见大轰哥炸鸡店排着队的五个女孩儿,还看见易购广场中央已经排成三长列的长桌和阳伞。麦当劳里零散坐着几个人影,成衣批发店的大门已经锁上,陆老师坐在柜台前面发愣,用一捆蜡烛轻敲着玻璃桌面。陆老师一走,永寿寺就快变成一个美食城了。
飞机阿姊说:“顾阿姨,你反正每天都坐在庙里,为什么不去帮陆老师开店呢?”
顾阿姨只管自己摇头晃脑折锡箔,看着就不像是能开店的样子。飞机阿姊从板凳上立起来,走进客堂间里,说:“桂师傅啊,你坐在庙里也是算账,去帮陆老师开店也是算账,为什么不去接手陆老师的店呢?”
桂师傅沉着脑袋往上拨了三颗算珠,然后往下拨了大概两颗,“我帮陆老师开店也是算账,坐在庙里也是算账,我干吗不好好坐在庙里呢?”
飞机阿姊一路踱出庙门,几乎一脚踩在门槛上。她看见大轰哥炸鸡店门口排队的女孩儿只有一个了,刘轰抄起他的铁罐子,在砧板和砧板上的肉上撒了厚厚一层粉红色的粉末。女孩儿下身穿着工业学校的校裤,衣服是粘着好多亮片的嫩黄色,她咬开塑料袋里的纸袋里的肉排,荤油味从她的嘴唇间往外渗。
飞机阿姊见过很多炸鸡店,它们大多很安静,就像是刘轰停工的时候一样安静。飞机阿姊说:“你屋里的油锅天天就跟爆炸一样,下锅的时候把肉上的水擦擦干不行吗?”
刘轰关了锅,微沸的油脂平静下来,刘轰说:“声音响点儿能碍什么事儿呢?该来吃鸡排的还是照样来吃,不吃鸡排的还是不吃。”
飞机阿姊拿了店门口的小团扇开始给刘轰扇,扇子上印着新菜品鸡翅包饭,九块五一整只,尝鲜价八块钱。刘轰凑到飞机阿姊跟前,抽走她手里的扇子,插回扇子框里,“你也知道罗斌杰每个礼拜六早上会来了,过两天早点来候着他就好。上个礼拜六他要去看亲戚,所以才提前一天来的。不过我劝你是别操那么多心,连我都能看出来你准备干啥,你家孩子能看不出来吗?看破不说破,佛经里面有没有这句的?”
飞机阿姊第一次听刘轰说这么长一段话,也是第一次发现刘轰有点儿大舌头,说话的时候像是嘴里在嚼一个馒头。刘轰往他的躺椅上一摊,对飞机阿姊勾了两下手掌。刘轰的店里一共也就够四五个人站立的空位,还被他的躺椅占了一半位置,飞机阿姊说:“我不进来,我就是问问你,你要不要把陆老师的店也买下来,然后雇一个店员?能不能赚到钞票是一回事,重要的是积累善报,把你开炸鸡店的现世报给抵消掉。”
卡车停在马路边上,发出悠长的泄气声音,从易购中心的玻璃顶棚下边涌出的男人们打开卡车的箱门。刘轰也发出了短促的泄气声音,他说:“你还是在想办法让你孙子来信佛,找我没用,我不信佛。”
飞机阿姊看着卡车上的烧烤架被一个一个往外搬,一个一个堆在黄色红色和绿色的格子地砖上;飞机阿姊看着陆老师点他手里的一沓一百块钱,点了一遍,点了第二遍,然后他开始把一张张绿色的五十块钱从钱堆里往外挑;飞机阿姊看着刘轰眼皮沉落,发出呼噜声;飞机阿姊看着1208路公交车在十字路口停下,在永寿寺站下车的只有一个人,他在公交站台的顶棚底下站了二十秒,然后开始走向桥的方向,飞机阿姊大约只能看出他是个男人,穿着白色的衣服,黑色的裤子,还有一双黄色的鞋子。
飞机阿姊看着这双黄色鞋子离自己越来越远,她想:今天是星期三,还是星期四?汪嘉康期末考试考完了吗?美食节开张以后,1208路公交车会不会没有位置,会不会有很多人带着肉串进到庙里来?那时候,陆老师的香烛店是不是已经关门了?
这双黄色的鞋子就消失不见了。
六
“易购中心第一届世界美食嘉年华”的横幅挂在香烛店正对面的两座五层楼中央,彩旗绕着空旷黯淡的易购中心挂了三圈。飞机阿姊看见五个年轻面孔走下1208路公交车,他们看起来都没比汪嘉康大多少岁。陆老师拖着大纸箱子后退着走路,撞到飞机阿姊的脚跟上,他喊飞机阿姊的名字,没有回应,于是他抬起手在飞机阿姊眼睛前面晃:“明天就礼拜六了,你带他来美食节,顺便到庙里去,说不定还能看见罗斌杰呢。”
飞机阿姊没有回陆老师的话,陆老师把他的卷帘门往下拉,一直拉到底,然后上锁。陆老师说,再会。
飞机阿姊回到永寿寺门槛里边的矮凳上,天色开始变得昏暗。易购广场的霓虹灯闪烁起不太明亮的光,串联着每一顶太阳伞的彩色灯泡也开始跃动,顾阿姨说:“看看倒也蛮漂亮的。”
顾阿姨把刚折完的三捆元宝安置在正厅的角落里,然后把掰好的豇豆装进红塑料袋里,顾阿姨说:“阿姊今朝哪能不回去?”
飞机阿姊说:“你猜猜看,明天早上会有多少人坐在大殿的台阶上吃他们的鸡翅膀和鸡排呢?”
顾阿姨说:“我要回去了。阿姊明朝早上来看看就晓得。”
飞机阿姊说:“你还有锡箔吗?我再帮你折一捆。”
阳光迅速地沉没,飞机阿姊折到第二十七个元宝的时候,阴影从飞机阿姊的头顶侵蚀到她的双手、她的脚跟。门外的灯光越来越刺眼,稀疏的人声摇晃着飞机阿姊耳边的空气。飞机阿姊闻见大轰哥鸡排的味道——花椒的臭味。她原本以为美食节开始以后,刘轰的鸡排就卖不出去了。她看着队伍从大轰哥炸鸡店的门口一直延伸到永寿寺的门槛前面,然后越过永寿寺。站在飞机阿姊面前的短头发女孩子说:“叫你早點排队你不肯来。”和她搭伴的长头发女孩子说:“不就是一个鸡排吗?”
昨天夜里,飞机阿姊打电话给阿华:“康康期末考试考完了吗?”阿华回答她:“我们明天带你出去吃个晚饭吧。”
飞机阿姊觉得现在大概已经五点四十分了。阿华去年在德国给飞机阿姊买了一块浅蓝色的手表,飞机阿姊把它放在床头柜里的铁皮盒子里。飞机阿姊觉得往日里空无一人的易购广场前至少拥挤着两百个人,他们都是来吃晚饭的。吃炸鸡排没什么不对,炸鸡排的味道确实不坏;还有烤肉串,辣椒粉和炭烤的味道灌入飞机阿姊的鼻腔,那确实挺香的。握着大轰哥鸡排的男孩被单手捧着一个奶油蛋糕盒子的老头儿领进永寿寺的门里,飞机阿姊说:“平常这个时间庙已经关门了,下一趟你们早一点来。”
飞机阿姊把她刚折完的锡箔元宝撂在半开着的大门边上,从矮凳上猛地站起来。她站得有点儿快,眼前充满光晕的景色变成一片惨白,她扶着厚重的木门,另一只手扶着正准备迈步出门的老头儿。老头儿说:“夜饭还没有吃吧,我们刚才买的鸡蛋仔还没吃过,你不要低血糖了。”
飞机阿姊抬起头。天空被门檐遮蔽了一半,另一半是玫瑰红色,有一道航迹云,没有星辰。去年过年的时候,飞机阿姊问阿大和阿二:“天上永远都是一片蓝,晚上变成一片黑,现在是这个样子,一百年前也是这个样子。你们开飞机不会觉得没劲吗?”她现在知道了,如今的夜空不再是黑色的,而是玫瑰红色,它也许永远都不会变回黑色。
飞机阿姊说:“我不是低血糖,我就是坐太久了。我进去看看电有没有关好,你们把矮凳拿出去,在门外面坐吧。”
没有等待回应,飞机阿姊关上大门。寂静,昏暗,空洞,永寿寺理应如此。
漫射光铺洒在菩萨的脸上,露出一双眼睛和半张嘴,飞机阿姊掸了掸蒲团上的灰尘,把散乱在供桌上的凤梨酥摆成三层的金字塔形。顾阿姨折的几千个元宝都堆在角落的纸板箱里,明天就会有好多客人进到这间庙里了,这些元宝还是放在客堂的柜台后面安全一些。
飞机阿姊提起一箱元宝,它很轻,汪嘉康一顿就能吃掉这么重的猪大排。她拉开客堂间的折叠门,门的关节处被风吹出骨折的声音。客堂间的玻璃柜里摆着细的蜡烛、粗的蜡烛、线香、红色黄色和绿色的香、写着“学业有成”的祈福带,还有“身体健康”“万事如意”,飞机阿姊把纸板箱子摆在桌上,摆了一箱、两箱、三箱、四箱。第四箱遮住了贴在桌角的支付宝付款码,飞机阿姊把它挪到了第一个箱子的右边。
飞机阿姊把散落在正厅门边的二十七个元宝挨个儿叠起来,她的左手虎口张到最大,恰好足够用一只手把它们带去香炉里头。香炉上的灰尘阻遏了月光反射,只有打火机的浅红色塑料壳闪烁微光,飞机阿姊点燃了第一个元宝,用第一个元宝点燃第二个元宝,二十七个元宝恰好够绕整个香炉一圈,寂寞的奢侈。
大殿两侧坐着二八一十六个各式各样的佛教神仙,中央坐着的是如来佛祖,或者只是俗称如来佛祖。汪嘉康读过《一本书让你记住佛教史》,还读过《佛教神话图鉴》,只有他才能说出这十七个佛的真名。“帮奶奶认识一下这十七个佛”实在是一个非常合理的借口——比她曾经用过的三四十个借口都更有说服力。如果飞机阿姊早点儿想到,汪嘉康现在可能已经是个虔诚的信徒了。
但这就是现世报,飞机阿姊不该试图以一己之力对抗命运的。她第一次抬头直视如来佛祖,佛是金色的,竟然还有些漂亮,红唇闪亮,手指尖上焕发着黯淡的夜光。
飞机阿姊磕了三个头。
她听见自己的呼吸声,听见发梢与蒲团轻触的摩拭声,她听见脚步声,一个轻快又沉重的脚步声,她说:“桂师傅,是我,我马上就准备回去了。”
嘈杂涌入,灯光涌入,猪油香气涌入。大门打开了,飞机阿姊听见了一个熟悉的声音,他通常冷漠,但很少愠怒,他的声音已经是个男人了,但他依然是个孩子:
“你总算看见我进到庙里来了。这下子你满意了吧?”
七
飞机阿姊坐在阿华二成新的越野车的后排,汪嘉康坐在副驾驶位置上。汪嘉康显然已经根据飞机阿姊的行动推断出了她阴险而周到的计划,一个连飞机阿姊自己都还没理清的计划。阿华说:“汪嘉康期末考试礼拜二就考完了,我跟他说要不要礼拜六带上你一起去美食节,他说你肯定不喜欢的,他现在比我还要了解你。”
灯火闪耀,寂静的空气,刹车,汪嘉康瞥了一眼后视镜。阿华说:“这么一点点小事,你跟奶奶有什么好生气的。”
越野车开进仲凯二村的小门,小门的宽度恰好足够越野车穿过。阿华在羊肠小道里穿梭、转弯、倒车,然后熄火。阿华说:“姆妈,你以后是不是不要一个人去看爸爸了,也不要一个人去庙里了?”
飞机阿姊说:“好呀。”
飞机阿姊打开车门,汪嘉康已经站在路沿上等着扶她了。她看见汪嘉康穿着一双浅色的运动鞋,还看见他纤长的手指。汪嘉康说:“我爸说话从来都不过脑子的,奶奶怎么能不去庙里,怎么能不去医院看爷爷呢?”
假使飞机阿姊从明天开始不再去永寿寺,顾阿姨是会想念她的,但这些天进到庙里来的人有那么多,他们都穿着不一样的鞋子,有穿跑鞋的也有穿皮鞋的,黑色白色和黄色的。还有,要是进到庙里来的十个人里有一个会化锡箔,一次化五十个,顾阿姨叠锡箔的速度就跟不上了,她得加班加点,还得专心。然后是桂师傅,他不能再整天玩儿他的算盘了。客人是买小蜡烛还是大蜡烛、买一支香还是每捆十支的三捆香,都全凭他的一张嘴,他不能再说他南边乡下拗口难听的土话了,仲凯北路街道的老人们都喜欢飞机阿姊的镇上口音。
等到美食节结束,他们也就该忘记飞机阿姊这个名字了。假使他们没有忘记,他们就会回到家告诉自己的孩子:庙里曾经来过一个叫飞机阿姊的老太婆。她要别人叫她飞机阿姊是因为她的两个儿子都是开飞机的,她的二儿子是个什么尉还是什么校,等同于营长还是团长。她就知道炫耀,但是有谁会羡慕她呢?两个月前她突然消失了,年纪这么大了,恐怕是身体不好吧。
还有老头子住的医院。护工桂花,隔壁七号床家的王阿狗和八号床上的罗老头,飞机阿姊和他们认得一年多了,他们知道飞机阿姊有个孝顺的孙子,但汪嘉康说得对:这世界上有几百万个孝顺的孙子,没人会在乎谁是其中的一个。
汪嘉康牵起飞机阿姊的右手,“罗斌杰的确是个值得羡慕的人”,汪嘉康说。
飞机阿姊和飞机爷叔结婚没多久的时候,飞机阿姊手上还戴着她奶奶给她的一根红绳子,这根红绳子是在她出生的那天从永寿寺里求来的。飞机阿姊结婚的时候,永寿寺已经变成了一间空房子,最大的佛头已经成了飞机爷叔屁股底下的凳子。
那天晚上,飞机爷叔提了半斤肉排骨回家,飞机爷叔说:“阿大快要生出来了,你把手上的绳子丢掉吧。”
阿大的出生和飞机阿姊手上的红绳能有什么关系呢?飞机爷叔那时候还是个漂亮的男子,飞机阿姊望着他脸上的泪痣,把排骨倒进钢盅盆子里,然后摘下手上的红绳,她说:“你帮我拿去丢。”
这根红绳没有被飞机爷叔藏起来,也没有被某个秘而不宣的信徒从垃圾箱里翻出来当作宝物。就像是被飛机阿姊丢进垃圾场的矮凳一样,它从此消失,就好像从来就没有存在过一样。
但汪嘉康和飞机阿姊不一样,他从来都不是一个受迫的人。
阿华回家了,汪嘉康躺在沙发上。汪嘉康说:“你知道释迦牟尼在成佛以前和天魔大战的故事吗?”
门铃响了,汪嘉康说他喊了外卖,一个是茄汁蛋包饭,一个是咖喱蛋包饭,他问奶奶要吃哪一个。
飞机阿姊拿出柜子里的筷子,汪嘉康把餐盒摆在桌面上。飞机阿姊吃了茄汁的,纯粹的番茄酱味道。汪嘉康说:“蛋皮只有这么薄一层也配叫蛋包饭吗?”
飞机阿姊咀嚼着一嘴的番茄酱味米饭,饭里还有些轻微的隔夜味,飞机阿姊把筷子架在塑料饭盒上:“康康啊,我刚刚呆在庙里,不是想着要把你骗到庙里去的。”
汪嘉康没有回应飞机阿姊的话,他开始讲他的故事:天魔的战象宽二十里,手中神兵能让整片大地颗粒无收整十二年,他的大军遮天蔽日,连地底下也布满了他手下的魔鬼。利箭、烈火、狂风、黑暗,佛陀却只是坐在菩提树下,一切灭世之灾全部化作飞花与尘埃。
汪嘉康说:“这要是放在语文考试里的话,就是一道送分题。‘最大的敌人就是自己,说得好容易。”
飞机阿姊说:“这就是现世报啊。”
汪嘉康说:“这应该叫作福报。”
飞机阿姊起身开灯,汪嘉康跑进厨房拿了两个勺子。“这不就是味多美油咖喱的味道吗?”汪嘉康拍桌大喊。
飞机阿姊看着日光灯管闪烁闪烁闪烁,像是美食节摊位上的彩灯闪烁闪烁闪烁,像是大轰哥炸鸡店顶上坏掉的霓虹灯闪烁闪烁闪烁。
飞机阿姊说:“我打算以后就不去永寿寺了,反正美食节开张的这段时间肯定不去。不过我还有一桩事情,你不要不高兴。”
四目相对。汪嘉康说:“我去一趟就去一趟吧,只要你不跟别人说‘汪嘉康跟我去庙里了这种坍台的话。”
飞机阿姊摇头,硬是带汪嘉康进到庙里又能有什么用呢?飞机爷叔小时候在永寿寺里坐的时间也不比飞机阿姊短。
然后飞机阿姊干咳了一声:“我就想看看罗斌杰是个什么人。”
八
飞机阿姊已经不记得她第一次听说“罗斌杰”这个名字是在什么时候了。大约是大轰哥炸鸡店刚开张的一两个月里,工业学校的学生还大都不知道这家店的存在,刘轰还有点儿和人聊天的空闲的那段时间。
飞机阿姊是不太愿意和刘轰聊天的。易购中心里早就开过那么几家炸鸡烧烤店,飞机阿姊亲眼看着它们一个个变得门可罗雀,然后消失不见。刘轰在庙门口卖炸鸡并不值得责备,生意人有生意人自己的规则,但现世报该来还是会来,飞机阿姊并不乐于结识一个转瞬即逝的人。
但刘轰的生意超出了飞机阿姊的预料,进货的小车从一周来一次变成五天来一次,又变成一周来两次。等到飞机阿姊想和他好好讲两句话的时候,大轰哥炸鸡店前的队伍已经没个休止了。飞机阿姊推测刘轰暗地里一定是个虔诚的人,说不定每次他上班之前都要偷偷去拜佛,也可能是晚上打烊以后。飞机阿姊从来都看不见他拜佛的样子,就像她也没见过罗斌杰拜佛的样子一样。
飞机爷叔住院以来的两年间,飞机阿姊每天十点钟出发去飞机爷叔的卫生服务中心,看着护工喂他吃完午饭,然后给他洗屁股。这时候大约是十二点钟,罗老头家的老太婆差不多刚好提着饭盒进到病房里来,她道个好就走去永寿寺,走到永寿寺的时候就快下午一点了。罗斌杰每周六到永寿寺来的时间都在上午九点到十点之间,在庙里大概也就逗留半个小时,买香酥鸡再花个十几分钟。他最晚一次离开是在十一点三十分,那天他是看着表匆匆跑走的,连香酥鸡都没有来得及买。
飞机阿姊当然想知道罗斌杰是个什么样的人,她先是从桂师傅那儿知道了他是复旦大学佛学院的博士生,然后从顾阿姨那儿得知他喜欢穿黄色跑鞋。当年桂师傅还是桂光头的时候,桂光头总是喊他的数学老师“将军的女儿”,她的父亲大约的确是个军队里的干部,但军衔一定比阿二要低上一些。如此推测,罗斌杰也许不是复旦大学佛学院的博士生,他可能只是个复旦大学的学生,可能只是个佛学院的学生,也可能只是个博士生——但再怎么说他也得是个学生。再过一年多,汪嘉康就会是某个大学、某个学院的本科生了,这也就与罗斌杰有了一点儿共通之处。
有了一个共通之处,就能有两个共通之处。罗斌杰信佛,汪嘉康也就可以信佛。飞机阿姊下定决心要与罗斌杰会面是在一个星期五的傍晚,她一边给汪嘉康盛萝卜汤一边说:“我明天出门的时间打算稍微早一点。”飞机阿姊相信罗斌杰是有用的——按汪嘉康的话说,这不能叫作“有用”,而该叫作“有善缘”。
第二天,也就是星期六,为了迎接这段善缘,她提前离开了卫生服务中心,放弃了在罗老头家的老太婆面前给飞机爷叔擦屁股的机会。但她来得还是太晚了些,她没能见到罗斌杰。
第二个星期六,为了防止再次错过,飞机阿姊决定下半日再去卫生服务中心。她从早上八点半开始就在永寿寺门口候着,一直候到十二点钟。她还是没见到罗斌杰。
第三个星期六,劳动节,周五就放了假的汪嘉康会到奶奶家里住一晚上,正是翌日早晨偶遇罗斌杰的最好机会。计划未能成功实施,顾阿姨说罗斌杰周五就已经去过了永寿寺,周六当然就没有去。
第四个星期六,阿华带飞机阿姊去鲜花节看花。罗斌杰准时到了永寿寺。
第五个星期六,飞机爷叔的屁股上长了息肉,飞机阿姊陪着他吊盐水。罗斌杰准时到了永寿寺。
第六个星期六,飞机阿姊早上九点钟到达永寿寺。罗斌杰没有出现,没人知道罗斌杰去哪儿了。
第七个星期六,罗斌杰没有出现。星期天的下午,顾阿姨告诉飞机阿姊:那个黄色跑鞋的早上来过了。
飞机阿姊有时候会觉得罗斌杰是故意在躲着她,但罗斌杰不光是没道理知道飞机阿姊的行踪,他甚至都不该知道有一个叫作飞机阿姊的人。
飞机阿姊没法解释她为什么就是没法见到罗斌杰,这或许确实只能说是现世报应:飞机阿姊的功德不及罗斌杰,而罗斌杰也不愿意认识一个扰人的老太婆,不愿意为她扮演一个传教士。汪嘉康在拒绝飞机阿姊的时候总爱说:“信仰是一个人的事。”他与罗斌杰或许确实有些相似。
三个礼拜以前的一个晚上,飞机阿姊把仲凯二村四十六号四○二的电话号码交给刘轰,喊刘轰把号码交给罗斌杰——能把罗斌杰的电话号码也给要来就更好了。刘轰说:“罗斌杰不会把电话号码给你的,他不喜欢别人知道他来庙里。”
飞机阿姊喜欢别人知道她来庙里,她希望所有人都记得她天天都来庙里。拜佛是件好事,是件值得骄傲的事。飞机阿姊说:“那为什么你们都知道他来庙里了呢?你们连他的名字都知道了,连他在什么学校读书都知道了。”
刘轰不太爱笑,即使是笑的时候,也是喉咙先响动起来,再勉强把嘴唇带动。他的嘴里喷薄出两声鹅叫,在第二声刚停下来的时候就刹住了:“我不知道,我不知道的。复旦大学根本就没有佛学院,只有哲学学院。”
刘轰深吸一口气,对飞机阿姊扇了两下手掌,一个表示“快走”的手势:“客人来了——哎,你要吃啥?”
九
早上八点半,飞机阿姊坐在永寿寺门口的矮凳上。矮凳还是那个矮凳,美食节还没到开幕的时间。顾阿姨说:“你认得罗老头吗?他跟你家老头住在一个医院里的。他的儿子跟我的儿子是小学同学、初中同学,现在也就四十几岁。小小年纪就生癌死了,作孽啊。”
飞机阿姊没跟罗老头说过一句话,飞机阿姊认识罗老头的时候,罗老头就是不会说话的。飞机阿姊想起罗老头家的老太婆说起过她的孙子,说他喜欢吃鸡腿菇,还喜欢韭菜炒蛋。飞机阿姊问顾阿姨:“你知不知道罗老头的孙子叫什么名字,是不是叫罗斌杰?”
顾阿姨当然不知道,她只知道折錫箔,剥毛豆,只知道罗斌杰穿的是黄色的跑鞋,庙外面锤子电锯的响声也没法让她从椅子上站起来。飞机阿姊顺着声音走到香烛店的门口,它现在已经不是香烛店了,留胡茬的工人把十尺宽的招牌从房檐上拆下来。飞机阿姊说:“这爿店怎么这么快就拆掉了?”
回应飞机阿姊的是一个穿着工业学校校服,手里提了两大马甲袋炸鸡排的高个儿男孩,他说:“陆老师——就是香烛店的前一任老板,下个学期开始要回我们学校上课了,说是香烛店生意不好。”
“他当了副校长以后反而要上课了?”
校服男孩显然没听懂飞机阿姊在说什么,他迟疑了三五秒,然后点头答应:“对,副校长当然也要上课的,不过上得不多。陆老师上得就比较多,要带一个年级的体育课。”
飞机阿姊看着男孩的背影,他的身形有些窄,但是走路的姿势和汪嘉康一模一样。飞机阿姊冲着他的背影喊:“你认得罗斌杰吗?”
男孩没有回头,他假装专注的样子也和汪嘉康一模一样。汪嘉康专心的时候很多,看书、写作业、走路、打游戏都能让他听不见每一句飞机阿姊问他的话。其实汪嘉康的耳朵很灵,他什么都知道。
飞机阿姊二十五岁的时候,每天早上出家门,穿过马路,然后右转,经过永寿寺的大门,一路直走,就能走到仲凯路幼儿园。她也不是非得求神拜佛,磕头烧香的,她走过永寿寺的时候,也就只想过要看一眼殿里的佛、莲花台上的菩萨——或者只是供桌、梁柱、青石地板。她有时候真的会进去看上一眼,和坐在正殿里踩缝纫机的小王和小张打个招呼,说:“我是特地来看你们的。”
飞机阿姊也不是非得说自己是去看小王和小张的,她有资格看看这座陪她长大的庙。到了庙里的佛被重新立起来的时候,她就不只是有資格了,拜佛很快就成了一件值得骄傲的事。
但飞机阿姊没有做这件值得骄傲的事。
直到阿大走了,阿二走了,飞机阿姊搬进仲凯二村,然后阿华搬进凯辉天锦园,永寿寺对面的老宅被改造成易购中心,飞机爷叔身体败坏到连一句完整的话都说不出,飞机阿姊也没去做这件值得骄傲的事。
飞机爷叔被送进永寿寺边上的卫生服务中心的那一天,飞机阿姊在病房里听说两个整天坐在庙里无所事事的人,一个叫顾桂花,一个叫桂光头。飞机爷叔得了肺病的那段时间里,飞机阿姊已经在自家阳台上立了菩萨像,还学会说“南无阿弥陀佛”,学会传达“现世报”的内涵。这一天,飞机爷叔终于变成了一个傻人。
这是一场多漫长的旅程啊。飞机阿姊的信仰行走了五十年才到达起点,但汪嘉康不需要了。汪嘉康第一次读《释迦牟尼成佛记》是在七年以前,他早就站在起跑线上,只等着开始奔跑的一刻。
美食节上的摊位一个个活跃起来,羊肉串在烤架上开始翻滚。大轰哥炸鸡店门前的队伍又开始拉长,在飞机阿姊眼前盘旋。罗老头家的老太婆领着浑身照烧汁香味的女孩儿走进庙里,飞机阿姊说:“八号床阿姨,你今天来庙里呀?”
“带我外孙女来美食节,等一下就一起去医院了。你知道的呀,我们老头子迷信得要死,他就是不喜欢闻肉的味道,只喜欢闻香的味道。上次我和我的孙子从庙里过去的时候,他一闻到我们身上的味道哦,就眯着眼睛咯咯笑!”
飞机阿姊陪笑了两声,“那你的孙子今天没来?”
“忙得要命!他说他学校里有论文要写,今天回不来了。”
罗老头家的老太婆和外孙女走进庙里,然后是一对挽着手的夫妻、戴着耳机和兜帽的高个儿、吃鸡排的三个女孩儿、光头和麻子、大波浪和胖子、奔跑但没有尖叫的背心男孩、追不上他的高跟鞋妈妈。人影从飞机阿姊的头顶上扫过,一个一个扫过。美食节会场里并没有太多的人,这些不太多的人里也没有几个在喧嚣,但美食节确实是喧嚣的。飞机阿姊说:“看起来我是可以准备回去了。”
汪嘉康有句话说得很有道理:“这世界上有几百几千万个孝顺的孩子,没人会在乎你是不是其中的一个。”为了病榻上的爷爷而去沾染香火的气味是个有创造力的善行,但善行是可揣测的,是不可复制的。等到飞机阿姊卧病不起的那一天,汪嘉康一定会在网上买一个香炉,而不是试图让一些飘忽不定的气味分子附着到自己的衣服和皮肤上。
汪嘉康最不喜欢的就是形式。事实上,也没有人知道现世报的衡量标准究竟是仪式还是信仰本身。
顾阿姨说:“再会。”
这声音跨过十四个人的身体缝隙,钻进飞机阿姊的耳郭里。
十
飞机阿姊低着头走在路上,周遭全是吵闹,她隐约听见有人喊自己的名字,“飞机阿姊”。先是一个陌生的男人,再是一个陌生的女人,然后又是一个陌生的男人。飞机阿姊回头,她听清楚了,他们说的是“大轰哥喊你”。
飞机阿姊小跑到大轰哥炸鸡店的柜台前面,大轰哥喊:“你怎么就走了呢?”
飞机阿姊知道,光是沿直线传播的,所以她看不见大轰哥,大轰哥也理应看不见她。可大轰哥不光看见她,还知道她要走。飞机阿姊说:“你怎么知道我要走呢?”
大轰哥没有回答她的问题,他把香酥鸡交到客人的手里,“等下准备去庙里逛逛?”他显然是故意装作不经意地说。然后他冲着飞机阿姊喊:“你在这儿等到十二点!”
飞机阿姊没道理继续等下去,罗老头的孙子今天不会来了。尽管没人说过罗斌杰就是罗老头的孙子,但飞机阿姊也不想问,她已经得到了一个答案。飞机阿姊也就是想要一个答案。
“罗斌杰今天不来了。你要是见到他,可以给我打个电话。”
“不来个屁!我跟你说等着你就等着,没错的!”
大轰哥把炸香菇和炸鸡锁骨装进一个塑料袋,“二十八号好了——哎,永寿寺是百年老庙,进去转一圈,出来就饿了,饿了就再买一份大鸡排。”
飞机阿姊理解了大轰哥的现世福报。
飞机阿姊等在1208路公交车的站台座位上,看着一车一车的人下车,走进美食节的场地。她看见老金、老汪和他的孙子、阿许、仲凯二村的夜班保安老谭和他的老婆、徐老师。她一个一个和他们打招呼,十一点,十一点半,十一点四十分,又一个一个和他们告别。
飞机爷叔当调度的时候,站台上连个时刻表都没有。现在的公交站台不光有时刻表,还能显示下一班车的到达时间,就连下一班车再过几分几秒能到站都算得准。现在的世界确实不同于往昔,飞机阿姊觉得自己似乎也不像以前那样虔诚了。易购广场濒临倒闭的时候她拍手称快,但她现在竟然也开始觉得大轰哥是个有功德的人。
1208,又来了一辆。飞机阿姊回头,透过浅绿的玻璃窗和两个肩膀,她一眼就看见了汪嘉康。飞机阿姊迎到汪嘉康的面前,“你怎么自己一个人坐公交车过来呢?”
“我回家换了个鞋子。”
飞机阿姊看见汪嘉康脚上的黄色跑鞋。汪嘉康说:“我爸去年去德国的时候给我买回来的,我现在鞋子太多了,穿不过来。”
汪嘉康没有给飞机阿姊留一个说话的当口,他轻牵着飞机阿姊的袖子,往永寿寺的方向迈开步子,“我一直觉得,那些求着被菩萨听见,被佛陀看见的功德都算不上是功德。菩萨不会喜欢那些总把自己的名字念给她听的人,他们只会因为贪欲而遭受惩罚。奶奶,你觉得你真的想把你的功德浪费在认识一个莫名其妙的罗斌杰身上吗?”
十二点还没有到,飞机阿姊还没打算离开公交站,但汪嘉康牵着她就走,穿过人潮。汪嘉康真的一点儿也不像飞机爷叔,就连他迈步的勇武姿势也极像年轻时候的飞机阿姊。
“不过,今天来庙里的人这么多,就算我把我的名字念给菩萨听,她也会觉得我是个凑热闹的。我们进去吧,汪嘉康第一次拜佛,还蛮值得纪念的”
飞机阿姊看着汪嘉康跨過门槛,直奔客堂,问桂师傅要了三捆香。飞机阿姊站在门厅里望着汪嘉康,望他脚上黄色的跑鞋,他拜佛的时候确实是有点儿像样。
汪嘉康用蜡烛点燃了三捆香。它们均匀地燃烧着,均匀地化为灰烬。汪嘉康敬拜四方八位,把点燃的香插进香炉的东南角。
飞机阿姊想要用“现世报”形容她所目睹的场景,尽管“现世报”是个发怒的时候才能用的词。她知道,“报应不光指恶报,也可以指福报”,这是汪嘉康十一岁的时候就教会飞机阿姊的知识。汪嘉康说过,遇上好事的时候可以直接喊“福报”,但飞机阿姊实在是一点儿也不想说出“福报”两个字,她就是想管这叫作“现世报”。
于是飞机阿姊仰起头,迈步——
她的耳畔响起佛音,天地翻覆,她的头颅击中一个柔软的东西,脚底踩上一个坚硬的东西。
飞机阿姊闭上眼,她发现自己还是能好好地呼吸,还是能好好地说话,她张开嘴唇,吸气——
“哎哎哎,我看你一张嘴就知道你要讲什么了,你不要讲出来——”
她听见汪嘉康的声音就在她的耳畔:
“——你以为绊倒在门槛上这种小事情,就够当你的现世报了?”
责编:周朝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