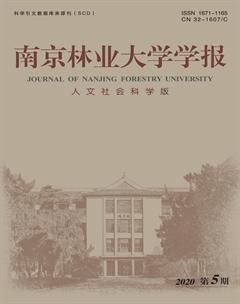论米兰·昆德拉的生态伦理思想
赵谦
摘要:米兰·昆德拉作为当代文坛具有相当影响力的作家,其作品中蕴含着丰富的生态意蕴。总体而言,昆德拉的生态思想可以分为自然生态和精神生态两个维度。作为城市生态批评的倡导者之一,昆德拉十分反感单调的现代化建筑群,认为它们破坏了自然的原始之美。他指出,现代化建设绝不能以破坏自然环境为代价,只有与自然和谐共生才是人类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正确途径。正是出于对城市环境污染的憎恶,昆德拉向往自然,追寻一种田园牧歌式的乡村生活。在昆德拉眼中,动物代表着善,是自然界中所有美德的总和。人与人的交往常常带有目的性与伪装性,只有人与动物的关系才能测试出人类真正的道德。因此,人类应该关爱动物,敬畏它们的生命。借助小说中的动物叙事,昆德拉表达了保护动物、善待动物的生态伦理观,同时对“人类中心主义”思想进行了批判与斥责,彰显出了强烈的生态意识。除了对自然生态的关注外,昆德拉也十分关注生活中普遍存在着的社会精神生态问题,主要包括家庭关系的异化、因不确定性因子产生的焦虑情绪等。此外,他的作品中也涉及其他的一些社会精神生态问题,如畸形的生命伦理观、悲观厌世的消极态度、窥探他人隐私等。通过对这些社会精神生态失衡现象的揭示,他将生态伦理观完美地融入到小说文本中,极大地增强了作品的现实启示功能。以全景视阈对米兰·昆德拉小说中的生态伦理思想进行深入研究,既有助于理解小说中的哲学内涵,也能为解决日益严峻的生态问题提供启示。
关键词:米兰·昆德拉;生态伦理观;自然生态;向往田园生活;关爱动物;社会精神生态;家庭关系异化
随着现代化建设进程的加快,一系列严峻的生态问题相继出现,严重影响了整个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生态批评逐渐发展成为文艺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视阈。追根溯源,西方生态批评理论发端于20世纪70年代。早在1974年,美国学者密克尔(Joseph Meeker)在《生存的喜剧:文学的生态学研究》一书中便使用了“文学的生态学”(literary ecology)这一术语,他指出生态批评的目的是“发掘文学对人类行为和自然环境的影响”。同年,卡尔·克洛伯尔(Karl Kroeber)将“生态学”(ecology)这一概念引入到文学批评中。1978年,威廉·鲁克特(William Rueckert)在《文学与生态:一项生态批评的实验》中提出“生态批评”(eco-criticism)的概念,并主张将文学与生态学结合起来进行研究。此后的十余年间,生态批评理论发展缓慢,并未在文艺理论界产生重大影响。到了1990年,美国学者格伦(Glen A.Love)在《美国西部文学》上发表了《重估自然:迈向生态批评》一文,再次将学界的目光聚焦到生态批评上。格伦指出,破坏生态将给人类“在可预见的时间内产生自杀式结果”。1992年,文学与环境研究会在内华达大学成立。之后,生态批评迎来了快速发展的时代。1993年,在国际生态批评界具有引领作用的《文学与环境跨学科研究》创刊,该刊高度关注世界生态批评研究领域中的新成果,及时刊发有见地的学术论文。1994年,内华达大学的斯科特·斯洛维克(Scott Slovic)对“生态批评”进行了重新界定,他倡导将多种学术方法引入到自然书写的研究中。随后,彻丽尔·格罗特费尔蒂(Glotfehy Cheryll)和哈罗德·弗罗姆(Hardold Fromm)合作编著的《生态批评读本》问世,该作将“探讨文学与自然环境之关系”视作生态批评研究的目的。到了20世纪90年代末,西方的生态批评与伦理学、环境科学等学科融合在一起,出现了诸如环境文学、绿色文学等新的研究视阈,呈现出跨学科、多角度、全面性的特点。1997年,里德(T.V.Reed)将环境公正思想融入生态批评中,正式提出了“环境公正生态批评”这一概念。此外,随着环境污染、核威胁、辐射等毒性物质危害的加剧,不少生态学者开始关注当代毒性话语,这也扩展了生态批评研究的维度。进入21世纪后,在劳伦斯·布伊尔(Lawrence Buell)、格里塔·加德(Greta Gaard)等众多学者的推动下,国外的生态批评研究持续发展,理论体系的建构也日趋完善。
在此大背景下,自20世纪初开始,越来越多的国内学者也开始关注生态批评研究。2002年,王诺在《文艺研究》第3期上发表了《生态批评:发展与渊源》,介绍了“西方生态批评的发展及其主要成果,追溯和探讨了生态批评的思想根源,并指出生态批评的未来发展应当解决的几个关键问题”,由此拉开了国内生态批评研究的帷幕。梳理前期成果发现,国内的研究主要包括对生态批评理论发展历史的梳理、以生态批评为视阈进行文本分析、对生态批评领域新理论的述评、国内外著名生态学者的访谈录和生态批评学术研讨会的纪要等。此外,部分研究者还从伦理学、环境科学对生态文学进行跨学科研究,他们从不同的学科视阈对生态批评的起源、演变和趋势进行剖析,为推动国内生态批评研究的发展问题作出了贡献。经过多年的持续研究,王诺、曾繁仁、鲁枢元、胡志红、韦清琦等一批学者脱颖而出,成为研究中的领军人物。在学者们的大力推动下,国内的生态批评研究日趋成熟,已经成了文艺研究领域中的一种主流视阈。
捷克裔法籍作家米兰·昆德拉是当代世界文坛具有相当影响力的作家,他创作的10余部作品陆续被翻译成中文出版,在中国读者中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在学界,昆德拉也拥有众多的研究者。根据中国知网的检索,截至2020年7月7日,以“昆德拉”为主题发表的文献总量达到2048篇,研究视阈涵盖哲學、叙事学、音乐学、伦理学等多个学科领域。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杨乐云便率先将米兰·昆德拉的作品推荐给国内读者。随后,李欧梵也向读书界大力引荐昆德拉创作的小说。20世纪90年代末,在李凤亮等一批学者的引领下,学界掀起了一场昆德拉研究的热潮。这一时期,研究者们主要从昆氏作品的译介、小说中的哲学意蕴、复调叙事艺术等视角,对其一些经典作品进行分析解读。近年来,国内的研究呈现下降的趋势,但依然不断有中青年学者加入到研究的队伍中,他们以符号隐喻、矛盾主题、创伤叙事、身份焦虑等视角为切入点,对昆氏的小说进行了全面的研究。笔者梳理了昆德拉的全部中译文作品,发现其中蕴含着丰富的自然生态意蕴和社会精神生态思想。遗憾的是,该视阈目前尚未引起研究者的关注。知网检索结果显示,迄今为止,以生态批评为视角对昆德拉小说进行研究的论文成果仅有5篇,皆为笔者撰写发表。这些成果主要是从精神生态理论出发,对昆氏部分小说中的精神生态失衡现象进行分析。然而,上述论文未涉及昆德拉的自然生态思想,研究对象也不够宏观,因而不能全面地管窥昆氏生态思想的内涵。本文以昆氏全部中译文小说为研究对象,归纳总结出其中的生态伦理思想,期待可以为后续的研究者提供启示。
一、向往自然:追寻田园牧歌式的生活
近年来,随着理论视阈的不断扩展,“生态批评内部衍生出多个新的研究领域,关注城市自然环境的城市生态批评即是其中之一”。梳理小说情节发现,昆德拉也是一位城市生态批评的倡导者,他十分反感单调的现代化建筑群,认为它们破坏了自然的原始之美。在他的处女作《玩笑》中,路德维克发现故乡多了许多陌生的现代化建筑,“楼房一幢又一幢地矗立着,毫无章法,不曾夯平的地面上满是尘土(没有绿草坪,没有人行道,没有路)”。这一景观,让他的心情变得异常不悦。无独有偶,《无知》中的约瑟夫回国拜祭亡母,却发现记忆中的墓地已经被高楼覆盖。因此,他迷失在令人反感的建筑群中,心中产生了一种陌生感。昆德拉评价道:“那把改变、破坏和毁灭种种景象的无形的巨大扫帚,几千年来一直在扫荡,但过去的动作缓慢,几乎难以觉察,而如今却变得如此迅猛。”与此同时,现代化社会中的各种噪声,也让昆氏难以忍受。《不朽》中,无处不在的噪声给阿涅丝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困扰。一次,她走在街道上,“右耳听着从商店、理发店和饭店传出来的喧嚣的音乐和节奏分明的打击乐器声,左耳则听着街上的喧嚣声、各种汽车单调的轰隆声、一辆公共汽车启动时的嗡嗡声。紧接着,一辆穿过马路的摩托车发出了刺耳怪叫”。最终,忍无可忍的阿涅丝只能用手捂住耳朵,继续前行。《无知》中的伊莱娜也曾有过被噪声骚扰的类似经历。一次,她和丈夫路过一个废弃的建筑工地,一个高音喇叭里突然爆出了喧嚷的音乐。这一突如其来的噪声,让伊莱娜十分难受,她捂住耳朵,哭了起来。正是出于对现代化建筑和噪声污染的憎恶,昆氏追寻一种田园牧歌式的乡村生活。在《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中,因为厌倦了都市的生活,托马斯和特蕾莎决定远离喧嚣,搬到乡下去过一种清静的生活。因此,他们从一位农民那里买下了一栋带花园的小房子,“窗户朝向一个山坡,坡上长满树干弯曲的苹果树。山坡的上方,果树林环抱着天际,只见山丘蜿蜒伸向远方”。农村的生活,让他们可以拥抱自然,与动物嬉戏,内心也变得平静。《生活在别处》中,因为母亲患上了抑郁症,雅罗米尔陪她去乡下的一幢别墅静养。住所坐落在一个人迹罕至的区域,自然景致十分优美。“房间里还有两扇窗,一扇是落地的,外面有个大阳台,在那里可以望见花园和小河的尽头。”在这样的环境中,雅母感到无比的轻松自在,心理疾病也慢慢疗愈。小说《无知》中,回归后的伊莱娜始终无法找回记忆中故乡的样子。然而有一次,她去郊外散步,来到一处宁静的街区,道路两侧全是树。这一景象,让她找回了记忆中的故乡,这才是她深深眷恋着的故乡。回国后的约瑟夫也深深地感受到故乡的陌生,但当他行走在田间时,蔷薇、小路、花草、树木等让他回忆起童年田园牧歌式的生活,于是让他产生了一种莫名的激动。随着人类现代化建设进程的加快,过去曲径通幽的乡间小路,逐渐被笔直宽阔的大马路所替代,参差散落的屋舍变成高耸林立的楼房,鸡犬相闻的幽境也幻化成汽笛飞鸣的喧嚣。通过小说这一文学媒介,昆氏表达了对田园牧歌生活的向往,在他看来,现代化建设绝对不能以破坏自然环境为代价,只有与自然和谐共生才是人类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正确途径。
二、爱护动物:反对“人类中心主义”
自古以来,动物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诸多的乐趣。昆德拉十分喜爱动物,将它们视为人类的忠实伴侣。对于这一论断,我们可以从他的小说中找到证明。《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中,小狗卡列宁每天上午闹铃响后便会兴奋地唤醒特蕾莎和托马斯,给他们带来一天的好心情。移居到乡村生活后,特蕾莎的工作是照料合作社饲养的40头母牛,它们性情温和,表现得快乐而幼稚,就像那些假装是14岁少女的50开外的胖女人一般。有这群温顺可爱的动物为伴,特蕾莎总能保持快乐的心情,抑郁症也渐渐好转,《告别圆舞曲》中,狗对人类表达出了亲近、友善和忠诚。然而,人类却因为它们的一些小缺点而要捕杀它们。一次,雅库布从一群用铁丝套环抓捕狗的老人手中救下了一只名叫鲍博的斗拳狗。狗很讨他喜欢,“短短几分钟里,它就无忧无虑地习惯了一个陌生的房间,跟一个陌生的人结下友谊”。随后,雅库布将狗送回了小旅店。当女主人叫唤它的名字时,狗马上开心地向她跑去。《生活在别处》中,狗是雅罗米尔孤独世界中忠实的陪伴者,对雅罗米尔而言,狗代表着动物世界里的善,是自然所有美德的总和。因此,狗面人身成了他绘画创作的主题之一。由此可见,昆德拉对动物持有一种友善的态度,对它们的描述也充满了溢美之词。
在昆德拉的小说中,动物“是一种具有特殊意义的象征性隐喻的存在”。梳理小说情节发现,对动物之死的叙述是昆氏小说创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昆氏一针见血地指出,人类为了使其对动物的支配权合乎神圣法则,于是杜撰了一些荒谬的故事和理论。如《创世记》中提到,上帝造人是为了让人类统治动物。笛卡儿也将人类视作大自然的主人和所有者,他否认动物有灵魂,认为它们只是有生命的机器。在这些思想的影响下,人类肆意地杀害动物,甚至以剥夺动物的生命为乐。《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中,托马斯同事家的一条圣伯纳纯种母狗产下四只小狗。为了排解特蕾莎的寂寞,托马斯在狗仔中挑选了一只回家饲养,取名为卡列宁。而没有被选中的狗,就是死的命。人决定着狗的性命,掌握着对动物的生杀大权。一次,特蕾莎带着卡列宁买完东西往回走,在小狗的引导下,特蕾莎发现了一只被两个孩子活埋的小乌鸦。她用指甲挖开了乌鸦周围的土块,将它带回家救治。乌鸦伤痕累累,爪子被折断了,全身不停地抽搐,最终,因伤势太重,乌鸦还是不可避免地死了。《告別圆舞曲》中,孩子们在一只猫的眼睛上钉着两枚钉子,割下它的舌头,绑住它的腿脚。更令人气愤的是,孩子们凶残行为的目的,仅仅是做游戏。《不朽》中,昆德拉讲述了名画家萨尔瓦多·达利晚年的一件轶事。他和妻子加拉驯养了一只宠物兔并将其视为生活伴侣。一次,因为要出远门,夫妻二人对如何安顿兔子绞尽脑汁。最终,妻子竟然将兔子杀死做成佳肴美餐了一顿,还美其名曰这是对它更彻底的爱。《无知》中,米拉达经过一家肉店,透过玻璃橱窗,她看到一具挂着的猪骨架,还有被扒光皮的家禽,脚爪全被截去了。此外,昆氏也提及了报纸上刊登过的一则关于俄国人入侵布拉格后,大肆杀戮狗和鸽子的新闻报道。对于人类残害和杀戮动物生命的行为,昆德拉表达了强烈的谴责。在他看来,《创世记》中的故事只不过是人类为屠杀动物寻找的借口,而笛卡儿的理论更是荒谬至极。自古以来,动物和人类一起生活在地球上,它们是人类忠实的伴侣。动物并非仅仅是有生命的机器,它们有自己的喜怒哀乐,也懂得知恩图报。如卡列宁的陪伴给特蕾莎乏味的生活增添了无尽的乐趣,哪怕在身患绝症、生命垂危之际,小狗为了照顾女主人的情绪,还要强颜欢笑,陪她出去散步。这一叙事情节让无数读者为之落泪。
昆德拉认为:“人与动物之间的关系构成了人类存在的一种永恒的深处背景,那是不会离弃人类存在的一面镜子(丑陋的镜子)。”人与人的交往常常带有目的性与伪装性,只有人与动物的关系才能测试出人类真正的道德。因此,对于动物,人类应该持有尊重与怜惜的态度。通过小说中的动物叙事,昆氏表达了保护动物、善待动物的生态伦理观,同时对“人类中心主义”思想进行了批评与斥责,彰显出强烈的生态意识。这些正义的生态价值观,对当代社会也颇具指导意义。经过千百万年的进化,人类最终才得以脱胎换骨,占据了食物链的顶端。不幸的是,有些目光短浅的人开始以自然主宰的身份自居,他们大肆杀戮野生动物,造成了它们的苦难。人类的愚蠢行为已经受到了自然的惩罚。如医学研究证明,人类历史上发生过的许多疫情正是人类非法食用野生动物所致。人与动物自古以来便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是一个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命运共同体。人类从来就不是自然界的主宰,也没有肆意剥夺动物生命的权利。因此,我们应该敬畏自然,停止一切屠杀野生动物的行为,这也是昆氏小说带给我们的生态启示。
三、关注生活中的“社会精神生态问题”
一般而言,生态批评包含自然生态和社会精神生态两个维度。自然生态批评主要关注人与自然的关系,而社会精神生态批评则将注意力聚焦于人与人的关系。随着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人们对物质享受的欲望日益膨胀。当自身利益与他人利益发生冲突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通常会变得紧张微妙。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生态批评理论也由传统的自然生态领域扩展至社會精神生态领域。在国内,鲁枢元最早提出“社会精神生态”这一概念。他在《生态文艺学》一书中指出:“自然生态体现为人与物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社会生态体现为人与他人的关系;精神生态则体现为人与他自己的关系。”此处,社会生态和精神生态的合体即为本文中的社会精神生态。刘文良指出:“要真正解决生态问题,不仅仅是要解决自然生态问题,更为根本的也许还在于要解决社会生态和精神生态方面的问题。”在昆德拉的意识中,“小说不是作家的忏悔,而是对于陷入尘世陷阱的人生的探索”,正因如此,他十分关注社会生活中普遍存在着的社会精神生态问题。“通过对这些不良现象的叙述,昆德拉揭示了现代社会中人类精神世界的贫瘠,反映出了其超前的生态伦理价值观。”
“家庭关系包括夫妻关系、父母与子女的关系、兄弟姐妹之间的关系等多个维度。”梳理小说情节发现,家庭关系的异化是最受昆氏关注的一个精神生态问题。在小说《玩笑》中,主人公路德维克和家人的关系就十分紧张。在他十三岁时,父亲被德国人抓进了集中营,从此和母亲相依为命。迫于生活的压力,路德维克几近辍学。幸好姑姑嫁给了一个有钱的企业家,资助他完成了学业。然而,不知感恩的路德维克从未真心感激过姑姑一家,反而对他们持有一种敌对的情绪。作为儿子,路德维克也十分不孝。读大学时,他为了一个不爱自己的女友玛凯塔竟然取消了暑假回家看望母亲的计划。在监狱劳教期间,只有母亲惦记着他,给他写信。然而,为了寻找音信全无的露茜,路德维克溜出了营地,为此被军事法庭判决去服18个月的劳役,错过了母亲的葬礼。同样,另一位主要人物考茨卡与妻儿的关系也十分疏远。他在布拉格有妻子和儿子,但他很少回家。他讨厌妻子的相貌和声音,还有家里那座钟一成不变的滴答声。因为妻子是一个贤妻良母,考茨卡找不到提出离婚的理由。为了躲避妻儿,他居然主动放弃了大学教师之职,抛下他们,去一个偏僻的国营农场工作。雅洛斯拉夫的家庭表面上和谐,实际上也充斥着各种矛盾。如为了表彰雅洛斯拉夫为民族艺术所作的贡献,人民委员会选定了他的儿子符拉第米尔在众王马队游行活动中扮演国王的角色。在雅洛斯拉夫十五岁时,捷克正处于纳粹占领时期的最后一年,当时,他也曾被选为众王马队的国王,上街示威游行。这一活动激起了市民们的爱国热情,雅洛斯拉夫和其父亲都特别看重这份荣誉。令雅洛斯拉夫失望的是,儿子对此丝毫不感兴趣,拿各种理由搪塞他,不愿扮演国王角色,在雅洛斯拉夫的一再逼迫下,才勉强答应。活动当天,雅洛斯拉夫发现了真相,原来妻子和儿子合伙欺骗他,儿子并没有扮演国王的角色,而是去参加年轻人喜爱的摩托车拉力赛。因为妻子充当了“帮凶”,雅洛斯拉夫大发雷霆,摔碎柜子架上的餐具和椅子,而妻子芙拉丝塔则始终背对着丈夫,头也不回。探究其家庭矛盾产生的根源,我们不难发现,雅洛斯拉夫平时对儿子缺少关爱,将家中的一切事务都交由芙拉丝塔打理。因此,妻子对他心存不满,儿子也是表面上恭敬、实际上叛逆。在昆德拉的小说中,家庭关系异化的例子不胜枚举。如《生活在别处》中,雅母十月怀胎,生下了儿子。然而,丈夫却对她因生育导致的身体缺陷十分在意,不愿与她在有光的地方亲热。《告别圆舞曲》中的克利玛、《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中的托马斯等男性因婚内出轨,导致了夫妻关系的紧张。因为母亲的过分强势,《生活在别处》中的雅罗米尔、《无知》中的伊莱娜、《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中的特蕾莎等与家人的关系十分淡漠。众所周知,家和才能万事兴。和谐的氛围不仅关乎每位家庭成员的健康成长,对社会的稳定与发展也至关重要。通过对种种家庭关系异化现象的叙述,昆氏给读者提供了丰富的反面案例,这对我们建构和谐的家庭关系具有一定的警示意义。
在昆德拉的小说中,不少人因生活中的不确定性因子产生了焦虑情绪,这也属于一种精神生态失衡的现象。日常生活中,不确定性因子无所不在。小说《生活在别处》开篇,雅母无法确定自己怀孕的地点,它可能是在某个夜晚广场的长凳上、某个下午在诗人父亲朋友的房间里或是某个早晨市郊的一个罗曼蒂克的角落。正如昆氏在小说《慢》中所述:“当事物发展太快时,谁对什么都无把握,对一切都无把握,甚至对自己也无把握。”还是以《生活在别处》为例,在花园中玩耍时,童年时代的雅罗米尔曾对母亲说了“生命就像野草”这一超越年龄的句子,不仅折射出了生活中存在着的不确定性,也深深地打动了多愁善感的雅母。生活中有着太多的不确定性,这让沉溺于自我想象中的雅罗米尔无法融入,因此,他痴迷于诗歌创作,借诗句来描绘自己的肖像,以此修正自己的面孔。现实生活中,雅罗米尔混乱、渺小,无法确定自己的价值与意义,而通过诗歌,他情感与梦想的世界变得具体化,这也弥补了他在现实生活中的缺失。对于雅罗米尔来说,诗歌将不确定的现实世界转变为确定的诗化世界,在诗歌的梦幻世界中,雅罗米尔可以轻松地掌控自己的人生。然而,诗歌给予雅罗米尔的毕竟只是一个虚幻的世界,当回归到现实世界后,他变得手足无措、无法适应,只能陷入焦虑抓狂的境地。同样,因为生活中充斥着不确定性因子,雅母一直在怀疑与自信之间徘徊。在姐姐的光环之下,少女时代的她极度自卑,于是,她渴望通过爱情来消除疑虑,建立绝对的信心,因此满怀激情地迎接怀孕的时刻。可悲的是,男友冷漠无情的态度让她的希望彻底破灭。雅罗米尔的诞生,给她带来了重拾自信的机遇,然而,渐渐长大的雅罗米尔与母亲的关系日渐疏远。正是因为生活中这些无法掌控的变数,让雅母不断地徘徊于希望与失望之间,由此产生了焦虑情绪。《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中,因为托马斯情感关系混乱,让特蕾莎对自己身体的魅力产生了怀疑。这种不确定性让她十分痛苦。一次,洗浴结束后,她站在镜子前注视着自己的身体,心中充斥着一种陌生感。她对眼前的身体感到失望和厌恶,因为它没有能力成为托马斯情感生活中的唯一。最终,不确定性导致了特蕾莎内心的焦虑,让她整夜做着噩梦,如她多次梦见自己被活埋了。托马斯每周才来看她一次。见面时,特蕾莎满眼都是泥土,什么也看不见,她的眼睛变成了两个洞,随后托马斯离开了。在他离开的时间里,因为害怕错过下次的约会,特蕾莎不敢睡觉。当她再次爬出地面见到托马斯时,他一脸失望,责怪特蕾莎变老变丑了。这一情形循环反复,特蕾莎始终无法入眠,也因此患上了抑郁症。笔者认为,不确定性是生活中不可避免的客观存在。以作品为鉴,我们应该正视并接受无处不在的变化,只有理解了变化的必然性,我们才能调节好心态,以一种轻松的状态去面对生活,避免陷入焦虑情绪。此外,昆氏的作品中也涉及其他的一些精神生态问题,如畸形的生命伦理观、悲观厌世的消极态度、窥探他人隐私等。通过对这些精神生态失衡现象的揭示,昆氏将生态伦理观完美地融入到小说文本中,这也极大地增强了作品的现实启示功能。
在《自然财富:环境史与生态想象》中,唐纳德·沃斯特指出:“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全球性生态危机,起因不在生态系统自身,而在于我们的文化系统。”作为一名心系社会的文坛大师,昆德拉也意识到了生态危机给人类带来的灾难性后果。因此,他利用小说这一文学媒介,将自己的生态伦理思想传递给广大读者,希望可以为改善生态环境贡献绵薄之力。一直以来,昆德拉都是学界关注的一个热点作家,梳理他的系列小说,我们不难发现,其中蕴含着丰富的生态意蕴。笔者认为,以全景视阈对昆氏小说中的生态伦理思想进行深入研究,既有助于理解小说的哲学内涵,也能为解决日益严峻的生态问题提供启示。
(责任编辑 张月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