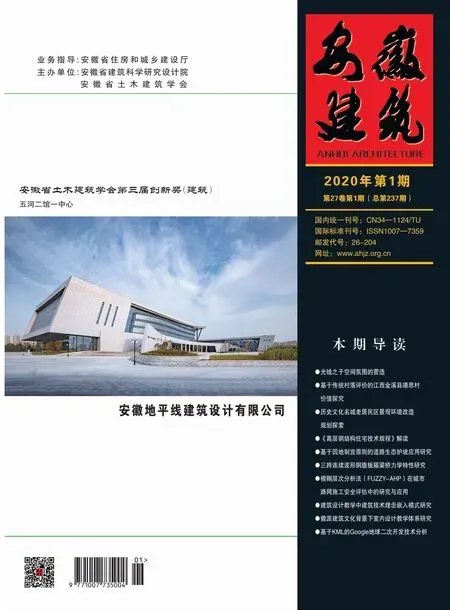光线之于空间氛围的营造
——卒姆托作品解析
胡春,杨娟
(1.安徽建筑大学建筑与规划学院,安徽 合肥230022 2.农业部南京设计院,江苏 南京210014)
我喜欢把各种材料、表面和边缘、光洁的或粗粝的置于阳光下,让物质神秘的深层、阴影以及黑暗的层次浮现出来,彰显出光线照耀在物体上的魅力。
——彼得·卒姆托
彼得·卒姆托是世界级建筑师当中设计作品最少的人之一,但每一件作品都会让人惊叹不已。他擅长以纯净的形式、富有表现力的材料、独特的构造处理、光线的奇妙组织,使建筑空间充满个性并丰富人们的感官,令人感动。尤其是光线,在他的建筑中,时而静谧时而神圣,如同乐曲的旋律一般,给人以震撼和美感。
1 神圣之光——Bruder Klaus教堂
人们对神圣的感悟缘起自宗教,因为宗教建筑总是着意渲染崇高神圣的空间氛围。天空象征着希望与永恒,“与天连接代表着一种卓越的宗教价值,因而将天空光引入室内就成为宗教建筑的最高理想。当微弱的天光以神奇和飘渺的姿态从上空倾洒到幽暗的教堂中时,人们对光的渴望便在瞬间升华成对神的景仰。”[1]出于此种宗教情结,建筑顶部的光线寓意神圣。
德国Bruder Klaus乡下的河边,矗立着一座土色封闭的狭长形多棱柱,与外部形态截然不同的是,内部空间呈曲线形,并且建造方式十分独特(图1)。卒姆托用112根松木扎了一座类似帐篷的结构,这个结构成为了教堂内部空间的模板,建筑师选用河沙,采用当地的砌筑方法,每天半米,用时24d完成整个混凝土的浇筑。之后在建筑师的控制下,在帐篷内部放一把火,燃烧了三个星期后,木材被烧毁,内部空间的模板自行解除,但松木模板留下了木质的纹理和被火烧焦的痕迹,据说至今墙壁上还留有松木的气味。
室内粗糙古朴,凹槽墙壁向上并同时向中心聚拢,形成了顶部树叶状的采光洞口(图2),光线倾泻而下,具有宗教意味的光呈现于幽暗的空间,赋予了建筑内部神圣的空间氛围,仿佛来自天国的神圣光辉,使人们的心灵受到洗礼和净化。而室内被熏黑的墙壁与光亮形成强烈的明暗对比,幽暗衬托了光的存在,人们进入教堂内部,在奇特的建构留下的黑暗和光明里,独自面对自己的内心。另外,从顶部投射下来的光线,使得内部空间上部与下部的明暗对比十分强烈,无形中增大了空间的竖向尺度,更加激发了教堂的神圣氛围。

图1 Bruder Klaus教堂
2 静谧之光——圣本尼迪克特教堂
路易斯·康说:“静谧,不可量度,是成为什么的愿望,新需求的源泉。它与光亮相遇。光亮是可量度的,依凭意志和法则,依凭已有事物的量度,是所有已有事物的形象赋予者。它们相遇于灵感的门槛上,这是艺术的圣坛,阴影的宝库。”[2]静谧是寂静、宁静和静默,光线划定一处静谧的所在,带给人们的感知是深度的、触动人心灵的,它能够让人们忘却尘世的喧嚣,能够让人们专注和冥思,能够唤起优越感和对已缺失的理想的向往。静谧之光,可以凝练简洁、可以飘逸灵动、可以炫目耀眼、可以幽静昏暗,终将引导人回归平静、回归真我。

图2 教堂内部

图3 圣本尼迪克特教堂
圣本尼迪克特教堂(图3)位于阿尔卑斯山脉高处的村庄,平面流畅的曲线是8字形的一半,采用全木制结构,37根独立的木支架支撑着木屋顶,墙体采用双层结构,木合板和木瓦表皮,木瓦外墙板在风雨的侵蚀下,颜色已经发生了不同的改变;木合板在室内形成了一个连续的界面,在构造上与结构柱脱离开,通过螺丝固定在木支架上,在室内,这种建构的逻辑清晰可见。教堂内部,只有合板墙被饰以银色亚光,其他皆为木材本色(图4),“这种效果是空间体验的基础,阳光从水平设置在屋顶边缘的天窗照进教堂,墙壁经过阳光的反射被消解成了幕布似的薄膜。木柱廊和屋顶的木结构形成了一个整体,令人想到巨大的华盖,一种特别被用在圣坛上方、类似天穹的装饰构件。”[3]

图4 教堂内部
檐口下的环形采光带将墙体同屋顶脱离开来,从外部看,从边缘至中心线逐渐隆起的屋顶,如同漂浮在群山之中的一片树叶。为了营造静谧的空间氛围,室内几乎没有装饰和色彩,只突出光的作用,晨光熹微之时,光线与室内细碎的阴影交织,光与影的视觉冲击将人带入沉思冥想的超然境界。当强烈的阳光从侧高窗射入,建筑空间中产生了黑白之间的退晕变化,室内处于灰色光影中,尽显洗练。而傍晚幽暗之时,微弱的光在明暗反差之下显得尤为突出,光明与黑暗的对比直入人们的内心深处,让身处其中的人们能平静和冥思。
3 雅致之光——布雷根茨美术馆
雅致是清新自然、精致典雅。雅致的空间氛围,要求空间中的光线以漫射光的形式出现,不能有强烈的光影变化、明暗对比,光线的强度、色彩和方向不再强烈变化,只均匀地洋溢在空间中,给人一种温柔淡雅的感受。
布雷根茨美术馆位于瑞士康斯坦丁湖边,由玻璃、钢和三片混凝土墙体构成(图5)。三道墙体呈风车状布局,是支撑整个建筑的结构,墙体与外部表皮之间可以布置楼梯、电梯等交通功能或储藏功能,巧妙的布局创造出一览无余的开放空间。建筑外表皮由尺寸相同的玻璃板组成,玻璃板使用金属支架固定在合适的位置,没有钻孔,再通过夹钳安装在后面的钢结构上。玻璃板间的缝隙向外部开敞,光线和空气可以自由地渗透进内部空间。晚间,建筑表皮向外散发柔和的光线,白天,室内的活动印迹映射到玻璃板上。

图5 布雷根茨美术馆

图6 美术馆内部
建筑一层是美术馆的大厅,直接通过玻璃表皮侧面采光,这里的光线柔和、均匀。而上部三层展示空间中的采光方式则完全不同,三片混凝土墙遮挡了大部分的侧向光线,采光主要依靠半透明玻璃板组成的吊顶。卒姆托构想奇绝,展厅的天花板和吊顶之间2.5m高的空间——被设计成光线收集器,光线和空气透过玻璃外表皮暴露的节点和边缘首先进入这里,而数百根细钢杆悬挂的玻璃板吊顶,又将日光散布到室内各处(图6)。“在建筑的核心部位,展厅的承重结构——三片混凝土墙体,使光线的方向改变,从而产生阴影和反射效果,并且调和光线的强度,给房间以纵深感。变幻不停的光线使人能感受到建筑的呼吸。这里的每一样事物都能渗透光线、风、甚至天气,建筑空间仿佛直接裸露于自然界中。”[4]持续波动的光线和空间让参观者能够感到太阳的位置,能够意识到光线的柔和变化,卒姆托出色地成就了一场光线的视觉盛宴,让参观者在其中完成了对艺术的膜拜。
4 神秘之光——瓦尔斯温泉浴场
当光线以一种不可预测的、出其不意的方式出现在建筑之中时,空间通常表现出神秘的气氛。这种处理方式一般会较多的出现在教堂建筑中,卒姆托在瓦尔斯浴场的设计中,着意营造宗教的氛围,浴场被作为一种仪式性的场所来解读。
瓦尔斯温泉浴场位于瑞士阿尔卑斯山里的边远村庄,海拔1200m(图7)。整个建筑一半掩入山坡,空间由东向西,从北至南从封闭逐渐开敞。建筑没有直接对外的出入口,需要通过山体的地下通道进入。屋顶上种植草皮,使建筑与周边环境构成一体。面山的外墙面,采用本地石材片麻岩,正立面设计了大面积的开窗与阳台。

图7 瓦尔斯温泉浴场
进入瓦尔斯温泉浴场的人总会有如同经历一场宗教祭礼的体验。从1970年代建的旅馆底层进入浴场,穿过昏暗的通道,游客进入一条长长的走廊,昏暗的光线不经意间从顶部的窄缝中射入。从此刻开始,游客感受到的是死一般的寂静和神的召唤,只能试探着找寻通向光亮的道路。室内空间曲折向前,进入了浴场大厅,大厅顶部有一些窄缝和嵌着蓝色玻璃砖的方孔,靠近室外的休息区域则拥有较大的落地玻璃窗,强烈的明暗对比,创造出一种戏剧化的空间效果。窄长的采光缝将建筑整体切割成各自独立的板块,射入室内的光线穿梭于各个空间中,不仅把建筑连接成大的流动空间,而且让冷漠、黑暗、寂静而又潮湿的建筑中充斥着一种沉重的神秘。“随着时间的改变,光线的投射轨迹不断改变。有时候,光像箭一般刺进水中,在水波中舞蹈,再撞向石壁,游走不定;有时候,光从顶蓬的缝隙中幽幽地渗透到石壁上,扩散到氤氲的蒸汽中,再消失在潋滟的水声里。很难分得清亮与暗的界限、静与动的分别。这一切都因为那些穿行其中的人体而获得生命。”[5]
5 总结
光线是卒姆托建筑设计中的一个重要元素,也成为了他建筑作品的特征。他很少放任光线肆意地进入建筑内部,而是根据不同的建筑性质进行严谨的设计,恰到好处地在空间中展现。Bruder Klaus教堂设计顶光赋予建筑空间神圣感;圣本尼迪克特教堂采用设在檐口的环形采光带体现建筑的宗教价值;布雷根茨美术馆的磨砂玻璃表皮和内部吊顶的处理,使光线均匀地展现在内部空间中,满足了展览建筑的需要;瓦尔斯温泉浴场的线性光源带着一丝神秘,一丝圣洁·……“人们仿佛被带离了现实的世界。卒姆托并非要求人们去相信什么宗教感,但他通过他的建筑区呼唤大家应该有一种超越世俗的意识。”[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