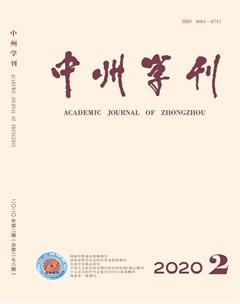防止党内问责泛化的有效路径探析
吕永祥 王立峰
摘 要:问责泛化是构建精准问责机制的一大现实障碍,亟待从理论上予以研究。基于问责要素的系统分析可知,问责主体的泛化、问责对象范围的扩大化、问责情形的泛化和问责方式使用的泛化,构成党内问责泛化的四种表现形式。体制内问责发起主体的权责定位不清晰、问责对象的申辩与申诉权利缺乏切实有效的程序保障、问责情形中的兜底条款被滥用以及数目字管理中问责任务指标和问责政绩考核指标设计不恰当,分别在不同的问责要素层面衍生出党内问责泛化问题。通过加强对体制内问责发起主体的权责清单管理、强化对问责对象的申辩与申诉权利的问责程序保障、科学设计问责任务指标与问责政绩考核指标等举措,系统解决党内问责泛化问题。
关键词:党内问责;问责泛化;问责要素
中图分类号:D262.6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20)02-0011-07
现代政治是一种责任政治,党内问责制是推动责任政党理念得以贯彻落实的具体政治制度安排。人們通常会将问责制的匮乏视为问题,期待通过设计越来越多的问责制度实现更好的治理效果。然而,过多的制度安排有时不仅不会解决问题,反而会加剧问题。①诚如寇佩尔(Koppell)所说:“虽然人们在‘问责是好的这一观点上极少产生争议,但是几乎没有组织会宣称自己‘问责过度。”②针对当前党内问责实践中出现的问责泛化等问题,十九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强调:“实施精准问责,防止问责不力或问责泛化、简单化。”③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以下简称2019年版《问责条例》)也将防止问责泛化作为健全党内问责制的一个重要方向。目前学术界对党内问责泛化问题尚缺乏深入系统的研究,鉴于此,本文将党内问责泛化作为专门的研究对象,对当前党内问责泛化的表现形式、内在成因与治理进路进行系统分析,以期为解决党内问责泛化问题提供理论思考。
一、党内问责泛化的表现形式
党内问责制是中国共产党关于问责主体、问责对象、问责情形、问责方式等各项问责要素及其互动关系的一系列问责制度安排的统称。从运行情况来看,当前党内问责制在全面从严治党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同时,也存在问责泛化等具体问题。党内问责泛化在各个问责要素层面上有着具体的表现形式,在实践中呈现出不同的情形。
1.问责主体的泛化
问责主体作为问责制的首要构成性要素,着力回答“由谁来问责”这一重要问题。党内问责主体是依据干部管理权限对触犯问责情形的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实施问责的组织和个人的统称。授权是问责的前提与依据,基于民主选举和组织任命两种授权方式的具体差异,莫尔干(Mulgan)将问责主体划分为基于“受影响的权利和利益原则”确定的问责主体和基于“所有权原则”确定的问责主体两种具体类型。④前者指向问责发起主体,是指权利和利益受到公权力侵犯的社会公众、社会组织有权利向有权机关提出发起问责程序的要求和呼吁;后者指向问责启动主体,是指对政府官员拥有管理权限的公权力机关可以对其失职失责行为直接实施制裁。问责发起主体和问责启动主体之间的差异体现在,问责发起主体虽然可以为启动问责程序施加舆论压力和提供问题线索,但是无权直接决定问责程序的启动和对问责对象的调查与惩处。与之相比,问责启动主体则直接掌握着问责程序的启动权以及对问责对象的调查与处置权。厘清问责发起主体和问责启动主体在性质、权限等方面的差异,对于理解党内问责主体泛化现象具有重要的意义。
党的十八大以来,关于督导组、检查组等各种非常设性机构的报道屡次见诸报端,这些机构通常是党和国家为完成特定任务而设置的任务型组织,是国家权力的重要的组织延伸。虽然这些任务型组织并非2016年7月施行的《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以下简称2016年版《问责条例》)规定的问责启动主体,但是它们可以凭借其监督网络和科层制权威为启动问责程序提供问题线索来源并施加压力,在性质上属于体制内问责发起主体的范畴。从规范意义上来讲,作为问责发起主体的各种任务型组织和2019年版《问责条例》规定的党委(党组)、党的工作机关、纪委及其派驻(派出)机构等法定问责启动主体各自享有不同的职责权限,在党内问责中两者应当是相互分工与配合的关系。然而在党内问责实践中,有的督导组、检查组基于其科层制权威,直接将问责处理意见乃至问责处理决定交给法定的问责启动主体,对问责启动主体依法行使问责权力造成不当的干扰。例如,“有的检查组、督导组在移交问题线索时,直接将具体处理意见一一列出,和盘端给纪委”⑤。事实上,党内问责主体及其职责权限具有法定性的特征,“不能谁说问责就问责”⑥,督导组、检查组等任务型组织越位扮演问责启动主体的行为,衍生出问责主体泛化的问题。
2.问责对象范围的扩大化
问责对象是因导致问责情形的发生而接受问责主体制裁的组织和个人,是各种问责方式施加的具体对象。问责对象范围的大小影响问责活动的广度和深度,是判断各类问责对象是否存在权责不对等现象的一个重要指标。从规范意义上来讲,问责对象范围的宽窄适度是问责主体精准认定问责对象的一种理想状态。但是在党内问责实践中,问责范围被人为扩大的现象时有发生。当一项问责事件引发社会舆论关注和上级领导的重视之后,有的问责主体为彰显对问责事件处理的重视程度与问题整改力度,有时会倾向于将与问责情形发生并无因果关系的部门和人员也纳入问责范围之中。例如,贵州省有的县(市)在调查核实贫困户错判、漏评问题的过程中,为表明执纪必严的“决心”,把与该问题相关的干部一律纳入问责对象。调查组提交的124名建议问责责任人员名单中存在问责对象范围扩大化的问题,后被贵州省纪委监委调整为79名。⑦
在条块交织的权责关系网络中,问责对象纵向范围与横向范围的扩大化构成党内问责对象范围扩大化的两种表现形式。一方面,在上问下责的纵向问责模式中,有的问责主体在确定问责对象时将问责范围“一竿子插到底”,问责对象向下级乃至最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干部无限延伸。例如,“在问责数量上,有的地方感觉偏少,只好想方设法凑数,本来问责范围只需到乡镇一级偏要扩大至村民小组”⑧。另一方面,在党政同责的横向问责模式中,当发生群体性事件处置不力等问责情形时,有的问责主体出于平息社会舆论压力和对上级机关有所交代等考虑,更容易将“多处分几个部门和干部”作为一种“理性”的行为选择。譬如,“南方某县曾发生一起群体性事件,该追责的部门本来已经明确,但县领导认为问责范围不够广,不足以体现问责决心,无法交差,于是把本无直接关系的部门也列入了问责名单”⑨。问责对象范围的扩大化,意味着有些对发生问责情形本不需要承担责任的党组织和普通党员干部被错误问责,这难免会侵犯其合法正当权益,削弱其履职尽责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3.问责情形的泛化
“问责情形是指问责对象在何种情况下应当对其行为承担责任”⑩,指向触发问责程序的具体情形。“责任在政治活动和公共管理中最一般的含义是指与特定的职位或机构相联系的职责”B11,中国共产党有自身的机构属性与职能设置,“党内问责”中的“党内”这一前缀限定了中国共产党设置的党内问责情形应当与中国共产党的政党属性与政党职能密切相关。2019年版《问责条例》第七条围绕党的领导、全面从严治党的主体责任与监督责任以及新时代党的建设总体布局来设置党内问责情形,充分体现党内问责情形设置的政党属性与政党特征。
从规范意义上来讲,党内问责情形的范围应当宽窄适度,既要在覆盖面上符合权责一致的原则,确保不存在权责不对等的空白地带,又要在内容上聚焦中国共产党管党治党的政治责任,确保问责内容不泛化。但是在党内问责实践中,有的党内问责主体逐渐偏离党组织和党员领导干部管党治党的政治责任这一设置问责情形的主轴,将党内问责情形“外溢”到日常行政管理和重要工作推動等其他领域之中。吉林省纪委在调研中发现,一些地方把不适用党内问责条例的一般性工作问题纳入问责范围,导致问责工作在问责事项上出现泛化现象。B12江西省纪委在开展调研时也发现,“有的党委(党组)以及领导干部把一些具体的一般性业务工作方面出现的问题都用问责这个‘筐来装,动不动把问责挂在嘴边,对问责情形界定不清,以问责代替日常监管,推动工作落实”B13。党内问责情形的泛化偏离精准问责的发展方向,极容易产生越俎代庖行为缺乏合法性和该管的事情没有管好的双重负面效应。
4.问责方式使用的泛化
问责方式作为问责机制的强制性要素的外在表现形式,是党内问责主体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法定职责的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实施的各种制裁方式的统称,对督促各级党组织和党员领导干部廉洁、公正、高效地行使权力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要发挥问责方式对党员领导干部的威慑和处置功能,就需要将其与党员领导干部的政治职务、党员身份、社会名誉和自由权利等利害事项结合起来。2019年版《问责条例》规定通报、诫勉、组织调整或组织处理以及纪律处分四种对党员领导干部的问责方式和检查、通报、改组三种对党组织的问责方式,这些问责方式分别与党组织和党员领导干部失职失责的行为性质、情节轻重、危害后果等事项相对应,体现了刚柔相济、错责相当的问责原则。
从规范意义上来讲,错责相当作为2019年版《问责条例》新增加的一项重要的问责原则,是指“问责主体应当根据责任人的行为性质、过错大小、社会危害程度以及情节轻重等来决定惩罚的强度”B14。然而,在党内问责实践中,有的问责主体存在执纪问责简单化的问题,“一有错就问责,一问责就动纪”B15。例如,“一些涉及村干部的轻微违纪问题,本可以批评教育,但还是给予了党纪处分,目的就是为了凑数,以完成目标任务”B16。问责方式的门槛降低与泛化使用,势必会带来惩罚机制的滥用,不仅影响党员干部履职尽责的积极性,而且也容易削弱问责结果的公信力。
二、党内问责泛化的成因剖析
究其根源,上述党内问责泛化问题的产生,主要是由以下几方面的原因造成的。
1.体制内问责发起主体的权责定位不清晰
问责发起主体有不同的类型学划分方法,在国家与社会关系这一分析框架之下,我们可以将问责发起主体划分为体制内问责发起主体和体制外问责发起主体两种类型。前者指向行使国家权力的各种国家机关以及由党和国家设置的巡视组、督导组、检查组等非常设性机构,后者指向社会民众、社会组织和新闻媒体等社会力量。中国共产党为了在复杂变化的环境中不断提升治国理政的灵活性和有效性,在各级地方党委及其工作机关等常设性政党组织之外,还设置了督导组、检查组等各种任务型组织。虽然这些任务型组织并非法定的问责启动主体,但是它们却可以凭借其监督网络和科层制权威为启动问责程序提供问题线索来源并提出权威性的问责发起建议,但是其无权将问责意见乃至问责结果强加给法定的党内问责主体B17,因此它们属于体制内问责发起主体的范畴。
在党内问责实践中,各级党组织为了充分发挥任务型组织的灵活性等优势,对其开展的组织管理和制度约束通常较常设性政党组织更为薄弱。在各种任务型组织之中,中国共产党除了对巡视组出台《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以外,对名目繁多的督导组、检查组等任务型组织尚未出台明确其权责定位的基础性党内法规。督导组、检查组等体制内问责发起主体的权责定位不清晰,在某种程度上容易带来干扰党内问责实践的问题。从规范意义上来讲,督导组、检查组等体制内问责发起主体在党内问责中承担的主要职能是发现问题线索和督促问题整改落实,触犯各种问责情形的党组织和党的领导干部应当由相应层级的党委(党组)、纪委及其派驻(派出)机构、党的工作机关等法定问责启动主体进行调查和处置。但是在党内问责实践中,有的督导组、检查组等由于自身的职责权限较为模糊、具有扩大职权的内在冲动等原因,并不仅仅满足于基于问责发起主体的身份提出启动问责程序的要求和呼吁,代替问责启动主体提出问责处理意见乃至直接作出问责处理决定的现象也时有发生。由此来看,派出机关对其派出的督导组、检查组等任务型组织的职责权限定位不清,导致它们虽为问责发起主体却越位扮演问责启动主体的身份,衍生出问责启动主体泛化的问题。
2.问责对象的申辩与申诉权利缺乏切实有效的程序保障
第一,问责对象在问责过程中的申辩权利缺乏切实有效的程序保障。问责机制的运行通常可以划分为提供信息、辩论和强制三个阶段B18,辩论阶段既是问责主体对问责对象提供的各种履职信息的消化吸收和理解运用,也是问责主体对问责对象采取强制措施的程序性前提,是问责过程中的关键环节。基于此,哈蒙(Harmon)指出:“在某种意义上,问责的核心就是问责主体和问责对象之间的对话。”B19在对话过程中,“问责主体有要求问责对象对其行为、决策及相关信息作出解释和说明的权力,而解释说明和证成对于问责对象而言既是义务也是权利,问责过程中不能剥夺问责对象进行自我解释和辩护的权利”B20。以权利制约权力是防止权力滥用的一种主要手段,党的领导干部对问责主体的质疑和调查结果享有申辩权,是防止问责主体在错误问责的歧途中越行越远的“制动装置”。虽然《中国共产党章程》第一章第四条和《中国共产党党员权利保障条例》第二章第十一条分别赋予党员在党组织对其进行党纪处分时进行申辩的权利,但是2016版《问责条例》在设置问责程序时并没有对问责对象的申辩程序作出明确具体的规定。受到程序性保障措施缺失等因素的影响,问责对象在问责过程中缺乏切实有效的申辩权利,容易加剧问责主体滥用问责权力的问题,衍生出“背锅式问责”“凑数式问责”等问责泛化现象。
第二,问责对象的申诉权利缺乏切实有效的程序保障。申诉权利是党的领导干部受到错误问责之后,向问责申诉机关请求更改或撤销错误的问责处理决定的重要权利,其有助于维护党内问责的公正性,对不恰当的问责处理决定进行事后纠错。规范、清晰和可操作化的运行程序是党的领导干部的政治权利的重要保障。然而令人遗憾的是,2016版《问责条例》对问责对象的申诉与救济程序并没有作出专门的规定,这使得党的领导干部在被错误问责之后缺乏清晰具体的申诉渠道,既不清楚向哪一个机构提出申诉请求,也不了解申诉的具体时限要求。党员干部的申诉权利缺乏程序性保障,不仅导致他们在被错误问责之后无法保障自己的正当合法权益,而且也容易使问责泛化的错误决定无法被及时改正。
3.问责情形中的兜底条款被滥用
2016版《问责条例》不仅从正面列举了党的领导弱化、党的建设缺失、全面从严治党不力、维护党的各项纪律不力和推进党风廉政建设与反腐败工作不坚决等五种具体问责情形,而且还通过设置兜底条款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上述问责情形可能存在的内容不周延性和难以随社会情势变迁等问题。这种正面列举与兜底条款相结合的立法技术,被许多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广泛采用。正面列举的问责情形涵盖内容的清晰化、多元化和具体化水平,会对党内问责主体适用兜底条款时享有的自由裁量权产生重要的影响。2016年版《问责条例》正面列举的五种主要问责情形未能系统涵盖党的政治建设这一执政党建设的首要环节,对每种具体问责情形的描述也较为抽象笼统。正面列举的问责情形的抽象性和模糊性特征与复杂多样的问责事件之间的矛盾,赋予党内问责主体适用问责情形兜底条款的较大的自由裁量权。自由裁量权作为一种政治权力,也存在被滥用的风险。各地区出台的2016版《问责条例》实施细则大多并未细化问责情形的正面列举条款,对党内问责主体适用问责情形兜底条款的自由裁量权无法进行有效的规制,这容易导致有的党内问责主体将与管党治党的政治责任无关的问责内容统统纳入问责情形的兜底条款之中。2016年版《问责条例》第六条设置的六种问责情形中,与环境保护、安全生产等具体工作有关的问责都被纳入“其他应当问责的失职失责情形”这一兜底条款之中,“结果导致严肃的党内问责被降格为针对普通干部和具体事项的工作问责”B21。
4.数目字管理中的问责任务指标和问责政绩考核指标设计不恰当
第一,有的党内问责主体为了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上级下达的问责任务指标,将无关的部门和人员也纳入问责范围之中,在数目字管理中设计不恰当的问责任务指标,是滋生“凑数式问责”等问责泛化现象的重要原因。“数目字管理作为一种理性的、精确的、可以进行计算的管理方式”B22,以量化的任务指标和政绩考核指标等形式在中国共产党管党治党的各个方面得到广泛的运用,“‘层层下指标,逐级抓落实,签订责任状,分级去考核是政府上下级关系的形象写照”B23。数目字管理是否科学合理,对各级党组织和党的领导干部的行为倾向具有重要的影响。错误的数目字管理方式通过设定脱离客观实际的问责任务指标这一中介,作用于党内问责泛化实践。有的“凑数式问责”现象之所以发生,是因为有的党内问责主体为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上级下达的不恰当的问责任务指标,基于趋利避害的理性人本性,具有将与发生问责情形无关的部门和人员纳入问责范围之中的冲动。
第二,一些地方的党的纪检机关将问责数量作为衡量问责工作政绩的主要指标,为在问责政绩考核中获取有利位置,具备盲目追求问责对象数量的内在动力。“测量能推动工作,若不测量效果,就不能辨别成功还是失败。”B24对问责效果的测量和评估是数目字管理运用的一个重要领域,通常以问责政绩考核的形式呈现出来。问责是党的纪检机关的一项重要职责,党的纪检机关实施党内问责的具体情况需要接受上级党的纪检机关等机构的量化考核。在有的地方,党的纪检机关为在问责政绩考核中获取评奖评优资格乃至政治晋升等利好,有时会作出回避费时耗力、难以量化考核的精准问责,转而盲目追求问责对象数量和问责案件数量的策略选择。在重数量轻质量的错误的问责政绩观的驱动下盲目追求增加问责数量,构成有的问责主体人为扩大问责对象范围的内在驱动力。
三、党内问责泛化的治理进路
1.加强对体制内问责发起主体的权责清单管理
非常设性机构的灵活设置在保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体制的韧性的同时,也带来了对督导组、检查组等任务型组织的监督问题。在当前政党治理网络日趋复杂的情况下,加强对督导组、检查组等任务型组织的管理和监督,是防止问责主体泛化的关键环节。派出机关加强对其派出的督导组、检查组等机构的管理和监督需要借助于一定的制度工具。权责清单制度具有权责定位清晰化、权责配置可视化等优势,已经被党和国家广泛运用于对各个党政机关的监管之中,具备向督导组、检查组等任务型组织推广的可行性。基于此,派出机构应当将赋予权力和加强管理有机结合起来,在赋予由其派出的督导组、检查组等任务型组织相应管理权限的同时,还应当通过清单化管理加强对它们的监督。具体而言,派出机关可以依据国家法律与党内法规等制度文本,探索性地编制督导组、检查组等各种任务型组织的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清晰化地呈现其权力边界和职责事项,帮助他们厘清问责发起主体和问责启动主体之间的权责差异,督促他們回归问责发起主体的角色定位以及发现问题线索和督促问题整改落实等职能定位,纠正越位扮演问责启动主体的行为。
2.强化对问责对象的申辩与申诉权利的问责程序保障
第一,中国共产党在重塑问责程序条款的过程中应当将问责对象的申辩程序确定为问责处理程序的前置性程序,为问责对象的申辩权利提供切实有效的问责程序保障。切实保障问责对象的申辩权利的一个重要方式就是,重塑2016版《问责条例》中的问责程序条款,将问责对象的申诉程序作为一项重要的党内问责程序固定下来,并将其作为问责决定机关作出问责处理决定的一个前置性程序。为了保护问责对象的正当合法权益,除符合案情简单、证据确凿、处分轻微等简易问责程序的构成要件的特殊情况以外,党内问责主体作出问责处理决定之前应当认真听取问责对象的解释与辩护并将其记录在案,以此作为党内问责主体作出问责处理决定的一个重要依据。2019年版《问责条例》第十一条规定:“查明调查对象失职失责问题后,调查组应当撰写事实材料,与调查对象见面,听取其陈述和申辩,并记录在案;对合理意见,应当予以采纳。”B25该条款为保障问责对象的申辩权利提供了切实有效的问责程序保障。通过机制建设保障问责对象的申辩得到问责主体的认真倾听和采纳,是今后各级各类党内问责主体贯彻执行问责申辩程序的重要着力点。
第二,中国共产党在重塑问责程序条款的过程中,还应当进一步完善问责申诉程序,明确问责申诉机构和问责申诉时限,为被错误问责的问责对象提供制度化的权利救济渠道,健全针对问责泛化导致的错误决定的事后纠错机制。保障问责对象的申诉权利,是维护问责结果的公正性与公信力的重要一环。健全问责泛化的错误决定的事后纠错机制,应当从为问责对象的申诉权利提供问责程序保障入手。2019年版《问责条例》第二十条对问责对象的申诉时限、申诉机构、申诉方式、申诉程序等事项做出具体的规定,为保护问责对象的申诉权利提供了重要依据。1个月的申诉请求时限和申诉处理时限兼顾了问责申诉的效率与公正两项原则,既有助于为被泛化问责的问责对象及时提供申诉渠道,使其从容不迫地准备问责申诉材料,又为问责申诉机关提供了足够的调查取证和分析研判的时间。为进一步完善问责申诉程序,还应当按照运动员和裁判员相分离的法治原则设置问责申诉机构,保障问责申诉机构的权威性和中立性。
3.通过丰富正面列举式问责情形,严防兜底条款被滥用
“责任政治不是消解自由裁量权,也不是完全‘限制自由裁量权,而是‘控制自由裁量权,用合适的方法既发挥自由裁量权的效用,又防止其滥用。”B26实体规则控制是通过进一步细化规则来压缩规则执行者的自由裁量空间的重要方式,秉持该种思路,中央在修订2016年版《问责条例》时,进一步细化和充实了问责情形的正面列举条款,以压缩党内问责主体适用问责情形兜底条款的自由裁量空间,有效解决滥用兜底条款带来的问责情形泛化问题。2019年版《问责条例》不仅围绕党的领导和新时代党的建设总体布局具体、详细地列举了各项具体问责情形,而且还将“履行管理、监督职责不力”“在教育医疗、生态环境保护、食品药品安全、扶贫脱贫、社会保障等涉及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上不作为、乱作为、慢作为、假作为”等情况确立为新增加的问责情形,这就进一步细化与充实了党内问责情形的正面列举条款,提升了党内问责事由的清晰化、具体化和多样化水平,为有效规制党内问责主体滥用兜底条款的行为提供了切实有效的制度支撑。
4.科学设计数目字管理中的问责任务指标和问责政绩考核指标
第一,在科学设计数目字管理中的问责任务指标时,应当根据不同地区和单位的实际情况,为各个党内问责主体设计差异化和灵活性的问责任务指标,推动党内问责主体按照“实事求是、依规依纪”的问责原则来合理确定问责对象范围。人为设定的问责任务指标一旦脱离客观实际和趋于僵化,就容易催生出有的党内问责主体为完成问责任务指标而实施“凑数式问责”的问题。鉴于此,今后在运用数目字管理方式测量和考核问责效果时,应当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根据不同地区和单位的实际情况科学设计灵活浮动的问责任务指标并赋予其合理的权重。在科学的问责任务指标的指引下,党内问责主体应当纠正不问缘由地将完不成问责任务指标作为一票否决事项的不恰当做法,以“实事求是、依规依纪”的问责原则为依据,确定问责对象的合理范围。
第二,在科学设计数目字管理中的问责政绩考核指标设计时,应当秉持问责数量和问责质量并重、问责效率与问责效果并重的思路,以均衡并重的考核内容纠正一些地方党的纪检机关通过盲目追求问责数量来博取问责政绩的不良倾向。党内问责工作的政绩有显性政绩和隐性政绩之分,两者分别与不同的问责政绩考核指标相对应,呈现出量化考核指标和定性考核指标之间的显著差异。基于此,将数目字管理科学运用于党内问责之中,应当秉持问责质量与问责数量并重、问责效果与问责效率并重的思路,统筹考虑问责案件数量、问责对象数量等量化指标与问责主体定性量纪的精准性、问责案件处理的政治效果、纪法效果与社会效果等定性指标,合理提高定性问责指标在当前问责政绩考核指标体系中的权重,鼓励党内问责主体自觉纠正盲目追求问责数量的行为倾向,更加注重问责案件定性量纪的精准度和问责案件处置的政治、纪法与社会效果。
注释
①Yang,K.Further Understanding Accountability in Public Organazations: Actional Knowledge and the Structure-Agency Duality, Administration &Society,2012(44) .
②Koppell J G . Pathologies of Accountability: ICANN and the Challenge of “Multiple Accountabilities Disorder”,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2005(1).
③管筱璞:《不枉不纵 精准问责》,《中国纪检监察报》2019年5月3日。
④R Mulgan.Holding Power to Account:Accountability in Modern Democracies, New York: Palgrave, 2003,p.13.
⑤闫鸣:《各尽其责,不越位更不缺位》,《中国纪检监察报》2019年4月25日。
⑥范赓:《问责不能泛化简单化》,《中国纪检监察报》2019年4月17日。
⑦云武:《精准有效用好问责利器》,《中国纪检监察报》2019年7月14日。
⑧B16阳建:《问责有指标?心态挺多样:凑数式问责,让基层干部“躺枪”》,《半月谈》2018年第21期。
⑨梁建强、周楠、高皓亮:《“找背锅人易,找负责人难”——滥用问责“五座大山”伤了基层干部》,《半月谈》2018年第19期。
⑩吕永祥、王立峰:《当前党内问责制存在的突出问题及其解决路径——基于问责要素的系统分析》,《社会主义研究》2017年第5期。
B11[英]戴维·米勒、[英]韦农·波格丹诺:《布莱克威尔政治学百科全书》,邓正来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594页。
B12吉林省纪委监委研究室:《以精准问责砥砺政治担当——吉林省开展党内问责工作情况调查分析》,《中国纪检监察报》2019年3月28日。
B13江西省井冈山市纪委监委课题组:《对精准有效用好问责利器的调研》,《中国纪检监察报》2019年6月20日。
B14赵峰:《党委领导干部问责制研究》,南京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3年。
B15卢福林:《问責务求精准规范》,《中国纪检监察报》2019年1月24日。
B17吕永祥:《新中国成立70年党内问责制的历史沿革、现实困境与破解之道》,《河南社会科学》2019年第7期。
B18Mark Bovens. Two Concepts of Accountability: Accountability as a Virtue and as a Mechanism, West European Politics,2010( 5) .
B19Harmon, M. Responsibility as Paradox: A Critique of Rational Discourse on Government,Thousand Oaks, Calif.: Sage, 1995,p.191.
B20B26王若磊:《政治问责论》,三联书店,2015年,第75、130页。
B21蒋来用:《“问责异化”的形成与矫正机制研究》,《河南社会科学》2019年第7期。
B22竺乾威:《数目字管理与人本的回归》,《中国行政管理》2011年第3期。
B23杨雪冬:《压力型体制:一个概念的简明史》,《社会科学》2012年第11期。
B24[美]戴维·奥斯本、[美]特德·盖布勒:《改革政府——企业家精神如何改革着公共部门》,周敦仁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年,第128页。
B25《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人民日报》2019年9月5日。
责任编辑:浩 淼 文 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