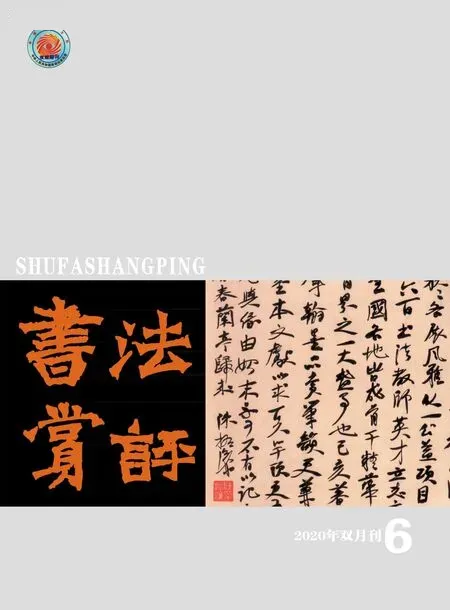试论梁文帝萧顺之建陵石刻及书法特质
杜 浩
南朝是中国历史上分裂割据、战乱频发的时期,更是文化繁荣的时期。在这一时期,墓葬建筑有新的秩序,以此而保留了大量类型丰富、形式多样的六朝遗物遗存,主要以石兽、石柱、石碑、石座为主,散落分布于南京及其周边地区,这些石刻记录了六朝的往事,是人们寻访六朝文明的重要标志性遗迹。目前已知的南朝陵墓石刻共计三十四处,其中南京二十二处,句容一处,丹阳十一处。[1]这些石刻皆体型巨硕、气势宏大、形象古朴、雕刻精湛,两两对称,历经风雨、彼此陪伴了一千五百余年。通过这些石刻建筑,不仅可以了解南朝的历史文明,对于当时书法特质的了解与文字的发展也有很大的意义。
一、梁文帝萧顺之建陵石刻
两汉时期,继承秦制,厚葬风气明显,王符在《潜夫论·浮侈篇》中说:今京师贵戚,郡县豪家,生不极养,死乃崇丧。或至金缕玉匣,檽梓楩楠,多埋珍宝偶人车马,造起大冢,广种松柏,庐舍祠堂,崇侈伤僭。[2]可见其厚葬之风。而到了南朝时期,情况发生了变化,其厚葬之风不如东汉,东汉时表现为地上与地下,地上设石柱与石兽、立祠、筑阙,地下修建豪华的墓室,设画像石,绘壁画。从现存石刻来看,南朝陵墓石刻主要由石兽、石柱、石碑组成,有的还有石座。
石兽从造型和等级上看,可以分为帝陵前的有角石兽和王侯墓前的无角石兽两种。自东汉出现墓前石兽以来,陵墓石兽的称谓一直没有确切的说法,在东汉时期多称“天禄”“辟邪”或“狮子”,到南朝时又称“天禄”“麒麟”或“狮子”,总的来说,可以把帝陵前的有角石兽称为麒麟,王侯墓前的无角石兽称为辟邪。石柱又称为表、华表、表木、标等,起到标明和指示的作用,完整的神道石柱由柱头、柱身、柱座组成。南朝陵墓石碑存世较少,大多数碑身已不见面目,仅留龟趺造型的碑座,完整的石碑由碑首、碑身、碑座(龟趺)构成。石座存世更少,现仅见于梁文帝萧顺之建陵。
梁文帝萧顺之(?-公元491),字文纬,齐高帝萧道成的族弟,梁天监元年(公元502 年),其子萧衍代齐称帝,建立梁朝,萧顺之被尊为太祖文皇帝,与其妻合葬陵寝曰建陵。陵前神道依次列有石兽、方形石座,神道石柱和石龟趺各一对,石制为青石。在神道的两侧,南边的石兽为麒麟,北边是天禄,相距约16 米,天禄身长3 米有余,残高2.00,颈高1.25,2.70 米;麒麟身长约3 米,残高2.30,颈高1.50,体围2.76 米。[3]石座有四块,每一块的边缘部位皆有“T”型榫眼的石块分置呈正方形平面的四角。石柱,称神道石柱,又称陵墓华表,分为上、中、下三部分。下部为石础,上圆下方,方形四面浮雕模糊不清,像是有仙人灵异,其上半圆则雕有一对环绕相对的翼龙,口内衔珠,四足;中部为柱身,柱表饰凹槽纹和束竹纹;上部有矩形石额,刻有阴文“太祖文皇帝之神道”八字,一侧为正书顺读,另一侧则是从左反书逆读。石额部分柱表雕以三重绳辫纹编织束竹纹,束竹纹以下改雕凹槽纹直至柱根。覆莲状圆盖中心雕出的圆窝与柱身顶端圆榫咬合置于柱顶。神道柱整个造型和谐协调,挺拔庄严。龟趺,状似海龟,雕刻简朴有力。[4]
二、书法特质
在魏晋南北朝的书法史上,字体的发展演变是一个特别重要的大事件。曹魏时期颁布“禁碑令”以来,碑刻甚少,北朝由于民族融合及佛教的兴盛,碑刻艺术繁荣,以“平城体”和“洛阳体”为代表。南朝以江左风流为尚,多为尺度手札,碑刻亦少之,而在梁文帝萧顺之建陵神道的两侧石柱上,在上方的石额上书刻有阴文“太祖文皇帝之神道”八字,两侧文字内容相同,但一正一反,可以反映当时石刻书法的面貌与特点。

图二

图三
观神道两侧石柱上方石额上的题字,八个大字为“太祖文皇帝之神道”,左边石额上的文字是正常书刻,右边石额上的文字则是左边的反写。从章法上来看,为两行四列,排布整饬又有气势。字体则以隶书为主,兼有楷书意味,横画、捺画多有隶书雁尾的特征,如“太”“祖”“文”“帝”等字的横画,捺画如“道”“之”等字较为明显。字形结构又偏于楷书,与同时期的《爨龙颜碑》意味相近,字形多由扁而变得方正瘦长,如“皇”“帝”等字,与北魏洛阳时期成熟的魏碑体面貌趋同。整体看来笔画有弹性,柔中寓刚,神采飞扬、气势雄强又丰肥憨拙,清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评此额为“《太祖文皇帝神道》若大廷褒衣,端拱而议”。[5]同时代的《吴平中侯萧景阙铭》,位于南京栖霞区,其石额上有“梁故侍中中府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吴平忠侯萧公之神道”二十三字,笔迹清晰,笔画遒劲平直,更偏向于楷书,又略带隶意,石额文字亦为反书,与梁文帝萧顺之建陵石柱左右两侧一正一反的书刻不同,《吴平中侯萧景阙铭》的石额文字仅存世有反文。
石额上的文字反书反刻是否反映了当时的一种什么现象。笔者通过资料的查询了解到,这种反刻的现象,与对面的正字相对,或相当于正字的相反影像,亦可能是南朝时开始并流行的一种字体。因其面貌呈反刻,并且文字的顺序打破常规,是从左往右,故称之为“反左书”。“反左书”一词早在古代书论中提及,南朝梁书法家庾元威在《论书》里说:“反左书者,大同中东宫学士孔敬通所创。余见而达之,于是座上酬答诸君无有识者,遂呼为众中清闲法。今学者稍多,解者益寡。”[6]所以说“反左书”很可能指的就是反书反刻,前文所述梁文帝萧顺之建陵神道的石柱额字以及吴平忠侯萧景墓的石额题字便是采用的这种书体。据庾元威说,“反左书”大约出现在梁代大同(公元535 年~546 年) 中孔敬通所创,而文中所列举的萧顺之、萧景等墓神道石柱题字均大同年间之前。[7]著名的史学家巫鸿对这种反书现象也作了解释,他认为神道一侧的反书是另一侧正书的镜像,分别为死者和虚拟的参观者而设。通过刻有正反铭文的神道,人们以双向视线同时朝向两个对立的方向去审视生死,这种独特的视觉方式在六朝的作家和艺术家那里十分普遍。[8]另外,还有学者认为,南朝受佛道及礼乐制度的影响,书法艺术有杂体的背景和更加丰富的艺术表现,反书即为其中一种特殊的艺术表现形式。
三、梁武帝萧顺之建陵石刻石额文字的价值影响
梁武帝萧顺之建陵石刻作为南朝时期陵墓石刻遗存最多之处,石柱上方石额的题字,无论对于考古美学,还是南朝书法艺术的研究,都有很大的意义。左边八个阴刻的正字,以及右面石额上的阴刻反字,短短八个字,虽然没有什么特别新奇之处,但是其隶楷相间的面貌、富有弹性的用笔以及雄强飞扬的字势值得我们学习,是练习大字摩崖类作品的极佳范本。与正字相对的反文石刻,虽然没有很强的艺术生命力,在南朝后基本没有再出现,但作为那一时期特定的产物以及其罕见性,还是值得了解研究的。客观地讲,对于印刷的启发,也有直接的影响,这种反书反刻从左到右的刻法,与之后的雕版印刷几乎完全一样。只要在华表上涂色,然后敷纸进行刷印,印在纸上的便是正体顺读的印刷品了。据载,这反书倒读的阴刻华表,是为了印下来送给参加祭祀的官吏作纪念品用的。[9]可以说,在华表上刻反书倒读的文字,其用途是很明显的,对后世有一定的影响。足以证明,早在公元六世纪初的南朝梁代初,中国可能就已经出现了用反刻文字取得正体文字的木版雕印技术了。
梁武帝萧顺之建陵石刻是中国古代艺术的瑰宝,它闪烁着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光辉,彰显了我国古代石刻艺术的杰出成就,也反映了中国古代人民高超的技艺和智慧,其史学、美学及书法价值不言而喻,尤宝重之。
注释
[1]邹厚本.《江苏考古五十年》.南京出版社.2000:287.
[2]张影,邬晓东著.两汉祭祀文化研究[M].哈尔滨:哈尔滨工程大学出版社,2017.11.
[3] 孟斌著.历代帝王陵墓[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6.10.
[4]江苏省六朝史研究会编.六朝史论集[M].合肥:黄山书社,1993.09.
[5](清)康有为原著;李廷华辨析.《广艺舟双楫》辨析[M].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17.12.
[6]栾保群主编.书论汇要 上[M].故宫出版社,2014.12.
[7]刘谨胜,刘诗编著.江苏碑刻[M].北京:中国世界语出版社,1994.12.
[8]巫鸿;郑岩主编.古代墓葬美术研究 第4 辑[M].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2017.06.
[9]张树栋,庞多益,郑如斯等著;郑勇利,李兴才审校.中华印刷通史[M].北京:印刷工业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