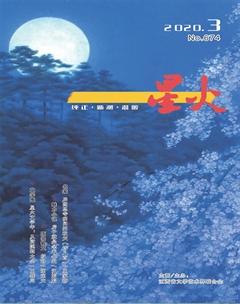木荷花开
伍忠红,江西南康人。文字散见于《中国校园文学》《现代青年》《今朝》等报刊,作品偶有获奖,诗歌入选《2018年江西诗歌年选》。
一
五月,老屋场的后山被一种小小的白色的花占领了。
那些花像轻扬的雪落入绿色的叶子间,风一吹,白色的波浪在山岭上起伏涌动,甚是壮观。我问母亲那是什么树花,母亲说是木荷。我很失望,这么普通的树怎么就受领了这样一个美丽的名字呢?
其实这种树我很熟悉,只是年幼不知其名而已。每次在树林里捡柴时,就能看见这种树成群结伙地长在山上。它没有马尾松那样粗壮伟岸的身躯,没有香樟树悠悠淡淡的香气,也没有桃李枇杷那样诱人的果实;大人打柴绕开它,我们小孩捡柴也不要它的枯枝,因为这种柴烧不着,在灶膛里“死火”。它太普通了,長在眼前,也被人视而不见。
木荷也结子,那是一种很坚硬的球形小果,黄褐色,成熟的果子从顶端张开裂成五瓣。母亲捡来一衣兜木荷果子,抽掉中间的柱头,再用火柴梗插进去,做成小小的陀螺。她拿起其中一个,拇指和食指捏住火柴梗用力一拧,然后迅速放开,木荷陀螺落在桌上就飞快地转动起来。看着陀螺旋转出优美的舞姿,我不禁高兴地拍起手来。
祖母从外面冲进来,一把抓起桌上的陀螺扔在地上,使劲地跺了几脚。她恶狠狠地对母亲说:“就知道耍这小把戏,没用的东西!”
祖母的样子把我吓住了。望着踩得一地零碎的陀螺,我伤心地哭了。母亲将我拉进怀里,脸贴着我的脸,泪水从我们脸间不断地往下流,冰凉冰凉的,不知是我的泪水还是母亲的泪水。
这是三岁起我记得的第一件事,它在我记忆里刻下了一道深深的痕。
二
母亲是祖母用十几块银元“买”来的。
祖母在父亲十岁时便守了寡,一场恶病夺去了她丈夫的生命,同时也留下了一堆债务。祖父去世后,倔强的她没有改嫁,带着父亲继续在老屋场生活。等母子俩将债还得差不多时,父亲已三十多岁了。父亲年轻时祖母舍不得让他外出学徒,后来落得身无长技,家徒四壁,没有哪家姑娘愿意踏进这个家门。祖母一咬牙,翻出她箱底的十几块银元(当年的陪嫁之物)卖了,把钱交到父亲手里。父亲就由媒婆领着穿过后山的林子,走进更深更远的一山村,从一个同样贫寒人家领走了母亲,带回到老屋场。
父亲领回媳妇的消息在老屋场不胫而走。屋场十几户人家倾巢而出,围在我家房前,他们像看怪物一样看着母亲,毫无顾忌地议论着,发出嘲弄的笑声。祖母气急败坏,没想到卖了丈夫大病时都舍不得卖的银元,娶回的却是这样一个儿媳。她躺在里屋的床上,大口大口地喘着气。屋外,嘲笑声一阵高过一阵,她感觉从今往后自己那张脸在老屋场没地方可搁了。
母亲左手向里弯曲,拖着一条瘸腿,歪斜地站在房屋前坪的人群中间。她垂着头,从脸红到脖子,浑身上下似乎有几万只蚂蚁在咬噬着她。此时,她多么希望刮起一阵大风,把她吹回到深山里,或有一口水井能让她跳下去。老屋场以这样的方式“欢迎”这位新成员。父亲看不下去了,从地上捡起一根木棍把那些看热闹的乡亲赶跑,给母亲解了围。
母亲是小时候打柴,从树上掉下来摔断了左手和右腿的。由于家境贫寒,山中缺医少药,她的父亲只是从山上扯来一些藤蔓,挖来一些根蔸,捣烂给她敷在伤处,后来就成了手曲脚跛的样子。到了婚嫁年龄的母亲,鲜有人上门提亲。一拖再拖,年二十七八,婚事毫无着落,还拦着后面的弟弟提亲。外祖父急得内心抓狂,恰好这时媒婆领着父亲出现了。外祖父看着眼前这个男子,年龄虽大了一点,但四肢健全,模样忠厚老实,便立即答应了。
母亲后来跟我说起这些事时,脸上平静若水。
三
在我看来,木荷唯一的优点就是易活,用客家话来说就是“烂贱”。只要有一点点泥土,甚至在石缝里,木荷都能扎下根,站住脚。
我家田头有两株木荷,直挺挺的,树冠伸展,枝叶茂盛,像两把张开的大伞。母亲说当年她在地里干活时,就带一把小竹椅放在树下,让我坐在那儿。在祖母眼里,母亲就是废柴一个,而且辱没门庭。然而,母亲不是废柴,她虽有残疾,但田里的各种农活,她总能想出办法去耕作。
我曾一遍遍目睹母亲种田的艰难。由于她的左手无法伸直,握不住农具,因此挖土时只好将腰弯得极低,右手握在锄头镰铲木柄的低端处,再用左腋夹住木柄的另一端。这样挖土力道是不够的,母亲须挖上三四遍,才能达到种庄稼的要求。当然,这样作田的效率也是极低的。种花生时,往往别人已经抽好沟培成了垄,而母亲却连地都还未挖好。祖母嫌她笨手笨脚,常对她一顿大骂。有一次,她冲到母亲跟前,一把把她推倒在地里。母亲不作声,强忍着泪水,抓住锄头,借势慢慢爬起来,又埋下头认真做活。
莳田时,因左手握不住秧苗,母亲就事先做好一个类似小孩钓青蛙的那种袋子。下田时,她将袋子挂在脖子上,用右手去袋子里取出秧苗插入泥里。边插秧边移动时,她那条残疾的腿就在水田里拖出一条条深深浅浅的沟,汗水和泥水裹着她的头发一绺一绺垂下来。
母亲做事很慢,但活做得细,田里的庄稼长得旺,收成也好。这虽让祖母在屋场挣回点面子,却怎么也改变不了她对母亲的成见。她就是块石头,不,是块铁,在祖母心里,母亲就是将她钉在耻辱柱上的那枚钉子。
四
在我们客家人的村庄,人们会在村头庄尾、溪流河边或田间地头,选取一株体型高大、枝繁叶茂的古樟、榕树、木荷等树拜为伯公树。伯公是客家的守护神,保佑着一方村庄百姓。在老屋场进入后山的路旁,就有一株郁郁葱葱的木荷。老人们说木荷至少百岁了,它自然就被老屋场拜为了伯公树。
母亲说起这株木荷,给我讲了个故事。
很久以前,有位小伙子去打柴,进山前来到这株木荷前,求伯公保佑他打柴顺利。可在山上砍柴没多久斧子就坏了,砍不了柴。小伙子很气愤,回到木荷树下指责伯公不灵。他把斧子扔在树下,要伯公把它修好,随后就回家去了。第二天,小伙子再来到木荷树下,惊奇地发现斧子竟然修好了。他连忙跪下恭恭敬敬地磕了三个头。
听罢故事,五岁的我起了一点小心思。我想起祖母对母亲的种种不好,想起邻里对母亲的百般嘲笑和捉弄,也想起因母亲我备受屋场小孩的欺凌……有一天,趁着天将擦黑,估摸着屋场的大人小孩都回到了家里,我就偷偷一人跑到伯公树下。我的心“突突”跳个不停,害怕此时有野兽窜出来,或飘过一团鬼火。不过,我最害怕的是遇到屋场那帮坏小子。他们一见着我就喊:“拐婆崽,拐婆崽,一瘸一拐,跌一跤,爬不起来。”平时他们这么喊叫,我会快速逃走,可如果现在被他们“逮着”的话,会坏我“大事”的。今天,我的“大事”就是向木荷伯公许愿!也真是幸运,没有遇上任何人。黑夜下的后山静悄悄的,木荷树默默地肃立在路旁,黝黑的树身闪着神奇的光,好像在等着我的到来。我跪在伯公树前,心里默念:“求求伯公保佑母親手脚好起来,不让祖母这般对待母亲,求求伯公让乡亲不再嘲笑捉弄母亲,让那帮坏小子不再欺负我……”我恭敬虔诚地磕上三个头。许完愿,我心里非常高兴。也许回到家,或明天一早醒来,母亲就恢复成了一个正常人,行走自如,而祖母、邻里也能善待母亲。
见我出门未归,家里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祖母骂骂咧咧,不断指责母亲。母亲似乎心有灵犀,径直走向后山。看着一个黑影一瘸一歪地走来,我赶忙跑过去,在黑暗中抓住那只熟悉的右手。母亲从我颤抖的手中体察出我的兴奋和恐惧,轻柔地说:“小孩子夜里不要乱走,要不,坏人会把我家南南带走的。”
晚上,我依着母亲躺在床上,向她说出了我的秘密。母亲搂住我笑着说:“傻孩子,我还没把木荷的故事讲完呢。”其实是这样的,那天傍晚,邻村一位铁匠从伯公树下经过,看见树下有把斧子,就捡起来带回了家里,把它修好了。晚上铁匠肚子一阵绞痛,他想也许是捡了那把斧子,伯公这么惩罚我吧。于是他连夜将斧子送回了树下。
“世上哪有什么神呀仙呀帮你,一切都要靠自己去努力的。”
五
母亲正是用她的努力改变她在老屋场的处境的。
无论什么时候,母亲见到谁都笑盈盈的(在我看来这是卑贱、讨好的笑)。家门前的桃李枇杷成熟时,哪家小孩打旁边经过,母亲都会摘一大捧给他。有时,她还亲自给每家每户送上一些。地里摘下的豆荚青菜,她也会这家给一把那家送一把。邻里有事,只要在母亲面前吱一声,她能搭把手的,都会热心去做。
却未见老屋场投桃报李。
我亲历过母亲一次挑大粪的事。那时我尚小,跟在母亲后面。她挑不了满担,只能挑个半桶。第一担很顺利。当母亲挑着第二担走在田埂上时,被草丛里的一根树枝绊倒了,重重地摔倒在圳沟里,粪液溅得她满身都是,样子狼狈极了。此时田地四周却响起了哄堂大笑声。母亲艰难地爬起来,泪水从她的眼眶大颗大颗滚落下来。我虽年幼,也能看出,树枝是有人故意藏在田埂草丛中的。
更为可笑的是,只要哪家地里少了南瓜茄子什么的,或哪家屋里不见了什么东西,他们便会把怀疑的目光投向母亲,指桑骂槐。在他们眼里,贫穷、残疾就是小偷的代名词。面对这些不堪入耳的咒骂,母亲不回骂、不辩解,也不自证清白。
祖母的恶言恶行、乡邻的嘲笑捉弄,渐渐在我心中锻造成一把钢刀。这把钢刀在母亲讨好的笑容里不断地磨砺着。我想终有一天我会亮出钢刀,让老屋场所有的人看到它的锋利!
我的这种想法无意间在母亲面前流露过。母亲说:“南南,我有残疾不受奶奶和乡邻待见,他们用言语和行为伤害我,但是我想,只要我努力让他们看到我内心的真诚、善良,他们就一定会认同我、接纳我的。”固执的我根本听不进母亲的话。我愤愤不平地历数着祖母和乡邻的恶行,被母亲厉声打断:“够了!你小小年纪,总记恨别人的不好,你不会有快乐的!如果你以为报仇就是对我的报答的话,我一辈子都不要这样的报答!我要的是你顶天立地做人,干出一番事业来,让别人尊敬你的同时,也尊敬你的母亲!”
第一次见母亲如此生气,我不敢做声。是母亲把我从悬崖边拉了回来。那时起,我发誓一定要奋发图强,长大后让母亲过上体面的生活,找回尊严。
我的家乡处在两山间一条狭长的山谷里,可耕作的田土很少,地里打下的谷子不够吃。每年青黄不接时,村民要靠买零米度日。母亲嫁入我们家之前,为度过粮荒,通常是父亲上山打好一担柴,逢集时挑到圩场上卖,换点米钱。有时柴不好卖,只好挑回,之后几日的吃食便无着落。母亲嫁来后,这种情况就此改变。
一年到头,除雨雪天,母亲基本都在地里。家里田少,只要看上某处山脚或缓坡,母亲就将它开荒,整成一畦一畦的田,种上番薯豆子之类的作物。她也会在无法开垦的石堆缝里,用小镢头挖开一个小坑,点上饭豆、绿豆、黄豆种子,再撒上一撮草木灰,用土埋好。每年她从开垦的荒地里都能收获大包小包的豆子,逢圩日就让父亲提到圩场上去卖,嘱咐他卖得的钱不要乱花,存起来买米或缴孩子学费。卖不完的豆子,母亲就用瓮装好。房间里,总是整齐地摆放着大大小小装满豆子的瓮。
秋天,我最喜欢跟在母亲后面去拾捡胖嘟嘟、红粉粉的番薯。挖回来的番薯在家里某个角落堆成一座小山,这些番薯也是我们果腹的口粮。
记得七岁那年,天异常干旱,庄稼几乎绝收。我们家因为前些年遗留下一瓮瓮的豆子,得以勉强度日。得知屋场其他人家日子难以为继时,母亲做出一个决定,将家中所有的豆子平均分成十几包,送给屋场十几户人家。祖母气得直骂母亲败家子,并竭力阻拦。这一次,她没有屈服。母亲叫上父亲帮她一起抬着这些豆子挨家挨户送去,还特意让我跟在后面。我很不解,也很不情愿:“他们对你这样,你干吗还送豆子过去呢?”母亲说:“其实,这点豆子也起不了很大的作用。不过,困难面前,能帮别人一把就帮一把吧。”
我永远不会忘记,当我们敲开一扇扇门,当母亲以她招牌式的笑容(我第一次认为这不是讨好他人的笑)出现在一户户门前,当母亲把一袋袋豆子递到乡亲们手里时的情景。他们先是惊讶,难以置信,然后拉着母亲的手不住地说谢谢。那一天,也是我第一次昂着头出现在屋场那些小孩面前。
渐渐地,老屋场对待母亲的态度在发生改变。再硬的石头,柔软善良的水也能流得进去。
六
我出生之后,父母觉得家境如此,就不再要孩子了。可我八岁那年,母亲意外怀孕了。父亲想让她流产。但祖母死活不许,她认为流产会招来血光之灾,会让家里倒八辈子的大霉。他们没能拗过祖母,就这样我便有了妹妹。妹妹的到来,让家中生活更加困顿不堪。妹妹两岁时,父亲在家待不住了,要去工地上做小工。出门不到三个月,家里出了大事。祖母在山谷打秋草时,不小心从坡上滚了下来,再也起不来了。母亲一瘸一拐跑到屋场,央求几个身强体壮的后生抬起祖母奔向了十几里山路外的镇上卫生院。
祖母下肢瘫痪,中风了。我清楚地记得,躺在床上的她紧闭嘴唇,眼睛里充满了恐惧。她一定是想到余生将要靠别人服侍度过,而她仅能依靠的又曾是她伤害至深的人,今后自己一定会遭受种种刁难,甚至百般折磨,而心中战栗不已吧。乡亲们觉得母亲报复的时候到了,他们很清楚这些年来祖母是怎样对待母亲的。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祖母的突然中风,我没有丝毫难过,反而有些幸灾乐祸。母亲觉察到我内心的想法,沉下脸说:“南南,虽然奶奶待你我不好,可再怎么说她也是你奶奶。她现在病成这个样子,我们应该原谅她,善待她。善才会有善报!”
母亲根本就不是乡亲们和我想象的那样!
自此,给祖母翻身、擦洗身子、端屎、接尿,每一样母亲都做得细心周到。她还经常叫上我一起服侍祖母。每日三餐,她必定是让我把饭端到祖母跟前。在母亲的影响下,我心里慢慢地生出了一点点与祖母的亲情,甚至对这个躺在床上的瘦弱的老人有了一丝丝怜悯。
得知祖母生病,父亲从工地赶了回来。看到在床上躺了近三月的祖母,身上干净整洁,也没生褥疮,他非常欣慰。蹲在床边,祖母拉着父亲的手说:“儿啊,是秀给我捡回的这条命。没有她,我就再也见不到你啦!”父亲拍着祖母的手,说:“娘,你安心养病吧,一切有秀呢。”几天后,他放心地返回了工地。
母亲这般服侍祖母让乡亲们大感意外。他们由衷地称赞母亲,敬佩母亲。多年以来,母亲的故事在老屋场一代一代流传,她也成了老屋场一代一代效仿的榜样。
一年后,祖母尊严体面地走了。那时父亲还在广东某个工地上。母亲请人去镇上的邮电所给父亲拍了份电报。那年代,一份电报至少三天才能送达,而父亲坐车回家还要两天。屋场的习俗,逝者须在三天内下葬。等不及父亲回来,母亲操持了祖母的葬礼。她请主事,报亲戚,置棺木,请道士,做法事,一切都安排得妥妥当当。乡亲们见证了母亲的干练,也由衷地感叹母亲的孝行。
五天后,父亲回来了。他在路上闻知母亲为他的母亲操持了一场体面的葬礼,也一路听到乡民对母亲不绝的称赞。他来到祖母坟前,扑通跪下,大喊一声:“娘!”磕了三个响头。他起身转向身旁的母亲,又扑通一声跪下,“秀,你是我们家的大恩人。”最后他对我们兄妹俩说:“你娘是个大好人,如果你们以后对你娘不好,天地不容!”
母亲此时已泣不成声。父亲紧紧地抱住她。母亲伏在父亲的肩膀上,终于嚎啕大哭起来。这是我第一次见母亲哭得如此酣畅淋漓,眼泪如此肆无忌惮。
周围的乡亲哭了,妹妹哭了,我也哭了。
我十五岁那年八月,一场家族遗传肝病带走了父亲。这对我们家是致命的打击。残弱的母亲如何支撑得起这个家?其时,我已收到县重点高中的录取通知书。我觉得自己已是一名男子汉,该由我来肩负养家的责任了。夜里,我来到母亲床前,只见昏黄的灯光下她默默地躺在床上,眼睛死死地盯着瓦梁。我对母亲说我不去念书了,我要去打工。母亲一听,支撑着从床上爬起来,扬起手给了我一个耳光。这是她唯一一次打我。
“你以为这是负责任的表现吗?你要是真正负责任,就该去努力读书,去考学!家里的事我会安排好的!”
母亲又一把把我拉进怀里紧紧地抱住我。我不禁大哭起来,母亲也哭了。那一夜,我们母子的哭声穿透了老屋场漆黑的夜空。
九月,我离开了朝夕相处的母亲,开始了高中住校生活。从此,生活的重负就压在了母亲残弱的身上。所幸,母亲在老屋场结下了人缘,每当农忙或有干不了的重体力活时,乡亲们都会主动来帮忙,并且时常接济我们家。
七
大学毕业之后,我在南方的城市找了份工作,打拼几年之后结了婚。每每跟妻子谈起母亲时,她都听得两眼泪汪汪。她说:“南子,我们一定要对妈妈好!”
妹妹考入大学后,我把母亲从老屋场接了出来。刚来的那段时间,母亲很不适应,睡不慣有席梦思的软床。在嘈杂拥挤的人群和车流中,她无所适从。城市尘土腥味的空气让她呼吸急促、胸闷不适,也让她对老屋场起了深深的眷念。所有的这一切,她隐忍着,尽量不在我面前表露出来。但母亲就是母亲,经过一段时间顽强的适应,她又像后山上的木荷一样,在城市落下了根。
一天吃饭时,母亲说:“最近,我去公园走了走,发现里面种了几排木荷。”我很诧异,心想这么普通的树也入得了公园的“大雅之堂”?饭后,我给一位园艺界的朋友打了个电话,问起这个事。朋友说木荷其实并不普通,它是一种美丽的观赏林木,很多城市在路旁或公园里都种有木荷作景观树。此外,木荷很难烧得着,具有良好的防火效果。将它混种于其他林木之中,或以它为主体,种成防火林带,能够起到很好的防火效果。
“它还是制作家具的良材呢!”这个我知道,家乡小县便是远近有名的“中部家具之都”,以生产各式家具而著称。用木荷做出的家具,木纹细致,美观典雅。
晚饭后,搀扶着母亲来到公园,我们从木荷树下慢慢走过。又是五月,正值木荷花开。看着树冠上缀满一朵朵洁白的小花,我眼前又浮现出老屋场后山那一片波涛起伏的木荷林。
母亲对我说:“南子,我百年之后,你把我的骨灰撒在老屋场后山的木荷树下吧。”
我郑重地点了点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