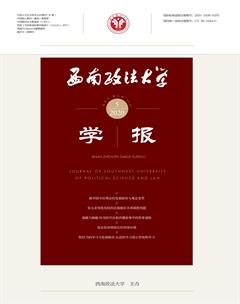宋元亲邻优先权的法源地位及其制度功能
摘 要:本文考察宋代以来传统亲邻优先权在不动产交易中的法源地位,以“官府-民间”“成文法-习惯法”“优先权人-买受人”三大关系为切入点,探讨亲邻优先权的法实现及其制度功能,主张该项制度能有效维护家族产业稳定、增强社会治理绩效,与交易自由、交易安全目标亦能达成利益均势。
关键词:亲邻优先权;法源地位;限定条件;制度功能
中图分类号:DF09 文献标志码:A
DOI:10.3969/j.issn.1008-4355.2020.05.02
历史法学派奠基人萨维尼主张:法律是“发现”而非“发明”。其阐述逻辑是:法律是民族精神的产物,是道德信念的表达,进而外化为习惯,最终,习惯被法学家、法官、立法者所发现并以权威方式予以确认,成为法律。庞德充分认可这种观点,但又另行主张:法律既是被“发现”的,也是被“发明”的。法律既是基于经验、道德、教化、经典文本产生的具体规则,也是基于理性需求进行的抽象立法活动。①相较之下,萨维尼与庞德的逻辑基点显然不同。萨维尼注重的是习惯的法源地位问题,庞德关注的则是习惯成为法源后的阐释解读与适用问题。以个案考察,宋元的亲邻优先权之“亲邻”标准并非是官府或立法者的“发明”,而是对民间习惯的“发现”和认可。一旦官方文本标准与习惯法文本标准出现矛盾,地方官都会遵循地方通行之“俗例”而非普适性的“法律”,显示了对民间自治法的优容与重视。
本文考察宋元亲邻优先权在不动产交易中的法源地位,以“官府-民间”“成文法-习惯法”“优先权人-买受人”三大关系为切入点,探讨亲邻优先权的法实现及其制度功能,主張该项制度能有效维护家族产业稳定、增强社会治理绩效,与交易自由、交易安全目标亦能达成利益均势。
一、亲邻优先权的法源地位
与西方近代以来的个体主义、自由主义立场和路径不同,传统中国社会治理并非遵循“个人-国家-社会”三大主体互动模式,而是典型的“家-国”二维空间。个人人格、意志、利益以家为单位,为家长、族长所掩蔽。此点虽然与西方理念和进路扞格不入,可诟病者多多,但从长时段考察,该制度毕竟维系了千余年的社会稳定与和谐,防范了人性的趋恶化和个体的极端行为,也成为社会秩序形成的基石,最终耦合中央政权的统一权威,成为社会治理、国家治理的一体化模式。
即如亲邻优先权,本属于民间习惯法,是为了确保家族财产安全而设立的防范机制,后来为官府所认同,成为一种成文法与家族自治法共同保护的制度。所谓亲邻优先权,系指业主在处分自有不动产物业时,亲族、邻佑在同等条件下享有优先购买权;在不动产出典或回赎时,亲族、邻佑于同等条件下享有优先典买权或回赎权。亲邻优先权主要规范亲族、邻居之物业典卖行为。所谓“物业”,系指田地、房屋、墓茔等不动产;所谓“典卖”,包括出典、出卖两种民事行为,因其法律程序相近,古代经常连用,此处一并论及;所谓“亲邻”,即服亲、邻佑之谓。亲邻优先权作为一种历史性存在,既在民间赢得了广泛的生存空间,还获得了官府的积极认同,显然属于马克斯·韦伯批判的中国式“无所不能的传统、地方习俗、与官方具体的私人恩惠”[ [德]马克斯·韦伯:《韦伯作品集V中国的宗教 宗教与世界》,康乐、简惠美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26页。]。
亲邻优先权为什么会存在?为什么会与韦伯所谓的“理性的法律与理性的协议”背道而驰?[ [德]马克斯·韦伯:《儒教与道教》,王容芬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58-60页。]真正的原因应当与中国家族制度的连续存在着必然的价值关联。韦伯敏锐地意识到这一点,认为宗族的作用在西方中世纪时已然烟消云散,而在中国却从未断绝,还方兴未艾。家族既是最小的行政管理单位,也是一种经济合股方式。具有难以克服的伦理性、封闭性、自足性特征,与西方城市法、共同体、市民阶层、自治行会、政治盟会相去甚远。[同上注,第140页。]
韦伯对儒教的“俗人伦理”的理论偏向,显然少了布洛赫和汪德迈等学者的客观与科学态度。布洛赫《封建社会》专注于历史本身,但从未以自身文化的演化尺度衡量其他文化。通过历时考察,布洛赫发现欧洲亲族义务圈于十三世纪后渐次缩小,亲属联盟亦不断被削弱,政府当局甚至会强制推行发誓脱离亲属团体,最终导致了家族的式微甚至解体,强大的公权力组织替代了传统家族力量,最终形成了“国家-公民-社会”的三维主体。[ [法]马克·布洛赫:《封建社会》(上卷),张绪山译,郭守田、徐家玲校,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240-243页。]相形之下,中国家族之历史命运及其与国家之关系迥异于西方发展路径,不仅保有强盛的生命力和独立性,还能与国家和谐共荣,互动互通。有鉴于此,法国著名汉学家汪德迈(Léon Vandermeersch)提出了两个极为重要的观点:一是中国家族不但是人口再生产(institution)的基本单位,还担负着经济、教育甚至政治的功能,中国的一切规范也都是从家族规范中演绎、改造而来;二是从根本意义上讲,中西文化是“差异性文化”,不能用自有标准去解释、评价他国文化。[ [法]汪德迈:《中国文化思想研究》,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6年版,第13页。]
揆诸亲邻优先权制度本身,宋元以来的官府在法源地位上一般采取三种策略,无论何种策略,都是最大程度认可其调节功能并赋予其合法性。
(一)直接上升为成文法
日本学者内田智雄、天野元之助认为宗族“先买权”源自于古代宗族共有制,而岸本美绪则认为亲邻优先权“是民间层次上人们为了对付土地自由流通带来的危险而构成的一种制度装置”[ [日]岸本美绪:《明清契约文书》,载王亚新、梁治平编:《明清时期的民事审判与民间契约》,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301页。]。可谓破的之论,但岸本认为亲邻优先权仅限于民间层次,于今尚可,于古则不尽然。
揆诸宋以来成文法,对亲邻优先权均有与家族自治法相同的行为规范。如亲邻优先权的顺序与范围,据《宋刑统》规定:“应典、买、倚当物业,先问房亲;房亲不要,次问四邻;四邻不要,他人并得交易。房亲着价不尽,亦任就得价高处交易。如业主、牙人等欺罔邻、亲,契帖内虚抬价钱,及邻、亲妄有遮恡者,并据所欺钱数,与情状轻重,酌量科断。”《宋刑统》卷十三《户婚律》,“典卖指当论竞物业”条。由是言之,亲族不动产处分必先问亲邻;亲邻在同等条件下不予典买或所批价钱低于业主所邀约价格,业主得以合意价格与旁人交易;如亲邻人等抑价典买阻碍正常交易,或业主、牙人共谋虚高价钱,欺哄亲邻,均需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根据开宝二年(969年)官方文本,亲邻优先权的具体顺序和范围如下:“凡典卖物业,先问房亲;不买,次问四邻。其邻以东、南为上,西、北次之。上邻不买,递问次邻;四邻俱不售,乃外召钱主。”[ 《宋会要辑稿II》,刘琳、刁忠民、舒大刚等点校, 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6805页。]延及南宋哲宗绍圣元年(1094年),亲邻优先权之亲邻序位与范围均有限缩,即典卖田宅“应问邻者,止问本宗有服亲,及墓田相去百步内与所断田宅接者”[ 《文献通考》卷五《田赋考五》。]。元代涉及不动产典卖时,继承了这一精神。至元六(1269年)年中书省复令太原路依“旧例”处理民人典卖田宅物业欺瞒亲邻典主、亲邻典主故行勒减价钱及勒要画字钱物等案中,就亲邻之顺序、范围再次明申:“诸典卖田宅,及已典就卖,先须立限取问有服房亲(先亲后疏),次及邻人(亲从等及诸邻处分典卖者听),次见典主。”[ 《元典章》卷一九《户部五·田宅·典卖》,“典卖田宅须问亲邻”条。]
据此,物业典卖交易是否成功取决于亲邻是否行使优先权。所谓亲邻顺序,
以亲为上,亲以五服等次别亲疏;邻佑次之,邻以东、西为上,南、北次之;典主或买受人之典买、买受权利因亲邻行使优先权而丧失或因亲邻放弃优先权得以实现。此种风习一直延续至明清以迄于今天之民间社会。明代民间契约如嘉靖三十年(1551年)六月《魏佛清卖苗田契》:“在城住人魏佛清续置亩田二段……今来要物使用,托中召卖,先尽房亲邻佑人等,各不成就,遂中引至本里邓法富出头承买。”[ 傅衣凌:《明清时代福建佃农风潮考证》,载《福建文化季刊》第1卷第1期,后重刊于傅衣凌:《明清农村社会经济》,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1年版,第173页。]清代民间契约如乾隆九年(1744年)(五月《叶林卷卖地契》:“立卖断骨文契字人外里风池坊叶林卷,承兄续置分得民田一段……且卷今因缺少银两,完编无从所办,情愿托中说谕,即将前田先问亲房伯叔兄弟人等各不承受后,凭中引到大康文学坊杨士朝边承买为业。”[ 杨国桢:《清代闽北土地文书选编(一)》,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2年第1期,第116页。]
上举二例说明:宋明以来之物业典卖亲邻优先权既属于家族自治法规定,也属于法定强制规范。至迟在明代,亲邻优先权已形成一项强有力的缔约条款,民间社会已将国家律令直接吸纳涵化入合同中,成为确保合同生效的必备条款。
(二)以习惯补足正式法源
亲邻优先权一旦进入成文法保护范围,其相关保护手段亦随之成为官府判案直接援引的依据。但正规法源仅能解决其核心功能实现问题,对于各类程序性要件,法律不可能面面俱到,只能通过亲邻优先权民间习俗补足。以业主告知义务为例,宋代判词明确引用民间习惯,要求业主欲出卖、出典物业,必须向亲邻人等履行告知义务。习惯法之精髓亦为成文法全盘采纳吸收。如对于处分墓地的书面告知义务,习惯法既有严明的规范,而据官员的判词,法律亦有完全相同的法定义务:“诸典卖田宅,四邻所至有本宗缌麻以上亲,其墓田相去百步内者,以帐取问。”[ 《名公书判清明集》,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322页。]
习惯法与成文法共同强调业主之告知义务,其原因无非有二:一是保障亲邻之身份性优先权,杜绝争讼;二是保护善意相对人。按照家族自治法与《宋刑统》卷一三《户婚》“典卖指当论竞物业”条之相关规定:如当问亲邻而不问或竟至中人、业主典主共谋欺罔瞒昧亲邻,则需承担民事责任及刑事责任,其典卖合同归于无效且可能承担刑事责任。此种风习于诸多少数民族中仍有保留。据高其才教授之研究成果,壮族之土地买卖,由卖主找中人并先通知房亲,房亲无钱方能卖与他族。苗族的家族优先权表现得更明显,外族卖主即使已确立了田价,只要族内人所出价钱不低于外族买主,仍应由本族人收买。典权亦复如是,本族人的典权优于外族人,只有在房亲或邻佑所出典价低于外人时,业主方可外典,且典主、业主之典当协议必须由双方亲族作证,以绝后患。[ 高其才:《中国习惯法论》,湖南出版社1995年版,第331-333页。]
(三)协助施行
由上可知,无论是作为正规法律,抑或是作为“俗例”,亲邻优先权在宋代无疑获得了成文法的认同,要么成为正规法源,要么作为法律的补充,成为官府判案的补充法源。此点固然反映了亲邻优先权自身具有合理性的质素,也反映了官府务实、亲民的优良品行。按照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真正决定制度绩效的是以个性化知识为基础的非正式制度安排。如果忽视传统、习俗等非正式制度,强行移入正式制度,不仅会毫无效果,还可能适得其反。[ [美]道格拉斯·C·诺斯:《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刘守英译,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49-50页。]
即便家族自治法未能上升为成文法,但如其实施过程中,需要官府予以配合、协助,官府一般会积极施为、妥为护佑。以亲邻优先权之保护程序而论,自汉至唐,都特别注重亲邻署契,即于物业出卖、典卖契约上签押,以杜绝后患。宋明以来,亲邻优先权入法,官府对其保护更是不遗余力。
1.缔约程式与文本注籍。中国契约文书定型较早,日常交易亦以质剂、要书、合同作为确定双方权利、义务的根据。就笔者所见,关于亲邻优先权在物业典卖中官府要求作为合同条款并呈报官府备案,始于北宋太平兴国八年(公元983年)赵孚之上书:“庄宅多有争讼,皆由衷私妄写文契,說界至则全无丈尺,昧邻里则不使闻知,欺罔肆行,狱讼增益。请下两京及诸道州府商税院,集庄宅行人,众定割移典卖文契各一本,立为榜样。”[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四,“太平兴国八年三月乙酉”条。]但年深日久,亲邻争占,有的当事人隐没契书,商税院检寻不到。有鉴于此,宋真宗乾兴元年(1022年)又晓示天下,扩大了合同文本的呈报数量:“应典卖倚当庄宅田土,并立合同契四本:一付钱主,一付业主,一纳商税院,一留本县。”[ 《宋会要辑稿12》,刘琳、刁忠民、舒大刚等点校, 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7464页。]
司法实践中,官府判案亦以契约为主要凭据。《名公书判清明集》中多有“典田宅者,皆为合同契,钱、业主各取其一。此天下之所通行,常人所共晓”[ 《名公书判清明集》,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149页。]
等语,说明若非有合同契约为据,很难胜诉。同时,契约也并非经双方当事人合意便能成立生效,契约立定后一定时期内,必“勘会业主、邻人、牙保、写契人书字圆备无交加”[ 《宋会要辑稿12》,刘琳、刁忠民、舒大刚等点校, 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7469页。]
,“执分书或租契赴官”按验亩角税亩分数之实”同上注。。 只有经官检验无误并交纳契税后,官府方“当官注籍,给凭由付钱主”同上注。 ,并于原业税租、免役钱等过割之后,官府始得在契书上加盖官印,予以确认,至此合同方告成立并产生约束力。
上述系列程序统称为“经官投印”。值得注意的是,之所以要求业主、邻居、牙保、写契人均需到场,是为了确保合同内容的真实性,如以后发生追夺或争讼之事则由上述人等负连带责任;同时邻人到场也是为了确保其经官放弃优先权。据宋代《州县提纲》卷二:“田户典卖,须凭印券交业,若券不印,未及交业,虽有输纳钞,不足据凭。”[陈襄:《州县提纲》,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4页。]由是言之,官府理论田宅争讼案件,以官府印契(而非私家白契)和买受人管业作为确权根据,也以此作为亲邻优先权享有人行使或放弃权利的标准,此即所谓“交易有争,官司定夺,止凭契约”[ 《名公书判清明集》,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153页。]。
2.知押、签押与合同效力认定。物业典卖契约必须由亲邻人等签押后,方可确保合同成立生效并免去后顾之忧。亲邻人等在业主转移不动产的合同契约上签署名字或押画手印,宋代称为“知押”。《名公书判清明集·户婚门·争业类》所载“莫如山诉莫如江案”中,莫如山以莫如江所签契照无其本人之签押而引发诉讼到官。[同上注,第152-153页。]
亲邻人等的知押和中人之签押都具有证约和担保两种功能,但亲邻之知押更有一种隐涵功能,即作为知情者,如其本人系优先权人,其证约、担保已默示其放弃优先权并承认业主对物业的处分结果。土族习惯法中买主付价金包括地价和三份钱,是在地价之外另备三份钱色,一份给中人,一份付写契人,一份送卖主之亲房人,就其原因是当地习惯法要求不动产买卖必须卖方亲房画押方能生效。[ 高其才:《中国习惯法论》,湖南出版社1995年版,第333页。]
3.公示公信效力之认定。从远古到现代,不动产买卖均以一定程序证明交易已经完成。上古的沽酒到今日民间宴饮,实质上都起到了物业典卖的公示公信作用。一定程度上讲,官方的印契只能证明合同成立并生效,而对于亲邻优先权而言,沽酒或宴饮则更具物权公示性并取得更高的公信力。
滋贺秀三在探讨“中人”的几种功能后,提出了为酬谢中人之宴会具有公告性质。美国学者宋格文、郭锦等人在论及中国古代契约“证人”(“中人”)的作用时,也阐明其证约性质,并进一步提出“程序的公开性和对证人及文书的强调,使证据起到了实际证明的作用”,并且沽酒、宴饮等契约仪式与远古盟誓仪式一样,“具有道德约束力和宗教约束力”[ [美]宋格文:《天人之间:汉代的契约与国家》,载高道蕴等编:《美国学者论中国法律传统》,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75-177页;[美]郭锦:《法律与宗教:略论中国早期法律之性质及其法律观念》,载高道蕴等编:《美国学者论中国法律传统》,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90-94页。]。如壮、苗、藏、彝、土、侗各族之“吃中”或“亲房谷”习俗,都是为买卖的合法性、有效性提供公示公信手段;同时,买方之所以愿意于正价之外另舍财宴饮或馈送卖方亲族,也不仅仅是使其将来履行作证义务,而是藉此逆推卖主之亲房邻佑放弃优先权,可谓一石三鸟,曲尽其意。
二、亲邻优先权的公力救济与例外
(一)利益博弈与文化迫力
亲邻优先权就是族内不动产交易过程中的利益博弈,属于一种社会行为。冯·诺依曼与摩根斯坦之博弈论主张“人生就是战略拼盘”,所谓社会行为就是以得失分配为目标的勾心斗角。格尔茨反对这种纯功利主义的泛滥,更推崇“生活就如一套规则”,主张社会就是由既定习俗和适当程序构成的紧密无缝的行动、反应世界。[ [美]克利福德·格尔茨:《地方知识》,杨德睿译,商务印书馆 2016年版,第38、40-41页。]在亲邻优先权推行过程中,“官府-民间”“成文法-习惯法”“优先权人-买受人”三大关系始终处于“博弈-平衡”状态,以实现各方利益的均衡,即便偶尔有欺蒙、妄冒等情节,很快会遭遇真正权利人的阻却,最终维持利益均势。
这种规则的力量显然来源于格尔茨所谓的既定习俗和适当程序。实际上,从其力量来源考察,亲邻优先权及其所维护的利益均势更接近于马林诺夫斯基的文化迫力理论。马林诺夫斯基在研究语言、法律、道德等社会制度的时候,认为语言、法律、道德作为文化的有效组成部分,绝不是简单的工具体系,也并不产生于自身内部,而是产生于特定的语境(context of situation),是特定风俗和精神文化的有机组合。所谓精神文化,即是人类通过习得、协力,获取规则、习俗、法律、规矩并完成自我注塑、形塑的地方性、集体性组织与活动。人类正是凭借这些规则、习俗、法律、规矩以及由此产生的文化迫力,实现社会团结、文化传递、群体化生存。[ [英]马林诺夫斯基:《文化论》,费孝通等译,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6-7、96-97頁。]
(二)官府的公力救济
考察“民间-官府”对待亲邻优先权习俗的态度可以有效印证马林诺夫斯基的理论。亲邻优先权在物业交易中受到侵害,一般是指业主不履行告知义务,擅立合同文书并过割离业,或典主、钱主与业主共谋欺瞒亲邻,此种行为在宋代属“违法交易”,亲邻人等可经官通过两种渠道进行救济并恢复、实现其优先权:一是以亲邻之法请官府发文追夺,亦即确认物业交易合同无效,双方返还。物业追夺后由优先权人收买;二是以亲邻之法之优先权,以典出之价回赎出典物业。
其中,最典型的是欺蒙。所谓欺蒙,是指伪造揩改契约、鼓诱卑幼、瞒骗族亲、地邻之类的不法行为,官府对此处罚极重,民间习惯对此也严加禁断。《名公书判清明集》所载判词中引大量案例,其中“伪冒”“违法”交易各条占相当比重。如“黄桂子与杨迪功重叠交易田户案”,伪作四至内有杨氏祖墓,以求优先取赎
;[ 《名公书判清明集》,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318-319頁。]如黄宗智私立伪契,意欲占田,被判“勘杖一百,真契给还,伪契毁抹附案”[同上注,第306页。]。至于欺瞒本家,是指无视法定的亲邻优先权,不令亲邻知闻而私下交易。宋代“洪百四案”更为典型。洪身病且死,却无送终办丧之资,其邻居张光瑞图谋洪氏产业既久,“乘人将死,夺人屋业”[同上注,第132页。],唆使其子写成契书,以其婿出名为契头,勾结洪百四之兄洪百三以长凌洪百四之子洪千二、洪千五,抑勒谋图,事败垂成,为洪百四出继子周千二说破控官,且诬告张氏父子“惊死乃父”,吴安道判张光瑞及其子其婿均合断罪,业本当还主,因其诬告,被拘入官,以示薄惩。元代亦有相同案例,至大元年(1308年)十月,“冠州贴军户张著告正军周元,于大德八年欺昧本家,将泺下桑枣地五十三亩暗地卖与伊另籍军户房亲周二等为主。礼部议拟即系违例成交,拟合改政(正),令张著依价收赎。”[ 转引自孔庆明、胡留元、孙季平编著:《中国民法史》,吉林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504页。]
由是论之,官府对于违反亲邻之法的处理措施一般有三:第一,刑法断罪。对有过错一方,一般施以笞、杖、徒、流等刑事处罚,以彻底禁断此类不良交易行为;第二,追还本主,优先权人依照通行价格购买或收赎;第三,财没入官。对于双方均有过错的交易行为,视其情节轻重,以产业钱货入官,以示惩戒。于官府而言,违法交易中违背亲邻之法者,如买主明知业主当问邻而未问且与之交易,则买卖双方承担连带责任,物业还主,价钱没官并对双方各处杖刑。至元代,亲邻典主的知情权或出卖人的告知义务更有明文规定,其具体情况有如下几种:一是通过立帐“批退”或“批价”,以此种方法如实反映业主是否告知亲邻,后有详述;二是亲邻优先权权利人不在本地,业主应遣人请问;三是业主如未履行告知义务而私辄卖出,优先权人可在百日内依卖价收赎;四是业主虽然履行了告知义务但又故意抬高价钱,阻止亲邻人等行使优先权,私下又以低价卖与第三人,此种情况,法律允许优先权人百日内依卖价收赎;五是如业主与买主有欺罔情节或故延时日,勒掯价钱而竟与第三人成交,虽过百日,法律仍许优先权人依卖价收赎。[同上注,第87-88页。]
物业典卖亲邻优先权制度在中国古代社会通行并逐步完善,说明了其合理性和实效性。亲邻之法在宋代要求亲、邻二者必须重合,到元代则两相分离。[ 霍存福:《论元代不动产买卖程序》,载《法学研究》1995年第6期,第88页。]但其立法原意并未发生根本性改变。
(三)亲邻优先权例外情形
但不可忽略的是,亲邻优先权显属身份性权利,如一味强力保护,则很难实现善意第三人与身份权受益人之间的权利平衡。有鉴于此,官府在明文、强力保护的同时,亦对其进行严格界定并予以多重限制,藉此保护市场,平衡亲邻与买受人之间的风险负担和交易成本。
详而言之,亲邻优先权的受限体现在人、地、时三方面。
1.主体限定。据宋代之法:“所谓应问所亲邻者,止是问本宗有服纪亲之有邻至者。如有亲而无邻,与有邻而无亲,皆不在问限。”[ 《名公书判清明集》,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309页。]
又据宋代之令:“诸典卖田宅,四邻所至有本宗缌麻以上亲者,以帐取问。有别户田隔间者,并其间隔古来沟河及众户往来道路者,不为邻。”[同上注。]此种律令对亲邻优先权作了人、地的限制,即物业典卖中的主体要享有优先权必须是服纪之亲,同时其地产或房产必须相互毗邻,二者俱合始为亲邻,亦即血缘、地缘二者结合,方能产生物业典卖中的优先权,否则即为妄执亲邻,须受官府追索理论。《名公书判清明集》中“陈子万案”足以说明此种限制在宋代已为官府所重视:陈子万家产败亡,与杨世荣合谋,以亲邻之法取赎三十前出卖的田产,后被判“妄执亲邻”,“勘杖一百”[ 《名公书判清明集》,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310页。]。
2.时效限定。至于时间方面的限制分为三种:一是亲邻优先权之行使,自典卖之日起满三年以应问邻而不问提起诉讼,要求行使优先权,官府不许受理。即亲邻优先权之一般诉讼时效为三年,超过三年,官府不再强行予以保护;二是典卖中如合同当事人(契头)一方亡殁经三十年,享有优先权之人取赎亲邻物业,官府不许受理;三是业主立帐取问亲邻必在法定时间内作出意思表示,“若不愿者,限三日批退,愿者限五日批价。若酬价不平并违限者,任便交易;限批不满,故有遮占者,仍不得典卖。”[ 《元典章》卷一九《户部五·田宅·典卖》,“典卖批问程限”条。]
以上三种时效制度,既保障了买受人和业主交易的效率,又促使优先权人积极行使其权利,免去交易后的争讼之累,以获取交易的安全性。另外,对于收购赎典产者,元代规定收赎期限是百日,超过百日官府不予保护;但如系欺昧亲邻典主则例外,虽过百日之限,并听“依价收赎”。此条规定可谓是对优先权的一种合法性救济,但同时也构成对优先权的一种时效限制。
3.“归就不问”与“墓田为上”。作为亲邻优先权的另两种限制是“归就不问”和“墓田为上”两大原则。所谓“归就”,系指家族亲房间发生的不动产产权有偿转让。[ 张晋藩:《清代民法综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42页。]此种交易,亲邻不得主张优先权。《名公书判清明集·户婚门》中黄子真自讼将田产“卖与本家,自是祖产,不应更问亲邻”[ 《名公书判清明集》,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120页。]
,显见当时家族与地方习惯法均有规定,官府法律亦有明文,故引以为据。所谓“墓田为上”,于传统中国,墓茔和祠堂分别代表了家族、国家、社会三位一体的精神纽带,故物业典卖凡涉墓田坟茔与祠堂,当事人与官府均严谨缜密,恐坏人伦名教。因之,当亲邻优先权与墓田坟茔主人发生冲突时,自应以墓田坟茔所有人利益为上。范西堂(应钤)在一则判词中说得特别明白:“墓田之于亲邻两项,俱为当问,然以亲邻者,其意在产业,以墓田者,其意在祖宗。今舍墓田,而主亲邻,是重其所轻,而轻其所重,殊乖法意。”[同上注,第121-122页。]换言之,凡涉墓茔、祠堂之物业转让需限制亲邻优先权,即使买受人已为受并占有使用,其土地使用权仍受到重重限制。突出表现即墓地典卖,古代地契中必须载明“阴阳”,如地产契约中并未约定“阴阳一并在内”,则买受人仅得耕种、不得进葬。[ 《民商事习惯调查报告录》,台北进学书局1969年版,第599页。]此即所谓“业可夺,坟不可夺”[ 《名公书判清明集》,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324页。]。
三、亲邻优先权的制度功能
按照西方近代以来的产权理论,每一个独立的决策者可以通过相互承认、合作、交易实现资源的分配和权利的均衡,此即所谓契约自由与利益博弈。这是产权的政治哲学基础,也是产权道德正当性获得的前提。但依照纽约大学哲学、法学教授托马斯·内格尔的观点,这种正当性虽然在道德意义上确实具有無可反驳和反对的权威,但却未必能够契合一切交易行为,特别是身份性交易行为。对于身份性交易行为,因为道德、伦理的介入,或者财产属性、效能关联,必须进行依照偏倚性保护。[ [美]托马斯·内格尔:《平等与偏倚性》,谭安奎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37-40页。]亲邻优先权为什么入法?为什么需要对其进行偏倚性保护?按照斯梅尔瑟的经济社会学理论,经济理性只是一个变项而不是一种原则;很大层面上,经济理性也并不反映人类心理的全部,而是一个动态过程,是策略性安排。[ [美]尼尔·斯梅尔瑟:《经济社会学》,方明、折晓叶译,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41-42页。]
无论是内格尔的偏倚性保护,抑或是斯梅尔瑟的策略性产权安排,都能有力解释亲邻优先权产生的动力机制与目标定位:维护家族不动产的稳定。我们从如下方面评价亲邻优先权的制度功能:
(一)亲邻优先权是维系家庭、地方社会稳定的物质基础和经济前提
亲邻优先权是中国宗族制度的必然产物,也是实现内部治理的有效制度供给。宗族公有制以及严禁卑幼私积私蓄财产是中国家庭的长期传统,这就从根本上排斥了个体对财产之独立处分权,其交易行为必须以家族利益而非个体利益为重。此种宗族血缘经济结构与同居其财的家庭结构相互结合直接导致了亲邻优先权的产生。聚族而居的村落地缘结构又间接刺激了该制度的发展与成熟,并使之最终趋于定型化。
换言之,任何一种经济制度或法律制度都是为了寻求一种利益平衡,否则就会丧失其存在的基础。表面上看,亲邻优先权保护的确实是“至亲无断业”“业不出户”的封闭性、身份性交易制度。梁治平先生认为,亲族先买权“一直是土地自由转让的障碍”,亲缘关系使土地“卖而不断,断而不死”[ 梁治平:《清代习惯法:社会与国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61页。]。
此种观点言之大过。亲邻优先权是否必然导致交易不确定性,阻碍了土地的自由转让?对此必须持有理性的历史立场。首先,土地、房宅等不动产物业之亲邻优先权是相对的、受限的,而非绝对的、毫无条件的;其次,中国家族史中虽有同居共财近七百年者,但其族户之分散聚合则是常有之事。除去天灾人祸之外,正常的交易仍占主体部分。康熙一朝,江苏“百年田地转三家”,乾隆时,苏州“田地十年之间已易数主”,康乾盛世尚且如此,动乱年代更不用说。因此,真正阻碍中国古代土地自由流转的原因源自于“以末(商)致富,以本(农)守之”的观念形态,而非亲邻优先权制度。[参见叶显恩:《徽商利润的封建化与资本主义萌芽》,载中国史研究编辑部编:《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62-263页;傅衣凌:《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5、80页。]
亲邻优先权的产生基础与动力源自于家庭互助互惠、以有补无,以有余补不足,藉此维系家族的稳定乃至于社会的稳定。严野义太郎认为:西方讲求个人主义和对立斗争,而中国村落(实则是聚族而居的家族集团)则有一种互相合作的亲和性。内藤湖南则认为:中国社会是建立在进步的公产制家族制度之上的,无疑说明了亲邻优先权自有其存在的社会根基,其调控亦具有正当性基础。[ [日]岸本美绪:《市民社会与中国》,载王亚新、梁治平编:《明清时期的民事审判与民间契约》,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357-358页。]
(二)亲邻优先权有效节约了社会治理成本
就其大者要者而论,因传统多聚族而居,所谓“邻”,名义上指地邻、房邻,但就其身份仍多系亲族。亲族之间不动产的转让,手续简单,大幅度节约了交易成本;同等条件下的亲邻优先权使业主获得了同等收益,既增快了资金融通的速度,也分散利用了家族内部的闲置资金,各得其益;更重要的是,亲邻优先权可杜绝物业典卖过程中出现的欺昧现象,既稳定了物业的使用价值,也节约了不必要的争讼成本。
传统物业典卖中亲邻享有优先权,即亲族人等的优先购买权或优先收赎权。此类优先权系出于族亲身份,具有极强的排他性。为防止信息不对称所引发的内部争讼,民间习惯法层面发明了极具创意的“亲邻批退批价制度”。所谓“批退”,是业主将所要出典或出卖物业之事项以书面形式作出,邀引享有优先权之亲邻批退或批价,谓之“立帐”。元代至元二年(1265年)和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有两份立帐文书,录之于后,以资证明。[ 转引自孔庆明、胡留元、孙季平编著:《中国民法史》,吉林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470-471页。]
泉州路录事司:南隅排铺住人麻合抹有祖上梯己花园一段山一段亭一所房屋一间及花果等木在内并花园外房屋基一段,坐落晋江县三十七都土名东塘头村,今欲出卖□钱中统钞一百五十锭,如有愿买者就上批价前来商议,不愿买者就上批退,今恐□□难信立帐目一纸前去为用者。
至元二年七月 日帐目
立帐出卖 孙男 麻合抹
同立帐出卖母亲时邻
行帐官牙黄隆祖
不愿买人 姑忽鲁舍 姑比比 姑阿弥答 叔忽撒马丁
晋江县三十七都东塘头住人蒲阿友祖有山地一所,坐落本处,栽种果木。今因阙银用度,抽出西畔山地经官告据出卖,为无房亲立帐尽卖,山邻愿者酬价,不愿者批退,今恐无凭,立此帐目一纸为照者。
至正二十六年八月 日
立帐人 蒲 阿 友
不愿买山邻 曾大 潘大
借鉴今时民法理论分析,上引两份立帐文书,一份属于房亲优先权批退,一份属于不动产物业山邻优先权批退。批退人书名画押其上,说明了立帐文书本身的重要性。
值得注意的是,麻合抹开立帐目明码标价,而蒲阿友卖山则未标价。麻合抹邀引亲邻批价,从文意上看并非少于其所出价额就不可成交,尚有通融余地;而蒲阿友则请求山邻酬价,迹近于无保留底价之拍卖(withoutreserve),是知二者均属要约诱引性质。如亲邻批退,则不用进入要约承诺阶段。如亲邻批价,则属要约性质,若业主同意,视为承诺。如业主于价格有异议,则为新的要约,买受人同意则为承诺,如此反复,至交易完成为止。
上述程序设计,其核心动力无外乎是确保家族财产之内部流动,最大程度保障家族不动产物业之稳定性。即便缺乏完善的批退批价制度,家族亦可通过家法对亲族优先权进行程序保障。一般有两种方式,一是“署押”。亲邻人等于不动产买卖契约上签押,不仅仅是作为“见作人”证明契约关系的成立,更重要的是可凭此签押推知其知晓买卖或典卖全过程,并由此推定其放弃亲邻优先权,此举经济实惠,又增强了交易的稳定性和安全性;二是公示。即通过一定的仪式将买卖行为及其结果向族众公示。以苗家习俗为例,外族买主即使与卖主确定了田价,但同家族人享有优先购买权,则仍由族人收买,此种习俗流传至今。因之,买主为了确保交易成功和防止亲族人等遮占干预,于是在买卖缔约之后,邀请双方亲族、寨头、中人饮宴,同时由买主送卖主之亲叔伯兄弟每人谷十斤,谓之“亲房谷”。此种仪式完成,买卖方告正式成立并生效,以后亲房人等不仅不能遮占族内所卖田宅,而且还有作证的义务。[ 高其才:《中国习惯法论》,湖南出版社1995年版,第331-332页。]此项程序前已涉及,此不具论。
(三)亲邻优先权是维护家族利益平衡的必要手段
中国社会数千年来以家族形式存在,家族、家庭财产均以公有为主体,类似于今日之共有,其内部管理绩效与模式亦多有可观。如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期,广东南海荷溪乡何垂裕堂族尚摹仿“议会”模式,推行家族公决,藉此平衡族产利益分配,体现了可贵的民主精神。[ 《南海荷溪乡何垂裕堂族规》:“不动产之买卖及其他处分等,须有本族全体会员十分之七出席,始得提议;又必有出席会员十分之七赞成通过者,始为合法之议决案,否则不生效力。”转引自费成康主编:《中国的家法族规》,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20页。]王铭铭教授在考察东南沿海厦、漳、泉经济文化区之美法村时,也以事实辩明1979年以后传统家庭、家族意识的复活与家族族权的回归。[ 王铭铭:《村落视野中的文化与权力》,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0页。]
亲邻优先权形式上是照顾亲邻的血缘、地缘关系,实则是维护家庭、家族的共同利益使之免受损害。民间习惯法中,有众多习惯可以证明传统社会族产对于家族内部的重要性,及其推行亲邻优先权之必要性、必然性。根据高其才教授的考察,佤族同姓家族对外来债权承担共同偿债的连带义务,如债务人欠债日久,债权人可抄家、拉牛、拉人,也可抄拿任何同姓或同寨之人的物品、牲畜。这类“父子相承,同姓共偿”的习俗已深入人心,等同法令。要避免同姓其他人的财产利益受到侵害,同姓之人就必须归为一体,共同对抗外来风险。如果放任债务人自由处理不动产,其后果最终势必要波及同族人之利益,故优先权的行使,可避免外姓占有本姓不动产甚至滋生狱讼械斗,也可以使同族人偿清债务后重新赎回不动产物业。饶有趣味的是,佤族人若以人抵债,同姓之人也享有优先权,如同姓不要方得外卖他人。这种视人为共同财产且同姓享有先买权固然是陋俗、恶俗,但却足以证明同姓保护生产力资源的真实动因及其行为选择。[ 高其才:《中国习惯法论》,湖南出版社1995年版,第348页。]
(四)亲邻优先权并不妨碍交易的稳定性
与梁治平先生所论正相反,物业典卖亲邻优先权适足增强了交易的确定性。亲邻优先权制度的创设本意是平衡买受人与亲邻人等之间的交易成本和交易风险。如前所述,物业典卖亲邻优先权是维系家庭社会乃至国家稳定的重要物质基础,法有明文,民有私约,这是客观的不可更移的史实。亲邻优先权的制定,确乎是以保护亲邻利益为首务,但不可否认的是,该项制度的确立虽然增加了买受人或承典人的交易成本,却大大降低了其交易风险。在遵守官方法律和私人契约前提下的交易所获得的正当性、合法性、合理性,将会使买受人、承典人免去无妄的诉讼成本甚至失业(罚没入官)的风险。由是论之,亲邻优先权在保护亲邻人等的利益前提下,也同等保護了买受人、承典人的利益。
综观我国古代物业典卖亲邻优先权制度,不仅可以确认该项制度的客观广泛存在,也可见官方与民间对该项制度的认同,更可以从中看出其维系中国传统社会和家庭稳定的历史性贡献,也不难发掘其立法、司法上的一系列成熟的技巧。苏力先生认为:中国古代的习惯、惯例在简单社会中比成文法更便利有效,它不仅降低了交易成本,而且可以建立预期规制行为。[ 苏力:《法治及其本土资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8-9页。]据此而论,将亲邻优先权视为一种合理的本土资源,并无不妥。
虽然亲邻优先权在二十一世纪已然式微,仅存在于特定的身份关联与财产关联领域,但探寻其动力机制、法源地位、制度功能不仅可以还原历史,亦可为今时立法、司法提供有益借鉴。一个世纪前,庞德认为对民法典进行解释和适用时,应恪守“属地法”原则,不能盲目追摹他国。“此乃中国法典,适用于中国人民,规范的是中国人的生活。” 特别是对源于传统儒家思想的系列制度,更应谨慎对待,不宜按照西方理念或模式一概否弃。庞德认为此类“伦理思想体系是法律秩序的坚强后盾”,进而认为中国正是因为这种悠久的道德传统和伦理习俗可以转换为被普遍认同的法律理念和具体规范,用以调整社会关系,塑造行为秩序。如果单纯使用比较法解释论和适用技术,既无力解决立法借鉴问题,即西方法典中国化的立法目标问题,也不能解决现实问题,即立法效能问题。唯有立足于中国人实际生活条件和法律适用土壤、立足于中国人关于社会秩序的基本理念、立足于中国人对法律秩序的目标和期待,才能真正造就合于时宜的法典。[ [美]庞德:《比较法和历史——作为中国法的基础》,载陈煜编译:《传统中国的法律逻辑和司法推理——海外学者中国法论著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0-11页。]
The Status in the Origin of Law and System Function of Relatives and
Neighbors Priority in Song and Yuan Dynasties
ZHANG Zhen-hua
(China Media Group, Beijing 100089, China )Abstract:
The present study investigates the status in the origin of law of traditional relatives and neighbors priority since Song Dynasty. Probing into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government and the civilians, the statute law and the customary law, creditor with priority and buyer, the present study discusses the application and system function of relatives and neighbors priority, and insists that this system can effectively maintain the stability of family business, improve the social governance performance, and achieves the interest equilibrium between free trade and transaction security.
Key Words: relatives and neighbors priority; the status in the origin of law; limited condition; system function
本文責任编辑:龙大轩
收稿日期:2020-07-03
基金项目:2018年度中国法学会基础研究重点激励类项目“传统家法:秩序构造与风险治理”(CLS-2018J03)
作者简介:
张振华(1977),男,土家族,湖北利川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交节目中心“法律讲堂”栏目编导,艺术学硕士。
① [美]罗斯科·庞德:《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沈宗灵、董世忠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