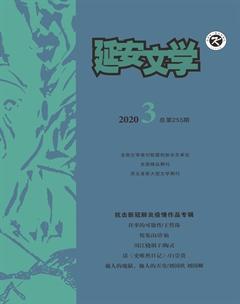洱海中轴线上的村落
北雁,本名王灿鑫。现居云南大理。作品散见于《人民日报》《滇池》《散文选刊》等,出版长篇小说《赶在太阳落山以前》等。
沿着洱海西岸湖滨一路向北,在到达苍山十八溪之一的锦溪入海口前驻足,在一块地名碑上阅读得知,寻访洱海两个月来,我的脚步已经到达洱海或者说是大理坝子的中轴线上。位于南磻溪村中央的大照壁和与之相距不远的分水石,将苍山洱海百二山河齐分为二。
在大理地方文献中说,“百二山河”是明嘉靖年间贬居云南的状元杨慎,在去往保山途经大理时题写的,后来就成了苍山洱海环抱中大理坝子的代称。因为位居洱海南北的上关和下关正好大约一百华里。也有人认为杨慎题写的“百二山河”是化用了“百二秦关”的典故,乃因大理坝子襟山带水,地势险要,居北的上关有“北关屏藩”之誉,守南的下关有“南天屏障”之称,南北扼守的关隘易守难攻,自古就是兵家常争之地。所以杨状元四个题字,精准地概括了大理坝子的地形特征。“苍洱无双地,百二由此分。”这是刻在石头上的古对,在这中轴线上的短暂停留,让我感到了一种里程碑式的特殊意义。
磻溪同样是个很大的白族传统村落,并且照样有南村和北村之分。沿着锦溪河畔行至入海口,又从紧挨洱海的村巷往北,七弯八拐,再至村北,最终又从村中心的环海西路走回来。如此两个多小时的行走,我逐渐探寻到了属于这个古老村落的田园诗意。其实初入村巷,我就发觉南磻溪在整个村子的历史意义更为久远。村道里,有许多新房在建,但还是有不少石砌的旧房保留了下来。村子南头一个围墙倾倒的观音寺里,一个戴草帽的木匠正在院心的两个木马中间削一根梁柱,那种神情专注、无比虔诚的景象一下子让我生发无限敬意。的确,在这种纯粹的手工技艺已变得非常稀缺的当下,只有在面对神灵的时候,那些形单影只的匠人,才有如此大显身手的机会。
在一两条古意盎然的巷道走个来回,我似乎听到了耳畔久远的历史足音,我确信那是根植在这块土地上的白族俚语,在与远古的神灵对话。金银花绕上花架,在一座低矮的大门后面探出了头,馥郁甘甜的花香,如同袅袅的余音,诉说着苍洱大地不会老去的光阴。抱着孩子迎面走来的年轻村妇,用一只手举着手机,伴着孩子的牙牙学语和远方的年轻爸爸聊着视频,让古老的村巷又多了一份生气。在一座临湖的院落门口,一个裸露的船体钢架下面,用旧渔网绑上的泡沫碎板,让人想到了大观楼长联中“元跨革囊”般的美妙。我似乎看到了一个父亲领着刚成人不久的儿子,就驾着这条简易的船只,从洱海碧波之上打鱼归来。
是啊,时间真是这世界最伟大的奇迹。我清楚地看到石砌的古墙中透视着历史的沧桑,尽管外表泥层剥落,但墙体的刚直与韧性却没有多大改变。有些废弃的院墙上面,仙人掌已长一人多高,球面绽放的小花蕾又喻示着一个季节的轮转。“石头砌墙墙不倒”,这样的旧居和墙体,留住的不仅是我们的记忆,更是一种光阴的见证,一种记录了我们这个民族勤劳智慧的最佳见证。这些天,洱源、大理等多个县市的砖厂,因为中央环保督查组入驻大理而被关停,老家正在建房的亲戚都因为没料下锅而停工。转眼七八个月过去,仅只二百多平米的规划,一座两层小楼硬是封不了顶。我有时就想,为什么我们不借鉴一下祖宗们的智慧?就地取材,或许我们就不会太多地依靠于那些成品建材。可能许多人会斥责我不懂建筑,但我却发觉我们这个时代的建设都只会照搬模式,无休止地“复制”“粘贴”,让所有房舍都成了简单的成品与半成品装拆。难怪我们现今的村镇只会千城一面、千村一面,再无区间、地理和气候的异同。
凭着先前锦溪之畔读到的文字导引,我很快找到了位于村中心的大照壁。只见照壁正中偏上的位置,依次横贴着四块圆形的大理石瓷砖,从右向左刻有“平分百二”四个大字。旁边的一块碑记注明,这个照壁建于清乾隆年间,而它所处位置正是上关下关百里坝子的中心,并有过多次重修,瓦顶壁画,墙头枯草,每一个细节都无不显示时光的旧意。“磻石镇中流平分山河百二,溪水归大海变成气象万千。”读到这个古对,我更是感到一种特别的意味。一路走来,在往南不远的富美邑、龙凤村、才村和小邑庄,我曾不止一次看到气势巍峨的大照壁,或者年代更为久远,却从未给人如此的庄严与神圣之感。
绕过照壁,就到了洱海边,和湖面相对的是一座重新修建的木瓦亭子,名曰:水阁凉亭。据亭后的碑文介绍,此亭又称“子母亭”。远远看来,还真有种子母相抱的建筑格调。左右两侧的梁柱有联写道:“平分百二如诗如画,气象万千可心可意。”据说古时,此处曾有隐君子垂钓于湖上。我在暮色苍茫之中远望洱海,似乎有一种穿透时光的直觉,只可惜今日的洱海,已经再无法与昨日的佳人相会。
从凉亭转回,照壁前面的广场紧邻学校,再往西不远的大青树下,我找到了那块“分水石”。它并沒有想象得那么巨大,一块不过一米多高的大青石,在时光的流转中沐风栉雨,此时已被打磨得十分清瘦和光滑。若不是有此特殊的意义,我感觉还真是一块普通的石头。而上面刻着的文字却将石头的来由归功于观音大士。大理有“妙香古国”之称,从古到今,在人们的信仰史里,观音有着远比如来佛祖更慈善美好的声誉,所有的人间造化之奇,似乎都得益于神灵的伟力和运筹帷幄,在面对所有自然天成的景致,都让人在内心深处生发更多的敬畏之感。千百年来,世居大理坝子的人们始终遵循着因果报应的道德伦理,在分水石侧畔的磻溪村本主庙里,我就看到了这样的对联:“隐恶扬善为非作歹纵来烧香也无益,敬老怀幼安分守己见吾不拜又何妨。”大黑天神,这是磻溪村的本主,远远对视,就给人一种威严无比的庄重之感。读罢对联,再次面对这个一脸恶相的神灵,我想到的是铁面无情的宋代名臣包拯。
本主庙前,大青树下,南来北往的车辆时常不断,寻访者的脚步隐藏在各种豪华车辆之中。在一个弯道上迎面而来,按着响亮的喇叭并且绝不减速,有着鲜亮的外地牌照和大地方的见识,便也有一种横冲直闯不可一世的阵势让人畏惧,于是窄逼的村道便如同一个几欲挤爆的气球,给几个正在玩耍的孩子带来无比的恐慌。在以前,洱海周边村落是一片相对封闭的世界。如今路修进来,当然就给我们打开了一道门、一扇窗,一个可眺望和通向世界的起点,但也带来许多视觉和心理暴力,甚至潜移默化影响着我们这些村落的,还有许多。
拐过一个弯就能看到一个临水的集市,场地较为宽广。此时在集面上看不到一个人影,可见这是一个早市,而相邻的村落之间似乎也知道错峰开集,于是那些聪明的生意人便在这些大小村落之间辗转往返,不知疲惫。在每天清早迎来洱海的晨曦,小集上必定人山人海。在那一阵阵嘈杂的只有本地村民才听得懂的白族口音中,洱海鱼虾、海菜、麦秸秆烧猪、环湖之畔的时兴蔬菜和各种现熟的特色小吃,便是洱海家园让人最为难忘的乡愁味道。记得高行健曾在他的小说中这样说过:“尽管你生在城里,在城市里长大,你这一生绝大多数岁月在大都市里度过,你还是无法把那庞大的都市作为你心理的故乡。”对于洱海,包括洱海边的每一个村落,我的每一次到达都会换来发现的惊喜,而且她亦无时无刻对我报以家园般的亲切。我情愿一辈子呆在这个岑寂的家园,永不归去。
小集成了磻溪南北两村的分界线。现今洱海村落之间的界线已经变得越来越不明晰,渐渐只剩老人脑海里一个不断抽象的概念,亦如我们这个时代越来越模糊的时间和空间。记得十几年前初习写作,我曾写过一个短篇小说,讲的是一个刚参加工作的乡村教师,常在有月亮的夜晚去约会他的女朋友,从南村到北村一段不远的距离,却让我写得相当漫长。在我看来,距离可以产生美。前些天读完张扬的《第二次握手》,这样的感觉更是让人坚信,只有距离,才可能把恋人之间一日不见如隔三秋的炽热衬托得更加迫切。包括在我们的古典诗词中,亦有过太多有关距离与时间的赞颂、怨艾、期盼、煎熬与感伤,李白、杜甫、王维、李商隐、苏轼、秦观、李清照、杨慎、纳兰性德,无一不是这方面的大师。但如今,那些因为距离而衍生的离愁别恨,或许就将随着科技、交通、建筑和城市化的日趋发达永远地消失。就如同我们可以在地球两端聊视频打手机,却很难有时间去吟哦“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的缠绵意境;同样,在日行千里的旅途中,我们依旧可以有效地利用短暂的碎片化时间,谈判、思考、读书、写作、聊天、发呆、淘宝、看电影、打游戏、刷朋友圈,却再不可能有当年的徐霞客、司马迁沐风栉雨地寻访故事了。
顺着向北的村街,不知不觉就来到了洱海边上的磻溪珠联阁,这是一个古色古香的砖瓦木阁。东西南北,为这个木阁在房舍挤挤的洱海之边空出了一个开阔的小广场,便也成了村民下午时光里最重要的聚集地。这种景象实在美好,背倚洱海,坐东向西,重檐歇山顶,三开间,抬梁式木构建,给人一种年月旷久的视觉直观。我在旁边的碑文上读到,这是一个保存较为完好的清代临水阁,始建于清光绪年间,距今已110多年,其设计及建筑出自亭阁大师韩珠之手,是与浩然阁等“洱海四大名阁”齐名的古阁之一。据碑文介绍,阁之得名,乃因建成后,时为太和县令的刘安科在大理石匾额上题书“珠联阁”三個字,故而一直沿用至今。在另一块石碑上我又读到,解放前夕,滇纵七支队曾经在此秘密开展地下活动。洱海之边的珠联阁因此更多了一重神武之气。
自古名山秀水多贤俊,洱海的秀丽风光,给苍洱大地的每一寸土地都留下了厚重的人文遗迹。在先前走访龙凤村中的洱水神祠时,被称为“四大名阁”之首的浩然阁仅只空留一个座基,据说位居洱海南北的珠海阁与水月阁早已不复存在,仅存的海东天镜阁却是原址重建之物。而今行步至此,我感到的是另一种怅惘。环而视之,村落,洱海,夕阳,北风,每一个角落的岁月沧桑都让我充满感叹。“苍屏洱境共一楼”,依稀看到阁上前人留下的墨迹,就是对这一派情景最好的表述,然而围着阁楼环走一圈,我却没能找到与之相对的文字。在暮色中离去,让我留连的不仅是这水天一色的风景,还有那些早已不见踪影的旧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