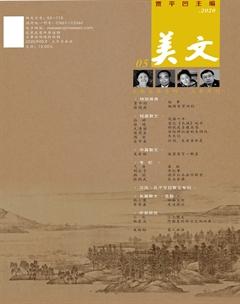编辑家贺鸿钧
张艳茜
尽管早已清楚,人生其实就是一场毫无意义的旅程,我们自己既无法选择搭上哪班车,也无法选择我们的起点在何时何地,一切来得都非常偶然,而终点又是不用期待的。史铁生说过:“死是一件无须乎着急去做的事,是一件无论怎样耽搁也不会错过了的事,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但是,当穆涛兄将贺鸿钧老师逝世的噩耗电话传来时,我仍然无法接受,总感觉像贺老师这样的人是与“离世”毫不相干的。且贺老师走得如此迅忽,我一时语塞,哀从心生。一首诗中的几句,就萦绕心头,这是《延河》曾经的副主编余念,笔名玉杲的诗人,悼念冯雪峰的诗句:
我不相信你会死,
光不死,诗不死,思想不死,
难道你会死吗?
偶然来到这个世界的我们,短暂的一生旅程,其实如流星般一闪而过。无数的人与你毫无关系,无数的人又与你擦肩而过。还有一些人,虽然暂时和你坐在了一辆列车里,却完全形同陌路,匆匆间,就可能天各一方。而能够始终在你的身旁,从陌生到相识到相知,并和你一同在旅行中,既能享受快乐,又能分担艰辛的,可是大浪淘沙寥寥无几了。
作为晚生后辈,虽未有幸在编辑岗位上,得到贺鸿钧老师的亲自指点与教诲,但是在我人生旅途中,我极为幸运地与贺老师在“同一条河”——《延河》上航行过,而她与一批杰出的文学编辑前辈,就像是航道上的灯塔,一直指引并照亮我前行。
现在门牌号是建国路83号的陕西省作协大院,曾经是国民党高级将领高桂滋的公馆。高桂滋公馆这个大院,院中有院,是个十分讲究的庭院式建筑,曾经有三个相对封闭完整的四合院,全部用青砖铺地,别有一番清幽古朴的感觉,每个院子,都种着较为名贵的树。
1954年11月,中国作家协会西安分会成立,之前作家协会筹委会负责人王汶石带人在西安城多个地方考察选择地址,最后选定在当时门牌号为建国路7号的高桂滋公馆。多年后,贺鸿钧对当年的省作协大院记忆犹新,那时,她刚刚结束中央文学讲习所的学习回到西安:“1955年春,我和丈夫李若冰走进作协大院,好不惊喜,门口鱼池的喷头水花飞舞,旁边是座大礼堂,礼堂旁的耳房还承载着重要的历史事件。1936年西安事变,张学良、杨虎城二将军在临潼的山上找到蒋介石,把他带到这里,耳房就是开始谈判的地方。前边是一个不小的花园,各种树木果木郁郁葱葱,葡萄藤搭起了一个一个环形的走廊,正是散步健身的极好场地。往前跨过圆门之后,是布局完全相似的三进四合院。”
1985年7月,我从西北大学中文系毕业,被分配到陕西省作协,进入了门牌号已改为建国路71号的大院,成为《延河》文学期刊的编辑。当时的省作协行政部门在“高桂滋公馆”的前边院落办公,《延河》编辑部和《小说评论》编辑部,在三个四合院中的两个小四合院办公。
曾经我在报刊书籍上见到的大名:胡采、李若冰、杜鹏程、王汶石、路遥、陈忠实等作家,突然以活生生的形象,行走在省作协大院里,出现在我面前,令我好生激动也好生紧张。这些作家们看似很平常,他们有着普通人一样的笑容,高兴时开怀大笑;他们也有普通人一样的情绪,激动时亦慷慨激昂。他们穿着朴素,走在街上,不点破身份,很难将他们和著名作家联系在一起。他们聚在一起时谈文学、谈时政、谈足球、唠家常,然后各自回到自己简陋的写字间,坐在嘎嘎作响的旧式藤椅上,伏在漆面斑驳的写字台前。那时,跃然纸上的文字,就使他们不一般了。他们的思想,他们的睿智,他们创造的形象,随同他们的文字跳跃着,高大着。一个一个的创作成果,也随着这些文字变为印刷品,不断地为人们制造着文学的盛宴。今天这个作家的小说获奖了,明天那个作家的长篇出版获得好评了,这些讯息,接二连三在省作协的院子里传播着。
中国当代文学的发生,延续了延安时期的文艺传统,借助“解放区文学”的资源和助力,形成于陕北红色根据地政权稳固以后的陕西文学,得到快速发展,从20世纪40年代到现在,陕西文学薪火相传三四代,在中国当代文学格局中,不仅成为其中不可或缺的部分,而且有着巨大的贡献。如同陕西作家一样,创刊于1956年的《延河》文学期刊,也在薪火相传中,形成了三四代编辑的继承。
在文学期刊这个园地里,由陕西省作协主办的《延河》文学期刊,因曾经发表了大量享誉文坛的优秀作品,在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上,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不能不捉笔书写的一个刊物。
从1956年《延河》创刊,到“文革”后期改办《陕西文艺》,再到“文革”结束后的20世纪80年代、90年代,《延河》能够与陕西作家一起,成为中国当代文学不容忽视的一部分,其中的原因,當然是陕西作家队伍的强大,但同时,也因为当时的《延河》编辑力量的强大。这个团队中的大多数,既是优秀的作家、理论家,又是优秀的编辑家。
1955年秋冬之际,刚刚成立不到一年的中国作家协会西安分会,开始筹备创刊《延河》文学期刊,陕西省委宣传部同意由戈壁舟、石鲁、杜鹏程、胡采、汤洛、魏钢焰等13人组成《延河》编委会,主编由诗人戈壁舟担任,副主编是汤洛、魏钢焰。编辑部主任由余念、胡征担任。文稿终审由作协副主席柳青代管。“《延河》创刊时的几期用稿,柳青同志不仅亲自审阅,而且动笔修改。他把稿子改好后,专程从长安县来到编辑部,和同志们一块讨论,谈他对每篇稿子的看法和意见。”(贺抒玉《柳青与<延河>》)时任西安市文化局局长的胡采,后调入省作协担任《延河》主编,此后,柳青不再审稿,全身心投入到《创业史》的创作中。刊物取名《延河》,一是因为这批创刊人都是喝过延河的水,从延安走出来的文艺工作者;二是因诗人戈壁舟的一首诗:“离别延河久,延河照样流,流入黄河流入海,千年万年永不休。”故而得名。
20世纪70、80年代,《延河》时任主编是王丕祥,副主编为贺鸿钧、董得理、余念。王丕祥早在延安时期就在文艺部门担任领导,是一位具有很高政策水平和丰富文学工作经验的老领导;董得理先是毕业于延安大学,新中国成立后又入中央文学讲习所深造,既通创作也懂理论,是一位在各方面都有着很高造诣的著名编辑家。余念即玉杲,是在40年代就已成名的著名诗人。这三位副主编也都是“老延安”。小说组组长路萌,副组长高彬、路遥,编辑有张文彬、白描、李天芳等;评论组组长陈贤仲,副组长王愚,编辑李星、李国平等,哪一个都是重量级的评论家,陈贤仲后来调湖北少儿出版社任总编辑,王愚、李星、李国平后来分别担任《小说评论》主编。《人民文学》资深编辑、后来的副主编崔道怡不无感慨道:“《延河》的编辑力量太让人羡慕了,在全国所有文学刊物编辑部中,恐怕再也找不到第二家。”
这个强大的编辑团队中,有三位秀外慧中的女性,无论颜值,还是才华都极为引人注目,一位是1957年始就担任《延河》副主编,笔名贺抒玉的贺鸿钧,即李若冰夫人,20世纪50年代就是一位令人瞩目的小说家,也是创刊后首任《延河》小说组组长;第二位是《延河》时任小说组组长高彬,即王汶石夫人,与贺鸿钧一样,高彬也是“米脂婆姨”。1948年米脂小女子高彬与1942年就来到延安的王汶石在一起工作,他们一同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做宣传鼓动工作,互相关心,互相照顾,在异常艰苦的岁月里建立了深厚的感情。1949年西安解放不久,他们就在古城西安举行了简朴、热烈的婚礼;另一位是小说组编辑张文彬,即著名女作家问彬,杜鹏程的夫人。他们同样是在炮火硝烟中相识相恋结为作家夫妻的。问彬创作的短篇小说《心祭》发表在1982年《当代》第2期,由珠江电影制片厂改编为电影《残月》,在全国上映后,受到好评。
我进入陕西省作家协会时,《延河》编辑部才完成新老编辑交替,没能与这样一支梦幻组合的编辑队伍同行。作为《延河》的后来人,我既得益于曾经的《延河》创造的辉煌,又时常在辉煌面前感到无比悲哀。那种文学盛世和文学期刊的巅峰时代早已离我们远去,是我们永远也无法企及的梦想。
改组后的《延河》编辑部,组成了顾问委员会和编委会,顾问委员会成员由胡采、王汶石、杜鹏程、李若冰、王丕祥、魏钢焰、贺鸿钧、董得理和余念等领导和老编辑们组成,虽然他们不再参与编辑部的具体工作,但是,他们的影响力丝毫未减。
那时,贺鸿钧老师的家还没有完全搬离71号院,所以经常与贺老师见面。每每见到她,或与她的目光相遇,或是交流,都能感受到贺老师作为知识女性特有的气质,她是真诚和善良的,也是从容和宽和的,这种气质是与生俱来的,也是丰富的人生历练的结果。
什么样的生活和生存环境,造就什么样的人。1928年贺鸿钧出生于陕北米脂县一个书香门第家庭,她出生的年代,正是刘志丹和谢子长等人领导的土地革命风起云涌的时期。贺鸿钧的父亲、伯父都是知识分子,母亲虽然是家庭妇女,在特殊的革命环境和家庭氛围影响下,也都先后参加了革命活动。贺鸿钧就读的是陕北第一所米脂女子高级小学,创办于1919年,曾经为米脂妇女解放、女子接受教育等方面做出过极为突出的贡献。现在口口相传的“米脂婆姨”的美名,就是缘于从米脂这所学校,从米脂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走出来一批又一批率先开化、有胆有识、秀外慧中的米脂女子、妇女先锋。贺鸿钧就读的米脂中学,是著名爱国人士、教育家杜斌丞先生和地方贤达的赞助下,在1927年创建的,抗日战争为“陕甘宁边区米脂中学”。在这样一个社会环境和家庭环境里成长的贺鸿钧,自然有着与众不同的觉悟。1944年,刚刚上高中,不满16岁的贺鸿钧,就和姐姐贺鸿训一起,听从党组织的安排,从米脂中学进入陕甘宁边区绥德分区文工团,投身于革命的洪流中,而她的个人命运也从此与人民解放战争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
紧张、严酷的战争生活,无时无刻不在考验着这个曾经衣食无忧的米脂小女子的意志。贺鸿钧在散文《我的路》中回忆:“我们文工团随军转战时,经常连着几天不能睡觉,顶风冒雪,爬山过茆,头上的柳圈抖擞,背上的背包越来越重,脚上布鞋露出了脚趾头,鞋底也穿了洞,沙子、碎石子自由出入。可恶的敌机还发出沉重的轰轰声尾随身后。那是一个随时随地都可能要用生命和献血去换取胜利的年代,没有牺牲的准备是不可能的。”
不畏艰苦不畏牺牲的贺鸿钧,经受住了炮火连天的军旅生活考验,1945年12月贺鸿钧光荣地成为一名共产党员。“虽然我常年累月在山沟里活动,可我心底的天地十分宽广。我们自觉地肩负起民族的希望,为夺取解放战争的胜利,准备随时随地献出自己的一切,包括年轻的生命。”(贺抒玉《掬几朵浪花——绥德分区文工团生活片断》)
随军转战陕北期间,贺鸿钧所在的文工团随西北野战军为部队演出兼做战勤服务。他们除了演出“鲁艺”创作的一些新秧歌剧,大都是自编自演的小戏,贺鸿钧坦言,她是“在对剧作一无所知的情况下开始写剧本的”。她与姐姐创作的小歌剧《喂鸡》曾刊登在1946年的《解放日报》副刊上,参与创作的剧本至少十多个。得空,贺鸿钧还学会了拉二胡、提琴。1947年,延安收复后,贺鸿钧与西北文艺工作团跟随彭老总的部队挺进大西北,那时,贺鸿钧已是女同志班的班长了。1949年西安解放不久,贺鸿钧随西北文學工作团进驻了百废待兴的西安。
中国作家协会西安分会成立不久,创刊一份刊物的呼声越来越强。1955年秋末初冬,筹办工作大刀阔斧地展开了——抽调编辑,申请经费,组织稿件,忙得不亦乐乎。贺鸿钧就此成为首批编辑部成员,并担任了《延河》小说组组长。“真正接近文学是在做了文学编辑之后,我当了三十年的编辑,编辑部对我来说,是一所很好的学校,也是一个瞭望社会生活的窗口。透过这个窗口,时代的风云,生活的波涛,作者的心态,读者的兴趣等等信息不断传来。”(贺抒玉《窗口》)
曾经担任《人民文学》主编的李敬泽说过这样的话:作为一个文学期刊编辑,如果不间断地工作在编辑岗位上,终其一生,其实也就是编辑几十本合订本。
文学编辑这个职业,通常被我们做编辑的自称为“摆渡人”,“为人做嫁衣”。 有一句流行语:一作家、二评论、三编辑。编辑的地位由此可见一斑。做编辑的最大苦恼,不是被有些作家成名后迅速遗忘,而是在文学事业发展过程中,尽管有编辑创造性的劳动付出在其中,但是,文学编辑价值却没有得到普遍的承认。
尽管大多数作家,在他们初入文坛时,得到过编辑的发现和扶持,然而,一旦他们风光于文坛,当初编辑的工作就被许多作家视作微不足道了,或者有意从记忆中删除了。
我在《延河》时听到过这样一件事,有一位作家,当初处女作发表时,得到过老编辑的指导,后来这位已经走红的作家在回忆文章中,却不记得有过此事,以为自己是横空出世的。
还有些作家,遇到编辑将他的作品修改、删节,便心生怒气,形容编辑是“屠夫”。但是,这些抱怨者可能已经有些小名气或是已成大气候。其实,当初他作为一个还没有被众多期刊认识的写作者时,正是在得到编辑大刀阔斧地修改过程中,得以成长的。当然,作家可能不这么认为,甚至会对编辑的修改表示不屑。
1985年7月我刚开始做《延河》编辑时,以为这是一条漫漫长路,也以为这是一条撒满阳光之路。在经历了许许多多坎坷之后,才逐渐体会了坚守的艰难与艰辛。我不断地问自己,我做这份工作的意义何在,我也不断地问他人,我的工作有意义吗?就在自问与追问之中,匆匆就过去了28年。最终,我没有坚持下来,驶离了《延河》的航道。好在还有《延河》合订本,它将我这28年压缩成不高的一摞杂志,告诉我,我还做了一点事。但是,我要寻找的答案就在这不高的一摞合订本里吗?
贺鸿钧的人生,有三十年压缩在《延河》的合订本里,在这些合订本中,我们能感受的到,无论是在光明的,还是黑暗的文学时代,贺鸿钧始终是一个真诚的,可以信赖的编辑者,一个无私付出的持灯者。无论是《延河》的创刊初期,还是“文革”期间的《陕西文艺》,以及伟大的20世纪80年代,贺鸿钧是可以毫无愧色地用“辉煌”来形容自己职业生涯的。有许多已成名的作家作品,都曾经她和《延河》编辑前辈之手呈现给读者。其中自然包括陕西省众多的作家,更有全国各地的作家、诗人,如贺敬之、李季、闻捷、秦牧、碧野、胡奇等等;也有很多文学新人,经他们的扶持与鼓励,而走上文坛的。
我手中的1966年之前不全的《延河》合订本,是从旧书网上高价购得的。泛黄的纸张,和陌生中有种亲切感的繁体铅字排版,似在告诉我,岁月的河流不会将一切都带走,有些东西会慢慢沉淀下来。同时也在提醒我,岁月也有不堪之处,略微一触碰,就可能发生破损。
《延河》创刊之后,呈现着欣欣向荣的发展态势,影响力迅速提升。岂料,“反右”运动开始了,就此改变了《延河》作为文学期刊的面貌。
找出1957年《延河》的合订本,就会发现,许多作家的命运也是从这一年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1957年的《延河》,从第2期起开始连载吴强的长篇小说《红日》,同期有玉杲的长诗《方采英的爱情》,第2期、第3期连续发表了张贤亮的诗歌,第7期上的作家和作品比较多,其中有康生的短诗两首《说延安》《忆延安》,还有张贤亮的诗歌《大风歌》以及朱宝昌的文章《杂文,讽刺和风趣》。从第8期起,风云突变,“随着反右运动的深入,《大风歌》和另一篇杂文(即朱宝昌文章,作者注)定为毒草。随即玉杲的长诗《方采英的爱情》也定为污蔑老干部形象的毒草。”(贺抒玉《教授·诗人·编审》)第8期上,刊发有《本刊处理和发表<大风歌>的前前后后》,文中附有张贤亮给编辑部的信和他创作《大风歌》后记,以及“《延河》编辑部召开批判《大风歌》的会议”报道,报道中讲到:作协主席柯仲平、副主席郑伯奇、胡采,及参会的王汶石、安旗等十多位作家评论家参加了会议并发言,认为:“这首诗的政治倾向是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诗中表现出来的思想感情与我们今天的时代感情是敌对的……”接下来的几期,连篇累牍地是对张贤亮、朱宝昌的批判文章,火药味十足,杀伤力极强。“刊物上发表了毒草,得追究责任,领导层如果连一个右派也找不出来,恐怕向社会和上级交待不了。渐渐地,矛头集中到了日常发稿的主任余念(即玉杲)同志身上。”(贺抒玉《教授·诗人·编审——祭诗人玉杲》)
批判余念的文章是从第10期开始的,当时年轻的评论家王愚也在10期上遭到口诛笔伐,原因是王愚撰写了一篇文章——《从文学实际出发》,针对此前周扬的文章和观点,对当时文学界,尤其是文学评论界的教条主义,以及违反艺术规律的风气进行了抨击。这篇尚未发表,已出清样的文章,成为王愚“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铁证”,地狱之门就此开启——王愚先是定为“右派”被停职,强制劳动、监督改造、住牛棚,后又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刑5年。《延河》第11期上,批判的炮火仍在继续,有一篇署名“宏均”的文章:《余念在“延河”编辑部干了些什么——揭发余念篡改“延河”方向和争夺“延河”领导权的活动》,文中例数副主编余念审稿中的“错误言论和罪状”:“在日常工作中,余念经常以他资产阶级的文艺观点和个人的好恶来取舍稿件。并且向编辑部的同志灌输他资产阶级的文艺观点。”
看过这篇文章,我有些疑惑,“宏均”很容易与“鸿钧”联系在一起。翻看《贺抒玉文集》,1993年在余念去世时,贺鸿钧撰文《教授·诗人·编审——祭诗人玉杲》中,我得到了答案:“编辑部同志们的揭发材料,指定由我整理成书面发言,后来又决定在刊物上公开发表。我从小生长在革命根据地,又是作协的党支部委员,在‘右派‘向党攻击之际,岂能不积极维护党的利益!只是对像余念这样的右派分子,不仅恨不起来,内心还那么同情。”读到这一段,我对如此坦诚、单纯,通透的贺鸿钧老师肃然起敬。在那个年代,谁都被裹挟其中,谁也难逃厄运。我能感受到贺鸿钧内心的纠结与煎熬——人性与党性,个人与集体,究竟如何厘清其中的是是非非?贺鸿钧真诚坦言:“‘反右之后,《延河》的领导班子做了调整,取消了编辑部主任这一级领导,余念做了小说组复审,我做了副主编。虽说地位发生了变化,我一直十分尊重余念同志,岂不知余念同志是位十分尽职的编辑,又是位极好相处的同志,他毫不计较地位的变化。”
“反右”之后,很快“文革”开始了。“作协的专业作家和《延河》副主编职务以上的同志都靠了边。后来还挂牌游街示众。当我挂着《延河》黑副主编的牌子被押上大卡车时,很不理解这次运动为何要损伤人的人格和尊严!……斗批改深入之后,我们一家一家被下放農村当社员,我带着孩子去了户县。”(贺抒玉《资深编辑董得理》)
1972年的秋天,在“文革”初期当做“修正主义的黑窝子”被砸烂的陕西省四个协会——作协、美协、剧协、音协的一部分干部,从被发配到边远农村去劳动改造的各个下放点、疏散地,调回西安,成立了一个“陕西省文艺创作研究室”。因为上级要筹备恢复《延河》文学月刊(自1956年4月至1966年7月,《延河》共出刊124期),研究室下面成立了一个基本由原中国作协西安分会《延河》编辑部的几位干部、编辑构成的编辑部。《延河》的刊名不能叫了,就改为《陕西文艺》。
在那样一个特殊的年月,这些文学前辈顶着种种风险和压力,一边想方设法避免“四人帮”对文学的戕害,一边为文学复兴和陕西青年作家的成长倾洒心血和汗水。1973年到1976年《陕西文艺》这三年的合订本,见证了陕西文学从“文革”的灾难中复苏到取得发展的一段重要历史;见证了日后为全国瞩目的“陕军”青年作家队伍的艰难组建和蹒跚起步;见证了在黑云压城的处境下文学前辈的正义、坚韧和智慧。合订本也倾注着文学编辑前辈的奉献、敬业和辛苦,同样浸染着他们的快乐、幸福和烦恼。
“1976年,敬爱的周总理去世不久,接着又发生了‘四五天安门事件,文化专制主义的制造者,紧锣密鼓地对文学刊物发出许多‘指示,最主要的是要刊物组织发表批判走资派的作品以及批儒评法内容的文章。当时《延河》编辑部里的许多老同志心情都是相通的,都十分反感这样的要求,都想抵制这种做法。于是大家就商定一条不成文的条约,每期最多发一篇这样的应景文章。对我个人而言,看到那些主观臆造生活的所谓小说还要签发,内心是痛苦的。……我便产生了一个想法,去农村当一段社员,宁可在广阔的田野上劳动,也不愿留在窒息人的办公室苦坐。”(贺抒玉《我的编辑心》)
不难看出,在那个愈来愈沉重,愈来愈炽热的年代里,贺鸿钧以她的良心和智慧在“有所为”与“有所不为”之间,为文学生态得到自由与发展,尽自己所能地提供着可贵的必要的空间和气候。
做文学期刊编辑,如果不是遭遇那个特殊年代,简单地说,做好两件事最为重要:一是发现新人,二是寻找好稿子。然而,这两件事做起来却实为不易。发现新人,需要有过人的眼光和才情;寻找好稿子,需要有阅读的宽度和高度。
《陕西文艺》创办之初,当时的陕西文学界,与全国其他地方差不多,一场冷霜过后草木凋零,满目萧条景象,很多作家还被打倒在地,不知何时能翻身,根本谈不上何时能进入创作状态。而没有作家队伍,文学刊物将如何办?这是当时“老延河”的编辑们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于是,他们分头到全省各地去做调研,寻找发现作者。只有稳定的作者队伍,刊物才有稿源的储备。
1973年春天,编辑部的副主编贺抒玉和编辑张文彬,去陕北延安为即将出刊的《陕西文艺》寻找作者组稿,在延川县革委会通讯组,她们见到了到处做临时工的返乡青年路遥。路遥当时的困厄落魄、路遥的思想才能,给她们留下了深刻印象。她们将路遥在1972年12月16日刊发在《山花》上的短篇小说《优胜红旗》带回《陕西文艺》编辑部,发表在1973年7月《延河》复刊号——《陕西文艺》上。这是路遥第一篇在公开的省级刊物发表的小说,标志着他正式踏上了中国当代文坛。路遥大学毕业时,又是贺鸿钧和时任主编王丕祥亲自到延安,说服延安地委宣传部和教育局以及延安大学,经过多方努力,又等待了半个月之后,1976年9月,带着一身陕北黄土地上的泥土和土窑洞的气息,路遥来到了繁华的古都西安,正式成为《延河》编辑部小说组一名编辑,开始了他人生的新时期。
《陕西文艺》创刊号上还发表了陈忠实的散文《水库情深》,紧接着,陈忠实的第一篇短篇小说《接班之后》刊发在1973年《陕西文艺》第3期上,且是小说栏目头条。贾平凹与《延河》的缘分则有过一些波折:“有一天,董得理来到办公室,把一本《上海文学》放在案头要我看,还说西北大学就读的大学生贾平凹的短篇小说在《上海文学》发表,怎么就没有寄给咱们?我建议他去组里问问,我怀疑给咱们寄了,可能被看初稿的同志退掉了也说不定。果然如我所说。董得理代表主编室告诉小说组,今后凡有贾平凹的稿子不要退,交上来,从此,贾平凹的短篇小说、散文在《延河》陆续发表。此后,谁漏掉好稿就是工作中的失误已成为我们不成文的规定。”(贺抒玉《资深编辑董得理》)
《延河》从1956年创刊始,便形成一系列良好传统,有一个传统,就是对待作者来稿,每稿必看,每稿必复。我入行之后,就是在老编辑张昭清的言传身教下,学会了审读文稿和给作者写退稿信的。张昭清则是从贺鸿钧、董得理、余念、路萌等人那里得到真传的。对待不适用的稿件,我们当时有两种退稿方式:一是信退,二是条退。信退就是由编辑写出对稿件的审阅意见,长处是什么,不足是什么,对作者有些什么建议和希望,编辑或署名或不署名,但都要盖上编辑部的章子,连同稿件一同寄退作者。条退是附一张事先印好的格式化退稿条,将稿件给作者退回。其实我们条退的稿件极少,绝大部分稿子,编辑都要亲自写退稿信,信中谈到的意见一般都很详细。那时,《延河》的自然来稿非常多,每天都能收到两大箩筐,编辑工作量之大可想而知,但大家都以奉献为乐,没有任何怨言。
一份刊物的影响力,说到底,是主编和编辑的理念在支撑着刊物的灵魂。反之,刊物的整体面貌,也对应着主编和编辑的审美追求和思想深度。
编辑前辈贺鸿钧,让我们晚生后辈崇仰的不仅是她对《延河》的热爱与付出,也不仅是她的审美追求和她的思想深度,我们更羡慕她有着美满幸福的家庭。
一个女人要想始终保持一种气质不被岁月侵蚀,除了自己有一份热爱的事业,那一定还要有一段稳定幸福的婚姻。而幸福稳定的婚姻里,一定有一个更有担当、情绪稳定,能在重要时刻得到支持的丈夫。
贺鸿钧与李若冰的爱情故事,自我一进入省作协大院,都有耳闻。经历了金戈铁马战争之后,作家李若冰和米脂女子贺鸿钧,随西北文艺工作团进入了刚刚解放的西安。1953年6月6日,贺鸿钧幸福地与作家李若冰结为伉俪,在西安东关杨家园的一间小屋举办了简朴的结婚仪式。“若冰以往发表作品用沙驼铃的笔名,结婚后,他为自己改名李若冰,为我起了贺抒玉的笔名。他用冰清玉洁象征我们爱情的纯净和执着。”(贺抒玉《大自然之子——李若冰》)婚后不到两个月,丈夫李若冰就为贺鸿钧收拾了行装,送她上了东去北京的火车,贺鸿钧在中央文学讲习所学习了两年。而李若冰则带着自己的行李奔赴大西北戈壁滩,投入到石油勘探者的行列,之后著名的《柴达木手记》问世。新婚的小屋里只留下了公家的桌椅板凳。“在我们看来,人的一生,爱情和事业缺一不可,获得爱情之后,就应当全力以赴向理想的事业冲刺。当初,难道不是他勃勃雄心和诗人如火的热情夺走了我的心吗?当理想和爱情在我们年轻的胸膛里融为一体的时候,新婚后的长久别离又算得了什么呢。”(贺抒玉《大自然之子——李若冰》)爱情不罕见,但长久婚姻里的爱情着实罕见。婚姻是相互的,两个人彼此尊重,彼此坦诚,彼此有爱,才可以幸福。婚后几十年来,李若冰贺鸿钧夫妇相濡以沫,妻子贺鸿钧是丈夫李若冰的第一读者,丈夫李若冰也是妻子贺鸿钧文学创作的有力支持者。共同的追求,共同的人生价值取向,造就了和谐,更造就了生命的充实。贺鸿钧以笔名贺抒玉发表了几十篇小说和散文,出版的第一部中短篇小说集《女友集》是李若冰代为编辑的,而李若冰的一些散文集,则是贺鸿钧编辑出版的。2008年在李若冰逝世三周年之际,贺鸿钧为丈夫编辑完成了《李若冰纪念文集》。
2006年,是《延河》创刊50周年,本以为可以认认真真地做一次纪念活动,其中一项是征集、编辑“我与《延河》”的回忆文章,我很想为历史留下些许记忆。哪怕有一天这本刊物不存在了,依然还有人能了解,曾经有一条流淌在文坛的《延河》是怎样的壮观。遗憾的是,《延河》竟草草地委屈度過了一个50岁生日。很多人不会理解,《延河》不仅是一本文学刊物,一本有着辉煌历史和文学传统的刊物,也是一本与许多人的青春和生命都割裂不开,有着血肉关系的刊物。
那一年,我向《延河》历史上第一任女副主编贺鸿钧老师提出请求,希望她能将《延河》历任主编写下来。几天后,贺老师电话给我,说她凭记忆,写下了一份“《延河》历届主编情况”。我去她家取,两人聊天竟聊到午饭时间。贺老师留我吃饭,我便毫不客气地坐下来。告别时,贺老师将那份“情况表”和一封书信给我。
我一直珍藏着贺鸿钧老师的信札,作为一份纪念,更作为一份激励和致敬。想来十分惭愧,作为编辑家贺鸿钧老师做到的,很多我都无法做到。唯有努力像她一样,无论世事如何艰难,都要去做一个善良宽厚的人,做一个内心丰盈的人,做一个真诚坦荡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