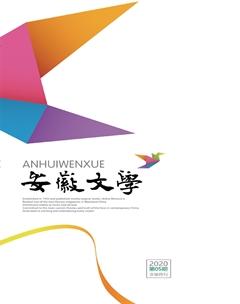观物小札
文河
花骨朵
花正打骨朵,早晨,露水落在骨朵上,有艳意。花骨朵累累满枝,好像会轻轻发出声音来。
最近学认篆字,发现花的骨朵,极像篆体的“心”字。
忽然又想到了晏小山的词,“记得小初见,两重心字罗衣”。过去女子的衣服,绣着双重的“心”字图案,好有情致。据说宋时女人衣裙上所绣的这种图案,正是类似篆体的“心”字,像含苞欲放的花骨朵。春风入怀,其人如玉。
花未开时,花里好像隐隐有一个什么故事在里面藏着。等开全了,发现天清地旷,原来什么也不曾发生,但心里有淡淡的愉悦感。
愉悦和快乐好像还是有所区别的,譬之于酒,大约愉悦是淡雅型的,快乐是酱香型的。
父亲请几个多年未见的老友吃饭,都是我少年时代认识的,让我过去斟酒。大家日复一日,都在平平常常地生活着。但多年不见,便觉他们变化很大。
人在时光中生活着,一天一天,慢慢老去了。也没什么太大的事情发生,你经历的,大家也都在经历,大同小异,司空见惯。但过了一段时间,便发现,每个人的人生,都成了一个独一无二的故事。这一点,和花开似乎相反。
前两天闲翻况周颐的词话,其中一则记载很有意思,说过去的蜀人,称四月寒为“桐花冻”。
桐花大,桐花的骨朵也大,像小喇叭。四月,桐花开放,香气甜腻,满树的花,很嘹亮似的。
春 波
十天前,和几个朋友开车到河南信阳陈淋子镇玩,昨夜刚下过小雨,四围山色如洗。早春,树木欲芽未芽,但竹荫竹色,明显变青了,变柔和了。竹荫沉沉如水,是水波的气息,静静的,虚虚的,是空中之色。返程的时候,又顺便去看华阳湖。一湖沉碧,这种碧是有生命的碧,比天空的蓝富有质地,给人一种空明圆润的奇特感觉。
记得有位西方学者说,读《老子》,给人一种“水的感觉”。的确,中国古人对水的参悟,达到了极致。中国传统文化的感知方式仿佛凌波微步,罗袜生尘,细致而精微,但又自然无隔,物我交融。唐诗宋词元曲,都有着水一般的空茫无际。
到野外散步,偶见一方池塘,临水坐了一会儿。春风中,水波一层一层地向岸边涌过来。水波的那种动态,太美妙了。古乐府中的焦仲卿妻,不能见容于公婆,被休离家之时,仍然严妆打扮好自己。“着我绣夹裙,事事四五通。足下蹑丝履,头上玳瑁光……”,诗句不厌其繁,工笔刻画了一个对自己对人世都郑重庄严、一丝不苟的女人形象。但这只是一幅栩栩如生的绘画,接下来,诗人写道:“纤纤作细步,精妙世无双。”这个形象才一下子活了,真是神来之笔。此时,这一层层涌动的春波,也当得起这两句描写。
奇妙的是,在这一方小小池塘里,层层春波涌动时,居然给人带来一种流向无穷远方的感觉。由此想到,正是因为我们有着一个肉体的限制,心灵才能抵达某种生命的永恒和无限。
暮晚,看西沙河。柳丝垂,春波静,新月如眉。这种静,是悠远柔和的静,涵容万物的静。也是一种母性的静,轻轻地呵护着什么。好像这个世界,会担惊受怕似的。
河畔草
“青青河畔草,绵绵思远道”(古乐府《饮马长城窟行》),为什么这么简单的句子,却有无穷的韵味?每次读之,都仿佛回到千年前的时光里——回到千年前那悠长细微的颤动里。
我一直渴望抓住古中国深处的那一丝颤动。
千年前的时光,温暖,苍茫,一样的悲欢离合。
荸 荠
上午妻子买回一些荸荠,我用清水洗净,发现荸荠的颜色蛮艳的。乌沉沉的,又透出红,是老红,带点紫。形状扁圆,有点拙,状若马蹄银,用手机搜索一下,果然荸荠又名马蹄。以形赋名,本为常见。柳宗元笔下的郭橐驼,亦如此。
年轻时,看中国画上的人物,老、拙,甚至丑陋,觉得不美,现在才渐渐明白一点,这其实是超越于寻常之美,从而达到大美的。这种传统的审美认知,应该是来源于庄子的朴、畸、憨,自在的心性超越于寻常的形质,不缚于物,也不缚于美,更不缚于任何观念。
我们的艺术追求是宁拙不巧,巧,太尖新,失之自然。凡自然天成之物皆美。一颗樱桃是美的,一个荸荠也是美的,就连土豆和红薯也是美的。
清水煮荸荠,煮过后,水里便有了荸荠的清甜,我喜欢喝这种水,称之为荸荠茶。有人喝茶,琐琐屑屑,千般讲究,达于极致,我觉得这已经失去喝茶的意义了。
用禅宗的意思来说,凡事做到极致,便岌岌可危,命悬一线。要么直见性命,超凡入圣,要么失足落崖,粉身碎骨。有所为,有所求,本是为安身立命的,结果却连立足之处也丧失了。无论艺术还是生活,真正的大境界,最终还是平常与通达。
汪曾祺的小说《受戒》中,那个菩提庵被讹叫成荸荠庵。荸荠庵比菩提庵好,亲切,有世俗的气息。记得有个寺院,叫枣花寺,名字也很好。荸荠就适合生長于潮湿多水之处,南方很多。收荸荠的时候,走在水田里,小英子故意用自己的光脚去踩明子的脚。汪先生写初恋,写绝了。
蒜 苗
还是冬天,母亲种的大蒜,给了我们一些。打过春,还没吃完,蒜瓣就发芽了。
妻子找两个盘子,把蒜头罗列在里面,用矿泉水瓶子接上自来水,随便注入进去,过几天,蒜苗就长出来了。
翠绿翠绿的蒜苗,齐刷刷的,一丛一丛,长得很旺,看上去像水仙。放在书房里,也很好看的。
有时熬咸汤,出锅前,妻子会用剪刀剪一束,洗净,切短,放汤里,提味儿。炒腊肉片,也放。薄薄的肉片,透明,放一些蒜苗,特新鲜。
这些蒜苗,剪去一茬,很快又发一茬。再剪,再发。还剪,还发。
看着光秃秃的苗茬,觉出了命运的残忍。从大蒜的角度来看,它们活得太悲惨了。但站在人的角度,又惊叹它们活得顽强。
惊蛰过后,又剪了一次,吃不出新鲜的味道,就不再剪了。
隔段时间,继续向盘子里注水。蒜苗长齐,长高。又过一段时间,这些蒜苗,开始从叶尖变枯,慢慢向下枯萎。——不由自主,想到了人的身体,先是指尖,然后是手臂,接着又是肩膀……
它们老了。
南 瓜
南瓜,这里写的是磨盘南瓜。笨笨的,拙拙的,虎头虎脑。
还有一种瓜,叫傻瓜。傻瓜不太好吧,但如果有女人喊你傻瓜,那往往也是透着甜的。
我们村,有一家人,不知得罪谁了。他家的南瓜,正长个的时候,被人用镰刀切开一个三角小口,向里面撒泡尿,然后再把三角小口合上,用叶子有意遮住。那个南瓜若无其事,继续长个。过段时间,该吃南瓜了,摘回放在案板上,一刀下去,哎呀,尿液四溢。那家人气得大骂三天。
齐白石画了不少南瓜图。瓜叶和瓜藤墨色淋漓,仿佛风一吹,叶片乱翻,就会刺啦刺啦响。几只瓜顺藤垂下,那么大,奇怪的是,却不给人沉坠之感。也有人说齐白石画风其实挺俗。但他的笔墨生机灌注,热情洋溢,毫发一线,皆具天地之机。这一切是超越于笔墨之外的。它源于一颗永不枯竭的挚爱之心。
中国文人,九曲回肠之后,世事看透,孤月寒潭自照,易冷寂。但还要苦中作乐地活着,便从些微寻常物事中,找到一些趣味,耽于其中。慢慢整个人便如一座假山,七窍玲珑,雅则雅矣,却磅礴之势尽失。老而弥坚,老而益壮,很难。
秋天,南瓜叶老了。南瓜叶大,厚,糙,从边缘开始,一点一点变残,变枯,斑斑驳驳,老得相当硬气。一个一个大南瓜,静卧在枯黄的细草丛中,从粗粗的瓜蒂开始,青黑纹路慢慢扩散开来,深青中透出苍黄,越到中间,黄得越饱满瓷实。用手摸摸,暖暖的,秋阳滟滟如水,仿佛全渗入了南瓜里面。种瓜的人拉着板车来了,随便摘了一个。南瓜好沉,得用两手搬着。放在车上,拉回去。可以熬南瓜粥。也可以先把瓜煮熟,然后拌上面,和好,贴地锅南瓜饼子。
熟透的南瓜很甜。日子苦,需要一点甜。
青 梅
街头有水果摊子,小贩是五十多岁的汉子,神情朴茂。问,油桃什么价啊。答,不是油桃,是青梅。再一看,果然。
青梅,名儿就好听。青鸟、青衫也好。当然,最好的是青春,尤其是逝去的青春。如果我写一篇怀旧的小说,写一个女孩子,小名儿就叫青梅吧。这世上,重名重姓的多着呢。《聊斋》里,也有个女孩子叫青梅。蒲松龄也喜欢这个名儿的。
我喜欢青梅,却不喜欢青梅的酸。杏也酸。我不喜欢酸,最不喜欢穷酸。但女孩子的酸,另当别论。怡红院里,那群女孩子,有时真是酸得可爱,群莺乱飞,花枝摇曳。
晴雯微含醋意的时候,艳极,也清极。晴雯早夭,也好。如果老了,有坠入尖刻狭隘的可能。袭人会始终四平八稳。
安娜·卡列尼娜,美丽高傲绝世,后来,当她对奥勃朗斯基醋意大发时,真让人别扭。托尔斯泰写作时天道无情。
曹操青梅煮酒,纵论天下英雄,真是千古畅快之事。《三国》里,我最佩服刘备,而最喜欢的却是曹操。不喜欢祢衡,狷狂终不抵正大。临江横槊赋诗,顶极的风雅。
唯有非常之人,乃能行非常之事。平凡的人,在梅雨季节,听风听雨。
望梅止渴,也与曹操有关。但望梅止渴,毕竟要好于饮鸩止渴。
偶 遇
有杏花天,碧云天,亦有“卵色天”。而伤情最是那奈何天。
《红楼梦》怡红院中的丫头麝月,伶牙俐齿,口才了得。还有一种茶亦名麝月。茶饼。古时画眉用的香煤,亦名麝月。
石蒜亦名彼岸花。亦有银蒜,银蒜是一种什么花?不,是古代以银铸就,其形若蒜,用以押帘之物。
有一种以供行脚(僧人)之用的取水瓶,有个古奥冷僻的名字:军持。豆瓣网有位作者,其名亦叫军持,如今始知此名之意。
有一种十六岁的敏感,是“一庭疏雨湿春愁”。
有一种色彩是 “伤心碧”。
有一种表述是“甜腻腻的”。
有一种用牛眼睛做的俄国菜叫“早晨醒”。有一种外国树德语名叫“国王的蜡烛”。
有一种可爱的“小”,叫“一点”。且看那遥山一点,明月一点。而绮艳最是那春心一点,如夕阳红尽处,波心那闪烁不定的光影一点。
火 车
那个小镇靠近铁路。我来时,刚通火车。白昼的喧哗往往掩盖了火车的轰响,但夜晚,声音就特别清晰。每每把我从沉睡中惊醒。
记得我曾在某本书的边角写下这样的句子:“火车来了,是在深夜。梦被碾得稀碎。”这个句子也许有点忧伤。
我记得那时的情景。似睡非睡中,就听见火车从远处驶来。开始,隐隐约约,像钢笔尖从一张白纸上划过。后来,轰轰隆隆,带着震撼性,仿佛近在耳畔。——仿佛是火车驶向耳畔,而不是火车的声音。再后来,又渐渐消失,什么也没留下。这个过程就像回忆载着隐痛,从胸口——这荒凉的平原——一闪而过。开始很重,后来变轻,一切都很真实,但又仿佛什么都没发生。
火车驶过,拖着漫长的黑夜,漫无边际。火车到达黎明还得多远?矮矮的房子,人醒着,窗外是树,枝上是巢,巢上是满天的星。风在空中吹着,很高,很远。
我想象出这样一幅画面:长长的铁轨,一列火车,车厢空空荡荡的,但靠窗的地方坐着一个人。那个人脸朝外,看不清楚表情。他的眼睛里好像看见了什么。
而火车到达黎明还得多远呢?
麦 子
麦穗都出齐了,正等着灌浆。麦子快盖住了外祖母的坟头。感觉外祖母离开我好久好久了。其实,才一百天。
我跪下,给外祖母磕头。额角挨着泥土,刚下过雨,泥土凉凉的。
麦地东边有条小路,一个老婆婆从那儿慢慢走过。我站起来,正好看见她。远远望去,真像外祖母。
过了一小会儿,我赶上她。她正蹲在路边捡拾几根杨树的枯枝。我望着她,心里一热,眼泪就流下来了。
大片大片的麦子,绿沉沉的,在风里一倾一倾。
我转身望去,外祖母的坟头已经看不见了。
芭 蕉
那年乡居,读《东坡集》。有“身如芭蕉,心如莲花”句。秀外慧中,多美的人,多美的形象。掩卷,走出门外,恰好看见妻子从微雨霏霏的绿草地上回來,怀中抱着新掰的玉米棒,缨络如火。
那时,高压电线在风里颤瑟瑟的,线上密密站满了麻雀。
黎 明
黎明是女性化的、植物性的。当然,是晴朗的黎明。这样描述黎明,也可以用来描述汉语。汉语是软的,然而又富有弹性。
黎明不是一种具体的指称,不是一个名词。黎明是一种意象,一种生命的气息。也可以说,黎明是一种美学。
思想者喜欢曙光,其实更喜欢黑夜。诗人才真正喜欢黎明。但古典诗歌则充满某种黄昏意象。一个典型:李商隐。
《诗经》是最初的早晨。是凤鸣。微风清和,一群凤凰鸣叫着,飞向地平线上那轮红彤彤的硕大无比的太阳。
谁是那稀有的黎明化的诗人?顾城。海子属于正午。这里仅就风格而言。
黎明是静的。春风也是静的。雪花也是。闪电呢?黑暗中的闪电,更有一种极端的宁静。——宁静到尖锐的程度。
春天和秋天的黎明是童贞的、有一点单纯的孩子气。夏天的黎明带点娇憨的羞涩。冬天的呢?则似乎带有一点学究式的知性。
地 名
山有欢喜山,滩有惶恐滩。岭有瘦牛岭,峰有回雁峰。县有闻喜县,村有买愁村。渡有秋娘渡,桥有泰娘桥。铺有三里铺,店有八里店。
人性的天真在世俗的复杂境况中,一定会显得悲怆。而地名,是单纯的。
又发现一个美好的地名:落星墟。
《山海经》里的地名,一个个空茫的没有人烟的世界。仿佛无论走向哪儿,都无法返回。看得让人寂寞、孤单。
《水经注》里的地名,历史和岁月,沧海桑田。
孤竹国,春秋时期的一个国名。凛冽苍茫的光阴中,最富诗意的一个国名:楼兰。潇湘(这两个字湮湮的,总有一种迷离清凉的感觉)。
杜子美《秦州杂诗》,“水落鱼龙夜,山空鸟鼠秋”。那么多的动物,挤在一起,但是并不热闹,空落落的。秋风吹到哪儿,哪儿似乎就一下子变得空阔。看注释,才知隐藏着两个地名,鱼龙川,鸟鼠山。
我是个方向感很差的人,记不住路。和朋友外出,导航不起作用的地方,如果我開车,他们就得负责记路;如果他们开车,我则只负责看风景。但我对地名却有一种偏好。
没有特色的地名,记不住。没有特色的人,记不住。
鲤
鲤鱼为鱼中之贵者。
鲤鱼长寿,传说可寿至千岁。一条一千岁的鱼,不是传奇,也是传奇。在人间,称万岁的是帝,称千岁的是王。然而,他们都不是传奇,他们只不过是权势的化身。
鱼跃龙门,唯鲤鱼能够做到,唯鲤鱼能脱胎换骨。这也是人类关于自身精神处境的一个隐喻。对自身的无限超越和提升,也是一种传奇。权势的世界里不存在传奇,而精神的世界里,则可以创造传奇。
李商隐曰:“水仙欲上鲤鱼去,一夜芙蓉红泪多。”哀感顽艳。李商隐是诗人中的一尾红鲤,身影如梦,游到哪儿,哪儿波光潋滟,宛若三尺明泉浸红玉。
鱼劳则尾赤,人劳则发白。
龙
龙有八十一片鳞甲,具九九之数。王摩诘诗,“闭户著书多岁月,种松皆作老龙鳞”。此种生活状态,一直让我神往。
龙性躁,易怒,亦刚硬。所谓,龙性难驯,但蛟龙畏铁。
龙视力极强,百里之外,纤毫可见。但龙却看不见石头,正如鱼不见水,鬼不见地。
蛇易皮,龙易骨。
相学家说,王安石的眼是龙眼。我喜欢王安石晚年的诗歌,超过喜欢苏东坡。王安石晚年的诗歌,是百炼成钢。更胜于黄庭坚的点石成金。
《庄子》载,“朱泙漫学屠龙于支离益,殚千金之家,三年技成而无所用其巧”。朱泙漫实则未达大道。真正有价值的事物,超越于实用性的目的,不可评估和界定。人生的最大追求在于生命的自我完善。技可超越,进而为道。但一个过于实用的目的,本身就是一种最大的限制。从而也让人生的过程变得单调无趣。
龙常变形,为蚯蚓,为蛇,为屋漏痕,甚至为掌纹。所以,这个世界从来是鱼龙混杂,真假难辨。
人中之龙,常常以最普通的形象出现。
雷 声
夜晚,天空响起很多雷声。在很远的地方响,好像那儿发生着很大的事情。
日本的川端康成说,钟声在远处比近处好听。很多声音都是这样,箫,笛,埙。雷声也是。
雷声在近处是一种恐怖,在远处,昏暗的天边,则很好听。
有的雷声空疏,清旷,倒和钟声有几分相似。然而,没有回声,比较斩截。
雷声响了,息了。息了,响了,起起落落。深夜,听雷,心事浩茫。
而《金刚经》上说,“应无所住,而生其心”。雷在天空,如心在尘世吗?
今年不收石榴,收枣子。早晨,看路边满树枣子,有喜悦感。我希望自己能变得更加世俗化,有烟火气。热爱微不足道的细节,对具体生活保持长盛不衰的兴趣。
有两天,墨汁里兑了水,在废旧报纸上写字,写“心平气和”,写“随遇而安”。很多耳熟能详的词语,现在倒咀嚼出新的滋味。
处暑已过,雷很快就收声了。《易经》的观念里,雷是可以存放的,就像窖藏果实。秋天,雷便回到了深深的地下。
天空将变得很静。
落 叶
早晨到父母那儿转了转,父亲正在扫院子里的柿叶。满地的叶子,有的已经变红了。树上还有很多。等几乎落光时,只剩下疏疏几片,点缀在苍劲老硬的黑枝上,通红欲燃,才最是好看。
落叶扫很好,不扫也很好。
扫是人事,不扫是自然。
父亲执着于人事,有落叶即扫。我倾向于自然,喜欢看落叶满地。
但儿子的散漫,有愧于父亲的严整。父亲性情温和,涵养宏大,从没有明确表示过对我的期望。
但我知道,我是辜负他的。
在父亲的眼中,落叶意味着生活中的杂乱。而我,则把落叶当成了一种生活的美学。
年少气盛的叛逆期过去了,我试图向父亲靠近,希望能成为他期望的样子。但已经不能了。我已经成了“另一个人”,根深蒂固。
有人说,当我们不能改变世界的时候,我们不妨改变自己。我并不反对这一生活态度。但很多时候,我仍是一个消极的反抗者。
当我不想改变自己的时候,我就对这个世界疏远。
荒 园
小园荒古。清秋,美人蕉尤显奇艳。抱臂昂首,立老松下,虬枝层叠,有幽深感。桂香一缕,细若游丝,销魂蚀骨。
人生可贵处,是可以观叶绿,亦能赏枝枯。最难得,繁花当胸,而气定神闲。汤显祖尺牍曰,达人所至,皆为彼岸。
此园十年前曾见。十年后重见,恍然如昨。时光悠悠,如一页书,轻轻翻过。然而,内心深处,某个难以确定的地方,还是“刺啦”响了那么一下。
枝 条
花好看,叶好看,枝也好看。《越人歌》,“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悦君兮君不知”,错综复杂的美,如此细密难解的感情,越长越旺,纠缠不清。
明清之際的吴伟业,身当国变,山河破碎。顺治十年(1653),吴被迫入仕。途经临清,天降大雪,赋诗曰:“辜负故园梅树好,南枝开放北枝寒。”不写梅花,写梅枝,冷浸浸的。
我父亲那儿挂有一副对联,“闲携小斧删梅树,自缚枯藤补竹篱”。藤和树,应该都没有叶子了,所以才能如此散淡闲适。
“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木叶脱尽,天就凉透了。那么多枝子,纵横交错,在寒风中,瑟瑟颤动。也许不是颤动,是悸动。风大的时候,枝条你碰一下我,我碰一下你,磕磕碰碰,身不由己,整个世界都乱了。无边无际的天,无边无际的水,一大片一大片的树影。一种冷清清的美。
禅宗里有“珊瑚枝枝撑着月”的话,玲珑疏朗,很有美感。真是枝好月圆。禅宗是一种智慧,却是一种带着美感的智慧。珊瑚枝,是从来不长叶子的,却有树的感觉,森林的感觉。
田 鼠
那天黄昏,去西沙河拍照。我想拍夕阳,就是那种又红又大的夕阳,映着河坝上几枝萧散的芦花。清凉的风缓缓吹着。
又苍茫,又温暖——最后的无法挽留的美,最后的刻骨的一瞥……
返回的时候,在河坝上,我看见前面有一个穿红袄的女人,三十多岁,骑着一辆旧三轮车。只见她停下车子,走到坝子边,在那儿半弯着腰,冲着什么在喊:“走啊!赶紧走啊!别在这儿了。”
在她脚下,原来是一只尾巴短短的田鼠。
它老了,也可能是病了。恹恹地在那儿趴着。
她顺手折了一根蒿草梗,轻轻地把它向草丛里拨拉,用叮嘱孩子的口气说:“在这儿多危险呐,赶紧躲起来吧。”
那只田鼠终于慢慢地爬进枯草丛里去了……
不以自我为出发点,不带任何偏见地去爱,一种自发性的爱——是近乎神的爱。
冬天,枯草的颜色,那种柔和的寂涩的黄,夕阳的余晖留在上面,又隐隐有点红。
责任编辑 夏 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