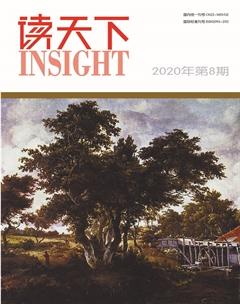现代文学中的叙事者和作者的创作心态关系
摘 要:本文从叙述者的不可靠性出发,剖析了《孤独者》中“我”与魏连殳的三次讨论,提出作者借“我”和魏连殳对峙和辩驳书写自我内心的困惑,实为文本中暗藏的第三位孤独者,同时结合鲁迅所处的时代环境,强调了其知识分子身份与“复调”写作之间的关联,指出知识分子在时代变革下所处的身心困境。
关键词:孤独者;鲁迅;不可靠叙述者;复调;孤独
一、 三个孤独者和一个人的孤独
每部小说都至少存在一个叙述者,他是叙述行为的直接进行者。现身的叙述者与作品中的其他人物一样,是作家创造的产物,也就是说,虽然叙述者有时可以代表作者的声音,但他不等于作者。在某些作品中二者的道德观念甚至会出现距离,叙述者所否定的东西,恰恰是作者要肯定和贊扬的东西,这就是“不可靠的叙述者”。“叙述者可靠性主要衡量标志,是叙述者与隐含作者的距离,也就是叙述者的价值观与隐含作者所体现的全文价值观之间的差距。”另一方面,《孤独者》的故事情节表明,魏连殳是以范爱农和鲁迅为原型的,他在成长经历与家庭背景方面和鲁迅、范爱农有很多相似。鲁迅正是借“我”的声音和魏连殳的声音互相对峙、互相辩驳,写出了自己内心深处的困惑。虽然“我”常常是站在魏连殳的对立面,对他抱着质疑的态度,但不管是质疑者还是被质疑者,他们都代表作者鲁迅在同一问题上真实存在过的矛盾对立的观点。从“我”和魏连殳之间的三次讨论中,可以看出叙述者“我”的可靠性是不定的,这主要是因为鲁迅自我剖析过程的反复与迂回以及“多疑”鲁迅写作的“双重结构”,当然也是《孤独者》的特殊性之一。下面举文中关键的三次讨论来证明上述观点:
第一次讨论是关于孩子。魏连殳认为“孩子总是好的,他们全是天真”,“我”发出质疑“那也不尽然”。(鲁迅原以为“青年必胜于老年”,希望在青年身上,可是大革命失败的教训,尤其是“杀戮青年的,似乎倒大概是青年”的事实,使他意识到了“青年又何能一概而论”,从而在青年与老年的传统命题上陷入了彷徨的境地。)
第二次讨论是关于孤独。魏连殳自认是所有人“消遣的资料”,“我”提出反驳“你看得人间太坏……你实在亲手造了独头茧”。(许广平针对鲁迅的道德敏感和愤激曾批评道“你的弊病,是对有些人过于深恶痛绝,简直不愿同在一地呼吸,而对有些人又期望太殷,不惜赴汤蹈火,一旦觉得不负所望,你便悲哀起来了。”鲁迅后来也自劝道“借自己的升沉,看看人们的嘴脸的变化,虽然很有益,也有趣,但我的涵养工夫太浅了,有时总还不免有些愤激……”)
第三次讨论是关于为何而活。魏连殳觉得“偏要为不愿意我活下去的人们而活下去”,“我”当时“总有些不舒服”,事后“在渐渐地忘却他”。(鲁迅曾说“苍蝇的飞鸣,是不知道人们在憎恶他的;我却明知道,然而只要能飞鸣就偏要飞鸣……大大半乃是为了我的敌人。”在复仇观念上鲁迅没有通过“我”的口来明确辩驳,直到魏连殳死后,才由“我”对出卖灵魂的报复方式无异于自杀的觉悟,来表明否定态度。)
《孤独者》虽然以第一人称的叙述贯穿始终,但叙述被局限在一个人的视野范围之内,只叙述人物知道的事,而无权叙述人物不可能知道的事,叙述者不再是那个无所不知的上帝,而是随着人物一步步走进故事世界,表达着人物的心理情绪。“我”是魏连殳命运的旁观者,从旁观察他的活动,揣度他的心理,一步步地走进他的内心。“我”对魏连殳的看法不是固定的,是在三次讨论中慢慢动摇,慢慢向他靠拢的。说这么多,主要想说明一点:“我”和魏连殳的地位是平等的,鲁迅没有把“我”当作一个权威的评判者,“我”和魏连殳从不同侧面代表鲁迅的声音,反映鲁迅内心的痛苦挣扎。因而“孤独者”是谁,不是文中的村民们或绅士们说的算,也不是“我”说的算,更不是魏连殳自己说的算,而是由读者自己判断。
在我看来,“孤独者”有三个——魏连殳、“我”和鲁迅。三次争论后,“我”和魏连殳友情的由浅及深,到读完信后,“(魏连殳)然而又似乎和我日加密切起来”。这暗示“我”已经在魏连殳筑起的高墙上打通了一角,“我”和他的悲欢能够相通,开始感受到他精神上的痛苦。这个时候,由于拥有“我”的理解,魏连殳就不算真正的孤独者,倒是“我”因为了解魏连殳而成了真正的孤独者:不仅受连累被绅士之流攻击,就连当事人魏连殳都说“我们大概究竟不是一路的”。“我”所不知道的,而为读者所见,实则是还有一个隐含的作者在看,读者正是通过这作者才了解“我”的孤独因子。说到底,孤独这个雪球在三人间滚来滚去,最后滚到最大时,就停在了鲁迅脚下。
二、 “复调”手法与鲁迅的创作心态
就像严家炎和钱理群等证明过的那样,小说中“我”和魏连殳这两个形象可以说都是鲁迅的化身,这种写作手法,有“复调”或“一体二分”的名称。此外,“鲁迅的复调或一分二体,体现的是一种‘朋友关系(朋友之间当然也有争论,但更多的是一致和同情),而不是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样的是‘烦人和‘审判官的关系。”这说法更能证明叙述者与人物在小说中处于平等的地位。
鲁迅小说的“复调性”根源于鲁迅内心的矛盾,小说中两种声音的冲突正是他内心冲突的外化,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复调特征比较集中于《彷徨》。当“五四”大潮业已低落,鲁迅正如他《题〈彷徨〉》诗描画的于“寂寞新文坛,平安旧战场”之间“荷戟独彷徨”的小“卒”,绝望而无所适从,苦闷彷徨的情绪正是导致小说出现复调的重要因素。李欧梵也曾指出,“在信仰与怀疑,希望与绝望之间的这些来回摆动,似乎正是鲁迅创作于20年代的几种体裁的作品的共同特征。这些波动不仅反映了他的情绪的波动,而且反映了他的思想中的根本的不确定性——对思想倾向和未来行动没有把握。”
说复调特征集中于《彷徨》这本小说集还不够准确,它更是以运用于启蒙或被启蒙知识分子为主。我们历来太偏重于认识“革命的鲁迅”和“鲁迅的革命”,密集地探寻鲁迅对国民灵魂和社会改造等问题的思考,然后我们会发现鲁迅在描写下层人民生活时,态度是非常坚定的,思路是比较清晰的,立场也是旗帜鲜明的,流露的彷徨心态是最少的。其实“鲁迅的彷徨心态较集中地存在于他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自身观照之中,即存在于他这一‘主体的深切体验之中……鲁迅作为知识分子的身心体验绝不是‘革命或不‘革命以及如何‘革的问题,而是怎样在社会革命和时代演变中寻找自己的位置并确认自己的命运。”《孤独者》中的魏连殳的行径,让我们体验到知识分子以灵魂冒险重新寻找自己位置的艰辛和痛苦,所谓的“艰辛和痛苦”当然不能仅用孤独感来笼统涵盖,但若是这种体验只为一个群体所认识,再复杂的情感体验都只是“孤独”。
参考文献:
[1]童庆炳.文体与文体的创造[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9.
[2]刘春勇.多疑鲁迅:鲁迅世界中主体生成困境之研究[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2009.
[3]谭德晶.鲁迅小说与国民性问题探索[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4]李欧梵.鲁迅的小说:孤独者与大众[M].伍晓明,译.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3.
[5]闫玉刚.走近鲁迅:改造国民性[M].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5.
作者简介:
徐妍,北京市,童趣出版有限公司。
inor-fareast;mso-hansi-font-family:Calibri;mso-hansi-theme-font:minor-latin'>):148.
作者简介:
李玉萍,山东省莱西市,山东省莱西市望城街道兴华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