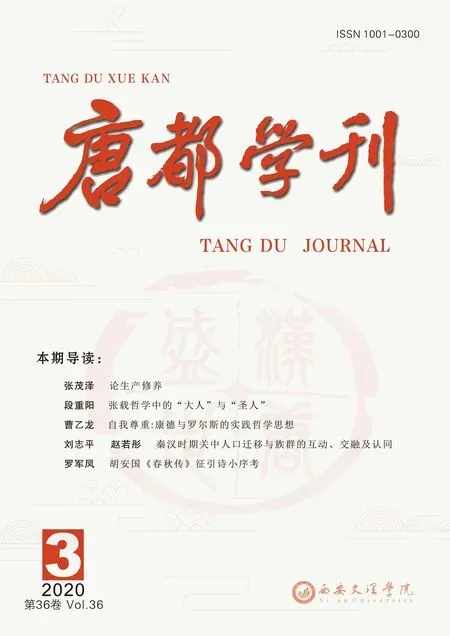心学、理学、关学的交会:冯从吾文学观的融摄维度
常 威
(周口师范学院 文学院,河南 周口 210023)
“出则为真御史,退则为真大儒,是本朝孔庑间第一流人物”(1)参见陈继儒《冯少墟先生集叙》。的冯从吾,是明代关学举足轻重的承继者,李颙称赞他“集其成,宗风赖以大振”(2)参见李颙《二曲集·答董郡伯》。。兼之会通朱陆的理学旨趣,使其成为关学史与儒学史上光辉耀人的重要人物。诚如翟凤翥所言:“先生之学以心性为本体,以诚敬为功夫,以天地万物一体为度量,以出处辞受一介不易为风节……论者谓杨伯起、张横渠、吕泾野诸夫子而后,一人而已。”(3)参见恭定《冯少墟先生传》。当然,自称“素不娴古文辞”(4)参见冯从吾《少墟集》卷15《答吴继踈中丞》。的冯从吾亦不乏诗文之作,并从中显露出心学、理学、关学多维思想的面影。“不娴古文辞”的自我定位一方面暗示了其不以诗文为意,而以理学为本的思想旨归;另一方面则表达了他不事雕琢文字、达意尚质的文学倾向。有鉴于此,受张载、程朱、阳明学多重浸淫的关学大儒冯从吾,其文学主张究竟呈现出一种怎样的面貌,他在其中又如何折衷、取舍,融贯浃洽,有必要加以推阐。
一、做圣人易,做文人难
优入圣域,一直以来是儒家知识分子期望达到的理想境界。随着宋明理学的产生,不管是程朱理学还是陆王心学,都对这一问题表现出浓郁的兴趣。不过,对于穷索外物以尽理的程朱理学来说,优入圣域终因外物无穷、难以格遍而成镜花水月的幻影。但是至陆王心学,他们承继了孟子的心性学说,通过明心见性、反身内索的功夫论,在化德性为德行的具体实践中,找到了一条简便易行的成圣之路。在他们看来,成圣不仅为可期之事,而且是容易达成的一个愿景。对此,我们从孟子的“人皆可以为尧舜”到王阳明的“良知良能,愚夫愚妇与圣人同”(5)参见王守仁《答顾东桥书》。,均可了然。当然,对儒家心性学说有专门钻研的冯氏显然更倾向于此,其尝言“若是肯去好问好察,肯去隐恶扬善,肯去发愤忘食,乐以忘忧,则舜孔有何难为”,进而高树了“做圣人易,做文人难”[1]237的理论宣言。这里冯氏将做圣人与做文人对举,虽然其意图在于劝进众人以殚精竭虑为文之心去做修行成圣的功夫,但是对二者难易之辨的论定不仅宣露了冯氏在阳明心学影响下的话语言说旨趣,而且故意推举“做文人难”的高标,一方面显示了他认为时人即使苦心钻研,文章成就也难以超越古人的事实:“吾侪自入馆来,朝而诵,久而讽,行思坐想,何尝一息不在诗文上用功,其诗文何尝一息不在班马李杜上模拟,真可谓殚精竭力矣!试自反之,其诗文视班马李杜竟何如邪”[1]237-238;另一方面则表现了他深刻的文章志道体悟。
冯氏《少墟集》将文人创作的文章大体分为多能与博文两类,而要想成为一个合格文人,显然不能瞩目于游艺功夫的“多能”(炫辞一类文章可归于此),而应倾心于志道功夫的“博文”。具体来说,“多能是游艺功夫,博文是志道功夫,不可混看。多能是艺,如射御钓弋之类,故曰:吾不试,故艺。博文是讲明道理约礼,是体验身心。此圣门精一之学,原自与多能不同。博文不是在艺上博,虽俯仰宇宙上下古今,只可谓之博文,不可谓之多能,博文与多能盖道与艺之别也”[1]62。这里,冯氏着重辨析博文与多能,可见其对承担志道重任之“文”的重视,对孔子“博学于文”的强调不仅暗含了不是所有的文章都为冯氏所关注,而更多地指向四书五经一类,而且博文与游艺的分歧又进一步将泛滥于文藻、章句的博文趋向做了澄清,进而明确了博文的进路在于明道约礼,这不但与穷索外物以尽知识的程朱理学不同,而且与晚明以来的博学风潮做了划界。当然,这显然也有着现实的指向。时至明代,尽管程朱理学由于官方推举的至高地位而风行天下,但是这时的文却并没有因为程朱理学的炽盛而走向文道合一之境,反而文、道逐渐趋向于离崩,以致时人每有“文佞”之谓,如张恒曰:“近世以古诗文名家,若秉华轮策。……惟意之雕琢,则燕石为珪璋;惟口所吹嘘,则枯荑为兰芷。文愈多而质愈漓,言愈工而道愈远。……文溺心,华胜实,酬应夺志,此近世文人之通患也。”[2]可见,此时的文人大多将文作为谋名获利的手段,而鲜少去涵养停蓄,“讲明道理约礼”,以故“文愈多而质愈漓,言愈工而道愈远”。冯氏对此亦洞见尤深,其《与友人论文书》曰:“今人为文,其主意与古人异,古人为文,主意在发理而翼圣;今人为文,主意在炫辞而博名。主意在理,故读理学诸书易入而易信;主意在辞,故不得不剽取《国策》《庄》《列》以涂人耳目。”[1]252这样的文章即使再多,也只属于多能一类,不符合冯氏心目中“博文”志道的文人标准。
有鉴于此,冯氏明确表达了重志道的主张,其曰:“呜呼!直道难容,枉道易合,与善人居难,与不善人居易,人情乎!……今之选古文者,不过论文章之工拙,至于所以为文何如,则未之辨也。余故表而出之,匪直游艺,且以为志道之一助云。”[1]236可见,冯氏不仅认为学人理应疏枉道而近直道,并且在此基础上推而广之,明确表达了文章不应以工拙作为追求的理想进路,而理应让文章成为志道的佐助工具,否则,落入游艺畛域的文章未免同二氏之书一样,去正学(道)甚远。
据上可知,依冯氏之意,文的功用在于宣阐圣贤之道,然而若没有坚定的体道、行道之心,文章难免会落于游艺一途,故其发出“做文人难”的感喟理固其宜。当然需要指出,冯氏之所以认为“做文人难”恐怕还有更为深层次的原因,其《做人说下》庶几道出了这层涵义。在这篇文章中,冯氏批判众人“特不肯去把做诗文之心为做圣贤之心”,而是“自入馆来,朝而诵,久而讽,行思坐想,何尝一息不在诗文上用功,其诗文何尝一息不在班马李杜上模拟,真可谓殚精竭力矣”,结果却是很难达到前人的成就,去班马李杜远甚。可以说,冯氏之所以有如此论断,除了古人难以超越外,显然还与其深厚的阳明学学养有关。要之,在阳明学濡染下,冯氏显然认为从根本心性上入手,即做圣人、存道心,成就圣人之心来为诗文,才是确保诗文不背离理道的不二法门。对此,我们可从冯氏就道心、人心的区分及解读中得以窥知,其尝曰:“不知心之精神是谓圣,果道心之精神耶?抑人心之精神耶?如果道心之精神也,则心之精神诚是圣;如是人心之精神也,则心之精神是谓狂,岂得概言圣哉!”[1]202可见冯氏明辨道心与人心的圣、狂差异而对道心极其看重,依此而言,如果为文之心是人心而非道心的话,这样的文恐怕只能谓为“假文”,其人也只能是背离于道的“假道人”,而从上述冯氏做圣人易而众人却不愿意为的表述中,不难想见时人鲜少道人之心而更多的是人心之心,这自然不符合冯氏认可的为文载道的完成理路,故而滋生了冯氏对“做文人难”的深入思考。
需要指出的是,冯氏不唯认为“做文人难”,循此理路,其进而触发了解读诗文亦不容易的思想倾向:“诗云:‘鸢飞戾天,鱼跃于渊’,即善说诗者不过以为点景之妙耳。……即善说诗者,又不过以为言天言文耳,而孰知其言天之所以为天,言文王之所以为文也。夫论理而至于上下察至于天之所以为天,文之所以为文,其精微奥妙亦至矣尽矣,蔑以加矣,而皆于诗中发之,诗岂易言哉!”[1]236这里冯氏以为《诗经》“鸢飞戾天,鱼跃于渊”的惯常表达,实包含了丰富的理道内容,只是若不以道心体之而以人心观览,则不免只能得出“点景之妙”的寻常之见。综上,冯氏之所以认为做文人不易,是因为道心并非人人常有,而解读诗文亦困难良多,因为人心之常亦每横加左右,并时刻阻碍着对理道的体认。
二、“作文害道”之辨与文质之辩
毋庸讳言,冯从吾认为理是儒家本归,“他以理之有无区分天理与人欲、道心与人心、善与利、善与恶、义与利、公与私,认为此外无道(《善利图说》)。又以这个理作为辨别儒与佛(老)、儒与俗的根本。”[3]如此论调,显然与程朱理学的理本主张一脉相承。而观冯氏《少墟集》,亦可知冯氏言语纯正切实,字字句句体现着其深厚的理学修养与救世情怀。冯氏自幼践履理学,痴心不改,其尝云“谈文谈诗不作一戏谑语,里中人以道学嘲之……不为变也”(6)参见冯从吾《森玉馆集序》。,是以赵南星《冯少墟集序》称述他“是真能学圣人者也,是真能为君子者也,是真能使天下人为君子者也”。而正是因为他对理学的极其看重,也极大地影响着他的文学认知及主张。
就文学的认知而言,理学与文学相互影响的情况,是理学家经常触及的一个问题,而作文害道则是较为常见的一个表达。例如程颐曰:“问:作文害道否?曰:害也。凡为文不专意则不工,若专意则志局于此,又安能与天地同其大也。书云:玩物丧志,为文亦玩物也。”[4]对于这一问题,冯从吾之论并不如程颐那么激进,明言诗文不应废,在《游秦小草序》中,顾生用曾“欲焚其所为诗文而颛精于理学”,而冯氏虽然对顾氏一心向往理学大加赞赏,但同时又以“子欲焚所为诗文,则诗文不必焚也”来劝诫,因为“所谓理学者,非外庸行而别求圣解也。如能诗文者不以诗文自满,不以诗文骄人,不以诗文骋离经叛道之语,若无若虚,成象成爻,天下理学莫大于是矣”,紧接着他又举具体诗文例证以表“诗文何妨于理学”曰:“三百篇多发理之谈,故为万世诗人之祖。汉魏以后人争工于词而不求精于理。……诗文理学分而为二,彼盖徒知以切磋琢磨为说理,而不知鸢飞鱼跃尤为说理之妙也。”[1]225他更喜欢像《诗经·大雅·旱麓》“鸢飞戾天,鱼跃于渊”那样,以自然之景对理趣的触发领悟为高妙,而不太喜欢《诗经·卫风·淇奥》“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之语久已定格为道德修养的比附义。从这里可以看出他对诗文如何达到“说理之妙”颇有思考。
这里冯氏显然不认为诗文与说理相碍,恰相其反,其认为以诗文说理,只要发挥妥当,亦有无尽的妙用。正是循着这一理路,冯氏表达了折中理学、文章的倾向,而理学与文学为一则是其理想的为文境界。其在《濂洛文钞序》中阐论曰:“三代以前,以理学为文章,故六经四子之书为万世文字之祖。三代以后信理学者或天资笔力不能为文章,为文章者或恃才傲世不肯信理学,此理学、文章所以分而为二也。……因刻濓洛文抄以救之。呜呼!学者读此而有悟,则理学、文章庶几可合而为一矣。”[1]210-211而其在《与邓允孝布衣》中也表达了类似看法,其曰:“忆昔有一文人曰周程张朱,不能为诗文,托之理学,遂成名于后世,意盖嘲之也。一客应云:‘周程张朱不能为诗文,一托理学,尚且成名于后世,若能为诗文者而又从事于理学,其名岂不在周程张朱之上邪!’其人大为惶愧,因悟而为世名儒。不佞闻其言快甚。”此则轶事表明冯氏并不轻视诗文创作,“为诗文者而又从事于理学”庶几可作为冯氏对理学、文章二者关系的总体倾向,是以其称述邓允孝“游秦佳刻,笔气超脱不群,从此熟去,不患不到李杜堂室也”[1]270。而为理学者借诗文以说理或能起到更好的效果,是以其在解读理道时也往往引用诗中之语以作说理的资助,如其尝在解释“淡”时引用诗语曰:“诗云:衣锦尚絅,恶其文之著也,只是个淡,故下文即曰淡而不厌,学者只凡事淡得下,其识见自别,其品格自髙,不患不到圣贤地位。”[1]108
毕竟冯氏理学思想深固,故而其持有的文学立场不可能脱尽理学的牵绊,这又不可避免地将理学凌驾于文学之上。冯氏虽然反对为理学不能为文学的主张,如“汉人之文、晋人之字、唐人之诗,自是宇宙奇观,自足令人欣赏,学者但以此为游艺之助则可,若以此为正学之妨则不可。”[1]62更抛除了“作文害道”的极端认知,但是骨子里却不可能涤尽理学家传统观念的影响,故其字里行间时常流露出轻视文学之论。如其言称“于诗文直榆荚视之”曰:“楚侗先生《维风编》中有云:知道者之于诗文,直榆荚视之可也,余读之以为知言。”[1]110又如其认为:“诗文一事虽亦是古今不朽之事。……(但)圣人功夫所重不在此,故圣人不禁人题诗、作文、写字,亦不教人题诗、作文、写字。天资高、有余力、不妨正务,学之无伤,不然,不学亦无伤。”[1]62而若二者必选其一的话,冯氏则明谓“弃去文词不理”曰“学者弃去道学不理诚不可,若弃去文词不理有何关系。……能文者自是能文,不能文者自是不能文。能文者而不理此,正道学不自恃其所长;不能文者而不理此,正道学不自护其所短。”[1]139
也正是冯氏持守浓郁理学旨趣影响下的理学、文学之辨,故而他虽每将事功、节义、理学、文学相提并论,但又标举理学为本的立论,如其《池阳语录》中称述“关中四绝”时曰:“吾关中如王端毅之事功,杨斛山之节义,吕泾野之理学,李空同之文章,足称国朝关中四绝。然事功节义系于所遇,文章系乎天资,三者俱不可必,所可必者惟理学耳。”[1]184这里,冯氏将李梦阳之文章罗列于关中四绝之一,足见他并不轻视以文章名世的方式,而“文章系乎天资”也使其脱去了理学家文章体认的迂腐气息,只是在文章、事功、节义之外,更看重理学而已。也正是在以理学为本的思想浸淫下,冯氏明确表达了“文章以理为主”的思想:“上而六经孔孟,下而濂洛关闽,夫非理学之渊薮,而修词之标的与!试取此诸书读之,犹令人鄙吝消融,心胸开朗,勃然有正人君子之思,即不然而亦不至于为纵横为虚无也,故曰文章以理为主。”[1]252“文章以理为主”颇堪玩味,其不仅表明冯氏对传统“文以载道”观的依归,而且对“理”的突显则暗示了其基本的理学立场,是他站在程朱理学角度,思考文章功用、明确文章价值的反映。
对此立论,我们从其对韩愈的极度推崇中可以窥见。其《董扬王韩优劣》曰:“愈之为文,岂颛颛刻画于词句间哉!第上书及门,其出处之际,尚有遗议,愈于吾道盖合者多而离者少也。程子谓愈亦近世之豪杰,谅矣!”[1]286不唯如此,这种“文章以理为主”的思想观念,在其《古文辑选跋》中坚持的选文标准中亦可窥见,如选文中未选韩愈《诤臣论》,对于未选原因,他论述曰:“退之果与亢宗厚善,忠告善道宻规之可也,如规之而听善则归友,不自以为功可也,如规之而不听不可则止,不成人之过可也,如不厚善则言与不言,置之不谈可也,乃见不出此而著着为论以翘人过,文虽工,其如失朋友之道何?”[1]290可见冯氏不选《诤臣论》乃在于其不符合儒学三纲五常之道,且不合于孔门中和之旨(《中和吟六言十绝》曰:“此心常是中和,犹恐客气易肆。若把此心放开,客气何所不至。”[1]313足见其对中和的推崇,而韩愈诤臣之论显然有泄私愤的嫌疑,故其不取),因此即使人如韩愈之美者,文虽工,亦不选取。此外,我们在其对宋儒之文的态度中也可以窥见。毋庸讳言,对宋儒充满眷顾之情的冯氏对宋儒之文亦充满欣赏,因此他极力为宋主理之文袒护曰:“夫宋之文载于性理(7)这里提及的《性理》一书所指为《性理大全》,冯氏在《少墟集》卷6曾将“四书、五经、性理、通鉴、小学、近思录”并举,是以可知。而翻检《性理大全》,此书广收宋代理学家周敦颐、张载、邵雍、朱熹等人的理学著作及语录,其文但以析理阐微为主,不以雕饰文字为念。这里冯氏极称之以代表宋文,可见他对明理之文的侧重。一书,其雕章琢句,焜燿耳目,不逮国策诸书,仆不敢强为左袒,但其析理阐义,羽翼圣经,亡论韩欧,即秦汉有之乎!”[1]252
冯氏“文章以理为主”也体现于他的诗文写作中,《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骘其创作曰:“其中讲学之作,主于明理;论事之作,主于达意,不复以辞采为工。然有物之言,笃实切明。虽字句间涉俚俗,固不以弇陋讥也。”[1]1具而言之,他的诗歌虽然今存不多,但大多是宣扬理道的性气诗。至于他的散文,更无时不在高扬着文以载道的旌旗。可以说,“他的散文毫不隐晦文以载道、经世致用的写作目标。甚至可以说从吾的散文是功利主义的,他要当时的社会以古代贤圣的言行为准绳,深思致力践,格物致知。”[5]
综上,以理为本根的冯氏在文学主张上也坚持文以理为主。这样一来,也形塑了其“文质并重,以质为主”的文质观,除了自己无意雕饰的文章书写可见其尚质的主张之外,他在《长安县志序》中重申了这一观念曰:“呜呼!志以纪事,惟求实录,第令后世文献足征,无贻以文胜质之诮足矣!乌庸绘章饰句以夸多斗靡为也。”[1]229不过冯氏尚质的为文倾向并非寻常意义上的普适抉发,筑基于文质之辨上的这一表述使其极具形而上的学理思辨意味。他在《池阳语录》中曰:“盖文质不是对立的,亦不是六分四分低昂的,譬之一木质也,斫而为器,则文矣;器质也加以彩饰,则文矣。文质岂二物哉!第雕斫彩饰不可太过,使文胜质耳。是知无方之爱敬皆从孩提知爱一念生来,知此可以论文质矣。”[1]196这里冯氏文质非二物的表达尤为引人瞩目,在其看来,文质同体,不可分离,离质则文无所发其用,离文则质无以自广,是以文即质的扩充面,质即文的缩小面,所谓孩提知爱与无方之爱者。稍后刘宗周的表述则更为具体:“文质同体而异情。质必有文,文乃见质,可合看不可相离。故曰:文犹质也,质犹文也。”[6]以此来看,冯氏文质非二的理论阐发乃是促使他不事雕琢文章书写的根源所在,而他的尚质侧重也因此脱离了一般层面上的文质分离及主从论调,而某种程度上也具有了“尚质即是尚文”的生成意义。
三、学贵自得与文需自得妙悟
学贵自得之说,前贤如程朱陆王等皆有阐发,如程颐曰:“学莫贵于自得,得非外也,故曰自得。”[7]而王阳明也因提倡自得而有对为己之学的强调,其尝曰:“学贵乎自得也。古人谓‘得意忘言’,学苟自得,何以言为乎?”[8]至会通程朱理学、阳明心学的冯氏也继承了他们在自得方面的理论主张而对自得每加强调:“心上默默有透悟处,默默有自得处,然后能一一尽道,一一当可尽道当可,非可以袭取而卒办也。”[1]201尤对阳明心学的自得成圣主张颇为倾心:“圣道在心,不在迹,学圣人者亦求诸心焉足矣!苟不能自得于心,而徒曰宗庙百官如此乎富且美也,登东登泰如此乎小鲁小天下也,则游宫墙、登泰岱者,其人岂尠哉!何希圣者竟寥寥也?”[1]222其又曾引用孟子之语明言自得的重要性及如何才能达到自得的方法曰:“可见学不到自得,终是支离,终不能取之左右逢其原,若不深造以道而曰我能自得,又无是理。”而紧接着冯氏又论述了与其自得之论相契合的“头脑主意”之说云:“学问功夫全要晓得头脑主意,深造以道,主意全为自得,博学详说,主意全为反约,博学详说正是解深造以道,反约正是解自得,以自得为主意,以深造以道为功夫。……学问晓得主意才好用功夫,用了功夫才得到妙处。”[1]205而在《池阳语录》中冯氏对如何达到自得而有主意之途表述尤明,其阐述“知止”则胸中自有主张曰:“孔子十五便知止于从心所欲不逾矩,所以终身学问都有着落。一知止则胸中便有主张,便有无穷妙趣,当下便活泼泼地,定静安虑正是知止妙处。”[1]186
不过或由于冯氏不满于程朱陆王的为己自得之说过于笼统,容易使人与老庄自适自得相混淆,因此冯氏又对二者辨析尤详,其曰:“自得自适与吾儒之说不同,只是要自家讨便益、讨受用,不管别人死活,此庄子之逍遥所以坏心术而得罪于名教也。”[1]193可见在冯氏看来,自得并不能只是自己受用,而应该遵循格物、致知、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逻辑进路,否则难免与庄子所言趋同。
需要指出的是,冯氏自得之说,虽然有对前贤的绍继,但更多的是源于其对儒家“反身归诚”心性之学的特别关注。可以说,师承许敬庵的冯氏受心学思想熏染,对阳明学非常推崇,其《答张居白大行》曰:“王文成之学,其得失正不相妨,其得处在致良知三字,直指圣学真脉,且大撤晩宋以来学术支离之障,晚宋儒者徒知文公著述之多,而不知其非有意于立言也。”[1]274而其“《辨学录》凡八十一章,其首章云‘圣贤学问总在心上用功,不然即终日孳孳属枝叶耳’,所以辨心学甚详”[1]4,由此更见其对传统儒家心性之学的瞩目,相较于前儒来说,有过之而无不及。也正因为冯氏对儒家心性之学的特别关注,故而激发了其对“自得”的强调,进而形成了重自家而不徇人的思想面向,其不仅认为《论语》“为人谋而不忠乎是就自家为师说,与朋友交而不信乎是就自家与朋友说,传不习乎是就自家为弟子说”[1]50,而且尝曰:“凡天下事果于道理见得明白,自家就该做去,不该徇人。……吾字正是圣人不肯徇人处,不然空慨叹一场,徒说别人,不是自家,依旧落了世俗蹊径。”[1]60由上可见,在冯氏看来,孔子“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言而不信乎,传不习乎”之语均是自家体悟之后的与人诉说。不惟如此,他还认为一旦自家于道理看得透彻,就该努力去做,万不可以别人之是非好恶为是非好恶,以免“落了世俗蹊径”。
而在冯氏学贵自得的思想主张下,其对诗文创作及相关评价也秉持了这一原则,于此而言,其论述举业文章时点出的为文需妙悟之说可为代表。其曰:“今四子书治举业者,举能言之海内坊刻几于充栋,中间亦有当者不当者。然为举业而作,则为文而解其义不为身心,而求其旨也,虽能疑且思,思而有妙解出,若过于汉之训诂,吾终以为得而未得。是纸上之机括,非心中之妙悟。”[1]37这里冯氏认为举业文章若不是自家身心体贴出来的,即使其妙解有过于汉儒训诂,然而只能谓为“纸上机括”,所谓得而未得者,而真正的举业文章,理应是在“心中妙悟”指引下发抒一己的自得之见。是故,其在《观书吟》又阐述了文章写作中“立意”的重要性曰:“立言先立意,意定始修辞,欲得辞中意,当看未立时。”[1]310显然,这里的立意自然也是自家体贴出来的“自得”之意。至于主意从何而来,冯氏亦有专论曰:“仆以为六经孔孟,其正鹄也,濂洛关闽,其嚆矢也,注精凝神于此,务必至于解悟而后已,则此心确有主意,而后间取国策秦汉及诸子百家之书读之。”[1]253这里冯氏认为立意应首先解悟孔孟理学诸书以获得自家主意,而后涉猎诸子众作辅助之,以此方为文,方可为朴茂、为大雅,为艺苑良工。
此外,冯氏为文需自得的思想面向,我们从其对朱伯明诗集的评述中庶几亦能窥知,其曰:“伯明自幼即嗜书,而尤嗜诗。……自三百篇而下以及我明空同诸子诗,无不昼夜伊吾,朗然成诵,而伯明之诗遂骎骎入古人堂室矣。为汉魏则汉魏,为盛唐则盛唐,而绝无纤巧脂粉、掇拾饾饤之病。”[1]236冯氏谓朱伯明“为汉魏则汉魏,为盛唐则盛唐,而绝无纤巧脂粉、掇拾饾饤之病”不能不说是朱伯明博学众人而自成一家之言、自得于心的反映,而冯氏以此称述之,亦表明了其认为为文不可“纤巧脂粉、掇拾饾饤”的理论向度,而所谓“掇拾饾饤”,则明确指出了为文不可抄袭堆砌,而理应自得于心的理论诉求。
四、动亦是静与为文法门
主静堪谓冯氏重要的理学旨趣,但是融会贯通的冯氏又并非舍动以专言静,在前贤如张载“静亦有动”(8)参见张载《横渠异说·上经》。、程朱“以静制动”(9)参见朱熹《朱子语类》卷67。、阳明学“静未尝不动,动未尝不静。戒谨恐惧即是念,何分动静”(10)参见王守仁《传习录》下。有关动静关系论述的影响下,其动静持论亦极具思辨色彩。如其首肯“心不妄动”解静之语曰:“心不妄动四字解静字,真发古人所未发,盖身不妄动易,心不妄动难,人心原是神明不测、活泼泼地的,岂能不动,只是不妄动,便是静,非块然如槁木死灰,然后为静也。”[1]39而其《答杨原忠运长》则详阐动、静之间的关系曰:“静时乃道之根本,方动时乃道之机括,动时乃道之发用。学者必静时根本处得力,方动机括处点检,动时发用处停当,一切合道,然后谓之不离。然必在静时根本处预先得力,方动机括处再一点检,然后动时发用处才得停当。”[1]261可见,对于冯氏来说,静乃是道之根本所在,而一切之动皆需在静时“预先得力”,方能停当无差。具而言之,“在这里,冯从吾说的静时的工夫是指戒慎恐惧、静坐和‘体验未发气象’等,而方动时的工夫则是指慎独、诚意。也就是提倡存养与省察同时进行,不偏一边。不过,由于静时是道之根本,动时是道之机括和发用,所以如果能在根本处得力,时时保持心体的湛然虚明,那么方动处就自然能够点检,其发用也就自然能够停当,‘随其所遇,不必一一推勘,而纲常伦理自然尽道,喜怒哀乐自然中节,视听言动自然合礼’,一切都会合于道。”[9]
值得注意的是,冯氏重视静并扩大了静的原属状态,而涵括了更为广泛的内容。其《示东昌聊城两学诸生》尝云:“有耳目口体便有视听言动,有视听言动便就有非礼处勿之云者,是动中求不动之意也,动而不动则动中能静矣,动中能静则静中能静,又何待言。静固静,动亦静,无内外、无将迎,此孔子之所以为四绝,而颜子之所以为四勿也。”[1]108对此,陈来总结曰:“冯从吾为关学学者,反对为学专归于静坐,所以主张不睹不闻是道体,可睹可闻、鸢飞鱼跃,亦无非道体;静是道体,动亦是道体。”[10]诚然,冯氏消融了动静的表面划界,代之于追求一种融合无间的动静状态,而一归于静。如其认为也应把读书、作文视为一种静坐休息的状态曰:“杜门静坐,息也。读书、作文、歌诗、写字,亦息也。与严师胜友讲道谈学,用以收敛身心,扶持世教,尤息之息也。如此常常用功,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1]149
而冯氏的这一理学动、静旨趣在其教导士子写作科举文章时也得以体现,其曰:“如诸生考试当题未出时,安得无故下笔,故曰无知。及题既出,因他题目才发动起我的文思,故曰叩,及文既完,尚还有一句一意不尽发于文内否?故曰竭。及交卷后,胸中依旧是题未下时光景,故曰吾有知乎哉,无知也。”[1]188显然,主张以静来涵养心性的冯氏认为文章的写作状态与流程也应合乎“静”。是以其云在未见科举题目之时,诸生要保持一种湛然虚明的“无知”虚静状态,所谓“静时乃道之根本”;睹见题目后,则要诚其意,发动文思,而竭尽自己的旨意,所谓“动时乃道之发用”;交卷后则需回归虚静的状态,所谓“动中求不动之意也,动而不动则动中能静”。显然,这样的写作规导是“学者必静时根本处得力,方动机括处点检,动时发用处停当,一切合道”真实反映,也是冯氏持守“论本体不离功夫、论功夫不离本体”(11)参见吕坤《呻吟语序》。的必然结果。而这一倾向其实不特为科举文章时是这样,对于写作其他文章亦有普泛意义。
五、躬行践履与以文观人

而冯从吾的这一躬行践履主张,在其维护讲学的《讲学说》中亦多有体现。可以说,时至晚明,流于空虚无根的讲学风气受到时人的质疑与批判,但是坚持道不讲不明与学人必有师的冯氏并不作如是想,其认为讲学之功用正在于消除弊端,所谓明道之用,只要讲学者将所讲之理学躬行践履,不务空言,则讲学亦无所伤。显然,冯氏反对时人废除讲学的主张,而极力为讲学张目,当然,当此之时,冯氏未尝不洞见到学人因杂引佛道而日益严重的崇尚玄虚风尚,故而其特意标出“躬行”二字,以救时弊:“药玄虚之病者在躬行二字,既学者多讲玄虚,正当讲躬行以药之可也。”[1]142而在《讲学说》中,其又重申这一观点曰:“讲学之谓何,且人之议之也,议其能言而行不逮耳,能言而行不逮,此正学之所禁也者,人安得不议之。吾侪而果能躬行也,即人言庸何伤。”[1]238
自然,这一躬行践履的理论主张与文学的交会,便表现为冯氏将文人之诗文与文人之行结合起来,进而有以诗文观人之论。其在回答“理学与举业同异”的问题时,便直接表达了“以举业体验于躬行便是真理学,以理学发挥于文辞便是好举业”[1]185的期冀(这一观点的抉发可谓冯氏为解决日益形式化的八股时文的一种救弊举措,其实就明中叶以后的学术风气来说,学而不行成为难以革除的时代弊端,所以王阳明高举“知行合一”的大纛,而冯氏亦重践履,均可谓明见问题本源)。而其《理学诗选跋》与《古文辑选跋》更是成为其践履以文观人思想的具体实施,其在《理学诗选跋》中明确指出选理学诗的标准在于观其人曰:“选理学诗与选唐人诗异,选唐人诗论诗不论人,所谓人以诗重也。选理学诗论人方论诗,所谓诗以人重也。呜呼!学者将人以诗重乎,抑将诗以人重乎?读是编可以自悟矣。”[1]289而在《古文辑选跋》又以具体事例阐述这一题旨并将之推广到理学诗之外的古文辞中曰:“余既辑古文成,或曰《李斯上秦王书》古矣,胡删之?曰:‘焚书坑儒,其人非也。’或又曰:‘既删之而目录中犹存其名,何也?’曰:‘存之以为世戒也,见做人一差,即文如李斯,亦不足传也。’”[1]290此外,其在评述他人的文学成就时也多瞩目于此,如其在《紫阳杨先生》中引述赵复之语评骘杨鉴山曰:“关西夫子江汉赵复序其集,称其志、其学粹然一出于正,即其文可以得其为人,其见重如此。”[1]341
甘蛰仙曰:“少墟哲学思想,在晚明时代大放异彩,其主要论点只是不偏于本体论的一极端,亦不偏于功夫论的一极端。既用这副不偏不倚的眼光,去观察历史上的孔家哲学,更用这种不激不随的手段,去批导当时的思想界。”[13]诚然,冯从吾不仅以一种不偏不倚的中和态度(冯氏有《中和吟六言十首》,由此可见其对中和的看重)去看待理学本体与功夫问题,更是将这一看待问题的思路扩展到文学认知的领域,从而在融汇心学、程朱理学、阳明心学的基础上,完成了其圆融又颇具启发意义的文学理论建构。可以说,他的理学、文学并不相碍,但以理为本的文学倾向明显烙刻了程朱理学的印记,将主静但又标举动亦是静的主张融渗于文章写作举措,固然是受到理学、心学、关学濡染互渗的结果,但又体现出自己的独有特色,其文须自得妙悟的思想则与阳明学派的文章观多有契合,而由注重躬行实践带来的对文人之行的重视则更多地是注重实学的关学传统氤氲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