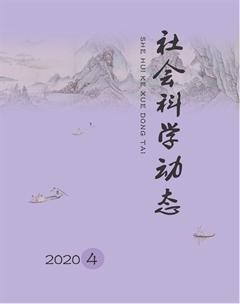论马克思异化理论的后现代批判形态转向
孙金琛 刘国帅
摘要:马克思的异化理论作为其思想中强有力的批判工具,在总体上呈现出由对人自我异化的批判向对人被物及与物关系异化的批判发展的趋势。在资本扩张的全球化视野下,异化理论经过了“法兰克福学派”与“法国理论”的吸收、发展及转嫁的过程,呈现出社会总体异化观与生活异化观的新形态。之后,鲍德里亚通过对消费社会的批判昭示了抵抗策略的复兴,其符号学与政经批判的结合塑造了激进的拟像世界;齐泽克将精神分析与政经批判相结合,开辟出“形式透视”的辩证策略;柄谷行人则深入政经批判的内部,通过解读马克思文本中批判立场的多重转变而提出了“联合”的抵抗策略。
关键词:马克思;异化批判;鲍德里亚;齐泽克;柄谷行人
马克思将异化理论与经济生产结合后,成功地揭示出“生产劳动—异化—社会”的图景,在此基础上开启了政治经济学批判并写作了《资本论》,建立了唯物史观的科学范式,但是异化概念的具体指涉却伴随马克思的问题转向而发生改变,国内外的研究者对此有不同的见解。例如阿尔都塞指出的“认识论断裂”(epistemological break),这种断裂意味着两种理论范式的转变,即从意识形态哲学向历史哲学的转变①;国内学者则在这一分别的基础上延伸出异化的“道德评价优先”与“历史评价优先”②,前者意味着人道主义的立场,后者则意味着唯物史观的立场。同时,这一创见弥补了阿尔都塞简单区分所导致的后果,即马克思视角的转变并不意味着前后期的见解相抵牾,相反,细读文本后会发现这两种见解往往同时出现,只是在不同时期各有侧重③。
除了分析马克思异化理论发展变化的过程外,马克思主义者或与马克思思想相关的理论家们,对异化理论的开拓与创新更是层出不穷。学术界习惯于将卢卡奇、葛兰西之后的二战时期德國理论家称为“法兰克福学派”,他们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及对其进行阐释,而不是用其他思想体系或理论观念去取代马克思主义。在他们之后,马克思主义研究形态开始变得多元和融合,出现了两种“后马克思主义”(Post-Marxism)的旨趣,一种以恩斯特·拉克劳(Ernesto Laclau)和尚塔尔·墨菲(Chantal Mouffe)为代表,他们质疑马克思主义在当下生活中的理论有效性与实践可能性;另一种后马克思主义的定义更为宽泛,他们没有一致的观点但却采取了相似的方式,即将经典马克思文本与不同的哲学范式相兼容,虽然继续停留在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框架内,但同时也将马克思主义延展到新的语境中去④。本文将在后者的基础上讨论后马克思主义中有关异化抵抗策略的不同主张,他们是在信息全球化的新背景下重新激活这一主题的,因此他们聚焦的问题相近但是却做出了不同的回应。
一、马克思之后异化理论的发展与抵抗策略的复兴
异化理论在马克思的文本中已经相当成熟,异化理论的发展经过了从以人道主义批判为主向唯物史观批判为主的转变。早在《论犹太人问题》中马克思就谈及人的解放,所运用的批判方式便是“道德评价”与“历史评价”的交叉进行。在谈及现代政治国家的建立时,马克思就注意到政治解放的虚假性,认为它不过是将“市民生活的要素,例如,财产、家庭、劳动方式,已经以领主权、等级和同业公会的形式上升为国家生活的要素”⑤,因此,人没有摆脱旧的社会关系与生产关系,只是在现代政治国家中通过将市民社会关系合法化来“解放”个人,而市民社会关系则成为了现代政治国家的“自然基础”。在此基础上马克思用犹太人的例子隐喻了资本世界的到来,即犹太人牟取利益的犹太精神在世界范围内横行,“犹太人用犹太人的方式解放了自己”。显然,马克思在这里攻击的正是黑格尔辩证法,这种“解放”的虚假性并不被马克思所认同,他一再重申“任何解放都是使人的世界即各种关系回归于人自身”,“只有当人认识到自身‘固有的力量是社会力量,并把这种力量组织起来因而不再把社会力量以政治力量的形式同自身分离的时候,只有到了那个时候,人的解放才能完成”⑥。“固有力量”也就人的生产力本身,这种力量与人的分离即异化。在《论犹太人问题》中马克思已经揭示了政治、经济关系对人的异化,但仍然是以“道德评价”为主的;而在随后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与《资本论》中马克思则主要通过唯物史观的方法详细考察了经济生产关系与国家制度关系,同时将异化的根源追溯到人的生产劳动关系中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使劳动条件和劳动产品具有的与工人相独立和相异化的形态,随着机器的发展而发展成为完全的对立”⑦,因此异化的总特征表达为“在现代世界,生产表现为人的目的,而财富则表现为生产的目的”⑧。
显然,异化理论在马克思思想光谱中是浓墨重彩的一笔,我们既要看到马克思在研究范式上的转变也要注意到批判立场的多样。总体上我们可以将马克思异化理论的转变总结为由对人自我异化的批判向对人被物及与物关系异化的批判发展。在马克思之后,异化理论被看作意识形态批判而一度遭到摒弃,不论是科学社会主义弥漫的第二国际,还是斯大林的《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都没有视异化理论为社会改造的必要手段,直到卢卡奇在《历史和阶级意识》1967年新版序言中提出“人的异化是我们时代的关键问题,并且无论资产阶级还是无产阶级的思想家,无论政治上和社会上的右派还是左派思想家都看到和承认这一点。”⑨ 在卢卡奇之前还活跃着一批苏联之外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他们被称作西方马克思主义(Western Marxism)或“法兰克福学派”,他们“通过将社会哲学和经验性的社会科学镕铸于一炉来克服马克思主义的危机”⑩,以霍克海默与阿多诺的《启蒙辩证法》为起点,宣扬了一种社会总体异化观的批判态度,他们指出,“人类为其权力的膨胀付出了他们在行使权力过程中不断异化的代价”,这一代价具体表现为“生存者之间各种各样的亲密关系,被有意义的主体与无意义的客体、理性意义与偶然意义中介之间的简单关系所抑制”{11},人与外界或他者的关系成为单调甚至是匮乏的,这在某种程度上呼应了卢卡奇。卢卡奇将异化问题放置在超越党派界限和社会形态的位置上,这样做的目的一方面是对斯大林主义提出异议,另一方面则是在苏联之外的地方寻求马克思主义的“复兴”。随着1968年的到来,“布拉格之春”昭示了以苏联为代表的东方马克思主义(Eastern Marxism)的幻灭,而法国的“五月风暴”则掀起了另一股马克思主义“热潮”,这一思潮被称为后马克思主义,其总的特征首先表现为一方面从马克思的问题出发,另一方面则积极融合其他哲学思想开拓新的研究范式;其次他们不像“法兰克福学派”那样彼此联系密切且拥有统一的阵线,后马克思主义者之间往往是离散的状态,但是在理论塑造上又保持着隐秘的相似性;再次,后马克思主义与“法兰克福学派”虽然都保持了马克思批判哲学的传统,但前者则进一步将批判的领域延展进生活之中,这也体现出经济全球化与信息全球化新背景下的迫切需要。
资本扩张走向全球化不仅为理论家们提供了新的语境养料,还为新的思想提供了契机。“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路线之所以仍然是马克思式的,原因之一在于其背景仍处在资本扩张期,不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还是美苏二元结构,都带有资本扩张矛盾的不同表现,而马克思的批判思想则完全适用于对资本生产、流通及总过程的分析。但是在全球化的语境中,为何后马克思主义者们会有不同程度的背向马克思?诸如让—利奥塔(Jean-Francois Lyotard)在政治哲学上表现出暧昧不明的姿态,而让·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则在批判哲学的范式上抛弃了马克思。当然也有以激进左翼思想家自居的齐泽克(Slavoj ?譕i?觩ek),以及意图恢复马克思哲学范式的柄谷行人,这些将在后文中得到讨论。笔者认为这折射出马克思主义在当代所面临的危机,即在全球化的资本结构下如何复兴马克思主义传统。后马克思主义者认为通过改进反资本主义的抵抗形式,可改进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所做的判断,而不是守望幽灵的回归(德里达语)。当下的资本世界结构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超出了马克思文本,诸如产业资本全球化的金融业,广告文娱、大众文化以及信息与人工智能,这些是马克思远未预料到的。但是问题的核心仍旧是资本生产矛盾与资本社会结构,因此我们仍然共享着马克思的问题,仍旧处在马克思的“时代”。
随着全球化进一步改变日常生活的形态,法国也出现了一批反思批判日常生活的后马克思主义者。亨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通过日常生活批判理论重新讨论了人与人化自然的存在关系,这一问题是在马克思的基础上结合存在主义展开的。列斐伏尔指出,人虽然创造了自身,但是人本身并非自己的产物,而是在创造活动之中实现的。恩格斯曾指出“劳动创造了人本身”{12}。列斐伏尔通过考察这一创造过程对人的反制,得出“当这种活动转而反对人的自身时,就有了外部的性质,并把人类引入社会决定论中,使人类蒙受极大的不幸”;面对资本结构化的世界列斐伏尔坦言“似乎分化、分散、矛盾等一切不好的东西今天都出现并集中在为数众多的不幸的人类身上”。这一现状促使他关注马克思的异化理论,但是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所设置的主体并非无产者而是整个人类这一存在者,因此异化是普遍存在的,甚至超出了卢卡奇对社会形态的认知,因而他申明“异化是全面的,它笼罩了全部生活”{13}。
面对固化的社会形态,伴随而来的便是“抵抗策略”的复兴。后马克思主义者们不仅感受到了马克思主义面临危机,而且人本身也面临着危机。可以说,抵抗策略区别于马克思的扬弃,抵抗策略作为面临危机的回应,缺少了扬弃内蕴的历史辩证过程,但是发扬了能动性的形式力量。让·鲍德里亚就对固化的社会形态进行了鞭辟入里的批判,在1970年出版的《消费社会》一书中便将其博士论文《物体系》中的新型主—客辩证法拓展为一种社会批判理论,这种新理论包含了卢卡奇等马克思主义者的异化理论,以及罗兰·巴特为代表的符号学理论{14}。有的学者认为这种方式“承接马克思批判现代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的问题意识,抛弃马克思的资本批判范式(政治经济学范式),创造新的符号批判范式(符号政治经济学),在范式转换中实现理论对现实的批判和对未来的谋划”{15}。这一描述的确符合鲍德里亚所塑造的理论特征。在一个被资本渗透了的社会中,作为存在者的人远比马克思时代的无产者虚弱,这一虚弱表现在精神的空虚、话语空间的匮乏及肉身的过剩上。因此鲍德里亚将消费视为一种意义的获取,意义的总体也就是符号的世界,通过把物的世界抽象为符号的世界来展示异化的深层结构。但是鲍德里亚激进地将这种批判范式诉诸一切既存的事实。在信息化过程中他激进地写下《海湾战争没有发生》(The Gulf War did not Take Place),认为数字符号成为了战争的“第二层皮肤”(second skin),取代了真实发生的战争而成为我们的共同记忆{16}。最终,鲍德里亚只能以一种无望的姿态宣布人们将置身于拟像世界,人将堕落于一种超真实(hyperreality),而回归真实感性世界的策略则是寄托于客体系统的“内爆”。鲍德里亚作为一个“现象级”的思想家,展现了资本信息全球化趋势不可逆转的悲观情绪,这也许是他背向马克思的原因之一,但是其抵抗策略的激进与失败并没有阻止这股浪潮的继续。正如前文所述,正是资本仍然作为当下世界的支配力量并不断异化着感性世界与人的关系,所以我们仍然处在马克思的视野之内,而不断地探讨马克思与当下的距离成为后马克思主义者的一个显著特征。
二、齐泽克的梦思与“形式透视”
将批判理论的视野重新拉回到政经批判场域内,这成为一部分后马克思主义者的“默契”,往往也是这一部分后马克思主义者表现出更接近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在方法论上,他们延续了这样一种传统,虽然聚焦于拜物教的批判但却不排斥其他哲学范式的介入,其原因不外乎寻求更加深入的理论工具来克服同一个基础问题,同时也暗含了当下问题的复杂性及不可化约的焦虑。政经批判除了揭露资本生产的实质还批判了拜物教问题,齐泽克通过弗洛伊德—拉康精神分析介入马克思的拜物教批判,通过将资本逻辑阐释为梦的形式逻辑,将商品交换背后的秘密喻作对梦的无意识“迷恋”,以此论证了“马克思对商品的分析和弗洛伊德对梦的解析之间,存在着血浓于水的同源关系”{17}。
在弗洛伊德对梦的解析中,梦被还原为显在的梦文本、潜在的梦内容及无意识欲望,齐泽克认为在对弗洛伊德的误解中有一种是致命的:那就是将梦的无意识欲望解读为先验的,任何针对梦文本所作的解释(梦内容)都被视为无限接近无意识,这种对隐藏内容的“迷恋”成为一种征兆。因此,齐泽克认定“如果在由显在文本隐藏起来的潜在内容中寻找‘梦的秘密,我们注定铩羽而归”{18}。后期弗洛伊德不厌其烦地申明顯在的梦文本与潜在的梦内容之前的区分,同时他认为任何企图跨越这一区分的人都忽视了另一种区别,即潜在的梦内容与梦的整体性的差异。而梦的整体性作为梦的外部设置,如同戏剧的剧场本身,它是纯粹结构性的也就是形式的,而所谓梦的无意识欲望便存在于整个结构上,却又不可化约为结构本身。这一区分揭示了梦的无意识欲望只是结构的运作过程而非先验的内容,但是却在梦的阐释中被作为解读的对象。齐泽克称其为“构成性压抑”(constitutively repressed),表现为将一种“表层”的东西作为目的来接受的结构性冲动。
进而,齐泽克通过对弗洛伊德的解读来论证拉康对马克思的征兆(symptom)说。拉康将马克思所发现的非对称性归结为资本逻辑中的征兆,它意味着一种“表面性”的异化现象,那就是人们身处非对称之中却视而不见,甚至将这种非对称视为“原初”存在的并被其决定着。在弗洛伊德那里,被误读的无意识便充当了征兆,无意识构成了解析梦的基础但是其本身却从未受过质疑。齐泽克认为只要我们将视野转移到“剧场”本身,而不是专注于“舞台”内容就可以破除误读的冲动。这种冲动在马克思那里被指认为商品交换形式的秘密,商品交换之所以能够完成“惊险的一跃”,就在于人们将商品“真实抽象”为一种价值交换形式,而忘记了商品交换乃是从实际的以物易物而来。但是齐泽克并没有在商品交换与资本逻辑的不同层次中进一步分析征兆的过渡,他只是很粗略地提及了两种情况。征兆在狭义上表现为商品所有者“想当然”地进行等价交换,这个时候人是站在完全个人的角度上思考交换行为的,他完全不会考虑到“劳动力—商品—剩余价值”这一整套外在的逻辑,因此人是始终身处“剧场”之内而不自知的;齐泽克很“顺利地”将征兆演绎为广义上的意识形态骗局,他认为“‘意识形态并非对(社会)存在的‘虚假意识,而是得到虚假意识支撑的这种存在本身”{19},因此当下的现实便是“实体性”的意识形态。齐泽克继承了拉康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精神,但是却没有对这一“过渡”进行清晰的说明,他所参考的是马克思对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的过渡原理,通过对拜物教的考察将其理论延伸至恋物癖,拜物教的奥秘在于“商品形式在人们面前把人们本身劳动的社会性质反映成劳动产品本身的物的性质,反映成这些物的天然的社会属性,从而把生产者同总劳动的社会关系反映成存在于生产者之外的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20};而恋物癖则表明了人与人的社会关系被统治于物与物的社会关系之下。这其中的差别体现了时代背景的不同,在马克思看来人是被迫进入到总的资本生产机器之中的,对齐泽克来说,“剧场”的先在性迫使他要超越这一逻辑进行反思,这也体现了资本全球化下反思批判的困难之处,正是在这种窘迫下他提供了一种“异想天开”的抵抗策略:“如果我们看穿了社会现实的真实运行,这种现实就会自行消解。”{21}
虽然这种逻辑上的“跳跃”使我们在齐泽克的思路上产生疑惑,但是齐泽克毕竟道出了征兆在广义上的批判可能,他通过提供一组构成性悖论来论述征兆如何作为抵抗策略,“‘征兆是一个特殊因素,它颠覆了自身的普遍根基;严格来说,征兆是属,它颠覆了自己的种”{22}。在这个意义上,意识形态批判是完全符合的,以等价交换为基础的商品交换在资本生产环节却颠覆了自身的基础。但是齐泽克没有在商品交换形式的内部逗留太久,他转而关注社会层面的意义,将“乌托邦”规定为一种不含征兆的普遍性的信仰,而马克思的异化理论旨在通过人的实践能力破除掉征兆本身,因此齐泽克隐晦地否定了实践本身的可能,希图凭借保守的观念革命来抵御现实的固化。与此同时,齐泽克在对“后现代文化”的批评中则表现得更加乐观,通过对现实政治灾难与好莱坞灾难电影的精神分析,齐泽克得出了“我们开始把‘真正的现实体验为虚拟的现实”{23} 的后现代征兆,这一征兆又在精神的层面促使我们难以全身心地投入当下的“现实”,它是我们“眼中之景”的构成性基础,但是眼前景观的过度增长又令我们反感,人们进而通过幻想匮乏来抵抗这种不安。齐泽克由此分析了身在福中的人为何时常幻想着灾难的突发并对“灾难”这一“实在界”抱有激情。然而灾难一旦来临,也只有旁观的“福中人”才能依然抱有激情吧,身处其中的人则如《钢琴教师》中的埃莉卡是难以承受其后果的。但是齐泽克却在这里点明了我们所站立的基础并非如其所愿的稳固这一事实,异化理论与精神分析创造性结合所取得的成功也在于此。在他对犹太问题的分析中终于承认了难以承受的实在界问题——犹太人作为社会的“突起物”并非是难以理解的,它恰恰是“隐藏社会对抗”的表层之物,因此,在齐泽克看来,异化的问题恰恰不在于现实的扭曲,而是扭曲的基础被隐藏了这一“现实”。
总之,齐泽克在拜物教的精神分析中批判了对物的价值“迷恋”,他认为“迷恋”情结正是来自对形式之外“剩余”内容的欲望。他通过将商品(物)交换形式与梦的形式同构揭示出无意识(剩余)的压抑,这种压抑成为支撑整个拜物教征兆的基底。但是这一基底并非是什么神秘的东西,正如马克思所言,商品的神秘之处恰恰在于其“神学怪诞的”形式外衣,齐泽克认为将其神秘化的不是别人正是我们自身,正是对商品交换中资本形式逻辑的漠然无视导致了剩余价值的反复,而非对称的资本结构恰恰便是建立在等价交换这一唯我论理想之上的。然而齐泽克这种“形式透视”的辩证法真的具备“消解现实”的能力吗?其透视的结果不过是将资本结构中不对等的形式逻辑摄于表面。单单只是直观到这一异化关系是不够的,齐泽克至多是将商品形式中的“迷恋者”放置到了梦形式外的“旁观者”上,其异化的现实依旧存在,随着主体在反复的转换中消逝,其抵抗策略最终有名无实。
三、回到马克思:柄谷行人再论“联合”
柄谷行人则通过马克思的批判哲学回应了现实异化与主体的问题。柄谷行人认为马克思的批判哲学首先是一种主体的“危机理论”,在马克思的经历中前后遭遇了黑格尔哲学的瓦解与英国古典经济学的失败,而在马克思思想的展开上则存在“认识论的断裂”;与阿尔都塞不同的是,柄谷行人并未将这种转变放置于一段时间或特定的几部作品之间,他认为马克思的思想是在不断地跨越中展开的,例如马克思首先是将国家与资本的问题视为宗教的问题加以批判的,“就德国来说,对宗教的批判基本上已经结束;而对宗教的批判是其他一切批判的前提”{24}。馬克思在接触并使用唯物史观方法后,通过对剩余价值的历史分析发现了“劳动异化”的问题,但这并非代表他直接放弃了宗教批判的立场,他在《资本论》中写道:“最初一看,商品好像是一种简单而平凡的东西。对商品的分析表明,它却是一种很古怪的东西,充满形而上学的微妙和神学的怪诞。”{25} 这个“形而上学的微妙和神学的怪诞”所体现的正是前文所述“道德评价”与“历史评价”并行不悖之处。但是柄谷行人并没有止步于这种描述性分析,他进一步追问了马克思为何会存在着两种策略(或两种评价立场)。
究其原因,这与马克思选择了异于古典经济学派与新古典经济学派的立场有关,柄谷行人认为正是这“之间”的立场使得马克思在对两派的肯定与批判中发现了货币的秘密。众所周知,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派通过汲取重农主义的主张,以突出商品使用价值来反对当时的重商主义;但是古典经济学派的弊端很快就显露出来,“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缺点之一,就是它从来没有从商品的分析,特别是商品价值的分析中,发现那种正是使价值成为交换价值的价值形式”{26}。而交换价值正是新古典经济学所注重的领域,他们热衷于消费者的“边际效果”而将劳动价值视为“形而上学”的神秘物,这自然与马克思的初衷相背离而受到批判,“一个物可以是使用价值而不是价值……没有一个物可以是价值而不是使用物品。如果物没有用,那么其中包含的劳动也就没有用,不能算做劳动,因此不形成价值”{27}。柄谷行人认为马克思的批判是恰如其分的,马克思正是在古典经济学的不足中发现了交换价值及价值形式的重要性,同样,在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批判中重申了使用价值的重要性。但是不论是古典还是新古典经济学均没有注意到价值形式的部分,要之,马克思正是在这里发现了货币的秘密。马克思说:“商品具有……的价值形式,即货币形式。但是在这里,我们要做资产阶级经济学从来没有打算做的事情:指明这种货币形式的起源。”{28} 在经济学中货币被作为一种历史的结果来看待,柄谷行人将这隐喻为黑格尔式的经济学可谓入木三分,他认为马克思的《资本论》正是通过将经济世界看作一个宗教世界,以此来构建自身的哲学与革命论 {29}。
具体而言,柄谷行人认为马克思的问题意识在于“为什么商品的交换必须通过货币,相反却认为劳动本身的‘社会性格是通过货币才得以实现的”{30}。诚然,马克思将货币看作资本世界的“利维坦”,货币通过攫取了一般等价物的位置而支撑起整个商品经济,这时,使用价值不再是通过交换成为价值,而是通过货币被描述为价值。这种“商品之间的共同事业”起初不过是众多交换形式中的一种,但是随着不断“扩张”,商品经济的交换形式成为了“世界性”的,同时它又不断地内化为不证自明的“真理”,这种颠倒正是马克思对经济世界的“宗教性”批判。众所周知,马克思批判过费尔巴哈将神内在于人之中的人道主义幻觉,他在经济世界中发现同样存在着这种幻觉,进而言之,正是对货币本身的拜物教支撑着这种幻觉。对货币的崇拜成为其“扩张”动力的基础,马克思从G—W—G'(价值—商品—剩余价值)的商品交换形式中发现了G—G'与G'(G+△G)两种资本增值方式,前者代表了守财奴式的“发狂资本家”,后者代表了资本家式的“理智守财奴”,在马克思看来这些均是“货币宗教”对人的内在化奴役。货币(商品)拜物教的“世界性”同任何世界性宗教一致,起源于共同体与共同体之间:“商品交换是在共同体的尽头,在它们与别的共同体或其成员接触的地方开始的。但是物一旦对外成为商品,由于反作用,它们在共同体内部生活中也成为商品。”{31} 柄谷行人以家庭内部的无偿交换作为反例,证明了商品交换的“世界性”幻觉并非是不证自明的,它远未成为我们现实生活的“绝对”基础;同时也表明了商品交换通过内在化将物变为商品的现实,即便是在家庭生活内部也逃脱不掉对物作为商品的认知。
柄谷行人应对这种幻觉(異化)所作的抵抗策略,便是提出了新的交换形式设想——联合(association),联合形式的思想取道于蒲鲁东和葛兰西并同时对二者进行了改造。对于蒲鲁东的联合主义,柄谷行人十分重视马克思对其劳动货币的批评,并提出以“必须有货币”同时又“不可有货币”的二律背反作为“新联合主义运动”(New Association Movement)的基础构造,这预示着新型通货的出现,其设想的可行性在于通过综合清零原理(zero-sum)来杜绝剩余价值,原理是一定区域内成员在公共系统中频繁交换只与劳动量挂钩的通货来达到共存,其通货的赤字与黑字最终结算为零,通货总量等于系统内劳动总量,因此避免了剩余价值的溢出。对于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柄谷行人充分肯定了其斗争路线的转移,即从生产领域(罢工)向再生产领域(市民运动)的转移,但是后者因为缺乏“中心”而无法再联合导致被系统重新吸收,套用柄谷行人的话,在此出现了“必须有中心”同时又“不可有中心”的二律背反,其解决的策略则是暴力的总体出击(general strike)向总体拒买(general boycott)的转变。柄谷行人还区分了总体拒买的“劳动消费者”与资本世界的“消费者”,在他看来消费者的主体地位是抽象的,不过是差异化欲望下的受动性存在,它遮蔽了资本—雇佣劳动的关系。这种对虚幻性的批判同样适用于批判鲍德里亚文本中的缺陷。而劳动消费者的设想则来自甘地的非暴力运动——一方面是拒买英国产品,另一方面则通过组建生产—消费合作社来维持运动,即主张以劳动生产者的身份投入到资本世界的消费领域进行斗争。
可以看出,柄谷行人旨在从没有主体位置的《资本论》中发掘抵抗主体的位置。他设想通过在商品交换形式的内部突出主体的能动性,因此使消费主体带着劳动者意识进入流通领域是其策略的关键所在,这一点则与齐泽克不谋而合;但是在买卖关系中主体边界毕竟是不明显的,这导致了他在日本的活动屡屡受挫。柄谷行人的“联合”抵抗策略可以称之为伦理—经济的结合,其成功之处是通过康德的二律背反发现马克思对商品经济批判中的背反形式,在对拜物教的内部批判中以批判货币的神秘性为主,透视了作为物的同时又作为价值的货币存在形式;而在对拜物教的外部批判中,揭露了抵抗运动的多维性与去中心化面临的困境。柄谷行人汲取了马克思批判哲学的灵敏与深度,但是却遗漏了历史哲学的发展维度,在他设想的多区域联合运动中显然忘记了不同区域商品经济发展的水平差异,而地区生产力的差异化更是难以支撑全球生产—消费合作社的有力开展。此外,其全面拒买思路的保守性则使得运动本身难以逃脱被权力收编、遏制的结局。尽管如此,其总体思路可以看作全球化背景下马克思主义抵抗策略的复兴一维,不啻为一种新的批判视角。
四、总结
马克思思想中的异化理论一直是国内外学界的研究重点,其突出体现了批判哲学本身的深刻性,但是我们不应该忘记马克思思想中唯物史观的科学精神,正是两种方法的兼而有之才使得异化理论获得了空前的阐释能力。如果说“法兰克福学派”与“法国理论”注重发展了批判哲学的异化理论,使得异化思想在资本全球化与信息现代化的当下生活中获得新的理论土壤的话,那么鲍德里亚、齐泽克及柄谷行人等向政经批判的回归则体现出科学精神的复兴。他们都致力于破解商品最后的“秘密”,不论是运用符号学介入导致使用价值被消解的鲍德里亚,还是通过精神分析对商品形式进行透视的齐泽克,以及发现马克思拜物教批判之背反性的柄谷行人,都在马克思政经批判的理论基础上尽可能地丰富并对接现实。当然其中不乏有迷误甚至是误读。率先将马克思政经批判纳入哲学范畴讨论的鲍德里亚就曾犯下过消解马克思的错误,这无疑损伤了其符号批判理论的合理性;而齐泽克的“形式透视”策略则滑入了唯理论的泥潭,希图以主体转换的方式消解大对体(the big other),这无疑丢失了实践领域的能动性。相较而言,柄谷行人则从伦理学维度重返马克思《资本论》,虽然其解读中存在着主观臆测的成分,但是与齐泽克不同的是,他在对商品形式的分析中植入了实践维度的复兴。不过实践主体的伦理维度又与马克思意识形态批判相抵牾,这一背反性也成为柄谷行人“联合”策略的一大困扰。
综上可以看出马克思思想及异化理论在资本信息全球化背景下所面临的挑战,如何在不言自明的商品经济中破除拜物教迷云,如何看待商品交换形式在社会交换结构中的地位,以及资本—国家—民族的强结构带来的历史困境,这些仍然需要更加深入的分析与探讨。
注释:
① [法]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顾良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4页。
② 俞吾金编:《被遮蔽的马克思》,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19—120页。
③ 例如,在《资本论》这一著作中,马克思当然是利用唯物史观的方法剖析了资本的生产、流通及整个过程,但是也饱含这样道德批判色彩的话语:“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参看《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871页。)
④ Simon Tormey & Jules Townshend, Key Thinkers from Critical Theory to Post-Marxism: An Introduction, London / Thousand Oaks / New Delhi: Sage Publications, 2006,p.4.
⑤⑥{2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4、46、3页。
⑦{20}{25}{26}{27}{28}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97、89、88、98、54、62页。
⑧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37页。
⑨ [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17页。
⑩ [德]魏格豪斯:《法兰克福学派 历史、理论及政治影响》上,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48页。
{11} [德]霍克海默、[德]阿道尔诺:《启蒙辩证法 哲学断片》,渠敬东、曹卫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6—7页。
{1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50页。
{13} 衣俊卿等編:《20世纪新马克思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第411—412页。
{14} [美]道格拉斯·凯尔纳编:《波德里亚 一个批判性读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46页。
{15} 张天勇:《问题承接与范式转换:鲍德里亚思想的深层逻辑》,《国外理论动态》2017年第2期。
{16} Jean Baudrillard, The Gulf War Did not Take Place, Bloomingeon and Indianapolis: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5, p.64.
{17}{18}{19}{21}{22} [斯洛文尼亚]斯拉沃热·齐泽克:《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年版,第3、5、15—16、15、16页。
{23} [斯洛文尼亚]斯拉沃热·齐泽克:《欢迎来到实在界这个大荒漠》,译林出版社2015年版,第9页。
{29}{30}{31} [日]柄谷行人:《跨越性批判 康德与马克思》,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版,第148、154、107页。
作者简介:孙金琛,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广东广州,510631;刘国帅,奥克兰大学商学院,新西兰奥克兰,1010。
(责任编辑 胡 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