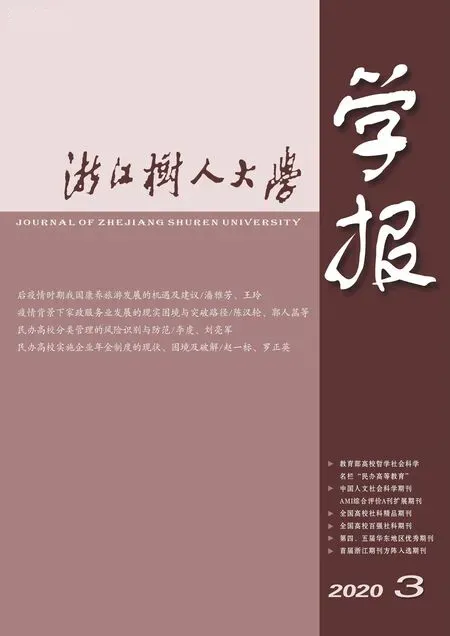论颂体的功能转型与魏晋颂体的叙事模式
汪妍青 林家骊
(浙江树人大学 人文与外国语学院,浙江 杭州 310015)
“颂”于生成之初,“以祭祀乐歌的身份构成正乐的主体”(1)郭英德:《中国古代文体学论稿》,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0页。。至孔子理诗,“纯取周诗”(2)班固著,颜师古注:《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708页。,列“四始”之序,以《清庙》为《颂》之始。所谓“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3)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936页。。“颂”遂由作为行为方式的乐歌仪式,过渡并定型成作为文本方式的文体(4)郭英德认为,礼乐变革导致宫廷仪式中正歌与变体的混合,乐师合编以《诗》之名广泛流传。此时,《诗》作为赋颂讽谏的文本方式及其功能特征渐趋强化,作为仪式的行为方式及功能特征则愈益淡化,而这是包括“颂”在内的“六诗”由行为方式转变为文本方式的主要原因。参见《中国古代文体学论稿》,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8-42页。。而《影弘仁本〈文馆词林〉》中所存崔骃“四巡颂”、马融《东巡颂》、刘珍《东巡颂》、张载《平吴颂》、曹毗《伐蜀颂》等篇,与其他类书中抄录的版本存在明显的差异。这些颂篇既可作为考证颂体功能的突破口,也可作为论述颂体发展形态的佐证。本文既以功能切入,讨论颂体在历时演进中文体功能、文本形态与叙事模式的确立。
一、两汉颂体功能的兼容性与文本形态的变异
以目见文献论,关于“颂”的最早记载见于《国语·鲁语下》:“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颂十二篇于周太师,以《那》为首。”(5)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点校:《国语》,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216页。后《文心雕龙·颂赞》有论:“风雅序人,事兼变正,颂主告神,义必纯美。”(6)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157页。至吴纳《文章辨体序说》则认为:“若商之《那》、周之《清庙》诸什,皆以告神为颂体之正。至如《鲁颂》之《駉》《駜》等篇,则当时用以祝颂僖公,为颂之变。故先儒胡氏有曰:‘后世文人献颂,特效鲁颂而已’。”(7)吴纳:《文章辨体叙说》,出自吴纳、徐师曾:《文章辨体序说文体明辨序说》,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47页。以此可知,颂于生成早期,用于宗庙祭祀中,以告神祝诵为功能之正,旨在沟通天人,庄严典雅,带有强烈的仪式属性。而“美盛德而述形容”(8)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156页;第157页;第157-158页。的“颂美”职能,则为鲁颂以降后起的功能变体。故彼时颂体书写,多以“二/二”式四言诵读节奏构成文本书写的主导句式,并于《诗经》三颂中庶几成为定制,所谓“时迈一篇,周公所制。哲人之颂,规式存焉。”(9)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156页;第157页;第157-158页。
至于两汉,以“告神”为功能之正的情况出现转变,颂体功能逐渐扩张,具备多功能并存的兼容性。这种兼容性最直接的体现,则是颂体文本形态的变异。刘勰《文心雕龙》对春秋至两汉的颂体功能与文本形态论述如下:
晋舆之称原田,鲁民之刺裘鞸,直言不咏,短辞以讽,邱明子高,并谍为诵,斯则野诵之变体,浸被乎人事矣。及三闾《橘颂》,情采芬芳,比类寓意,又覃及细物矣。至于秦政刻文,爰颂其德,汉之惠景,亦有述容,沿世并作,相继于时矣。若夫子云之表充国,孟坚之序戴侯,武仲之美显宗,史岑之述熹后,或拟清庙,或范駉那,虽浅深不同,详略各异,其襃德显荣,典章一也。至于班傅之北征西巡,变为序引,岂不襃过而谬体哉!马融之广成上林,雅而似赋,何弄文而失质乎!又崔瑗文学,蔡邕樊渠,并致美于序,而简约乎篇。(10)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156页;第157页;第157-158页。
此则材料,值得关注者有二。其一,颂的文体功能在文本写作中逐渐扩张,春秋以降,在通神与颂美外,又出现讽谏这一功能变体。至屈原《橘颂》,颂又与“言志”功能产生系联。至两汉时期,颂体这种功能的兼容愈为明显,所谓“至于汉初郊祀,乐章全体颂音,而独不追三颂而踵奚斯,应《九韶》而继咸墨”(11)孙梅著,李金松点校:《四六丛话》,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33页。,且其加重了与其他文体的互渗程度,时常出现同名异体或异名同体的现象。同名异体者即以“颂”名之,但是未必以告神或颂美为主要目的。如屈原《橘颂》、马融《广成颂》皆属此类,尤其王襃《圣主得贤臣颂》,实为论议之文。异名同体者与此相反,虽未必冠以“颂”名,却共同指向颂体的颂美职能。此诚如黄侃所论:“变其名而实同颂体,则有若赞,有若祭文,有若铭,有若箴,有若诔,有若碑文,有若封禅,其实皆与颂相类似。此则颂名至广,用之者或以为局。颂类至繁,而执名者不知其同然,故不可以不审察也。”(12)黄侃:《文心雕龙札记》,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69页。这类现象于两汉时期的碑文中颇为常见,如蔡邕《光武济阳宫碑》《陈留东昏库上里社碑》《太尉李咸碑》,其于散体序引中,皆有类似“敢用作颂”“树碑作颂”等指示性文句。而这种文体间的杂糅与互渗是颂体发展演进的必经阶段。
其二,与功能兼容性伴随相生成的,是颂体文本书写形态的变异。黄侃于《文心雕龙札记》有言“其体或先序而后结韵,或通篇全作散语”(13)黄侃:《文心雕龙札记》,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69页。。颂体至于两汉,其文本形态并非拘泥于四言韵语一格,而是多有变异,甚至出现散言与韵文的杂糅行文。王襃《圣主得贤臣颂》,以文为颂,以论述贤臣之道为目的。并几乎以散言行于全篇,偶有长句骈偶之文,如“所任贤,则趋舍省而功施普;器用利,则用力少而就效众”(14)班固著,颜师古注:《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823页;第2827页;第2828页。“圣主必待贤臣而弘功业,俊士亦俟明主以显其德”(15)班固著,颜师古注:《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823页;第2827页;第2828页。“是以圣王不遍窥望而视已明,不单顷耳而听已聪”(16)班固著,颜师古注:《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823页;第2827页;第2828页。。又如《碧鸡颂》,虽仅残存数韵,亦可见不会则的骚体句式,如“泽配三皇,黄龙见兮白虎仁,归来可以为伦。归来翔兮,何事南荒”(17)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359页。。
这种文本形态的变异,最典型者在于以赋为颂,尤其是以汉大赋之法写作的颂体之文,其以三言、四言、句腰虚字句等多种句式行文。如刘勰所举《广成颂》,针对“文徳可兴,武功宜废”(18)范晔撰,李贤等注:《后汉书》,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954页;1963-1964页;第1969页;第1969页;第1969页。的狭隘论断作讽谏之章,整篇以四言为主,以句腰虚字句为辅,又有其他句式交错使用,如连用九组三言偶对句,以述回辕行旅之途:“泝恢方,抚冯夷,策句芒,超荒忽,出重阳,厉云汉,横天潢。导鬼区,径神场,诏灵保,召方相,驱厉疫,走蜮祥。捎罔两,拂游光,枷天狗,緤坟羊。”(19)范晔撰,李贤等注:《后汉书》,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954页;1963-1964页;第1969页;第1969页;第1969页。又存五言偶对“忽蒐狩之礼,阙槃虞之佃”(20)范晔撰,李贤等注:《后汉书》,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954页;1963-1964页;第1969页;第1969页;第1969页。,七言偶对“收功于道德之林,致获于仁义之渊”(21)范晔撰,李贤等注:《后汉书》,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954页;1963-1964页;第1969页;第1969页;第1969页。,八言偶对“闇昧不睹日月之光,聋昏不闻雷霆之震”(22)范晔撰,李贤等注:《后汉书》,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954页;1963-1964页;第1969页;第1969页;第1969页。等。此颂除了未应用主客问答这一形式外,其他行文句式与汉大赋颇为相类。又班固与傅毅同题之作《窦将军北征颂》皆以句腰虚字句主导行文。边韶《河激颂》行文虽以四言为主,却并非韵文。
此外,崔骃“四巡颂”,即《东巡颂》《西巡颂》《南巡颂》《北巡颂》与马融《东巡颂》,在严可均以《初学记》《太平御览》《艺文类聚》为底本辑录的文本外,还存在日本影弘仁本《文馆词林》(以下简称《词林》)的版本。《词林》所录补足严氏所辑断章残句。而两者又因文献存录机制的不同,在文本形态上有所差别。现各取崔骃与马融《东巡颂》的一段为代表,以作说明(见表1)。

表1 《全后汉文》与《文馆词林》在文本形态上的差异
由表1可见,两者最典型的差异在于句式使用,严氏所辑崔骃与马融颂体文中的句腰虚字句,对应到《词林》中则为“三X二兮,三X二”的骚体句式。而《词林》中,崔骃“四巡颂”与马融《东巡颂》,悉数以“三X二兮,三X二”骚体句式主导行文,刘珍《东巡颂》则以句腰虚字句主导行文。“兮”字之有无虽与文献存录机制与文本传抄中的差异密切系联,但在同一类书、同一文体与同一主题之下,依然存在这种文本差异,则不应当排除两汉时期颂体、赋体、骚体三者间出现文体互渗的可能性。
以此可见,颂体发展至两汉,与其他文体的互动逐渐加强,除通神与颂美之外,又与讽谏、言志等功能相兼容。具体到颂体写作中,文本形态则突破四言韵文的局限,常以句腰虚字句或骚体句主导行文,又间以三言、四言、七言及以上长句。可以说,文体功能的兼容性与文本形态的变异相互影响,互为因果,两者共同作用,使两汉颂体呈现出颂名至广而颂类至繁的局面。
二、“颂美”功能的强化与魏晋颂体形制的确立
汉末以降,颂的文体功能与书写形制逐渐稳定,生成之初的“颂美”之变体渐趋取代“告神”之正体,成为颂体功能的主流。刘勰虽认为魏晋之颂属于“褒贬杂居”的“末代之讹体”(23)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158页。,但以目见材料观之,汉末魏晋的颂体,核心功能渐趋统一于美颂,对应到文本形态中,则重新确立了以四言韵语主导结言的规则形制。
这一规制首先体现于汉末碑文写作中(24)林晓光:《论汉魏六朝颂的体式确立及流变》,《兰州学刊》2011年第2期,第138-143页。,汉末碑文的流传以蔡邕为多,其余则多是阙名之篇。彼时碑文写作,分为散言与韵语两部分,虽以“碑”为名,然而在散言叙述之末却标注“敢用作颂”等字样,以明称颂之意。以蔡邕为典型的碑文写作,于序引中明确标注“颂”名时,虽亦存在书写形态的不稳定,偶有三言连韵成篇者,如《王子乔碑》,连用22组三言偶对句,又如《太傅胡广碑》(其三),以8组三言偶对句结篇,但四言韵文结言占据的比重颇有压倒性优势。深究这些碑文中的“树碑作颂”之篇,悉数以沟通天人,颂美前贤功德,以祈降福子孙为主要目的与情感旨归,“通神”作为行为方式的功能虽然渐趋退化,但其内涵与价值被保留在文本写作中。例如蔡邕《光武济阳宫碑》韵文部分,以“赫矣炎光,爰耀其辉。笃生圣皇,二汉之微。稽度乾则,诞育灵姿”(25)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879页;第879页;第879页;第879页;第879页;第1144页;第1145页。起篇,沟通天人,以明光武帝天降神授君威的正统性。后又列序其自讨逆至登基理国诸事,所谓“匡复帝载,万国以绥,巡于四岳,展义省方。登封降禅,升于中皇”(26)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879页;第879页;第879页;第879页;第879页;第1144页;第1145页。,极尽颂美之能。末以“爰兹初基,天命孔彰。子子孙孙,保之无疆”(27)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879页;第879页;第879页;第879页;第879页;第1144页;第1145页。收尾,以祈光武帝之灵护佑汉祚绵长。再如《陈留东昏库上里社碑》,“社者,土地之主也。周礼建为社位,左宗庙,右社稷”(28)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879页;第879页;第879页;第879页;第879页;第1144页;第1145页。,“社”本身便带有幽赞神明,接续人神之属性,蔡邕以“惟王建祀,明事百神。乃顾斯社,于我兆民”启篇,明社之神性。其后则重点颂美虞宗之勋:“爰我虞宗,乃世重光。元勋既立,锡兹土疆。乃公乃侯,帝载用康。”(29)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879页;第879页;第879页;第879页;第879页;第1144页;第1145页。又如《太尉乔玄碑》,乔玄为汉末名臣,秉性质直而不惮强御,身居高位而拔擢贤良,蔡邕为之所颂,以昭芳烈。由于此篇乃为名臣作颂,故而不再强调天命与神性,然其余文辞与前属亦相类,述其平生行状,颂赞其功勋德业。汉末碑文中以“颂”为名的篇什,以明君贤臣等身居高位者,或山川湖泊、祠庙里社等带有神秘属性者为写作对象。这种四言碑颂的大量出现,渐趋将颂体的写作形制规范化。在随后的发展中,碑颂的写作形制逐渐被过渡推广到其他颂体写作中,成为魏晋时期颂体形制确立的序曲。
建安曹魏时期,目见所存颂体,除王粲《太庙颂》穿插6组三言对句,繁钦《砚颂》全篇以骚体句式行文,韦诞《皇后亲蚕颂》与傅嘏《皇初颂》中三言、四言与句腰虚字句混合使用而以句腰虚字句为主导,何晏《瑞颂》四言与句腰虚字句并行而以四言为主导,其余篇皆以纯四言韵语主导行文。
值得注意的是,彼时为数不多的颂体中,依旧保留了两汉时期的“序+颂”形制,而这一形制与两汉颂体最大的区别则在于颂序部分骈俪化的加强,其序颂打破了两汉时期以散文结言的传统,时有骈偶韵语的加入,其中以曹植《孔子庙颂》为典型,此序言中有曰:“天人咸和,神气烟煴。嘉瑞踵武,休徵屡臻。殊俗解编发而慕义,遐夷越险阻而来宾。虽大皓游龙以君世,虞氏仪凤以临民。伯禹命玄宫而为夏后,西伯由岐社而为周文。”(30)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879页;第879页;第879页;第879页;第879页;第1144页;第1145页。序言中这类骈偶韵语的出现,将颂体正文的一部分内容转移到序言中,从而为颂体四言韵语的范式化提供了可能性与可操作性。
这一时期,颂体书写的对象依旧对两汉有所继承。保留了对居高位者的颂美、对宗庙社稷的祈愿与对瑞象灵兽的敬畏,书通神明,祈福后世。高位者如曹植《皇太子生颂》《贤明颂》、韦诞《皇后亲蚕颂》;宗庙社稷者如曹植《社颂》、王肃《宗庙颂》;瑞象灵兽者如何晏《瑞颂》、薛综《麟颂》《凤颂》等。而诸篇什写作,亦以颂美为重点。但与此同时也应注意到,彼时“颂”体在书写对象的选择上出现了“下移”趋势。其不再拘泥于庙堂之尊者或是川岳宗庙之灵者,而是将花草等日常物品皆纳入颂美范围,但亦不同于屈原《橘颂》的言志属性,而是纯粹的比德颂美,如曹植所作《宜男花颂》,所谓“福齐大姒,永世克昌”(31)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879页;第879页;第879页;第879页;第879页;第1144页;第1145页。。这类咏物类颂体在两晋时期得到承继与发展。而颂体写作对象的范畴虽然向外扩张,但本质上依旧不离颂美功能。
至于两晋,以四言韵语结言的文本形态已然达到绝对统一,但不可否认依旧有极个别变体的存在。如刘伶《酒德颂》,句式行文在押韵的基础上颇具变幻,是目见两晋颂体中唯一一篇以颂体之名陈平生之志的文章。其行文跳脱,既是己身狂放性格的外在呈现,亦是对司马氏高压政治的一种反抗。又如张载《平吴颂》中,《词林》所存序颂几乎以骈偶之式写成,补严可均所辑残章(32)张载:《平吴颂》,见《日本影弘仁本〈文馆词林〉》,(日本)古典研究会1969年版,第112-114页。,可以作为建安以来颂序骈俪化的佐证。其正文则以四言与句腰虚字句并行,是对前代武部与礼部类颂体如班固《窦将军北征颂》、崔駰《四巡颂》等写作形制的继承,也是文体功能兼容性的残留表征。因为这一类题材在两晋时期几乎以赋体行文,如潘岳《西征赋》、陆云《南征赋》、袁宏《北征赋》。又如鸠摩罗什《赠沙门法和颂》,与后世五言诗体相类,而这类五言体,与佛教的翻译与普及甚为密切(33)颂体于释氏中的变体,详见《论汉魏六朝颂的体式确立及流变》之“五、七言体式的出现与佛偈借名”,参见林晓光:《论汉魏六朝颂的体式确立及流变》,《兰州学刊》2011年第2期,第140-143页。,于释氏赞体中更为普遍,大盛于南朝,于此不赘述。总体而言,目见仅存于两晋的颂之“变体”并不能改变颂体以四言立体的大趋势。
实际上,自西晋始,四言韵语正式确立为颂体写作形制的正体。在这一写作形制中,主要特质有二。其一,就文体功能论,颂之“名”与颂之“实”庶几合一,绝非刘勰所谓“褒贬杂居”的“末代讹体”,颂美之能得到绝对的强化并成为主流,讽谏言志等功能随着诸文体分类的进一步明晰而渐趋弱化,最终归属于诗体与赋体。两晋颂类,题材凡四种,即:君后名臣类,如左芬《武帝纳皇后颂》、陆机《汉高祖功臣颂》、陆云《祖考颂》。盛世颂美类,如傅咸等人《皇太子释奠颂》、挚虞《太康颂》、潘尼《后园颂》、陆云《盛德颂》。草木物色类,如成公绥《菊颂》,王赞《梨树颂》、辛萧《芍药花颂》。释道隐逸类,如潘岳《许由颂》、陆云《登遐颂》、庾阐《乐贤堂颂》。而无论何种题材,皆以纯粹颂美为基本原则,彻底将“颂”于文体生成之初的“美颂”之“变体”转型为“正体”,且这一职能的使用场合虽再不拘泥于宗庙祭祀,且频有“下移”之势,但颂美的目的与功能依然是统一的。其二,就文本形态论,在四言韵语的基础上,部分篇什依旧保留“序+颂”的模式,而序言的篇幅比例不再占绝对优势,渐趋打破了汉末“并致美于序,而简约乎篇”(34)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157页;第158页。的写作状态,或与颂平分秋色,如潘尼《释奠颂》,或进一步突出了颂的文体地位,序仅作为引导,简约成章,如陆机《汉高祖功臣颂》。且序的骈俪化程度愈为密集,时有超过颂体正文部分的情况。如潘尼《释奠颂》序中,3组三言句与句腰虚字句皆为偶对,12组四言存偶对者10组,4组五言偶对3组,其偶对率远超《释奠颂》正文。颂序的写作,将颂的写作缘由等部分说明在序中呈现,从而规避了颂体正文写作中的烦琐表达,对四言韵语结言的规范化颇有裨益。
三、颂体的叙事性与魏晋颂体的叙事模式
《文心雕龙·颂赞》对立颂之大体作出探讨:“原夫颂惟典雅,辞必清铄;敷写似赋,而不入华侈之区;敬慎如铭,而异乎规戒之域。揄扬以发藻,汪洋以树义。”(35)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157页;第158页。“发藻”与“树义”是实现颂美功能的两种途径,尤其是“树义”一项,使颂体带有了明显的叙事性。
(一)句的组合与颂体的叙事性表征
在以语法意义的停顿作为划分句式节奏的依据时,颂体四言以“二/二”式主导行文,又以“一/三”式为辅(36)语法意义的划分,参见林家骊、汪妍青:《论唐前七体文骈偶句式的生成》,《浙江学刊》2018年第5期,第190-198页。,并涵盖数种固定句型。且颂体四言中谓词性短语的使用与名词性短语相较,占据绝对的压倒性优势。
需要说明的是,颂体四言偶对句的句法结构与非偶对句的句法结构并无二致,所不同者,仅在于二者行文的篇章位置与具体的表意指向。颂体偶对在魏晋时期的使用频率虽相对较低,但其句法结构在颂体四言中具备典型性,兹以颂体偶对句式为例,概述颂体四言的句法表现形式,进而论述颂体的叙事性特征。
以目见文本论,颂体的名词性短语多为定中式,且清一色为“叠词+中心语”结构,如曹植《皇太子生颂》“喁喁万国,岌岌群生”(37)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145页;第1903页;第1761页;第2002页。,挚虞《太康颂》“严严南金,业业余皇”(38)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145页;第1903页;第1761页;第2002页。,傅咸《皇太子释奠颂》“光光舆服,穆穆容止”(39)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145页;第1903页;第1761页;第2002页。,潘尼《后园颂》“明明天子,肃肃庶官”(40)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145页;第1903页;第1761页;第2002页。,曹毗《伐蜀颂》“桓桓南藩,朗朗齐算”(41)《影弘仁本〈文馆词林〉》,(日本)古典研究会1969年版,第110页。等。这类词组,基本主于胪列与描述,在颂体写作中的使用十分有限,通常与其他句式相组合,或骈偶,或散行,表示逻辑的各种关系。
谓词性短语在颂体书写中占据绝对的主导,在“二/二”式中,句法结构主要呈现五种形态:一是主谓式,如“洪声登假,神祇来和”(42)曹植:《孔子庙颂》,出自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144页。。二是述宾式,如“席卷要蛮,荡定荒阻”(43)潘尼:《释奠颂》,出自房玄龄:《晋书》,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511页。。三是述补式,后二字多为方位名词,以表地点。如“飞声八极,翕习紫庭”(44)左芬:《武帝纳皇后颂》,出自房玄龄:《晋书》,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961页。。有时又表动作行为的方式途径,如“陶化以正,取乱以奇”(45)挚虞:《太康颂》,出自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903页。,或表示动作完成后呈现的状态,如“挹之不冲,满之不盈”(46)牵秀:《彭祖颂》,出自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946页。。四是联合式,此联合式于多数情况下,两字间多构成述宾关系,如“穷发反景,承正受朔”(47)挚虞:《太康颂》,出自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903页。。五是连谓式,如“从容燮理,散诞飞缨(48)史援:《后汉史君颂》,出自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219页。”。同时还存在特殊固定用法,如主谓结构的倒装句“武关是辟,鸿门是宁”(49)陆机:《汉高祖功臣颂》,出自萧统编,李善等注:《六臣注文选》,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889页。、判断句“静也渊默,动也天随”(50)释慧远:《襄阳丈六金像颂》,出自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402页。。这五类句法结构中,以主谓式与述补式的使用最为频繁。
在“一/三”式中,句法结构主要呈现四种形态:一是主谓式,如“学犹莳苗,化若偃草”(51)潘尼:《释奠颂》,出自房玄龄:《晋书》,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512页;第1512页;第1511页;第1511页;第1512页。。二是状中式,多数情况下以方位名词类作状语。如“上好如云,下效如川”(52)潘尼:《释奠颂》,出自房玄龄:《晋书》,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512页;第1512页;第1511页;第1511页;第1512页。。三是述补式,常用“以”字句表动作的目的或方式,如“铺以金声,光以玉润”(53)潘尼:《释奠颂》,出自房玄龄:《晋书》,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512页;第1512页;第1511页;第1511页;第1512页。。四是述宾式,如“违兹九土,陟彼高冥”(54)牵秀:《黄帝颂》,出自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946页。。“一/三”式亦存在一些固定结构,如隶属于述宾结构的“或”字句“或涌于地,或降于天”(55)王肃:《宗庙颂》,出自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181页。,“如”字句“如日之升,如乾之运”(56)潘尼:《释奠颂》,出自房玄龄:《晋书》,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512页;第1512页;第1511页;第1511页;第1512页。,隶属于主谓结构的“不”字句“化不期月,令不浃辰”(57)傅嘏:《皇初颂》,出自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249页。。在这几类句法结构中,以状中式与主谓式的使用最为频繁。
经历赋化后,四言句式虽因名词和形容词类双音词的大量使用而逐渐成为适宜于铺陈与堆砌的“典型的赋化四言句式”(58)葛晓音:《先秦汉魏六朝诗歌体式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38页。,但仍保留着大量的谓词性词组与叙述性质,因此,四言句式兼备铺陈与叙事双重属性,适宜于多种句式结构的组合与辞意的表述,从而生成多种逻辑关系。而颂体四言行文,正是这种叙事属性的体现。其在两句为一组的视域下,单句间相互配合,共同完成一次逻辑表意。在颂体写作中,除并列关系外,一组两句间的逻辑关系主要有五种:一是因果关系:如“德伦三五,配皇作烈”(59)曹植《学宫颂》,出自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144页。;二是目的关系,即后一句为前一句的目的,如“乃建宗圣,以绍厥后”(60)曹植:《孔子庙颂》,出自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144页。;三是陈述关系,如“如彼仪凤,乐我云韶”(61)潘尼:《释奠颂》,出自房玄龄:《晋书》,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512页;第1512页;第1511页;第1511页;第1512页。;四是设问关系,如“妙化伊何?惠无不柔”(62)曹毗:《伐蜀颂》,出自《影弘仁本〈文馆词林〉》,(日本)古典研究会1969年版,第110页。;五是方式关系,即后一句为前一句实现的方式,如“无或安逸,在盈思冲”(63)潘尼:《后园颂》,出自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002页。。以此可见,四言句式容量的局限性与语法结构的多样性间存在着极大的间隙,通常需要借助一组两句共同完成一次语意逻辑的表达,这就使颂体的叙事性带有散文的特质,这一特质在颂美功能正式确立的早期尤为明显。
(二)魏晋颂体的叙事模式
根据以上对颂体使用句式的分析可知,在实际写作中,通过“发藻”“树义”落实的“美颂”功能,并非盲目地借助摛藻铺陈以美盛德之形容,而是以谓词性短语主导行文,构建一个脉络清晰的逻辑闭环,这个闭环包括颂美缘起、颂美勋业(或品性等值得颂美之处)、结语定论三部分,贯穿颂体写作的始终,成为颂美的叙述主线,从而形成“通神受命—颂扬功德—祈福被泽”的叙事模式。考察这一叙事模式,可以发现原本在颂体生成之初用于宗庙祭祀的“告神”功能,虽然随着所颂对象与赋“颂”场合的下移渐趋消失,但依旧保留于颂体的文本写作中,成为叙事模式的重要环节。
而在“颂扬功德”这一环节,对美颂主体功勋品性的书写,更是以线性的叙述为主,横向的铺陈只是作为叙述的点缀。即颂美对象的重点在于如何完成勋业与勋业完成的步骤,或是德行体现的具体事宜,而非铺陈描绘勋业如何宏大或是德行如何光明。
颂体的这一叙事模式在汉末碑颂中便初露端倪,如前文所论蔡邕《光武济阳宫碑》《陈留东昏库上里社碑》皆属此类。其在魏晋时期得到继承与发展,庶几可涵盖彼时所有四言韵语结言的颂体写作。无论是简约短韵如牵秀《黄帝颂》《老子颂》,还是累读积篇如陆机《汉高祖功臣颂》、曹毗《伐蜀颂》皆不离此式。兹以曹植《孔子庙颂》为例,以作具体阐释说明。其颂曰:
煌煌大魏,受命溥将。并体黄虞,含夏苞商。降厘下土,上清三光。群祀咸秩,靡事不纲。嘉彼玄圣,有邈其灵。遭世雾乱,莫显其荣。褎成既绝,寝庙斯倾。阙里萧条,靡歆靡馨。我皇悼之,寻其世武。乃建宗圣,以绍厥后。修复旧堂,丰其甍宇。莘莘学徒,爰居爰处。王教既备,群小遄沮。鲁道以兴,永作宪矩。洪声登假,神祇来和。休徵杂遝,瑞我邦家。内光区域,外被荒遐。殊方重译,搏拊扬歌。于赫四圣,运世应期。仲尼既没,文亦在兹。彬彬我后,越而五之。并于亿载,如山之基。(64)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144页。
此颂为碑拓本,文本的完整性与可靠性相对较高。其以线性叙述勾连结篇,首叙曹魏立国,自“煌煌大魏”至“靡事不纲”为通神环节,论证魏国受命自天的正统性。次说孔庙修立之缘由与目的,“嘉彼玄圣”至“以绍厥后”,由孔子宗庙屡遭兵燹而倾颓至文帝悯此状而敕造修建以为后世子孙供奉,一组上下两句间,其逻辑多构成因果、承继、目的关系。再述孔庙修建竣工之盛况,自“修复旧堂”至“永作宪矩”,庆贺孔庙与夫子之道的复兴,四组四言句,在逻辑上属于方式、陈述、并列、目的关系。后由“洪声登假”至“运世应期”,叙述孔庙修成后的天降祥瑞之象,“内广区域,外披荒遐”则是对前句“休徵杂遝,瑞我邦家”的说明与形容。篇末由“仲尼既没”至“如山之基”,又回归于对修立孔庙意图的强调,再次说明曹魏受禅后文化根基与政治政权的正统性,并为后世子孙祈福。五层叙述,逻辑的纵向递进清楚明晰,层层深入,诠释了颂体“汪洋以树义”的内涵。
这一叙事模式的适用范围甚广,无论是分章共记一人一事,还是分章分叙多人多事,皆通过这一模式进行。前者如曹毗《伐蜀颂》,其颂美晋氏乏蜀之事,凡十二章。章一至章三沟通天人,旨在说明晋氏的正统性:所谓“宣皇基之,天经重焕”(65)《影弘仁本〈文馆词林〉》,(日本)古典研究会1969年版,第109页;第110页;第110页;第110页;第111页。“迹摸唐虞,轨出殷周”“我皇继祚”(66)《影弘仁本〈文馆词林〉》,(日本)古典研究会1969年版,第109页;第110页;第110页;第110页;第111页。。章四至章十为写作重点,记叙晋氏基业的创立,并将晋氏之盛与蜀地之鄙作对比,所谓“大化雨施,洪润云行”“皇家之屏,唯才曰慎”“蠢矣蜀,敢窜边外”“乃命南藩,奋旗电逝”(67)《影弘仁本〈文馆词林〉》,(日本)古典研究会1969年版,第109页;第110页;第110页;第110页;第111页。。章十一与章十二则以勋业为关照,祈福后世:“往迹缅哉,于今齐轨”(68)《影弘仁本〈文馆词林〉》,(日本)古典研究会1969年版,第109页;第110页;第110页;第110页;第111页。“敢扬圣猷,垂之后昆。”(69)《影弘仁本〈文馆词林〉》,(日本)古典研究会1969年版,第109页;第110页;第110页;第110页;第111页。虽然分章行文,但是叙事逻辑具备连续性与共同指向性。后者如《汉高祖功臣颂》,分别颂美汉高祖刘邦的三十一位功臣,如其颂张良:
文成作师,通幽洞冥。永言配命,因心则灵。穷神观化,望影揣情。鬼无隐谋,物无遁形。武关是辟,鸿门是宁。随难荥阳,即谋下邑。销印惎废,推齐劝立。运筹固陵,定策东袭。三王从风,五侯允集。霸楚实丧,皇汉凯入。怡颜高览,弥翼凤戢。托迹黄老,辞世却粒。(70)萧统编,李善等注:《六臣注文选》,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888-889页。
其以叙事张良平生事迹为主线,起首“文成作师”至“物无遁形”沟通天人,渲染张良永言配命的天纵之才,其后由“武关是辟”至“皇汉凯入”颂扬功德,是颂美的重点,记述张良辅佐刘邦平定天下,建立汉朝的旧事,其以线性时间为序,即从佐策入关鸿门化险,至荥阳危难下邑奇谋,再至献策高祖封王于韩信,又至固陵受困,运筹帷幄,终败项羽于江东而三王五后来集,聚贤良之心,末至四海既宁汉朝立国。而最后两组四言式则说其功成身退,归隐修道之事,为张良其人增添几许神秘之感。
以此可知,魏晋时期的颂体写作带有明显的叙事性,其以四言谓词性短语主导结言,多样的句法结构与丰富的逻辑关系相组合,为颂美主体的线性记叙提供了必要保障。
综上所论,“颂”在早期生成时以“告神”为功能正体,作为乐歌的仪式,隶属于行为方式的一种。其后则由行为方式逐渐发展成文本方式,经历两汉时期功能的兼容阶段,至于魏晋,正式确立“颂美”为功能正体,于此基础上形成了以四言韵语结言的文本形态。颂体四言又以谓词性短语主导行文,因句法意义的多样性而构建出丰富的逻辑关系,从而使颂体呈现明显的叙事性。因此“颂美”功能的执行,以叙事为主,铺陈为辅,形成了以“通神受命—颂扬功德—祈福被泽”为主线的叙事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