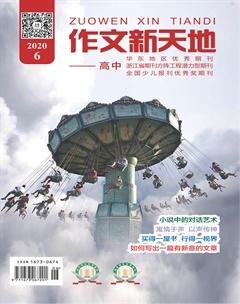“我”可靠吗
王蓓
德国作家伯尔的《在桥边》,小说开头“我”自认为“是一个不可靠的人”,小说的结尾,主任统计员却拍着“我”的肩膀,说“我”是个“好人,很忠实、很可靠”。那么,“我”究竟可靠不可靠呢?
我们发现,从文本表面上看,“我是一个不可靠的人”。在文中我们可以看到,“我”对数人的这份差事并不热爱,在工作时有点“任性”:
·有时故意少数一个人;当我发起怜悯来时,就送给他们几个。
·当我恼火时,当我没有烟抽时,我只给一个平均数;当我心情舒畅、精神愉快时,我就用五位数字来表示我的慷慨。
·所有在这个时间内走过的人,我一个也没有数。
·所有一切有幸在这几分钟内在我蒙眬的眼睛前面一列列走过的人,都不会进入统计中去而永垂不朽了,他们全是些男男女女的幽灵,不存在的东西,都不会在统计的未来完成式中一起过桥了……
但细读文本,我们不难发现,“我”诚然“是个好人,很忠实、很可靠”。
| 一、忠实于自己的心灵|
伯尔1939年应征入伍,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曾负过伤,当过俘虏,对法西斯的侵略战争深恶痛绝。在小说中,伯尔借“我”揭示战争和政治力量给普通民众带来的毫无意义的苦难。小说中的“我”,既是作者虚构的人物,也是作者自身的缩影。“我”并没有因为“他们替我缝补了腿,给我一个可以坐着的差使”而宽恕战争给人带来的心灵的伤害。小说中叙述人称选用“他们”,就明显地表明了伯尔的立场,这是一种距离感,带有深深的排斥、厌恶的味道。
我们再读上面列出的这组文字就可以发现,这不是“我”的任性,而是“我”对这份枯燥、无聊、灰暗的工作的不满,是为了生存不得不数的无奈,是一种无声的反抗。
“我”在日复一日的数数中显得无奈、麻木,直到有一天,桥头上走来了一位美丽的姑娘,唤起了“我”对美好爱情的憧憬,也使得“我”麻木的心因为爱情而得以苏醒。“我”似乎寻找到了那个有着真情实感的自己,原来她就是“我”一直在寻找的生命的原动力——无忧无虑,天真无邪。“我”爱她,这点是毋庸置疑的,她走来时,“我”没有把她计算在内,因为“我一辈子也不会把这样漂亮的女孩子转换到未来完成式中去;我这个心爱的小姑娘不应该被乘、被除、变成空洞的百分比”。她是属于“我”一个人的,此时此刻,一切都不重要,丢掉工作也在所不惜,好久没有这样真实地活着了。当那个美丽的姑娘走过桥头,“我”苍白的精神世界里被注入了一股清泉,“我”窒息已久的灵魂也因为“我”对爱情的憧憬而顿时苏醒了。美丽的姑娘在“他们”的眼中,只是一个数字,是和别的任何一个从桥上走过的人没有区别的数据,也许是象征着创造的财富值,也许是象征着政绩,但是在“我”眼中,因为真挚的爱情和复苏的精神世界,姑娘就是一个鲜活的有生命的个体。通过小说中的“我”,我们可以看见伯尔对生命个体的尊重,对人的存在价值和生存意义的关注。
“我”自我贬低为“不可靠”的人,“我”的“不可靠”只是针对把和“我”一样遭受战争伤害的人当作物品来对待的战后的政府和人们。而面对过桥的姑娘时,“所有在这个时间内走过的人,我一个也没有数”。对爱情的憧憬,也算是对“我”遭受战争创伤的心灵的一种抚慰。尽管“我也不愿意让她知道”,但这种关于爱情的激动人心的描述却能让我们隐约感受到,“我”在不重视精神关怀的时代氛围中保持个人精神追求的无可奈何的自找其乐的情绪。正如《教师教学用书》所指出的:“实际上,小说中的暗恋,主人公也并未把它作为一种可以实现的现实追求来看待,而更多是作为一种精神寄托来对抗这个忽视人的精神存在的社会氛围。”这无疑是伯尔塑造“我”这个形象最真实的内心诉求。
| 二、可靠于对现实的清醒认知|
伯尔之所以被称为“德国战后最伟大作家”,正是因为他有着高度的社会责任感,敢于描写德国战后的创伤。关于一个国家的战争创伤,一般人首先想到的总是哀鸿遍野、满目疮痍,所以描写着力点往往就落在物质建设上。而伯尔却对战后德国重建中偏重物质而缺乏精神关怀的问题,以及小人物在这种历史背景下的痛苦挣扎和苦恼彷徨予以深刻的剖析和反思。
众所周知,战争所带来的创伤并不会因战争的结束而立刻消散,而是会长久地驻留在经历者的生活里。小说开篇“缝补”一词耐人寻味。“缝补”即缝制修补,多用于破衣服、破鞋子等物,而小说中“缝补”的对象却是“腿”。“我”为什么不说“他们”替“我”治好了腿而是“缝补了腿”?比较一下“治好”和“缝补”这两个词,“治好”追求的是疗效,表达出的是政府对战争受害者的一种关怀;“缝补”追求的是形式,只做表面工作并不求疗效怎样。“缝补”无疑更能表达出“我”对战后德国政府把人当作物品一样对待,不给予人价值和尊严层面的关怀与帮助的社会现实的嘲讽。也正是基于对这样一种社会现实的清醒认知,才有了下文“我”对被安排的工作的懈怠及随心所欲。
战争摧毁的不仅仅是桥梁、肉体,还有战后人们的信仰和价值观;战后需要重建的也不仅仅是桥梁和腿,还有信仰失落、价值观崩塌的迷惘的心灵。用物质重建一座新桥简单,但是重建人的心灵就绝对不是“补腿”、奖励“数马车”“美差”這种好大喜功的形式主义作风所能解决的。
如果说小说中的“新桥”暗示小说的背景应该是战后德国重建,那么“他们”自然就是德国政府。“我”能看到“他们以用数字来表明他们的精明能干为乐事,一些毫无意义的空洞的数目字使他们陶醉”;“他们”看到数字时“脸上放出光彩”“容光焕发”“心满意足”“眼睛闪闪发亮”;“他们喜欢这个未来完成式”。在“我”的眼中,“他们”醉心于数字上的增多,即便这些是虚假的数字,“他们”努力做些面子工程,企图搞出些“政绩”,并不真正关心人的生存状况。“我”的可贵在于在那么多人迷失在数字的海市蜃楼下,“我”还能保有一份清醒,渴望着美好的希望和受创精神家园的重建。在废墟上进行战后重建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他们”只关心物质,而完全忽略人的精神存在,甚至忽略了隐藏在数字化效率社会的经济繁荣表象下的废墟。小说借助“我”的所见所感,表达了伯尔对缺乏精神关怀的社会现实的思考。
或许,这就是伯尔的伟大之处,总能在看似平淡的笔调里,触及社会生活的本质!
- 作文新天地(高中版)的其它文章
- 本期言论
- 我们为何存在
- 买得一屋书,行得一视界
- 爸爸和他的母校
- 蓝色畅想曲
- 山前既相见, 山后又重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