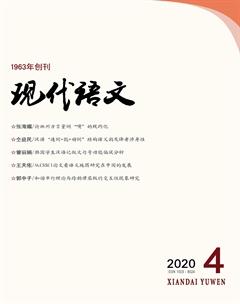论林州方言量词“嘴”的规约化
张海媚


摘 要:普通话中的“嘴”为借用量词,而林州方言中的量词“嘴”,无论从词义、结构还是从使用地域上来看,显然已规约化成典型的量词。从范畴化的历时过程和范畴化的共时表现来看,林州方言量词“嘴”的规约化层级较低,仅限于修饰固体食物。这大概和“嘴”的原指义和“嘴”义泛化后作为“人和动物的饮食器官”这一核心功能有关。
关键词:“嘴”;量词;林州方言;规约化
林州市地处太行山东麓,豫、晋、冀三省交界处,东与安阳县、鹤壁市、淇县接壤,南与辉县市、卫辉市相连,西与山西省平顺、壶关两县毗邻,北隔漳河与河北省涉县相望[1](P1)。《中国语言地图集》将林州方言划归为晋语邯新片,“晋语”是李荣以入声有无的标准从北方话中独立出来的方言[2]。从地理分布上看,“这是一个相当封闭的地理环境,巍峨的太行山和古老的黄河以及山西南部的太岳山脉、中条山脉作为天然屏障,抵挡处于强势的北京官话方言的西进与中原官话的北上”[3](P2-3)。诚如林焘所言,语言和社会一样,越是封闭,发展得就越慢;越是开放,发展得越快[4]。晋语区处于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中,通常情况下发展得要慢一些。不过,林州方言中的量词“嘴”却是个例外,它比普通话发展得还要快一点。
在普通话中,“嘴”并不是一个典型的量词,大多数语法专著或现代汉语教材均未提及,如朱德熙的《语法讲义》[5](P48-51)、吕叔湘的《现代汉语八百词》[6]、
赵元任的《汉语口语语法》[7](263-277)、郭绍虞的《汉语语法修辞初探》[8](275-431)、房玉清的《实用汉语语法》[9](P278-285)、邢福义的《汉语语法学》[10](P192-197)、刘月华等的《实用现代汉语语法》[11](P129-136)、张斌主编的《现代汉语描写语法》[12](P140-149)、黄伯荣、廖序东主编的《现代汉语》[13](P21-23)、胡裕树主编的《现代汉语》[14](P288-289)等;只有极少数学者将“嘴”视为是“借用名量词”,如卢福波[15](P484)、郭先珍[16](P189)等。不过,就“借用量词”的归类来看,很多学者仍是将其看作名词的,如谭景春[17]、宗守云[18](P143)等。
河南林州方言量词“嘴”和“口”在对食物的修饰上有明确分工,凡是液体类流质的食物都用“口”修饰,如“一口汤、一口水、一口可乐”等;凡是固体类非流质食物都用“嘴”修饰,如“一嘴馒头、一嘴米饭、一嘴苹果、一嘴面条”等。同时,它具有“少量”义,如“就剩这一嘴馒头了,快吃掉”“这是谁剩的一嘴米饭啊,不吃完”。林州方言量词“嘴”的这一用法与普通话借用量词“嘴”的用法有别,无论从词义、结构还是从使用地域来看,它都不再只是临时借用,而是已经规约化(conventionalization),成为一个固定、典型的量词。
一、林州方言量词“嘴”的规约化
关于“规约化”,方梅对此阐述得比较到位。方梅指出,文献中提到这个术语时有两种意义,一是指语法化过程的第一步,特定的句法结构逐步专门用于某种特定的功能;另外一种意思是指,在语法化的初级阶段,特定的组合形式或者结构式常常用于表达某种意义或者体现某种特定的功能。从意义解读的角度来说,规约化过程就是其整体意义解读越来越难以从其组合成分的意义直接获得的过程,或者说是语义透明度逐步降低的过程。规约化程度越高,其评价解读越是其词汇意义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越是不依赖语境[19]。
就量词“嘴”而言,主要是指其语法化过程中的语义演变和“一量名”结构的定型化。当它的意义虚化、用于数量结构与名词结合紧密,而且在其他地区也能找到相似用例以资佐证时,我们就判定量词“嘴”已经规约化,即这一用法在林州地区得以约定俗成并固定沿用。下面,我们就从词义、结构、使用地域三个方面,对林州方言量词“嘴”的规约化体现进行具体分析。
(一)词义
在普通话中,量词“嘴”表示“满、全”。卢福波指出,“‘口表示吃一下的量或通过口的部位动作的量;‘嘴则表示食物等与整个嘴的部位接触或塞满有关的量。”[15](P484)如“灌了一嘴啤酒、塞了一嘴面包、啃了一嘴泥、烫了一嘴泡”等。在普通话中,可以说“慢慢吃,塞那么一嘴,怎么嚼啊?”而不能說“慢慢吃,塞那么一口,怎么嚼啊?”在林州方言中,量词“嘴”在修饰固体食物上则表示“少量”。例如:
(1)这个西瓜甜不甜?你尝一嘴不就知道了。
(2)就剩一嘴米饭了,吃完再走吧。
(3)(对小孩)吃了这一嘴馍再去玩。(嘴=圪瘩/疙瘩)
(4)a.(对小孩)吃了这一嘴苹果。(嘴=圪瘩/疙瘩)
b.(对成年人)吃了这一个苹果。
例(3)中的“一嘴馍”,也可以说是“一圪瘩/疙瘩馍”。“圪”缀以其使用频率高、结构类型独特而成为林州方言乃至晋语区的一种非常重要的语法现象。王临惠考察了“圪”类词的语法功能,认为它只有附加性的词汇意义而没有语法意义,其附加意义概括一点说,就是“小”[20]。因此,“一嘴馍”即“一圪瘩/疙瘩馍”,言其量小(少)。在例(4)中,小孩吃的量少,故用“嘴”;而成年人吃的量大,故用“个”。“个”是汉语普通话典型量词,“嘴”和“个”对举,其量词义十分明显。
一般来说,“临时量词的意义比较实在,基本没有虚化。而专职量词的词义比较虚灵,虚化的程度较高。”[17]人们在理解普通话量词“嘴”时,相应的名词概念总会在头脑中出现,如“塞了一嘴年糕”意思是“塞满了一张嘴那么多的年糕”,要借助名词“嘴”来理解“量”,名词意味强。在理解林州方言量词“嘴”时,头脑中则不会出现相应的意象,如“就剩这一嘴馒头了”,把“嘴”换成“圪瘩/疙瘩”,也不会引起意义的变化。这说明其词义较空灵,虚化程度较高。
(二)结构
卢伟伟指出,“‘一量名结构中,当量词的语法化程度较低时,该结构中一般可以插入‘的,而当量词的语法化程度较高时,该结构中一般不可以插入‘的;当量词与‘一语义上结合紧密,以表示名词的数量时,该结构中一般可以插入‘的,而当量词和名词结合更为紧密,主要对名词起限定、描绘作用而不是重在计量时,该结构中不能加‘的。”[21](P29)
在普通话中,“数词+嘴+名词”的结构较为松散,中间可插入结构助词“的”,如“一嘴的米飯、一嘴的馒头、一嘴的饮料”等,“嘴”与名词的接近度比较高。在林州方言中,“数词+嘴+名词”中间不能插入“的”,可以说“尝一嘴西瓜、剩一嘴馒头”,而不能说“尝一嘴的西瓜、剩一嘴的馒头”。这说明林州方言量词“嘴”与“一”和名词的结合比较紧密,“嘴”作为量词的语法化程度高。
(三)使用地域
量词“嘴”的上述用法并不仅仅局限于林州方言,据山西晋城的同事告知,他们方言中也有“一嘴饭”的说法。比如说吃米饭吃到最后,剩下一点点,就说最后一嘴;汤之类的就说最后一口。林州与晋城同属晋方言,可以说,修饰固体食物且表“少量”的量词“嘴”,在一些晋语方言区中是普遍使用的。
除了晋语之外,在李荣主编的《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的42个方言点中,银川话也有同样的用法,如:“碗头还剩嘴把饭了,你等一下子,我就吃好。”据北方民族大学的马君花教授告知,在宁夏北部平原,均用“嘴”修饰固体,用“口”修饰液体,表示少量。张正霞对重庆忠县方言特征词“嘴”进行了考释,在忠县方言中,“嘴”专用于计量月牙儿形状的食物[22]。既然是月牙儿形状食物,就不可能是液体,如作者所举用例:“还剩两嘴鸭蛋,你们两个把它分了”,句中的“两嘴”即“两牙”,“牙”侧重弯细,亦有“少量”义,与林州方言量词“嘴”的用法其实是相同的。使用地域的广泛,也说明林州方言量词“嘴”的规约化并不是孤例。
不过,在林州方言中,“嘴”除了修饰固体食物外,也可以用来计量“胡须、酒气、口疮、燎泡、泥沙、脏话、方言”等。值得注意的是,在计量这些对象时,它是“满、全”义,中间可插入“的”,名词意味明显。那么,为什么“嘴”只在修饰固体食物上实现了规约化,而在计量其他对象时尚未规约化?“嘴”的规约化程度如何?除了规约性的因素之外,一个量词和哪些名词匹配是否还有内在的选择理据?张敏指出:“量词与名词的选择性共现关系实际上是它对名词代表的概念进行范畴化的反映。”[23](P71)量词的范畴化虽然本质上是共时平面的多义现象,但如果能够在历时平面得到佐证,就可以进一步提高范畴化分析的可信度[18](P122)。下面,我们通过考察“嘴”对名词选择的历时情况和共时表现,尝试着对这些问题予以解答。
二、量词“嘴”对名词选择的
历时和共时考察
(一)历时考察①
嘴,本义是指“鸟嘴”,字形作“觜”[24](P54)。《广韵·纸韵》:“觜,喙也。”在东汉至隋的中土文献中,它仅指鸟嘴;但在中古译经中,“嘴”已不限于指鸟类,还可用来指称虫、蚊、峰等昆虫类的饮食器官。至唐代,“嘴”的义域进一步扩大,可以用来指称其他动物和人,不过用例很少,整个唐五代还是多用于鸟类[25];用于人时多带有贬义色彩,如唐代王梵志《世间慵懒人》诗:“出语觜头高,诈作达官子。”即使到了宋金时期,仍然有“人嘴尖”的说法,其贬义意味不言而喻,如金代无名氏《刘知远诸宫调》第一【黄钟宫·快活年】:“妯娌傍边弩觜胮唇,不喜些些。”基于此,吕传峰将鸟嘴的隐性义素特征概括为[+尖利]、[+坚硬]、[+凸出],这从其常见组合“铁觜乌”“大鸟长嘴”“金刚觜乌”等中亦可窥知[25]。
由于“嘴”具有[+坚硬]、[+凸出]的特征,“嘴”最初用作量词时,主要用于计量带一定硬度的嘴的“外附物”,即“胡子”。例如:
(5)却说碧峰长老一嘴连鬓络腮胡子,人人都说道:“长老何事削发留须?”(明代罗懋登《三宝太监西洋记》第四回)
(6)去时虽然长大,还没这般雄伟,又添上一嘴胡须,边塞风俗,容颜都改变了。(明代冯梦龙《醒世恒言》第五卷)
同时,由于“嘴”具有[+尖利]的特征,于是,与“嘴”匹配的名词逐渐由“口外”扩展到“口内”,也用于计量“牙齿”。例如:
(7)一只金丝犬又古怪,张开一嘴的狗牙,露出四只那狗爪,奔向前来,就象个虎窜狼奔。(明代罗懋登《三宝太监西洋记》第七十回)
量词“嘴”之所以能与名词“胡须”“牙齿”率先形成选择关系,是在于它们语义特征的一致性,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词与词的组合除了要受句法功能的限制外,还受语义选择的限制,而语义选择的限制则往往表现在语义特征上。”[26](P17)值得注意的是,此期的量词“嘴”还能直接修饰形容词“尖利”,如《西游记》第七十三回:“两眼光明,好便似双星幌亮;一嘴尖利,胜强如钢钻金锥。”这也是词与词组合遵循语义一致性基本原则的很好说明。
随着“嘴”使用义域的扩大,不再局限于鸟、虫、蚊、峰之类而用于其他动物或人类后,“嘴”本身所具有的[+尖利]、[+坚硬]、[+凸出]的语义特征尽管慢慢磨损,“但对于人来说,突出在外的是唇”[27]。因此,“嘴”可以用来计量唇上的附着物。例如:
(8)这晁无晏只见他东瓜似的搽了一脸土粉,抹了一嘴红土胭脂。(清代西周生《醒世姻缘传》第五十三回)
当“嘴”用于“人或动物”时,凸显的是其作为人或动物饮食、说话的器官,因此,也可以把“嘴”当作容器来修饰容器内的物体。例如:
(9)贾蓉又和二姨抢砂仁吃,尤二姐嚼了一嘴渣子,吐了他一脸。(清代曹雪芹《红楼梦》第六十三回)
(10)心想,这一喝,准闹一嘴茶叶,因闭着嘴咂了一口,不想这口稠咕嘟的酽条咂在嘴里,比黄连汁子还苦。(清代文康《儿女英雄传》第三十七回)
(11)三爷说:“拿点漱口水来,你这个招儿真损,闹了一嘴石灰。”(清代佚名《小五义》第十六回)
又由修饰固体物扩展到修饰液体物、气体物。例如:
(12)众狐说道:“仙姑不要着急。等他们将酒菜吃上两嘴,尝着甜头,咱们再大展法力,闹他个望影而逃。”(清代醉月仙人《狐狸缘全传》第十四回)
(13)又抽鸦片,一嘴的烟味,比粪还臭,教人怎么样受呢?(清代刘鹗《老残游记续集》第四回)
(14)老残道:“诗虽不会做,一嘴赏花酒总可以扰得成了。”(清代刘鹗《老残游记续集》第七回)
(15)这也不管什么干净,将自己口中涎沫咕哝咕哝了半天,就是一嘴的白沫子。(清代佚名《小五义》第八十回)
再由修饰具体物扩展到修饰抽象物。例如:
(16)旁边却站着一个方巾襕衫、十字披红、金花插帽、满脸酸文、一嘴尖团字儿的一个人。(清代文康《儿女英雄传》第二十八回)
(17)你也不问问缘故,一嘴的屁话混糟蹋人。(清代陈森《品花宝鉴》第五十八回)
(18)正待上岸,见旁边一号大船,船上灯烛辉煌,多少差官在船头上向埠头要马要轿,一嘴的京腔闹个不住。(清代坑余生《续济公传》第一百四十五回)
(19)打算已定,一摇二摆的走到那客栈里面,深怕人识破,便撇了一嘴的北方话。(清代坑余生《续济公传》第二百十三回)
从上文的分析可以看出,量词“嘴”在明代产生,经过明清时期的逐步演进,其计量对象扩展过程如图1所示:
在上述文献中,当“嘴”用于“一量名”结构时,虽然具有量词的功能,但“一嘴”与“名词”的结合不够紧密,中间可插入“的”,如例(7)中的“一嘴的狗牙”、例(15)中的“一嘴的白沫子”、例(17)中的“一嘴的屁话”等,名词义显豁。同时,无论是“一嘴胡须、一嘴石灰、一嘴烟味、一嘴赏花酒”,还是“一嘴京腔、一嘴北方话”等,“嘴”均表示“满,全”,用“嘴”这个具体可感的人体器官来计量不同事物的“量”。
(二)共时考察
我们通过检索北京大学CCL语料库,对其中借用量词“嘴”的用法进行了归纳,具体如表1所示:
在共时平面中,“嘴”范畴的扩展基本上是沿着由口外到口内、由附着到含有、由具体到抽象的引申链条。由于“嘴”的原指义具有[+尖利]、[+坚硬]、[+凸出]的语义特征,因此与“嘴”具有部分相同语义特征的“胡子”便优先成为“嘴”的匹配對象,其他成员基本都是由这一原型成员扩展延伸而来。有研究者指出,“原型成员既是认知的核心,也是历史的源头。”[18](P100)量词“嘴”最先修饰“胡子”正说明了这一点。紧接着,口外附着物从坚硬发展到非坚硬,如“一嘴油腻”。然后,由口外坚硬附着物扩展到口内坚硬附着物,如“一嘴牙齿”;口内附着物亦从尖利扩展到非尖利,如“一嘴溃疡”。由内附物进一步发展到内含物,在内含物中,首先出现的是固体物,它大致可分为可食和非可食两种;随后出现的是流体物,主要有液体和气体两类,液体亦分可饮和非可饮。这说明“嘴”不仅是饮食或说话的器官,更是纳物的“容器”。无论是外附物、内附物还是内含物,都是具体的,由具体物再向前扩展延伸,就出现了抽象物。
总的来看,“嘴”共时的范畴化过程与其历时的发展基本是一致的。需要说明的是,在共时的通语用法中,“嘴”显然是借用量词。例如:
(20)轻轻的啄开它,我们就看见了那新鲜红嫩的内部,同时我们已染上了一嘴的红水。(鲁彦《故乡的杨梅》)
(21)先笑后说话,一嘴的长形小珍珠。(老舍《同盟》)
(22)一嘴的黄牙板,好似安着“磨光退色”的金牙。(老舍《老张的哲学》)
(23)在那边的时候是一嘴的新主张与夫司基,刚到,刚到这边便大家夫司基妓女!(老舍《猫城记》)
在上述例句中,无论是修饰液体物、具体物,还是抽象物,均需借助“嘴”做为容器的大小来考察所容之物的量;量词和名词之间均有“的”,数量结构和名词结合不够紧密;“嘴”的名词性特征显著,表“满、全”义。这些特征与修饰固体食物、表少量的林州方言量词“嘴”,有着显著的区别。
三、林州方言量词“嘴”的
规约化程度及动因
结合量词“嘴”范畴化的历时扩展和共时表现来看,与“嘴”匹配的名词尽管很多,但在林州方言中,只有在修饰固体食物上实现了规约化;其他和普通话一样的用法,如计量“胡须、酒气、口疮、燎泡、泥沙、脏话、方言”等,理解时仍需借助名词“嘴”来考察其“量”,名词性特征明显,充其量为一个借用量词。我们认为,“修饰固体食物”之所以优先规约化,是与量词“嘴”的范畴化动因有着密切关系的。
(一)语义特征的一致性
语义特征的一致性是量词“嘴”选择名词进行组合的先决条件。刘晨红指出,“两个词语能够组合成一个句法结构,关键是看两者是否具有某方面共同的语义特征。”[28]“胡须”([+坚硬]、[+凸出])、“牙齿”([+坚硬]、[+尖利])与“嘴”的原指义([+坚硬]、[+凸出]、[+坚利])具有部分相同的语义特征,因此,它们作为范畴扩展的原型成员优先进入与“嘴”的搭配选择中。在此之后,随着“嘴”的[+坚硬]、[+凸出]、[+坚利]语义特征的磨损,在选择与之匹配的名词时,也就淡化了这方面的要求,从而出现了胭脂、石灰、茶等具体名词;由具体名词再发展到抽象名词,就走到了范畴的尽头。这和宗守云的论述是一致的:“范畴从原型成员开始,一步一步地向前扩展延伸,先是扩展到表面上相近的相关的事物,再扩展到表面上看不出来的相近的相关的事物,最后扩展到完全看不出来的事物,这就走到范畴的边缘了。”[18](P100)
(二)容器图示和容器隐喻
人体是一个三维容器,有“吃进”“吸入”“呼出”和“排除”等生理现象,还有“走进”“走出”等一系列与外部世界相互作用的物理空间关系,这样的结果就形成了一个抽象的图式,即容器图式[29](P21)。“嘴”作为人身体的一部分,亦有作为容器的功能,它虽然是饮食器官,容纳之物却又不局限于饮食(如馅饼、馍、肉粽、面包、烧饼、热茶、稀饭等),也包括非可食的固体、非可饮的液体(如泥、沙子、墨、血)等。由于容器都有一定的形体并占有一定的空间,而空间的容积或面积容易计量,于是人们便用具体可感的空间去描述固体物的大小和液体物的多少,甚或是离散的、无法触及的气体(如臭气、酒气等)的数量。因此,但凡人们想要计量的物体都能成为其中的容纳物,而不一定考虑物体能否食用或饮用的性质。
与此同时,“容器图式可以通过隐喻扩展运用于抽象的认知域”[30]。“嘴”被看成容器图式,既有纳物功能,亦有取物功能;既有取具体物的功能,亦有取抽象物的功能。“由嘴说的话”和“与嘴有关的语言”便是从“嘴”取出的抽象物;这是把“嘴”看成容器,把“话”或“语言”隐喻为“物体”,于是就有了用容器来量度物体的可能。“在这种隐喻中,隐喻不仅仅是一个孤立的范畴向其他领域的另一个范畴的语义扩展,更重要的是范畴之间的连接和关系。”[31]而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就是“容器—功能”关系。
(三)转喻
转喻有各种认知框架,如“整体—部分”“地点—机构”“成品—材料”“容器—内容”“范畴—特性”等[32]。其中,“一嘴胭脂”和“一嘴油腻”,就是基于用“嘴”这个整体来指代部分“嘴的外围”这一转喻的前提下而产生的。如“一嘴胭脂”不是說整个嘴都涂上了胭脂,而是“嘴”的一部分即“嘴唇”有胭脂;“一嘴油腻”亦然,不是整个嘴里都是油腻,而是突出“嘴”的外部边缘沾满了油腻。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在量词“嘴”范畴化的动因中,语义条件是其得以扩展的先决条件和核心要素。由于“嘴”的本义具有[尖利]、[坚硬]等语义特征,而且这些语义特征在东汉至宋的一千多年中一直保留着,根深蒂固地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和意识,于是在很多情况下,“嘴”已成为人或动物进食的利器。如唐代刘禹锡《聚蚊谣》:“露花滴沥月上天,利觜迎人著不得。我躯七尺尔如芒,我孤尔众能我伤。”再如唐代元稹《人道短》:“蚊蚋与利觜,枳棘与锋铓。”因此,凡是非流质的、需用牙齿咀嚼和啃食的就多用“嘴”来修饰。此外,“嘴”泛指“人或动物的饮食器官”后,可以视为容器,这时它最主要的功能即是“进食”,因此,用以修饰食物便成了“嘴”最常见的用法。在语义条件和容器功能的双重制约下,随着用例的逐渐增多,用“嘴”修饰“固体食物”先迈开了规约化的一步,从而成为林州方言中修饰固体食物的典型量词。
在修饰固体食物方面,林州方言量词“嘴”无论是在词义还是在结构上,都表现出与普通话不同的特点,它已经规约化为典型量词。不过,结合量词“嘴”范畴化的过程和轨迹来看,这种规约化的程度较低,尚处于量词“嘴”发展的初始阶段。正如方梅所言,规约化的一种含义即指语法化过程的第一步,随着语法化过程的终结,规约化才能达到最高层级[19]。就“嘴”这一个案来看,据吕传峰[25]、贾燕子[33]等研究,直至清末,“嘴”方取代“口”而成为口语中表{mouth}的常用名词。在此之前,“嘴”主要处于与“口”的竞争替换中;在这之后,又以发挥名词的职能为第一要务,无暇分身于名词虚化为量词的语法化工作。这就是普通话中为什么“嘴”是借用量词的主要原因。当然,普通话与方言的发展未必同步,相对而言,林州方言量词“嘴”发展得稍快一些,在修饰固体食物上,它已由借用量词发展为典型量词。
参考文献:
[1]林州市志编纂委员会.林州市志[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4.
[2]李荣.官话方言的分区[J].方言,1985,(1).
[3]侯精一.现代晋语的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4]林焘.北京官话溯源[J].中国语文,1987,(3).
[5]朱德熙.语法讲义[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6]吕叔湘主编.现代汉语八百词(增订本)[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7]赵元任.汉语口语语法[M].吕叔湘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8]郭绍虞.汉语语法修辞新探[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9]房玉清.实用汉语语法(第二次修订本)[M].北京: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2008.
[10]邢福义.汉语语法学[M].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6.
[11]刘月华,潘文娱,故韡.实用现代汉语语法(增订本)[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12]张斌主编.现代汉语描写语法[M].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0.
[13]黄伯荣,廖序东主编.现代汉语(增订五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
[14]胡裕树主编.现代汉语(重订本)[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17.
[15]卢福波编著.汉语教学常用词语对比例释(维文版)[M].北京: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2004.
[16]郭先珍.现代汉语量词用法词典[Z].北京:语文出版社,2002.
[17]谭景春.从临时量词看词类的转变与词性标注[J].中国语文,2001,(4).
[18]宗守云.汉语量词的认知研究[M].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2.
[19]方梅.负面评价表达的规约化[J].中国语文,2017,(2).
[20]王临惠.山西方言“圪”头词的结构类型[J].中国语文,2001,(1).
[21]盧伟伟.“一量(的)名”结构研究[D].锦州:渤海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
[22]张正霞.释忠县方言特征词“嘴”[J].重庆教育学院学报,2003,(2).
[23]张敏.认知语言学与汉语名词短语[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24]刘君敬.名词“嘴”用字的历时考察[A].四川大学汉语史研究所,四川大学中国俗文化研究所编.汉语史研究集刊(第十五辑)[C].成都:巴蜀书社,2012.
[25]吕传峰.“嘴”的词义演变及其与“口”的历时更替[J].语言研究,2006,(1).
[26]邵敬敏,任芝锳,李家树.汉语语法专题研究[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27]张薇.“口”、“嘴”辨析[J].语言教学与研究,2005,(2).
[28]刘晨红.临时名量词与名词匹配的认知机制[J].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2).
[29]Johnson,M.The Body in the Mind:The Bodily Basis of Meaning,Imagination, and Reason[M]. 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7.
[30]李瑛.容器图式和容器隐喻[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4,(5).
[31]熊仲儒.量词“口”的句法认知基础浅探[J].巢湖学院学报,2003,(2).
[32]刘晨红.器官名词作临时名量词的认知分析[J].修辞学习,2007,(3).
[33]贾燕子.“口”“嘴”上位化的过程和原因[J].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5).
Abstract:“Zui(嘴)” as a borrowing quantifier in Putonghua, in Linzhou dialect, the quantifier “zui(嘴)” is clearly defined as a typical quantifier in terms of meaning, structure or region of use. However, from the diachronic process of its categorization and the synchronic performance of its categorization, the level of its conventionalization is still low, limited to the modified solid food. This is probably related to the original meaning of the“zui(嘴)” and being as the core function of “human and animal eating organs” after the generalization of “zui(嘴)”.
Key words:“zui(嘴)”;the measure word;Linzhou dialect;conventionaliz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