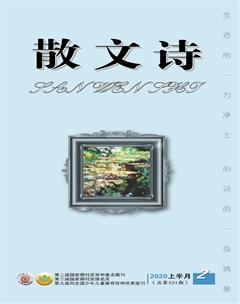世界散文诗:在思想的隐喻里展开或释放(七)
黄恩鹏
博尔赫斯的作品受到不同文化遗产的影响,跨越了不同的时间和空间,不了解这一背景,就很难理解他的创作思想。博尔赫斯的独特之处,在于他能把时间和空间当作作品的主体,而人则成为客体。小说、散文如此,诗歌与散文诗更有所体现。博尔赫斯认为诗歌、小说、繪画、雕塑等文学艺术的主题是有限的,也是大致上雷同的,多少年来一再相互重复、类似,无所创新,但如果予以不同的处理手法,置于不同的时代背景,并置换于空间时间,就能有所创新取得效果。在博尔赫斯笔下,生活从来就是一个扑朔迷离、虚虚实实、令人眩晕不已的迷宫,同样的情节循环往复。但是,高明的作家诗人定能让读者有所惊异地在文字中发现先前从未觉察的事物。那些事物是具有精神性质与指向的。博尔赫斯《达卡》:
达卡位于太阳、沙漠和海的交叉点。
太阳罩住我们,天空、沙丘压住公路,像潜伏的野兽,海充满怨恨。
我见过一个阿位伯酋长,他蓝色的袍子比燃烧的天堂更炽热。
电影院旁边的清真寺发出祈祷文一样明净的光。
向阳茅屋之后,太阳像小偷,爬上了墙头。
阿非利加永恒的命运交织着英雄事迹、偶像、王国、纠缠的森林和刀剑。
我得到了一个黄昏和一座村庄。
博尔赫斯早期主张极端主义。极端主义是以拉法埃尔·坎西诺斯·阿森斯为首的一伙诗人于1919年在西班牙创建的,当时博尔赫斯也在那里。他们在宣言中说:“我们的号召是‘极端,在我们的信条中,能一视同仁地容纳表现新追求的一切倾向。”博尔赫斯于1921年回到布宜诺斯艾利斯,并将这一新的文学流派移植到拉丁美洲。他在《我们》杂志上概括了自己的美学原则:(1)抒情最主要的手段是比喻。(2)摒弃不必要的连接词、句和多余的形容词。(3)去掉修饰成分、说教、忏悔、景况叙述和苦心追求的隐晦。(4)将两个或更多的形象融为一体,从而使诗句更耐人寻味。①极端主义是一种“语言冒险”,但又锻造了绝佳的语境叙述方式。这种创作方式,为博尔赫斯开启了一个“隐喻”的窗口。从这个窗口,他看到了时间对于人生的捉弄。人在时间面前,永远是奴仆而不是主人。一切与时间抗衡的举动都是十分可笑和自不量力的。因此,无论是从短篇小说还是诗歌,大部分是以时间为主题意旨的。我认为,博尔赫斯的散文诗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一篇小小说。因为里面有着小说元素。或者说他的小小说是一章散文诗也不过,因为里面有着散文诗的精神性质和语言镜像。
《达卡》可说是博尔赫斯作品中非常重要的一篇。从表面上看,很像是哲理诗,凡是他的短篇小说中所表达的哲理,在诗中也同样地表达了。如:人生的虚幻。时空的混乱。生死的不分。以及代表这些哲理的象征。如:梦。镜子。迷宫。老虎。等等,无不在他的文本里出现。也可以说,他的诗是他的短篇小说的补充;或者说,他的短篇小说是他的诗的补充。实际上,我们不要把博尔赫斯想象成一个哲学家,他就是一位诗人和小说家。他的作品,是幻想文学。哲理性的文本,只不过是他的幻想的一部分。因为他自己就曾说过:“我使用哲理,是作为文学的工具。我自己并不是一个思想家。我使用各种各样的哲理,作为描写的材料。我在写作时,并不企图教训人;我只是想写出一个使人感到有趣的故事,写出一首使人感动的诗。换句话说,我首先着眼的,是感情。”②这章文本的语言镜像却是明澈的。
他看到了好的天地壮景:太阳、沙摸和海。看到了一个多元无序,又支离破碎的整体。看到了一个阿拉伯酋长,一个宗教的虔诚与不可捉摸的雕像。沙漠与海的对立。清真寺的宁静与电影院的喧哗对立。一个空间构成的生存统一机体,那些权利与自由的东西。“太阳”“沙漠”“海”“天空”“公路”“野兽”“蓝色的袍子”“燃烧的天堂”“电影院”“清真寺”“茅屋”“小偷”“墙头”“偶像”“王国”“纠缠的森林和刀剑”“一个黄昏和一座村庄”,等等,组成了一个古希腊式的悲情气氛。这里的多种镜像体验,以及镜像与镜像之间的对比与比拟是显而易见的:古老的与现实的。喧哗的与宁静的。国家的与民间的。从容不迫与他所不能理喻的逃遁。大与小。旧与新。等等这些,都在时间和时空的跳荡里,展放出一个个诡秘的细节。而“我得到了一个黄昏和一座村庄”,这光明即将逝去的最后归宿,有着宗教色彩:宁静。澹泊。与上述的阿非利加的“英雄事迹”“偶像”“王国”“纠缠的森林和刀剑”这些人类的桎梏相比,黄昏和村庄,是一个纯净、宁谧的象征。两者对比,哪一种更有力量,更有着耐人寻味的精神依托,就显而易见了。有如一个古与今相环相套的故事,有开始、有情节的展开和结束,令人品咂不尽。
如果说博尔赫斯早期的作品难读,那么他的晚期作品就比较容易领会了。他的诗有着相当的文本喻意,在一些诗文中,他对于时间的迷恋之作比比皆是。在他笔下,生活是个扑朔迷离、虚虚实实的迷宫。同样情节循环往复,但总会让人发现其中未曾觉察的秘密。如《趾甲》《布局》《王宫》《祈祷文》《无尽的礼物》等等,帕斯就曾在《弓手、箭和靶子》一文中,佩服博尔赫斯语言洗练、意境虚幻,说他“善于用最少的语言表达最多的内涵”。在他的作品里,物理学和逻辑学的一条最基本的原则遭到了他的有意悖反——因果颠倒。或者他自己为自己设想了许多关于时间的诸多“可能”、对梦幻的倾慕,等等。且看他在《梦之虎》中就有这样的句子:
童年过去了,虎和我对虎的热爱都老了,但它们仍在我的梦里出现。它们在那隐藏的,或者说,混沌的层次占着优势。因此,睡着的时候,有些梦使我愉快,我马上就知道自己在做梦。于是我想:这是梦,完全偏离我的意志,此刻我有无限的力量,我要召唤一头老虎。③
现实与梦的距离遥不可及。但“有些梦”让我知道“自己在做梦”,这想必一定是美好的,谁愿意让一些不美好的在思想里出现呢?那么,有着无限力量的我,又该怎样对待那偏离我意志的梦?擅用暗喻的博尔赫斯在许多作品中都透出一种古希腊悲剧味道。作品虽然短小,却暗示一个大的哲学命题:生命无常,境遇也无常。在语言的冷凝里,他所缔造的神话、错配身份、时间强有力的循环,等等,都串成了绵绵不绝的想象链,在时间的缝隙间寻绎诸多哲学问题。但是,“虎”是什么?是真实存在的虎,还是个人内心激荡“不羁”的精神性?是顺着帕拉那河漂流下来的、亚马逊密林和植林岛的“虎”?还是背着堡垒、有无限力量冲锋陷阵的英武“战士”?也许后一种更符合他的精神品格——他寄盼于威仪力量的大兽。
这是博尔赫斯呈现的内心。或是那无法抗拒的、比这大兽更凶猛的现实存在。对博尔赫斯来说:虎,就是一种“属于不可能的大小”,虽出现不过一瞬,却是一种永远存在的灵魂征兆与精神镜像。如他的诗《老虎的金黄》中所要体现的,是“西下的夕阳”快要沉落的那只“朦胧的光亮、难测的阴影和原始的金黄”之孟加拉老虎。事实上,它隐喻的是:迅忽、快捷、难以捕捉的、对人生命摧残巨大的时间。时间就是梦之虎。
博尔赫斯的《鸟类学命题》更有非凡“时间的闪烁不定”的精神性质:
我闭上眼睛,看见一群鸟。这视象维持了一秒钟或不到一秒钟,我不知道自己看到了多少只鸟。是一定的还是不确定的数目?这问题牵涉到上帝存在的问题。假如有上帝,数目就是确定的,因为上帝知道我看见多少只鸟。假如没有上帝,数目就不能确定,因为没有人能够点数。就这件事来说,我所见的鸟是少于十只(姑且这样假定)而多于一只;然而我并没有看见九、八、七、六、五、四、三或两只。我看见的是十与一之间的一个数目而不是九、八、七、六、五等等。这个数目,作为一个整数,是不可以设想的;因此,上帝存在。
这是一个带有数学经验的文本。一如博尔赫斯所说的那样:“凭借经验是不能接近数学的。”④
“数学通过定义可以得到证明。可数学并不因此就是实在的”。⑤那么,博尔赫斯到底要证明什么呢?一群鸟的影像是闪烁不定的。用闪烁不定的意象来求证一个确定性,似乎有着很大的矛盾存在。不確定的意象与确定的意象,会有着怎样的结果?那么,只有猜测了——“我闭上眼睛”才能看见。事实上,诗人有意“拉开”了想象的空间,以数字的不确定性来喻示一种不可预想的未来。由此牵涉到“上帝是否存在”的问题。“假如有上帝,数目就是确定的。”但是,无人知道“我”到底看见了多少只鸟?我也不知道到底有多少只鸟?在少于十只与一只之内,到底是几只呢?还是那种在时间的闪烁不定状态下的,飘忽不定的生命感受。那么,就只有上帝——这个冥冥之中存在的至高无上的圣灵能感知得到。在这里,诗人有意在十与一之间圈划了一个范畴,有意创造一种数字的“不确定性”。那么肯定是其中的某一个数字了。
哪一个都无关紧要,哪一个又都十分重要,都是可能性的存在。在存在与虚无之间,最后他还是选择了存在。但他不可以虚设定论,他最后才说出了——“因此,上帝存在”这一个三段论的哲学命题。以语言镜像的虚实,印证了柏格森的“时间与自由”的理论——心理时间与实际时间的辨证。这章作品如同宙斯的九个指环那样的迷离:宙斯是希腊神话里的主神,他的指环每隔九夜会衍变出八个同样大小、同样瑰丽的指环,每个再变出八个,循环不已。永远地没完没了,像色彩在天上变幻着,无所穷尽的数理之迷。就连他的小说,也都有着散文诗的精神性质,指证一种时间对于生命的阉割。那些在时间里逐渐剥除羽毛的生命,回光返照着历史具体的意识。他谈到镜子和反映的形象,是简单的暂时的交替,或者是梦境的幻想,来自于每一瞬间的记忆。而记忆则是时间的另一维度的精神征象。诗人认为,“随着每一瞬间的逝去,有一扇门在我们背后关上,我们再也不会打开。所有的东西都成定局,因为它们属于不可侵犯的规律,但是希望还是有的,希望来自太阳西下的彼方,那里有典型和耀光在等待。”⑥
这种极端主义的写作总是带有语言的极端冒险。但他们是有准备的,也是经历过探索的。从而形成了一种迂回曲折、隐喻暗示的手法,来反观现实的存在。它既不同于现实主义的精确具体描写“我”与这个客观现实的关系,也不同于浪漫主义的热衷于表现主观体验和情绪。它总是把现实与虚拟的事物融在一处,在一种幻境氛围里加以再现,然后能通过色彩斑驳、光怪陆离的画面和形象的折射,曲折地反映现实世界。借此达到一种揭露或批判的目的。而现实一如幻境那样扑朔迷离。他的《开端》也是这样。“两个希腊人在谈话:也许是苏格拉底和帕尔米德斯。最好还是不要知道他们的名字,这样,故事会简单些,神秘色彩也浓些。”而“谈话的主题是抽象的。他们有时会暗示到彼此都不相信的神话”,先是道出了两位哲学家的名字,后又让大家不要知道,因为这样有一种神秘感,不能预感到他们在谈什么?但又是人人都可谈的问题,是神秘的,也是公开的。那么谁说了什么,谁说服了谁指证了什么,都不是问题了。因为他们彼此都不相信的神话。“不要神话不要比喻,他们思考或者尝试思考。”最后,由开头的“也许是苏格拉底和帕尔米德斯”到了最后,则是“两个无名氏在希腊某个地方谈话,是历史上的大事”,这历史上的大事,人人都能谈,而不是不能谈。这里,谁与谁在谈已不重要,因为他们“已经忘记祈祷和魔术”。没有一切规定性和现实的干扰,论题就是论题,即使是谬误的论调,也得不到结论,因为对于集体来说,是无意识的,更是麻木的,或是与自己无关的。但这“历史上的大事”确乎来讲,是两个谈话者的而非别人的。这又是一种什么样的整体知觉呢?
博尔赫斯的作品的特点是幻想。有时到了荒诞不经的地步,然而他是以充沛的诗意来写这种幻想的。因为他认为这应是“我生活中所见所闻的事情的象征;不过我不是直接说出来,而是通过幻想的描写说出来而已”。⑦他认为,一部作品,如果不能超过作者所预期达到的效果,就没有价值。而关于他所说的效果,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分析理解。但是有一点则是肯定的:他是以一种曲迂逶迤的手法,来表明他对周围或者这个世界的看法。亦即是对现实的讥讽、不满的抗议。从而带着某种悲观主义色彩。那么,到了后期他不再相信什么文学流派,而是抛弃了他开始主张的极端主义,真正走人了一种将神话传说、古老寓言和现实融为一体的现实主义。“是在现实主义中发芽生长起来的”。他对诗歌的见解是:“一种语言是一个传统,一种抓住现实的方法,而并不是符号的随意集合。”他在《关于某次对话的对话》对话的内容中这样写:“我提议马塞多尼奥一起自杀,那么就可以继续讨论下去,不受骚扰”。只有自杀的人在一起对话,才能继续不受任何意识形态制约或骚扰,这是一个多么有意味儿的对现实的讽刺!那种隐含着的讽喻现实,为诗人们提供了更深刻的文本探研。现实主义才是语言的活力。
最后,诗人又更深地将语境的隐喻推向纵深,“我记不清楚我们是不是那个晚上自杀”,这就更让人有种玄之又玄的思考。也对应了A所言的“在人的一切遭遇中,死亡必然最没有作用”,因为死亡是不存在对话的。
注:①转引自赵德明等译的《拉丁美洲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第387页。②参阅《视界》周刊1979年第52卷第6期《博尔赫斯访问记》。③参阅《拉丁美洲散文诗选》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作品部分,陈实译,2007,花城出版社,第45页。④【阿根廷】奥尔兰多·巴罗内《博尔赫斯与萨瓦托对话》,赵德明译,1999,云南人民出版社,第85页。⑤【阿根廷】奥穹兰多·巴罗内《博尔赫斯与萨瓦托对话》,赵德明译,1999,云南人民出版社,第86页。⑥【阿根廷】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巴比伦彩票》,王永年译,1993,云南人民出版社,第5页。⑦参阅《视界》周刊1979年第52卷第6期《博尔赫斯访问记》。
——读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乌尔比纳的一名士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