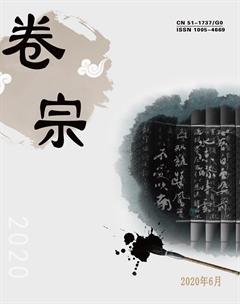游走在“模糊”与“明晰”间的散文英译
摘 要:现代散文是一种重要的文学形式,贵在言简意深,意蕴深厚,充满了朦胧的美感。本文首先探讨了翻译中模糊的定义,然后从修辞、文体、和文化层面简述了汉语散文中模糊的成因,最后从翻译过程角度提出了散文中的模糊语言翻译策略。
关键词:散文英译;模糊语言
中国文化一贯崇尚“雾里看花、水中望月”的朦胧美感,这体现在诗、画、书法、音乐、雕塑等方方面面,中国的语言文字也不例外。汉语是语义型语言,在几千年的重意、重神、重风骨、重凌虚的哲学和美学传统影响下,形成了一种注重内在关系、隐含关系、模糊关系的语法结构素质(转引自丁国旗等 2005:41)。相较汉语而言,英语虽然也有模糊之处(如善用抽象大词),但总体而言语法严谨,语义质朴简洁,注重逻辑。汉英两种语言在模糊性上的差异一方面使翻译有了更多的灵活性和可能性,另一方面也造成了翻译,尤其是文学作品的翻译困难。散文以短小精悍,言近旨远著称,模糊语言的概括性、灵活性和延展性在一定程度上使得散文能以有限之篇幅描绘无穷之意蕴。因而,研究散文中模糊语言的翻译无论对于散文英译还是模糊语言翻译研究都有重要价值。
1 翻译中的“模糊”与“明晰”
毛荣贵在《翻译美学》中谈到,“模糊语言”是指“语词具有朦胧而又广远的语义外延”,“在语言表达中舍工笔而求写意,极力营造‘由朦胧产生一时费解,由一时费解走向豁然开朗的阅读效应”(毛荣贵 2005:231)。邵璐认为,翻译学中的模糊语言是指源文本和目标文本中具有不确定外延的话语,其特点体现在所指对象界限的不确定性(邵璐 2011:63)。其实,模糊是一种距离感,距离的两端,一端是能指,一端是所指,一端是作者“所言”,另一端是作者“欲言”。这两端的距离越远,对应性表现得越间接,理解需要调动的认知储备和文化背景越多,理解开放度越大,那么模糊性就越高,反之则越低。由此可见,明晰和模糊就像远与近一样,是一个相对概念而不是绝对概念,是一种程度而不是二元对立的两级。翻译中的模糊又具有双重性,第一层是原语能指和原语/译语所指之间的距离。由于原语读者能够调动足够的认知储备和文化背景,将能指和所指连缀起来,理解原文的意义,欣赏模糊所带来的朦胧美感。翻译中的另一层模糊则是由译语能指到确切的原语/译语所指(原语所指与译语所指具有同一性)之间的距离。由于原语读者和译语读者在认知储备和文化背景上的差异,若译者采取直译,把模糊留给译语读者,那么译语读者可能无法真正理解原文作者想要表达的意义和情感。若译者把原文掰开嚼碎,那文学的朦胧美可能就消失殆尽。理论上来说,最好的翻译效果是保持这两层距离大致等同,也就是保持朦胧美,尽力传达原文的意义,情感及美学效果。但是在实践中,要实现这种效果十分困难,需要译者根据两种语言特有的文化和历史语境,考虑译文读者的认知背景做出多方调整。
2 散文“模糊”缘何而生
模糊性是人类思维的本质特征之一。作为人类思维载体的语言不可避免地带有模糊性特点,这一特点在认知层面上深刻揭示了语言自身存在的本质特征,丰富了人类对语言实质的认识(邵璐 2011:1)。语言使用者的思维模糊和特殊意图,语言所反映的客观世界的复杂性,语言中能指与所指对应关系模糊,以及语言使用者的解码能力差异都会造成模糊。对于散文来说,模糊现象主要源自于修辞层面、文体层面和文化层面。
2.1 修辞层面
散文的风格活泼灵动,多用比喻、拟人、双关、通感、反复等修辞手法来增加文章的文学性与生动性。由于认知储备和文化背景的差异,译文读者对所指及修辞所涉及的其他对象的理解都有一定的模糊性。
例2:秋并不是名花,也并不是美酒,那一种半开,半醉的状态,在领略秋的过程上,是不合适的。
译:Unlike famous flowers which are most attractive when half opening, or good wine which is most tempting when one is half drunk, autumn, however, is best appreciated in its entirety.
此例运用了连锁隐喻的修辞手法,把领略秋之韵味与欣赏名花和美酒作了对比,用“半开,微醉”来衬托领略秋所需要的酣畅淋漓的状态。此例的模糊在于这个隐喻并未明示领略秋的过程中什么是合适的,留给了读者想象的空间。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降低了模糊度,译为“autumn is best appreciated in its entirety”,通过肯定的方式来表达原文中因否定而变得模糊的含义,同时以一个抽象词“entirety”来说明欣赏秋就是要以酣畅的态度赏其整体的韵味。虽原文的模糊之美有所减损,但原文深刻的意义得到了很好的传达,抽象词的使用又弥补了译语中的模糊美感。
2.2 文体层面
中国传统美学强调散文要抒情写意,绘形传神(王平 2011:330)。散文语言精练,刻画入微,隽永含蓄,这使得散文读起来似乎具象可感,而散文“体物言志”的体裁特点使这种具象成为一种假象,所有具象可感的事物都只是冰山一角,而意義与情感却被淹没在思绪的海洋中。这给散文翻译带来了“具象性模糊”,即由于作者描绘的具体事物与作者想要传达的情感在译语文化中并没有对应关系,无法引起译语读者的有效联想,从而导致意义缺失。
例3.(南国之秋)比起北国的秋来,正像黄酒之于白干,稀饭之于馍馍,鲈鱼之于大蟹,黄犬之于骆驼。
译:Southern autumn is to Northern autumn what yellow rice wine is to kaoliang wine, congee to steamed buns, perches to crabs, yellow dogs to camel.
此例对比了南方和北方的秋,作者在文章开头便点明北国的秋来得清,静,悲凉,南方的秋来得慢,润,淡,例中几对意象的对比也是基于这几个特点而言。中国人也许知道黄酒清淡甘爽,白酒浓烈馥郁;稀饭湿润清淡,馍馍干硬实在,鲈鱼细嫩柔滑,大蟹肉质厚实;黄犬机灵小巧,骆驼沉稳敦实。这种微妙的感触正是南方的秋天与北方的秋天带给人的不同体验。中国读者能对这些具象事物产生有效的联想,找到这些事物与南北秋日的联系。但译语读者仅凭直译后的意象,几乎不能解析模糊的真实语义,这样的“具象性模糊”经过翻译后很难被理解。
2.3 文化层面
文化带来的模糊性贯穿了修辞层面和文体层面的模糊,与它们共同造成了翻译中模糊性。文化意象由于形成的历史渊源不同,文化系统间不互通的情况在所难免(孙艺风 2004:217)。由于文化系统的不互通,译语读者无法获取解码所需的文化背景,语言符号与其所指之间的对应关系已经被扭曲,甚至完全打破,所以原语读者眼中的“模糊”与目的语读者眼中的“模糊”并不是在同一视角下的。
例4:它可能是一条现代的乌衣巷,家家有自己的一本哀乐帐,一部兴衰史,可是重门叠户,讳莫如深,夕阳影里,野草闲花,燕子低飞,寻觅归家。
译:It may be a modern version of Wu Yi Xiang, a special residential area of nobility in the Jin Dynasty southeast of todays Nanjing, where each family, secluded behind closed doors, has its own covered-up story of joys and sorrows, and rise and decline. When the sun is setting, swallows will fly low over wild flowers and grass on their way to their nests.
此例中涉及了乌衣巷这一文化意象。乌衣巷今位于江苏南京,晋时为名门望族的聚居区,但而后豪门世族衰落,渐渐沦为寻常百姓。同时,《乌衣巷》也是刘禹锡的一首诗,“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斜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所描绘的是世族没落,物是人非的怀古之情。例句中的后半句则是化用了该诗的意象,突出了巷历尽哀乐兴衰后飘逸洒脱的特点。这一例句有深刻的文化背景和文学互文性,由于译语读者对Wu Yi Xiang这个地名无法产生任何文化联想,因而无法理解为什么巷中会有“哀乐账”“兴衰史”,为什么要描绘“夕阳”“野草闲花”和“燕子归家”。在翻译中,译者选择了音译加阐释的译法,补充了乌衣巷的基本背景,对于后半句由古诗化用而来的意象,译者保持了其模糊感,将更广阔的联想空间留给译语读者。
3 散文中“模糊语言”的应对策略
对于模糊語言的翻译,大部分学者都提到过四种策略,即“以模糊译模糊”、“以明晰译模糊”、“以模糊译明晰”、“以明晰译明晰”。然而,翻译是一种创造性的艺术实践,这种创造性决定了对于翻译不能设置固定的条条框框。因为风格和形式的巨大差异,译者在翻译每一个新的文本时,都需要运用主观能动性来确定翻译策略。此外“模糊”和“明晰”本身就是相对概念,在“模糊”和“明晰”之间有无限的可能性。真正的模糊语言翻译实践中,译语由于受到原语意义、原语模糊度、译语规范、译语读者认知储备和文化背景的限制,往往都是游走在“模糊”与“明晰”之间的。
译者首先要从母语读者的角度出发,充分发挥母语读者在认知背景和文化背景上的优势,对原语模糊处进行阐释,有歧义的则穷尽其可能,运用意象的深究其旨意,营造意境的描摹其画面,以此来无限接近原语的所指,以尽可能达到明晰原意的效果。
接下来,译者要做的就是在译语中还原能指与所指的关系,这是一个距离由近及远的过程,距离不能过近,以防过于直白,译语缺乏张力和文趣;不能过远,以防译语读者的认知储备与文化背景不足以解码。这一阶段首要的目标是保证意义得到准确忠实的传达,其次是尽可能还原原文中能指与所指的距离感,保证朦胧美的再造。此时,译者要调整文化视角,从译语读者的角度去考量原文的意义,引(诱)导读者进入创造性的想象之中,从而去完成获取意义的过程(孙艺风 2004:46)。译者需要不断地游走在“模糊”与“明晰”之间,按以上的原则,选择一个最适宜的模糊度。
在同一句话中,每译一处模糊都要做一次距离的选择,在“模糊”与“明晰”的中间选择一个未定点,这样的距离选择将整个篇章连缀起来,模糊与明晰交相呼应,共同构成符合译语规范,充满文学语言模糊美感,且留住散文风格美的译文。
注释
①文中的所有译例均选自张培基著《英译中国现代散文选(一)》,例中黑体为笔者加注。
参考文献
[1]丁国旗,范武邱,毛荣贵.汉英翻译过程中模糊美感的磨蚀——兼谈对中国角逐诺贝尔文学奖的启示[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5,(10):40-44.
[2]毛荣贵.翻译美学[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5.
[3]邵璐.文学中的模糊语言与翻译——以《达·芬奇密码》中英文本比较研究为例[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4]孙艺风.视角阐释文化——文学翻译与翻译理论[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
[5]王平.中国传统译论的美学特色研究[M].杭州: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2011.
作者简介
李丹(1991-),女,汉族,四川成都人,助教,硕士研究生,成都大学外国语学院,研究方向:翻译理论与实践,大学英语教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