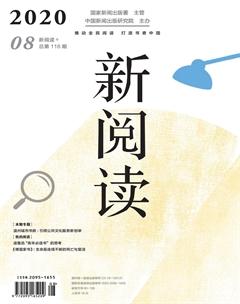淘买旧书 不亦乐乎
范典

对书,有一种不能割舍的情怀。在电子媒介、手机盛行的当下,书似乎成为很多人“断舍离”的对象之一。而我,在家里堆了好几座“书山”,仿佛与书为伍,才能心安。
有一阵子没买旧书,是因为出版社源源不断寄了新书来,家中的书已堆放不下。以至搬家时处理了一部分,有些实在割舍不下,又搬来狭仄的屋内。犹记得老父亲帮我抬起新买的床,将书一本本码放至床下。几大箱书堆在客厅墙边,看电视都碍眼,像是在做地摊生意,懒得收拾,一个个纸箱堆叠着,实在不够雅观。逢上抄煤气、送快递的人,往门口一站,总要问一声:你是卖书的吧?害得我不知怎么回答才好。后来索性就买来简易的书架,叠放起来后,又遭孩子踢碰,架子散了,又买个木制的书架,狠狠拧紧螺丝固定住,这才安下心来。
买旧书的原因其实很简单。喜欢书的人性格比较沉静,不会过多消耗在一些无聊的事情上,有时,触碰到一本旧书,它的体貌特征往往带有前主人的生活印迹。有时是一滴咖啡渍,有时夹有一张旧照片,或者包有书皮、盖有收藏印章和购书签名。
买旧书,便宜是一方面,只需出点零花钱,把人家嘴上叼的烟瘾钱省下来,就可换来几本书,何乐而不为?况且有个好处,它是独一无二的,握在手上有年代感的书,发霉的纸张、与现在格格不入的情怀和语调,甚至排版模式,都让我们有可供研较之处。最重要的,我已然对淘书这样的行为,当作人生中一大乐趣。这是经年积累下来的经验和习惯,换工作易,改习惯难。就像前几年,已80高龄的台湾诗人郑愁予来杭时,我们一同作陪酒席,他酒后豪迈称: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就让江山去改,我们不改!
最早,我在小县城上初中时,夜市有小贩拉来几个纸箱,堆放着旧书盗版书,我很爱淘,仅花10元,可以买到一本厚厚的《红楼梦》,1987年岳麓书社出版的单行本。虽然排版密实,字体如黑蝇,仍聚起眼力,一口气啃完全书。一辈子最勤奋、最不吃力的年纪,应该就数这个阶段了,虽然看书一知半解,属于囫囵吞枣,但至少能一口气读完全书。不像年龄大了,被生活中各种琐事牵连,常读了个开头,注意力便被别的事情给转移了。
地摊上买来的盗版书虽然错字一麻袋,但可以满足一位小城少年的求知欲,知道这世上还有斯坦贝克、杜拉斯这样的作家。到杭州后,2004年前后,住在城西,晚上逛文三路,会发现最后几个摊位竟然在卖旧书,总会买上几本外国文学,不擅讨价还价,但还是硬着头皮左挑右拣,装满整个背包,像蜗牛一样把又沉又厚的书驮回住处。认识的老板中,印象最深的属小刘,江西人,不仅个子长得小,眼睛也很小,很懂做生意,见你多买,常会多赠你一本书,因此客源极好。那条路整改以后,夜市取消,卖书的商贩统一集中到浙江图书馆门前那块空地上,名曰“假日书市”。我因为住得远了,很少光顾,但是偶尔去图书馆借书,在摊前徘徊,就会认出那个熟悉的身影来。几年不见,旧书的身价已然不是当年的地摊价,品相差的都要三五元一本,版次印刷量稀缺的更是要价不菲。我常不敢下手。
书商泛滥,旧书的品质也良莠不齐,很多书商依仗着对爱书人的了解,漫天要价;而且我手边的书读不完。除了出版社寄来的新书,图书馆一次可借十几二十本书,我又何必花一堆钱囤书?
直到有一天,假日书市被图书馆领导一声令下,要求所有商贩统统搬出,留出的那片空地就用作停车场。为此,书商们郁闷不已,多年来集聚起的人气和客流,因为场地的更换,一去不返。他们新搬迁去的杭州二百大收藏品市场,租用的是地下室,除了一些熟客,很少再有人光顾。那个地方倒是离我现在的单位很近,为了照顾他们生意,我这才重新光顾,成了他们的座上宾。
爱书人都在微信群里,买书大户也就几位,每周必买,似乎越买越带劲。买来的书,还要拍照在群里秀一秀,大家品头论足一番,带羡慕的,带怨嗔的,唯有书老板不吭一声,怕得罪了其他没淘到好书的顾客,有时发个红包解解愁。我常一去就买几十本,有时一买就是六七十本,大多都在小刘老板那儿买,他价格公道,别的老板我也不熟,怕被宰。另外,时间也耗不起,常趁单位午休时间跑出去,最多一个半小时淘书。淘完书,早已被霉味熏得喉咙刺痒,急忙忙冲出门去洗手,再返回付钱。
我淘的书,多为外国文学,品相要求好一些,出版社倒不打紧,只要不是盗版书,国内几大有名的出版社我都知道。实在品相太烂的书,我又不想花大价钱,如果低价倒可接受。常要求老板帮我给书套个塑料袋,以防霉菌肆虐。
我也每周会去另一个书店,沈记古旧书店,老板姓沈,所以我叫他老沈,六十多年纪,剃个平头,说话爽气,从不让人讨价还价,但他说的价格都很公道。老沈的可爱之处,在于他既在做书生意,又游离在书之外。你要找什么书,跟他说不管用,他就嘴一撇:自己找,我不知道。太阳好,他就丢几本书在门口木桌暴晒,自己守在玻璃门边,用口哨吹出一支支革命年代的歌曲。那曲调倒很优美,看得出这个老沈,骨子里其实是个文艺工作分子。
我常跟他唠嗑,聊过就熟了。知道他在大企业里待过,也不差钱,见过大场面的人,退休后就算身体康健,也不想像人家那样去坐班,再拿老骨头去挣几块搏命钱。宁可每周给爱书人谋点福利,也给自己挣几块零花钱。他志不在散客,而是那些需要大批量旧书的客人,多用来装修,会所里充门面。所以老沈在良渚那边还有大仓库,轻易不去翻货,人家要的量多,才带去搬。想来,有这么个门脸房,还有个大仓库的老头儿,应该是不愁吃穿的。所以他的随性,久而久之,大家见惯不怪,倒更乐意前去搭讪。他在富阳还有房子专门用来存放稀缺书籍,常年开着空调,托人照看。他说,百年之后就都捐了。
有一次,我在他那儿买书,挑好一摞往他桌上一摆,又调头去挑几本书,他也没正眼看。恰好来了一对年轻男女,像是在展览馆做事的,常买点旧书当赠品,他们抢在我前头结账,我便索性等他们走了再去结。结果发现自己放在桌上的书被他俩顺手买走了,心头窝火,又不好冲老沈发。那可是花了时间从那么多书里挑出的心仪之书,结果就这么被顺走,伤心了好几个小时。想想为了几本旧书,找去人家展览馆毕竟有点迂腐,还是算了。以后再买书,把选好的书必定牢握在手,死也不放。
小刘那儿买书,刷个微信、支付宝都是可以的,但老沈那儿必得是现金。为此,裤兜里不存钱的我,还为了买旧书,临时问同事借钱。以至于好几次,那同事见我中午拎了一袋书,便笑话我:又去买书了,看得完吗?我最好的方法,就是尽量让老板帮我装一只不透明的袋子,这样谁也看不出里头装的是啥,同时也只能在心里默默回应同事:淘书人的心情你们不懂。
因为有了群,我才知道这世上,还有比我更疯狂的买书人。比如宁波的“玉鼎真人”,见他经常出差,一到上海、杭州、南京、苏州等地,除了工作,首要任务就是买旧书。一次至少也有十来本,还到群里晒书,秀一圈,惹大家眼红。另外,也有在杭州电子科技大学任教的肖老师,买的都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书,还有作者签名,也有国外淘的书,版本各异,同一种书,竟然好多个版本,真是让人羡慕嫉妒恨。国外的书品相好,插畫漂亮,但价格同样不菲,那和收书人的财力是密切相关的,有时只能望洋兴叹。
我不太相信,买了书的人一定会读,但买书会上瘾,尤其看着群里别的人发出淘来的书,总觉得该入自己手的书会全部跑去别人手上。就像那书在潜意识中朝你喊:放着这么个便宜你不占,偏给别人占了去!中国人普遍占便宜占惯的心思就会涌了上来,赶忙趁着大家都在午休的时候,骑个车跑过去,早早把好书买了来。这样,算不算是一件挺有责任心的事呢!
作者系浙江省作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