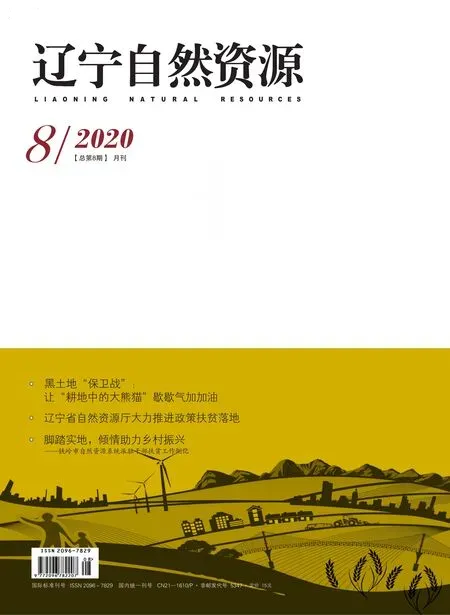农田非粮化进退何难
·利用基本农田发展非粮产业在一些地方普遍存在,主要受经济效益和增收意愿等因素驱动
·一些地方认为必须大幅度、大规模减少粮食播种面积,改种经济作物,才可以增加农民收入
·占了耕地,实际补充的有些成了林草地、有些被抛荒,维持平衡的是数据库里的数据,可能受影响的是粮食产量
在湖南某市,一处山头被分割成两部分,一边是被灌木和草丛覆盖的林地,一边是有机耕道和水池等配套设施的梯土地。旁边的一块石碑上明确写着“土地开发项目,新增耕地19.88公顷”,但梯土地里种植的却是林业作物油茶。
占补平衡,是土地管理法确定的一项耕地保护基本制度,按照“占多少,垦多少”原则,建设占用多少耕地,各地政府就应补充划入多少数量和质量相当的耕地。但在实际落实中,补充的耕地有的实为林地,不适合种植粮食,有的则改种了林业作物。
记者在湖南、贵州、山东、广西等地调研发现,部分地区占耕地补林地,农田用于非粮生产趋势明显,以此促进农村群众增收、壮大村集体经济。
多位受访基层干部担忧,农田非粮化趋势进一步加重可能影响粮食安全,但纠偏又可能损害农民利益,影响政府公信力。
三因素驱动“田种树”
采访中,湖南某地一位村民告诉记者,村里大量劳动力外出务工,种植粮食等农作物无人打理,而种植林业作物不仅无需打理,效益还高得多。以杉树为例,只要经过15年生长期每亩就能有1万多元收益。
“村里基本上都是种杉树、马尾松和柚子。”这位村民说,如果给她一块耕地,她肯定愿意种杉树。
记者调研发现,利用基本农田发展非粮产业的“田种树”现象在多地存在,主要受三方面因素驱动。
一是农民迫切希望改变种粮收入偏低现状。
贵州省都匀市墨冲镇一块连片700亩左右的坝区,以前一直是种植水稻,但由于产值比较少,从2012年开始种植蔬菜。“为了追求更高效益,农民调减了玉米等低效作物的种植,改种高效经济作物。当地的农业产业发展方式也跟着转变,由过去一年两季两收转变为一年三季四收或多收的高效种植模式。”都匀市相关部门负责人说。
二是地方政府期望以此带动脱贫、为农民增收。

记者调研发现,一些地方认为必须大幅度、大规模减少粮食播种面积,改种花卉、板栗、高粱、茶叶、花椒等经济作物,才可以增加农民收入。
贵州省农科院研究员王天生告诉记者,2012年贵州省“一号文件”提出要将农作物播种面积中的粮经比由6∶4调整为4∶6以后,有的地方在落实时,提出了3∶7、2∶8、1∶9的比例,大大压缩粮食播种面积。“一时间,干部带头下乡砍苞谷、毁田坎,改种各类经济作物。”
三是工商资本进入后更加偏好收益稳定的非粮项目。
在山东泰安某村,记者了解到,当地通过合作社将土地流转给工商资本,农田种起了果树,村民和村集体收入都增加了。一位村干部告诉记者,村民获得保底分红、收益分红、工资收入,年人均纯收入突破2万元。村集体通过投资樱桃项目建成纸箱厂提供包装服务,从负债30余万元变成年收入30多万元。
双重“潜规则”难追究
我国《基本农田保护条例》等法规要求,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占用基本农田发展林果业。2018年2月,原国土资源部发布通知要求全面实行永久基本农田特殊保护。
然而多地基层干部向记者坦言,利用基本农田发展非粮产业并不鲜见。“大家都是明着干,不说破。因为这涉及农村群众的饭碗和增收,并未实际追究。”他们表示,这已经成为一种“潜规则”。
“恢复种粮的话,成本高,而且不容易得到老百姓的支持,因为种茶比种粮赚钱多了。”湖南省益阳市安化县自然资源局副局长陶文武说。
在一些地方,利用基本农田发展非粮产业也已经成为推动乡村产业振兴的重要抓手。基层干部担心,这种普遍存在的现象,一旦被纠可能引发农村群众、工商资本、村两委、行政执法部门等之间的矛盾。
耕地占补平衡制度在实际执行中也面临“潜规则”。
湖南某地一位自然资源部门的干部告诉记者,按照占补平衡的相关规定,补充土地只要在开垦成耕地后的几年内种植农业作物,项目就算验收合格。此时数据库里会将其用途更新为“耕地”,并保持数年时间。“至于之后是种树还是抛荒,我们就不管了。”
记者调查了解到,不少验收合格后的“耕地”,有的因为经济效益等因素,改种了经济林、草皮,实际变成“林地”“草地”,有的则因为不适合种植粮食而被抛荒。
湖南某县农业农村局一位副局长表示,当地部分地区存在不同程度擅自改变土地种植类型的情况。目前当地有数千亩这样的地,尤其在一条国道大概10公里沿途,两边种的都是经济作物。抛荒现象也比较普遍。“去年我们统计了一次,全县17个占补平衡的点,其中3个抛荒,水源和配套设施都不好。”他说。
提升耕地精细化管理水平
占了耕地,实际补充的有些成了林草地、有些被抛荒,维持平衡的是数据库里的数据,可能受影响的是粮食产量。
有受访基层干部担心,农田非粮化趋势进一步加重可能影响粮食安全。他们建议,全面、正确、科学地理解粮食生产发展和经济作物生产发展的辩证关系。
根据国家和贵州统计公报数据计算,王天生说,2012年,贵州粮经比为6∶4,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4753元,是全国同期7019元的67.7%;而2019年,贵州粮经比调整到3∶7,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0616元, 是 全 国 同 期16021的66.26%。“同自己比,我们的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加了123%,但与全国比,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占比却降低了1.5个百分点。”
“粮经比并非农民增收的主要矛盾,农业发展水平低才是问题的症结所在。”王天生认为,在守住耕地红线的前提下,种植业结构调整应主要由市场引导。
同时,受访基层干部期待,提升耕地精细化管理水平,根据实际情况对基本农田进行甄别,及时剔除不能满足发展粮食作物需求的土地,明确利用农田发展林果业等的相关要求和条件,变“潜规则”为“明规则”。
“国家和省里以前对新增耕地的产业结构调整是认可的。新增耕地,尤其是旱土的,可以做果园、茶园或种药材。”陶文武说,但今年5月以来连续下了几个文件,要求按照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的线上数据复查新增耕地,不能非粮化。“我们共有682公顷非粮,如果全部核减,压力较大。”
在部分受访基层干部看来,与其将每亩数千元的土地整理资金用于占补平衡的新增耕地开垦,不如将其用在既有耕地的中低产田改造和治理抛荒田上,通过提升质量和单产潜能来保障粮食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