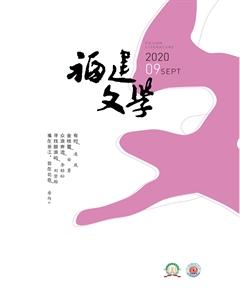动物记
吕永超
铃铛
邻居一脸紧张地说,你家铃铛受伤了,在卯儿沟里死命地叫。父母听这话正是黄昏,顿时,他们眼前全都是黑夜。
铃铛是我家放养的一只本地母山羊。我们那儿家家户户都养山羊。为了便于识别,父亲亲手做了一个铃铛,镌刻上自己的小名两个字,挂在羊的脖子上。山羊每走一步,叮叮当当的脆响就传得很远。母亲赞许地看了父亲一眼,说就叫铃铛吧。父亲嘿嘿一笑,算是应答。自此,老家左邻右舍,都知道我家的母山羊叫铃铛。
铃铛遭遇不幸,一家人不敢耽搁片刻。父亲操起救护绳索,母亲连袖笼也来不及扯下就提起马灯,我打开手电筒,三个人迅速冲出门外,小跑着直奔卯儿沟。
卯儿沟离我家两里多地,山路曲折,高低不平。母亲走得急,碎石踢破了她的大脚趾甲,鲜血直流。母亲席地而坐,眉毛拧成一团又很快舒展开来。她指挥我撕开袖笼布,裹上父亲弄来的止血草,简单地包扎一下。我发现,那白底蓝花的袖笼很快被染红了。父亲接过电筒,塞到母亲手中,劝她等在原地。母亲不耐烦地挥挥手,说我不会拖你们后腿,坚决地站起身,跛着腿继续前行。
卯儿沟是深沟,常年泉水淙淙,这个季节草木肥美,是山羊最爱去的地方。母亲边走边咕哝着责备铃铛,都怀上肚子了,咋就爬山过沟不小心呢?她又自嘲,铃铛是初次怀孕,经验不足,不过有了初一,以后十五就不怕了。父亲不同意母亲的看法,铃铛比人还聪明,这个时候是不会轻易把脚弄伤的。他长叹一口气,十有八九是中了夹子。
我的老家地处丘陵,多野獾野兔。农人闲来无事,就择地放夹子,总有些小动物中埋伏,成了美餐。
铃铛诚如父亲所言,后腿被隐藏在草丛中的铁夹夹住,动弹不得。铃铛见了我们,高兴地甩着尾巴,亲切地哞哞叫唤,惊起林中宿鸟噗噜噜地乱飞。我把电筒架在矮树枝丫上,定光照射铁夹的位置,腾出的手提着马灯,照着父亲去起夹子。母亲抱住铃铛头部,爱怜地抚摩安慰。
夹子锯齿扎进铃铛肌肉中。父亲咬牙用力去掰。我听到弹簧叽叽地反抗。夹口一点点扩大,铃铛后腿因疼痛而轻微地颤抖。铁夹终于从铃铛后腿移开。它欣喜地从母亲怀中挣脱,急切地站立,一个趔趄,撞到父亲的左手。只听父亲哎哟一声,铁夹放过了羊腿却咬住了他的大拇指。母亲憋足劲,满脸通红地拉开铁夹。就这么不到一分钟的时间,父亲大拇指乌黑发紫。他朝大拇指吐了口唾沫揉了揉、摔了摔,才舒了口粗气。母亲白了父亲一眼,开着玩笑活跃气氛,说秤不离砣,公不离婆,一个伤手一个伤脚,老天真公平。父亲顾左右而言他,猫头鹰开口不是好事。母亲侧耳细听,说你耳朵泛潮,哪有貓头鹰一说?我听出父亲的弦外之意,吃吃而笑。接着父亲哈哈大笑。母亲如梦初醒,随手扯起一把芒草,高高地举起又轻轻地落在父亲的背上。
父亲简单地包扎铃铛后,就嘿一声,架在背上背回家,涂上正红花油,圈养。在一个月光如水的晚上,脚未痊愈的铃铛,早产了。它很痛苦,眼睛几乎要从眼眶里凸出来,鼻翼一张一翕,急促地喘息着。它一下生了三只,但只有一只母羊羔存活。在父母的惋惜中,小羊羔跌撞几下爬了起来,钻到铃铛肚皮底下寻奶吃。铃铛快速地舔干羊羔湿漉漉的身子,这身子立即变白了,像卯儿沟山顶上飘动的白云。
我惊异羊羔的生存本能,在它娘肚子里就完成了从爬行到站立行走的历程。母亲对铃铛格外照顾,给它喝汤,汤里面放盐,羊奶更丰盈。第二天,母亲边喂精料,边说,铃铛,你女儿是在有月亮的晚上生的,叫月月好吗?铃铛眨巴眨巴眼睛,得意地扭动脖子,默认了。
7、8月农忙,父母全部心思几乎都放在稻田上,经常忽略铃铛。铃铛当了妈妈,食量明显加大。它要喂养月月,就毫不客气地撞开圈门,自己去觅食。嫩草化作甜蜜的乳汁,滋养得月月一天一个样。父母乐滋滋地盘算,待到秋天,月月一定能换来好价钱。
可是,在一天凌晨,全家人被一声声惨叫惊醒了。
父亲冲进羊圈,只见铃铛伏地瞪眼,口吐白沫,全身抽搐。身下,羊羔还在寻找乳头。铃铛中毒了,不知道到底吃了什么。父亲把它抱进堂屋,它却拼命地往门外刨着抓着,还淌下泪水。
“铃铛……”它分明听见我母亲的叫唤,也听懂了,泪眼直勾勾地看着,瞅得我母亲泪珠一颗颗,一步三回头地去请兽医。
父亲端来肥皂水,他和我合力撬开铃铛的嘴巴,希望通过灌肥皂水催生呕吐,减轻它的中毒症状。
但是,铃铛坚决不从。
父亲示意我去抱来月月。铃铛立即不反抗了,深情地看着月月,用尽最后的力气,长哞一声,没等来兽医,头就歪倒在一边。
天亮了,母亲用最难听的话骂街。月月却围着铃铛僵直的躯体,一会儿细细地叫着,一会儿去拱它的腹部……
父亲沉重地走到院中枣树下,挥镐挖了一个坑,把铃铛放进里面,掩上黄土,伤感地说,枣树有铃铛做伴,明年开的花更香,结的果更大更甜。
整整一天,母亲没有下地干活,守着月月,尝试着用多种办法喂养它。
月月奇迹般地活了下来。
鸠鸠
夏日偶患风寒,头昏脑涨,去药店买药,心情不好。刚进门,有鸟语传来,“你好,你好!”“欢迎光临,欢迎光临!”只见收银台背后的发财树中吊挂鸟笼,一只八哥头顶一撮毛,全身漆黑,泛着金属光泽,双爪紧抓栖木,黄眼球黑眼珠,骨碌碌地转。讨巧的八哥,让我心灵愉悦。
八哥是中国南方常见的一种鸟类。《诗经·召南·鹊巢》三章都以鸠居鹊巢起兴,用平实语言描写了婚礼过程,同时也有了成语“鸠占鹊巢”。个中鸠者,不是斑鸠,实为八哥。这也是本人读到的最早记载八哥的文本。八哥自古是一种学嘴学舌的鸟,《燕京杂记》说:“街上闲行者有臂鹰者,有笼百舌者,又有持小竿系一小鸟使其上者,游手无事,出入必携。”“笼百舌者”中鹩哥为上,八哥次之。
我是养过八哥的。当年出版社催得急,我没日没夜地撰写完饮食文化散文集《舌尖上的美味》后,人已虚脱,一连几天睡在床上,迷迷糊糊不见清醒。侄儿得知信息,特地从老家赶来,捎带一篮土鸡蛋和一只雏鸟看我。我眼光放亮,精神爽利,百病全无。
下床第一件事情,就是逗着这只雏鸟。这家伙长着稀拉的绒毛,从头到尾都是通红的嫩肉。我一看就知道是出生不久的八哥,两边嘴角上尖长形黄斑,是它典型的印记。小时候掏鸟窝,我见过。侄子微笑点头。我很得意,就把小八哥放在手心。这鸟虽然不能站立,却懂得人对它疼爱,在手掌上拱来拱去,痒痒的,却不能一握。小八哥自若地瞪大眼睛,看天看地,全然不知道什么叫危险。
我问侄子,记不记得我带他捕捉八哥的事情。侄子说童年往事难忘。他用浑厚的男低音复述着那个久远的故事:我用系着绳子的矮筷撑起半边箩盖,里面放点碎米,搂抱他躲在窗下,手拉细绳,屏住呼吸,观察窗外。贪吃的八哥见到食物,叽叽喳喳飞过来,一步一步地跳进箩盖里,又一点一点地使劲啄米。看准时期,拉绳筷子倒,八哥成了箩中之物……一晃20多年过去了,当年看着活蹦乱跳的八哥,咯咯的笑声如黄莺出谷般清亮的侄子,如今长成用呵呵一笑来表达分寸的男子汉。他说,大伯,就叫它鸠鸠吧,您曾告诉我,八哥原本叫鸠。他记得我跟他讲过《诗经·召南·鹊巢》。我满足地朝他厚实的胸脯送上一记轻拳。
鸠鸠不能不吃东西。我忘记了怎么样喂养它,就使劲抠开它的小嘴,把碎菜塞进其中。它并不买账,一摔嘴,菜就出来了。侄子嘿嘿笑着说,大伯,你忘记了。他接过鸠鸠,用指甲轻轻磕碰它的喙,它闻声把嘴巴张得大大的,同时发出“咯咯咯咯”的叫声。我忽然明白,侄子说我忘记的真正内涵,不单单指如何喂养小鸟,而是暗示我遗忘了童年的情趣。不得不承认,我被灯红酒绿的都市钝化了。我感激地拍了拍侄子的肩膀,是不是触摸牧笛横吹坐牛背的童年?
鸠鸠长得真快,几乎一天一个样子,不断有黑羽毛从身上冒出來,不久出落成一只年轻的鸠鸠了。因为还不会飞,就在笼外生活。它像初学走路的孩子,不知深浅地东扑西跳,花瓶被它弄翻在地碎成八瓣,短暂停顿后它依然故我。我并不恼怒。我对它有了感情,只要吹一声口哨,它就朝我蹦来。再长大些,在蹦跳中还来一两次展翅。我十分欢喜。在我精神虚脱的时候,侄子送来了一个小生命,启动了人之心脉,催生了心之绿叶,感觉体内元气在一点点恢复。我感谢鸠鸠!
鸠鸠会飞了,更加调皮可爱。家人建议,买只鸟笼圈养。我没有同意。我掐算着时间,在选好的一个日子里,上公园放飞。八哥的世界应该是天空,不是笼子。天空是八哥的舞台,大地是它的故乡。在饲养过渡时期,我就着阳台用竹篓给它搭建一个简易的栖身之地。它住得很惬意,在栖木上憩立、踱步、喝水、吃食、拭喙、磨爪、跳跃、攀缘笼壁,心安理得。它不挑食,米粒、谷子、玉米、花生、黄豆、蔬菜、蛋壳、碎肉以及鸟饲料都喜欢,来者不拒。它很爱清洁,在卫生间浴盆里放上清水,它会跳进其中,兴高采烈地在水中哗啦啦地抖擞,然后湿淋淋地回到笼子里,用嘴喙精心梳理打扮。它还喜欢鸣啼,每天清晨都会婉转地欢叫,每一个段落都从三声“叽——叽——叽”开始,然后进入主题,平缓时如山间的小溪,高亢时似冲天的号角,常常引人心中荡漾,共振共鸣。它能够学嘴学舌,但比人诚实,绝不会添油加醋、搬弄是非。
在有限的时期内,我不停地逗弄鸠鸠。它总是听话地飞来,落在我的手上、肩上或头上,兴之所至,还啄我。我感到轻轻的痛,很快乐。
可是有天傍晚,我下班开门回家,竟然没有鸠鸠跳过来迎接,屋内静静的。猜想,它是不是耐不住寂寞,从窗户飞走了?可是铝合金窗门紧闭。我冲进卫生间,八哥淹死在浴盆中。买回的鲫鱼在水底摆尾,鸠鸠僵硬地浮在水面上。
侄子从我这里取道到上海上班,中间来了一次电话,我从他焦灼的嗓音中听出了大学毕业后谋事的艰辛。又过去了几个月还是不闻音信,而鸠鸠的事也过去很久。我却常常想起鸠鸠,想起与鸠鸠相连的人……
风寒痊愈,在小区散步,一只八哥在树上唱着好听的歌。从外形看,这只八哥与鸠鸠并无二致。我想,或许它就是鸠鸠的化身?就试着吹了几声口哨,它侧头看了我一眼,朝我啼了几声,展翅飞远了。
责任编辑陈美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