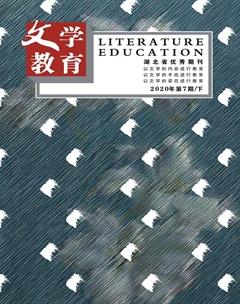金曾豪散文与“江南现象”研究
陶开颜 查能
内容摘要:金曾豪是常熟籍重要散文作家。其作品不僅为我们展示了个体生活的现实,也展现了江南地域、江南文化对作家的深刻影响。本文将从地理、个人、生活的多元维度,发掘金曾豪首部散文集《蓝调江南》与区域文化“江南现象”之间的必然关联与文化价值。
关键词:金曾豪 《蓝调江南》 江南现象
金曾豪诞生于常熟练塘的一个中医世家,温雅的家风和秀美的风物,使金曾豪养成了沉默敦厚、勤学善思的性情,而曲折的人生造就了他坚韧不屈的情操。他的生平和为人,潜移默化的牵引着他的行文风向。作为著名常熟籍作家,金曾豪以其纯澈灵性的儿童小说和清俊秀丽的散文作品在文学界享有盛誉。此后他一直致力于儿童文学的倾心创作,同时以散文为载体,对江南风土人文全力弘扬,总计出版了40多部专著。
然而,关于区域文化和相关作家的研究,理论雏形提出虽早,但是成体系的建树很少。大多研究者都埋头于主流文化的热门作家群体,对其反复咀嚼,却对相对冷门的区域及作家缺乏关注。金曾豪的散文也有着相似的处境——由于过于耀眼的儿童文学光环,其散文被迫处于边缘地位,与之相关的研究甚少。实则,其散文风格鲜明且独树一帜,气质清新秀美,真实生动地重演生活,富有童真、童趣,极具知识、文学色彩,诗性审美价值也极高。因而本文将从研究金曾豪散文的薄弱点入手,以区域文化为大视域,从地理、个人、生活的多元维度,发掘 “江南现象”对金曾豪首部散文集《蓝调江南》的生成意义,并以此补全金曾豪作品研究的谱系。
一.地理的江南
特定的环境匹配着特定的创作建构,这是一种无从造假的标识。作家身处的环境极大概率呈现在他的文学作品中,形成难以磨灭的地理印记。
(一)小镇轻波——金曾豪散文的“水现场”
车前子曾在《江南话本》中这样描述:“清水淡墨,它被描在暗黄的毛边纸上,一块云、一团烟,云而已、烟而已。”[1]金曾豪自小生活在阳澄湖畔的常熟练塘,作为典型的江南小镇,练塘无疑具有这些清浅幽远的江南意味。金曾豪也通过截取美景,渲染出江南风貌,用这些灵动别致的开幕和转场,使行文流畅毫无斧凿痕迹。
金曾豪极爱也极善写水,“练塘是一条白练般飘逸的河。河穿过镇子,镇子便随了河的名。水乡小镇常常是这样得名的”[4];(《呼鸭》)“水乡,河浜如网,淌淌船很忙,很快活”[4];“少女捉住一朵菱头,提起来,一把红菱灿然出水。若有斜阳晚霞映照,红玛瑙似的更好看。淋漓的水也成胭脂色了”[4];“就有一两只红蜻蜓飞起来,在水面上盘旋”[4];“江南的城镇除了街巷,总还有一个水系网络着。常熟城里有好几处‘三步两条桥,走三步路就能踩到两条桥,可见河之多”[4](《网船》)湿润的气候,丰沛的雨水,造就了密布的河网,水与江南密不可分。依水而建的住宅店铺,略带腥味的网船,繁忙的商船,藻荇间的土婆鱼,采红菱的少女,盘旋的蜻蜓……氤氲的水汽,夹杂着人声鸭鸣扑面而来。这零星的几点水色却晕出了生活人气,晕出了澄澈风情。
江南的物与人都被水的现场裹挟,诸如那些刺透历史迷障,具有不竭源流的经典江南意象——《采莲曲》中荷叶罗裙、芙蓉如面的采莲少女,《望海潮》里“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的乡邦风土,《菩萨蛮》中“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的悠然姿态。水给予江南一种仿佛芦花深处飘渺而来,揉和神话想象、诗性智慧和审美思维的终极气质。
(二)笔尖微澜——金曾豪散文的“水化”情结
在金曾豪的散文中,水作为一种意象产物,却又从具象的形体中逸散开来,以情感、气质之姿浸润笔端,使行文风格也似潺潺流水,细腻平和,抚慰人心。
《八音刀》洗头的疲倦感、理发时“洗心革面”的愉悦感、洗发皂“五洲固本”的气味,一切都是平凡生活的安逸与静谧,老派的亲切,朴素和庸常的诗意。《一头有名字的羊》放羊、割草是享受大自然的气息,闻着清香给人踏实之感。《家里的灶头》一家人在灶头边忙活感受人世间的秩序……一派祥和与安逸,娓娓道来,作者也罢,散文中的人也罢,已是流水入海。水深无声,人情也如此。
诚然,水“温柔时可以像女人的泪,刚强时可以冲破坚固的堤”[2],金曾豪散文平静之中,却有着流向心灵的力量。或于《八音刀》永生为去世的父亲剃最后一个头中感慨岁月流逝,或于《一头有名字的羊》荣小弟不慎落水、白雪生离死别中见证“我”的成长,或于《家里的灶头》想起过世母亲往昔叫唤吃饭声音时的唏嘘不已……淡淡的叙述中透露出藕丝连连的情谊,江南的人情杂糅在琐碎的生活片段中,似恬静的水面上仍有波澜动荡,不是直涌向心头,而是圈圈泛起,轻柔,却足以压迫一时半刻。
二.个人的江南
莫言在《每一个写作者都离不开乡土》中说到“作家创作的故乡情结是难以磨灭的,很多作家都是自觉地运用乡土文学,全世界的作家几乎无一例外。作家创作到一定层次以后,必然会开发利用他的故乡,他的童年,即便写着与故乡无关的作品也会在其中发现故乡的影子。”[3]童年作为最初的生命体验,金曾豪对其充分挖掘,使记忆拥有了深发和外化的多重可能。
(一)故园乐土——金曾豪散文的儿童视角
金曾豪童年与江南小镇的零距离接触,是他散文创作的灵感源泉。真实的场景、真实的人物、真实的故事,所有的真实都在真诚的笔下展现出来,理所当然地会给人一种真挚的亲切感,卸下防备,欣然接纳。用孩童的视角,亲身经历在江南小镇发生的故事,于日常生活中感受人来人往的善意,享受柔软又宁静的氛围,不追不赶地阅读完整本书。
以自身为线索展开的长幼、同辈之间的人情网络最是真挚动情。父亲对于少年金曾豪有着深刻的影响。正如《树德堂》里所写的,他同病人侃侃而谈,通察病理又善解人意。他的儒雅风度“和中药店的情调是相一致的。”[4]父亲常带“我”来小坐片刻,陶冶情操、熟悉草药,耐心告诫“我”好好练字,传承家族的文气和医术。
母亲善于讲故事也勤于家务,是一个朴实善良的劳动妇女。她和“我”的互动都极为温馨,具有浓郁的烟火气。一家人在母亲地带动下围绕着“家里的灶头”热火朝天的忙活起来,巧手的母亲用简易的食材烹制出味美的菜肴。而在《萤火虫,夜夜红》中,母亲用夸张的想象将丰富的人生经历编织成趣味纷呈的故事,给予了“我”最初的文学启蒙。
孩提王国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度,儿童游戏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发明。金曾豪笔下的同辈友谊是这样的纯粹。《呼鸭》中男孩子与鸭子上天入、地枪林弹、怪叫连天、水花四溅的激烈战争,《萤火虫,夜夜红》摸着黑的“转转”经历,《电影船》斗智斗勇、“忍辱负重”的潜伏……这些游戏活动并非出于什么功利的目的,而是任凭天性,有感而为,饱含着旺盛的生命活力和无限的好奇与创造。
这些文章通过孩童的视角重新梳理了往昔细碎的日常,折射出一种纯粹且真实的老派的岁月静好,让人不禁被这个柔软清丽、人情温婉的江南小镇俘获。
(二)得失长歌——儿童视角下的成人思考
江南文化是感性的,它能发掘苦难掩埋的诗意。金曾豪是敏感的,他能洞察主流裹挟下的私语。文化和作家一拍即合,淡淡的忧愁成了文学最蕴藉的底色。
社会的动荡,人性的破败并没有粉碎金曾豪纯净的童心和对生活的挚爱,他将对逝去故乡的无限眷恋与怜惜付诸笔端,以童年时代的自己为锚点,用孩童的视角勾连起那个江南小镇的风貌况味,行云流水的文字背后是一种穿透时空的在场感。他的作品洋溢着内在的愉悦和感恩,一丝不苟地清点着故乡给予自己的每一份馈赠,每一丝感动。如茶馆中“可以清心也”汉字独特妙处的馈赠;评弹给予的文学艺术方面的教益;中药材具备的文化魅力;灶头带来的美食与家人互动的温馨;月亮下的故事会……
“童年推到了一堵堵文字的高墙出来,那些渐渐消逝的事物被张开的手臂拦住。”[1]悠远的回忆能让快乐褪色成忧伤,热闹的老茶馆,清澈的河流,八音刀的绝技,灶火,老树,白雪,沈兴,父亲,母亲都成了淡淡的影子,再见不到。
贯彻在金曾豪行文之中的欢喜和忧伤,紧紧的贴合着“得到”和“失去”,就好比那理发店里的那一幅西洋风景画,“得到”它的时候,年少的金曾豪是何其地感动。可终究是“失去”了,“那幅风景画已经不在了,镜框里换了伟人的照片。”[4]在特定的岁月里,生活和人性失去了声音,逝去注定无法挽回,但它已经以更美好的形式被永久铭记,“找不到这幅画可能不是坏事,真找到了,说不定反而会破坏了珍藏在我记忆中的美丽。毕竟,用现在的眼光看,那也许只是一幅印刷粗糙的风景画而已。”[4]金曾豪也许就是怀着这样忧郁而庆幸的复杂心情,去书写那个失落的江南吧。
三.生活的江南
温养在江南自由温润的文化风气里,无论是贩夫走卒还是知识分子,都拥有健全的人格精神和乐观的生活态度,他们所参与创造的风俗无疑是汪曾祺口中“生活的抒情诗”。而金曾豪也致力于去描绘这些可亲可敬的小镇居民,这种淳朴健康的民俗风情。
(一)活色生香——金曾豪散文中的风俗现场
茶馆开的最早也总是最热闹,茶客大多是熟客,老年人居多,常携鸟带狗,谈天说地—— “上至国际风云军国大事,下至家长里短鸡毛蒜皮”,“若是发生家庭矛盾、邻里纠纷,当事人往往会约定到某茶馆‘吃讲茶。”[4]茶客们多厚道热忱,正义感十足地主持公道,又能侃能说,就像几个老人议论瞎子阿炳,离奇灵活的开头创作也为生活润色不少。又比如说书的男女先生。“远远不只在讲故事,他们把难叙之事娓娓道来,把难状之物呈之目前,把难言之情诉出微妙,看似随口而出,其实句句都是有心。”[4](《茶馆》)传神生动的说书,温文尔雅的先生,聚精会神的听众,偷听的孩子还在和蚊子战斗。事后还会有懂行的听众和评弹艺人交流切磋,共同传作。这小小的一个剖面就把小镇人们日常时光的怡然自得,乡间邻里的亲切热络,生活观念的乐观积极写得极真极醇。
毕竟民以食为天,小镇的吃食自然是极丰富又极考究的。金曾豪打小又是极熟络,对小镇的美食地图了如指掌。铺开来讲,茶馆里的排骨面;书场上西瓜子、南瓜子、花生米之类的消闲小吃;曾舅母的鸭蛋;巷口的臭豆腐干、爆米花、麦芽糖、蛳螺;自家灶上的饭粢糕,大锅上的一品锅、螃蜞豆腐……江南人既勤快又手巧,也乐于琢磨吃的花色,外面的零食能点嘴,家里的菜色又稳够自足,自然便宜贪嘴的大人孩子。金曾豪是极懂行的:“‘喊面要讲清楚加什么面浇,还有是否免青,是否紧汤什么的。‘免青就是免放葱花。那时我常想,‘免青的人真憨,那洒了葱花的汤面有多香啊!”[4](《茶馆》)即使只是小生意,茶馆也很是上心厚道。面怕冷,故放在篮子由小伙计提着跑,即使是清汤寡水被葱花吊了味以后也是香极,更别说让狗馋的不能自已的排骨面。而极香又极臭的臭豆腐干,“卖家就把炸成金黄色的臭豆腐干放在一片绿色的通心叶上递给你。锅边小几上备有红色的辣酱,任你去抹。翠绿、金黄、鲜红组合在一起,悦目得很。花几分钱可获得味觉、嗅觉、视觉三方面的愉悦。”[4](《巷口小吃》)这写法,俨然是在刻画一件不得了的艺术品,而吞吞吐吐、神神秘秘的店家也俨然一副高人做派,让人愈发好奇。这些立体式的吃喝玩赏倒也将江南人满地鸡毛里娱乐精神发挥到了极致。
金曾豪所描绘的这个粗看有些土气,实际却满是亲昵人情的“土熟”風俗现场,将老派江南骨子里的温情表现得淋漓尽致。
(二)生活歌者——金曾豪散文中的可爱小人物
创造并享受着这种美好风俗的人们,是金曾豪散文着力更深的生活主人公。他们在并不富裕的物质条件下,仍秉持热爱之心,是罗曼罗兰笔下当之无愧的英雄。
比如说《八音刀》里三位各具特色的理发师:“刀功了得,传说年轻时能用剃刀劈死飞过的苍蝇”[4]的沈兴;擅长“紧拉慢唱”剪子功夫的雄生,被喜欢掏耳朵的顾客青睐的永生。除了本职理发,理发师可以说是身兼数职、多才多艺,有什么困难求助,一支烟的事儿。此外沈兴的心宽体胖,爱开玩笑,雄生的听书黄酒,他们恪守职业道德,他们也享受生活,这群匠人的形象栩栩如生。推销梨膏糖的小贩“小热昏”总唱着那首即兴的开场曲《吃不吃歌》,总能通过一些有趣幽默或刺激或通俗的故事吸引人们,善于演绎神话传说的年轻理发师前前老可以把孩子唬得一愣一愣的。金生老汉是个养牛老手,最神的是他能从牛胃里取出异物。老汉养的独角牛忍受痛苦保护小主人,而老汉则保护刺伤他眼睛的独角牛。牛与人结下深深羁绊,老汉牵独角牛,两个老伙计晃晃悠悠的走过桥。这些人们构成了小镇最主要的故事,以他们坚韧乐观的性格讴歌着生活。
生活的歌唱者不仅仅是他们,书里的歌者是这些可爱可亲可敬的小人物,而书外的歌者则是金曾豪。他极大的削弱了现实的矛盾,丝毫没有旧时代的陈旧气息,他深知他的文字并非对于生活的严刑拷打,致力于发掘一些琐碎的日常,去写茶客闲谈,先生说书,少年少女的呼鸭,船上的电影,巷口小吃的制作销售……从这些热气扑腾、有滋有味的民俗现场,追寻其背后的美好人性,文化不灭的“童心”。
结语:但如今江南文学却深陷失语的四重窘境:基于近代文化格局西方哲学理论的大框架,中华文化的生态空间遭到了极大的挤压,身为非主流文化且拒绝政治发声的江南文化更是受到了孤立。同时狭隘化的自身创作,较低的文化产能,以及最为关键的被迫同质化的现实土壤,都使江南文化处于近乎绝境的话语边缘。
而金曾豪试图用一种语言,一种文字去复活江南,使具有地域美,个人情,生活真的唯美江南从失语的泥泞中挣脱。他通过对江南地域最为真挚纯净的描摹,用清醒而又清晰,精致而又谨慎的笔调,以无以匹敌的生命意识,将江南的物与人紧密的羁系起来,使得惯常的私人庭院式的物质江南跃迁到精神故里式的灵魂江南。
远离政治云烟,摒弃现实喧嚣,以琐碎描绘真人间,用日常讴歌真性情。金曾豪笔下的老派江南,有草间的萤火,有船上的电影,有巷口的小吃,有远去的呼声,有棚下的白羊……蒙着薄薄微雨,并不明媚,但已足够温馨。在钢筋混凝土的寂寞现实蹒跚迁徙满身尘埃,蓦地看见这样一个熟悉的江南,怎能不怅然而涕下?
参考文献
[1]车前子.江南话本[M].广州:花城出版社.2002.12
[2]錢歌川.巴山夜雨[A].//俞元桂,姚春树,汪文顶,等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卷二.1990:215
[3]莫言.每一个写作者都离不开乡土[N].检察日报.2007-4-27(BI)
[4]金曾豪.蓝调江南[M].苏州:古吴轩出版社,2003.
[5]樊均武.水性江南:近现代江南散文的观照视角与审美特质[D].浙江师范大学,2011.
[6]周红莉.江南意象的记忆与阐释——论90年代后江南散文[J].文艺争鸣,2006(6).
常熟理工学院大学生创新项目课题论文。项目名称:《金曾豪散文与“江南现象”研究》;编号:XJDC2019183;参与人:陶开颜,查能;导师:周红莉,常熟理工学院,教授。
(作者介绍:陶开颜,常熟理工学院汉语言师范专业学生;查能,常熟理工学院汉语言师范专业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