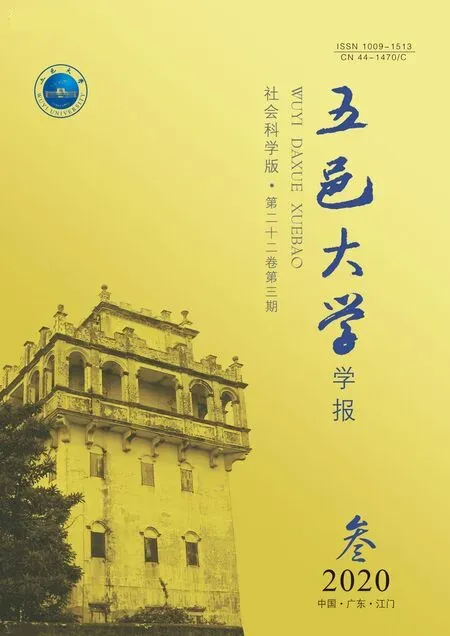试论饶宗颐的道教研究
邵小龙
(上海大学 文学院,上海 200444)
2018年2月6日,世纪老人饶宗颐在香港辞世,告别了他一生挚爱的中国文化。饶宗颐1917年8月出生于广东潮安。饶公的大部分学术成果,在他生前已汇集于《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①,这部煌煌巨著也就成为他留下的重要学术遗产。饶宇颐的治学范围异常广阔,十四卷的《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便是明证,在《二十世纪学术文集》第五卷宗教学中,其中的《道教探原》和《老子想尔注校证》,则是饶先生道教研究的集中反映。关于饶宗颐先生的《老子想尔注校证》,施舟人(Kristofer M.Schipper)曾撰文有所论述[1],但收入《道教探原》的其他有关道教的论著,尚有进一步讨论的空间。
一、对出土道教文献的研究
1952年,饶宗颐开始在香港大学任教。两年后在香港为学生讲授《老子》《庄子》等,前后持续三年[2],这算是饶宗颐从事道教研究的开端。后来饶宗颐也指出,自己“最先和敦煌学结缘是因为从事《道德经》校勘的工作”[3]。
1955年,饶宗颐的《吴建衡二年索紞写本道德经残卷考证(兼论河上公本源流)》,刊载于《东方文化》。1956年4月,他的《老子想尔注校笺》,又在方继仁的资助下,在香港出版。
当时藏于大英博物馆的《老子想尔注》,由斯坦因(Marc Aurel Stein)于1907年携至英国,编号为S.6825,这件写本首残尾全,正面尾题为“老子道经上 想尔”。中国学者向达和王重民,在20世纪30年代前往欧洲调查敦煌吐鲁番文书,对此写本都有所关注。
1939年,向达发表了《伦敦所藏敦煌卷子经眼目录》,其中将S.6825著录为《老子道经》(580行)。1957年,这篇目录又被收入向达的《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一书中。同年,英国汉学家翟理斯(Herbert Allen Giles)之子翟林奈(Lionel Giles,一译小翟理斯),在其去世的前一年,出版了《英伦博物馆汉文敦煌卷子收藏目录》(DescriptiveCatalogueoftheChineseManuscriptsfromTunhuangintheBritishMuseum),翟林奈将S.6825著录为“老子道经上”,并对其作者和“想尔”二字有所关注。[4]1958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王重民的《敦煌古籍叙录》,但结合王重民为S.6825所作叙录标注的日期,就可知在上世纪30年代,主要在巴黎调查拍摄敦煌文书的王重民,对这件收藏在伦敦的敦煌文书也较为关注。他在1939年4月18日所写的叙录中,依旧将S.6825命名为“老子道德经 想尔注”[5]1962年,王重民等参与的《敦煌遗书总目索引》,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其中刘铭恕撰写的《斯坦因劫经录》,进而将S.6825著录为“老子道经 想尔注”,所附小字说明称:“已经香港某氏影印问世”[6]249。
综上所论,饶宗颐不拘泥于S.6825的尾题,率先将其定名为“老子想尔注”,并对其作者加以详细的考证,还在方继仁的资助下,首次将S.6825的照片,以出版物的形式公之于众。《老子想尔注校笺》出版以后,则进一步推动了其他学者对此文献的研究。
1956年8月,饶宗颐与罗香林出席了在巴黎举办的第九次青年中国学者会议[7]。首次到访法国的饶宗颐,将出版不久的《老子想尔注校笺》持赠法国学者,在法国中国学界引起强烈反响[8]43。1965年末,饶宗颐受戴密微(Paul Demiéville)和法国国家科学研究院之邀,再次前往法国进行学术研究,得以亲检由伯希和(Paul Polliot)带到巴黎的敦煌文书。此后,饶宗颐分别于1976年和1978至1979年,前往法国远东学院和法国高等研究院,饱览法国国家图书馆所藏的敦煌文书。
在此基础上,饶宗颐在1979年完成《论敦煌残本〈登真隐诀〉(P.2732)》,刊登于是年出版的《敦煌学》第四辑。国内外学者伯希和、王重民等,对P.2732就早有涉猎。在伯希和整理的巴黎所藏敦煌文书目录(CataloguedelaCollectionPelliot,FondsdasManuscritsChinoisdeTonen-huang)中,对P.2732有著录,这份目录由罗福苌将部分译为中文,先后于1923年和1932年发表。罗福苌将P.2732的著录文字译为:“道经注,字佳。背为《入理缘门论》一卷,末署缘观论。贞元十年,甘州大宁寺落藩僧怀生以朱笔校改。”[9]648一年后,陆翔所译的伯希和目录,也刊行于《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第八卷第一号上。陆翔的译文为:“华文。一面道经有注,字佳。似为七世纪时物。对于道家律令成立史实,此书殊为重要,中间有藏文一行。他面为《入理缘门论》一卷,末为《缘观论》。此抄本由甘州大宁寺落藩僧怀生于贞元十年(七九四甲戌)以朱笔校勘”[9]737。
时任北平图书馆馆长的袁同礼,基于王重民和向达拍摄的敦煌文书照片,在1940年发表了《国立北平图书馆现藏海外敦煌遗集照片总目》,其中称P.2732为道经五页,小字注文又言:“此系答问语。”[9]856建国后,王重民在《伯希和劫经录》中,则将P.2732著录为“残道经”,并有小注云:“有注,阐呼吸导引之术。背为‘入理缘门’一卷,后题作‘缘观论’,末有贞元十年题字”[6]271。
P.2732首尾俱残,并无题名,因此判断其内容存在一定的难度。饶宗颐则依据《道藏》,将P.2732正面的内容考定为陶弘景《登真隐诀》残文,并进而指出写本第二纸补入的两行吐蕃文与吐蕃内相尚婢婢有关,至晚于贞元十年(794)已流入蕃僧手中。饶宗颐进而将P.2732写本与《真诰》、《登真隐诀》及《三洞珠囊》相比勘,指出敦煌写本虽在唐以前,但也存在讹误及脱文。又将敦煌写本与《云笈七签》、《洞真西王母宝神起居经》及《上清三真旨要玉诀》的敦煌写本(P.2576v)和传世本相对照,发现与传世的道经相比,写本内多保留六朝以来的字体,其中所录韵语,必注出用韵之数,且保留的陶弘景原注更为详细;进而推测《道藏》中的《洞真西王母宝神起居经》与《太上西王母宝神起居玉经》存在联系,认为《洞真西王母宝神起居经》的时代,可能在《登真隐诀》和《真诰》之前。此外,饶宗颐还结合《紫文行事诀》(P.2751)和《灵宝真一五称经》(P.2440)的注文,讨论了道经中的“合本子注”。饶宗颐对P.2732第二纸正面的内容加以校录,附于文后,以便读者对此残卷有所了解。
一般研究者如果事先不能确定写本的内容,大略借助写本中的中君、杨书、小君等词汇,估计可以断定其与茅山上清之关系,但若非对《道藏》足够熟稔,便不能将此出土文献与《云集七签》《三洞珠囊》及其他敦煌道教文书相互参证,多有发明。此文体现了饶先生对原卷的充分利用和对道典的熟练把握,唯所录卷背朱笔题记略显不辞②,与法国学者所录的题记存在出入。文中又称“左玄右玄祝辞六见”云云[10],疑“六见”当作“又见”,“六”“又”二字,或形近而讹。

提要中除考辨写本的作者、钞者、钞写年代和在敦煌文书中的互见情况外,还结合文字、书法、目录版本校勘、职官、制度、地理、宗教等方面的知识,又利用《道藏》、碑刻、简帛、墓志等材料,对写本的内容加以多方面的阐发,廓清了许多重要的历史问题。
以上所列道书,玄宗御注《道德经》收入《道藏》洞神部,《度人经》收入《道藏》洞真部,《无上秘要》收入《道藏》太平部,《二教论》《道藏》未收,收入《广弘明集》卷八,《龟山玄箓》收入《道藏》正一部,《太玄真一本际经圣行品卷第三》《阅紫箓仪》《玄言新记明老部》等《道藏》均未收。
20世纪初面世的敦煌文书,以佛教道教文献、四部文献写本和社会经济文书为主。相比于后两者和敦煌的佛教文献,敦煌道教文献保留了许多后世失传的文献。因此被重新发现以后,这些道教文献题名的确定和提要的撰写,也成为敦煌道教研究的基础工作。饶宗颐长期讲学于海外,能够亲研原卷,又对传世道教文献非常熟悉,不仅纠正了日本学者大渊忍尔在敦煌道教研究中的疏失,也是完成敦煌道教文献定名和提要的不二人选。
二、对传世道教文献的研究
除出土道教文献外,饶宗颐也曾为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所藏的传世道教文献撰写过提要。这些提要皆见于1970年香港龙门书店出版的《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善本书目》。
《冯平山图书馆善本书目》分宋元本、明刊本和钞本三大部分,后两部分之下又依四部分列各文献。其中在明刊本子部下,著录有宋林希逸撰、明施观民校《庄子鬳斋口义》。在钞本子部下,著录有《太清金液神丹经》、《神仙感遇传》和《三洞珠囊》,明释德清《老子道德经发隐》,清郝懿行之妻王照圆的《列仙传校正本》二卷、《列仙传赞》一卷和《梦书》一卷。饶宗颐为以上的传世道教文献分别撰写了长短不一的提要。
《太清金液神丹经》、《神仙感遇传》和《三洞珠囊》属于冯平山图书馆所藏《道藏》零本,这些道藏钞本原为天一阁旧藏,后归刘氏嘉业堂所有,嘉业堂藏书散出后,港大教授林仰山(Frederick Sequier Drake)为香港大学购入其中的一小部分。[11]
饶宗颐先生对传世道教文献《老子》《庄子》《文子》《抱朴子》《太平经》等也有深度研究。在《(传老子师)容成遗说钩沉——先老学初探》中,饶宗颐对《老子》思想的来源,进行了探索。他结合传世文献中“老子受学于容成”的记载,认为《庄子·在宥》所载广成子答黄帝问道的内容,及马王堆帛书《十问》黄帝问容成的内容,与《老子》有密切的关系。此外,《庄子》的《则阳》《齐物论》《养生主》等篇目中,也都有容成思想的表现。饶宗颐又结合马王堆帛书《十六经·顺道》的记载,认为老子的思想不仅来源于容成,也有取自大庭之处。在此基础上,饶宗颐先生进而指出,《老子》一书由若干记载前代的“重言”缀合而成。
饶宗颐的这一重要论断的学术意义,正如赵逵夫先生所说:“历来学者们研究儒家思想,只上溯至孔子;研究道家思想只上溯至老子。而魏源提出老子思想是有所继承,并非凭空产生的问题。……近年中有香港中文大学两位先生从这方面加以探讨,成振聋发聩之声。一为饶宗颐先生”[12]。
在《战国西汉的庄学》一文中,饶宗颐对阮籍、嵇康之前的庄学加以讨论,并对闻一多《古典新义》中有关《庄子》的部分观点作了辨正。闻一多认为西汉人讲黄老而不讲老庄,饶宗颐则举出《淮南子·略要》中已将老庄并称。闻一多认为两汉没有《庄子》的注本,饶宗颐则认为,清人俞正夑已指出淮南王便有解庄的作品《庄子略要》。闻一多认为桓谭曾向班固的从伯父班嗣借《庄子》,但班嗣致书桓谭婉拒,因此桓谭未曾读过《庄子》。饶宗颐根据《新论·本造》所记有关庄子的评价,认为桓谭可能读到了《庄子》。闻一多认为崔譔曾最早为《庄子》作注,饶宗颐则认为崔譔为东晋议郎,向秀早在崔譔之前就有《庄子》注本20卷。其实综观饶公此文,不仅纠正了闻一多对庄子的看法,而且对宋高似孙等均以阮籍、嵇康作为庄学先导的观点也有所辨正,将庄学流行的时代,上推到战国西汉时期。
三、文化背景下的道教研究
在谈到自己与敦煌学的时候,饶宗颐认为自己只是将敦煌石窟所出的经卷文物,作为辅助的史料,他更“喜欢运用贯通的文化史方法”[3]。其实非特敦煌学研究,饶宗颐在道教研究中也常运用文化史的方法。1983年12月,饶宗颐应邀出席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金禧纪念学术讲座,发表了《道教与楚俗关系新证——楚文化的新认识》的演讲。饶宗颐虽系粤人,却对楚文化情有独钟,从1940年完成《楚辞地理考》,到1954年发表有关仰天湖楚简的论文,从1964年亲睹长沙子弹库帛书,再到此后研究楚帛书和新出楚简,饶宗颐对楚地的文化,有着深刻而独特的认识。用饶宗颐自己的话说,他“把《楚辞》、楚地理、楚简、楚帛书联系起来,就有意识地研究楚文化了”[8]90。
在《道教与楚俗关系新证》一文中,饶宗颐将道教也与楚文化相结合,认为楚文化是滋生道教的土壤,因为楚人崇信“黄神”,以巫医之术为人治病,这些都是楚人宗教意识的体现。马王堆汉墓的出土文献,包括《老子》《十六经》《日书》《刑德》《导引图》《去谷食气》《养生方》《五十二病方》等,也属于《道藏》内涵中最重要的部分。他进而指出,秦汉时期黄老学在理论和方技两个层面并行,从理论层面上而言,就是道家;从方技层面上来说,便是“道教”。
饶宗颐认为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养生方》和《五十二病方》提到的黄神,可以追溯到甲骨卜辞和马王堆帛书《十六经》中的黄宗,以及传世文献所记的黄帝。黄神原为楚地巫医赶鬼所请之神,后来被道教徒沿用,并非三张的创造。饶宗颐还指出,道教的醮因云气占而生,同样源自楚俗。《道藏》四辅之名,亦见于马王堆帛书《周易》和《十六经》。道教中天师之名,早已见于《庄子》和马王堆帛书《养生方》。
此前的学者在讨论道教的起源时,往往结合传世文献的记载,将道教起源与传世文献中的黄老学说相联系。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题的简帛,极大地丰富了人们对战国秦汉时期黄老学说的认识,饶宗颐便借助这些材料,钩稽出楚地与道教的关系。因为长期从事甲骨文的研究,又对出土文物多有关注,因此饶宗颐将甲骨卜辞中的黄宗和湖南宁乡黄材出土的人面纹方鼎,与传世文献中的黄帝及黄帝四面的记载结合起来,最为令人称道。
在《论道教创世纪及其与纬书之关系》一文中,饶宗颐运用比较研究法,通过分析道教创世说,来讨论历史上道教与佛教及其他宗教的关系。他根据《广弘明集》所载《化胡经》与《盘古传》的关系,结合敦煌所出《老子化胡经》卷十(P.2004)中,“洪水滔天到月氏,选擢种民留伏羲”的说法,认为这是道教对人类产生的表述。
饶先生继而征引《原始上真洞仙记》《度人经》《广弘明集》《太上老君说平安灶经》等典籍所记的道教创世说,并认为这些记载可能受到盘古神话的影响。《摩登伽经明往缘品第二》载帝胜伽指出婆罗门法认为大自在天(一译摩醯首罗,Maheévara)创造世界,系为妄说。帝胜伽之所以有这样的判断,也缘于其“博练四韦陀典,秘密之要无不了达”[13]。所谓四韦陀典,分别是《梨俱吠陀》(Rigveda)、《娑摩吠陀》(Sāmaveda)、《耶柔吠陀》(Yajurveda)和《阿闼婆吠陀》(Atharveda)。饶先生认为《梨俱吠陀》第10卷第90首“布鲁沙”(Purua)所记的巨神创世,便是大自在天创世说的来源。“布鲁沙”提到众神举行祭祀时,以布鲁沙为牺牲,他的口、双臂、双腿和双脚分别成为婆罗门、刹帝利、吠舍和首陀罗。其意念形成月亮,其眼中生成太阳,其口产出因陀罗和阿耆尼,其呼吸形成伐由[14][15]。婆罗门法认为自在天化出天地、日月、虚空、草木、河山、海洋等,明显受到《梨俱吠陀》的影响。《摩登伽经》东汉后期由安世高译为汉文后,其中的巨神创世和自在天创世,以及盘古创世的神话,又被道教徒所吸收,最终形成道教的创世论。
这篇论文视野宏阔,引用大量道经、纬书、佛典和古印度上古诗歌,体现出饶宗颐宽广的学术视野、敏锐的问题意识。饶先生此前曾措意于巴比伦创世史诗,也对基督教、印度教和佛教的的创世神话有所研究,因此并不局限于此前许多学者以道教文献而讨论道教创世,或者仅对中国古代佛道两教的关系展开,而能够在比较研究的视野之下,对道教的创世说有深入拓展。但文中尚有两处可待商榷之处,收入《大正藏》的《摩登伽经》,文中均作《摩伽登经》,其中一处还写作《魔伽登经》,恐系笔误。文中又称《摩登伽经》中的梵天为印度教的湿婆(Siva),亦属笔误。据上下文,大自在天当为印度教的湿婆,而梵天为Brahmā,并非Siva。
除此以外,饶宗颐还努力拓展道教与其他宗教及其他学科之间的关系,完成了一系列重要的论文。其中包括,讨论道教与经学及其他宗教的关系的《〈太平经〉与〈说文解字〉》;讨论道教与地理的《〈太清金液神丹经〉(卷下)与南海地理》;讨论道教与艺术的《吴县玄妙观石础画迹》、《淮安明墓出土的张天师画》和《西安鼓乐与全真教》等。
结语:饶宗颐道教研究的渊源与特色
综观饶宗颐的学术道路,曾广泛受到“四庵”和陈寅恪的影响。这“四庵”分别为沈曾植(字乙庵)、王国维(字静庵)、陈垣(字援庵)和叶恭绰(字遐庵),其中饶宗颐的敦煌学研究最初受到叶恭绰的影响,沈曾植和陈垣都曾从事道教研究,而饶宗颐的道教研究更多则受到沈曾植的影响。饶宗颐特别在《道教与楚俗关系新证》一文中,先后引用沈曾植对“醮”和“五斗”的说法,并对后一说法提出不同的意见。饶宗颐也指出,“因为看了王国维的书才受到沈曾植先生的影响”,自己“最佩服的是沈寐叟先生”[8]85,甚至在诗歌创作上也受到沈曾植的影响[8]93-94。
但是饶宗颐的道教研究,又不同于沈曾植、刘师培、胡适等,在阅读《道藏》的基础上进行吉光片羽式的阐发;也不同于于刘咸炘、许地山、傅勤家等,力求勾勒中国道教及典籍的整体面貌;更不同于陈垣、陈寅恪等,从宗派与地域等入手,讨论一定时期道教的发展状况④。
整体而言,饶宗颐的道教研究,呈现三个方面的特征。其一,重视出土资料。正如《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的《小引》所言,“20世纪为中国学术史之飞跃时代”,主要缘于“地下出土文物之富及纸上与田野调查史料之大量增加”[16]。饶宗颐在道教研究中,首先利用敦煌文书,后又辅以简牍帛书,并与《道藏》等传世文献相释证。他在熟稔掌握《道藏》的基础上,对阙名的敦煌道教残简加以考订,解决了一些悬而未决的重要问题,将此前“猜笨谜”式的命名,引向研究正途。其二,不拘泥于旧说。关于道家学派的讨论,众皆以老子为起点。饶宗颐却以为不然,他充分利用传世和出土的文献材料,勾稽出《老子》的思想来源。宋人高似孙,明人焦竑,近人汤用彤、闻一多、钱穆等,皆以阮籍为庄学的先驱,饶先生则将荀子以来论庄之说摘引出来,并加以分析,将此前的说法向前推进了数百年。其三,立足文化视角。饶宗颐对道教的研究往往从具体文献入手,对相关问题进行阐发,但又不拘泥于文献或道教本身。在与施议对的谈话中,饶宗颐指出:“从高处向下看,这么一来,视野就扩大了。否则,只是微观,就看不到大问题。”[17]他对道教的研究,应该也秉持这样的理念,能够优游于道经、儒书、释典和宗教以外的其他学科,形成深刻而独到的见解。
注释:
① 分别为新文丰出版公司于2003年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于2009出版的《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前者为繁体字版,后者为简体字版,均为十四卷二十册。
② 题记录文见《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卷五,202页。
③ 这部书年由广东人民出版社修订重印时,易名为《法藏敦煌书苑精华》。
④ 陈垣在致蔡尚思的信中说:“欲成一专门学者,似尚须缩短战线,专精一二类或一二朝代,方足动国际而垂久远。不然,虽日书万言,可以得名,可以噉饭,终成为讲义的教科书的,三五年间即归消灭,无当于名山之业也。”见陈智超编注《陈垣往来书信集》,三联书店,2010年,383页。这些主张也可以看作陈垣治学旨趣的写照,此条材料蒙王皓博士提供,特致谢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