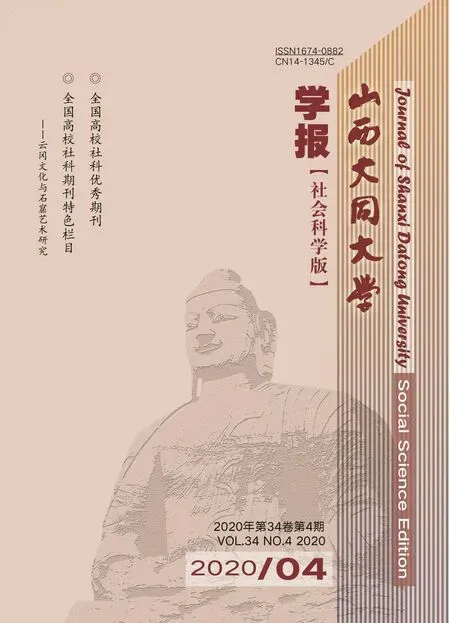老年人精神需求满足与社会支持的关系机制研究
——基于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CLASS)的数据
李肖亚,孙金明
(廊坊师范学院社会发展学院,河北 廊坊 065000)
习近平总书记在改革放开4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40 年来,我们始终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全面推进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不断改善人民生活、增进人民福祉。”随着老年人口的增加,中国进入老年社会,未富先老的国情吸引了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如何应对来势汹汹的“银发潮”,保障老年人老有所依的民生福祉成为整个社会的共同焦点,老龄化和老年人成为学术研究的热点问题。老年人的精神健康是老年人安享晚年的保障,是老年福祉本身的题中之意,也因此成为本文的关注点。
一、研究综述
社会支持理论起源于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主要是社会学、社会工作、心理学等社会科学领域和精神病学、流行病学等医学领域的研究主题。古典社会学大师涂尔干在其《自杀论》中即关注到社会支持对于降低自杀率的积极作用。[1]文化人类学家拉德克利夫·布朗首先突出了“社会支持网络”一词。[2]但社会支持理论的快速发展则是在20世纪60年代,并于20 世纪70 年代成为独立的学科分支。作为一个跨学科概念,社会支持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概念定义,甚至对于社会支持应该包含的内容也是有分歧的。在社会学领域中,社会支持研究主要集中于社会资本、社会关系网和社会资源;在社会工作领域中,社会支持研究的对象主要有老年人、妇女、留守儿童、大学生等;在社会心理学和心理学领域,社会支持研究主要应用于抑郁症、精神病、吸毒、慢性疾病等的治疗。[3]
Cohen将社会支持看作一种帮助个体有效应对生活事件压力的资源。[4]Cobb将社会支持定义为社交网络中个体能够感知被尊重、被关心的信息。[5]韦恩·韦登认为,社会支持指“来自个人社交网络的多方面的援助与情绪支持”。[6]程艳敏认为“社会支持是个体所经历的一切社会关系提供的有助于减轻个体心理应激反应、缓解个体心理紧张状态、提高个体社会适应能力的各方面帮助”。[7]Lin 等将社会支持分为情感性支持和实质性支持(如财务支持、家务等)。[8]Morgan 等将社会支持分为情感支持和工具性支持两个方面。[9]邱海雄认为社会支持至少应该包括主体、客体、内容三个要素。[10]瞿小敏也认为应该对老年人社会支持的质量、内容以及老年人自身作为社会支持的客体对其自身所获得支持的具体感受进行研究。[11]
部分学者认为社会支持的对象是社会中的弱势群体,有的学者则认为全体社会成员都有成为社会支持的对象的可能。笔者比较认同后一种观念。彭扬帆研究了社会支持理论视域下失独老年人的心理健康援助,提出了政府、社会和社区三位一体的失独老人心理健康救助机制。[12]韦艳将社会支持分为代际支持和社会交往两个层次,其中代际支持主要包括生活照料、经济支持和情感支持三个方面,最终得出代际支持中的生活照料和情感支持以及社会交往对农村老年女性孤独感具有显著性影响的结论。[13]李建新将社会支持操作化为家庭支持和社区支持两个变量,发现获得更多家庭及社区支持的老年人对生活质量的评价也会更高。[14]吴敏则将社会支持量化为感知支持,即个体感知到而非实际获得的支持,并得出社会支持绝对规模量的大小并不必然改善农民工的心理健康的结论。[15]瞿小敏将躯体健康和心理健康两个变量作为中介变量来分析社会支持对老年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并发现情感性支持可能比生活照料等实质性支持作用更大。[11]
结合现有理论与研究成果,本研究将社会支持视为一种能够帮助个人提升社会适应能力的社会资源,将其分为物质支持和精神支持两个层次,并在这一层次上展开研究。
二、数据来源和研究方法
(一)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源于中国人民大学组织的一项全国大型老年调查项目(China Longitudinal Aging Social Survey,CLASS),是一个全国性、连续性的大型社会调查项目。在全国范围内以60 岁以上老人为调查对象,共获得有效样本11511 人。本文根据研究需要,从中剔除掉作为因变量的“精神状态”变量的未填答个案,并为了提高研究的效度,进一步剔除掉职业变量的未填答个案,最终筛选出5991个样本,其中的有效样本为男性2979 人,女性2970 人,农业户籍人口2205 人,非农业户籍人口3782人。
(二)研究方法 本文主要基于SPSS24.0版本进行分析,主要的分析方法有统计描述和二分类logistic 回归分析。其中统计描述主要是对目前老年人的精神状况及不同种类的物质支持进行描述分析,主要有“积极状态”和“消极状态”两种维度;均值分析主要用于不同群体特征的老年人的精神状态的比较;二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则用来探寻社会支持作为自变量和老年人精神状态作为因变量之间的关系进行考察,并作为本文的主要讨论内容。
因变量老年人精神健康状态积极时取值为1,概率为P(0≤P≤1),老年人精神健康状态消极时取值为0,其概率为1-P,其线性回归方程为:

将上述方程做Logit变换,得


以上即为Logistic回归模型。由上式可逆推出

变量经过对数化处理的logistic模型,能够较好的满足定量变量的建模要求。
(三)具体的数据处理 本文将老年人的精神状况作为因变量,该变量是由共12 个陈述的总加量表得分计算出来的综合分值。该量表包括“过去一周您觉得自己心情很好吗”,“过去一周您觉得孤单吗”,“过去一周您觉得不想吃东西吗”,“过去一周您睡眠不好吗”等12 个问题。每个问题设置没有、有时、经常三个答案,分别赋值1 分、2 分和3分,每个被调查者的最终得分小于19 的话转化为取值1,也就是“积极状态”大于等于19的话转化为2,也就是“消极状态”。
自变量根据社会支持的定义,将已有的社会支持分为物质支持和非物质支持,其中涵盖了正式支持和非正式支持的分类因素,精神支持包括由家人、亲戚或朋友提供的精神层次的非物质的支持;物质支持则指由亲友和亲友之外的社会组织、社区或国家提供的金钱、实物、服务等方面的支持。其中,物质支持包含的问题有享受的社会保障待遇、接受的社会服务、社区提供的活动设施、是否受到老年优待等问题;精神支持包括同住人数、婚姻状况、健在的子女数量和可求助亲友数。享受的社会保障待遇由老年人每个月的各项社会保障待遇相加得到的总额再进行分类。可求助的亲友数量是一个由6个问题组成的总加量表的得分转化而来。
除因变量外,笔者还纳入了学界认为的可能影响老年人精神需求满足状态的其他变量作为控制变量,有年龄、性别、婚姻状况、教育程度和退休前的职业、户籍这几个变量。
(四)研究假设 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社会支持资源越充足,老年人精神需求越容易获得满足。
假设2、子女数量越多,精神需求越容易获得满足。
假设3、老年服务越丰富,精神需求越容易获得满足。
三、研究结果
(一)中国老年人精神健康状况的现状 统计数据显示,中国大部分老年人的精神状态比较积极,达到69.8%。但是考虑到中国老年人的基础数额较大,精神状态消极的老年人为数也不少。非农业户籍老年人比农业户籍老年人精神状态更积极,前者比后者积极者比例多达15%,说明户籍对于老年人晚年的精神状态影响较为显著。男性老年人比女性老年人精神状态更加积极,前者比后者比例多11%,男性较女性更容易有积极的老年生活;在消极状态人口中,男女比例则基本持平。从职业类型上看,不同职业类型间差距较大,国家和企事业单位的领导,其老年人精神状态积极的比例最高,达到81.1%,远高于农林牧渔从业者的56%,这也从侧面印证了户籍对精神状态的影响,非农业户籍老年人大部分集中于非农职业。从学历上看,呈现出非常明显的正相关态势,学历越高,精神状态积极者比例越高,每个学历层次之间相差了将近10个百分点。此外,年龄不同的老年人精神状态也不同,60—69 岁的低龄老年人比70—79 的老人精神状态积极的比例高接近4个百分点,70—79岁的老年人又比80—89 的老年人积极比例高接近3 个百分点。
从健在子女数量和可求助的亲友数量上来看,可求助的亲友数量多的老年人比可求助亲友数量低的老年人精神状态积极的比例高,没有可求助亲友的老年人消极的比例达50.2%,而可求助亲友数量高的老年人消极比例仅为27%。健在的子女数量对老年人精神状态的影响则体现在有无健在子女上,无健在子女的老人消极的比例达46.8%,而有健在子女的老年人中这一比例仅为30%左右。而健在子女的数量对老年人精神状态的影响则不显著,健在子女为多个和1个的老年人精神状态差别不显著。此外,婚姻状况也对老年人的精神状态有显著影响,有配偶的老年人精神状态积极的比例为75.1%,而无配偶老年人这一比例仅为56.6%,相差将近二十个百分点。
所利用的社会服务、拥有的社区活动场所和是否享受老年优待这些差异也会影响老年人的精神状态。基本体现为可利用的服务越多、拥有的社区活动场所越多、可享受老年优待,老年人越倾向于积极的精神状态。而在物质支持方面,影响最显著的因素则是社会保障总额,社会保障额度高的比额度低的老年人精神状态积极的比例高接近三十个百分点。
(二)老年人精神健康状况的影响因素分析为了确定老年人的精神状况和社会支持的关系,笔者按照社会支持的分类构建了三个模型,第一个模型纳入控制变量和精神支持因素的变量,第二个模型纳入控制变量和物质支持因素的变量,第三个模型纳入前面所有类型的变量。通过三个模型确定各个变量的影响大小及在模型中的变化。
模型一可以分析出社会支持的精神支持方面对老年人精神状态有显著作用,精神支持的整体资源越丰富,老年人越倾向于积极的精神状态。其中,婚姻状况、可求助亲友数和同住人数的显著性水平都小于0.001,对老年人精神状态有显著性作用。具体表现在有配偶的老年人精神状态消极的发生比是没有配偶的老年人的一半;全模型中控制了其他影响因素后,有配偶的老年人精神状态消极的发生比是没有配偶的老年人的一半。可求助亲友数为0 或1(得分小于等于6)的老年人精神状态消极的发生比是可求助亲友数大于3 的老年人的3.1倍;在控制了其他影响因素的全模型中,可求助亲友数为0或1的老年人精神状态消极的发生比是可求助亲友数大于3 的老年人的3.1 倍。从同住人数上看,独居老人精神状态消极的发生比是同住人数5 人以上的老年人的1.6 倍;控制了其他影响因素后的全模型中独居老人精神状态消极的发生比也是同住人数5 人以上的老人的1.6 倍。健在子女数量对老年人精神状态的影响则不显著,有0个健在子女的老年人精神状态消极的发生比仅是有3个及以上健在子女的老年人的1.1 倍;在控制了其他因素的影响后这个数值仍然是1.1。考虑到健在子女数量和可求助的亲友数可能有共线性,在剔除可求助的亲友数量这一变量后重新进行Logistics回归分析,模型一中健在子女数量的显著性水平为0.558,全模型中健在子女数量的显著性水平为0.546,仍不具显著性作用。在全模型中同时纳入健在子女数量和可求助亲友数的交互作用,交互作用亦不具显著性作用。这在一定程度上佐证了李建新、韦艳之前的研究结论,即有非亲属交往对象和交往频繁的老年女性孤独感大幅下降,来自子女的社会支持会随着子女数量的减少而减少。[13][14]这个结论与贺寨平的研究结果不是很一致。[16]
模型二显示的是社会支持的物质支持层面与老年人精神状态的关系。社会保障待遇总额每月1000 元以下的老年人精神状态消极的发生比是社会保障待遇每月3000元以上的老年人的1.5倍;在控制了其他影响因素的全模型中,社会保障待遇总额每月1000 元以下的老年人精神状态消极的发生比是社保待遇每月3000 元以上的老年人的1.5 倍。享受老年优待的老人精神状态消极的发生比是不享受老年优待的老年人的0.88倍,在控制其他变量影响因素的全模型中这一数值保持不变。在社会服务方面,没有社会服务的老年人精神状态消极的发生比是接收3 项及以上社会服务的老年人的1.2倍;在控制其他变量影响因素的全模型中,这一数值增长到1.7。有0—1项社区活动场所的老年人精神状态消极的发生比是有4项及以上社区活动场所的老年人的1.3 倍;在全模型中控制其他影响因素后这一数值降低到1.2。
模型二的Nagelkerke R2较模型一要小,说明社会支持的物质支持层面的因素对老年人精神状态的影响要小于精神层面。其中,仅有社会保障总额这一因素的显著性水平小于0.001,其他变量的影响都不显著。这个结论在一定程度上和其他学者的发现并不一致。[14]笔者进一步分析发现,社会服务等其他变量影响并不显著的原因在于,目前中国针对老年人的专门服务和其他物质支持仍然太少。如下表所示,在老年饭桌、日托、心理咨询等老年服务中,91.4%的老年人使用过0项,剩下的则是使用过1—3项,使用过4项以上的老年人数则为0。在老年活动场所方面,35%的老年人没有专门的社区活动场所,剩下的43.5%的老年人有1—2 项活动场所。同时,有62.7%的老人为享受过老年优待。
在控制变量中,所有的模型都显示性别、年龄、宗教信仰、户籍这些变量对老年人的精神状态没有显著性影响,学历和职业的显著性水平都小于0.05,对老年人精神状态具有显著性作用。具体表现为学历越高,老年人精神状态消极的发生比越低,学历为文盲的老年人精神状态消极的发生比是学历为大专及以上老年人的1.688 倍;从职业上来看,职业为国家机关和企事业单位领导人的老年人精神状态消极的发生比是无业老年人的0.7倍。

表1 老年人物质支持现状
四、研究结论
社会支持理论认为,个体周围的社会资源所提供的精神或物质支持有助于个人降低心里紧张状态,减轻个体心理压力,更好地适应社会生活。通过实证分析,结合社会支持的相关理论,我们得出如下结论:第一,社会支持资源越丰富,老年人的精神状态也更积极,笔者的第一个研究结论得到了实证验证。无论是物质支持还是精神支持都显示出这样的作用方向。物质支持和精神支持中的任何一种支持资源的丰富都有利于老年人的精神状态向积极的方向发展。
其次,在具体的支持类型中,精神支持层面作用更显著的变量是“可求助的亲友数”和婚姻状态。能够见面联系的亲友数越多,能够提供帮助的亲友数越多,老年人的精神状态越积极。而健在的子女数量在这个问题上并不具有显著性影响。
再次,在所有类型的物质支持资源中,社会保障资金总额的影响最为显著,当下的中国老年人受国家的社会保障政策影响更大。老年社会服务和老年活动场所这些相对正式的支持类型则影响不显著。我国在为老服务方面还相对薄弱,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同时,在分析过程中我们发现,中国老年人的精神状态呈现出显著的城乡差距,契合了我国的城乡二元化格局。老年人整体上精神状态积极人数远大于消极人数,但同时亦存在大量缺乏社会支持的老年人,处在物质和精神双重匮乏的境地。物质支持中起最主要作用的社保待遇在城乡之间的差距较大,调查数据显示仍有不少老年人没有享受任何社保待遇,与此同时部分老年人的每月社保总额加起来接近10 万(包括退休金)。这种差距深层次地影响着老年人的精神健康和身心健康。
根据研究结论,本研究提出以下政策建议:一、加速统筹城乡之间、地域之间、行业之间的社会保障政策,健全农村老年人救助机制,尽快实现应保尽保的社会保障政策的全国统筹。二、加速推进社会工作队伍建设,尤其是农村社会工作,社会工作者介入独居、丧偶和失独老人的精神需求。在老年服务领域,深化老年社会服务内容,创新老年社会服务形式,使更多的老年人有机会使用更专业的老年服务。
本研究还有以下不足之处:一、对于社会支持的操作化定义,限于篇幅所限,仅从社会支持的物质和精神层面来测量,没有关注老年人的个人老化态度和主观上对社会支持的利用度。二、在具体的变量选择上,仅考察了健在子女数量这一因素,而没有纳入具体的子代对亲代的支持状况;在社会服务的考察上也是从社会服务的量上进行测量,没有能深入社会服务的微观层次,测量具体的老年社会服务差异。本研究计划进一步深化这两个变量的测量,探索社会支持与老年人精神健康状况的微观作用机制,以促进实现老年人安享晚年、老有所乐的老年保障。
- 山西大同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的其它文章
- 云冈石窟第6窟佛传故事犍陀罗文化因素初探
- 同大学者风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