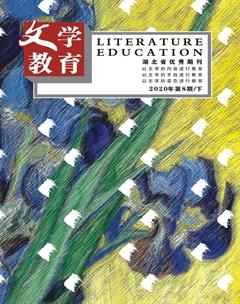网络的故事语法
2019年年底,和所有放寒假前的日子一样,充满了各种各样的聚餐。不过这一年的聚餐有了新的娱乐项目——大家一边胡吃海塞,一边调侃网络上新近流行的段子:“全世界都知道武汉被隔离了,只有武汉不知道武汉隔离了”。事情逐渐明朗起来,汉口那边似乎发现了传染病。但是,汉口的真实情况什么样,身边人也不过是“听说”。实际上,虽然身在武汉,我已经有三四年没有去过汉口了。汉口发生了什么,我们能获知的也是来自网上的段子:“全世界认為中国是疫区,中国认为武汉是疫区,武汉认为汉口是疫区,汉口人民表示该吃吃,该喝喝,该聚会聚会,该逛街逛街。”
随后我就回了老家,后面对武汉了解,全是依赖网络了;即使有朋友提供的消息,也一样来自网络。在老家期间,我作为武汉来的人得到了特殊照顾,也受到了些许的提防。和许多网民一样,我通过网络与武汉发生着激情澎湃的联系——比在武汉时还了解武汉,比在武汉时还关心武汉。但实际情形什么样,我只能坦诚自己并不清楚,因为我不在现场。但是,在这个网络时代,网民比当事人更了解事件,这一点竟然成了常态。这个神奇的结果是怎么形成的?它对今人的思维带来了什么影响?这是需要引起我们思考的。
一
我们对世界的认识并不是直接的,而是经过了思维中介的筛选;某种意义上“真正的”世界是不可知的,我们只能停留在所知的那部分世界之内。康德把他的这个发现自诩为“哥白尼式的革命”,确实毫不过分。与此相应,他给我们的教导是“批判”,这个词的意思是说,我们能看见的都是有限的,不要过分相信眼见为实,世界总是还有无数另外的可能。
打个通俗的比方,康德的意思是说,人要看见世界,就得有副眼镜。这个眼镜,就是人类的文化系统,尤其是种种符号手段。从语言、图像、文字到复杂的大众媒介,这些都是人类看世界的眼镜。作为康德的后裔,二十世纪的人文科学也提醒我们,所有这些眼镜在某种意义上都是变色镜、哈哈镜,它并不“如实”地再现世界。
人类的文化眼镜及其功能有一个复杂化和独立化的发展过程。语言应该是人类发明的第一副眼镜,接着是简单的图画,然后是文字,这是几千年来人类再现世界的基本手段。这些手段的重要功能,是掌握甚至垄断对世界的认知。但总体来说,这些传统手段的能力有限,并不足以垄断人民的视野。比如,熟悉文字写出的经典的人可能会变成不识时务的“书呆子”,但不识字的大多数人仍然有自己的世界观。总之,这些再现手段没有凌驾于生活之上。
但现代传播技术的发展让文化眼镜的功能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首先是印刷技术的普及,让书籍和图像进入寻常百姓家,“虚构”和“假象”第一次冲击了人类视觉;接着是广播、电影和电视的出现,让看不见的信号布满了星辰和诸神曾经占据的天空,改变了“明星”和男/女神的含义。而且,随着电视节目在新世纪之后实现了24小时不间断播出,媒介获得了某种永生。当然,更具革命性的变化则是互联网的出现,以及智能手机和物联网让网络充斥到了生活的每一个角落。而这个变化的本质,就是再现世界的手段,开始垄断了生活的真相;原本服务于生活的眼镜,开始遮蔽了我们的双眼。我们需要沿着这个思路来思考网络的本质和影响。
二
符号再现出来的,不只是信息,而是被加工、编码的信息。加工的过程,就是让鸡零狗碎的材料具有一个整体性的框架,让“天然”、“无辜”的人和事显示出一个有意义的秩序。但加工编码的目的,不只是让人看见事物,还包括让人习惯看待事物的视角——就像狡诈的眼镜商不只是要帮你看清世界,还要让你适应他的眼镜。所以在历史上,对符号尤其是文字和书写的管控是权力运作的关键领域,也是宣传教化的重要途径。由于普及性以及全时空覆盖的特点,网络获得了文字不敢想像的威力。而且,更关键的一点,它的运行似乎实现了自动化和自我维持,不再需要权力的额外监控和推动。让我们以普通网民的经验为例,看看网络的这一加工编码程序是如何运作的。概括而言,网络中的信息以及网络本身,是按故事那样的方式被结构的,网络具有民间故事那样的语法。
第一个特征,高度典型化的人物设定。“从前,有个人”,这是故事的经典开场。人物的名字是无关紧要的,关键是他在故事中的“人设”。网络中的人物,同样是以人设的形象出场的。但这句话不只是说,只有被赋予人设,人物才能在网络信息中出场;还是说,在网络中出场的人物,注定会沦为人设。
记得几年前,有新闻报道过国内某高校某院系某政治身份的学生约会百余人的事件,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例子。我之所以在此尽力避免提及任何明确的“描述”信息,正是为了不落入网络人设的陷阱。因为作为一件极为恶劣的事件,这里提及的所有信息都会受到玷污——不止是当事人,相关的学校、专业、政治身份等等都会受到连累。谁若不信,请自己私下做这个思想实验,我只想指出其中的逻辑要害:在网络中,语言的概括性功能僭越了描述性功能。这就是“武汉发生了病毒感染”被扭曲为“武汉病毒”、武汉人=病毒的原因。“武汉”原本是一个描述性的限定词,却作为一个概括性的共名被“感染”了。
第二个特征,高度戏剧化的情节结构。故事的戏剧化是指,尽力删除无关的情节,只保留能推动主题发展的要素。这样形成的主题,则是一个高度清晰的价值命题。所以民间故事可以转化成一个伦理法则——“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网络同样倾向于建构戏剧化的情节和清晰的价值观。
有学生考试作弊。该生跳楼。这是最近一则网络新闻中的情节要素。但单纯依靠这些要素不能使之成为故事,也不会成为轰动的新闻。要成为故事,必须在这两个可能相关也可能无关的事件与行动之间填补上明确的因果关系。比如:有学生考试作弊,“由于”老师未及时干预,“导致”该生跳楼。这就成了一出无良的教师和冷漠的教育残害学生的大戏,主题明确,价值清晰。当然,剧情也能翻转,主题也能重构——这是我们非常熟悉的特征。但是要占据网络,高度戏剧化是关键,清晰的善恶斗争是关键。
第三,高度简单化的因果分析。叙事也是一种因果分析范式,一种价值审判机制。与上述特征相关,网络倾向于将这一分析和审判高度简单化。在前面那个学生跳楼案例中,我们不知道、也没有人分析这个身份是学生的人,他的年龄、性别、性格、爱好、情绪、星座等等无数可能的因素。因为,在故事中、在故事的要求中,这都是无关的信息,“学生”的人物设定只将它限定在了与这一社会身份相关的人物关系中:老师、校长、学校。经过这么一番删繁就简,因果分析开始变得极为简便:或者老师(学校)错,或者学生错;或者是学生脆弱,或者是老师冷漠——简洁的背景设定没有为其他的可能原因留下空间。于是,一场教育制度批斗开始了,或者,一场关于青年人使命的宏大论述出场了。事情本身是什么样的,没人关心。在现实中,人的行动原因肯定是多方面的,不同原因之间的主次更是难以厘清的。但是,网络中的叙事,却不善于把握复杂性。我们假设,如果有后续的调查发现,该生平时喜欢玩电子游戏,那么这个故事会带来一场电子游戏大批判。这并非没有可能,因为已经有评论从一个案例发掘出教育市场化批判的大主题了。
三
实际上,这些年来引起轰动的新闻事件,几乎都具有上述特征——鲜明的人设,明确的主题,单一的因果分析。一个事件可能被不断翻转,被炒热,被遗忘,唯有这个叙事逻辑依旧。但是,受到网络叙事语法影响的,不只是新闻事件,下面的诸多例子会显示,网络本身是充满了故事结构的。在这里,我想进一步说明,这种结构对于“网民”的思维方式甚至人格形态发生了何种影响。
最直接的影响,是教条主义的泛滥。教条主义的本质就是看待事情时的“一根筋”思维,只考虑原则,不考虑现实;将某一原则、价值推向极端,不考虑生活是由多种原则和多种价值构造的。比如,学生就应该认真学习,老师就应该热情教课,警察就应该严肃办案,夫妻就应该恩爱。在某种意义上,这些要求都没错,但都有其合理适用范围,一旦越界,便是教条。
前几年有新闻说,几位民警在现场办案时嬉笑打闹,被人拍了照传到网上,相关人员受到处分。这就是一种网络教条主义的表现。在不影响工作的情况下,民警为何不能嬉笑?何况嬉笑可能只是抓拍瞬间的表现。网上流传的另一张照片应该更为网民所熟知,内容是某大学课堂上。老师讲课时一大片学生趴在桌上睡觉。正如许多人的跟帖评论显示的,这是一副被赋予了鲜明主题的图像,而主题不外乎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的慨叹:“现在的大学生……”,或“现在的大学老师……”但这同样是一种教条态度,仿佛只有“嗷嗷待哺”才学生的天职,可是,哪个做学生的没有上课走过神,片刻的走神会有多大的危害呢?在教条主义思维下,公众人物成了最直接的受害者。如果某明星夫妻出场时十指相扣,一定会被解读为宠溺恩爱,一旦没有牵手,一定会被解读为貌合神离。于是,与网民的这种纯洁思维相对应的,当今的公共文化日渐虚伪化,迎合网络教条主义的种种“秀”文化横行。
与教条主义的相关的另一种影响,是极端主义思维的日常化。网络叙事倾向于呈现一种明确的价值观与单一的因果性,这使得网民缺乏看待世界的通达眼光与分析事件的复杂眼界,非黑即白的思维泛滥。最常见的情形,是某些职业和机构的形象被高度刻板化了,比如,今天说到官员,很难不与腐败联系起来;说到教授,则直接被污名化为“叫兽”。建立起这种联系的不是严谨的统计对比,而是网络叙事的联想机制。另一种常见的情形,则是分析事件时的单一因素决定论。比如,面对许多复杂的公共事件,许多人的工具箱中只有一件“制度决定论”的法宝。某数亿人口的大国强大,一定是制度优越,几百万人口的城邦富裕,也是制度优越,即使两国的制度差异极大;而只要某国换了制度,王子和公主就会快乐地生活下去了。
最终,这给思维带来的最大危害是,在网络世界,事物的具体性消失了,就事论事的分析消失了。事物只剩下了共名所指称的那些性质,其个体性被堙没。比如,武汉等于病毒,湖北人都有毒;更极端地,一张P出来的假照片,就能代表上千万人的水深火热。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应该是基本的逻辑要求,但在网络世界,这一规则不怎么受人待见。对事件因果性的分析被局限在根据叙事主题选定的少数因素甚至单一因素上。最后,具体事件实际上被搁置一边,网中泛起的是针对这些因素和价值主张进行的辩论。某小学生作业被老师批评;该小学生跳楼。这是最近一则新闻中透露出来的信息。实际上,没有人敢说这背后究竟发生了什么——我们都不是知情者;但大家都在围绕那些叙事主题进行的义愤填膺但迂阔无效的制度大审判。
最终,在我们的网络时代,每一条表述都变成了一条宏大叙事,每一个见解都在针对“这个世界”,每一个人都是胸怀天下的政治家,每一条新闻都透露出世道沦落的玄机,每一个不同主张都意味着心怀不轨的异端,每一次辩论都是价值世界的生死决斗。每一个人都可能被人设化和刻版化,每一个人都在强化某种单一立场:自由主义、女权主义、环保人士、爱狗人士……
四
任何信息都是被再现手段加工编码过的,这本来是一种常态。但由于网络的“铺天盖地”性质,用故事语法编码的网络,日益垒砌出一个刻板的世界形象,近年来成熟的大数据技术则有使之进一步强化的危险。这是一个逐渐板结的媒介,它像民间故事,只有叙事母题的复制,但不再有叙事模式的更新。熟知了某一母题的网民,思维越来越习惯于这一模式,并以为那就是世界的真相;由于媒介的无孔不入,如今手握智能手机的网民,更像全知的上帝,透过黑屏俯视世界,且以为世界只有方吋之大。但与上帝不同,我们又没有超越的本事,只能沉浸在黑屏中的世界里不能自拔。与网络诞生之初许多人的浪漫设想相反,网络并没有给大多数人带来更宽广的视野和更通达的胸怀。
但是,再现不等于世界,媒介不等于生活。这是康德给我们的教诲。在漫长的时代里面,人们借助故事来理解这个世界,但不会完全迷信故事。人们从故事中明白了好人坏人,并依然把故事称为“瞎话”、“日白”,这是一种健康的批判态度。在今天,这一批判立场依然有效,却更为艰难。因为,在一个符号充斥、万物互联、黑镜统治的时代,故事变得防不胜防,我们一不小心就会踏入故事的泥潭。
不過,小心区分再现与世界、媒介与生活仍然是网民必要的基本修养。永远记住我们所见的并非世界的全部,事情还有另外的细节,生活还有无数的可能;必须明白我们的视界的有限性,不要将自己误认为正在俯视世界的上帝;接下来,尽力回到事情的细节,发掘事件背后更复杂的影响因素,增加工具箱中的分析手段,这才是自诩“批判”的人真正的和必要的任务。
胥志强,文学博士,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