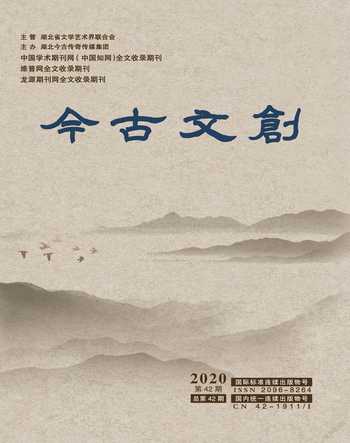文学地理视阈下的楼钥使金纪行诗
【摘要】宋孝宗乾道五年(1169)冬,楼钥奉命出使金国,全程历时月余,往返数千里,途中他以地名和时间为线索,挥笔写下了十三首纪行诗,作品中不但有离家远游常见的羁旅之愁,还饱含着对故土的深情和对金虏的痛恨,格调沉郁雄健,颇具前人以诗为史的遗风。这样的特色既是产生于彼时两国对峙的特殊历史环境,也受到创作者由宋入金、横跨南北的频繁空间位置变换的深刻影响。
【关键词】楼钥;使金诗;行游诗;文学地理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0)42-0004-03
楼钥(1137—1213),字大防,又字启伯,号攻媿主人,明州鄞县(今浙江宁波)人,历仕宋孝宗、光宗、宁宗三朝,累迁签书枢密院事、参知政事,嘉定六年卒,赠少师,谥宣献,《宋史》卷三九五有传。楼钥工诗擅文,著作丰厚,今存《攻媿集》一百二十卷及《范文正公年谱》。真德秀赞其曰:“嘉定起为内相,俄辅大政。向来俦辈凋丧略尽,而公岿然独存,遂成一代文宗。”
孝宗乾道五年(1169)冬,三十三歲的楼钥以书状官身份随舅父汪大猷出使金国,一路笔耕不辍,除撰成日记《北行日录》外,另作有纪行诗十三首,详细记述了沿途见闻感悟,分别是《使北①雪中渡淮》《泗州道中》《灵璧道中》《灵壁道傍怪石》《相州道中》《陈留柏》《即事》《腊月二十五日大人生朝》《初出燕山》《元日》《京城外丘垅》《雍丘驿吏》及《过安肃军》(后四首有目无辞)。这批作品多以地名为题,创作顺序清晰,基本上贯穿了楼钥出使过程的始终,在文学欣赏和历史考证上都具有较高的价值。
一、楼钥使金纪行诗的地理空间构成
曾大兴《文学地理学概论》将文学家的地理分布分为静态和动态两种,动态分布“是指其流寓、迁徙之地的分布”。而且又有长时段和短时段的区别,楼钥的使金之行即属于长时段动态分布。“文学家的流寓迁徙,扩大了他们的生活与写作的空间,丰富了他们的地理体验,使他们有机会领略不同的地域文化,从而提高自己的思想认识和创作水平。”楼钥正是在历时月余、横跨南北的出使过程中,在宋、金对峙的历史背景下,构建起一个独具特色的文学时空。
孝宗乾道五年(1069)十一月,楼钥自南宋淮南东路盱眙军出发,沿汴水一路北上,经泗州、宿州、亳州、归德府和拱州而至南京,然后横渡黄河,又历滑州、浚州、相州、磁州、洺州、邢州、赵州、真定府、定州、中山府、保州、安肃军及涿州,最后到达金国中都,单程近两千三百里(宋制,约今1280公里②),以牛、马、驴牵引的畜力车和渡船为主要交通工具,辗转于今天的江苏、河南、河北等地,空间位置转换频繁,地区环境差异明显,这使得其诗不论是意象选取还是情感内涵都随之一变,呈现出与以往行游作品截然不同的基调和风格。
二、楼钥使金纪行诗的文学景观书写
文学景观是文学地理学研究中的特有概念,“是指那些与文学密切相关的景观,它属于景观的一种,却又比普通的景观多一层文学的色彩,多一份文学的内涵。”简而言之,所谓文学景观,“就是具有文学属性和文学功能的自然或人文景观。”
文学景观的内涵极为丰富和复杂,它会随着时间、创作主体以及读者的变化而变化,可以不断地被完善、改写甚至是颠覆。
(一)南北迥异的自然景观
秦岭—淮河线既是宋、金两国的政治和军事分界,同时也是我国重要的地理分界,南北气候差异极大。据《北行日录》记载,楼钥等人于乾道五年(1169)十一月二十四日抵达淮南东路盱眙军,次日即是冬至,这时候北方已经开始进入一年中最寒冷的季节,因而“雪”便成为其纪行诗中出现频率最高的意象。
楼钥是明州鄞县(今浙江宁波)人,且出生于宋室南渡之后,在他此前的人生中,或许从未亲身感受过北地的严冬,故在其以往的诗作里尽管也不乏对雪的描写,但却是典型的江南景致。
“浅春寒尚深,忽见云糢糊。撒盐压衡茅,晨兴粟生肤”(《同官登敕局小楼观雪》)、“玉树琼枝无限好,雪窗高阁不胜寒。直疑天上梅花落,莫作人间柳絮看”(《喜雪》)、“开门一看天宇阔,素蜺百万翻长风。琼楼玉宇满妙界,千林宝树春玲珑”(《雪》)。在似水柔情的江南,仿佛就连雪也变得温婉起来,它们是九天落梅,是玉树琼枝。
诗人的身体虽然感到寒冷,内心却并无萧瑟之意,他满怀赞叹地欣赏着自然的杰作,并期盼来年的丰收,“晓风吹起雪漫漫,来兆丰年喜有端”(《喜雪》)。
相比之下,北方的雪就要粗暴许多,不仅下得大,而且来得急。“宿雪助寒色,相看汴水滨。轻车兀残梦,群马溅飞尘。行役过周地,官仪泣汉民。中原陆沈久,任责岂无人”(《泗州道中》)。
宋代的泗州城位于淮河北岸,在今江苏省盱眙县沿河村一带(118.46°E,33.02°N),它既是自唐以降的水陆交通枢纽,亦为南宋与金国交战的前线重镇,从这里开始,就进入了金人的实际控制区。大雪下了一整夜,诗人在汴水之畔与亲人(按《北行日录》载,当是其季舅汪大定)执手惜别,正式踏上漫漫无期的北使之路,行走在沦入胡虏之手的祖宗故地,看着那些因为见到朝廷仪仗而痛哭流涕的遗民同胞,想必令他身心俱冷的不仅是北方的酷寒,更有山河破碎、国破家亡带来的凄凉和悲愤。
“行尽穷边岁亦殚,倚门应是念衣单。宁知今日幕南地,不似去年江上寒。乘马惟欣日可爱,逢人长说雪初乾。三衾四袄半无用,何必重歌行路难”(《即事》),据《北行日录》所载推测,这首诗应大致作于乾道五年(1169)十二月二十四日前后,此时楼钥刚刚经过河北西路安肃军(今河北徐水),距离目的地已然不远,而天公也同样作美,久雪初晴,诗人的愉悦振奋之意溢于言表。然而这种心情却并未持续太久,在父亲的生辰当天,楼钥再一次被浓烈的乡愁笼罩,不由得回头凝眸,南望故土,正所谓是“客途行及五千里,寿宴须开十二楼。南望飞雪天样远,太行山外久凝眸”(《腊月二十五日大人生朝》)。
雪作为一种自然事物,并无固有的情感基调,其象征意义主要与创作者的心态有关。如果说之前的雪在楼钥眼里满是凄凉萧瑟之意,那么在归途中的这场雪则清冷通透,令人为之精神一振。“风卷清淮夜不休,晓惊急雪遍郊丘。坐令和气三边满,便觉胡尘万里收。瑟瑟江头辉玉节,萧萧马上点貂裘。归来风物浑相似,二月杨花绕御沟”(《使北雪中渡淮》)。
据《北行日录》所载推测,这首诗应作于乾道六年(1170)一月二十八日前后。楼钥等人顺利完成任务,终于回到了日思夜想的祖国,胡尘顿收,和气四生,似乎连风急浪高的淮水也变得清澈可爱起来。实际上,诗人这种兴奋的心情已经持续了很久,《初出燕山》即云:“去国三千里,还家第一程。都缘人意乐,便觉马蹄轻。落日催心速,飞云逐望生。莫嫌归去晚,犹得趁清明。”《北行日录》中也提到此前一日“过县即见龟山塔和淮山,一行已不胜喜悦矣。”可谓是归心似箭。
(二)引人慨叹的人文景观
东南虽然繁华,但对矢志北伐、还都开封的宋人来讲,始终都只是暂供落脚的偏安之地。
楼钥北行途中,脚下所踏虽名异乡实为故土,他或许此前从未来过这里,但是却早已从浩如烟海的典籍中、从师长的谆谆教诲中,深刻地了解过曾经的家园,因而当其真正身处其中,亲眼目睹这一切时,不论是耳熟能详的名山大川,还是荒草萋萋的古城旧陵,都不能不引起他心中种种复杂难言的情绪。
北使队伍离开泗州后便进入宿州,第一站是灵璧县(今安徽灵璧),这里自古至今皆以出产奇石闻名,在北宋时曾是花石纲的采集地之一。楼钥等人行经灵璧时遗迹尚存。《北行日录》载:“两岸皆奇石,近灵璧东岸尤多,皆宣、政花石纲所遗也。”花石纲之役劳民伤财,其后不到三十年,金人的铁蹄便踏破了汴京城门。当楼钥以弱国使臣的身份亲临此地,心中的悲痛与愤懑之情可想而知,于是他提笔写下了《灵壁道傍怪石》,诗云:“饱闻兹山产奇石,东南宝之如尺璧。谁知狼藉乱如麻,往往嵌空类鑱刻。长安东风万岁山,搜抉珍怪穷人间。汴流一舸载数辈,径上艮岳增孱颜。当时巧匠斲山骨,寘之河干高突兀。干戈动地胡尘飞,坐使奇材成弃物。君不见黄金横带号神运,不数台城拜三品。只今零落荒草中,万古凄凉有遗恨。木人漂漂不如土,坐阅兴亡知几许。行人沉叹马不前,石虽不言恐能语。”昔年闻名天下的奇物被随意丢弃在路边,入眼处尽是一片狼藉,而曾经那个如日中升般的泱泱帝国,也早已辉煌不在,山河沉沦,徒留遗恨。诗人驻马徘徊,心情久久难以平息,可最终亦只能化作一声长叹。眼前的块块顽石,若是可以开口说话,想来也会向人们哭诉自己悲惨的命运吧!
楼钥跟随队伍沿着汴水继续北行,这条在某种意义上承载着大宋荣光的黄金水道,如今却几乎断流,两岸的膏腴之地皆成废土,遗民同胞于严刑峻法之下忍辱偷生,眼前的一切都让他感到痛彻心扉,黍离之悲油然而起。
《北行日录》载:“行数里,汴水断流。人家独处者,皆烧拆去。闻北人新法,路傍居民尽令移就邻保,违者焚其居。”“淮北荒凉特甚,灵璧两岸人家皆瓦屋,亦有小城,始成县。”紧接着,楼钥又被道旁荒草中的一座古坟吸引了目光,其虽无碑,却有来往行人脚踏所成之路直抵冢前,可见谒者众多,四下一打听,才知道竟是虞姬之墓,他这才猛然想起,原来距此地不远,便是千年前垓下之战的遗址所在,听说城外的山坡上,仍然有祭祀汉高祖刘邦的庙祠存留。
《北行日录》载:“虞姬墓在西岸荒草中,横安二石板,相去尺余。隆兴间,我得泗、虹,以此墓为界。县外山上有从祠,高帝庙也。”与诗人时间相去不远,同样北行使金的范成大和周煇也都各自在行记中提及过此事。范成大《揽辔录》载:“庚申,过虞姬墓。墓在道左,双石门出丛草间,往来观者成蹊。”周煇《北辕录》载:“虞姬墓在西岸,虽无碑,却有村墅名。”
英雄红颜灰飞烟灭,皇图霸业皆随逝水,楼钥想起惨遭胡虏蹂躏的故国家园,心中更添沉痛之情,《灵璧道中》诗云:“古汴微流绝,余民尚孑遗。高丘祠汉祖,荒草葬虞姬。垓下空陳迹,鸿沟怆近时。膏腴满荆棘,伤甚黍离离。”其实,楼钥诗歌中的黍离之叹,常与“出使”这一情境有关,如“曾为假吏到燕山,送子长征不作难。故国能无叹禾黍,中原应欲睹衣冠。”(《送蒋甥若水使属北行》)、“经帷亲见犯天颜,口伐何劳抗可汗。故国应悲周黍稷,遗黎犹识汉衣冠 。(《送倪正父侍郎使虏》)”这样的现象既是由金国马踏中原、南宋偏安一隅的特殊历史环境所决定,也是宋代士人“大都富有对政治、社会的关注热情,怀有‘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的典型反映。
当然,漫长的旅途中楼钥也并非始终沉浸在忧郁低落的情绪里,如夜宿陈留县(今河南陈留)时,他便颇为悠闲地静卧于驿馆,窗外皎洁的月光和参天的柏树相映成趣,耳畔清风徐徐,遂生放任山水的隐逸之念。《陈留柏》诗云:“驿门深闭柏参天,月可中庭夜影圆。人静好风喧客枕,坐令归梦到林泉。”
宋诗尚平和冲淡,楼钥晚年更是极为推崇陶渊明,写了大量模仿后者的山水田园作品,其审美旨趣从此诗中或可初见端倪。
经过故都汴京时,想必楼钥心中当有更为复杂的情绪,但可惜的是竟无作于此段行程的诗歌流传下来,仅存的一首《京城外丘垅》亦是有目无辞,不过根据《北行日录》的记载,大致能够推测出它的内容。
“车行四十五里,道傍多陂塘,路颇迂回。古冢相望,发掘无疑。”金人占领汴京后四处烧杀抢掠,不惟城中百姓惨遭荼毒,就连城外的古坟旧冢都难以幸免。《三朝北盟会编》卷三十载靖康元年正月二十日,“又闻金人虏掠城北,屠戮如故,而城外后妃、皇子、帝姬坟墓欑殡发掘殆尽。”《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四载建炎元年四月,“敌之围城也,京城外坟垄发掘略遍,出尸取椁为马槽。”面对如此凄凉荒败之景,楼钥又怎会不感到愤懑痛惜呢?可想而知,《京城外丘垅》一诗不外是痛斥金虏、渴盼北伐的言志抒怀之作。
相州在今河南省安阳市与河北省临漳县一带,自商周以降而至唐宋,始终处于中原正统文化的核心地区,先贤辈出,古迹无数,当楼钥踏足此间,自是别有一番感受。
《相州道中》诗云:“千古兴亡一梦惊,就中物理似持衡。茜花空染朝歌血,荒草犹祠羑里城。但见反身知自咎,谁言修政欲相倾。知音只有昌黎操,臣罪当诛主圣明。”相州旧为殷商国都,羑里城则是周文王被拘而演《周易》之地。武王伐纣之战,死伤无数,眼前遍地盛开的茜(又作莤)花传说中乃是“漂杵余血所化”楼钥行走在古道上,心中除了慨叹兴亡之外,更多的却是联想起如今并不乐观的朝野局势,责备自己未能像韩愈那样辅佐君主,以换得政治清明和天下太平,拳拳之心跃然纸上,而在后来的仕宦生涯中,楼钥也并未辜负自己的初心,始终直言敢谏,不徇私情,在任职中书舍人时“代言坦明,得制诰体,缴奏无所回避”,连光宗皇帝都叹曰:“楼舍人朕亦惮之。”
三、结语
文学作品产生于特定的时代背景之下,也受限于一定的地理空间,这里的地理空间包括自然和人文两个方面,大至山川河湖、古城旧都,小到一草一木、亭台楼阁都在其中,它们不仅是创作者的描写对象,反过来也会影响创作本身。
楼钥素以擅写行游诗闻名,在其留存下来的大量同类作品中,使金纪行诗具有极其鲜明的特色,我们在分析時,除了要结合宋、金之际的特殊历史环境,也不能不考虑到楼钥由南入北、横跨千里的空间位置变换给诗歌创作带来的深刻影响。
注释:
①四库本、武英殿本、丛书集成本俱作“北行”,此据底本目录改。
②据闻人军《中国古代里亩制度概述》,宋代一里(营造尺)约相当于今天的556.38米。
参考文献:
[1](宋)楼钥撰,顾大朋点校.楼钥集[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
[2]曾大兴.文学地理学概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
[3]顾宏义,李文整理标校.宋代日记丛编[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3.
[4]王水照.王水照自选集[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
[5](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6](宋)李心传编撰,胡坤点校.建炎以来系年要录[M].北京:中华书局,2013.
[7](元)脱脱等.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85.
作者简介:
梁洪汀,男,土家族,湖北恩施人,文学硕士,中南民族大学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研究方向:唐宋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