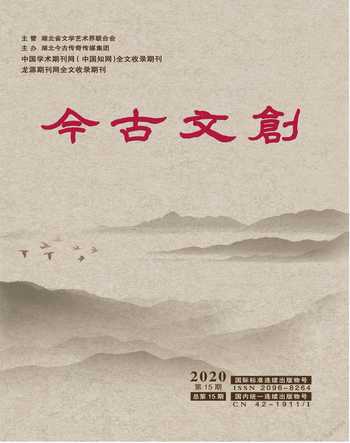从莫言《蛙》中姑姑的形象来分析生命的拯救、毁灭与救赎
【摘要】 莫言在《蛙》中对妇产科医生姑姑投射了大量的目光,通过讲述其在计划生育时代浪潮下由迎接生命的“送子观音”到扼杀生命的波澜起伏的经历,揭示了姑姑对于生命的拯救、毁灭与救赎的三个阶段,表达了她对于生命的敬畏以及时代和人性的反思,全文闪烁着对于生命强烈的人道主义关怀。
【关键词】 蛙;生命;忏悔;人性;反思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0)15-0012-02
莫言在这部作品中对作为妇产科医生的姑姑投射了大量的目光。通过讲述其在计划生育的时代浪潮下由迎接生命的“送子观音”到扼杀生命的波澜起伏的经历,揭示了姑姑对于生命的拯救、毁灭与救赎的三个阶段。作品以大时代为背景,描写了农村小人物的悲欢离合以及对于生命选择话语权的丧失,为读者揭示了一出关于“生”的疼痛悲剧。
一、迎接生命——生命的拯救
姑姑万心继承父业,成为一名民间接生医生,后来进入卫生科学习专业医学知识,由此便与医生这份职业结下了不解之缘。作为一名医生,她具备许多优秀的品质。
她无视阶级差别,为地主的老婆接生;她深知时间对于产妇和婴儿的重要性,在接到接生消息的时候总是骑着自行车从小桥上疾驰而过,有时不免使狗都受到了惊吓;她对于传统的接生婆表示痛恨并认为传统的接生方式是封建的、迷信的,一定程度上更是愚昧的,这种方式有时还会造成产妇和婴儿生命的丧失。传统接生婆接生只是为了获取物质上的利益,姑姑在陈鼻家为王胆接生时打田桂花便体现了这一点。
除此之外,姑姑内心怀有对于生命的敬畏之情,内心对于生命更是一视同仁,在她的眼里,万物皆有平等的地位,生命诚可贵。因此,她不仅为人接生,还为牛接生。当母牛舔舐着小牛身上的黏液时姑姑的口半张着,眼神很慈爱。此时的姑姑身上无时无刻不在体现着人性的光辉,她将自己的职业赋予了神圣的使命,在这个使命下她尽全力捍卫生命的尊严。
20世纪50年代国家由于劳动力短缺,经济急需要发展,因此鼓励生育。在高密东北乡,“蛙”不仅象征生育繁衍的图腾,更是吉祥物。新生儿如同青蛙一般呱呱坠地,呈现繁盛繁衍之势。那个时候是姑姑的黄金时代,她犹如送子观音一般为众人接生,只要把手往产妇的肚子上轻轻一摸,便能抚慰她们疲惫以及紧张的神经。
当时围绕在姑姑周围的不仅仅是呱呱坠地的新生命,还有成群的蜜蜂和蝴蝶。那时她被视作生命的符号,她怀着菩萨般“普度众生”的爱,为人们带去了福音与希望,对于妇产科医生的她来说,初生婴儿的哭声是世上最动听的音乐。她那个时候是极受欢迎的,作者也对生命怀有敬畏之感。
二、扼杀生命——生命的毁灭
1965年,“一个不少,两个正好,三个多了”的口号响彻贫瘠的高密东北乡。作为当地卫生所的一把交椅,姑姑无疑是帮助政府实施计划生育的最佳人选。当时农民“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观念无疑与姑姑的立场背道而驰,此时的她由生命的缔造者变成了生命的毁灭者。姑姑“送子观音”的形象在人们的心目中轰然倒塌,她的行为引起了人们的不满。因此在她执行计划生育政策时,行为遭受阻力的同时也酿造了不少悲剧。
张拳的妻子怀上了三胎,姑姑强迫其妻子引产,最终张拳妻子跳河导致大出血,由此造成了一尸两命的惨象。面对这种情况,姑姑却以一种冷酷无情的旁观者的姿态欣赏这个场面。
陈鼻的妻子王胆因为超生被姑姑追击,她为了保护女婴而四处逃亡,最终去世;主人公蝌蚪的妻子王仁美因为偷偷取下了避孕环而意外怀孕,在姑姑的逼迫下走上了手术台,最终导致一尸两命,种种血的事件都是人间悲剧。在这里我感受到了这些小人物在逼仄的生存空间维度下的无助与绝望,冷漠与暴力,一切被置于边缘化。在这部小说中,作者将女性之间的混乱、挣扎、困境以及代价描绘了出来,“死”在这部作品中不是一个形而上的悬空问题,而是一个能把一家人彻底吞噬的无底洞,一切都无解、无望、暗无天日。
在她将生命扼杀于襁褓之时,众多社会底层的女性遭受着灵与肉的煎熬与炼狱,她们丧失了生育孩子的话语权。她剥夺了生命存在的尊严,使她们的内心遭受着虐杀,尽管她们也进行了无畏的反抗,但是这种反抗却微乎其微。小人物的悲剧在作者笔下写得如此动情,作者运用朴实而有力量的文笔来描写这些女性人物,同时也给予了这些人物温情的悲悯之心。
此时姑姑的灵魂发生了畸变,她的手上沾满了鲜血——一种芳香,一种腥臭,一种崇高,一种罪恶。
三、忏悔生命——生命的救赎
晚年的姑姑并未意识到自己犯的错有多么深重,直到她有一次醉酒之后不知不觉走进了一片洼地里。月光之下,四周寂静,唯有虫鸣,她行医几十年,走过很多夜路,从来没感到害怕,但这天晚上她体会到了恐惧的感觉。那天晚上的蛙声如哭,仿佛是无数受了伤害的婴儿的精灵在发出控诉。被她扼杀掉的婴孩如同蛙一般,对她穷追不舍,神情恍惚的姑姑为此意识到了自己之前犯下的罪孽深重,她饱受精神的折磨与摧残,她害怕蛙,更足以显示出她内心深处潜藏着的恐惧。
为了赎罪,她嫁给以靠捏泥娃为生的泥塑大师郝大手。她将泥娃供奉起来,让这些泥娃产生灵性从而去他们该去的地方。她尝试用这种近乎幻想的方式寻求精神上的解脱,并祈盼在忏悔中得到灵魂的救赎,此时姑姑的人性也开始逐步复归。然而姑姑手下的得力干将——小狮子,由于年轻时候为人做引流,扼杀的孩子多了便遭到了老天的报应,因此不能生养。为了替蝌蚪家传宗接代,她不惜使用代孕产子的方式,让自己抚养过的陈鼻的女儿陈眉为自己的老公蝌蚪生育。最终,在姑姑的“帮助”下,小狮子将陈眉的孩子占为己有,但是却又酿造出了另一出悲剧——陈眉疯掉了,姑姑上吊自杀了。
如果说之前姑姑种种行为是逼不得已的,那么在一定程度上她是一個受害者,她还可以为自己的行为赋予一个合法化的理由,从而获得内心的平静。而晚年姑姑帮助小狮子抢夺陈眉孩子的行为则显示出了对于自身道德的违背以及人性的剥夺,她再一次沦为了施暴者。她忏悔的精神是可贵的,但是造成的后果却是可悲的,生命在她的手上既获得了拯救又遭到了扼杀。最终小说以九幕戏剧的形式而告终,舞台上所有看似正常的人,其实都不正常;看似不正常的人——陈眉,却最正常。小狮子、姑姑又再一次利用自己的双手将别人作为母亲权利的资格剥夺。姑姑上吊自杀失败,这也恰好侧面印证了之前姑姑忏悔的虚无和缥缈。
纵观全文,每个人物都经历了从犯罪到反思再到救赎的过程,袁腮私下为王仁美取下了节育环由此导致了王仁美意外怀孕、被迫流产以及死亡等一系列后果,后来袁腮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并向蝌蚪道歉以及向王仁美进行心灵的忏悔;陈鼻将妻子王胆视作传宗接代的生育工具,由此造成了妻子被迫流亡在外时的死亡。晚年的他以堂吉诃德般近乎疯癫的形式进行赎罪,看似愚蠢,实则只有他自己知道内心的痛苦与不堪;同样,主人公蝌蚪由于自己党员的身份不能丢,要起国家干部的带头作用,故为了前途逼迫妻子王仁美引产,结果却造成了一尸两命。最终“我”在给杉谷义人的信中说:“我渴望通过写戏剧的方式来进行自我内心的忏悔与救赎。”
然而这种忏悔方式真的有用吗?在最后一封信中,“我”对这种毫无任何实际意义的忏悔方式给予了无情的批判。 “但是剧作完成之后,内心的负罪感却未减轻半分。”由此可见,这種对于生命的忏悔是虚空的,并不可能使灵魂得到救赎。在这个基础上,人性的复归也显得极其艰难,作者对生命表达了强有力的反思。
四、小结
本雅明曾经说过,任何一部记录文明的史册无不同时又是一部记录残暴的史册。在时代洪流的浪潮中,姑姑既是天使又是魔鬼,既是施暴者又是忏悔者。然而戏谑之处便是在忏悔的过程中姑姑又成了杀人帮凶,想要赎罪却导致了更深的罪恶。她不仅是作为她这个个体而存在,她更是一个时代的象征。她代表着被时代洪流裹挟而无法依照自己的本性生活的人,时代在她的身上刻满了烙印的同时也承载了作者对于时代以及人性的无限反思。
所谓悲剧就是将美好的事物毁灭给人看,同时美好的事物在被毁灭的过程中显示出的悲剧感也得以侧面印证了它的崇高,这从一定程度上也论证了悲剧与美学之间潜藏着的关联性。莫言先生正是将社会中的小人物置于现实生活生存的空间维度下,将她们的逼仄、困苦与辛酸娓娓道来,从而使人们经历了一场深邃的阅读之旅以及一场悲剧美学的视觉盛宴。在文本中,不仅与主人公同喜同乐,更与她们同悲同泣。与此同时,这也唤起了人们心底的良知,呼唤更加关注现实。文学的真正使命在于通过它,让人感受到生命的本相,并经由文字倾听超越存在的声音。莫言正是用他特有的文字为读者展示了一副斑驳的历史画卷,从而勉励人们感受生命、尊重生命。
莫言用文字为生命潜心搭建神龛,在神龛前他自省、忏悔、祈祷。他敬畏生命,他救赎生命,他反思生命。
参考文献:
[1]李玉萍.女性意识的觉醒与历史困境——以莫言《蛙》中姑姑的形象为例[J].江科学术研究,2019,14(04):58-62.
[2]沈勇,王海珺.试论莫言《蛙》的隐喻艺术中社会矛盾的冲突构织[J].延安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9,33(03):88-91.
[3]陶倩影.论莫言《蛙》的疼痛性书写[J].遵义师范学院学报,2017,19(04):69-71+82.
[4]张嘉星.莫言《蛙》中“姑姑”人物形象分析[J].延边教育学院学报,2017,31(01):15-18.
[5]袁泓.时代的烙印——论莫言《蛙》中姑姑的悲剧[J].名作欣赏,2015(36):25-26.
作者简介:
蒋晶晶,女,汉族,山西吕梁人,学生,文学硕士,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