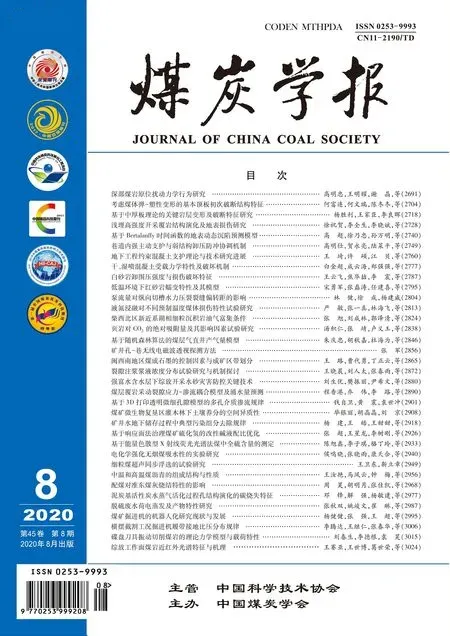干、湿喷混凝土受载力学特性及破坏机制
白金超,成云海,2,郑强强,3,李峰辉,李 波,吴 斐
(1.安徽理工大学 省部共建深部煤矿采动响应与灾害防控国家重点实验室,安徽 淮南 232001; 2.山东科技大学 煤矿充填开采国家工程实验室,山东 泰安 271200; 3.安徽理工大学 土木建筑学院,安徽 淮南 232001; 4.重庆大学 煤矿灾害动力学与控制国家重点实验室,重庆 400030; 5.重庆大学 资源及环境科学学院,重庆 400030)
喷射混凝土(简称喷砼)支护广泛应用于煤矿井巷、边坡、隧道、地铁、涵洞等岩土工程中[1]。根据喷射工艺的不同主要分为干喷、湿喷2种[2]。干喷混凝土由于成本低、工艺简单等,在我国广泛使用,但干喷混凝土也一直存在粉尘大、回弹率高、强度低、均质性差等弊端[3],喷层易出现开裂、剥离、片落等问题,威胁人身安全,特别在软弱岩层、大断面、高应力、高温、淋水或涌水、施工扰动的复杂工程环境中,干喷混凝土支护的上述问题更加严重。为了解决干喷混凝土支护存在的上述问题,近年来国家积极发展湿喷混凝土支护技术,相比于干喷混凝土,湿喷混凝土粉尘小、回弹率低、强度和均质性均有所提高,支护效果得以改善[4-5]。
目前许多学者采用多种手段对混凝土失稳机制进行了研究。田威等[6]应用CT扫描技术对混凝土破裂过程进行了细观试验研究,着重探索了混凝土材料细观损伤演化规律;邓明德等[7]利用红外遥感技术研究混凝土在单轴加载直至破坏的全过程,得出了红外辐射能量随压力变化而显著变化的实验规律;于庆磊等[8]采用数值模拟方法对不同受力条件下混凝土破坏过程进行了研究,得到了复杂应力状态下非均匀混凝土材料中的裂纹扩展过程。
国内外也有很多学者利用声发射(Acoustic Emission,以下简称AE)监测技术研究混凝土的破裂过程,并得到了许多研究成果。如SCHIAVI A等[9]根据混凝土在单轴压缩实验中产生的高频信号(AE)和低频信号(ELEs),研究了混凝土试件的损伤过程;OHTSU M和CARPINTERI A等[10-11]应用声发射技术对混凝土结构的损伤程度进行了监测;刘茂军等[12]对比研究了不同强度等级及不同碳化龄期混凝土单轴受压的AE特征,得到了随应力的增加AE活性急剧增加点明显前移的规律;尹贤刚[13]对受载岩石与混凝土AE特性进行了对比试验,指出两者在加载临近峰值强度时均有明显的“耗时”现象;张亚梅等[14]对普通混凝土和橡胶混凝土弯曲的损伤区域进行研究,发现了混凝土强度、脆性与AE活动的联系。以上是利用AE监测深入研究喷混凝土的重要基础。但是针对2种试样不同作用机制,喷层开裂、剥离和片落的损伤机理即不同喷混凝土的力学特性与破坏规律、支护性能与支护理论等缺乏研究,指导工程设计的依据落后于工程实践。
笔者团队在北京地铁16号线安家河段(2014)、广州地铁交换站(2018—2019年)等工程进行了相关试验。采用实验室试验与AE监测相结合的方法,着重研究2种试样力学特性和基于定位监测破裂分析的破坏机制。
1 2种试样力学试验
1.1 试样制作
试验材料为:P.C42.5R的水泥,粒径为5~12 mm的碎石,细度模数大于2.5的中、粗砂以及速凝剂(干喷为粉状铝酸盐速凝剂,湿喷为无碱液体速凝剂)。其中水灰比为0.5,水泥∶砂子∶石子=1∶2∶2,粉状铝酸盐速凝剂∶水泥=0.035∶1,无碱液体速凝剂∶水泥=0.06∶1[4]。
根据《岩土锚固与喷混凝土支护工程技术规范(GB50086—2011)》规定:检验喷混凝土强度的标准试块应在不小于450 mm×450 mm×100 mm(长×宽×高)的喷混凝土试验板上,用切割法或者钻芯法取得。大板尺寸为500 mm×500 mm×100 mm,如图1(a)所示。喷制大板过程如下:
(1)在作业面附近,将模具敞开一侧朝下,以80°(与水平面的夹角)左右倾斜置于墙脚。
(2)在模具外的边墙上喷射,待操作正常后将喷头移至模具位置,由下而上逐层向模具内喷满混凝土。
(3)将喷满混凝土的模具移至安全地方,用三角抹刀刮平混凝土表面。
(4)在潮湿环境中养护1 d后,脱模(本次采用洒水养护),在巷道内养护28 d后运至地面。现场喷射的大板如图1(b)所示。
根据《岩土锚固与喷射混凝土支护工程技术规范》GB50086和《普通混凝土力学性能试验方法标准》GB/T 50081规定的试样尺寸,对养护好的大板在石材切割机上切割成各试验所需尺寸,其中抗压强度、轴心抗压强度、劈裂抗拉强度试验试样各取6个,共计18个。试样尺寸分别为100 mm×100 mm×100 mm(长×宽×高)、100 mm×100 mm×300 mm(长×宽×高)和50 mm×50 mm(直径×高),如图1(c)所示。
1.2 试验内容及测试方法
在实验室利用RMT岩石力学试验机对2种试样分别进行6组单轴抗压试验、轴心抗压试验和巴西劈裂试验,试验加载速度为0.3~0.5 MPa/s。该系统可跟踪记录实时应力、应变值的大小,并可导出以时间为自变量,应力、应变等为变量的原始数据。此外,采用美国贯入法混凝土强度检测仪ASTMC803-82分别测试了2种试样2 h龄期的强度,每组测点为6个。该混凝土强度检测仪依据标准贯入阻力的原理进行测试,采用压缩弹簧施加载荷,把一钢制测钉贯入混凝土中,依据测钉贯入的深度来判定混凝土的强度。
1.3 试验结果分析
分别选取试样5抗压强度试验、试样2轴心抗压强度试验和试样3巴西劈裂的试验数据,绘制应力-应变曲线,分别如图2~4所示。28 d两种试样各试件的单轴抗压强度、轴心抗压强度、巴西劈裂强度及2 h龄期强度测试结果见表1。

图4 试样3两种试样抗拉强度应力-应变曲线Fig.4 Stress-strain curves of specimen No.3 of dry shotcrete and wet shotcrete under Brazilian tensile test
由表1可知,干喷混凝土7个测点的2 h龄期的强度平均为0.7 MPa,而湿喷混凝土2 h龄期早期强度平均为1.19 MPa,相对于干喷混凝土提高了70%,大大提高了喷混凝土的早期强度。而湿喷混凝土的早期强度的提高,可以快速增强巷道围岩的稳定性,避免混凝土的开裂、剥落,从而更好的适应巷道围岩的变形。此外,6组28 d湿喷混凝土试样的单轴抗压强度、轴心抗压强度和劈裂抗拉强度平均值分别为31.8,22.5和5.90 MPa,而对应的6组28 d干喷混凝土试样的单轴抗压强度、轴心抗压强度和劈裂抗拉强度平均值分别为20.9,15.3和3.17 MPa,湿喷混凝土试样相对于干喷混凝土试样的单轴抗压强度、轴心抗压强度和劈裂抗拉强度分别提高了52.15%,47.06%和86.12%。由此可知,湿喷混凝土的最终强度与干喷混凝土相比也显著增强,故湿喷混凝土长期支护强度明显大于干喷混凝土。湿喷混凝土的力学性能不仅在早期有明显的增强,对于长期力学性能也有显著提升,有利于控制变形。
如图2,3所示,2种试样在单轴加载和轴心加载下应力-应变曲线与脆性岩石在相同加载形式下的类似,都经历了压密阶段、弹性阶段、塑性阶段和峰后破坏4个阶段。

图2 试样5两种试样单轴抗压应力-应变曲线Fig.2 Stress-strain curves of specimen No.5 of dry shotcrete and wet shotcrete under unconfined compression test

图3 试样2两种试样轴心抗压应力-应变曲线Fig.3 Stress-strain curves of specimen No.2 of dry shotcrete and wet shotcrete under axial compression test
2种试样的巴西劈裂试验的应力-应变曲线如图4所示,在抗拉强度峰值应力之前,应力-应变成线性关系,达到峰值应力之后,混凝土试样劈裂破坏,强度立即降为0。整个过程的应力-应变曲线与岩石的巴西劈裂试验的应力-应变曲线类似。因此,2种试样的力学变形性质与岩石类似,可以看成脆性岩石进行分析。
最后,为了比较2种试样的均质性,分别计算4种试验各强度的方差,计算结果见表1,表明:干喷混凝土28 d龄期单轴抗压强度、轴心抗压强度、劈裂抗拉强度及2 h龄期早期强度方差均明显高于湿喷混凝土,说明干喷混凝土强度离散性明显大于湿喷混凝土,干喷混凝土均质性较差,而湿喷混凝土均质性明显提高。
综上所述,2种试样的力学变形性质均与岩石类似,进行相关分析和处理时可以等同于岩石。湿喷混凝土无论是早期强度、最终强度还是均质性都大于干喷混凝土,由此表明湿喷混凝土支护效果好于干喷混凝土,但2种试样在载荷作用下内部空间裂纹萌生、扩展、贯通的演化机理尚不清晰,本文通过2种试样单轴压缩的AE试验,根据试样的AE信号特征和定位技术,研究2种试样的失稳破坏过程。
2 干喷与湿喷混凝土单轴加载AE试验
2.1 试样制作
试验大板的制作与前述大板制作方法一致,试样制作完成后运至实验室进行钻芯取样、双端面磨平,加工成尺寸为50 mm×100 mm(直径×高)的试样,如图5所示。加工2种试样每组各6个试验试样,分别编号为G-1~G-6,S-1~S-6。

图5 试样制作过程Fig.5 Preparation process of specimens
2.2 试验内容及测试方法
试验采用加载控制系统与AE监测系统2套装置。试验加载在RMT岩石力学试验机进行,该系统可跟踪记录实时应力、应变值的大小,并可导出以时间为自变量,应力、应变等为变量的原始数据。AE监测系统具有自动存储、计算AE各种参数的功能,如图6(a)所示。AE信号采集时采用8个传感器,固定于试样表面,实现对AE信号的实时监控和三维定位,传感器布置如图6(b)所示。

图6 AE试验示意Fig.6 AE test schematic
为保证AE传感器与试样良好接触,增强AE测试效果,使用凡士林作为耦合剂,将AE传感器粘贴于试样表面,并用橡皮筋进行固定。试验前,先以铅笔芯为模拟源进行预试验,检查其对信号源的响应程度,同时排除外部的撞击、摩擦等机械噪音的干扰,调试正常后再开始试验。试验时,单轴加载试验和AE试验同时进行,加载系统采用轴向位移控制加载,加载速率为2×10-6m/s。加载系统自动记录力学试验过程参数,AE仪器内部所配软件通过对8个传感器接收到的信号进行处理,得到红色AE源定位标记。
2.3 试验结果分析
2.3.1应力、撞击数、能量与时间关系
选取AE参数中具有代表性的撞击数和能量参数,分别反映AE信号的活度和强度。AE一个通道上所探测到的AE信号数量称为撞击数,用于评价AE活动。AE能量是表征信号源强弱的特征参数,根据试验数据分别做出干喷混凝土试样G-3和湿喷混凝土试样S-3的应力、撞击数、能量与应变的关系图如图7所示。

图7 G-3和S-3试样的应力、撞击数、能量与应变的关系Fig.7 Relation between stress,hit number,energy and strain of G-3 and S-3 specimen
由图7可知,干喷混凝土G-3试样和湿喷混凝土S-3试样在单轴压缩下破裂过程中AE信号基本特征一致,可划分为3个不同的阶段。第1阶段为初始压密阶段(图7中Ⅰ阶段),大约在峰值应力的0%~20%,此阶段AE比较活跃,但AE信号强度比较低。AE信号主要来源于初始缺陷的闭合效应及少量的微破裂。但在Ⅰ阶段中干喷混凝土G-3试样的撞击数明显大于湿喷混凝土S-3试样的撞击数,说明G-3试样的初始缺陷明显多于S-3试样,可能是由于干喷作业时干料输送到喷头处与水接触时间短暂,水灰比极不稳定,混凝土混合不均匀导致的。此外,干喷混凝土G-3试样和湿喷混凝土S-3试样Ⅰ阶段的AE特征也验证了前面力学试验得出的湿喷混凝土的均质性明显好于干喷混凝土的结论。第2阶段为AE平静阶段,大约在峰值应力的20%~80%(图7中Ⅱ阶段),此阶段两试样的AE特征基本一致,均为AE活动性明显减小阶段,且变化不大,AE能量仍然较低。说明在此阶段试样内初始缺陷已经压密,内部微裂纹处于相对稳定和缓慢发展阶段。微裂纹由第1阶段在骨料与水泥的黏结面上扩展延伸到骨料和砂浆[15-16],但由于骨料强度较高,裂纹尖端的应力集中尚不足以使其产生裂纹,限制了裂纹扩展,试样内积聚能量。第三阶段为AE增长阶段,大约在峰值应力的80%后(图7中Ⅲ阶段),此阶段AE活动性迅速增大,当荷载增加到峰值应力时,主裂纹迅速贯通,AE能量突然增大,之前积聚的能量瞬时释放,造成试样破坏,试样宏观破坏后,AE能量和撞击数逐渐减小。干喷混凝土G-3试样的峰值后应力较湿喷混凝土S-3迅速降低,这是因为湿喷混凝土具有较好的均质性缓解了裂纹尖端的应力集中,裂纹的汇聚和扩展较缓慢。而干喷混凝土在荷载达到峰值应力时,由于其自身均质性较差,其主裂纹迅速贯通,承载能力快速下降,表现出明显的脆性破坏特征。这也是干喷混凝土经常出现喷层易开裂、剥离、片落等问题的主要原因。
2.3.2AE事件定位结果与分析
图8和9分别为2种试样各试样处于不同应力状态时AE试验定位结果。

图8 干喷混凝土G-1~G-4试样破裂过程中AE试验的定位结果Fig.8 AE events location results of G-1,2,3,4 specimens of dry shotcrete

图9 湿喷混凝土S-1~S-4试样破裂过程中AE试验的定位结果Fig.9 AE events location results of S-1,2,3,4 specimens of wet shotcrete
从图8可以看出,干喷混凝土试样在峰值应力的0~10%时,试样内的AE定位分布规律呈现一种离散、无序、随机的出现方式。当载荷超过0.35σc之后,试样内部AE定位事件明显开始向局部区域集中,说明此处试样内部已经产生了初始裂纹,出现明显的应力集中现象。同时从加载试样也可以看出,当载荷为0.70σc时试样表面应力集中部位出现肉眼可见的细小裂纹。此后,当荷载达到σc时,试样内的AE定位事件数明显增加,并沿主破裂面快速扩展直至内部裂纹全部贯通,最终在AE定位事件集中区域出现明显的贯通裂纹,如图10所示。而从图9可以看出,湿喷混凝土试样在整个加载压缩过程中AE定位事件均未出现明显的局部集中区域,且当达到峰值载荷σc时,AE定位事件仍呈离散分布,未集中在某一区域,说明湿喷混凝土均质性优于干喷混凝土。
对比干喷混凝土G-1~G-4试样破坏AE定位图8和湿喷混凝土S-1~S-4试样破坏AE定位图9可得出:
(1)在低荷载作用下(0.10σc以内)干喷混凝土产生的AE定位事件明显多于湿喷混凝土,而由于这一阶段加载荷载很小,混凝土内部产生新裂纹的可能性较小,主要由于原始缺陷的闭合效应及极弱裂隙扩展导致。由此说明干喷混凝土内部原始缺陷明显多于湿喷混凝土,该结果与图7得出的2种试样Ⅰ阶段AE信号特征一致。
(2)干喷混凝土试样AE定位事件主要集中在某一区域内,出现了明显的空白区,而湿喷混凝土AE定位事件大多呈离散分布,试样内没有出现AE定位事件的空白区。由此可见,干喷混凝土均质性很差,加载破裂过程中试样内部应力分布不均,容易出现应力集中区域,应力集中区域易发生微破裂,形成AE定位事件集中区,而在应力水平较低的区域易形成AE定位事件空白区。在应力集中区微破裂快速扩展直至裂纹全部贯通,试样失去整体承载作用,这也是干喷混凝土强度低的主要问题,而湿喷混凝土均质性较好,加载破裂过程内部应力分布较均匀,微破裂比较分散,抵御载荷能力增强,湿喷混凝土强度较干喷混凝土明显提高。该结果与前面得出的2种试样力学性质一致。造成2种试样均质性差异大的主要原因是干喷混凝土干料在喷头处与水短暂接触,水灰比不稳定,喷射前未与水充分拌合,而湿喷混凝土在喷射前骨料、水泥、水经过充分搅拌,试样拌合均匀。
(3)干喷混凝土试样内部定位事件比较集中,实际主破裂往往出现在AE定位事件集中区域,如图10所示。而湿喷混凝土AE定位事件呈离散分布,湿喷混凝土均质性较干喷混凝土为好,抗压强度和抗拉强度均高于干喷混凝土,当试样内部发生损伤时微裂隙的扩展也较干喷混凝土缓慢,且裂隙的长度和宽度也相对较小,因此裂隙贯通的概率也较小,完整性相对较好且呈离散分布,而干喷混凝土则较为集中,由此得出基于破裂分布的破坏机制。
3 破裂能量的损伤变量与损伤比较
3.1 损伤变量的确定
20世纪50年代末,H RUSCH[17]首次将AE技术应用到混凝土研究中,并指出混凝土试样凯撒效应仅存在于极限应力的80%以下的范围内。自此国内外很多学者开始关注并开展混凝土试样的AE特征研究,如文献[18]研究了混凝土试样破裂全过程的AE特征,探讨了频谱特征、能量变化、AE试件计数率等与试样失稳破坏过程各阶段的对应关系;文献[19-22]论证了AE事件累计计数、撞击数和信号幅值可以很好描述试样损伤破坏过程;文献[23-24]考虑不同AE信号达到时间不同对混凝土结构中的损伤进行定位;文献[25-26]利用AE对混凝土的破坏机理进行了研究,通过AE信号区分混凝土的破坏模式。
前人研究得到AE信号的变化与损伤具有一致性,能直接反应试样内部的损伤,故可利用AE参数来衡量混凝土损伤程度[27]。
AE能量是AE信号的量化体现,可综合反映AE振幅、振铃计数等AE信号参数。通过AE能量去分析试样的力学性能更为直观和更有说服力。
定义损伤变量D为断面上微缺陷面积Ad与无损时断面面积A的比值,即D=Ad/A。
假定试样无初始损伤,截面面积为A,截面完全破坏时累积AE能量为Nm,则单位面积微元破坏时的AE能量为:n=Nm/A。
受压过程中,混凝土截面为Ad时,累积AE能量为:N=nAd=NmAd/A。
联立上述关系式可知N-D关系,即D=N/Nm。根据N-D关系式,求AE累计能量与总累计能量比值,可得D随轴向应变ε的变化关系曲线。
3.2 损伤变量拟合与分析
根据图11,12拟合试验数据,得到关系式,比较2种材料的损伤。为更具代表性,进一步对图11,12应力应变曲线对应的损伤变量进行拟合。

图11 干喷混凝土损伤变量、应力与应变对应关系曲线Fig.11 Relationship between damage variable and stress to strain of dry sprayed concrete

图12 湿喷混凝土损伤变量、应力与应变对应关系曲线Fig.12 Relationship between damage variable and stress to strain of wet sprayed concrete
由干喷混凝土拟合得到近似关系式:
lnDG=-exp[-a(ε-b)]
其中,a,b与干喷混凝土内部损伤有关,a=2.389,b=0.475;DG为干喷混凝土的损伤变量。
由湿喷混凝土拟合得到近似关系式:
其中,c,d与湿喷混凝土内部损伤有关,c=0.324,d=0.690;DS为湿喷混凝土的损伤变量。
分别对关系式进行求导,得一阶、二阶导数:
干喷混凝土:
D′G=DGaexp[-a(ε-b)]
D″G=a2DGexp[-a(ε-b)]{exp[-a(ε-b)]-1}
湿喷混凝土:
D′S=d-1(1+exp[ε-c)/d)]-2exp[(ε-c)/d]
结合损伤变量、应力对应变的曲线和数学关系表达式,讨论2种试样损伤变量与力学性能指标之间的关系及二者的共性与不同。从数学表达式入手讨论,能从视觉感性认识转化到数学表达式上的理性认知。
3.2.1喷射混凝土破裂一般规律
(1)在2种试样损伤变量、应力对应变的曲线中,以损伤变量表示的AE能量与应变变化有明显的对应关系,两者的一阶导数均大于0,则表示随着应变的增加损伤变量均呈增大的趋势,这是由于随着应变的增加,2种试样内部都经历由最初的初始缺陷的闭合效应及少量的微破裂,到裂纹缓慢发展阶段,再到主裂纹贯通造成试样的宏观破坏这3个过程,同时试样内部表征损伤的损伤变量也在逐步增大。
(2)分析2种试样损伤变量的二阶导数可知,当εG=b和εS=c时,两者的二阶导数均为0,即曲线均出现拐点,这是由于干、湿混凝土应变分别达到b,c时,其裂纹扩展开始慢慢向裂纹贯通发展。
在2种试样试验中,以损伤变量表示的AE能量随应变的增加而增大,且均经历初始缺陷闭合效应、裂纹发展阶段和裂缝贯通3个阶段,两者均在各自特定的应变下试样内部裂纹开始逐步贯通。
3.2.22种试样损伤特性
(1)应力应变曲线出现拐点的坐标不同,这是由于湿喷混凝土的单轴抗压、轴心抗压和劈裂抗拉强度均高于干喷混凝土,其峰值应力所对应的峰值应变也较大,当裂纹扩展至贯通时,湿喷混凝土所对应的应变要大于干喷混凝土。
(2)2种试样损伤变量、应力应变对应关系拟合曲线上拐点左侧的变化率不同,干喷混凝土的增长率较湿喷混凝土的增长率大,这是因为干喷混凝土干料在喷头处与水短暂接触,水灰比不稳定,喷射前未与水充分拌合,其内部初始缺陷较多均质性较差,从而导致内部颗粒间黏结强度比湿喷的低,在初始外力作用下若颗粒间的黏结键破坏,应力将向其他颗粒间黏结键缓慢转移,破坏就进一步增加,因此在荷载作用下的初始阶段,干喷混凝土的AE事件撞击数较多,对应的损伤变量大,增长率也比湿喷混凝土的快。而湿喷混凝土在喷射前骨料、水泥、水经过充分搅拌,试样拌合均匀,均质性较好,试样内部颗粒间黏结好,黏结强度也较干喷混凝土高,且初始阶段荷载较低很难达到湿喷混凝土内部的黏结强度,试样的整体性也较好,因此湿喷混凝土的损伤变量较低,增长率也稍慢。拐点右侧湿喷混凝土损伤变量增长较快的原因是试样此时承受的荷载较大,颗粒间的黏结键开始破坏并迅速将应力向其他颗粒间集中,使得裂纹从萌生到贯通经历的时间较短,损伤变量增大且增长率高。而干喷混凝土由于均质性较差,初始阶段颗粒间的黏结键就已经开始逐渐破坏,裂纹缓慢发展,当进入裂纹贯通阶段时,裂纹已经发育完全只差贯通,因此所需能量比湿喷混凝土小,损伤变量增长率也稍慢一些。由此说明湿喷工艺的优越性。
4 结 论
(1)得到了不同龄期干、湿喷混凝土不同强度特征、均质性显现特征,以及单轴压缩下破裂过程中AE信号特征,说明了干喷混凝土延性弱于湿喷混凝土、更易产生脆性断裂的破裂机理。
(2)以损伤变量表示的AE能量与应变变化有明显的对应关系,干湿喷混凝土损伤变量随着应变的增加呈增大的趋势,但是在应变达到峰值应变前,湿喷混凝土损伤变量的增长率小于干喷混凝土,而在达到峰值应变之后,情况则相反。
(3)建立的干、湿喷混凝土损伤变量本构模型,计算曲线与试验曲线拟合度较高,能够为喷射混凝土支护设计和分析提供一定理论支撑。
致谢本研究团队成员田厚强、牛西安、邹成松、任禹、王维德等对论文撰写做出了贡献,在此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