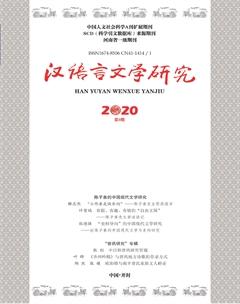“工作着是快乐的”
解志熙
摘 要:本文从陈子善先生关于现代文学文献史料的研究、现代文学的治学旨趣及其主办的现代文学研究刊物等方面,扼要介绍了陈先生40余年的学术业绩及其成就。
关键词:现代文学文献;现代文学研究;《现代中文学刊》
三月初,偶然得到消息说,陈子善兄即将光荣退休,华东师大中文系将为劳苦功高的子善兄举办一个小型的荣退仪式和文献史料研讨会。我虽然是一个怕出行、寡交游的懒人,但子善兄却是我极爱重因而乐于交往的好朋友,值此际会,欣然向往!所以闻讯后,立刻向透露消息的人表示,我自掏腰包也要去看望子善兄,幸而得到华师的惠允,颇快慰于此行也!
子善兄是现代文学研究界公认的文献史料大王,人所共知的学术劳动模范。数十年来,他在现代文学文献史料研究上,坚持不懈,劳苦功高,经他之手发掘出来的文献史料,数量之巨、质量之高,让人数不胜数,堪称海量,这大大丰富了中国现代文学的遗产宝库,也成为一代代现代文学研究者共同利用的“公共资源”——毫无疑问,每个研究现代文学的人,都受惠于子善兄发掘的文献,没有哪个人敢说自己从未分享过子善兄的成果。子善兄的劳绩显著地促进了現代文学研究水平的提高和学风的改变。但子善兄长期以来却是“无名英雄”,甚至得不到应有的待遇和公正的评价,记得2003年北方学界向子善兄学习、在清华举办了一次小型的“中国现代文学的文献问题座谈会”,与会的学者如孙玉石先生、刘增杰先生、钱理群先生都纷纷为子善兄鸣不平,一致赞誉“子善之善、善莫大焉”,足见公道自在人心。
子善之善表现在文学趣味上是开阔宽容,颇有“泛爱众”之风度。子善是“文革”后期在大学时参与《鲁迅全集》校注从而走上文献研究道路的,但子善不像许多鲁迅研究者那样,从此以鲁迅之趣味为趣味以致以鲁迅之是非为是非,他对现代文学保持着广泛的爱好和兴趣,持之以恒地发掘了形形色色的现代作家佚文,而又以其博闻多识为资,深入细致地考订了那么多复杂的文学关系和文学史实,显著地推进了现代文学问题的考证学之研究。比如,梁实秋和陈西滢都是鲁迅狠狠批判过的作家,而子善兄很早就发掘了二氏的大量集外文,让他们重新站立在中国文坛。当然,子善兄很尊重鲁迅,但他遇到鲁迅与他人矛盾的问题,总是力戒偏听偏信,而以文献史料为据,细致考证纷争纠葛的真情实际,努力做出实事求是的分析。比如鲁迅与林语堂二人在1929年8月28日的一场饭局上闹翻了,鲁迅当日的日记有记云:“席将终,林语堂语含讥刺。直斥之,彼亦争持,鄙相悉现。”鲁迅研究界向来惯以鲁迅之是非为是非,对林、鲁矛盾的评判就不免偏向鲁迅了。在我的印象中,记得是子善兄最早注意到重出江湖的林语堂日记,看到其中有“八月底与鲁迅对骂,颇有趣,此人已成神经病”之记载,从而还原了事实之真相——鲁迅由于疾病与性格的原因,不免敏感和褊急,误解和迁怒于人的事也是有的,他到底是人而不是神。而子善兄则天生有一副好性情和好兴致,不仅爱现代作家作品,而且喜欢港台文学,还有出版史、初版本、毛边本乃至音乐,快乐地搜集和书写着,其广博无人能及,考证精审而持论宽和,从不偏激。
子善之善,还在于他有一副学术为公的好心肠。他发掘了那么多文献史料,无保留地供学界采用,而别人用了他提供的文献,往往有意忽略不提他,子善却从不计较,无怨无悔!后来子善兄又亲力亲为、接办了《中文自学辅导》,倾心将它打造成一个以发表现当代文学文献史料研究为特色的《现代中文学刊》。在子善兄的努力下,这个刊物已成为最受学界关注和欢迎的现当代文学文献史料研究专刊。子善办刊物,没有那种等米下锅、爱来不来的官办作风,也无意把它视为个人趣味和小圈子的自留地,他既秉持学术为公之心,又能广结善缘,且不辞辛苦,常常风尘仆仆于南北道上,深入会场书斋拉稿子——每听到某地某人手头有好稿子,他就立即出动,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直到对方乐意交付《现代中文学刊》而后已。因此,这个刊物才办得越来越有生气,内容越来越丰富,稿源则源源不断。这在当代学术刊物出版史上,绝对是绝无仅有的善举。我自己就是深受子善善意感动的一位。记得2010年岁末,我突然发现诗人卞之琳的百年诞辰被忘记了,于是匆匆就近召集在京的部分学界朋友,在清华举办了一场小型的“纪念卞之琳百年诞辰座谈会”,并与陈越君匆匆编录了一份以卞之琳佚文为主的“卞之琳研究资料”,供朋友们参考。这个短短一天的座谈会,是悄悄进行的,不知道子善兄是从哪里得到消息,他很快就北来找到我,恳切地要我把卞之琳的佚文资料一并交给《现代中文学刊》发表。后来再见到子善兄,他也总不忘要稿子,并且希望我推荐学生们所写的比较合适的稿子给学刊发表,我的学生们也因此受惠不少。不待说,在国内外受到子善兄惠顾约稿的学者和学子们,还有很多很多。毫无疑问,子善兄这样做,并非由于“乐善好施”之人情而是出于繁荣学术之公心,这种公心在当今学界是罕见的。
子善之善,还在于他辛勤耕耘、乐此不疲地劳作数十年,却从不计较什么学术名利,也从不讲究什么学术门户。郑子瑜先生说:“阿英之后有子善。”这是很高的评价了,但郑子瑜先生说这话的时候,子善兄还是“中青年学者”吧,后来的发皇以致广大,郑子瑜先生不及见也。如今回头看,子善兄从事现代文学文献史料研究已逾40年,其搜求之勤、发掘之多、考订之精、涉猎之广,自有现代文学研究以来,一人而已!当文献史料研究得不到公正评价的时候,子善不以为悲,而近些年来文献史料研究渐受重视和肯定,子善也不因此而倨傲,他主持的《现代中文学刊》也同样重视阐释性的论作。我记得有一次见他,忍不住为他鸣不平,子善兄却全然不以为意,淡然说:“没关系的,活总得有人干啊!”正唯有平和通达的心态和尽其在我的精神,所以子善兄总是乐陶陶地干活不迭、搜求不已、努力不辍,并且在办刊上坚持兼容并包、论说与文献并重的方针。子善兄在学术上的确是没有门户派别之见的,所谓理论派、史料派之高下或者京派与海派之好歹,在他那里都是无须计较、不必轩轾的,这一点非常难得。每与子善兄聊及学术,见人有一得之善,他必称许之,人有不善,则必默而宽容,他总是看到别人好的一面,从不以己所长而轻人所短,也从不与人争短长。子善兄的这种宽厚包容的雅量和超越派别门户的涵养,是最有助于促进学术共同体共同发展的善意。
上世纪50年代,女作家陈学昭写了一部小说,名为《工作着是美丽的》。“工作着”是否就一定“美丽”,我不敢确信,我更欣赏那时也很流行的另一句话——“工作着是快乐的!”说来,人生最无聊的恐怕就是饱食终日、无所用心、无所事事,所以英雄无用武之时的陶侃才会每天搬出搬进一些砖头,给自己找点活儿干,免得无聊也。其实,所谓“工作着”也就是有活儿干,而况能有自己喜欢的活儿可干,岂不快哉!古语云“仁者寿”,子善兄乃是真正的仁人君子,刚过七十的他虽然光荣退休了,但我坚信他必定是一个长寿人。可以肯定,在现在和将来的相当长一个时期,子善兄的身体还是会棒若往常、精干如昔的。因此,退休对子善兄来说绝非学术工作的收束,而必定会有一个新的开始和进一步的发舒。不难想象,对子善这样一个真正闲不住的人来说,总有干不完的活,而他又是那么爱干活、会干活,则荣退后过得快乐是必定的。对此,我坚信不疑。谨祝子善兄康健长寿、晚年快乐、善上加善!
2019年3月15日草于清华园之聊寄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