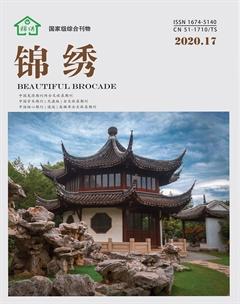李箱作品《翅膀》中自白的表达及思想意识的转变
朱卿
摘 要:20世纪30年代的韩国处于社会剧变期,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对当时的文学创作产生了直接或间接影响。30年代的韩国文学在韩国近现代文学史上占有至关重要的地位,同时也是韩国文学转型的关键时期。如若考察韩国20世纪30年代的文学场,笔者认为不可回避的便是被众多学者所关注的、在韩国文坛至关重要的作家——李箱。本文以李箱的代表作《翅膀》为中心,考察了李箱作品中用怎样的方式进行自白的表达的同时,又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争取自由和解放,以及“我”的思想意识的变化。
关键词:李箱;《翅膀》;自白的表达;自由;思想意识
一、引言
文学作为反映政治较为灵敏的一种表现形式,成为我们研究韩国近现代发展史不可忽视的重要工具之一。众所周知,20世纪30年代的韩国由于长期受日本帝国殖民主义统治肆虐,以致整个韩国到处充满了贫困、饥饿、监视、恐慌和迫害;同时,韩国知识分子的受压迫感和绝望感亦日益加深。基于此,如若选取一人来考察30年代的韩国文学的话,笔者认为,不可规避的便是——年仅27岁便离开人世的文学鬼才——李箱(本名金海卿)。至今,在韩国具有重要分量的文学奖项——李箱文学奖,便是为纪念李箱而设;韩国著名诗人、文学评论家金起林曾评价说:“他死后韩国现代文学倒退了半个世纪”[1],尽管这般评价有些夸张,但可以看出李箱在韩国现代文坛是举足轻重的人物。因此,本文拟以李箱最具代表性的作品《翅膀》(1936年9月,發表于《朝光》)为中心进行分析研究,旨在从多个角度探求作品中展现的主人公自白的表达及其思想意识的转变过程。
二、自白的表达:真实的揭露
《翅膀》是以第一人称“我”写就的。然而,对于男性主人公“我”而言,“我”的存在并不是普遍父权制下作为主体的存在,而是无任何经济来源和社会活动、“像鸡和狗一般一声不吭地吃着给我的食物”,之于妻子是“驯顺的身体”、自愿被奴役的存在。与之相反的则是主人公的妻子“莲心”:虽然是妓女,但对于主人公来说拥有绝对的优越性和控制力。对于20世纪30年代的韩国社会来说,殖民统治下的父权制传统依旧不可动摇,女性是男性的附属品,男性占主体地位。然而,李箱笔下设定的“我”则是过着男女性完全颠覆的生活。
小说开篇便描述“我”是“剥制了的天才”,是“愉快的”。意味着“我”是有能力的天才,但处在不能活动的处境中,然而却为之感到愉快。显然,这里是一种自嘲亦或是反讽。
18株盛开的鲜花中,我的妻子是最美丽的一株;在这进不来光的白铁皮屋檐下,无论她走到哪里都是绚烂夺目的。因此,我守护着这株花——不对,被这株花所束缚的我自然是难以形容的、令人尴尬的存在。[2]
上述引文中可以看出,主人公“我”本以为可以保护妻子,却在妻子的控制中生存。而这一叙述同样与“剥制了的天才”相照应:身为丈夫在男权至上的父系体系中本应具有不可撼动的权力地位,然而主人公却是软弱无能的、完全处于一种劣势,可见“天才”实则是对“我”亦或是主人公背后的作者李箱自身的一种自嘲,甚至是对当时知识分子在殖民统治下“被剥制” 的一种反讽。因此,李箱用这样颠倒的方式设定“我”的目的是什么?为什么“我”的处境有别于30年代被固定化的社会规范所规定的大部分男人的处境?
在笔者看来,这是李箱有意为之的结果,是作者借主人公“我”的一种自白;同时,“我”的存在亦不是“剥制了的天才”般的存在,而是现实中的小丑和傻瓜。正如巴赫金所说:“小丑、傻瓜在自己周围形成了特殊的世界、特殊的时空体……他们有着独具的特点和权利,就是在这个世界上作外人,不同这个世界上任何一种相应的人生处境发生联系……他们看出了每一处境的反面和虚伪。因此他们利用任何的人生处境只是作为一种面具。”[3]主人公的房间是照不进阳光、封闭的空间,而就在这样的空间中他享受着躲在被子里思考各种问题,喜欢因封闭而安逸的“绝对状态”。值得注意的是,在“我”的周围形成了特殊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我”反复研究妻子的职业,通过细致地描述妻子的一系列活动——来客、外出、获得钱、在晚上等——不难发现妻子实际上是妓女。然而“我”却始终没有得到答案,就像是傻瓜无私心的天真和正常的不理解。恰是基于此,“我”不停地思考和观察仿佛成为了作者利用“我”傻瓜的形象细致地公开妻子的个人生活,揭露殖民统治下产生的畸形的资本主义世界的特殊方式。
此外,“我”的“不理解”这一形式也可以看作是自白的体现。“这里有的是真实……所谓自白就是这样的一种表白形式。它强调的是:你们在隐瞒真实,而我虽是不足一取的人但我讲了‘真实。”[4]“我”趁妻子晚上外出第一次溜到外面时,“我”将银元兑换成了五元的纸币,当主人公来到许久未见的街道时几乎令其惊讶,但却并未使其感到无比兴奋,很快便觉得累了。“我”没有任何想花钱的念头,甚至是完全丧失了花钱的机能。当“我”回到家后被妻子追问为何要出家门时,“我”想要向妻子道歉便走到妻子房间将五元纸币交给了她。“第二天当我醒来时,我在妻子的房间里,在她的被子里。这是我在(门牌号)33号生活以来第一次在妻子房间里睡觉……当我把钱交到妻子手里时我感到了无法言说的快感。”当“我”第二次想出门时,“我”因找到了两元钱而感到有好运气,回到房间后主人公把两元钱又给了妻子,妻子最终什么也没说,让主人公睡在了她的房间。可以看出,由于“我”对妻子职业的“不理解”产生了“我”与妻子间存在的交易,即像其他来客一样花钱留在了妻子房间;同时,主人公的所作所为又充满了滑稽和讽刺,如同小丑那样用“怪僻行为”向读者揭露着那个时代存在的虚伪和陋习。此外,通过妻子对于金钱的态度可以推测出金钱在韩国资本主义萌芽阶段的威力,即,钱是既支配人们的行为、意识又满足人们欲望的一种有效手段;同时,也可以看出作者向我们揭露了当时社会各阶层间存在的扭曲了的意识形态和浸透在人们生活中的恶劣的常规。
三、对自由的高喊:飞吧,飞吧,再飞一次吧!
我停下了脚步,真想这样大喊一声。
翅膀啊,再长出来吧!
飞吧,飞吧,再飞一次吧!
再飞一次吧![5]
引文是小说最后“我”的高喊,“我”对于“翅膀”和飞翔的渴望实际上暗含着对妻子及社会建构的机械化的、扭曲的生活秩序的一次突破,同时也可以看作是颠覆“我”与妻子之间不对称的性别二元对立体系的可能性,以此发现“我”思想意识转变的轨迹。
如果说“翅膀”是“我”对于自由的向往、对挣脱束缚的欲望的话,那么“被子”则是与其相对的意象。起初被子对主人公而言是必不可少的生存工具:“我”在被子里思考;给“我”温暖、安逸;不抛弃“我”、欢迎并等待着“我”;使“我”不在乎幸福或是不幸,在其中以睡觉代替一切活动。不难看出身处被子里的主人公是以在这个世界上的外人的身份存在的,换言之,主人公与任何人没有且不想有任何交集,“喜欢像最懒惰的动物那样懒惰”并心甘情愿地活在妻子建构的机制中。因此,被束缚在封闭而没有光照的房间里的主人公认为“对于我来说,人类社会是不亲密的,生活是不亲密的,所有的一切都是生分的。”试问,妻子在小说中又代表了什么?李箱这样设定妻子的形象有什么意图?笔者看来,不妨将妻子看作是30年代在韩国的日本帝国主义殖民统治的一个缩影,那么妻子对于主人公的控制则映射着殖民地时期知识分子所受的迫害及其在黑暗中的孤独和绝望。此外,主人公“从未向妻子询问过任何问题”,即主人公在妻子面前是个只存有内心活动的失语者的同时,可以看出当时知识分子主体性(支配力量)和身份性的缺失。这便意味着,殖民统治下的知识分子所经历的痛苦是“不能~,亦或不能是~”,而他们失去的便是“能够不~,亦或可以不是~”的身份性。
伴随着主人公“我”一次次的走出家门,“我”的思想意识亦随之开始变化。
第一次:并未对许久未见的街道感到兴奋,很快便感到疲惫。
第二次:没有感到疲惫,想要快点见到妻子,却觉得时间走得太慢而难过。
第三次:来到京城站的茶室点了一杯咖啡打发着时间,冒雨回家。
第四次:发现妻子一直给我吃的是安眠药阿大林,便跑出家门来到了山上,讨厌世间的一切,并对妻子产生隔阂。
第五次:想到妻子想要杀我,感到委屈便跑出家门,之后从京城站来到????(当时百货商店的名字)楼顶上回忆自己过去的26年时光并向自己发问——这一生中有什么欲望?我甚至很难认识到自身的存在。之后来到污浊的街道,感到自己被看不见的黏糊糊的绳子缠住,难以挣脱。正午汽笛声响起来,我的人工翅膀有冒出来的迹象。而在脑海中被抹掉的希望和野心的页面,就像翻字典般在闪烁。
通过上述对主人公思想意识的总结,可以看出主人公起初对外界事物提不起任何兴趣,只是为了打发时间,为的是能够在午夜一过便回家见妻子;直到发现了妻子的计划,便主动跑出家门,脑海中被抹去的希望与野心复燃。正如福柯在《性经验史》中提到的那样:“几千年来,人一直保持着亚里士多德眼中的的那种状态:一种活着的动物,但具有着用来进行政治生存的额外能力。而现代人则是这样一种动物:作为一个活着的存在,其生存反而因其政治而变成了一个问题。”……一个社会的“生物现代性的肇始”,是在那作为简单的活着的身体的物种和个体,开始在社会的诸种政治策略中承受危险时。[6]主人公“我”正是发现妻子给“我”的感冒药实际上是安眠药,并开始怀疑妻子想要杀害“我”时,“我”才开始成为真正意义上成为现代人。象征着“我”不再是任由妻子摆布,软弱无能的寄生者,“我与妻子命中注定是不相称的、跛脚的”关系,同时象征着我将成为在危险中重拾希望和野心,大声高呼的人。这里,尤应注意的是“正午汽笛声”对主人公的启蒙作用。之前“即使是刺耳的声音,我会使其以泰然平静的声音进入耳朵,因而我总是感到安心”,然而这种安心实际上是主人公在妻子统治下的自我麻痹,同时亦可以推测出20世纪30年代的韩国知识分子在殖民统治下的自我妥协。对于“正午的汽笛声”,笔者认为存在两层意义。其一,代表了文明的产生。殖民统治下的资本主义萌芽虽然在很大程度上使社会秩序变得扭曲,但同时也引进了新的文明生活方式。其二,为知识分子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为他们争取主体性、获得自由和解放提供了可能性。
四、结语
20世纪30年代的韩国文学在韩国近现代文学史上所占地位可谓至关重要,同时也是韩国文学转型的关键时期。大量描述劳动者都市经历、农村生活及知识分子的苦恼和社会命运走向的“通俗倾向小说”、“农民小说”、“农民启蒙小说”等诸多文学体裁出现,1935年随着KAPF(朝鲜无产阶级艺术家同盟,又称卡普)解体文坛再次发生巨变,知识分子不得不依靠个人力量对抗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因而,本文立足于探求20世纪30年代韩国知识分子殖民统治下思想意识的变化及其写作的表现手法,选择了在韩国文坛与学术界备受瞩目的作家李箱久负盛名的代表作《翅膀》为考察对象进行了探究。通过阐释李箱在《翅膀》中所使用的自白手法以及主人公“我”所展现的“小丑与傻瓜”的意象,能够看出作者利用“我”揭露了殖民统治下产生的畸形的资本主义世界和当时社会各阶层间存在的扭曲了的意识形态和浸透在人们生活中的恶劣的常规。此外,通过分析作品中多次提及的“被子”和“翅膀”两个寓意上相互对立的意象,以及主人公“我”在一次次出门后思想意识的转变,可以看出作者通过“我”的高喊表达了对当时知识分子冲破殖民統治的束缚,试图变身,重拾希望和野心的希冀。当然,李箱的作品中亦有需要我们继续探究的地方。如在对女性的描写上,《翅膀》中妻子的形象虽然有别于其他作家小说中的人物形象,虽然将其设定为政治位阶最底层的妓女,在与主人公“我”的关系中却拥有很强的优越感与控制力,在父权体系下过着完全颠覆性的生活。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作者是要给予她身份话语权,而是为了通过她展示畸形的资本主义世界和“金钱溺爱者”的恶俗。以后,对于李箱作品中女性形象的分析无疑是填补本文不足的有力保障。
参考文献
[1]金起林,《故李箱的追忆》,《朝光》,1937年6月。
[2]李箱,《翅膀》(李箱小说选),??????,2000 年,第71页。
[3]巴赫金著,白春仁、晓河译:《巴赫金全集 第三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355~356页。
[4]柄谷行人著,赵京华译:《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第78页。
[5]李箱,《翅膀》(李箱小说选),??????,2000 年,第109页。
[6]吉奥乔·阿甘本著,吴冠军译,《神圣人:至高权力与赤裸生命》,中央编译出版社,2016年,第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