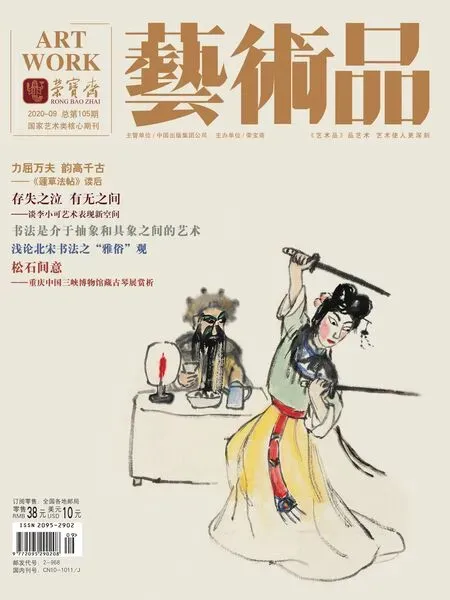浙江省博物馆《金石书画》系列展览第四期导读(上)
文 /桑 椹
(本文作者任职于浙江省博物馆)
《金石书画》第四卷,分碑帖、书法、绘画、文献四个门类,收录作品二百零六件。其中碑帖部分,下设周希丁青铜器全形拓艺术、张效彬旧藏善本碑帖,以及沙孟海与碑帖鉴藏三个小专题。绘画部分,主要有金石家绘画专题。书法和文献部分,则分别为明代名家手卷和宾虹草堂友朋书札(三)——傅雷致黄宾虹书信专题的上篇。现分类导读,以飨读者。
碑帖
《金石书画》以往各期,一般都会以全形拓作为开篇,渐已成为惯例。本期重点介绍的是现代青铜器全形拓代表人物周希丁先生的作品。
周希丁(1891——1961),名康元,原名家瑞,以字行,晚年别署墨庵,斋号石言馆,祖籍江西临川,生于北京。早年在琉璃厂做学徒,1918年开设“古光阁”古玩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先后供职北京市人民政府文化教育委员会文物组、首都博物馆等单位,负责摹拓古器物和文物鉴定。
周希丁早年为了传拓,曾参加过画法研究会,学习西洋透视技法,故其所拓器物全形立体感强,各部分比例结构十分合理,此外用墨也极为讲究,给人以匀净苍润之感。陈邦怀评其所拓全形“审其向背,辨其阴阳,以定墨气之浅深;观其远近,准其尺度,以符算理之吻合。君子所拓者,器之立体也,非平面也,前此所未有也。”1成就之高,堪称20世纪全形拓第一大家。
周希丁曾手拓故宫武英殿、宝蕴楼以及陈宝琛、罗振玉、孙壮、徐世章等诸家所藏铜器,尤其是为陈宝琛澂秋馆所拓的青铜器全形,多以六吉棉连纸淡墨精拓,极为精妙,后由容庚整理出版成《澂秋馆吉金图》一书,影响很大。首都博物馆藏有一卷《冰社雅集图》,冰社是民国初期北京著名的金石收藏与研究社团,周希丁时任副社长,社址即设在琉璃厂古光阁后院,而陈宝琛、罗振玉、孙壮等当时都是冰社的重要成员。
近年由上海书画出版社出版的《国家图书馆藏青铜器全形拓集成》中,收录了不少周希丁的全形拓本。今从浙江省博物馆藏碑帖中精选周希丁传拓青铜器全形二十种(主要为陈宝琛澂秋馆和孙壮读雪斋藏器),对全形拓感兴趣的金石爱好者,可从中一窥“周拓本”的艺术魅力。
大克鼎,又名善夫克鼎,西周中期器,铭文共二百九十字(含重文七字,合文二字),光绪十四年(1888)夏出土于陕西扶风,同年秋冬时节,归金石家潘祖荫所有,今藏上海博物馆。此鼎出土时,铭文大半为铜锈所掩,漫漶不清,光绪十五年(1889)春,经潘祖荫组织幕僚洗剔除锈后,始见精拓流传。大克鼎铭文的未剔本,传世十分少见,据仲威介绍,上海图书馆也仅藏有周庆云藏本一种。2本期收录的是新发现的浙江省博物馆藏吴士鉴(1868——1934)旧藏本,包括全形拓本和铭文未剔本各一轴。
端方馈赠金石友朋的秦权全形拓本,《金石书画》已展出过二种:赠黄士陵本(第一期,浙江省博物馆藏)和赠罗振玉本(第二期,海宁博物馆藏)。本期收录的是拓赠孙诒让者,系同一权,此权在端方藏权中算得上是尤巨且精者,故屡见传拓。拓本上方有光绪二十八年(1902)端方长跋,提及恰逢孙氏温州同乡黄绍箕(仲弢)南还,特托其转交,与第一期展出的端方送给孙诒让的古埃及造像拓本,应为同时所赠。浙江省博物馆收藏的孙诒让旧藏文物数量尚有不少,均为其孙孙延钊(1893——1983)20世纪50年代捐献,包括西周麦方鼎、《温州办学记》手稿(《金石书画》第三期)以及数十方自用印等。
近年来,经过国内影视剧的戏剧化演绎,铁齿铜牙纪晓岚的形象,已可谓家喻户晓,深入人心。据野史记载,纪晓岚还酷嗜旱烟,所用烟斗奇大。3浙江省博物馆藏有一种阅微草堂烟斗全形拓本,管身上刻纪晓岚手书铭文:“牙首铜锅,赤于常火,可以疗疾,可以作戈。”民国初年原物曾归陈汉第(伏庐),陈氏又在铜锅后部补刻了一段铭文,并手拓烟管全形。陈汉第(1874——1949),字仲恕,号伏庐,杭州人,陈豪子。幼承家学,工书画篆刻,尤嗜金石,藏印颇丰,有《伏庐藏印》传世。本馆收藏的碑帖精品中,如阮元赠刘喜海初拓《爨龙颜碑》册(《金石书画》第一期),以及本期收录的初拓《隋元公暨夫人姬氏墓志铭》合册,皆为当年伏庐旧藏。
纪晓岚烟斗拓本流传颇为罕见,上海图书馆藏有一幅,4此外国内某拍卖会上也曾出现过一种吴湖帆旧藏本,上有吴湖帆题跋,由吴跋知为陈汉第当年拓赠叶恭绰,叶氏又转赠给他的。5目前所见,似仅此三件,可见当时确实传拓不多。金石小品杂项,种类繁多,近年来已逐渐成为玩家新宠,但传拓烟管者实属冷门,或多或少带有猎奇的成分,终归不是金石收藏与研究的正途。

傅雷致黄宾虹的第一封信(1943年5月25日)
张效彬(1882——1968)是民国时期重要的碑帖收藏家之一。本名玮、字效彬,后以字行,号敔园,斋曰镜菡榭,河南固始人。早年曾留学英国剑桥大学学习经济,北洋政府时期,出任驻俄远东(伯力)领事,十月革命后归国,先后任教于中国大学、辅仁大学等高校,生平酷爱书画碑帖收藏,所藏善本碑帖甚夥。固始张氏镜菡榭藏品,今大多收藏于首都博物馆、故宫博物院等单位,在国内各大拍卖会上也时有出现。本期收录首都博物馆藏张效彬旧藏善本碑帖五种:明拓《石鼓文》卷(宝熙、张效彬题跋)、《吴天发神谶碑》册(王懿荣、盛昱、陆心源题跋)、旧拓《隋龙藏寺碑》册(赵世骏、张效彬、蒋式芬、宗树楷、李在铣、徐坊等题跋)、北宋拓《多宝塔碑》册(张效彬题跋)、宋拓《定武兰亭序》册(何绍基、张效彬题跋)。邹典飞曾有专文,对首都博物馆收藏的张氏重要碑帖做过详细介绍,可资参阅。6
今年是沙孟海(1900——1992)诞辰一百二十周年,长久以来,沙先生作为一位金石学家、碑帖鉴定家在学术史上的地位,似被其书名所掩盖,本期碑帖部分,特推出“沙孟海与碑帖鉴藏”专题,希望通过展示馆藏碑帖拓本上沙先生当年的题跋、题签等文物墨迹,帮助大家更好地认识其作为学问家的另一面,并以此寄托我们永远的缅怀之情。
沙孟海并非收藏家,个人所藏的碑帖数量其实不多,1960年,他曾一次性捐赠浙江省文管会自藏碑帖一百三十余种,以唐宋以后的墓志碑刻、题名残石等居多,除了初拓东汉《马姜墓志》后被定为三级文物外,其余都只归入一般普通品,从版本角度来看,实无珍秘善本可言。这既和他的生平经历和经济状况相符,也反映出沙先生收藏拓本的主要目的,还是作为书法临习、学术研究的参考资料。不过,其中有几种早年得自师友馈赠的拓本,如东汉《西狭颂》《郑固碑》册页,均系甬上藏书家蔡鸿鉴(1854——1881)墨海楼旧藏,前者封面上有他早年恩师,民国初年宁波著名书法家张琴(1864——1938)的题签,很有可能即是张琴送给沙孟海的留念之物,册尾尚有1958年金石家陈伯衡应沙孟海之请所作题跋一开。又如易忠箓(1886——1969)所赠“玲珑四犯”古玉拓片。两人相识于1938年,当时沙孟海在汉口中英庚款董事会任干事,彼此一见如故,“相见狂欢”(《沙村印话》),此后十余年间,书信往来不断,交流金石篆刻,语不及他,成为至交。1943年中秋佳节,时任西北大学教授的易忠箓,让夫人万灵蕤淡墨精拓家藏琥、璧、鱼、蝉古玉四器,旁注器名及玉材,并手书和姜夔《玲珑四犯》词一首,寄赠沙孟海,以遥寄思念之情。像此类反映沙先生早年师承与交友情况的拓本,应是这批捐赠碑帖中较值得关注的部分。
馆藏碑帖拓本上,有沙先生题跋的约有三十余种,包括宋拓《姑孰帖》残册(《金石书画》第三卷)、《仓颉庙碑》、《飞来峰直翁翼道题名》(以上题跋亦见《沙孟海论书文集》)、东汉《嵩山三阙铭》(《金石书画》第三卷)、《曹全碑》(乾字未穿本)、《尹宙碑》、北魏《高贞碑》、符秦《邓太尉祠碑》、隋《苏孝慈墓志》三种、明拓《皇甫诞碑》、清初拓《怀仁集王圣教序》、《南宋石经》、《尚书省郎官石记》(伪刻)等,至于各类书画碑帖上的题签数量,则不下百计。这些题跋、题签,大多书于20世纪70年代前期,这里有一段历史背景需要说明。“文革”期间,沙先生曾受到冲击,并二次遭到“隔离审查”,直至1973年5月,才正式宣布撤销对其所谓“审查”,恢复工作。是年冬,74岁高龄的沙孟海被安排到浙江省博物馆文一街保管部上班,此后数年,主要负责整理馆藏碑帖。据馆里老辈回忆,当时沙先生的办公地点,就在库房走廊的过道上,靠墙摆了一张书桌,每日的工作是给馆藏拓本登记造册,并为碑帖写签记、题跋,还曾为一、二级藏品棉布画套加写题签。因为都是博物馆藏品,沙先生的题签或题跋,都不是直接写在碑帖上的,而是用毛笔另写一纸,夹在册中,或者粘贴在拓本背面,从这一细节中,也颇能反映出他生平为人处世公私分明的态度。
从目前留存的沙孟海碑帖题跋内容来看,有的是对原册装裱次序紊乱所作纠正,如跋东汉《尹宙碑》册(吴士鉴旧藏)、跋南宋拓《姑孰残帖》册(沈曾植旧藏)即属于此类性质。有的是对石刻铭文中的人名、地名等史实的考证,如跋《飞来峰直翁翼道题名》,经沙先生考证后认为,直翁是南宋孝宗时宰相史浩的字,吉甫应是曾几,而非朱家济先生认为的吕惠卿,可谓甚确。还有的涉及拓本断代,如沈树镛旧藏唐《皇甫诞碑》拓本册,赵之谦题签定作宋拓,沙先生仔细校勘后,认为定明拓较为合适,从而纠正了前人的偏颇。当然,更常见的内容,是与文字校勘有关,有几种还是对馆藏多份拓本进行所谓“联校”,如东汉《仓颉庙碑》(二种),隋《苏孝慈墓志》(三种)上,即有他校勘众本,考证先后优劣之后撰写的跋语。
历来碑帖作伪手段繁多,诸如翻刻、伪刻、镶填、涂描、剪补、做旧等等,层出不穷,令人防不胜防,故俗称“黑老虎”。沙孟海先生在碑帖鉴定方面,可谓经验丰富,各种伎俩,往往能被其一眼识破,结论亦大都令人信服。如馆藏《尚书省郎官石记》册,经其鉴定后,认为实乃伪刻:

沙孟海像

隋元公暨夫人姬氏墓志合册 初拓本 陈叔通旧藏(左)

周希丁拓周史颂匜全形 陈宝琛澂秋馆藏器(右)

沙孟海跋宋拓《姑孰残帖》册 浙江省博物馆藏
此本只书前半篇,妄删篇首“夫”字,并又妄增“者哉”二字,后题贞观元年欧阳询书,欧安能书陈九言之文?何况书刻均不佳,定是伪刻。
馆藏东汉《尹宙碑》拓本册,十三行“福德”“寿不”等多处明拓本考据均未泐,但沙先生却认为:“字较大且劣,当是另刻填补”。馆藏北魏《高贞碑》拓本册,“于王”二字完好,沙先生细察后,发现有描补痕迹,并非初拓。读沙先生的碑帖题跋,我们即惊羡其学识渊博,考辨入微,更能体会到他对于学术问题绝不粗枝大叶,敷衍了事,而是深入思考,不囿旧说的可贵品格。如他在馆藏宋拓《忠义堂帖》影印本前言中认为,以往把颜真卿书法特征归结为“粗肥多肉”“蚕头燕尾”的观点,“观此帖便知其不然”,可谓阐前人所未言。跋馆藏东汉《曹全碑》拓本册(乾字未穿本),推测“此碑是生前所立,君讳全之讳字,意当时少留空未书,死后乃补刻,故其字特大。”观点让人耳目一新。在《晋朱曼妻薛氏买地劵跋》中,指出此劵应是先刻横画,竖画有漏刻,并非是为了省笔。诸如此类的独到创见,在沙先生的题跋中不乏其例,虽属吉光片羽,亦当以金玉珠贝视之。
碑帖部分还收录有汉碑善本三种:浙江省博物馆藏旧拓《白石神君碑》册(刘鹗旧藏并跋)、《韩仁铭》册(吴士鉴旧藏 “谓京”未损本),上海博物馆藏《安阳残石》四种合册。后者系黄易赠赵魏初拓本,收录嘉庆年间河南安阳出土的《子游残碑》《正直残碑》《元孙残碑》《刘君残碑》等汉隶残碑四种,先后经沈树镛、徐子静、刘世珩、戚叔玉等递藏,前有邓传密题端,后有沈树镛、翁同龢、吴郁生、褚德彝诸家题跋或观款,每种残石后皆有赵魏临本,册末还附有黄易致赵魏尺牍一通,颇具文献史料价值。
文献
文献部分,本期推出的是浙江省博物馆藏傅雷致黄宾虹书信的上篇。傅雷与黄宾虹的友谊,是我国现代艺术史上的一段佳话。两人彼此仰慕赏识,在傅雷眼中,“石涛以后,宾翁一人而已。”(傅雷致刘抗信)。他不懈余力地向世人推介黄宾虹的艺术,黄苗子先生誉其为宾老艺术的“护法神”。黄宾虹对这位忘年知己也十分器重,称赞傅雷“评驾旧画,卓识高超”(黄宾虹致傅雷信)7。
傅雷与黄宾虹早在20世纪30年代初在上海时即已相识,但两人真正的交往则始于1943年。此后,虽见面次数寥寥,但书信往返十分频繁。自1943年5月,至黄宾虹去世前的1954年11月,通信持续达十一年之久。其中,傅雷致黄宾虹的书信,目前大部分收藏于浙江省博物馆,总计一百十八封,另有残简八封。这批信札的撰写时间主要在1949年以前,其中1943、1944两年间的通信即多达六十一封,几乎占了一半以上。多数信用毛笔书写,后期也有部分是用钢笔写就。信札很大一部分内容有关论学谈画,记录了傅雷对黄宾虹和中国绘画艺术的思考与解读,充满真知灼见,堪称“中国绘画史上的奇迹,其深刻处罕有其匹”8(王中秀语)。还有较多内容,则涉及筹备庆祝黄宾虹八十寿辰在沪举办画展,以及傅雷为后者推售作品、出版著作、代收润笔等杂务而不遗余力多方奔走之事,反映了两人之间的友谊至深弥笃。遗憾的是,黄宾虹给傅雷的信,经过“文革”后大多已下落不明,仅留存下来二十二通9,用当代着名黄宾虹研究学者王中秀先生的话说,无疑是“中国画史的劫难”10。
浙博藏傅雷致黄宾虹的这批信札,1992年,曾由上海古籍出版社以《傅雷书信集》(以下简称《书信集》)的名义出版过手稿影印本,后傅雷之子傅敏整理点校《傅雷书简》(以下简称《书简》)时,从中辑选了一百零一通,成为目前社会影响最大、最为普及通行的版本。
《书信集》影印时间较早,且为黑白印刷,当时用纸不佳,原信笺纸底纹和钤印等,都模糊不清,欣赏效果差强人意。此外,在编排方面也存在不少问题。
首先,《书信集》存在遗漏缺页的情况。如第二十一通(1943年10月15日)、第二十三通(1943年10月30日)、第二十五通(1943年11月4日)、第二十七通(1943年11月12日)、第三十一通(1943年11月29日)、第四十通(1944年2月8日)、第四十六通(1944年5月22日)、第七十一通(1945年12月27日)、第七十七通(1946年2月17日),原信中所附的便条、书目、账单等,均未能完整影印。第十五通(1943年10月1日),原信上方尚有一段傅雷用铅笔书就的补白,《书信集》中也未能印出。此外,不少信封其实保存完好,从资料完整性的角度,也应一一补录。
其次,《书信集》中个别信札还存在错简的情况。如原编纂者也注意到第十一通的内容和落款日期不符,特在目录中加以备注说明。其实,这是由于此通信札的最后一页与第三十七通的末页,出现次序错乱造成的,傅敏根据影印本整理点校,也未能发现这一问题。
再者,原件尚有少量文字撕缺的情况,《书信集》出版方当时似曾作过一些描补处理,但从反映文物原貌的角度看,其实并无必要,所以这次影印时,秉持一仍其旧的原则,未再作任何电脑处理。
本次整理过程中,最大的惊喜,莫过于发现了八封傅雷致黄宾虹的佚信(均为残简)。当年《书信集》影印时,或考虑是残件的原因,均未予收录。其中有一通长信,尚存六页,信中傅雷分列逐条,向黄宾虹汇报有关刊印著作、画款支配、成立艺术研究社团、出版刊物、拟定润例、钞书工资等事宜,史料价值颇高。
鉴于上述原因,我们认为,这批信札早年虽曾出版,但仍有重新整理影印的必要。本期先刊出1943、1944两年间通信六十二封,以及新发现的八封佚信部分。有关书信的具体撰写时间确定上,主要依据《书信集》和《书简》编纂者的考证意见,未作大的变动,特予说明。

展厅现场

吴士鉴旧藏西周大克鼎铭文未剔拓本

沙孟海跋东汉延光四年砖 浙江省博物馆藏
注释:
1史树青《悼念周希丁先生》,《文物》,1962年第三期。
2仲威《从大盂鼎和大克鼎传世善本看潘祖荫的吉金收藏》,《书与画》,2020年第三期。
3《清稗类钞》云能容烟叶一两许,姚元之《竹叶亭杂记》则作可盛烟三四两。
4图见仲威《纸上金石:小品善拓过眼录》下册,170页,文物出版社,2017年。
5图见上海明轩2017年春季艺术品拍卖会图录。
6邹典飞《旧京碑帖收藏家张效彬的事迹及藏品介绍》,《书法丛刊》,2018年第四期。
7有关傅雷与黄宾虹的交谊,早年有黄宾虹女婿赵志钧的回忆文章,后黄苗子、王中秀也皆有撰文,近年来,澳大利亚学者罗清奇又著有《有朋自远方来——傅雷与黄宾虹的艺术情谊》一书(中西书局,2015年),详尽记述了这段友谊的始末,均可资读者参考。
8王中秀《编年注疏黄宾虹谈艺书信集》,148页,人民美术出版社,2016年。
9上海教育学院古籍整理研究室编《黄宾虹书信集》(手稿影印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
10同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