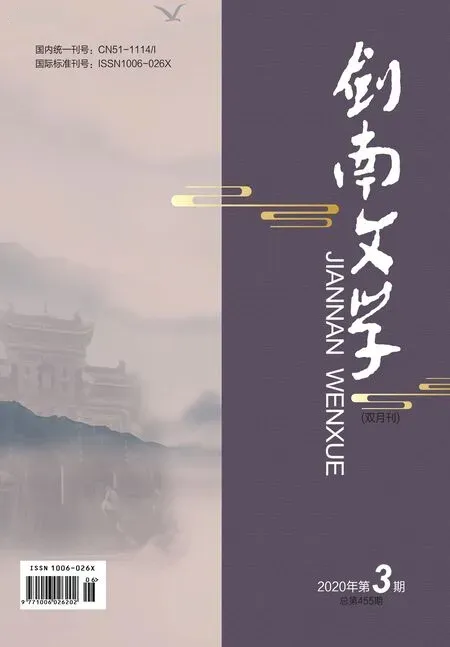这一天
□谭雪花
映雪是被吵醒的。
她试图用枕头把脑袋蒙住,无奈声音太大,掩不住,心里暗自懊悔不听自家老王的话,每晚非要坚持开窗睡觉。
摸出枕头下面的手机一看,八点都没到呢。楼下的动静是越发地大了,听上去还不止是两个人的声音。这对于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日益冷清的小区来说,倒也添了一点人气。
映雪披上棉服,走到窗前往外看,果然又是楼下那个犟老头在闹。说起这个犟老头老张,还真跟茅厕头的石头一样,又臭又硬。年前,在政府的牵头下,小区要对楼梯和楼顶安全隐患进行整改,单元十户人家,其他九户都同意了,唯有这个老张头,坚决不签字。楼栋代表和邻居分别上门做工作,均是油盐不进,还跟人吵了几架。大家后来猜他不配合,大概是因为出去租房要花钱,加之他家在二楼,对加装电梯之类的改造,自觉受益不大,所以不情愿。为了完成签字,众人合计,大家共同出资,给他一家在外面租房。没想到老张头仍然不同意,把上门的工作人员骂了个狗血喷头:“你们有几个臭钱了不起啊,老子不差钱,我就是不搬。”工作人员气得哭,给大家一说情况,大家都觉得老张头一家不可理喻。
今儿这大清早的,这老张头又闹的是哪一出?
“我在屋头都蹲出煤炭灰了,咋就不能出去走走?街上人花花儿都没有一个,哪个来传染我噻,哪个来传染我噻?”这是老张头的大嗓门。
“大家都在屋里头待得住,就你一个人要闷死?你没听说昨天小区旁边那家医院才来了个疑似病人啊,你非要出去惹!感染了可不是你一个人的事,全家都要一起隔离!你今天出了这个门,就别回来了,你不怕老娘怕,一家大小怕。”这是他老伴儿的河东狮吼。
“传染传染,天天你们都在念,这么大个城,几十万人,也才7 个人得肺炎,搞得鸡飞狗跳,门都不让出了,跟坐牢一样。凭啥不要我回来?我偏要回来,你个胆小怕死的老婆子。”
对于预防传染,映雪对这种说法深以为然:100 个人里面,80 个人严防死守,18 个人无所谓,2 个人到处作死,这2 个人就会通过18 个人让80 个人的努力白费。老张头算18还是2 呢?这就是人们常说的为老不尊的人吧?映雪心里很是鄙夷,却没有作声。
热闹看完了,映雪也就不打算接着睡,洗漱完毕之后,来到客厅,看见十八岁的儿子穿戴整齐地坐在沙发上,满面愁容。
“楼下吵到你啦?”
儿子今年高三,高考已进入倒计时,此时正是最关键的时刻。说起来这一届的高三学生,大略也是他们的命数。有人说,这届高三堪称传奇:出生遇非典,高考遇肺炎,不宜复读 (全国多地明年实行新高考模式,取消考试大纲)。学校原计划二月一号复课,因疫情形势严峻,又搁置了。省教育厅的文件,隔两天又在更新,总结起来就两字:“待定。”开学遥遥无期,只能自己在家复习。
儿子如今是全家人的重点保护对象,故而映雪在年前就对娘家和婆家的兄弟姐妹“三令五申”:不要串门,不要聚会,疫情面前,人命第一,任何侥幸都有可能夺人性命。她甚至对年前执意要回江安老家的弟媳妇放了狠话:“你若是执意要回去,回来后就不要和我们接触了。假如因为这个影响了我娃儿高考,我是要埋怨你们的。”这话可以说是相当的不留情面了,但映雪觉得自己实在是不敢拿儿子的事情来打水漂,小心小心又小心,以至于家中掌事的大哥都私下批评她有点紧张过度了。
“妈妈,我想去医院一趟。”儿子声音有点低沉。
“咋的了?!”映雪一下子紧张起来,现在“医院”跟“病毒”一样,是个敏感词汇。
“我昨晚拉肚子,还呕吐,睡前症状不是很严重,就没跟你们讲,结果半夜起来好几次,又吐又拉。”儿子顿了一下,小声说:“我觉得自己还有点发烧。”
映雪这下汗毛都竖起来了,眼下,“发烧”就是个禁忌。真是怕啥来啥!在厨房里忙活的老王提着菜刀出来,也是一脸焦急。“咋就发烧了嘛!”他说。
一家人面面相觑,屋里出现了短暂的沉默,而后,父子俩都把询问的眼神投向了映雪。这个时候,映雪倒是感觉到自己是“一家之主”了。
映雪这个时候的脑子也是慌乱的。微信上到处都在传,一旦哪里发现了病患,马上从开始的单元楼栋隔离,然后封闭整个小区,邻里之间很快就会出现铺天盖地的质问和责怪。去医院?映雪第一反应是排斥的,现在发烧去医院意味着什么?后果是什么?她想都不敢往下想。可是不去吗?这段时间以来,不断扩散的疫情和不断攀升的数据,又在提醒每个人都有被感染的可能,不能心存侥幸。
“我还是去医院吧!”还是儿子做出了选择,“早去晚去都得去,早去早治疗。”说到后面,声音怯怯的,毕竟还是一个孩子。
老王默不作声地脱下围裙和家居服,穿上了外套。映雪从内心的纠结中缓过神。“我们先冷静一下,”她用手势示意父子俩,“你说你发烧,量过体温没有,多少度?”
“还没量,” 儿子说,“你摸摸我是不是有点烫嘛?”
“糊涂!”
映雪一下子就生气了,然后从医药箱里找出一个电子温度计。这个温度计是几年前在网上买的,也不知还能不能用。她使劲甩了几下,看见上面显示了数字,还有电,这才递给儿子,示意他夹在腋下。
映雪认为,根据他们最近活动的范围和情况,儿子是断不会染病的。
“时间到了。”儿子取出体温计。
夫妻俩异口同声:“多少度?”
“37.3。”
“那是有点发烧哦。”老王这下也愁眉苦脸了。
映雪依旧不甘心,把温度计猛甩几下:“量量我!这个温度计很久没有用了,量量我就知道准不准了。”
又是一个五分钟过去。
“多少度?”这下,换父子俩异口同声了。
“35.8。”
“咋个可能?!”这下是三个人异口同声。
“所以我就说不准嘛。”映雪一下子舒了口气,“我们先咨询一下医院,再决定去不去,好不?”
电话接通了医院的朋友,医生朋友仔细询问了症状,详细了解了儿子的生活规律和饮食习惯,得出如下判断: 估计是空腹食用了过多的柿饼,加之春节期间的饮食过于油腻,造成胃肠道感染,引起腹泻和发热。建议先居家观察一天,吃点止泻养胃的药 (比如藿香正气液),再吃点感冒药,多喝水。特别强调不要外出,随时观察体温。
这个时候,医生的话就是定心丸,一家人一致决定居家观察。儿子立刻服用了气味冲天的藿香正气液,映雪三五两下就把茶几上剩余的柿饼给扔了,吩咐老王重新改菜谱,回厨房熬粥。
老王是个“惰性气体”,因为身体不好,加之家住顶楼,又没有电梯,平常回了家,十匹马都别想把他拉下楼。可今天他就是觉得家里的药不管用,不顾映雪的阻止,口罩、帽子、手套……全副武装地出了门。一会儿的工夫,就气喘吁吁地拎回来一大包药。映雪边给他喷洒酒精消毒,边无奈地摇头。老王很冲地对她说:“你不要管,不出去一趟,我就始终心不安。”
一个上午在焦急和苦熬中过去。午后,儿子起床,倒是没有腹泻了,可电子温度计上面的数字,依然是37.3 度,没辙的老王苦着脸不说话。这下,换映雪全副武装出门了。老王追到门口问:“你又干啥去?”
“我买水银温度计去,这个电子温度计肯定不准。”
小区大门口,从左到右不过两百米的距离,经营着四家药房。映雪一一走进去,每家的店员都是一如既往地热情:“温度计早就没有了,是和口罩一起脱销的。”
映雪失望地走出药房,又拨通了医生朋友的电话。讲真的,这些天已经够给医生朋友添乱了,先是找口罩,后是买紧俏药品,打电话咨询……她都有些不好意思打扰人家了,但又想不出其他的办法,她只能硬着头皮打电话。朋友在电话里悄声告诉她,她正在开会,会后联系,然后匆匆挂了电话。
平常宅在家里不觉得冷,在外面走动一下,才发觉天气还是很寒冷的。宽阔的大道上空无一人,往日繁华的酒店也是门庭冷落车马稀,街上一派 “千门万户闭,唯有药房开”的景象,说不出来的冷清。街角处有几个戴红袖章的,应是社区的防疫工作人员,他们不时探头警惕地往映雪这边瞧。映雪想,要是自己继续在这里站着,估计他们就会过来“关心”自己了。为了节约一个口罩,映雪决定不回家,就在这附近边溜达边等医生朋友开完会打电话。
围着小区走了几圈,映雪终于等到了医生朋友的电话。医生朋友说,就在刚刚开完的会上,医院再次强调了疫期的管理工作,重点就是医疗器械、医疗物资的集中管理和统一分配问题。朋友不无遗憾地告诉她:“真的是爱莫能助!”
映雪望着阴沉沉的天,心里说不出来的难受。平生第一次,她感受到了深深的无助和不知所措。拖着沉重的双腿往回走,握在手里的手机不时传来震动,心烦的她点开一看,是邻居群里大家转发的各种关于疫情的信息,和互相鼓气的话。映雪看完不无感慨地发了一句:“现今找个温度计,都比登天还难!”并配了三个痛哭的表情。
快走到楼下的时候,映雪接到一个陌生的电话:“邻居,刚刚在群里看见你在四处找温度计。我家年前多买了一支,如果你急需,我们可以支援你。”
映雪大喜:“是是是,我急着要,太感谢了,请问您是哪家?”
“二楼老张头家。”
老张头?就是那个她鄙夷的自私自利的犟老头?映雪的嘴张成了“O”型。
“特殊时期,我就不给你送上门了。我已经把温度计用口袋装好,挂在我们家门把手上面,你自己来拿一下。”
映雪从一瞬间的错愕中惊醒,连声道谢。经过二楼的时候,她果真看见老张头家的门把手上面挂着一个白色的小塑料袋。
望着这支温度计,映雪不禁生出许多感慨。突发的疫情,像一块巨石砸进了我们原本平静有序的生活。它带给我们恐惧和困惑,也唤醒了我们内心的善良。或许我们曾经有分歧,甚至曾道不同不相为谋,但在巨大的灾难面前,我们仍然能团结一心、彼此温暖的。有这样的力量在,谁还能说我们翻不过去这道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