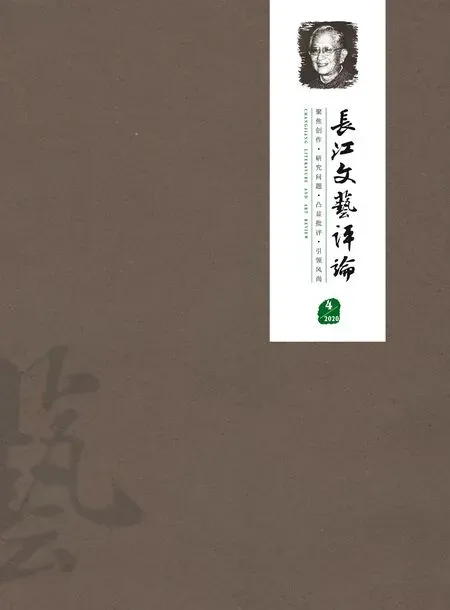饶晓志:叙事策略、喜剧风格与“电影工业美学”的渐进之路
◆李 冀
近年来,在戏剧界颇有建树的80后导演饶晓志,凭借《你好,疯子!》《无名之辈》两部影片成为“新力量”导演中的“有名之辈”。他的作品通过疾病书写和疯癫影像的双重叙事策略、现实化和荒诞化的喜剧风格,建立起极具个人特色的风格属性,同时在“体制内”收获了口碑与票房的双赢。饶晓志导演以其卓有成效的创作实践,成为“电影工业美学”原则下兼顾“艺术性”与“商业性”的探路者。
一、叙事策略
(一)疾病书写:疾患苦痛与入骨创伤
不管是《你好,疯子!》中的精神分裂患者安希,还是《无名之辈》中身体或精神有一定“缺陷”的主角们,都通过斑驳光影完成了饶晓志导演的疾病书写。两部影片通过疾病隐喻反映了个体生命在当今社会“流动的现代性”中所表现出来的焦虑与挣扎。“像任何一种极端的处境一样,令人恐惧的疾病也把人的好品性和坏品性统统都暴露出来了。”[1]
两部影片中的女主人公自身都存在“影子的热情与身体的单薄”[2]之矛盾。安希对绘画艺术的敏感和创造力、马嘉旗骨子里隐藏的柔软善良形成两个人的生之欲和个体热情,而主体人格的难以掌控和高位截瘫导致的不自由带给她们生命的匮乏,这种现实的无奈和负担不时地提醒并刺痛着她们。安希痛苦,马嘉旗绝望,强烈的本能倒逼着她们尽快做出抉择。庆幸的是两名“弱女子”在想象或现实中得到了温情的感化与庇佑,勉力确立起自己人格的主体地位,勇敢地活下去,在自我蜕变成长的道路上艰难前行。
两部影片中人物的“疾病”更多地表现为“创伤”。《你好,疯子!》中,情感与爱的匮乏让安希受到严重的心理创伤,所以她沉浸在幻觉与梦境交织的混乱状态之中。由她头脑中幻化出来的六种附属人格都不约而同、不同程度地“受伤”了。被围殴后拄拐、脑震荡、哮喘病、因车祸伤颈、手腕上的割痕及流淌的血液,这些都是安希精神创伤的外化,她对真情、正义、保护的渴慕和求而不得、屡受挫败迫使其在幻境中用“负伤”的状态来顾影自怜、压抑自我。
《无名之辈》中,马嘉旗尖刻毒舌、生无可恋的歇斯底里状态可谓“创伤后应激障碍”的电影化表达。遭遇惨烈车祸使其终生只能在轮椅上度过,头部成为唯一可以支配、自由活动的器官,即便轻生都没有自主能力。肢体上持续遭受的束缚和永远的麻痹让她体会到“生不如死”的悲凉感和无力感,于是马嘉旗变得“不正常”了,只有通过对周围人刻薄的辱骂、强烈的刺激发泄内心积郁的愤懑、委屈与对“无能”之身体的自暴自弃。马先勇因醉驾导致妻子丧生、妹妹残疾、女儿愤恨,丢了协警身份的他潦倒落魄,内心始终被深刻的负罪感所萦绕和封闭,用表面的麻木与不堪来“赎罪”,期待着遥遥无期的宽恕。“悍匪”胡广生实际上“色厉内荏”,他真正的“伤痛”是其自卑与脆弱的心病。轰轰烈烈干大事的“威武”行动其实是持枪抢劫手机店,被网友嘲笑为“年度最蠢劫匪”的鬼畜视频让他即刻崩溃,自尊瞬间被摧毁。影片结尾处虚弱的胡广生倍感幻灭、涕泗交流,玩具枪喷洒的水等于往他流脓的“内伤”处狠狠地撒了一把盐。
(二)疯癫影像:理性制约下的“非人”状态
在福柯看来,“疯癫”已经超越了病理学的初始范畴,隶属于人类文化价值符号体系和文化意识形态系统,被纳入到批判与反思现代性的话语体系与哲学层面。“疯癫不是与现实世界及其各种隐秘形式相联系,而是与人、与人的弱点、梦幻和错觉相联系。……疯癫所涉及的与其说是真理和现实的世界,不如说是人和人所能感知的关于自身的所谓真理。……它完全是一个普遍景观;它不再是一个宇宙的形象,而是一个时代的特征。”[3]
进入21世纪,中国电影“富有古典意识的‘正襟危坐’让位于现代反思的‘疯癫叙事’。喜剧化疯癫影像电影作品不断涌现。”[4]不少国产电影作为源于现实、反映现实、介入现实、高于现实的文化艺术产品,通过疯癫影像的叙事方式和话语系统,以或荒诞不经或幽默调侃的态度抒发情感与体验、表达心声与愿望,成为一面恰当映照社会与时代症候的镜子。
《你好,疯子!》中的安希作为一个疯癫者,却被塑造为一个品行单纯、人畜无害的悲情女“疯子”形象,摆脱了社会大众在有限认知中对所谓精神病人的刻板印象(“可怖”“变态”“扭曲”“伤人”……)。片中安希的主体人格与六种附属人格构成一个临时团体,这既可以看作对一个生命个体之多重人格的集中展现和自我主体性在确认过程中所可能遭遇的激烈冲突与艰辛调和,也可以视为社会的缩影,是一群人面对极端环境所暴露出来的芸芸众生相。刚被莫名抛入仿若凋敝车间、破败仓库之类的幽闭空间(精神病院)时,惊惶不已的六个人表现得“一团和气”、相安无事。后来,他们通过合唱、跳肚皮舞、表演词语、模仿进化论等狂欢游戏的形式竭尽全力地证明自己不是精神病人。在“群策群力”的过程中,“犯错—禁闭”的模式被默许实施,尤其是得到“七个人中有一个是疯子”的“院长旨意”后,六个人更是互相猜忌、打压、侮辱,自私、贪婪、欲望、敌视等负面情绪暴露无遗,一个个像是得了“失心疯”,变得癫狂异常,几近失控。这所阴森晦暗并带有一丝神秘颓败气息的精神病院,在四周布满摄像头的密闭空间里,在院长充满淫威的“密切监视”之下,理性与疯癫之间的二元对立关系被威胁与解构,它们的界限变得游离暧昧,随时可能发生置换。
《无名之辈》中,“憨皮”“憨贼”“疯婆娘”“变态”“奇怪”“神经病”“废人”“有病”“脑子进屎”“脑壳昏了”“鬼畜”和“倒憨水、冒憨气”等一系列骂人“疯傻痴呆”的词语夹杂着方言俚语不绝于耳,疯癫话语溢出银幕,深入观众内心。劫匪胡广生和李海根这对“不知天高地厚”的青年土老帽儿,誓做剑走江湖的“头盔侠”,却是没有智谋远见、文化常识和野心抱负的“阿呆与阿瓜”。从打得稀烂的“出牌路数”即可窥出两人的无勇无谋、神经大条。他们满怀向往却盲目无知:一个要出人头地,立志“做大做强”,一个单恋坐台女,要抱得美人归——愚蠢怪诞的笨贼人设给观众留下荒唐滑稽的印象。“奇葩”劫匪神不知鬼不觉地闯进刁蛮乖戾、一心求死的马嘉旗家,在她尖利粗鄙语言的刺激下,原本怯懦的胡广生如坐针毡、气急败坏,他口中的“疯婆娘”也最能形容她既灰心颓靡又充满戾气的狂暴之态。可以想见,常年憋屈在家里,“捆绑”在轮椅上,生而不得、死而不能的马嘉旗似乎有迈向疯癫的充分理由。
二、喜剧风格
有学者认为,中国当代喜剧电影创作总体上有两种思路,即荒诞的现实化与现实的荒诞化,分别对应荒诞喜剧电影和现实喜剧电影。从美学角度而言,基本上可以用三方面特征来鉴别和评析这两类喜剧电影,即构建故事基础的时空背景环境,故事逻辑主线的特性,人物性格发展的特征与主题所呈现的性质。[5]藉由此阐释框架考察饶晓志的电影文本,可以见出这两种路径在其创作实践中的探索、开拓与融合。
(一)《你好,疯子!》:荒诞的现实化
1.荒诞假定的故事环境。片中虽出现了精神病院的相关设置与场景,但缺乏现代化医院设施与医护人员(除了电击椅子、办公桌、安希的床等有限“摆设”和一名院长/医生),与世隔绝的密室透出被弃置于废墟之上的末日既视感,阴郁恐怖、没落荒凉的气息叫人不寒而栗。而闪烁着诡异红光的摄像头和仅有的一个小口(用来送盒饭和药物),让人联想到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1984》中极权制度下的政府办公环境。架空的空间设置营造出悬疑的情境,从一开始就奠定了荒诞的基调。事实上,片名所彰显的游戏化色彩也输出了一种荒诞感。
2.故事主线的现实性发展。影片讲述了七位城市从业者的故事,同时透露了其职业状况和人性的复杂背面:富有耐心与爱心的宠物医生会有懦弱和明哲保身之时;伸张正义的律师可能在利益面前迷失为讼棍,向不公妥协;勇敢探寻真相、理性清醒的记者也可能激进暴戾、自以为是;作为知识分子的历史老师仁爱慈祥,有些古板迂腐;八面玲珑的项目公关通过非正当手段达到目的;有些痞气的出租车司机文化层次不高,自卑鲁莽,却有热情实在的一面;画家则敏感忧郁,内心世界细腻丰富。正是他们身上贴近真实生活的优缺点,将“找出一个疯子”的终极任务变为人性大考验,考场上丑态百出、反转不断,让人啼笑皆非。故事被一步步推向高潮,在反讽性的情节发展中映射现实,引发观众思考。
3.人物性格的理想趋向与主题的哲思化。正如勒庞所言,“群体的某些特点,如冲动、急躁、缺乏理性、没有判断力和批判精神、夸大感情等等,几乎总是可以在低级进化形态的生命中看到。”[6]当这群“乌合之众”的行为近乎原始的野蛮人时,主人公安希一度处于凄凉无助、迷惘仓惶的心境,但六个人/六种附属人格还是被她/她的主人格打动、感化,纷纷良心发现,停止内讧,放弃攻讦、质疑与伤害。他们的道德感被唤醒,要让纯净的人受到应有的呵护,帮助“六神无主”的安希找回自我。只有令躁动的能量平和“安”静下来,才会升腾起阳光与“希”望。终于,安希出院了,开始走向独立、健康与成熟。安希的“心病”是一个人的,也是社会群体性的。安希康复,患病的社会也终将被疗愈。《你好,疯子!》通过“假戏真做”传达出引人深思的主题:人不得不学会克服人性弱点、克制过多欲望,努力尝试接受孤独并与之友好共处,才能与纷扰的世界和解,去接近圆满与幸福。
(二)《无名之辈》:现实的荒诞化
1.自然逼真的故事环境。故事发生在贵州省都匀市这座西南边陲不起眼的小城,蜿蜒的河流、陡峭的石阶、狭窄的小巷、古老的石板街、陈旧的楼屋和千姿百态的桥,一起勾勒出阴雨连绵、逼仄曲折的叙事空间。高原之地上的桥城,配合人物接地气的西南官话,俚俗韵味十足,极富地域特色的人文环境铺垫了叙事的现实感。这些“在地化”特质的凸显和“陌生化”效果的生成都会触发观众或共情或好奇的心理基础,为后续故事的发展增强可信度和可看性。
2.故事主线的荒诞化发展。故事主要由两条线索构成:“持枪抢劫”与“丢枪破案”。案发后,新闻报道和网友视频、犯罪现场和目击者都时刻提示描摹着枪的“在场”,而马先勇正巧丢失了要用来邀功以恢复协警身份的枪,所以他要协助破案以便“寻枪”。抢劫案迫使劫匪闯入马嘉旗家,“人质”马嘉旗碰巧是马先勇的妹妹;在追踪侦破的过程中,马先勇跟警察都被劫匪所戴头盔的来源“误导”,带出了与两条线索可能有所关联的所有人物及其错综复杂的互动关系。影片尾声处,马先勇才明白劫匪的“枪”并非他所丢掉的“枪”。被“误认”的“枪”仿若漂浮的能指,却在一开始就放出“烟雾弹”,形成一张看似严密无比的网。影片围绕“枪”造成悬念,依靠大量的巧合、意外与误会,在一天之内聚拢了一群“无名之辈”,将两条线索引人入胜地融汇到一起。虽也有人对情节设定的非现实性提出疑问,但更多受众对此保持宽容,他们体认着荒诞底色下的人生真实,并与之同频共振。
3.人物性格的生动呈现与主题的感性化。影片塑造了各式各样的底层小人物,他们面临不同困境,有不同愿望,经历过不同的悲喜,用不同方式在生活布下的网中努力突围,在一声叹息之后继续负重前行。一个个鲜活有趣的形象背后是渴望尊严、活出本色的灵魂:改过自新当协警以弥补家人,找回为兄为父的尊严(马先勇);成为有一番辉煌事业的厉害角色(胡广生);把心爱的姑娘娶回家(李海根);做诚信有为、敢担当的老板(高明);拼命也要维护被折辱的父亲(高翔)。四肢僵直、心如死灰的瘫痪女马嘉旗通过请劫匪帮忙摆造型拍照的方式表达着“生之恋”;被金钱俘获的小城“按摩师”肇红霞感动于穷小子李海根的真爱,在被警方讯问的关键时刻选择“包庇”他;马先勇的女儿放弃对粗暴父亲的记恨,用心疼和温柔重新接纳他;被骂成“小三”的刘雯虹在爱人高明落难之时,义无反顾地站出来与一伙地痞拼命……所有这些,都是市井小民力争“自尊与爱”的极致表达,成为荒诞却不浮夸、奇异却不矫情的现实缩影。《无名之辈》通过“真戏假做”道出底层人物的悲喜苦乐,呼唤人性的暖光与坚韧向上的力量。
三、“电影工业美学”视角下的考察
“如果将‘电影工业美学’作为一种整体的概念,那么我们可以细分为重工业美学、中度工业美学、轻度工业美学。……中度工业美学电影,它主要以典型化的故事为核心,以类型化工业流程为美学配方,以人物命运为动力要素,陡转、延展、聚焦或裂变社会现实和个人遭遇,实现电影与社会的双向互动。”[7]就此而言,饶晓志的作品尤其是《无名之辈》是堪称黑马级的“中度工业美学电影”。陈旭光教授提出:建构电影工业美学体系可以遵循“电影四要素图式”,即“作为影像之源的客体世界或想象世界,作为生产者的生产主体,作为本体的电影形态、电影作品,作为接受与传播的第二主体的观众及媒介”[8]。“又可简化分为电影的文本内容、生产机制和传播接受三大层面。”[9]融合上述学术观点,可进一步分析饶晓志导演作品在“电影工业美学”方面的表现。
(一)电影文本内容:双重叙事策略下的“典型化”故事
有观众指出,《你好,疯子!》与美国电影《致命ID》有颇多相似之处,剥开故事表层(人格分裂者的精神世界),二者实际上迥异其趣:《致命ID》是非常缜密“烧脑”的惊悚电影,恐怖悬疑色彩极为浓重,指向人性深处的邪恶;《你好,疯子!》是在悬疑喜剧基调的烘托下展开荒谬的剧情,故事走向并未停留在揭秘释悬的层面,而是通过一面多棱镜折射出城市阶层在现代洪流中人性的幽微复杂和情感欲望的扭曲变形,述说普通人对理想完美人格、对内心向往与需求的深沉渴望。导演说,同《你好,疯子!》一样,“《无名之辈》仍然是一个封闭空间的故事。封闭的不止是那个屋子,还有那座桥,那个城市。它只是把一群人、一群困兽放在了一个小城里。……《无名之辈》里‘尊严’这个主题是比较明显的,但对我来讲,‘无名之辈’这四个字才是主题,才是我创作的出发点,哪怕只是小人物或平凡人,他也有尊严,有孤独,有爱情,还有底层的浪漫。”[10]
两部电影都是讲中国人在生活中被困和突围的故事。《你好,疯子!》侧重内在自我层面的焦灼,《无名之辈》聚焦身份认同层面的忧虑。虽然人物的离奇遭遇跟很多观众的真实生活并不相像,甚至似无交集,但两部影片通过疾病书写和疯癫影像的双重叙事策略,直指现代人的“通病”,反映出当下中国都市工薪阶层和底层小人物所处的、较为普遍的文化语境和时代症候,因而能够收获大批观众感同身受的眼泪和心领神会的笑声。虚构的传奇故事凝结着共通的情感和普世价值观,借由通俗夸张的演绎和世俗化的表达,“典型性”逐步彰显,从而打动了更多观众。
(二)电影生产机制:改良升级版的类型化配方
作为电影圈的“新人”,饶晓志的作品不完全是严格按照规范标准的工业化流程制作的,但从影片的形态、类型、风格、演员表演等方面来看,他在逐渐向电影工业体制中心倾斜,在向“电影工业美学”精神靠近。他“在拍电影之前做了十年的舞台剧,主要是在市场这个空间里打拼,……没有做太多过于迎合市场的作品,……也没有做太多过于当代的、贝克特风格的戏剧,主要是希望能够在两者之间寻求一个平衡。”[11]可见,饶晓志对文化产品的商品属性和文化市场机制是很清楚的,也愿意去找电影“商业性”与“艺术性”的结合点,并努力在体制内发出自己的声音。
1.类型风格的革新。荒诞的现实化也好,现实的荒诞化也罢,饶晓志的两部影片都剑指鲜活的“现实”之态,抱有现实关怀,关注现实焦虑。《你好,疯子!》聚焦内在的心理现实,《无名之辈》则渲染外部的生活现实——二者汇流,印证出新世纪中国喜剧电影在现实品格和类型取向上所呈现出的总体面貌。
受舞台剧思维的影响,饶晓志的电影都不是写实的,但喜剧外壳下包裹着荒诞悲剧的严肃表达,有着某种“电影工业美学的诗性内核”[12]。导演认为,其作品的喜感与幽默气质与开心麻花、周星驰的电影截然不同,不是那种直接性的,“可能也是戏剧对我造成的影响,我认为喜剧性和严肃性并非不能相容。”[13]两部影片基本上找准了观众人生体验和生活情感的最大公约数,没有故弄玄虚,也没有孤芳自赏的喃喃絮语,更没有深度陷入作者个人化情绪的漩涡里。总体来说,通过“喜剧”桥段的积累弱化了清高自我的精英意识和过度私人的感性化宣泄,通过“悲情”涵义的挖掘去尝试着撞击观众的心弦,提醒他们注意喧闹、自嘲、戏谑背后的感伤与刺痛。这也与“电影工业美学”的思想趋于一致:“在电影生产中弱化感性、私人、自我的体验,……不是一种超美学或者小众精英化、小圈子化的经典高雅的美学与文化,而是大众化,‘平均的’,不那么鼓励和凸显个人风格的美学。”[14]
2.高分表演对明星制的超越。饶晓志电影中启用的基本都是实力派演员,像《你好,疯子!》中的万茜、周一围、金士杰、莫小棋等,《无名之辈》中的陈建斌、任素汐、章宇、潘斌龙、王砚辉等。他们不属于当红的明星大牌,甚至寂寂无闻,但凭借精湛的个人演技把角色演绎得入木三分、丝丝入扣。万茜凭《你好,疯子!》荣获第24届北京大学生电影节最佳女演员奖;任素汐、章宇等人的出色表演为电影赚取了“好演员的春天到了”的口碑基础,甚至衍化为“好电影的春天也要到了”的赞誉;而相声小品演员潘斌龙的转型突破也让人倍感惊喜。演员集体认真敬业地为观众提交了一份高分试卷,打破了人们对演员领域做区隔的思维定势,也验证了饶晓志甄选演员的独到眼光。他说:“我认为演员就是演员,我特别不喜欢区分话剧表演和电影表演。在我看来,表演只有好的表演和坏的表演,好演员在舞台和电影里都能表演得很好,其间的区别只是分寸感的问题。”[15]
(三)电影的传播与接受:人物命运与社会现实的互动实效
1.《你好,疯子!》运营策划失利的教训。《你好,疯子!》是饶晓志的电影处女作,从一开始,导演“就刻意去打破自己的惯性思维、叙事方式,首先在文本上做了最大化的区别,可以说舞台剧剧本和电影完全不一样。”[16]影片确有不少闪光点,包括重重幻影的揭示,对人性变异和社会强权的嘲讽,女主一人分饰七角的精彩演绎等。遗憾之处在于,悬疑色彩偏重,在对社会现实和个人遭遇展开的双向意指方面,也有些语焉不详。
该片的宣传口号是“疯进元旦,笑出疗效”,试图营造“疯狂跨年”的气势。相较1500万元的投资,1569.2万元的票房收入显然不尽人意。影片“所呈现出来的效果却是经得起推敲和实践检验的,甚至有人称之为2016年最佳影片。……这次票房失败更应该从宣发方面进行反思,‘选择新年档期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影片惊悚悬疑的风格在新年档期尤其不受欢迎。’”[17]影片宣传定位的偏差导致档期选择失误,不是大制作,没有大明星,宣发力度小,未能引爆足够的话题热度……好口碑与惨淡票房形成让人瞠目结舌的反差,制片方也不得不接受“叫好不叫座”的遗憾结果。
2.《无名之辈》“制宣发”的有益经验。《无名之辈》的宣传标语是“人生如戏,笑着活下去”。该片投资3000万元,最终以7.93亿元票房收盘。对比前作,《无名之辈》更加谙熟观众心理和市场风向,操作也更为沉稳机智。小成本影片突破好莱坞大片的夹击而“扬名立万”,得益于宣发切入点的精准亲民和病毒级别的口碑传播效应。
片名本身带有一种“迷思”色彩,容易在观众之间引发一探究竟的好奇感。故事围绕着小城市的一群普通人曲折多舛的命运遭际展开,急于获取社会认同的人(眼镜儿、大头、波仔,绰号取代了其真实姓名),有名无实的人(马先勇、高明,状态与其姓名涵义相反),毫无生意的残疾人(一天天捱日子的年轻姑娘马嘉旗),都为自己所理解的“尊严”而抗争着。如蝼蚁般渺小的他们疯狂闹腾着,竟合力奏响了现代社会普罗大众孤独心理的最强音。为增强影片“接地气”的贴近感,制作方通过制造我不是无名之辈话题,发布了一系列关于无名小人物的海报,一张张质朴平凡的面孔配上两行扎心实在的“无名”体简文,励志而温暖,进一步缩短了电影与广大观众的心理距离。名人、素人在观影后,迅即通过微博、微信等网络平台纷纷力挺、推荐,更让口碑迅速发酵。电影上映第3天,作为“公知”同时也是“新力量”导演的韩寒发微博:“除了导演编剧一流以外,《无名之辈》的表演也非常棒,……好电影能拯救你的眼睛和心情,好导演好演员就应该有更好的回报,希望大家狠狠买票,让这些优秀的电影人们名利双收吧。”
饶晓志前后两部电影的变化可以窥出电影市场的某些规律,而其作品与“电影工业美学”原则的吻合度也渐高。饶晓志表示,他还没想好下一部电影做什么,也不确定是否会继续关注底层人物。期待这位“新力量”导演能够秉持初心,在其戏剧思维的启发助益下获取更多新突破,在“电影工业美学”浪潮中更加从容、娴熟和稳健,不断推出具有个人标志化风格的上乘之作。
注释:
[1]【美】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程巍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8年版,第40页。
[2]刘小枫:《沉重的肉身》,华夏出版社2015年版,第131页。
[3]【法】米歇尔·福柯:《疯癫与文明》,刘北成、杨远婴译,三联书店2012年版,第27-29页。
[4]焦仕刚:《当代中国电影疯癫影像叙事论》,《当代文坛》,2016年第4期。
[5]王璐,杨璐:《荒诞的现实化与现实的荒诞化——中国当代喜剧电影两种创作思路初探》,《当代电影》,2011年第9期。
[6]【法】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冯克利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第25页。
[7]李立,彭静宜:《再历史:对电影工业美学的知识考古及其理论反思》,《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期。
[8][14]陈旭光:《论“电影工业美学”的现实由来、理论资源与体系建构》,《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期。
[9]陈旭光,李卉:《争鸣与发言:当下电影研究场域里的“电影工业美学”》,《电影新作》,2018年第4期。
[10][11][13][15]饶晓志,陈晓云,李卉:《〈无名之辈〉:一种逆袭的可能》,《电影艺术》,2019年第1期。
[12]徐洲赤:《电影工业美学的诗性内核及其建构》,《当代电影》,2018年第6期。
[16][17]牛春梅:《〈你好,疯子〉票房惨淡话剧改编电影冰火两重天》,http://media.people.com.cn/n1/2017/0119/c40606-2903411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