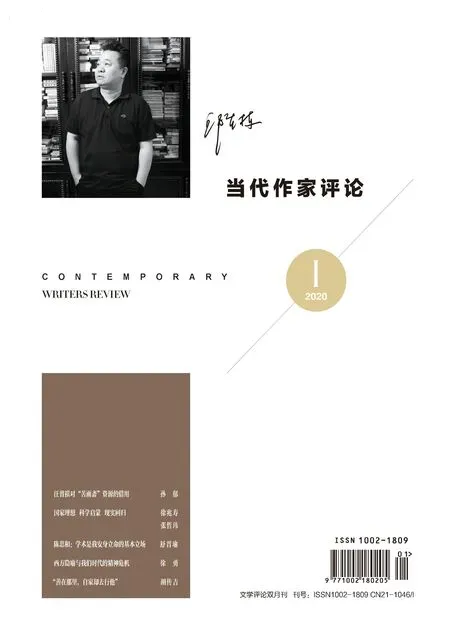邂逅密敌:汪曾祺的《复仇》*
〔美〕费佳兰 著 潘 莉 译
“一个短篇小说,是一种思索方式,一种情感形态,是人类智慧的一种模样。”(1)汪曾祺:《短篇小说的本质》,《汪曾祺全集》第3卷,第31、29、29页,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
“我们设想将来有一种新艺术,能够包融一切,但不复是一切本来形象。又与电影全然不同的,那东西的名字是短篇小说。”(2)汪曾祺:《短篇小说的本质》,《汪曾祺全集》第3卷,第31、29、29页,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
正如抒情主义的爆发与战时流离失所的迫切推动了诗歌和漫画领域的形式创新,战争的混乱现实也激发了虚构小说家对形式进行实验。尤其在战争的最后几年,针对精巧线性情节与英勇主人翁叙事的缺乏,许多作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张爱玲在1944年《自己的文章》一文中批评了“善与恶,灵与肉的斩钉截铁的冲突”的“古典的写法”,(3)张爱玲:《一个人的文章》,《流言》,第93-94页,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2。并说道:“我以为,文学的主题论或者是可以改进一下。”她认为,“写小说应该是个故事,让故事自身去说明,比拟定了主题去编故事要好些。”(4)张爱玲:《一个人的文章》,《流言》,第93-94页,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2。张爱玲对过度发展的情节的厌弃与战时许多作家一致。在《明治文学之追忆》一文中,周作人表达了相似情绪:“老实说,我是不大爱小说的,或者因为是不懂所以不爱,也未可知。我读小说大抵是当作文章去看,所以有些不大像小说的,随笔风的小说,我倒颇觉得有意思,其有结构有波澜的,仿佛是依照着美国版的小说做法而做出来的东西,反有点不耐烦看。”(5)周作人:《明治文学之追忆》,钱理群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362-363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为了代替依“美国版的小说作法”而人为设计的情节结构,周作人提出一种较为宽松的文章结构,选择了对于中国读者更为熟悉的“随笔”风格。正如战时的诗歌,作家们也更倾向于倡导小说的“散文化”。(6)战时作家对散文化需求的倡导与战时诗歌的“散文化”(prosification)和“文章化”(essayization)一致,但在这里,散文化唯一合逻辑的翻译是“文章化”(essayization)。除了采纳散文元素,他们还认为小说也应该借鉴其他文类。例如,沈从文曾敦促小说应该从诗歌、绘画、音乐和散文中汲取元素。
与在联大的老师沈从文一样,汪曾祺也认为短篇小说应该借鉴其他文类。在《短篇小说的本质》一文中,汪曾祺写道:“至少我们希望短篇小说能够吸收诗、戏剧、散文一切长处,而仍旧是一个它应当是的东西,一个短篇小说。”(7)汪曾祺:《短篇小说的本质》,《汪曾祺全集》第3卷,第31、29、29页,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汪曾祺声称,正是由于中国作家以往并未重视短篇小说,使
得短篇小说缺乏一个严格的界限,因此短篇小说特别适合这种跨文类实验。(8)汪曾祺:《短篇小说的本质》,《汪曾祺全集》第3卷,第28、22页,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此外,汪曾祺发现,与中长篇小说所要求的持续叙事相比,短篇小说的松散形式明显更适合于刻画战时混乱的现实。
在他第一本短篇小说集《邂逅集》(1949)中,汪曾祺尝试对短篇小说进行实验,并试图扩展短篇小说的文类界限。(9)汪曾祺:《邂逅集》,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49。他将其写于战时和战后的八个故事收入该集:《复仇》(1944)、《老鲁》(1945)、《艺术家》(1948)、《戴车匠》(1947)、《落魄》(1947)、《囚犯》(1947)、《鸡鸭名家》(1947)、《邂逅》(1948)。在每个故事中,汪曾祺的第一人称叙述者“邂逅”一系列“他者”,包括一个和尚、一个前士兵、一个哑巴艺术家、一个木匠、一群罪犯、两个来自其故乡高邮的男人,以及一个盲人表演者和他的女儿。汪曾祺表示,该集子选用“邂逅”之名旨在呈现第一人称叙述者的多样经历,并且更普遍地表达文学灵感的偶然性。正如他自己写道:“我的小说的题材,大都是不期然而遇,因此我把第一个集子定名为‘邂逅’。”(10)汪曾祺:《〈汪曾祺短篇小说选〉自序》,《汪曾祺全集》第3卷,第166页,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
从更广泛的角度而言,“邂逅”标题反映了汪曾祺的生活观:“散漫的”“充满偶然”,而非“编排连缀出来的”。(11)汪曾祺:《短篇小说的本质》,《汪曾祺全集》第3卷,第28、22页,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事实上,汪曾祺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生活是十分颠沛流离且“充满偶然”的。与穆旦不同,汪曾祺并没有与联大师生一起长途徒步去昆明。战争爆发之际,汪曾祺是一名高中生,当日本军队占领其故乡高邮,他逃到附近的一所佛寺藏身了六个月。1939年,汪曾祺途经上海、香港和越南辗转到达昆明,并成为联大学生,在那里他向沈从文学习并主修中国文学。1944年,汪曾祺离开联大,在昆明郊区一所中学教了两年书,1946年进行了短期归家探亲。此后,汪曾祺前往上海,在那里教了两年书并于1948年春移居北京。
对于汪曾祺来说,尽管战争年代充满了出乎意料的旅行与偶然的相遇,他的文学背景却呈现出中西影响兼收并蓄的融合。汪曾祺这样描述他的大学生涯:“我读的是中国文学系,但是大部分时间是看翻译小说。”(12)汪曾祺:《自报家门》,《汪曾祺全集》第4卷,第286、288页,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汪曾祺引用过并受其影响的作家包括安德烈·纪德、弗吉尼亚·伍尔夫、让·保罗·萨特、安东·契诃夫、普利米奥·阿索林(荷西·马尔迪奈斯·卢伊斯的化名)、马塞尔·普鲁斯特、伊凡·屠格涅夫和赖内·马利亚·里尔克。(13)汪曾祺:《自报家门》,《汪曾祺全集》第4卷,第286、288页,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尽管汪曾祺提到外国作家对他作品的影响,他的文学训练同样深深地沉浸于中国传统美学之中。除了在联大主修中国文学外,汪曾祺还记得他在少年时就已会背诵宋词并熟读古文。此外,他的许多小说受到中国本土文化的启迪,包括古代哲学著作《庄子》,苏轼的诗文,杜甫的诗,明代学者归有光的散文,以及沈从文、鲁迅和废名的小说。
汪曾祺沉浸于多种异质影响——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的混合之中,与他的老师沈从文所走的道路相似。沈从文的小说受到西方作家和思想家的影响,如詹姆斯·乔伊斯、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契诃夫、阿尔丰都·都德、玛克西姆·高尔基、居伊·德·莫泊桑、屠格涅夫、威廉·莎士比亚和纪德,同时也受到本土影响,包括明清白话小说、《庄子》、司马迁的《史记》以及陶渊明的传统诗歌。(14)见金介甫(Jeffrey Kinkley)在《不完美的天堂》中关于沈从文文学影响的讨论,〔美〕金介甫编:《不完美的天堂》(Imperfect Paradise),火奴鲁鲁,夏威夷大学出版社,1995。总体而言,汪曾祺的小说与战前其他新传统主义的京派作家相似,如试图寻找“传统中的现代性”和“现代性中的传统”的周作人和废名。(15)这些术语借自史书美在《现代的诱惑》一书中对废名小说的分析,见〔美〕史书美:《现代的诱惑》(Lure of Modern),第192页,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2001。面对各种潮流,汪曾祺的作品含纳了异常多样的文类,包括诗歌、散文、戏剧、音乐、绘画、“乡土”小说,以及流行武侠故事。此外,他的文学语言十分流畅,并借鉴了传统美学、西方现代主义和本土方言。汪曾祺战时短篇小说美学上的松散与散文化的特质也可见于由路翎、卞之琳、端木蕻良、萧红、沈从文、张爱玲和师陀所创造的其他战时现代主义作品之中。(16)关于1940年代由路翎、卞之琳、端木蕻良、萧红、沈从文和张爱玲创作的战时短篇小说的形式实验分析,见钱理群编:《对话与漫游:四十年代小说研究》,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关于师陀小说的讨论,见〔美〕戴伊(Steven Day):《没有战场的英雄》(Heroes without a Battlefield),第77-121页,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博士论文,2009;戴伊:《师陀》,〔美〕穆润陶(ThomasMoran)编:《中国小说家传记辞典1900-1949》(Chinese Fiction Writers 1900-1949),第209页,法明顿希尔斯,汤姆森·盖尔出版社,2006。关于路翎短篇小说的分析,见〔美〕舒允中:《内线号手:七月派的战时文学活动》(Buglers on the Home Front),第107-128页,奥尔巴尼,纽约州立大学出版社,2000。
在本章中,我将细读汪曾祺《邂逅集》中的四个故事:《复仇》《老鲁》《鸡鸭名家》《邂逅》,并将按时间顺序进行讨论,从写作于1944年的《复仇》开始,以写于1948年抗战后的《邂逅》结束。通过与战后文章《短篇小说的本质》和几篇文章的对话来分析汪曾祺短篇小说,我将绘制战时汪曾祺现代主义风格的发展图谱。与他早期小说注重内在性的显著西方现代主义风格不同,在战后时期,汪曾祺开始书写普通百姓,并从方言和口语中汲取灵感。他对自己挪用西方现代主义技巧也变得愈加批判,这在他讨论弗吉尼亚·伍尔夫1924年创作的现代主义作品《本涅特先生和布朗太太》的《短篇小说的本质》一文中十分明显。
无论如何,即便重点转移了,汪曾祺所有的短篇小说都体现着各种各样的本土与西方的影响。在《复仇》中,他利用道家哲思和弗洛伊德思想,将传统武侠故事重新书写成为关于战时暴力内涵的哲学沉思。《老鲁》延续鲁迅书写被压迫的他者的现实主义短篇小说传统,但与鲁迅精心策划情节结构不同,汪曾祺采用一种更为松散的散文风格。《鸡鸭名家》体现汪曾祺对乡土流派的吸收,并运用意识流叙事来揭示乡土如何在他流离失所的叙述者心灵中被重塑。最后,我认为,《邂逅》可以被阐释为是汪曾祺对伍尔夫《本涅特先生和布朗太太》的重写,在其中他将伍尔夫在小说中使用的火车隐喻改编成了一位返乡作家的一次渡轮之旅。
1942年,诗人卞之琳在联大学生杂志《文聚》特刊上发表了他译的里尔克的散文诗《旗手》。同一期,卞之琳还撰写了一篇文章。在文章中他声称,里尔克的作品通过将诗歌、短篇小说、史诗和电影等元素融合在一起,体现了现代小说的理想。在描绘里尔克散文诗的电影品质时,卞之琳写道:“《旗手》虽不像电影,可也是一景一景地展下去,截去了中间的连锁——这也是现代写小说,尤其写叙事诗的既成也是该有的一般趋势,因为尤其到现在大家受过看电影的训练以后,讲故事再这样供给许多可省的桥梁也许反成了障碍,叫人不耐烦。”(17)卞之琳:《福尔的〈亨利第三〉和里尔克的〈旗手〉》,《文聚》,昆明,文聚社,1942年11月14日,收入《卞之琳文集》,第472-473页,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
对于联大学者来说,里尔克的“一景一景地”发展和避免“可省的桥梁”的散文诗体现了一种新颖的、虚构的小说创作方式,这种方式支持抒情主义的表达。此外,卞之琳还赞扬了里尔克对暴力的非英雄的和反法西斯主义的描绘:“里尔克在这里却只是推荐充实的生活,与任何主义都不相干,并没有像法西斯蒂们一样盲目地歌颂战争。他展示得美的是有血有肉的充实、行动、强烈的爱与死。照这个情形来推测,纳粹军队里如果还有读书的机会,也可能又会流行起《旗手》吧。”(18)卞之琳:《卞之琳文集》,第483页,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
与联大其他人一样,汪曾祺对卞之琳翻译的里尔克作品印象深刻。(19)关于卞之琳译作对汪曾祺短篇小说影响的分析,见姚丹:《西南联大历史情境中的文学活动》,第292-293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在冯至1944年写的《伍子胥》后记中,他特别提到了里尔克的散文诗是这一作品的主要灵感来源。见刘福春编:《冯至全集》第3卷,第426-427页,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此外,冯至女儿冯姚平也曾回忆她父亲在阅读卞之琳译作后深受感动,随后创作了《伍子胥》,见冯姚平:《心底的热流》,2011年6月7日访问,引自http://culture.163.com/edit/001205/001205_43816.html。在《短篇小说的本质》一文中,汪曾祺回忆他读完译作后,在沈从文的课上站起身大叫:“一个理想的短篇小说应当是像《亨利第三》和《军旗手的爱与死》那样的!”(20)汪曾祺:《短篇小说的本质》,《汪曾祺全集》第3卷,第19、29页,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此后不久,他写了一篇关于“一个理想的短篇小说”的文章作为老师沈从文布置的题目的答卷,在这篇文章中他认为里尔克的散文诗是小说写作的典范。(21)汪曾祺:《短篇小说的本质》,《汪曾祺全集》第3卷,第19、29页,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在《短篇小说的本质》一文中,汪曾祺重述这一观点,并且赞扬里尔克跨越短篇小说和诗歌之间的文类界限的形式实验。但与此同时,他也声称里尔克的诗歌缺乏散文的“随意说话的自然”“广度”和“美”。(22)汪曾祺:《短篇小说的本质》,《汪曾祺全集》第3卷,第29页,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
两年后的1944年,汪曾祺写下了他自己的关于一个流浪剑客的非常规故事——《复仇》。(23)1944年版的《复仇》可见《汪曾祺全集》第1卷,第29-38页,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除非另有说明,文中所有对《复仇》的引用均出自1944年版。该小说由史雅堂(Adam Schorr)和史书美译成英文,题为“Revenge”,收录于《译丛》(香港)1992年第37期,第35-42页。在这一作品中,他不仅将诗歌和小说元素注入故事,还将散文元素带入,以期超越里尔克的形式实验。正如他在1982年写的《〈汪曾祺短篇小说选〉自序》中所说:“我年轻时曾想打破小说、散文和诗的界限。《复仇》就是这种意图的一个实践。”(24)汪曾祺:《〈汪曾祺短篇小说选〉自序》,《汪曾祺全集》第3卷,第165-166页,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1946年,《复仇》在《文艺复兴》杂志上发表,这一版后来成为《邂逅集》中的第一个故事。1941年,汪曾祺曾写过一个早些版本的《复仇》,该版同年在重庆《大公报》上发表。(25)关于1941年版《复仇》,见《汪曾祺全集》第1卷,第1-6页,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
汪曾祺的小说《复仇》,尤其是第二个版本,可以理解为是对旷日持久的抗日战争的一种清醒回应。(26)金介甫也发现了汪曾祺老师沈从文的战时作品中的反英雄崇拜,并对此有所评论。见〔美〕金介甫:《沈从文传》(The Odyssey of Shen Congwen),第249-250页,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87。正如历史学家易社强(John Isreal)在对联大的研究中所描述的那样,抗日战争后期,或称之为联大的“考验的岁月”(“years of trial”)(27)见〔美〕易社强(John Isreal):《考验的岁月:1943-1945》,《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Lianda),第333-366页,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98。的特点是,加剧的轰炸袭击、通货膨胀、粮食短缺,以及学校补给和经费的缺乏。此外,昆明的居民还须忍受美军的存在,汪曾祺回忆说,这些美国兵带着妓女,大声地开着吉普车四处乱转,留下的保险套散落在他曾深夜漫步过的宁静的墓地四周。(28)汪曾祺:《观音寺》,《汪曾祺全集》第4卷,第184页,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
然而,尽管《复仇》两个版本都是针对战时文学赞美暴力的主流而作,这两个版本的结构却截然不同。第一版可以看作是关于一个侠义剑客不断寻找仇敌的儿童睡前故事,它以副标题“给一个孩子讲的故事”开头,以警告结束:“不许再往下问了,你看北斗星已经高挂在窗子上了。”相比之下,第二版以《庄子》的《外篇·达生第十九》中反对暴力的警句开头:“复仇者不折镆干。虽有忮心,不怨飘瓦。”(29)《庄子》原文见陈鼓应编:《庄子今注今译》,第467页,北京,中华书局,1983。《庄子》中该句后的文字继续着同样的主题:“是以天下平均。故无攻战之乱,无杀戮之刑者,由此道也。”(30)〔美〕任博克(Brook Ziporyn)译:《庄子:基本读本》(Zhuangzi:The Essential Writings),第78页,印第安纳波利斯,哈克特出版公司,2009。在谈到道家哲学对自己创作的影响时,汪曾祺在《自报家门》中说道:“有评论家说我的作品受了两千多年前的老庄思想的影响,可能有一点,我在昆明教中学时案头常放的一本书是《庄子集解》。”(31)汪曾祺:《自报家门》,《汪曾祺全集》第4卷,第290页,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
在《复仇》第二个版本中,道教和佛教主题显而易见,包括对“庄周梦蝶”的暗示;(32)“庄周梦蝶”回应着“事物变形”的概念。对“庄周梦蝶”的分析,见陈幼石:《中国古文的意象与思想:韩柳欧苏古文论》(Images and Ideas in Chinese Classical Prose),第148-149页,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88。在梦中,汪曾祺的小说主人公回忆和尚“飘然而去”,“双袖飘飘,像一只大蝴蝶”。此外,在第一个版本中,小说主人公和头陀一起在山上挖一条隧道,而第二个版本以一幅更令人回味和抽象的图景结束:“有一天,两副錾子同时凿在虚空里。第一线由另一面射进来的光。”理解这些叙事的一种方法是将它们视为对轮回或虚空的佛教概念的指涉。此外,最后一句话中“射进来的光”可以看作是对启蒙的追求和对暴力场域的精神超越的象征。正如穆旦和叶浅予在战争后期开始倾向于哲学的和自我反思性的主题,汪曾祺在他重写的《复仇》中也表现出相似的转变。
除了获得一种哲学和精神意义的内涵外,第二版本还遵循了卞之琳的建议——在叙述中避免“可省的桥梁”,创造像电影一样的“一景一景地”展开的故事。比较两个版本的开头部分有助于阐明它们之间的不同。第一个版本起于旅行者跋涉至一座寺庙,希冀得到一些干粮果腹:
一缶蜜茶,半支素烛,主人的深情。
“今夜竟挂了单呢。”年青人想想暗自好笑。
他的周身装束告诉曾经长途行脚的人,这样的一个人,走到这样冷僻的地方,即使身上没有带着干粮,也会自己设法寻找一点东西来慰劳一天的跋涉,山上多的是松鸡野兔子。
第二个版本同样以素烛和蜂蜜的意象开始,然而删除了解释旅行者为何长途跋涉后深感饥饿的细节。取而代之的是,叙事被生动的感官形象和看似不连贯的反思所打断:
一支素烛,半罐野蜂蜜。他的眼睛现在看不见蜜。蜜在罐里,他坐在榻上。但他充满了蜜的感觉,浓,稠。他嗓子里并不泛出酸味。他的胃口很好。他一生没有呕吐过几回。一生,一生该是多久呀?我这是一生了么?没有关系,这是个很普通的口头语。谁都说:“我这一生……”
在《复仇》第二个版本的英译本中,虽然史书美将该段翻译成过去时态,但考虑到中文是一种无变体语言,原文中的时态其实是模棱两可的。然而,原文中汪曾祺使用的“现在”一词(史书美译成“在那时”)传递了一种当下感。若是译成现在时态,汪曾祺的文字便获得了叙事动力。
在整个故事中,汪曾祺经常使用“现在”一词来不时强调主人公思想的当下性。(33)唐湜也对他所称谓的汪曾祺小说中“进行式”的普遍使用做出评论。见唐湜:《虔诚的纳蕤思——谈汪曾祺的小说》,钱理群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493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汪曾祺曾说,通过描绘主人公脑海中思想和图像的流动,他试图模仿他从阅读西方现代主义作家(如詹姆斯·乔伊斯和弗吉尼亚·伍尔夫)的作品中所学到的“意识流”技巧。(34)陆建华:《汪曾祺的春夏秋冬》,第73-75页,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5。的确,正如李陀在分析《复仇》时所观察到的,该故事中汪曾祺的写作风格明显是现代主义和欧化的,这在他运用意识流技巧和大量使用代词时可以明显看出。(35)李陀:《汪曾祺与现代汉语写作——兼谈毛文体》,《今天》1997年第4期。在《谈风格》一文中,汪曾祺自称《复仇》有他“模仿西方现代派的方法的痕迹”,还说他“竭力想摆脱我所受的各种影响,尽量使自己的作品不同于别人”。见《谈风格》:《汪曾祺全集》第3卷,第341页,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
然而,在《自报家门》中,汪曾祺自述他的散漫而意象式的散文也部分受到宋代诗人和散文家苏轼的启发:
我很向往苏轼所说的:“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我的小说在国内被称为“散文化”的小说。我以为散文化是世界短篇小说发展的一种(不是唯一的)趋势。(36)汪曾祺:《自报家门》,《汪曾祺全集》第4卷,第292页,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
汪曾祺的故事以流畅和散文化风格为特征,一如徜徉在主人公和叙述者思想和感官印象的交替流动之间,与苏轼作品产生回响。在这个意义上,汪曾祺的散文反映了他的观点,即文章形式体现“随意说话的自然”。(37)汪曾祺:《短篇小说的本质》,《汪曾祺全集》第3卷,第29页,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特别是,鉴于鲜明情节的缺失和汪曾祺不时散布其间的哲学反思,可以将《复仇》理解为是关于战时暴力与时间流逝的哲理文章或冥思。
汪曾祺使用意识流技巧产生了一种散文流,而当图像、思想、情感和记忆流通主人公心灵时,这种意识流也产生了一种抒情即时性。此外,汪曾祺通过在故事中途加入一段自由诗,增强了《复仇》第二版的抒情元素。在该部分,他描写了大片水面上闪烁的阳光,并描绘了以雨、雾、海水和白沫出现的水的各种形态。此外,汪曾祺在“角”和“鸟”、“端”和“烟”、“船”和“转”之间押韵,还使用了头韵。诗中“灯”和“荡”的发音与故事中不断响起的和尚敲磐发出的“丁——”声产生共鸣。
除了吸收诗歌和散文形式元素外,《复仇》还包含许多如彩色绘画般的段落。在一个场景中,叙述者如此描述旅行人:“你,一个小小的人,向前倾侧着身体,在黄青赭赤之间的一条微微的白道上走着。”在另一个场景中,主人公试图回忆他母亲的身形:“而投在母亲的线条里着了色的忽然又是他的妹妹。”并且,在自由诗部分,汪曾祺呈现出一幅兼具具体和抽象元素的生动图像:“来了一船瓜,一船颜色和欲望。”
汪曾祺不仅容纳视觉上令人回味的图像,并使用押韵和听觉上产生共鸣的意象,这符合他所坚信的短篇小说应当包含绘画和音乐元素的观点。在《短篇小说的本质》一文中,汪曾祺称赞了拉宾德拉纳特·泰戈尔和马塞尔·普鲁斯特将其他艺术形式融入他们自己的小说中的尝试:
泰戈尔告诉罗曼·罗兰他要学画了,他觉得有些东西文字表达不出来,只有颜色线条胜任;勃罗斯忒在他的书里忽然来了一段五线谱,任何一个写作的人必都同情,不是同情,是赞同他们。(38)汪曾祺:《短篇小说的本质》,《汪曾祺全集》第3卷,第29页,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此外,在《两栖杂述》中,汪曾祺将创作小说的过程比作绘画。见汪曾祺:《两栖杂述》,《汪曾祺全集》第3卷,第197页,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
因此,阐释《复仇》的方法之一是将其视作一次文类实验,这种实验不仅横跨诗歌、散文和小说,而且横跨音乐与绘画之间的界限,并通过一系列通感扩展短篇小说的边界。然而,这个故事可以接受多种不同的阐释,正如我们的分析,它可以被理解为关于暴力的道教式沉思。此外,它也可以被理解成在写作武侠小说过程中的作者的元小说肖像。这种具有表演性的解读符合汪曾祺在《短篇小说的本质》中的主张,即短篇小说应从戏剧中汲取灵感,从而使其获得“活泼、尖深、顽皮、作态”。(39)汪曾祺:《短篇小说的本质》,《汪曾祺全集》第3卷,第28页,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这种解读的证据可以在故事开头附近找到,故事讲述到旅行人独自面对一支闪烁的蜡烛,开始记下自己的旅途:“可是原来描写着静的,现在全表示着动。他甚至想过自己作一个货郎来给这个山村添加一点声音的。”这里,叙述者使用了包含“写”字的“描写”一词,表明这个旅行人剑客已经参与关于他的旅途的描述。然而,尽管汪曾祺的主人公试图对自己的旅途进行一个连贯的叙述,但故事似乎在讲述过程中发生了变化,最终他以“在相似的风景里做了不同的人物”而结束。
叙事视角的转变增加了这种错位感。汪曾祺的主人公/叙述者意识在矛盾的声音中嘲弄自己。有时,他把自己幻想成自己故事中的英雄,并大胆宣布他的复仇计划:“但是我一定是要报仇的!”“我要走遍所有的路。”然而,叙述者有时嘲笑并轻视旅行人剑客。叙述者质问:“你是否为自己所感动?”在另一个场景中,叙述者转换至第三人称视角嘲笑了剑客对他自己困境的怜悯:“他为自己这一句的声音掉了泪,为他的悲哀而悲哀了。”虽然在这一段落,叙述者用第二和第三人称交替指涉他的主人公,但在上文引述过的开头段落中,叙述者则用第一和第三人称交替指称旅行人剑客。事实上,贯穿整个故事,汪曾祺的叙述者转换在第一、第二和第三人称之间而没有使用语法标识来暗示这种叙述视角的改变。这些句法转变的作用在于模糊叙述者和主人公的界限——尚不清楚谁该为呈现在读者眼前的这个武侠故事负责。
此外,通过如此迅速的视角转换,汪曾祺将他的故事向具有意识分裂表征的弗洛伊德式阐释开放。事实上,在战时,汪曾祺在沈从文的指导下读过弗洛伊德,并且,沈从文自己的战时小说如《看虹录》中刻画的心态各异的人物也反映了弗洛伊德的影响。(40)关于沈从文对弗洛伊德和精神分析学的兴趣的更多分析,见〔美〕金介甫:《沈从文传》(The Odyssey of Shen Congwen),第254页,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87。
从这一角度分析,汪曾祺的主人公与其“敌人”之间的冲突可以被阐释为关于自我与阿希斯·南地(Ashis Nandy)所说的“贴身的损友”(“Intimate Enemy”)或置身殖民境地的自我之间相遇的一种精神分析式寓言。正如南地的观察,被殖民者既在物质层面受到殖民者的法律引介,又在内化殖民者意识形态时受到心理层面的影响。南迪认为,这种“第二形式殖民”是在“殖民主义不但殖民人的身体,还殖民他们的心智”时发生,结果是“西方无所不在,在西方的内部与外部,既在结构之中,也在心智里面”。(41)〔印〕阿希斯·南地:《贴身的损友》(The Intimate Enemy:Loss and Recovery of Self Under Colonialism),第6页,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2010。借助南地的理论视域,在主人公看来,汪曾祺的叙述者和和尚之间的相遇可以被理解为东西方意识形态(如弗洛伊德主义和道教)之间冲突的寓言。事实上,当叙述者/主人公渴望道教层面的和平与超越,并符合弗洛伊德的心理观念时,他发现他的意识不断地处于分裂状态。更甚者,当他采用以大量使用代词和强调心理内在为特征的西方化的文学风格时,他发现自己已然深陷殖民者语言之中。
为了报复,叙述者将自己想象成一个英勇的剑客,从而展现了南地所说的被殖民者的“超级雄性质地”(hyper-masculinity),该男性试图通过建立一个防御性男性身份来克服殖民暴力带来的阉割可能。(42)例如,南地描述了印度男性试图“用殖民者之矛攻其之盾而重获一种作为兴都信仰者之印度人的自尊”,去寻求“一个对同胞和殖民者都可以接受的超级雄性质地或超级刹帝利自身”。见〔印〕阿希斯·南地:《贴身的损友》(The Intimate Enemy:Loss and Recovery of Self Under Colonialism),第52页,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2010。事实上,通过创作一个请求留宿于寺庙的剑客的故事,汪曾祺将他自己战时流离失所求助于寺庙的经历彻底改造成了一段英勇的旅行,而非与数百万其他人一起逃亡的难民之旅。(43)关于汪曾祺对他自己在战时流离失所于一所寺院的描写,见汪曾祺:《〈汪曾祺短篇小说选〉自序》,《汪曾祺全集》第3卷,第92-93页,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还可见汪曾祺:《关于〈受戒〉》,《汪曾祺全集》第6卷,第336-340页,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关于汪曾祺战时流亡至寺院的虚构性再创作,见汪曾祺:《庙与僧》《受戒》,《汪曾祺全集》第1卷,第65-71、322-343页,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然而,与南地的被殖民者不同,汪曾祺的叙述者最终决定不对其敌人复仇,而是试图握手言和。
在史书美关于《复仇》的解读中,她在寓言层面阐释汪曾祺的剑客和“敌人”之间的和解,作为“自我与他者”或“中国与西方”之间消除隔阂的隐喻:最终,这种自我与他者区别的取消可以隐喻性地被解释为中西方区别的消逝。事实上,在汪曾祺的作品中,人们不再能够找出纯粹的中国因素或是纯粹的西方因素。汪曾祺散文能够抓住人物内心想法的诗学厚度,是苏轼“散”之美学和西方现代主义心理描写倾向共同作用的结果。这种“散”的风格的结果又类似于今天的后现代。(44)〔美〕史书美:《现代的诱惑》(Lure of Modern),第383页,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2001。
正如史书美所指出,因各种文类、叙事和时间观的实验以及受到的中西文学影响,汪曾祺文章的“散”接近了后现代。史书美关于汪曾祺小说中的中西融合的观察,与汪曾祺自己关于他努力跨越中西文化鸿沟的陈述相吻合。在散文《两栖杂述》(1982)中,汪曾祺将他自己视为“两栖类”或“杂家”,一位在作品中融合不同文化传统的作家。(45)汪曾祺:《两栖杂述》,《汪曾祺全集》第3卷,第196-203页,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我总是希望能把古今中外熔为一炉。”(46)汪曾祺:《两栖杂述》,《汪曾祺全集》第3卷,第202页,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也可见汪曾祺:《我是一个中国人》,《汪曾祺全集》第3卷,第299-304页,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在这篇文章中,汪曾祺说道:“外来影响和民族风格不是对立的矛盾。民族风格的决定因素是语言。”还可见他在《捡石子儿(代序)》中关于中西美学的相关言论,《汪曾祺全集》第5卷,第244-251页,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
然而,尽管汪曾祺在《复仇》中试图消除传统与现代之间的隔阂、自我与他人之间的鸿沟,但他笔下的头脑中不断产生对话的精神分裂的剑客却证实着消除这些鸿沟的困难。在某些方面,汪曾祺成功地引起人们对中西美学差异的关注。例如,大量使用代词和指示词的快速转换便是一种与中国传统散文或诗歌相异的西方现代主义风格的标志。(47)李陀指出《复仇》第一段中有15个代词,见李陀:《汪曾祺与现代汉语写作——兼谈毛文体》,《今天》1997年第4期。此外,他对分裂心理的描写和对自我的现代主义关注与他在该故事中涉及的佛教和道教关于和平与和解的主题并不相符。被阐释为一种心理分析寓言,汪曾祺的小说很大程度上并非代表了自我与他者界限的消融,而是呈现着叙述者的心理战役——在旷日持久的战争和外国入侵的混乱之中努力找寻个人意义和哲学慰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