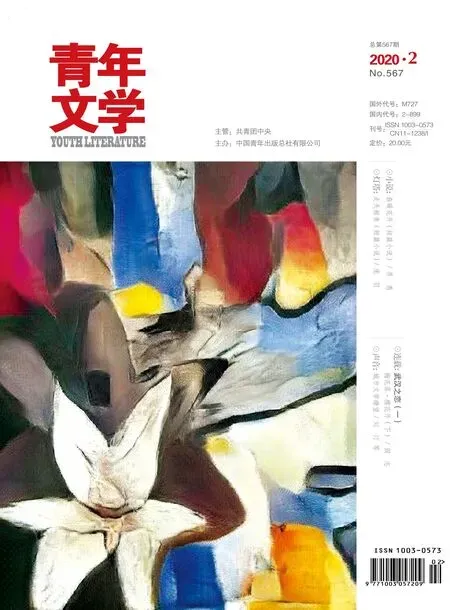宇宙飞船
文/庞 羽
在霍金所说的那个世界之前,我们的宇宙是个摇摇晃晃的孢子。有一天它决定做些什么:于是它破开了。为了缓解疼痛,它隐匿了过于亮眼的星系。谁也不知道这些星系在哪里。可它们就是在那里,闪烁着我们看不见的巨大光芒。
哥哥说这些时,神情总是很忧伤。我不知道这个世界会有人为自己的诞生感到惭愧。你知道吗?哥哥转头看着我。我们身上每一个元素、每一个分子都来自一百四十亿年前的那次爆炸。我们的眼睛,来自伽马射线下的一颗彗星;而我们的指甲,又来自仙女星座第八颗红色星球上的一座丘陵。在我们出生前,我们身体的所有部分都已经存在。在一股温柔的力量下,我们凝聚成我们。而我们死去后,我们的所有部分依旧存在。在另一股神圣的力量下,我们完成了从此处到彼处的旅程。
我不知道哥哥到底在说什么。但我知道他很了不起。他说的话,就像雪白的灯光照射在夜路上,我们穿行,消失,直至身后的白雪覆盖了脆弱的光芒。我依旧相信那些白雪。哥哥一个人立在白雪中,像一把雨伞遗落在四下无人的商场。我明白那种感觉。当独居的你打开冰冷的冰箱。当邮局寄来一封已逝世的老友的信。当苦练多时的你跑到了第一名,却无人与你击掌。后来,我和哥哥到夫子庙吃糖葫芦时,哥哥突然停住了脚步。我问他怎么了,他举起糖葫芦棒,说宇宙飞船舰队要起飞了。看着哥哥的笑脸,我才明白,这个世界宛如一道堤岸,哥哥的海洋从未涨潮。
哥哥拿着大学毕业证书回来时,阿爸正在切牛肉。这几年正是经济寒冬,企业效益不行。阿爸和妈妈讨论过多次,哥哥应该找个怎样的工作。哥哥常常和阿爸顶嘴,关你什么事。阿爸难过地垂下头。哥哥觉得自己是阿爸的外人。阿爸让他考个公务员,或者找银行。哥哥沉默。妈妈将辣椒酱和醋拌在一起,双手一拢,牛肉片排在了酱料碟边缘。阿爸热情地招呼我们吃饭,转身去了厨房,啪的一声,他拍碎了蒜瓣,碾碾细,刀刃一挑,码放在牛肉筋腱上。
我不喜欢牛肉配大蒜。哥哥说。
阿爸用筷子将蒜末拨了拨。
哥哥再没说话。他吃了两碗饭。我看着他的筷子在耳侧纷飞攒动。原来哥哥吃饭这么快呀。后来我喜欢上了一个爱吃饭的男孩。那个男孩爱吃学校门口的盖浇饭,我陪他去。大部分浇头都是我吃的,那个男孩吃了两份白米饭。我心疼他,同时也想起了哥哥。哥哥这么用力地吃饭,是为了抵御什么吧。他明明知道不是自己的错,却一遍遍地道歉。他是那种不把碗里的东西吃完,就感觉对不起主人的人。我和那个爱吃饭的男孩分手后,才体会到哥哥的艰难。米饭里有大量的能量。却又那么便宜。哥哥和我说过,天上的星星其实是神明撒的一把米粒。我们的地球也是。我喜欢他说的这些话。在日后的漫长岁月中,再没有人和我表示过对于宇宙的关怀。
次年夏日,我来到了这座以鸭血粉丝闻名的城市。哥哥没有成为公务员,也没有考取银行。哥哥在南京的哪个角落,我一直无法得知。阿爸说随他去。哥哥还是那时的倔脾气。阿爸和我说过,他第一次去妈妈家时,哥哥将家里所有饭碗摔得粉碎。阿爸将一只碗拼凑起来,摆在了哥哥的窗台前。后来,阿爸和妈妈结婚,又有了我,哥哥没有发一次脾气。然而这次,我觉得哥哥是真的生气了,他不是生我们的气,他是对自己生气。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能够原谅自己,直到春节过后的一天,哥哥出现在了我住所的门前。
你有五号电池吗?哥哥的第一声问候是这一句。
哥哥这大半年来在做什么,阿爸不知道,我也不知道。妈妈问过阿爸,阿爸说不要汇钱给他。我在南京一家美容机构上班,每个月都会往他的账号里存点钱。我很担心他。我怕他找不到工作。我怕他和别人打架。我更怕他吃不饱。全家便利商店的饭团太小。便利蜂的包子皮太厚。美好超市的代购太贵。我想起我们中学时的夏令营,我和哥哥一起来到了南京。哥哥请我吃糖芋苗,我请哥哥吃南京烤鸭。哥哥吃得那么香。我又点了一份金陵小馄饨、一碗赤豆元宵,哥哥全部吃完了。哥哥说,将来我们要是找不到他了,那他一定在南京。如今,我穿梭于南京各个他可能出现的地方。哥哥都没有出现。似乎从他消失的那天起,他就再也不必吃饭了。
我们之间没有一句对话。哥哥默默吃掉了我电饭煲里的剩饭。桌上摆着掏空了的咸鸭蛋,还有碟子里一摊玫瑰腐乳的红色汁液。哥哥的出现让我感到有点忧伤。我想让他留下来,橱柜里还有一套被褥。
哥哥拿走了半袋子咸鸭蛋,还有剩了小半瓶的腐乳。
我问他什么时候再来。
哥哥耸耸肩。也许他很快会再来。他还需要五号电池。
我去全家便利商店买了两板五号电池。它们整齐地排列着。串联……并联电路。我闭上眼睛,仔细搜索着中学物理知识。我将那些电路画成了人的脸。方的脸,扁的脸。哥哥皱起眉头。哥哥给那些脸添上了头发。我扑哧一声笑了出来。哥哥又给它们加上了腿。我点了几根腿毛。随后我们将试卷上所有的电路图画成了脸。
突然,哥哥对着法拉第的电磁旋转图愣了神。彩铃啊。哥哥说。地球的南北极会电磁互换的。
那会怎么样呢?
那时候,四季、日夜都会没有意义。一切都被倒置了。
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我问他。
我们应该离开这里。哥哥笃定地说。
我没有问他如何离开这里。我喜欢听他讲这些故事。这些故事不需要开始,也不需要结束,只需要此刻。此刻,我在这里听他讲。此刻,他告诉我这些宇宙的奥秘。
可能就在哥哥走后,我稍微理解了一点他说的话。黑洞是一种茧状的生物,它选择隐藏自己,并默默吞掉那些疼痛。我不知道黑洞会不会哭。那些黑色的小眼泪一滴一滴掉落下来,又被它们的主人吸了回去。我为黑洞感到悲伤。它是个什么都需要自己消化的可悲生物。想到这儿,我好想抱抱黑洞。它应该流泪,它有流泪的权利的。可是它从未被看见。很多很多东西,就像哥哥说的,很多东西是看不见的。然而它们存在。它们一直在跳动,扑通扑通,在我们尚存温暖的怀抱里。我仿佛抱着一个瑟瑟发抖的小鸡崽。这是我们的宇宙。这也是我们。
我将冰箱一角的苹果拿了出来。它在那里待了好长时间了。
我将苹果一笔一画描了出来。它已经缺水皱缩了。可我觉得它还是很美。苹果的每个瞬间都很美。哪怕它腐烂了,也有逝者如斯夫的哀愁之美。我勾勒着苹果的每一道皱纹。看到皱纹,我想起了生命中所有珍贵的瞬间。我物理考了一百分,哥哥考上了一所好大学,阿爸在哥哥的升学宴上喝得酩酊大醉。他说,彩铃要是考上了大学,他会白酒红酒葡萄酒一起混着喝到天亮。很遗憾,我没能看见这些晶莹的液体在阿爸身上发挥的奇妙作用。
哥哥,我们死了会去哪里?那年正在习画的我,问身边读书的哥哥。
对于宇宙来说,哥哥放下书。对于我们广阔的宇宙来说,并不存在死亡。“死”只是一个闸门,我们从这个世界去了那个世界而已。我相信我会去车轮星系,做一团星云,一颗恒星,一个蓝色的小陨石。当然,我的陨石寿命完成后,我还会成为其他的东西。所以,对于我们这些渺小的人类来说,我们不会死,我们只会衰老。
艺考时,我交上去的就是一幅星系图。我并没有考上那所大学。但我知道哥哥是对的。
哥哥并没有和我要五号电池。我在那家小美容店里,给人按摩头皮、去除黑头、疏通筋络。我有这样的能力。从小,哥哥就说我有描绘事物的卓越才能。我不知道什么叫作“描绘事物”的才能。后来我渐渐明白,我能将哥哥的故事复述出来,我能勾勒一个苹果的轮廓,我也能重塑一个人面部身体的曲线。这都是在描绘事物。我很感谢神明给我的这个才能。也许此行一路,有孤独,有悲伤,也有情难自已的心动。但一直陪着我的,是我的这个才能。哥哥已经提醒过我了。
在等待哥哥来拿五号电池的日子里,我谈了一段平静的恋爱。男孩是我们美容院的顾客。他腰椎不好。他给我买了两束玫瑰,一盒巧克力。我们去了游乐园,公园,咖啡馆。后来,他带我去奥体中心看了演唱会。嘈杂的歌声中,他接了一通电话,然后他就和我分手了。
“窗外的麻雀,在电线杆上多嘴……”
彩铃啊,男孩转头看着我。我和你说件事,别生气。
你说什么?我大声说着。
“手中的铅笔,在纸上来来回回……”
彩铃啊,对不起,她回来了。我们分手吧。
你再大声点。说这话时,我已经猜到了,但我只想听得清楚些。
“秋刀鱼的滋味,猫和你都想了解……”
我说——男孩喊了起来。周围的观众们纷纷回头,看着我们。我说——我们分手吧!
一瞬间,舞台上的一束浓烈炽热的黄光照射在我的脸上。好了,全世界都看清我的表情了。我有点生气,甚至想把脚上的鞋子拔下来扔到他脸上。然而黄光一闪而逝。周围的观众们回过头去,手拉着手,唱着歌。我当了一秒钟的家庭伦理剧主角,随后被遗忘。
男孩已经不见了。
“雨下整夜,我的爱溢出就像雨水……”
我拉起了旁边女孩的手:我能和你一起唱吗?
女孩露出同情又理解的表情。我们握着手来回摆动着身体。
那天,我把嗓子都唱哑了。回到家,我煮了一碗咸鱼蒸饭。这是哥哥最爱吃的食物。我那时真想念哥哥呀。他总是把咸鱼肚留给我。小时候,临近年末时,阿爸总是夜里出去钓鱼。他说大鱼喜欢在夜里活动。他确实钓到了不少大鱼。他将大鱼剖开,去掉内脏,均匀地抹上盐粒。那时,我闹着要养猫,阿爸还把我打了一顿。
阿爸寄来的咸鱼还有一大长条。我一直想给哥哥,但我联系不上他。我知道阿爸不会给他寄咸鱼的。也许妈妈正在做腊肠,肯定会给哥哥留一份。哥哥从没喊过阿爸“爸爸”,但阿爸还是供他吃饭,供他读书。我知道阿爸是个顶顶好的大好人。不然阿爸宁愿养猫,也不会给哥哥做咸鱼饭。
接到哥哥电话时,我正在兰州拉面馆吃羊肉泡馍。那天下午我有两个客户约了做身体,美团上还有几单零散生意。
彩铃啊,下午你能来我这儿一趟吗?哥哥有气无力地说。
怎么了?今天下午吗?
哥哥“嗯”了一声。
你在哪里?
哥哥告诉了我地址。我知道那里。那里租金便宜,地方又大,就是靠着江边,太冷。
哥哥,你能等我一会儿吗?我得赶过去。
嗯。不急。哥哥挂断了电话。
我叫了一辆滴滴出租车。南京城穿梭在我的发尖上。有那么一瞬间,我以为我能刺破这个古老而繁华的都市。并不然。我的头发扬了上去,飘摇着,如同一只黝黑的手安抚着这个满是伤疤的城市。我有点怜惜它了。我想,如果以后我成为一颗星球,有了自己的城市,我愿意还用这个名字。出租车路过了繁华的新街口,嘈杂的三山街,我从没想过,这些地点、这些人物、这些情节,都是与我有关的。它们就像雪一样落在我的记忆里。哥哥在南京读的大学,我经常去看他。他带我去了梅花山,又吃了正宗的梅花糕。梅花糕太烫了,我含在嘴里舍不得丢,又被烫出了眼泪。哥哥哗的一下把我的嘴合上。我刚想叫,那一口梅花糕就被我吞了下去。哥哥又给我买了一份梅花糕,说幸福是双份的。想着,我紧紧抱着我怀里的保温袋。里面是拉面馆最好吃的羊肉抓饭,两份。我得快点见到哥哥。
兴许是多日未见,哥哥的食量又增大许多。他吃完了两份羊肉抓饭,又从冰箱里取了一些冷冻饭,热了热,拌着羊油吞了下去。可他还是那么瘦。在我记忆中,哥哥从来没有胖过。妈妈曾经为此着急。但哥哥的个子噌噌噌地长。妈妈曾经说漏了嘴:“可真像他啊。”随即,妈妈又不说话了,脸埋入了油烟机的阴影中。我听到了。阿爸也没说什么。阿爸并不高,还比妈妈矮一点儿。我也没长高。不过这并不影响我成为哥哥的跟屁虫。
小时候,哥哥打架从来没输过。但他不喜欢打架。他的个头算巷子里同龄人中最高的。我喜欢让他攥着我的双手,在原地打转。哥哥力气大,总是能把我抡得离开地面。这种离心运动游戏,被哥哥称作“飞上太空”。他告诉我,在宇宙中,人是没法好好踏在地面上的,稍微一不留神,人就飞起来了。我咯吱咯吱笑着,让哥哥拎着我旋转。哥哥还告诉我,如果他是地球的话,我就是月球;如果我是地球的话,他就是太阳。我们的手臂,就是牛顿叔叔说的“万有引力”。因为哥哥说的这些话,我的初中物理还考过一百分。阿爸很高兴,说彩铃将来也是搞科研的料。后来物理复杂了起来,离心力、力矩、加速度,我头晕脑涨。提到数字,我就头疼。这是遗传阿爸的。早些年,阿爸做了些店面生意,因为不会管账,全都亏了进去;但阿爸还是开开心心的。别人说我功课不行,阿爸反驳过去:我家彩铃可是拿过一百分的。
我说哥哥。看着哥哥抚摸着脖子下的食管,喉结咕咚咕咚地上下,我居然有点于心不忍。我说哥哥,你要是没饭吃的话,就到我这儿来吧。
哥哥不说话。他伸出舌头,将碗边沿的饭粒收进嘴里。
哥哥你好歹回家看看妈妈吧,我们都很担心你。
哥哥放下碗,垂下头。我也沉默着。突然,哥哥站了起来,拉着我的手:跟我来。
打开那扇门,我被里面的景象吓到了:一个茧形的铁制机器,完美而均匀地立在卧室中央。我放开了哥哥的手,不由自主地向前走着。机器不大,但够一个人坐在里面。它的外形是由黄色、红色、白色的破旧汽车外壳焊接而成的,四处连着电线,尾部有个类似于煤气罐的设备,机器里面的座椅,看得出是一个平底锅。
我的哥哥要坐着平底锅飞上太空了。我想笑,努力地弯了弯嘴。但我又感到哀伤。是的。哥哥要走了。哥哥注定要离开这里的。
你真的要走了吗?我问哥哥。
啊。哥哥似乎在想着其他事,被我一问,反而吓了一跳。彩铃能帮我找个废弃电脑吗?我需要控制系统。
嗯。我想了想。我觉得你还需要对讲机。你要是去了外太空,没人和你说话,多无聊啊。
说得也是。哥哥掏出了手机,又放下。
我觉得现在中国网络点还没有覆盖到地球外面。我说。哥哥,你再留一段时间吧。
哥哥皱了一下鼻子:彩铃啊。
什么事?我说。
彩铃啊,我是说,最近过得……唉,我真不是个当哥哥的。哥哥埋着头,我能看见他脑袋上青色的发迹。
我更想知道哥哥过得好不好。我说。
哥哥垂着头,靠在茧形机器边上,一不小心触动了按钮。喇叭响了起来:倒车,请注意,倒车,请注意……
我俩扑哧一声笑了出来。宇宙里是没有声音的。哥哥曾经对我说。宇宙是沉默的。它不需要你告诉它什么,而它什么都知道。如果你到了宇宙,想和你身边的人说话,哪怕你和他贴着身体,贴着耳朵,他也听不见你在说什么。这多么让人难过啊。你和那个人两小无猜,或者,你和那个人无话不谈,但到了如此浩瀚博大的宇宙空间,我们都无法理解对方。这让我和宇宙有了一点芥蒂。我不想让哥哥去那里。即使那里能让哥哥一跳三尺高,能让哥哥飞起来,让哥哥感到开心。即使那样,我也不会同意的。
你过得好就好。哥哥冲我笑着。你们不要担心我。
离开哥哥的住所时,我看见了厨房旁边挂着的两条咸鱼,特别大,特别长。一条已经被切掉了一半。哥哥还是那个胃口。我穿上鞋子,走入凛冽的江风中。
知道了哥哥在哪里,我心情变得开阔了许多。美容店里来了一笔大生意,去帮人家集体婚礼化妆,说是什么世纪婚礼,这些新人都是元旦时认识的。当时造成了不小的轰动,许多情侣都报名了。这九十九对新人,都是精挑细选的。我收拾好化妆包,关掉了汗蒸室的灯。老板说今天没有顾客预约。我将美容店锁好门。
坐在地铁二号线上,我凝视着窗外。从这个角度,我只能看见宇宙的一半。另外一半,在我的身后。哥哥看到的是哪一半呢,东一半,西一半,还是左一半,右一半?我被我的念头快逗笑了。如果我和哥哥背靠着背坐在一起,那我们看到的是宇宙的全部吗?想到这儿,我突然原谅了生命里的那些孤独。每个人的孤独都是一半的,你一半,我一半,当我们相遇,我们就会拥有完整与繁盛。真幸运啊,我有哥哥。是他告诉了我这些奥秘。这条地铁人流涌动,又有多少人能关心头顶上的宇宙呢?我们曾是这个宇宙滋生繁衍出来的病毒,而我和哥哥一样,想成为它真正的一部分。
婚礼在草坪上举行。九十九对新人正热切地观望着各自的亲友。我握着眉笔,真心祝福他们的人生真如元旦那么美满。我画出了眉峰,又画出了眉尾。
主持人高声讲解着。现场人很多,几个孩子打翻了蛋糕,中年妇女们聚在一起聊天,新人们又对阴云密布的天气表示着不满。今天不适合宇宙飞船的发射。我脑子里冒出了这样一句话。我仿佛看见了哥哥大口大口吃蛋糕的场景。我希望明天、后天、大后天,甚至余生中的每一天,都是阴天。
婚礼进行曲响起。妇女们拉住了来回跑动的孩子。新的蛋糕被推了出来。主持人宣扬着爱情的不易,追光打在他的脸上。我突然想起那个男孩,不只是他,还有那个爱吃盖浇饭的家伙。他们现在生活得如何?他们现在应该也有爱的人了吧。我感到释然。似乎生命中所有人的出现,都是让我们变得更好一些。更好的你,更好的我,哪怕这个“好”非我所愿,那也是我们必须到达的地方。一对对新人走了出去,后面的跟上来。就像宇宙。对。我想起了哥哥的比喻。星系撞击,迸裂,重组,好比免疫细胞吞噬树突状细胞一样。原来我的身体里也有一个小小宇宙呀。我感到幸福。
草坪婚宴开始了。我吃了水果,蛋糕,橘子果汁。一个小男孩啃着羊骨头,桌上还有一碗被挖得遍体鳞伤的米饭。小男孩的母亲让他慢点吃。他“嗯”了一声,扔掉羊骨头,把半张脸埋进饭碗中。几粒米掉了下来,像星星。男孩放下了碗,又跑出去拿里脊肉串。那只碗坐在桌子上。神奇的是,它正一点点、一寸寸地往上攀爬着,似乎空气中有一个透明的阶梯。碗和桌子间出现了空隙。这些空隙一点点地变大,宛如太阳挣脱了地平线。那只碗停在半空中,平稳了一会儿,嗖的一声,飞走了。
我手里的果汁掉落在地上。没有人注意到。妆容整齐的九十九对新人举起了酒杯。
哥哥让我去一趟。他已经将宇宙飞船搬到了江边。今天很晴朗,万里无云。
行驶在过江的隧道里,我的眼泪止不住地涌了出来。出租车时快时慢,车窗外的风景抖动着。我相信不是我的眼睛,而是这个世界在呼吸,剧烈地呼吸,它太疼了。它每呼吸一次,就会有许多看不见的东西消失,又有许多看不见的东西出现。我不知道我失去了什么,又会得到什么,但我和这个世界一起痛着,一起体会着时光的碾磨与碎裂。我的哥哥,我的哥哥去了外太空,我会发了疯似的想他的。可是,我的哥哥,他在外太空怎么吃饭呢?他需要筷子,碗碟,牛肉,咸鱼,阿爸的蒜末他也不会拒绝的。可是,外太空有什么?除了无边无际的寂静,深入骨髓的寒冷,我的哥哥能吃得上饭吗?一碗碗饱满的、喷香的、热乎的白米饭,捧在手心里,进入食管,胃部,大肠,小肠,最后成为我们的一部分。我的哥哥……我感到心痛。
江边有哥哥高高瘦瘦的身影。哥哥似乎比那个宇宙飞船还高。哥哥朝我招手,一遍遍的。我知道,他不是在和我打招呼,他是在和某些东西告别。他背负着它们太久了,如今他要脱掉它们,轻装而走。我朝哥哥走着,脚下是褐色的江滩,一枚枚泥脚印跟随在我的身后。我面前的是没有泥脚印的宇宙。而后面的宇宙却拥有了我可爱的脚印们。
哥哥。我站在他的面前。你还记得小时候我问的问题吗?
什么问题?
你对我说过,地球的南北极会电磁互换的。那时候,一切都会被倒置,四季、日夜都会没有意义。然后我问你。我快哭出来了。我问过你,那应该怎么办?
嗯。我是说过这些。哥哥回避着我的目光。
我知道怎么办了。我放开紧咬的嘴唇。我期待那个时刻的到来。到了那时候,你是妹妹,我是你的哥哥。那时,我来保护你,我可以保护你,我会带你去任何地方。
哥哥抽了抽鼻子,眼圈红了。他转过身,坐在平底锅上,关闭了舷门。
倒车,请注意,倒车,请注意……喧闹的叫声中,我咧开嘴,想笑,眼泪却啪嗒啪嗒地往下掉。也许很久后的一天,我有了自己的家庭,我的女儿问我,她的舅舅去了哪里。我该如何回答?我应该说,她的舅舅就在天空上吗?明明哥哥没有死,明明哥哥可以好好地活在这个星球上,难道我要告诉她,我的哥哥被外星人抓走了吗?
噗的一声,宇宙飞船尾部的煤气罐瘪了下去,整个飞船抖了一下,静止了。
哥哥喘着粗气,闯出了飞行器,他攥着我的手,拉着我飞也似的跑。泥泞的江滩上出现了两排脚印。
卧倒!哥哥大喊着。他扑进了烂泥里,我也是。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哥哥抬起了满是烂泥的脸。两个泥人互相看着,不说话。
我以为……我以为它会爆炸……哥哥突然笑了,却有两行泪水从烂泥上流过。
它不会爆炸,我会爆炸。我站了起来,从上往下捋着烂泥。
对不起啊,彩铃。哥哥喃喃着。
我交叉着胳膊,嘟着嘴。哥哥愧疚地看着我。我倏地拉住了哥哥的手,沿着长江边跑啊跑啊。阳光照射在江面上,一片亮眼的平阔。一艘巨大的轮船和我们一起跑着。可是无论我们如何跑,我们的速度似乎都比它快,而与此同时,我们又跑不过它。对。参照物。哥哥和我讲过这个物理原理。参照物是用来判断一个物体是否运动的另一个物体,它能说明一个物体是在运动还是静止。就比如我们坐在地铁里,对于地铁来说,我们是静止的;对于地面来说,我们是运动的。就是因为这个原理,我打败了班里的物理课代表,考到了一百分。
我和哥哥跑到了一块礁石上。
我的双手在嘴边环成了一个圆:宇宙——你听见了吗——周彩铃要保护周宇宸——永远永远保护他——
哥哥站在我身边。我不知道哥哥怎么想的,但我觉得,似乎只要喊出哥哥的名字,哥哥就真的成了哥哥。
彩铃啊,我是叫周宇宸啊。哥哥嗫嚅着。
是啊,哥哥。
我们坐在了礁石上,我们的腿来回拍打着空气,江潮来回拍打着礁石。
哥哥,你知道吗?我看着哥哥。妈妈告诉我,她见到阿爸时,哥哥还没有名字,哥哥的名字是阿爸起的。宇宙的宇,北极星的宸,王者的宸,阿爸说,哥哥以后是会做航天员的。搞不好,还会称霸宇宙呢。我问阿爸称霸宇宙是什么意思,阿爸说,就是像奥特曼一样,维护正义,打败怪兽。我那时还不高兴,这么好的名字,居然给了哥哥。
哥哥抬起头,看着天空。
你知道太阳离我们有多远吗?
我没有回答,哥哥也没有再问。我知道哥哥是高兴的。他为他活在这个星球感到了由衷的高兴。
回到美容店,我洗了个澡,打开了汗蒸室的灯。里面很温暖。我将衣服晾晒在了里面。满屋黄色的光,照耀着我。我不再不知所措。我不再渴求温暖。我不再用自己锋锐的边缘,来试探彼此之间错落的空隙。
不知过了多久,我脱下了被汗水浸湿的汗蒸服,换上了一身干燥的衣服。还是没有顾客。我铺好了美容床。床是窄小的,仅仅能容我翻身。我洗了脸,打开小气泡美容仪,躺在了床上。
美容仪里呼出雾气,蒙蒙地罩在我脸上。我有了窒息的感觉。我想起了一件事。在我还小的时候,经常和哥哥去水码头玩。我还不会游泳。有一次,哥哥在岸上玩耍,我在岸边捞水草,一个不小心,我掉入了河里。那时,我真正地体会到了失重。宛如悬空一般,脚探不到底,蓝色的天空越来越远。河水灌入我的喉咙里,我没有喊,只是闭上眼睛,享受着这种身在宇宙的感觉。我会回到那里,我终究会回到那里。哥哥离我远去了。就像“飞上太空”游戏一般,他拉着我的胳膊。只是这一次,他真正把我甩到太空里了。
我被哥哥救了上来。哥哥自责了好久。
我睁开了眼睛。雾气朦胧中,我笑了。哥哥和我说过霍金,霍金进入太空,可以躺着,而宇航员要进入太空,也是躺着的。除了容易固定外,还和人体的结构有关,当人体飞离地球时,他所要承受的重力比平时多好几倍,平躺的话,能减少心脏给身体供血的负荷,宇航员会更安全一些。
我躺着。等待起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