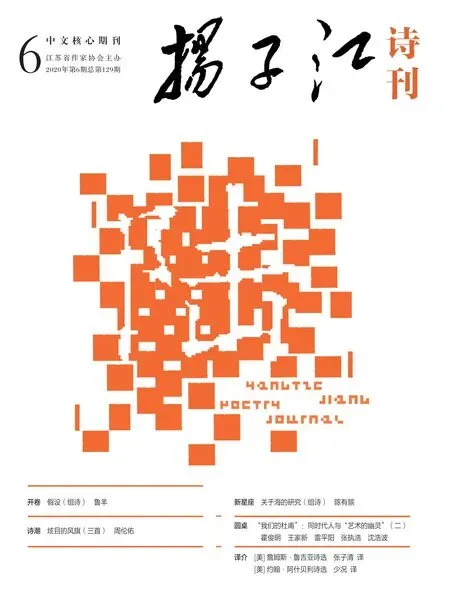词语的转换(组章)
刘华
雨夜听歌
以音乐针灸,刺入鼓噪的心房,捻转、提插,等待,雨声禁止入耳。出租房被锤炼成一只铁皮罐。一辆马车上,有人挥动着电的鞭子,自海的对岸而来,隆隆滚动的车轮,碾不碎海水中的盐。窗户后面的坟墓,腆着肚子,举起盛大的空杯。一个人趴在床上阅读,折翼的蝴蝶掉落在花丛中。他常用这些暗喻告诫自己:春天的花园,需要十二月的耐心经营。
窗 外
窗外的雨水已经鸣金收兵。在这之前,雨滴在空中编织一件水衣,这件湿漉漉的衣服是为屋顶、马路、山坡……一切没有窗户的事物而准备的,以及一辆骨骼隐隐打颤的板车——由松木或樟木手工制作,属于冷兵器时代的产物。它拖拽一个中年男人前行,而他像折叠刀一样折叠着腰。雨水淘气地钻进塑料覆盖下的板车内部,并找到几百个煤炭压制而成的煤球。板车便流下黑色的血液。而他脖子上的蓝毛巾,被乌云遮蔽。
词语的转换
一个动词,像一颗子弹,在你小步走向峭壁悬崖时,从眼角射出一弯新月的光,使你的脚步颤抖,如头顶雷电闪烁。父亲成为形容词的时候,你正背上行囊,从村里出发的班车上探头,发现父亲的眼角,透着珍珠般的光明。当父亲转化成副词,他已变得若有若无,你走在南方城市的滨江大道上,父亲只能远远遥望,对着一只手机的按钮发呆。父亲被命名为名词那天,突然有眼泪从地心冒出,你曾以为干涸的泉眼,此刻水正汩汩流淌。父亲的影子,在你刚毅的脸上,波光粼粼。
凌晨五点的咳嗽
一声比一声绵长,隐含尖锐的水花。有人在敲玻璃窗。潜行在睡梦中的我迫于武力威胁,返回到现实世界。辗转身子,以及新一天的灵魂。中年男人的咳嗽,一锤锤,坚持不懈,通过一楼墙壁和空气传导力量,砸在三楼出租房的透明玻璃窗上。破碎声从肺腑经由喉咙,卡顿、吐出。在声音的鞭笞下,沦为一个俘虏,跟随这一阵尖锐的敲打,我被捆缚在现实的席梦思上。啊。这声音里隐现父亲的影子——认命,掺杂着不甘和坚韧。大脑的螺旋桨试图起飞,我不得不关闭眼睛的按钮,让自己回到黑暗中去,然而,已不可能了……
树 影
一棵樟树举着灯柱在黄昏里蘸墨,马路是一张宣纸,被一座座睡梦中的房子镇住。枝叶混迹在墨水间,这是国画在运行、呈现,而他热爱色彩斑斓却如沉默的羔羊。街道上空无一人,他与影子同时蹲下来,相互感慨子夜的风在吹冷琉璃瓦。一只乌鸦突然从身后飞来,像被一件袈裟缠缚,身后拖着寂静的尾巴。而黎明来了,一只巨大的隐形的手,便清洗记忆,或这幅水墨画。
在天上看云
飘浮在空中,我担心它们从天上坠落。记得那时年纪小,常透过土房子里的木窗,窥视山顶云朵的变幻,想象自己骑着云朵的马,修炼成长衣飘飘的神仙,到十万八千里外历经仙履奇缘。后来,我乘飞机飞到天上,在天上看云朵编织迷宫。地上的保利大厦、钱塘江无限缩小,再宏伟的事物在高处,都有其渺小的一面。我从云朵边经过,看白云远去又归来,而机翼的轰鸣,让一具肉身泛起波澜。在地球上仰望云朵,让雨滴化成河海,任万物沾染水的母性。带一朵云回地面去,已不再可能。
猫
金黄色的猫溜进宿舍,阳光也跟在后面。我站成圆规,而它绕着我的右腿,画出一个个圆圈。并对我说出低分贝的猫语,喵—喵!它琥珀般的眼睛闪亮着。我从风尘仆仆的行李中,抽中了一本诗集,并大声朗诵了一句莱蒙托夫的诗:“它寻求什么,在遥远的异地?它抛下什么,在可爱的故乡?”它似乎听懂了,并停止了呼叫。窗外的风在鞭打南昌的香樟树。我在五米长的房间里航行到了圣彼得堡,没有间歇地把莱蒙托夫当作食材,为清晨的来客烹饪早餐。
出租房
一股抽象的气息,鼻子像闯入暴躁的雨林当中。推开这十平方米的出租房,六月开始潜入梦幻泡影。像一册日积月累的档案——早晨八点收集刷牙的气味,晚上九点网住削苹果时的气味,剥开葵花籽的气味,在城市蒸笼溢出的汗味……它全心全意爱他带来的女人或男人,一本书或一支香水。有时他辗转难眠,它就匍匐在一旁,逗弄几只蝈蝈或蛐蛐。他走时,带走一切物件,却忘了向它道别——“每个开始,毕竟都只是续篇……”
榆 树
孤零零的童年,从未被孩子们当成一只鸟,一朵云,一匹奔驰的马。对于造物主将它安置在一条混乱的水沟边,它绅士般缄口不言,甚至向春天伸出鲜绿的枝丫。男孩和女孩闪亮如火焰。一排壮硕的柳树弯下腰,并伸展翅膀,化成一匹匹天马,就要飞离村庄,到夕阳之外的星辰大海。至于为什么去那么远的地方,他们还没什么概念。多年以后,站在空荡荡的街边,那些展翅的声音,窸窸窣窣,仿佛窗外洒落的几滴雨声。村庄里的很多事物,正进行一场永恒的迷藏。
蛙 鸣
无法睡去的夜晚,是大脑不停运转,还是眼睛不肯闭上?像载着空油箱来到加油站,像黄昏大火燃烧森林,出于惯性,还是青春期综合征的正常反应?嘴唇说不清楚为什么,而心里在翻转旋涡。由此,耳朵越来越敏感,长出触角,捕捉到角落里的蛐蛐在吹着喇叭,七楼下面的荷塘里,无数只闹钟发出自然之鸣。我们活在脆弱的身体内,寻找演奏的小提琴。
大 海
唯有地球仪才能看见、抚摸,尽情使用一次海水。在北纬28°东经120°,一些琐碎的丘陵阻挡西伯利亚寒流,高山都已走失,还未在电线杆上贴上寻人启事。昏黄的县城装不下大海的一片羽毛,只能以诗为生活涂上蔚蓝。像一尾鱼穿梭在结构复杂的人海。我见过最干净的海,是在特朗斯特罗姆的诗中。读海的鳞片,幻听海啸。大海浩瀚,涌动盐的苦与咸。我曾在盐中制造海市蜃楼。
风 筝
一个人越来越轻,轻的部分到哪里去了,无人提问。在田野种稻子,在公路边种草种树……无枝可攀时,跟随板车的负重慢悠悠来到集市,为一个人煮面条,泡米豆腐,调制微辣、中辣或魔鬼辣的早餐。一缕缕白发牵动岁月轮转,她向大地深处奔跑,却越来越轻,只要装上一个转盘、一根丝线,她随时像一只风筝飞升。风里的母亲,一直停在风里,什么地方也不去。这些风,穿过她的骨髓,将她一点点弄皱。她就在悬浮中,等我。为我的行程买单的女人,掏光了所有的积蓄,和丰盛的青春。
醒
醒得最早的,是路灯下哈着热气的包子铺,凌晨四点挖渠引水,以酵母滋润面粉。穿蓝衣服的清洁工,在银色的黎明里挥着铁铲,趁人类还未从席梦思上爬起,运走了一车又一车人间的废物。一声长长的鸡鸣穿透城市森林,是楚国暗藏至今的隐士在拨弄琴弦,没有人听见流水从高山倾泻。桥下的湘江还未开始晨跑,运砂船以及两岸的草木冷清又缓慢,而旧梦还在被窝里拖着逝去一日的尾巴,那些沉睡中的人,我也曾睡在他们当中。68路公交车悄悄踩住短暂的刹车。有一个穿军绿色棉袄的人一言不发,穿过了大半个城市……
镜子只能照见
镜子只能照见,而不能记住。如何把自己留在这物质世界,她找到唯一的办法——去照相馆,以胶片保存昙花一现的身影。在路边的榆树下,她眺望着来路,等班车从云溪村开往县城。无人的黄昏,抽屉中的信封堆叠,她以眼睛抚摸饱含记忆的相片。此刻,世界停止运转,她仍是披着一头乌黑发亮的长发的姑娘,对南方世界持有青春期的躁动。不知道想起了哪些往事,眸子从灰烬中亮了起来。在她脸上的波涛里,有一个男孩正驾驶帆船前往未知领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