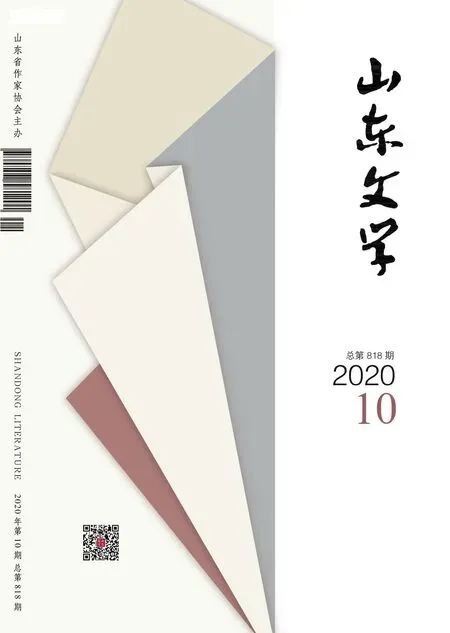现代文学中的青岛小说·抽枝
桃源梦忆
对于1898年变成德国租借地的青岛而言,新兴城市的长成源于强悍的外力。及至辛亥革命的“一声炮响”为这座城市送来了一大批遗老遗少,来自民族内部的现代化变动才愈发明晰起来。
1917年8月1日,燕齐倦游客著写的《桃源梦》由上海四马路的民权出版部印行。尽管这是部章回小说,但愤的是旧道统,无奈间兴的是新文化。它用了几近纪实的笔法,书写了德国强占胶澳后至日德战争爆发期间晚清遗老遗少的青岛生活,其间道及的种种场景和细节犹若一部早期青岛的历史画卷。它以近乎《官场现形记》的方式打开了青岛的开端史,既以略带挑剔的眼光完成了人群批判,又呈现出了青岛社会现实中的诸多生动。故而,它在青岛的小说历程中有着极其特殊的地位和意义。
晚清遗老之所以视青岛为“桃花源”,大致可归结为这样三点:其一,在清帝退位后,王胄云集的天津太乱,十里洋场的上海又离旧都太远;其二,青岛成为德国租借地后,现代化的城市迅速崛起,红瓦绿树,洋房林立,气候不寒不暑,出行可舟可乘——胶济铁路和海上客运极其便利;其三,租借地的管辖,亦可作为政权的“法外之地”,有足够可能酝酿一些政治活动。
对遗老而言,无论避世者,还是伺机起事者,固然找到了他们的“桃花源”,但于国人而言,这种糜集不免带有几分可憎。一方面,遗老很容易被视为败落正统的朽坏者;另一方面,他们还有可能就是逃亡中的劫掠者。
一如遗老遗少最早云集的宁阳路一带被视为“赃官巷”一样,作为小说作者的燕齐倦游客恐也无法排拒这样的认知影响。他笔下的遗老遗少自然不免丑陋:他们席卷府库一空逃亡后,不以为耻反觉心安理得;私生活荒唐无度,污秽淫邪;在德国殖民者面前,气节败落,低三下四;虽然时有吟诗作赋,雅集唱合,但在现代公共生活方面洋相百出——赴宴会不守时、看电影听演讲时大声喧哗随地吐痰、走路相互推让拥塞道路、不懂餐会礼仪往地上吐骨头、官服马蹄袖扫翻水烟袋洒出满桌臭水……
《桃源梦》在极尽揶揄和批判的同时,也凸现了现代文明对遗老们的改造和影响,比如他们要被迫尊重新一代剪掉辫子的权利;他们也要明白法律的存在,以免受到洋人麾下中国巡捕的训斥;他们不得不将自己的子女送进西式学堂;为了相互声援、卫护权益,他们也得学会联络青岛商界的头面人物建立“敦谊会”,拟定会章,不时集会……
如许种种,透露出在早期的青岛殖民历程中,在新式文明的催迫下,中国旧有的文化自信与民族文化面临着挣扎与崩塌。在主权失落的土地上,当英日联合对德宣战后,一场战争也就在所难免了。眼睁睁面对即将荒唐生发的战乱,遗老们不得不丢下苦心经营的住宅和一切,仓皇散去,终而留下这样的叹喟:“为全老臣节,来作异乡人,海外烟尘恶,中原祸患频,首阳何处是,别思泪沾襟。”
有关作者燕齐倦游客的生平,目前尚无确切的考证。从“劫余老人”的序二中看,他与燕齐倦游客“识于松禅相国座中”,“松禅相国”即是翁同龢,说明作者与翁氏有交往与过从。
序一、序三、序四则分别出自长沙张冥飞、刘铁冷和南沙姚民哀。刘铁冷是民权出版部的核心刊物《民权素》的主编之一。《民权素》是一本汇编性的期刊,汇辑了《民权报》上登载的论文、诗词、游记、散文、小说、笔记。民权出版部的创办人徐天啸,是《玉梨魂》作者徐枕亚的兄长,也是《民权报》的主编,在《民权报》停刊后改办民权出版部。该出版部既以民权为名,自然会让人联系到“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的“三民主义”,亦即不难明白,这是一个有“共和国”价值指向的机构,由此,也可理解《桃源梦》何以对于晚清遗老遗少有些“不恭敬”了。
虽然体裁为小说,《桃源梦》的现实指征是不言而喻的,许多遗老都可“对号入座”,连他们在青岛的寓住地都有真实的路名标注,这也说明作者在青岛肯定有长期的居住经历,一如结尾所言:“世之君子,当作一篇谎话看也可,当作一篇实在事看也无不可。”
大抵也是因为太看重于世情和细节的描摹,小说写作多少显得有些拖沓、琐碎,这是其不足处。
与《桃源梦》荡开青岛小说写作缘起的形式类近,直至1920年代早期,青岛报纸副刊上的小说,均采用章回体的样式,语言形式也是文白相间。其中1923年由青岛商人隋石卿操办的《青岛晨报》即曾连载平江不肖生的长篇武侠小说《半夜飞头记》。
白话新小说的开端,在青岛本土写作,应以顾随的《乡愁》为始。有资料查证,1924年9月6日的 《青岛时报》曾刊有《乡愁》,署名“羡季”。
此“羡季”即为执教于胶澳中学的顾随。是年7月21日,刚刚到青岛不久的顾随完成了《乡愁》的写作。在给卢继韶的信中说:“写了一篇东西,叫《乡愁》,才脱稿,是仿《立水淹》《寂寞》那些东西而作的。但是可怜得很,写出来的一点幽默Humor的性质也没有,只是黯淡。大约是心情变迁及年龄长大的关系。”
信中所及《立水淹》是顾随1923年9月在济南女子职业学校教书时所写,其时他兼着《民治日报》的编辑,也在山东省立第一女子中学上课。《立水淹》1924年8月19日刊于《民国日报》文艺副刊,最初拟名《乡居》《乡居纪事》。写的是乡村大雨后遭遇水淹的情形。文中透露的“我”的阅读,与乡村淳朴的生活相比甚为闪耀——“晚间我独自在屋看了回波多莱尔的诗集,便熄灯睡了。”
这无意间的一句,可见当时顾随的阅读趣味,而他在不久后写散文《母亲》时,还引用过梅特林克的诗句——“过去的人们生存在活人的记忆里”。
《青岛时报》的《乡愁》因只存残篇,已难以窥清小说的具体内容,但其与《立水淹》相承续的意味与语境,可以想见。
1925年3月印行的《浅草》第一卷第四期,刊发了顾随的短篇小说《失踪》,这篇小说后来收录于鲁迅编选的《中国新文系大系·小说二集》。小说的写作时间是在1923年12月,也是顾随在济南时期。刊行时,顾随还在青岛。仅从这期刊物的著作者,即可看出顾随的一些交谊关联,其中,冯至刊有诗歌《吹箫人的做事》《河上》,陈炜谟刊有《狼筅将军》和《编辑缀话》,陈翔鹤刊有四幕剧《沾泥飞絮》和诗歌《短筝》,这些人和另一位“沉钟社”成员郝荫潭先后来到青岛。
从陈炜谟1924年8月20日给杨晦的信中可以看出,他和陈翔鹤、冯至都是顾随初来青岛的这个暑期来的,陈炜谟告诉杨晦说,青岛一个月的旅行,使他的性情改变了不少。“我们既没有自然的勇气,只好忍痛活下去。离青岛的前几天,翔鹤一人大醉后大哭,这给我很大的教训。眼泪毕竟是没用的,而且世界上值得眼泪的事太少了。——所以,近来我的泪一直到眼边,便既止住,已由伤感而生愤,因愤而激了。”
在顾随的这三个友人中,冯至来得最早,是和顾随一起来青岛的。在这期间除写了《在海滨浴场》组诗,还写了几篇散文和一个独幕剧,他拿给陈翔鹤和陈炜谟看,有一位题写了“In the Storm”,顾随遂题写了“暴风雨中”。
这次行旅也为陈翔鹤后来执教于青岛市立中学奠下前缘。
顾随在1926年9月离开青岛前,完成了小说《浮沉》的上半部,他在1925年7月12日给卢继韶的信中说:“《浮沉》上半部已脱稿,然仍须大加削改,始能见人。故此刻尚不克寄呈。至于下半部何时下手,何时告成,则更无确期。缘于上半部要写一与世沉浮、随波逐流之青年——其实大部分,仍以我自身为影射。至于下半部,余颇思再写一强有力冷无情之青年,与上半部之主人公作一对照。但此项‘模特’儿,在现时之中国,甚为缺乏。思维再四,或将以武杕生君为粉本也。对于写此与下半部之预备,已打算妥当。至少须一读尼采之 ‘Thus Spake Zarathstra’,斯梯儿纳之 ‘The Ego and His Own’,及叔本华之《悲观哲学》(三人皆德人也),始能着笔。”
1925年12月12日,顾随还依据《论语·述而第七》演义写成了小说《孔子的自白》,后刊于《沉钟》第五期,是作的写法和笔调极像鲁迅的《故事新编》,笔法和气息有如1922-1926年间鲁迅写的《补天》《奔月》和《铸剑》。其实,包括顾随读波多莱尔也是受到了鲁迅的影响。据冯至回忆,鲁迅在说“摄取来的异域的营养又是世纪末的果汁”之后,又列举了王尔德、波特莱尔、安特列夫等几个名字,顾随就“按图索骥”找来阅读。
在顾随离青前,杨晦也曾来青岛小住,缘于其弟杨兴楷时在胶澳中学读书。
不久成为杨晦妻子的郝荫潭,来胶济铁路青岛中学执教是在1932年初。河北平山人郝荫潭,曾就读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国文系,是1925年成立的沉钟社后续成员。据鲁迅1929年5月25日致许广平的信中记载:“10点左右有沉钟社的人来访我,至午邀我至中央公园去吃饭,一直谈到5点才散。内有一人名郝荫潭,是女师大学生,但是新的,我想你未必认识罢。”
《逸如女士》是郝荫潭创作的一部长篇小说,1929年连载于《华北日报》副刊,1930年1月20日以《逸如》为名被列为《沉钟》丛刊的第九种单独印行,小说共分66节,由冯至作序。有研究认为,这部长篇小说几乎就是郝荫潭个人的自叙传,也代表了那一代女作家的写作倾向。这部长篇小说不但集中展现了“她们怎样的爱、怎样的憎、怎样的悲哀”,并且“赤裸裸地没有一点儿蒙蔽。”
如冯至在“序言”中所说:“数月前曾与废名君闲谈。他说,中国文学史上固然也有女诗人能列于第一流作者,但总觉得在那些作品里并没有把女性的特殊的情绪表现出来,同男作家的多半是没有什么分别的。这话骤听很新奇,细思实有道理。同是人类,本不应该分彼此,但因为生理不同,心理各异;如求了解,困难孔多……人生之幕常是蒙着一半;女性的灵魂里有无数宝藏,而无从探视。现在却想不到从《逸如》里仿佛懂得了许多。”
时在胶济铁路青岛中学读书的赵俪生记得郝荫潭对他的影响:“那时我写了一篇作文,描写大学路和黄县路拐角处一洞石桥的水塘,春雨落时激起的一轮一轮的涟漪。不知为什么,它受到了郝老师的赏识,她大加圈点批语,并在发作文时大讲一通。这一行为,倒不在于在当时小小的教室里增高了我在同学中的声誉,它更高更大的作用是,启发了我终生写文章的至死不衰,甚至当代不少名人当面告诉我说,他每在目录上碰到我的文章,就非找来读不可。我是如何培养成了这点可怜的魅力的?我自己不清楚,但假如有人死命要问的话,那么我只能说是郝老师赐给的。”
学生赵俪生家住在城市贫民集中的台西镇,三个供给他读书的姐姐,大姐在日商茂昌鸡蛋公司做工,二姐和三姐则在英美烟草公司做工。赵俪生在胶济铁路中学读了六年书。初中时即热爱新文艺,喜欢鲁迅的《呐喊》《彷徨》,周作人的《雨天的书》《自己的园地》《泽泻集》。赵俪生还跟同学们组织过一个文艺社,叫“浪花”,在胶济铁路办的《胶济日报》上组织过“浪花”副刊;在1934年12月11日《明天》副刊发表有《寒蝇》,已用笔名“冯夷”;后于1936年1月22日在《青岛时报》开辟过副刊《浮世绘》,发表白话诗、散文、短篇小说和译作等,在第二期翻译过一篇散文《盛开的花》,译自《人道主义》1935年春季号,作者Olga Koksharova 系沙俄时代一个西伯里亚铁路局长的女儿,当时任教于美国的一所大学。
冯至在《逸如》“序言”中提到的废名,也是他们“浅草社”的旧友,于1931年初来到青岛。他在是年1月12日还给周作人写了封信:“今早发一信,把日子都记错了。青岛这地方很好,想在这里住它一个春天,另写一信给平伯,请他或由他另约几位与杨振声有交情者共同写一信与杨替我谋三四点钟功课,不知如何,请翁就近向平伯打听一下。我写给平伯的信是由清华大学转,当能收到。”信末注明“来信寄青岛铁路中学修古藩转”。
这一时段的胶济铁路青岛中学,曾一度紧紧“依偎”着国立青岛大学——1930年春至1931年暑假前,曾租用青岛大学第四校舍上课。
周作人遵请给俞平伯写了信。此前,为了同样的事情,周作人也曾帮杨晦向杨振声提过一次,但杨没有答应。废名的事,也一样没有结果。废名转而应了铁路中学的聘,在学校大约授了一学期的“文学史”与“学术文”。
废名提到的修古藩是赵俪生十分感谢的第二位老师——“修老师是大量将鲁迅、周作人作品和译品印成油印讲义发给我们的人。我们开始知道有《域外小说集》《现代小说译丛》《日本短篇小说集》,都是从他讲课中得知的。他还推荐让我们订《沉钟》和《骆驼草》这类北大继《语丝》之后出版的小型新文艺刊物。”
修古藩192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在《沉钟》上亦发表有《清明》《恶作剧》《打赌》《孤独》《审判》《潘润之》《钟家坝上》《山谷》《危源远》《龙王镜》等多篇文字。
较之于郝荫潭、修古藩、废名等“浅草社”“沉钟社”同人,王统照对胶济铁路青岛中学的影响自1929年就开始了。
《山雨》与《热流》
从《剑啸庐诗存》可以看出,王统照家1923年在青岛已置有观海楼。这一年他母亲卧疴,王统照即由北京回返家中探望。三年后,母亲病重,王统照再次折身。不久,母亲在1927年初春病逝。王统照好不心伤——“我甚么兴致都似丧失了!更少创作的意念。”
这时王统照的文学心思也是灰冷的,尽管他在此前已经印行有长篇小说《一叶》《黄昏》,短篇小说集《春雨之夜》,但在返回青岛之前,他在北京翻译朗弗楼时因误译遭遇了强烈的指责,这也让他感受到受伤和落寞。
1927年,王统照在青岛服母丧,同时校录、刻印父亲的遗作《西轩诗草》。1929年开始任教于胶济铁路青岛中学和青岛市立中学。
在胶济铁路中学,王统照的到来对学生文学社团的发动产生了积极影响。学生郝复俭(白石)组织了“绿萍社”,在《胶济日报》出刊文学周刊;学生臧宣达(迪文)、谭祖彝(春岩)、王志馨(宁生)等组织了“涛社”,在《青岛民报》出刊《南风》周刊。
在市立中学,周浩然、于黑丁、李白凤等成为王统照的追随者。有研究说,李白凤为了追随王统照,从胶济铁路青岛中学初中毕业后,放弃了继续在免收学费的铁路中学读高中,而被父亲视为忤逆,对他的生活支持也时断时续。这迫使李白凤不得不在课余时间到海滨教人游泳、教小姐骑自行车或替富人遛狗以贴补用度。
此时的王统照刚刚在“十分烦郁”的秋冬之间汇编了自己的第二部短篇小说集《号声》,收录小说九篇,交由上海复旦书店印行。“自序”里说,是在赵景深的劝说下才有了这个念头:“我只是由痛苦与烦郁中将所见、所闻、所感,所想象到的写出而已。”
《号声》中写于1927年10月的短篇小说就有五篇,有《买木柴之一日》《海滨之后》《读〈易〉》《沉船》《号声》。《买木柴之一日》显露出自叙传式的焦灼:“想现在一家的大小责任在自己身上,自从春初母亲病故了,半年来所有的只是悲哀和忧虑。而地方上的情形变更,几亩田地的收入不够,按了地丁的预征与特捐,一次又一次,他计算,并且听亲戚家也都说,再来一次非变卖产业不可了。却又卖与谁呢?”
写于10月22日的《沉船》取材于青岛“现德丸”海难。1927年是山东大灾之年,旱灾、蝗灾并发,灾区遍及56个县,山东近半数人家遭灾,而税赋丝毫不减,农民们无以谋生,纷纷踏上闯关东的路途。因为青岛是山东最主要的出海口,每日往返大连的班轮频繁,一些难民就选择从青岛乘船出发。来自鲁西南的,多从红石崖坐小火轮到小港,再换乘大火轮去东北。1927年9月17日,在青岛和红石崖之间往返的日本小火轮“现德丸”号,因超载造成海难。由于连日海雾,难民积留严重,一艘准载客120人的船,搭载乘客超过400人,船行驶至灵山卫塔埠头处触礁沉没。日籍船主和船员抢用救生设备逃生,经中国商轮“运发成”和美国水艇驰援侥幸救出了121名乘客,有300余人死亡或失踪。
《青岛晨报》报道说,罹难者中最为凄惨的有许、孙两家人。许家14口人只一人遇救。孙家幸存了一名叫孙全的14岁少年,其父母兄弟共14口全被淹毙。灾难发生后,日籍船主沧谷晋吉、机船长川端利吉被控贪图钱利违反航行规则而遭抓捕。但经日本领事保释被释放。获救的121名幸存者仅仅每人赈济了5块大洋,打捞上来的180多具尸首被草草掩埋于湖岛公墓。
王统照写《沉船》的愤懑可想而知。他在处理这个题材时却用了很大的克制,增加了车夫和乡村野店的穿插与见证,车夫一步步把背井离乡的刘二曾一家送向港口,也送向死亡;乡村野店的主人少年时也是富裕人家,在邻村学塾里读过书又曾上过城里的书院,后来也做过“先生”,只是因为不再有学生,才改了“行”……
《沉船》得自现实题材,却以有象征色彩的手法表现出来——一个用煤渣和草屑铺成的“东方古旧海岸”;一群贫困、善良的劳苦农人和小手艺人,他们身后古旧、可爱的乡村一去不返,前面,是要忍受了倾轧的死亡之海……
写《沉船》时的王统照明显尝到了人间的苦味,与文学研究会时期徘徊在爱与美的感伤中的王统照已然不同。《沉船》之后,王统照在青岛还作有《刀柄》《隔绝阳曦》《火城》《旗与手》《记忆的神秘》等几个小说,直至1933年长篇小说《山雨》问世。
王统照在《山雨》的“跋”里说,1931年8月,他和叶圣陶讲,《山雨》意在写出北方农村崩溃的几种原因与现象,以及农民的自觉。叶圣陶极为赞成。小说写作从1932年9月始,到12月初旬写成,大致用了三个月的时间。“虽然大概的构图是经过几番寻思,而调制材料也还费过相当的时间,不过写完之后总感到不满,尤其是后半部结束得太匆忙了,事实的描写太少,时间又隔离的太久。原想安排五六个重要人物,都有他们各个故事的发展,并不偏重一两个主角,在写作中终没有办到,所以内容还是太单调了。这是我觉得脱懒与不安的。”
《山雨》由叶圣陶亲自校订,1933年9月亦由叶圣陶主持的开明书店出版。一个月后,茅盾化名“东方未明”在《文学》第十期给予高度评价:本书大半部的北方农村描写是值得赞美的。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没有看见过第二部这样坚实的农村小说。这不是想象的概念的作品,这是血淋淋的生活的记录。在乡村描写的大半部中“到处可见北方乡村的凸体图画。”
茅盾当然也指出了这部小说的问题,包括25章写得有些伤感等等。
《山雨》的故事不复杂,写的是相州农民奚大有在卖菜时,因与士兵发生争执被绑走。他的父亲奚大叔花了几百元钱,才把满身是伤的大有保释回家。为了还债并应付各种捐税,奚大叔卖了部分土地,在穷愁中病逝。丧父的大有也因此脾气越来越坏。土匪到处作乱,税捐和军队的勒索有增无减,大有决定卖了家中仅剩的两亩地还清债务,离开“残破、穷困、疾病、惊吓的乡间”,携妻带儿来到都市T城投奔在日本纱厂做工的童年朋友杜烈。杜烈也未帮他找到工作,他只得靠卖饺子、到码头上扛货、拉洋车等养家糊口。刚离开家乡时,大有还存有进城挣钱赎回土地的想法,但几经挫折,他的幻想破灭了。在杜烈和其妹杜英、祝先生等进步青年的启发下,大有若有所悟,后来听说好友徐利投“绿林”以复仇也失败了,大有渐渐明白了家乡为什么那么衰败,外国人为什么敢欺侮中国人。
《山雨》的结尾,写到了日本人打砸×报、烧×部的事件,以“有本事,叫大火毁灭了全中国!”“不!烧吧,烧吧,烧遍了全世界!”结尾。
结尾的素材如《沉船》得自“现德丸号”事件,也与青岛的真实事件有关——1932年1月9日《民国日报》刊发《韩国不亡,义士李霍索炸日皇未遂》的消息,引发日侨民团暴动,他们打砸了《民国日报》社,纵火烧毁了国民党青岛市党部。
《山雨》在印行的三个月后,遭到查禁。原因是“内容颇含阶级斗争意识”,开明书店因此受到上海特别市党部的警告处分,并被勒令禁止发售该书。开明书店遂删掉了《山雨》24-28章(由370页删至312页),并删改了“跋”中的“革命的”“以及农民的自觉”等字句,做了重新刊行。同时还将“中央宣传委员会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的准印通知附于书后。
《山雨》遭禁的理由,由结尾不难想见,相较于党部被烧的内容呈现,所谓“阶级斗争意识”显得更为模糊。至于后来有传说王统照因此上了“国民党的黑名单”避走欧洲,有研究查证,当时所谓“中国‘普罗作家’姓名表”中并无王统照; 而从《欧游日记》中亦可看出,王统照出游时搭伴的是一个“济南教育团”。
王统照自我检讨过《山雨》后半部的失败,确实失之于在故事构划上的仓促,这与他是否真正充分了解工人生活和城市贫民的生活也是有关系的。但茅盾所谓第二十五章的“伤感”,恰恰更符合主人公奚大有的茫然与迷离。在当时的王统照那里,模糊的、感觉的牵动,是渐次清醒的一种样式,正像一次醉酒。
好的文学作品未必是清晰的,态度化的。王统照有别于一般现实主义写作或者普罗文学写作的价值,也正是在此。
《山雨》所爆发的文学影响不言而喻。而在《山雨》出版之前,王统照即开始了另外一个长篇的写作,那就是《热流》,这部后来被误以为“写于抗日战争时期的上海”的长篇小说,自1933年7月8日开始在《青岛民报》的“民报副刊”连载,后改至“艺林”连载,至1933年12月23日,连载了67期后中辍。中辍的原因,于黑丁在1934年1月25日《文化列车》第八期中刊发的《青岛文坛通讯》有详细披露。这部长篇后改名为《双清》连载于上海《万象》杂志。
王统照在青岛写就的其他短篇小说,《刀柄》和《火城》分别刊于他主编的《青潮》月刊第一、二期;亦可视为他写给青岛文学青年的示范之作。《刀柄》借着义合铁匠铺生意兴隆的视角,写到乡间兵器生意的热闹——各路人马打造兵器是为了征伐,而民众则是为了自卫。一把有着云铜刀柄的大刀,来自石峪的一个姓贾的乡绅,他把地都分了,带领乡人习武自卫,结果还是在反抗强征的过程中,被手枪和几百支长枪击溃。15个被擒获的俘虏中,有贾乡绅自幼儿习武、操练大刀的儿子。这把被夺来的大刀重新送到铁匠铺开刃,“局子里”的人要用它来“正法”俘虏。而这刀当年也正是由义合铁匠铺精心打造……义合铁匠铺的吴大用老板,在落满雪的法场上,看到了贾老头眼光已散的儿子,看到了扬在他头上的大刀……
《火城》以更简约的笔触勾勒了军阀对乡间小县城生活秩序的毁坏,能演说、能作文章、能拉选票,还能召集自卫军自任军长的军阀,与不断涌现的土匪一样,这一群去,那一群来,城里的人不得不一边连夜轮班值守,一边花钱买平安;而县城牢狱里,也不时散发着鬼喊——城外的匪要冲进来,狱里的匪要冲出去。就在盛夏炎炎的火城,县城监狱外的阎王巷中,乘凉的人们在谈论着这几日因土匪攻城而发生的厮杀……
与王统照的小说共同刊发于《青潮》月刊的,还有王匠伯(姜贵)、李同愈的小说。王匠伯也出自诸城王氏,是比王统照矮一辈的族亲,又名王意坚。他的长篇小说《白棺》后连载于《青岛民报》。有研究查考,王匠伯曾就读于胶澳中学,《白棺》应是其学生时代的作品,《青潮》作刊发时,他已离开了青岛。
江苏常熟人李同愈,在《青潮》第一期上发表有小说《父子》,他1927年来到青岛,系青岛电报局的职员,后担任电报局《电铎》月刊的编辑干事。1931年,李同愈在叶圣陶主持的《小说月报》第22卷2月号同时发表了诗歌《半年》《嘱托》《翘首》,小说《异国的悲哀》。
李同愈在青岛的文学影响,以1934年7月《忘情草》在生活书店出版而全面铺开,这部小说集收录了李同愈的14个短篇。1934年9月11日起“李斐”连续四期在《青岛时报》“明天”副刊推介此书。“同愈镇日价堆在脸上的笑容,温和的态度,惯会向女人们说笑的那张流利的嘴,正如他许多作品里轻松的笔调美丽细腻的描写,富有‘兴趣’的故事。”
李斐认为,李同愈“笔调清澈描写心理细腻处,很有点像沈从文氏,虽然《忘情草》里的题材大都太琐碎,和偏重于讲故事式的‘色情趣味’,然而有几篇经他这种笔一描写,也不失一篇轻松流利可读的文字。”
王统照和李同愈,均与叶圣陶有交往,事实上也构织了他们共同的文学格调,包括《沉船》也是发表在叶圣陶主持的《小说月报》上。
叶圣陶在1927年6月之后接掌《小说月报》的编务,正是因为“四·一二”以后,前主编郑振铎因躲避搜捕而赴欧洲游学。叶圣陶上任后,更强调弱化时代的呼应,向文学本体的回归,一如上任之初他即在《小说月报》第18卷第6号“卷头语”中所说:“画人物先习素描,学唱歌先练声音,往后的造诣如何高深伟大是无限量的,但若越过了先在的阶级,执起画笔便涂,挺直喉咙便唱,将成就些什么呢?”
由之也不难理解,王统照对《青潮》的定位,何以会对“政治类”文字没有兴趣。
在王统照身边成长起来的小说家,还有于黑丁等人,他在市立中学曾参加“无名社”,其短篇小说处女作《乡情》经王统照修改推荐,1930年发表于同样是叶圣陶主持的《中学生》上。
1930年,于黑丁的父亲在吉林病重。于黑丁遂北上探望,在东北经历了“九·一八”事变,1932年回到青岛,后组织了“汽笛文艺社”。这也是《青岛民报》“汽笛”周刊刊载他以“秋雁”为笔名,写《辽宁之夜》等东北见闻文字的因由。1933年8月8日,于黑丁以“丁厂”的笔名写了小说《恐怖》,在“汽笛”上连载了七期,写的正是“汽笛”周刊的事,三个编辑,“邹”是周浩然,蜜司林是林映(郭锡英),事件正是《青岛民报》副刊编辑因为反帝宣传,一个被抓捕,一个被迫辞职,经友人提醒也深有可能牵连到办周刊的他们。他们愤怒而失望,觉得失去了可以前行的道路。及至最终,“汽笛”也如《恐怖》所写,停止了嘶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