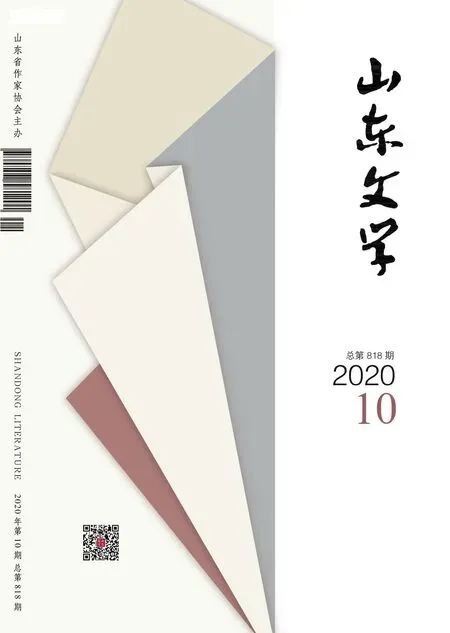沈从文的选择
——《沈从文的后半生》阅读札记
1949年对于很多作家来说,是人生轨迹转移的锚点,从第一次文代会的发言就能感知到,一部分作家踌躇满志,另一部分作家犹疑自卑,而沈从文全然被排除在外,失去了写作的资格。
小说承载着它不应该承载的东西,写小说的人,则被筛子精挑细选。很不幸,沈从文被这张筛子排除在外。
沈从文的最后一部小说是《传奇不奇》,载于朱光潜主编的《文学杂志》,从此他再也没有完整的小说发表。沈从文的后半生,因为舍弃了文学而进入了更偏僻的领域,注定远离大众甚至文学史家的视野。
文学史上的记录戛然而止,但是沈从文接下来的人生却仍然等着他去完成,虽不为人知,却依旧可称之“隐秘而伟大”。也幸而有《沈从文的后半生》这本书,为我们详细讲述了不再写作的沈从文是如何度过他的后半生。
这本书是在从单位回宿舍的公交车上读完的,有过在长沙蜗居十平米出租屋的经历,自是对沈老一直以来苦于一个住所而不得的困境而心有戚戚焉。彼时济南已经进入春季,五点多钟的天空依然有阳光和绿荫,透过公交车窗而进入的风也不再那么凛冽,且带有一点点潮润的暖意。车行路上,手上的书页也随着前行时而洒满阳光,时而陷入阴影,所以逐渐忘记公交车的人上人下,好像周围的一切都消失不见。于是逐渐融入到了书中的氛围,看到书中沈从文赞颂济南“街道又干净,又清净……极显然这种环境是有助于思索的。它是能够帮助人消化一切有益的精神营养,而使一个人生命更有光辉的”,不免心中有“与有荣焉”的得意,而当看到沈从文一而再再而三地被打断文物研究的进程,甚至被下放到湖北干校的坎坷经历,心里也有急切的焦灼——为什么他的磨难还没有到头!
关于沈从文的后半生,金介甫的《凤凰之子:沈从文传》与凌宇的《从边城走向世界——沈从文传》都有所涉及,前者简略深刻,后者婉转多情,而张新颖作品的特别之处在于,他大量引用了沈从文的书信和文章材料,使得沈从文的生命真实可感。作为传记写作,张新颖并没有带入过多的议论和点评,而是尽可能地选取沈从文的书信和文章原文,如同小心翼翼地保存着一口清澈的泉眼。这样的写作方式,虽然可能消隐了作者的价值判断,好处则是非常克制,并在材料的取舍之间看出作者所隐藏的情感。作者张新颖在《九个人》一书中谈及这本著作,用“故事”来概括这本书的主旨,他说这是“在绝境中创造事业的故事”“超越受害者的故事”“创造力的故事”“爱的故事”“时间胜利的故事”。以“故事”的思维统摄全篇,也造成了这本书在辨析史料、质证存疑等等外部研究中有所遗漏,与其说这部小说是一种“传记史”,不如说这是作者精心剪裁沈从文的言语和事迹而造就的一部“非虚构小说”,虽然失之史家的冷静,但仍然有文学家的丰沛和温情。时间和空间的转移是明线,而潜藏在深处的是融入“长河”“有情”的历史以及生命的完成,如盐入水,有迹无痕。
沈从文在《边城》中的文字被汪曾祺形容为“鼓立饱满,充满水分,酸甜合度,像一篮新摘的烟台玛瑙樱桃”。他的语言能让人一眼就觉察到仅仅属于他自己,“静止、结实、对称”,寥寥几笔却能传神。在书中引用的无数文字中,隐隐地能看出围绕在沈从文后半生的三个话题——物质文化史研究、时代与个人的关系以及活泼不拘束的审美观。
“为什么我手中的笔,突然失去了光彩,就是我手中的笔,为什么一下子会光彩全失,每个字都若冻结到纸上,完全失去相互关系,失去意义。”
——《沈从文的后半生》第41页
学者姜涛的学术论著《公寓里的塔》探讨了在上世纪二十年代,“文学青年”如何徘徊在“街头”和“公寓”之间,迷茫于自己未来“志业”的选择,其中有专章论述沈从文在北京的早年经历。从“窄而霉斋”中走出的沈从文似乎用他的笔碰开了一条路,从他所厌倦的军旅生活逃离,成为大学教授。当纸上的虚构王国无法继续搭建的时候,他又在西南联大搜集“花花草草瓶瓶罐罐”的基础上,开始“由艺术和文化的理想出发,落实到历史文物方面的具体事情”。这实在不是他一时的异想天开,其中思想脉络,从他在沿着湘江顺流而下之时,便在心中思考。而且他“经手过眼”的文物数量,也不在少数。沈从文青年时期在陈渠珍处做幕僚之时,便过眼了陈渠珍收藏的种种古物,并开始收集各类碑帖,而沈氏在西南联大之时,各种文物收藏也添置了不少。汪曾祺在文章中曾经忆及,沈从文称赞在集市上购来的一件黑红两色的大漆盒,说这样的纹样可以做《红黑》杂志的封面。经历了这些积淀,才有《中国服饰史》这样的著作诞生,如此种种因缘,最终结为善果。对于沈从文开始转向历史文物研究的努力,书中是这样评价的——“由自然的爱好和兴趣,发展到对世界、生命、自我的认识和体会,并且逐渐内化为自我生命的滋养成分,促成自我生命的兴发变化”。
在1947年发表的一组“北平通信”中,沈从文说“希望用‘美育’与‘诗教’重造政治头脑之真正进步理想政治”,虽然那些文字在当时的局势下可谓“痴人呓语”,但在十几年后,这个理想却以另一种形式实现了。那便是从事文物研究。
1963年,沈从文写了《过节和观灯》,发表于《人民文学》第4期,其中有一部分《记忆中的云南跑马节》被更名为《云南的歌会》被入选为人教版八年级语文课,成为大部分人对于沈从文文字的最初记忆。这篇文章虽也有那个年代常用的颂歌,更多的是一种民俗与名物上的充盈与丰满。他细细描绘“性情明朗活泼”的赛歌妇女、热闹至极的 “金满斗会”、有着“犀皮漆”的马鞍,虽然这幅画卷的背景已不在描绘他所熟稔的湘西,但还是有着同样热烈的边地风情,他那讲述“边缘的神话”的愿景,依然是没有变的。
这也是他一直所推崇的史学观念——“由物证史”。所以历经磨难,一本煌煌巨著《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终于著成。
“艒艒船还在作梦,在大海中飘动。原来是红旗的海,歌声的海,锣鼓的海... (总而言之不醒)。”
——《沈从文的后半生》第157页
沈从文的后半生,是不得不由“思”而进入“信”的一生。“时代”与“个人”的矛盾,在他的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在豆瓣网站上,作家班宇留下了他对于这本书的评价——“沈将生命与境遇尽力隔绝开来,以沉浸与专注,来抵抗时代的荒谬与虚无,难得并且有效”。如果说在沈从文早年,是用写作在“黑暗涧谷上造塔”(袁一丹语),而他后半生的文物研究,则是在“丰饶民族历史情感”的基础上,积极地“做点事”,为自己剩下的人生建造一座新塔。我想张新颖在裁剪材料之时,是很为他的境遇而愤慨的。不然张氏也不会在书写一连串沈老被命运种种捉弄之后,又提及其他国家的学者对沈从文作品的研究与推崇,这让人唏嘘不已。但沈从文的命运其实比那些被尊于潮头又被浪潮抛下的人好得多,远离了文艺的风暴中心,远离了时代的主流,他反而找到了自己的园地,耕耘出了自己的收获。
张新颖是这样总结的——“强大的潮流在力量耗尽之后消退了,而弱小的个人从历史中站立起来,走到今天和未来。”
“当时的我呢,天不亮即出门,在北新桥买个烤白薯暖手,坐电车到天安门时,门还不开,即坐下来看天空星月,开了门再进去。晚上回家,有时大雨,即披个破麻袋。”
——沈从文检查稿
在历史博物馆的工作条件是困窘的,书中的沈从文一直希冀于一个办公桌而不得,而不得不“在午门回廊凑合了几年”,但即便是这样,沈从文还能领略到自然景物中事事物物的美丽。即使迫不得已所写就的检查稿,他的文字依然是那么饱满美丽。他亲近自然的一切事物。1956年,沈从文重返青岛疗养,这是在他生命早年留下深刻印迹的城市。海令人静默深思,淘深着他的生命。而自然对他陶冶,让他性情不喜拘束,而热爱所有自然展现天性的事物。“活泼”就是沈从文文章中常用的一个词,他在解放初期说:“时代极其活泼,而文坛极其呆板。”在沈从文论及文物的文章中,“活泼”也俯拾即是,他指称殷商时期的雕玉兼具“秀美活泼”和“严峻雄壮”,唐代造型艺术“色调鲜明,组织完美,整体健康而活泼”。这来源于他那不受拘束的审美观,是从他的湘西故乡逶迤而来,那青山绿水,边地奇景,苗族风情。沈从文就是被这样的东西所滋养的。
其实让他着迷赞叹的是这些器物之中凝结的劳动者智慧。汪曾祺说:“他热爱的不是物,而是人。”这种对劳动人民的关注,从沈从文的文章可以一脉而知,他追忆“看到小银匠锤制银锁银鱼,一面因事流泪,一面用小钢模敲击花纹。”工艺美术在中国有着源远流长的历史,但由于古代士农工商的排序,很多能工巧匠的佳名便埋没在历史风烟之中。沈从文是这样认识那些工艺美术品的——“一切美术品都包含了那个作者生活挣扎形式,以及心智的尺衡,我理解的也就细而深。”
由此,文人的“抒情史”退隐了,而劳动人民的“心史”显露出来。
在凌宇的《沈从文传》有这样一则材料:有一年,黄永玉去一个林区考察写生,他将在森林里的生活和见闻写信告诉沈从文。收到来信,沈从文写了一封长信作复。在信中,沈从文谈了三点自己的经验:一、充满爱去对待人民和土地;二、摔倒了,赶快爬起来往前走,莫欣赏摔倒的地方耽误事,莫停下来哀叹;三、永远地、永远地拥抱着自己的工作不放。
汪曾祺在沈从文八十岁寿辰时写就一联:玩物从来非丧志,著书老去为抒情。
叶赛宁在诗中说:“不惋惜,不呼唤,我也不啼哭,一切将逝去……如苹果花丛的薄雾
金黄的落叶堆满我心间——我已经再不是青春少年。”
又听到腰乐队的歌曲《一个短篇》中的歌词:“社会阵场上的勇将,在轰烈的炮火中间,别忘却身心的和睦。奋勇呀然后休息呀,完成你伟大的人生。”
沈从文的人生落幕了,全书也到此完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