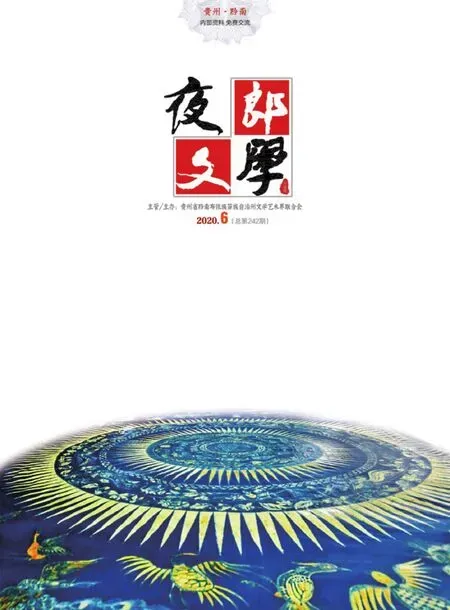亲人书
刘燕成
他们识字太少,或者不识字,又因老了,哪里都去不了,只好守着村庄,守着老屋,日起而出,日落而归。
二叔
那一夜,二叔搂着父亲,拼命地喊,可是,父亲再也没有答应他了。父亲走了,二叔说,他等于少了一只手,许多话,他不晓得和谁说了。这是我第一次亲眼看见二叔伤心地哭。
二叔和父亲,是村子里出了名的好笔杆。父亲教我们写毛笔字的时候,就说,你二叔,不也是我强迫着操练毛主席语录写成了字的么。看着父亲那很得意的样子,我们没有谁不敢相信父亲。后来,二叔总会给字儿写得漂亮的兄弟姐妹们多发几毛压岁钱。自古,村子里就有一种偏见:字个儿写得漂亮的,才是真正的有文化。因而,父亲和二叔,尽管只上过五年小学,却在别人眼里,他们就是文化人,是最懂知识和礼节的。平日里,好在我也喜欢那些舞文弄墨的事儿,于是左邻右舍都说,刘家的佬二,笋子高过竹了。每每听得别人夸赞,父亲和二叔比我还要高兴,乐呵呵的,说,他读了那么多书,总不能都是读进牛屁股了,应该的嘛。
为生计,二叔走南闯北,他和父亲都吃苦不少,那时,什么都讲家庭成分,包括读书,也是要凭据家庭成分来读的。富农的崽,读什么书呢,难道还想翻身当富农,给我放牛去吧。村支书这样一句话,二叔和父亲,便就做了一辈子老老实实的农民。二叔给我们摆谈这些往事时,总是郁郁寡欢的,长长地叹气,眼睛润润的,就连胡须,都是直直倒立着。若是喝了半两酒,他便会语无伦次地叮嘱我们:争气!争气!要学会争气啊!
二叔喜欢喝酒。困了,倦了,累了,要喝了酒后方才舒服。高兴,逢喜事,或庄稼长势好,种儿收成不错,也要喝酒。酒是二叔自个儿酿的,用苞谷,红苕,高粱,或者大米,煨火慢慢烧烤。平日里,一个人在家,便是细细地饮,直到喝见了缸底,便又烤上几锅,放在黑屋角里,逢节日,则舀出来喝。当然,每每逢得有客人来屋,则是要多喝几杯的。若是遇得客人不好喝,捏着酒壶硬是不让倒酒,劝了数次,还不见松手,二叔便会装出发气的样子来,愤愤地,说:怕我没酒喝么,长江黄河干了,我家酒坛子,是不会干的。弄得满堂人,捧腹大笑。
二叔好客,且为人处世敢作敢当,村子里的人给他取绰号为“院长”,二叔觉得这个绰号没哪里不好,人家喜欢那样称呼他,便也乐呵呵地答应着。村子里的大小事,别人都喜欢说与二叔听,他们喜欢听二叔是个什么处理意见,年轻人都出了门打工,留守村庄的老人和妇女,凡事都喜欢二叔给他们拿个主意。乡里干部到村里去时,总是劝二叔入党,劝二叔向组织靠拢,村民还一致要二叔当村长,二叔不干。二叔说,村长太小,还是当“院长”好。
我曾经在一抹薄薄的玻璃块内见过二叔和父亲年轻时的合影,穿着上下各两个口袋的白衬衣,灰色裤子,留三七分的两块瓦发式,脸上堆满了年轻而又甜蜜幸福的笑容,他俩并排站着,甚是英俊潇洒。二叔和父亲的照片,常常使我想起这些匆匆流逝的岁月。是岁月,催人老,催人离去,这个关口,轮到谁,都躲不过的。有一日天将要黑之时,我在老屋外的晒场上,看见楼下的二叔,弯着腰,低着头,吃力地背着一捆干柴棒,正往家里赶。二叔在一梯稍高的石阶上,徘徊了好一阵子,他颤悠悠地伸出左脚,想努力跨上石阶,但明显力气不支,便又退了回去,伸出右脚,正想往上扑,然而迎来一个筋斗,哗啦的一声,柴棒从二叔背上滚落了下来,正压着了他的腿。我几乎是一口气冲了下去,一双手举起压着二叔的干柴棒。二叔努力爬了起来,装着没事的样子,但我明显发觉,二叔已经是真的老了。一个人,吃完人间那么多的苦痛,历经人间那么多的灾难,便就匆匆老去了。至今,那张白衬衣照片上的两个人,一个已经去了好些年了,另一个,也是接近花甲之年的老人了呢。
每一次离开村庄,二叔总要送我翻过老屋对面的那座坳岭,有时,是要直接把我送至六里外的乡场上,见我赶上了回城的客车,方才回屋。在城里工作和生活了这么多年,可二叔在送别时的那句话,我是不会忘记的——崽啊,好好工作,好好生活!
二娘
几年没回家,便发觉,二娘是真的又老了许多。
二娘是同村吴家的长女。村庄里,吴家女性名多带“兰”字,如:吴满兰、吴水兰、吴子兰等,因而,二娘名长兰,长念zhang。
我是从偷吃二娘的酸菜开始,喜欢上二娘的。母亲去得早,菜园子一年四季荒芜着,家里缺菜吃,我们便去偷二娘的酸菜。从老屋的后窗翻进屋内,轻手轻脚地,悄悄打开菜缸子,若是一开坛便能能闻得菜香,酸酸的,咸咸的,有点儿刺鼻子,便是已腌好的酸菜,伸手进去,便可抓出一大把,用事先准备好的黑塑料,包好,之后,又从后窗,爬出屋。当然,我们每次的秘密行动,均是有堂弟们帮忙的。二娘育有二子,大的叫成星,小的叫晋星,我们年纪悬殊不大,打小关系要好,整日的,打成一堆。成星早已晓探好二娘的菜缸子隐藏的地方,他说,在屋角最黑处,总是可以找得到菜缸子的。于是成星在前面带路,我们在后窗的屋壁下垫上几块砖,人踩在砖块上,仰着头,伸手将窗子轻轻往外拉开一条缝,身子从缝儿里钻进去,便就翻进了屋。待得酸菜偷到了手,后窗下的砖块儿,是得立即清理掉的,包括一不小心留下的深脚印,得用细泥,埋好。
二娘不晓得我们到底偷了多少回菜,甚至,我们不晓得二娘到底清楚我们偷过她的菜么,总之,至今都没有听到二娘提起过她的酸菜的事。一缸缸酸菜,被我们偷空了,带到学校,当饭吃,这倒是节约了父亲的不少开支。我们从读小学六年级开始,便住校了,每星期从家里带上米,秤了重量后便交给学校食堂,我们一点儿也不喜欢学校食堂里的那个老厨师,他给我们打饭时,总是将饭粒抛得很松,总是不够吃。我们只好用偷来酸菜,当饭吃。
细细算来,这些事,都过去20 多年了。现在,我们的大哥贵星,那个被我们称作佬三的营星,佬四成星,佬五晋星,他们也都各自成了家,各自过着自己的生活,而二娘,却是老了。
在家族的男丁兄弟当中,我排行第二,亲人们喜欢称我为佬二,但二娘总是把佬二的“二”念得很刺耳,她读er,去声,音很高,老远就听得见,辩得出。村庄里,念去声的“二”,是还有许多别的含义的,其中,有做人做事很厉害,雷厉风行,说话算数,能力很强,有本事等意思在内。在城里,很久没了老家的消息,我便会给父亲回几个电话过去,但父亲走了之后,我的电话总是回给二娘。妻也常常说,二娘能干,一大把年纪了还干着那么多的农活,辛苦了一辈子,不容易。
一次回屋,刚走到村口,就看见了二娘,她坐在屋外的晒场上,一个人,寂寂的。我看见那些咋暖还寒的风,卷起了二娘的花头巾,她黑旧的衣襟,在斜阳下翻飞着。她也老远就看见了我,大声地,喊着,佬二回来了!这一刻,我是多么的幸福。我发觉真正的娘亲,就是娘那一声不由自主的让她大声呼喊的乳名。我们出门在外,无论是漂泊,沦落,还是体面的为官,在娘眼里,我们是她极不忍心丢失在外的儿女,是带泪的牵挂,是痛心的思念。
夜里,二娘摘下火炕上的两挂烟肉串,用她刚刚腌制好的老酸菜,配上自家栽种的香料,猛火煎炒。二娘还给我们斟了两土壶包谷酒,教我们慢慢的饮。我们饮酒时,二娘便在一边细细地听我们天南地北的酒语。那些不着边际的话,二娘以为全是真实的。偶尔,二娘也会打断几句话,插几件家事进来,要我们好好地记着,掂量着。有时候,二娘也会说起我们早去的父亲和母亲,说他们辛苦了一辈子,没有享到我们的福,很不值得,倒是让她做二娘的,见到了我们今日的美好。二娘说这话时,便露出一副幽怨的样子。二娘还说,村庄里,谁和谁,往日总是无由地找我们的茬儿,甚至,打过我们,骂过我们,但我们不敢还嘴,任凭人家随意的打,随意的骂。谁教我们那时家庭成分高呢。二娘说。好在现在的他和她,没以前那样敢欺负我们了。说完这些,二娘脸容上渗出了一丝丝浅浅的得意和满足的笑容。夜半里,我们一直都在猜拳斗酒,用城里人的“十五二十”和“剪刀石头布”,一直玩到次日凌晨。我知道,和我猜拳的这些兄弟姐妹,他们还年轻,过不了几日,他们是要浪到外面去的。年轻的人们,没有一个是愿意留在村庄里的,只是在外面遇了不顺心的事,吃了苦头,方才又回到村庄里来躲一躲,养一养。最后,又留得二娘在屋里,一个人,寂寂的,守着我们的家。
我每一次回城时,二娘总要用黑塑料,偷偷地给我包上一些刚腌制好的新鲜酸菜,她总是不会忘记,摘下几串炕好的烟肉,洗净后,塞在我的背攘里,教我吃很久,都没能够吃得完。
满舅
小时我总是觉得,肉铺里的那些卖肉者,他们想吃多少肉就有多少的肉可吃,实在是太有口福了。满舅就是这样有口福的人。
肉铺是设在小镇街面的中央路段旁,一栋黑旧的二层吊脚老木楼,楼上是检疫所办公室,楼下则是肉铺,三进房子,共有十来个铺子,最挨近路边的那个潘老幺肉铺,就是满舅的。满舅姓潘,是二姑婆的独苗子,深得姑婆疼爱,村里人都喊潘老幺。
满舅什么时候做起了卖肉的营生,我是不知道的。大概从我有记忆起,他就是一个屠夫了的。村子里常常泛起满舅的吆喝声:“买猪喽——买猪喽——买大肥猪喽”。声音粗犷,洪亮,大老远都听得见。父亲好客,每每听得那寨脚传来满舅的声音,他便朝了那声音传来的方向,高声大喊:快快进屋来吃饭喽!
乡下人和乡下人,总用不得称名道姓,光凭那声音,就知道是谁喊谁了的。满舅进屋,端碗,正想吃饭,父亲把手横过去,夺了他的碗,然后递上满碗的酒,说,光知道吃饭,没有意思,喝酒。于是他们乐呵呵地笑着,一抬碗,咕咚几声,满碗的酒一口就饮尽了。下酒菜自然是满舅送给父亲的猪腰子。满舅说,腰子难卖,丢了又可惜,送你下酒吧。父亲好饮,且炒得一手好菜。在炒熟的猪腰子里加上一些香葱、大蒜粒、山藾叶、老姜等佐料,便是一道下酒的好菜了。
肉铺里的肉,几乎是从周边的村寨买去的。卖肉者从村里买去的是猪,卖出来的是肉,但是,卖猪的是老百姓,买肉的也大多是老百姓自己,卖肉者赚的就是老百姓的血汗。不过,真正赚钱的,恐怕是二楼那些收税的人。每个肉铺子都有固定的检疫费,他们在肉上盖上红印子:已疫检。一个印子一块钱,没盖印儿的,一律不准上市,更不得放到肉铺里来卖。据说满舅是因为懂得为人,和检疫所的人关系近,自然是得了许多免费的印子,据说他的检疫费也是按最低标准收取的。
肉铺里有一个做屠夫的幺妹,是湘西南那边的美人儿,继承了父业,成了卖肉者。她长得丰满,极富骚韵,但二楼检疫所的人偏就不喜欢,她便去讨好满舅。每每路过满舅的铺子时,她总是故意地用胸贴着满舅的身子擦身而过,眼光总是湿湿的,说话也没有遮拦,弄得你心子儿痒。满舅那会儿还没有讨上媳妇,能有那档子艳福,心里正乐着。“软软的,热热的,真大”。满舅喝饱了酒,便情不自禁地要把那事儿说给父亲听。父亲总觉得一个卖肉的女人,终日的操刀砍杀,到底是不会好到哪里去的。便就劝着满舅,千万不得鬼迷心窍。
与满舅邻居的那个肉铺老板,做了一辈子的卖肉生意,快要接近古稀之年了,一直都舍不得歇下来。这老鬼,最拿手的活儿不是卖肉,是耍秤杆子,少你二三两秤,不多,但也不少,你去找他,他便再割一小块的肉丢给你,陪你一个笑脸,你想骂他的欲念,就消了。大多的人,懒得去计较,少了就少了,下次央他多割上几两,也就罢了。这个老鬼也就是靠着这不断的短斤少两的秤儿,弄得富贵了起来,据说他是七十五岁那年,方才丢去了卖肉的活儿,专门的坐在屋里享受那余下的光阴。我到镇子里上中学那会儿,还见得几回他的面,油光的三七分头式,笔直的西装,领上捆一条花领带,富足的豪气一点儿也不减当年。只可惜人已老,身上的四肢已经明显不够用,拄着拐棍儿,步幅蹒跚的在街面上路过。
检疫所后来搬迁了,肉铺的那栋木楼连同地块一起被卖掉了。还好,卖掉肉铺那年,满舅讨来了自己的美人儿,他们一起返了村子,细心耕种着姑婆留下的那几分地。
一个农民,他到底是离不开土地的。我觉得卖了半辈子肉的满舅,就是这样子的一个人。
干爹
小镇紧壤湘西南的那边桥,每日都会摆上一个摊儿。铁锤、榔头、细铁丝,起子、火钳、老虎夹、钢钉磨成的铁钻……这类铁器物就挂在摊子空箱内的晾干上。箱子旁边整齐地码放着不同码子的鞋,鞋堆高的,则为已经修好的鞋儿,矮一些的,则为还没有修好或即将要修好的鞋。箱面是一个用来操作修鞋的平台,摆放有各色鞋线、烂胶片,502 胶水和别的其他胶水或杂物。箱面极窄,可最后还得留下一些空地,用来摆置修鞋临时搁放的工具。修鞋者,是我的“结伢”(干爹),一个刚刚而立的小老头,头发蓬乱,胡须似乎从来就没有刮过,长长的,垂在下巴上。他戴一副眼镜,样子却是很打精神的。
我是很少得去镇上玩耍的。仅仅是因为我长得丑,脸上患得有一种疟疾。一种被村里人唤作观音虫的病菌,啃噬了我的脸皮,干辣辣的。我用鼻涕、口水,给自己的脸儿解潮,缓解疼痛。结果,人越长越丑,父母觉得我已无脸见人,便就将我关在家里。可是,干爹一点儿也没有嫌弃我。他挑着修鞋的工具箱,爬过老屋背的那座坳,远远地,朝着我家的老木楼,隔着坡,喊我的乳名:
阿火——阿火——
我打开后窗,小心翼翼地爬到阳台上,沿着门前的竹尖望下去,我看见了干爹,他的肩上多了一条洁白的汗巾(大概是某女人赠送的)。他正坐在坳下的树脚,擦着汗,等我。实际上,干爹原本是一个和我素不相干的人。因为父亲相信命相,父亲说,我的命相属火,要保住我健康成长,就得找一个命相属水的本家人,来压一压我的火。我和干爹赶到小镇摆摊的桥头时,太阳就已蹦跳出来了,街面上也已经来了不少赶场的人。干爹是单身汉,出门从来就没有什么牵挂,一个人的家,一个人出了门,屋子就空落了。我给干爹做伴,多少让他觉得了不少的温暖。我容貌的丑,被他的寂寞掩盖了。
干爹修鞋的时候,我就待在一边打杂。一会儿给他递上起子、刀具、或者修鞋用的线条,一会儿又得接过他刚刚修好的鞋子,将鞋子整齐地摆放在鞋箱旁,甚至有时候,得跑到湘西南那边的白水洞,打井水喝。我实在是懒,干爹连声催了几次,我都懒得动身,于是他便责令我:你去不去,你到底去不去。他手里举着修鞋的细铁丝,做着要打人的样子。我扭捏着身子,慢腾腾地,老半天也不给他把水打到摊子里来。干爹在鞋摊边渴得心里慌,四处打望着,却依然不见得我人影儿,干脆就丢了摊儿,跑到桥下的溪里,喝水。
实际上,干爹的生意一点儿也不好。不,应该说是他一日的收入实在太少,生意倒是火爆的紧。一个赶场日,干爹要修理上百双的鞋子,有的是破了皮,有的是断了底,还有的是脱了色。哪儿烂了,干爹都能修,但价钱一律五分一次,而且,熟人熟面孔的,免费修理。如此下来,一个赶场日也就充其量五块钱的收入。可气的是,时常会遇得收税的人,不管你是卖菜也好,修鞋也罢,一个摊儿收三元的税款。干爹说,三元,得修多少次鞋啊。干爹的话,是说给收税的人听的。可是空闲的时候,干爹抱着我,教我做算术题,题目是:修鞋五分钱一次,一天修一百次,一天能得多少钱。我闭起眼睛都能回答,五块。然后他又说:假设减去三元税钱,最后剩好多钱呢,如果我还是能够回答得出,他便又说:三块钱,要修多少次鞋。这时候,我猛然觉得,干爹说给收税人的话,有时候却也是说给我听的。
太阳就要偏下西山了,街面上的人儿稀了,干爹开始收捡摊儿了。摊儿上是一地的鞋子,修好了却还没有认领的、来认领过了却还没有修好的、刚刚带过来的、摆放很久了的,一切还停留在摊子里的鞋,干爹都似若宝贝一般,小心翼翼地放回了鞋箱内,上了锁儿,回到屋后再翻出来修理。
末了,干爹总不会忘记跑到肉铺里,割上一刀肉,挂在鞋箱的担子那头。我跟在干爹的担子后面,心里想着晚上的肉宴,大滴大滴的口水,情不自禁淌了出来。
向叔
向叔是2012年8月17日走的。这事情虽在意料之中,但真正听到噩耗的那一刻,泪水还是忍不住流了下来。
向叔家就在我家老屋坎塆下不远的一个半坡上,小时我们常常在他空空的木屋楼上捉迷藏,后来向叔把屋子装修了一番,接进了叔母,我们不得不另选了玩游戏的地方。
幼时,我总是非常的畏惧向叔,虽然向叔长得面目和善,说话细声细气的,从来不随便打骂小孩子,但我仍是不敢轻易靠近他。即便后来长大懂事儿了,与向叔半路相遇时,仍只是礼节性地道一声问候,从不多话。
2000年9月,我高中毕业考取贵州大学,成为家族中第一个本科大学生,向叔听到这个消息,心里像乐开了花一般,逢人便说我是他最懂事的侄儿,知道上进。这一年9月,好像整个寨子都在为这件事儿欢喜,但父亲却怎么都高兴不起来,因为数千元的大学学费随之立即成为压在父亲心头的一块巨石。
向叔读懂了父亲的心事。他轻轻地对父亲说,我卖牛崽的钱还没有动,可先借给你缓解燃眉之急,我需要用时你再慢慢还我。我躲在书房里,透过木墙洁白的风孔,我看见父亲和向叔的影子,两双粗糙的手,正推过来挪过去地为借钱的事儿争吵着,最后父亲收下了向叔的钱。
时间一晃就差不多过去了12年。2012年4月初的一天,我接到一个从福建打来的电话,电话那端说:河星(我的乳名),怕是你听不出我是哪个了吧,我是你向叔呀。我确实猜不到向叔会给我打来电话,虽然我听人说向叔和寨子里别的一伙人都在福建打工,可10 多年不见,淡忘了向叔的声音了。向叔想请我在贵阳寻一家可治疗肝病的大医院看病,我问他是谁患了肝病,向叔突然低声告诉我,是他自己。向叔接着把他在福建几家医院的诊断结果和记录有病历的纸片发传真到我的办公室,我拿着向叔的这些资料第一时间找到了医学毕业的高中同学,一看,傻了眼,是肝癌晚期了。
后来向叔又给我说,不准备到贵阳来看病了,让我不要操心了。但大约过了三个月样子,我又接到向叔的电话。他再次要求我尽快联系看看在贵阳有没有可治疗肝病的大医院,我想着省人民医院距离家近,便急匆匆跑去预约了门诊号。2012年7月的一日,向叔从老家匆匆赶到贵阳来,可那一日单位上指派我参加一个重要会议,我没能亲自到车站去接向叔,而是待我会议结束赶回家时,已是夜深人静之时了。我进到屋,看见向叔还坐在我书桌旁,默默地想着什么。向叔瘦了许多,眼睛深深地凹陷了下去,腿上还带有打工时留下的伤疤,走路一瘸一瘸的,俨然不是我脑海里的向叔了。次日一大早我们就去了省医,但结果一点不理想。后来听得重庆有比较好的肝病医院,因而次日的晚上,向叔就买了赶赴重庆求医的车票。
再后来,我给向叔打过几次电话,电话里得知向叔的病情一日不如一日好,但他仍惦记着我的事。向叔来贵阳时,我的妻子正怀有身孕。每次电话里向叔都要问,宝宝生了没有,宝宝乖不乖。我说,生了,很乖,谢谢您挂念。我便听见电话那端,向叔咯咯的笑声。可是没过多久,向叔就走了,村庄里,我又少了一个至爱的亲人。
屈指算来,向叔去世距今好些年了,可是时间并未有冲淡我对向叔的怀念。
大姐
母亲走了,大姐就挑着了母亲的担子,在我们的记忆里行走。
印象中做的第一件坏事是和弟弟一起去偷吃别人菜地里的黄瓜,那是大姐出门三天后,我和弟弟趁天刚刚泛黑,肚皮贴着黄泥巴地一路慢慢向黄瓜园爬去,我们偷偷地卧在瓜棚下美美地吃了一餐生黄瓜,想不到第二天便拉起肚子来,才觉得事情不妙。不久前黄瓜刚刚被打了虫药,吃下去怎能不拉肚子呢。但更为可怜的是,我躲在茅厕里,听见黄瓜园里传来叔母的骂声,第三天叔母顺着脚印走到了我家来,抡着大姐的衣襟要和大姐理论并要求赔偿,大姐气得无语,狠狠地抽了我几竹鞭。
幼时,我和弟弟都很淘气,我们去偷砍别人的茶树来做陀螺,或者是盗偷家里的煤油在漆黑的夜里去照黄鳝等等,每次我们犯下祸害,别人首先指责的是大姐。碰到狠心人家,不仅指责大姐教养我们不严,就连我们去世了的母亲,也被揪出来指骂,实在是让大姐伤心至极。
最让大姐快乐的事,莫过于我们学期考试领着奖状回家,那金灿灿的奖状上镶嵌着的不单单是一个名字,那是一种无以言比的喜悦和骄傲。早早地,我们就想像着大姐看到奖状后将是一种怎样的喜悦。直到天色暗了下来,听见屋后堆柴的空屋里传来大姐放柴的声音,我们跑出门口,看见大姐从我们奖状前走过,昏暗的夕阳余辉里,逐字逐句念着奖状上的名字。
此后的岁月,我和大姐相互渐渐生疏起来,尤其是大姐有了自己的家和两个宝贝儿子后,我们的联系仅仅局限于节假日的礼节性往来了。直到一场突如其来的病痛在那年寒冷的十月降临到父亲身上,为了照顾父亲,大姐常常在两个家之间奔波。
每每看见大姐忙碌的身影,我便想,倘若母亲依然健在,大姐就不会如此劳累。大姐到底是没能守住父亲,那年的四月,父亲匆匆走了,留下无限悲痛让我和大姐慢慢咀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