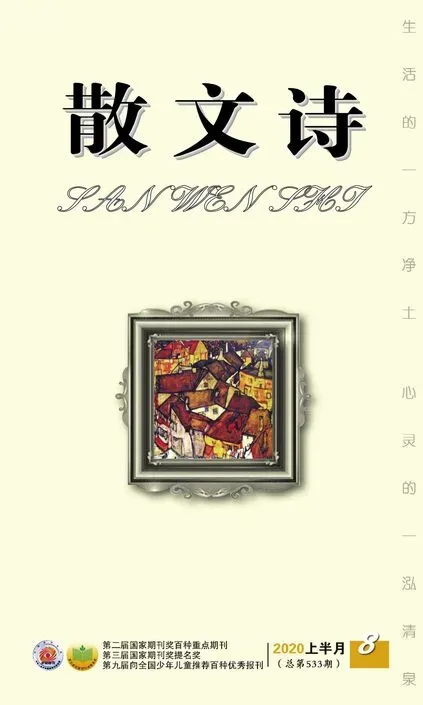我的湖
◎梦天岚
自画像
先不说沧桑,这个词的分量太重,轻易说出会显得矫情。
我坐在湖边的石阶上,眉头轻皱(这个世界并没有亏欠我什么),那轻皱的眉头里肯定有正在收拢的波纹。我的高鼻梁就快触到落日的余晖(让我仿佛看到往昔岁月在劳作中泛动的油光),我的目光则像是刚刚从僵直中醒来(它不忍抛下那些疲惫的身影),唯有紧闭的嘴唇仍然保持着接吻时的温软,只是皱纹更多更深了,预想中的老态已露出端倪。
这真的是我吗?
能道出这样的疑问一定是因为还保持着一颗年轻的心,这说明面容并不可靠。
我端详着自己——这张自画像。时间是我惯用的笔法(它更像一把雕刀),而这世间与我有过交际的万事万物会让我提炼出足够的颜料。令我没想到的是,湖水会成为一张画布,它自带显影液,随时可以显现,也随时可以消隐,不着痕迹。
我无意修改自己。
凡与生命有关的涂抹都有其必然性。动荡的湖水似在诉说,以连绵不绝的波纹。在我看来,它从未真正地平静过,亦如我的内心。当这种诉说浮现在脸上时,又形同沉默。
时间是一座看不见的尖顶档案馆,它无时无刻不在拍照、收集、整理、编号、存档,一动不动的,地上跑的,天上飞的,这世间万事万物的所有影像都标注了它们所属的日期和地点,时间档案馆戒备森严,无从查阅。人类也有档案馆,他们相信文字,以为文字能代替时间。
我的自画像在显现的那一刻就已被时间存档,没有征得我的同意,湖水就已发挥照相机的功能。
我只有一次次来到年嘉湖,一次次站在堤岸上看湖水中的自己,每一次都不相同,时间只允许我回忆,我不得不接受这样的事实。
我打算在合适的时候,用笔给自己画一张自画像,尽管没什么把握,甚至完全有可能不像我。没关系,我时常有不像自己的时候。不像的部分,会像很多人。
他们正排着队走在堤岸上。
树桩
树桩下震裂的泥土显出新意。我没有停歇,尽管双手磨出水泡,我还得继续敲打下去,用一柄铁锤,“梆…梆…梆…”一下一下地敲打。湖岸边的水因此有了轻微的颤动,示我以持续不断的涟漪。
我打下去的树桩就在年嘉湖畔。没事干的时候,我就在鸟鸣声中扛着一把铁锤到湖边去。我的树桩只能一点一点地铆入泥土,这个过程是那样缓慢,仿佛泥土中有不可抑止的痛需要忍住。那些在湖边漫步的游客,以为我要把年嘉湖拴在这棵树桩上。他们先是怀揣着好奇之心,驻足观望、摇头,或者感叹。然后怀着各自的心思,带着不可忖度的疑惑离去。
我不是担心年嘉湖会跑掉,它没有腿。也不是怕它被风吹走,与它相比,风和绸缎都要轻浮得多。
其实我最真实的想法是,把自己拴在这棵树桩上,像拴一头牲口。不管你信不信,我连绳子都准备好了,尼龙的。我要把自己拴在这里,和年嘉湖紧紧地拴在一起,我的树桩只会越打越深。
之所以钟情于这样的假想,或许是因为预感到了什么。就好比相信,终有一天,我必将弃它而去,用这不可托付的肉身屈服于世俗的蛮力。
多年之后,我打下的树桩自然会无人理会,偶尔会有一只掠过湖面的水鸟停在上面,待它展翅再度飞起时,它会因此背负一个人回眸时的深情。它飞得那样自在,那样轻盈,对自己所背负的东西却一无所知。
这些年我打下的树桩越来越多,湖边、河岸上、小区里、土坡上……它们一根紧挨着一根,放眼望去,就如同一片被砍伐过的树林。
五月之诗
五月的空气里有蚯蚓被锄断时散发出来的泥腥味,有蔷薇花在墙头争吵得不可开交的香味。
我再一次来到湖边。这种无意识的到来并没有被湖水所感知,尽管它的敏感超过我的想象。我猜想,它一定是全身心沉浸在这个五月里,不肯分神。跟我一样,它在寻找五月的诗篇,那属于它的部分,它怎么能轻易交给一个无名的诗人。
我并没有因此感到沮丧。五月属于诗的盛宴,我是那个没有得到邀请的误入者。好在没有人为难我,也没有人来验明我的身份。
宴会已经开始,年嘉湖早已布置好它的亭台轩榭。
阳光和风的热舞似乎从未停过,它们在微波起伏而又光溜如镜的湖面上滑行,快四,华尔兹,伦巴,那样密集而优雅的舞步没有谁能够模仿;柳树,香樟树,苕杉,枫树,银杏树,它们是盛装的绅士,有的随意地站在那里,有的列着队,频频点头,挥手致意或用身上无数片叶子鼓掌;麻雀、灰喜鹊,栗背伯劳,叼鱼郎,八哥,鹧鸪,老鹰,还有穿紫色燕尾服的燕子,它们偶尔从堤岸边的林子里飞出来,有的在空中盘旋,有的一掠而过,有的发出鸣叫,它们是记者、转场歌手、调音师、线路检修工;想必湖里的鱼也不会闲着,各种各样的鱼成群结队游过来游过去,它们是食客、巡逻队、游泳健将、闯荡江湖的浪子。当夜幕快要降临的时候,还会有各种各样的昆虫登上舞台,它们是鼓手、小提琴演奏家、合唱团、交响乐队……
没有诗歌朗诵会。不像人类,它们从来不朗诵诗,它们只呈现诗。诗自带光环穿行在它们中间,会引起小小的骚动。在诗出现的地方,它们会礼节性地退让,以便让出最好的位置。但它们从不朗诵,尽管它们有最嘹亮最清澈的嗓音,它们也不。它们只是在一旁看着,感受着,感受着诗带给它们的种种神奇和美妙。
不要问它们诗是什么。它们不会回答,因为它们正沉浸其间。
它们不仅有辨识诗的眼睛,还有辨识诗的心灵。
它们甚至会自觉地参与到每一首诗里去,成为其中的一个名词,甚至是一个并不起眼的标点符号。它们很乐意这样,并引以为傲。
它们的专注让我感到羞愧。
一首五月之诗,我竟不知从何写起。
夜虫奏鸣曲
有谁知道,那些鸣叫里有不被穿越的隧道。虫子们聚集在湖畔的树林、草丛、石头缝里,它们采碎石,铺铁轨,开着机车,把夏天提前搬运到这个春天。多么繁密,这燃放中的炮仗和星光下的骤雨,让我看到墙、圆弧棚顶和对一个世界的挚爱。
它们中的低吟浅唱,它们中的歇斯底里,让各种声部叠加在一起,没有一丝令人感到刺耳的杂质。它们个个精通音律,是天生的演奏家。
而我的世界清冷、沉寂。无边月色下,如同马蹄已逝的旷野,只属于凝望和等待。我一次次远离这里,又一次次折返,带着不可言喻的伤痛,回到内心的波澜。
该用怎样的汹涌才能应和。G大调奏鸣曲从未停止,声浪扑面而来,一层层将我推搡、包裹。当我经过,身后的空隙会被迅速填满。月光以从未有过的皎洁与湖水言欢,无非是让我更深切地感受自己——
我如此平静,这多么可耻。
一只鸟飞走了
一只鸟飞走了,我认出那是一只白头翁。
这么冷的天,即便是有翅膀,我也不会飞走。
要不要把年嘉湖也一起带走?它频频回旋,很快,它发现这个想法是多么不自量力。
它飞起的时候,扇动的翅膀像快要熄灭的火焰。它的鸣叫,徒劳而忧伤,这有点不像它。可以肯定的是,它不是昨晚在寒风中呼号的那一只。相对于呼号,它的鸣叫里缺少的是懊悔和绝望。
我了解它,总是想在纷乱中确定什么。可这次它的确定变得有点艰难,一定是有什么让它难以取舍。而那远方,一定有它曾经错失过的时光在等着它。我确定它必定会离开这里,离开之后必定不会再飞回来。正是因为这样,它既怀着一种急迫的心情,又飞得有点缓慢。偌大的天空,它是那样细小,细小得像凝在针尖上的刺痛。
它终究还是飞走了,不像曾经的我,一个羽翼渐丰的人,哪怕是逆着风飞翔,也是快乐的。属于我的快乐总是如此短暂,而更多的爱是靠不住的,总逃离不了被割舍的命运。每当感到懊悔和绝望的时候,我却愈加沉默。
天高地远,它会飞向何处?当我这样问,是在暗暗庆幸自己留了下来。而对于一只飞走的鸟,我便是它留下的一片空白。不关乎记忆,也不关乎未来。
湖畔的香樟树
立冬之后,有几棵香樟树因为倾斜,一些枝叶已伸进湖里。它们在水里触摸着什么?那天空的倒影多么虚幻,一触即碎,而湖水又那般冰冷。
所有能说出的语言都清瘦了许多,它们聚在一起,参与到香樟树的交谈之中。当它们说到风,风就大了些;当它们说到雨,雨就下得有点急;当它们终于说到那只飞走的鸟,天空就变得更灰了,仿佛天空只是用灰遮住了它。
我有点失望,它们没有说到更远的地方,一场可能的大雪在我的想象中已出现过多次。
我最终还是理解了它们,就如同它们理解我的沉默。
有时我把手伸向它们,它们会有莫名的感动,仿佛我伸向它们的手不太自然,有时甚至有点猜疑,或者充满不知来由的羞涩。它们则会借助风,稍加掩饰,我恰巧会看到湖水激荡的样子,看到它们正试图把手从湖水里抽回来。
那该有多么艰难,当时光呈现出一定的弧度,并定格在那里。
漫步者
我有时夹杂在他们中间,那些漫步者,总是能让生活在傍晚时分保持它应有的常态。沿着湖岸的曲线,他们不疾不徐地走着,这是属于他们的闲适时光,是另一种流动。我有时也会抽身出来,一个人坐在湖边的石椅上吸烟,看着他们一个接着一个,走过来或者走过去。若是走上一个整圈,原本擦肩而过的人很快就会重逢,但他们不会在意。
我倒更像是一个局外人。天色越来越暗,湖边亮起的灯光照不见我,我是一团黑影,有着极其模糊的轮廓。我看着那些漫步者,他们在灯光下闪烁着没有表情的脸。我只好看着自己又加入到他们的行列,一副忘我的样子,在他们之间疾走,像是在奋力追赶什么,哦,不,我走得太快,更像是要奋力甩掉什么。
此时的年嘉湖是比我更深的黑影,它轻轻地拍打着湖岸,在灯光能够照见的一小片地方涌动,仿佛黑需要连续不断地传递。
如果我是一滴水,年嘉湖则是一个转盘,我可能是它最先溅出来的那一滴。这让我既感到兴奋,也感到害怕。我迫使自己放缓脚步。跟他们一样,仿佛我的身后有一根绳子在牵着,而绳子越拉越长,有被拉断的危险。
我们在湖岸上漫步,从此岸到彼岸,浩浩荡荡。
湖里的天空
清晨,年嘉湖上的雾气还未完全散去。它是天空迫不及待要找到的一面镜子。
当天空终于照见自己,它的面容浑浊不堪,想到近在咫尺的蓝,不禁黯然神伤。
那个向湖里哈气的人,也不能将这面镜子擦得更亮。在错过秋天之后,他脸上的冬天是灰色的,或许比灰色更灰。
还有那个望着天空发呆的人,他想到了什么,纵有明眸清澈如许,那浑浊又该当如何交还?
谁又在轻叹?湖水不能抹平的皱纹,料想时间更不能。
在湖岸划出的边界里,天空陷入无边无际的沉思。
一片树叶
那曾经被嫩绿所托付的枝头已空空如也。
一片树叶在湖底沉睡。
它生命中的春天好像又回来了,排着队的还有燠热难当的夏天,而对于秋天它最刻骨铭心。它还梦见自己从树枝上掉落的那个下午。风并不大,却让它感受到一种震慑人心的萧条。
至此,秋风不能言说的它终于明白——“凛冬将至”,不仅仅是一个古老的预言。
终于可以在一片枯黄中摊开自己,它的水面脉络清晰。它的湖很小,它是湖中之湖;它的湖又很大,是可穿越四季的湖上之湖。
可现在,它像是年嘉湖的一只眼睛,于那幽深之处,它试着睁开自己。
忍着饥饿的鱼群曾追逐过它,翻滚的淤泥也试图将它覆盖。它在湖中越陷越深,它能看见的也越来越少,甚至开始一点点腐烂。
是啊,凛冬将至。一片树叶却找到了一个温暖的所在,在湖底,它将邂逅它的亲人,一些散落的种子,几根残缺的树枝,或者数枚有着坚硬外壳的果核……它若回忆,一只被遗弃的陶罐会成为它的近邻。
年嘉湖从此有了一张属于自己的藏宝图。耽于心跳的频率,就算是没有风,它也不再平静。
湖的量词
在面对年嘉湖时,我有意避免用一个量词去表达它的存在。以前只是一种无意识的行为,这样的次数一多,就难免会认真地思考其中的缘由。
一个,一片,一湾,一泓……
放在湖的前面,好像都不够准确。
个,过于随意,当人们不知道如何用一个量词来表达时,个,便成了万能量词。一个湖,念起来总感觉有点别扭。
“片”,表述的似乎只是湖的一个局部。
“湾”和“泓”,与“片”大致也差不多,出于形象思维的惯性,总感觉这几个量词都不能代表湖的全部。
汉语的丰富性在面对湖时多少有点词穷的尴尬。
相比较而言,既然没有一个特定的量词,也只有用“个”来表述。
一个湖,还有比一个湖更准确的表述吗?
应该是有的,只是词穷的不是汉语,是想象的缺失。
如果湖是安静的兔子,那它就是一只;如果湖是玻璃的镜子,那它就是一面;如果湖是不小心掉在地上的冰凉月光,那它就是一轮;如果它是一座城市用来呼吸的肺,那它就是一叶……
如果我的想象足够丰富,似乎任何量词都可以与之匹配。
当一个年嘉湖出现在我的面前时,有时我会想到那是一群,各种各样的湖,它们纠缠到一起,相互谩骂、厮打、和解、拥抱,最终亲密地合为一体。
只是它还是它——年嘉湖,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就如同我,我也是一个,汇入人群中可以甘于平庸而不被认出,也可以在黑色的沉静中捧出天空一样的蔚蓝。
可有时,我并非一个,也是一群。
这个下午
一种无可名状的愉悦推搡着我,让我看到清风的手格外纤长和柔软,身边的年嘉湖正泛起小的波浪,如无数张笑得合不拢的嘴,想必它的愉悦更甚于我,宽阔,绵延,感性,多汁,不可抑止。
我并不知道我的愉悦从何而来。它有可能过于复杂,也有可能过于简单。当一个人的身体变得轻盈时,那一定是愉悦起了作用。
这个下午的阳光也是刚刚好,不急不躁,不紧不慢,像一个称职的油漆工,将成吨成吨的金黄色涂料均匀地刷在树梢上、堤岸上、草地上、湖面上,薄薄的一层,像金箔,仿佛是为了匹配这样的愉悦。
对于人的一生而言,这样的时刻何其少。正因为亲眼看见过年嘉湖被抽干的样子,也知道时光对于一个人意味着什么,才知道所有的表象下面都隐含着鲜为人知的深意。对这种深意的探询,往往会耗费我们太多的心力。每个人似乎都浸泡在自己的水域里,太久了,会喘不过气。无数次我们以为浮出了水面,只不过是透一口气之后又沉了下去,我们都有一颗秤砣的心。不像此刻,心是柔软的,潮湿而透亮,它与年嘉湖像是处在同一个频率上,它们漾起的水波是如此吻合,那不断扩散开去的光的纹理是那样透亮,如同置身于仙境。
这个下午,我就浸泡在这一愉悦之中,或者说,是愉悦填满了这个下午。
是真的吗?我问自己。
当愉悦来得这样没有征兆,我竟然开始怀疑自己。这不是出于对一场美梦的怀疑,我知道它是真实的,我怀疑正是因为它太过于真实,以至这种真实在我的面前变得迷幻起来。
或许我太久没有享有过这样的愉悦了,或许我早已习惯面对现实的疲累和烦扰。
一个人要养足怎样的精气神才能领受这样的愉悦,才能让这样的愉悦像孩子一样单纯而持久,才能让心灵盛开成一座花园。甚至情不自禁想告诉身边的人,熟悉的也好,陌生的也好。就算没有一个人与我分享,这样的愉悦也不会削减半分。
空气也像是受到感染,仿佛整个人进入到一个预设的情境。这情境看上去多么虚幻,因为时间一点一滴见证了这种愉悦,它又是真的愉悦。
时间会因此停顿下来吗?
为这个下午。
一个下午,多么短暂,但它想成为永恒。倘若时间帮不上这个忙,它只有依靠记忆。
永恒太久,一生就够了,一生是记忆的极限。
趁这个下午的愉悦没有消失之前,我要将它封存好,完整地交给记忆。
我的湖
谁也别跟我抢。它就在那里,从东边的一扇小门进去,一眼就可以看到。
我的湖,它正是我现在看到的样子。再多的阴影也不能遮掩它,再多的光也不能将它收买。它跟我一样,保持着内在的清澈和沉寂。对于不可持续的热情,它有着异于庸常的淡漠。
谁也别想抢走。
我的湖,它一直在我的身体里晃荡。多年来,它始终固守着属于自己的边界,也理清了所有藤蔓的纠缠,习惯在每一个晴朗的日子里翻晒鸟鸣,在月色和树阴里坦露内心的隐秘。
我像一根树桩一样站在这里,不,我本身就是一根树桩。白头翁飞走了,还有鹧鸪、斑鸠、乌鸫、灰喜鹊,还有叫起来像救命一样的八哥和栗背伯劳。
我等着它们再一次飞来,成群结队也好,形单影只也好,让它们有一个歇脚的地方,顺便在湖水里照见自己。
谁也别想把一湖水搅浑。就算空气中遍布流言,树木因之枯黄,道途满是泥泞,我也会固守这方水域。大风过后,终会云开雾散,万物在洗涤中复归澄明。
那些妖冶如火的时光啊,将不断沉积在湖底,无非是月亮本该就有的花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