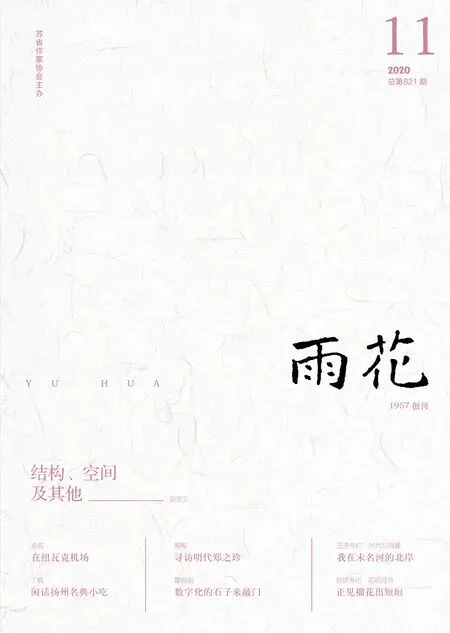别动我快件
说出来不怕你笑话,我新买的房子是个破房子。我不是没长眼睛,当初看房时,我就察觉到檐沟西南角这边漏水,水渍一圈一圈洇成天青色,像老树的年轮。中介和前业主一唱一和,说这是檐沟的防水坏了,一般十年以上的房子都存在这样的问题,这还算情况好的,重做防水小事一桩的呀,也花不了几个钱。我信以为真了。事实上,后来我花了两千块钱找人上屋揭瓦重做了防水,搬进来还没住上两个月,一场大雨彻底拆穿了他们的谎言。我与中介交涉多轮无果,只好自认倒霉,有什么好计较的,我可没打算在里头住一辈子。为了让孩子挤进全县城最好的师范附属小学,我们凑齐了首付款,借了银行十年贷款,买下这套学区房。它就是这么破,破得趾高气扬,你不买,后面排队的人一长串儿。
抱怨归抱怨,但既住之,则安之。不管怎么说,粉刷一新之后,凑合着能住,除了下雨天心情糟糕一些。其实,比房子更糟糕的是小区整体环境和物业。小区经历过一次老小区改造,从围墙外面看一片光洁,像浓妆艳抹的老妪。要是打开每一幢楼房下面的铁门,就像让老妪龇牙给你看,门背后的斑斑锈迹立刻暴露无疑。楼道里石灰墙上的内容就更丰富了,通下水、打洞、开锁的小广告层层叠叠,呼应着这个信息不断更新的时代。小区是开放式的,两扇大铁门常年敞开,我怀疑它的铰链一经转动就会脱落。至于安保系统,只有一个看门的老头,他大部分时间把头仰挂在座椅靠背上,细长的脖子总让人担心一不小心就会断掉。与老头为伴的是传达室里一茬又一茬的快件,它们来自各家快递公司。据传,老头的工资是由快递公司而不是物业公司发的。这似乎印证了他看的是快件,而不是那两扇破门。所以说,在这里,经常遇见一位衣衫褴褛的流浪汉并不是值得大惊小怪的事。
啰嗦这么多,绝不是存心吐槽,我是想说,这老小区也不是一无是处。据我了解,当今的快递公司一般不送件入户了,只派送到快递柜、小区传达室、附近超市等聚集处,有点像20世纪90年代农村送信的,只送达供销点,然后各家自取,稍显进步的是,他们会发一条提醒短信。这就显现出我们小区的优越性了,快件到了传达室,老头会进一步派送,送件上门。快递公司发送提醒信息,说您有快件在小区传达室请速取件,等我下班经过那里时,快件已经在家门口等我了。我住在五楼,网购的热情却能长期保持高涨,省去取件的繁琐,让我感觉占了大便宜,这使我对小区的不满一扫而光。一俊遮百丑,人总要往好处看的,对不对?
自从我们住进了“新”房,8 幢501 室,其实最大的不称心不是屋顶漏水,不是小区环境,而是没有电梯,这是不可改变的客观事实。起初我是没把这当个事的,不就爬楼梯吗,简单,我们年纪轻轻,腿脚没毛病。老婆以减肥的名义,把楼梯当健身器材,乐在其中。而对我这个微胖又慵懒的人来说,一次次爬下来才深刻体会到,这真是对肉体和精神的双重折磨,尤其是刚到家门口,发现手机或钥匙落在车里了,那一刻简直崩溃。有一阵子中午下班,我以加班为由,不愿回家,可办公室里的转椅不好午休,我常常一下午提不起精神,吃老板批评。
为了让生活更加美好,我决定首先解决午休问题。穷则思变嘛,我准备把楼下的车棚利用起来,改造成临时房间。
说是车棚,其实早就丧失了停车的功能,各家的自行车、电瓶车一律挤塞在楼道间里,车棚如果改名叫杂物间也许更确切。我们当初住进来时,也没心思、精力和财力来理车棚的事,聚了两三个月的工资后,我决定简单理一理。车棚里有一张前业主留下的一米二宽的旧床,收拾清爽,我就可以在单位食堂吃过午饭后,回到小区在车棚的床上躺一躺。
车棚在楼房的最底层,十五平方米,半地下,阴暗潮湿。也不知道前业主一家在里面干了什么,车棚里头一片狼藉,简直连我农村老家的猪圈都不如。水泥地和墙面上一块块一片片的霉斑、黑渍,像蛤蟆皮一样让人倒胃口。床摇摇晃晃,像被折腾多了,床上铺一张破草席。更要命的是床下,垃圾满地,碗、筷、盆、卫生纸、方便袋,乱七八糟应有尽有。最里面竟然还有一张X 光片,我用扫帚够出来时,白森森的腿骨戳入眼帘,吓得我一哆嗦。好奇心驱使我把片子捡起来看了看——姓名:刘良汉;年龄:65;意见:左腓骨下段骨折。姓名不是前业主,他家也不姓刘,懒得管他是谁,我直接把片子塞进垃圾袋。我花了休息日整整一天时间,总算把里头收拾清爽,又把床一阵敲打,试了试,只要不折腾,能用。但地面和墙面的污渍实在铲不干净。在这样的环境里怎能睡得香呢?我和老婆商量后,打算从网上淘些较便宜的地砖和墙面漆,再请瓦工、漆工、水电工通吃的表叔抽空来应个急。表叔的儿子也就是我表弟,前年在上海创业,周转不开,向我家借过一次钱,自此我家有事找表叔帮忙,他从不收工钱。用他的话说,滴水之恩,涌泉相报。也因为他这句话,当表弟再次因资金问题找到我时,我也没好意思一口回绝。
快递的速度真是快。我下单后隔了两天,六箱地砖和一桶墙面漆整整齐齐码在了我家门口。我看了看地砖的规格,80cm×80cm,一箱三片装,48 公斤。我一屁股坐到地砖堆上。我才爬上五楼,得先缓口气。我在考虑,是该给老头一笔上楼费呢,还是请他倒贴我下楼费?三个多月占的便宜一下子连本带利还尽了。我真想冲到小区传达室,指着那颗成天歪在椅背上的头颅大吼一通。
但我忍住了,我所住的那幢楼在小区的最里面,下楼走到传达室有一百多米距离,为了骂他一顿,来回二百多米,不划算,还不如省下力气把地砖往下搬。我在楼道里大吼了一声,宣泄了一下情绪。我上下折腾了两趟下去,就感觉整个人快要虚脱了,我真的只适合坐在办公室的转椅上设计设计广告。六箱呢,他是怎样扛上来的,得花多少力气,他是天生神力还是脑壳进水?一定是脑壳进水了,我坐在楼下的花坛边上,左手为右手按摩,右手敲打大腿,比中场休息的拳击手还累。这时,一辆自行车颤悠悠驶过来,真是冤家路窄,我一下子拦上去。老头歪了两下车龙头,懵懂地下了车。他有时睡得久了,也会出来透透气,以巡逻的名义在小区里转一圈。
我指着他,差点就破口大骂,看他头发近乎花白,一脸褶皱,想想还是忍住了,他也不容易。我尽量和声细语地说,你老人家送快件也不能太拼命啊,这么重的玩意儿上五楼,闪了腰谁负责?
老头一脸茫然,送什么快件?
我指指地上的一箱地砖。
老头说,快件都是各家自取的,每天几百件,你叫我一家家送,要我老命不是?
我说,我家从来没取过,不都是你们送的?
不是我送的,我吃饱撑的?
见鬼了。
小伙子你是几楼的,看着面生。
我仰头用目光指指顶楼,8幢501的。
8幢501就是你家?
我点点头。
这些日子你家的快件不少啊,不都是你家老头子拿的吗?
我家老头子在乡下种田呢。
他不是你家老头子?
哪个他?我越发糊涂了。
看门老头比划一阵,表达不清楚,最后干脆说,就是那个有点像流浪汉的老头。
哦……可他跟我没关系啊。
他不是你家老头?
什么眼神?我声音高起来,我怎么可能让老头子去流浪?
你家老头子,不,那流浪汉脑子不灵,没事老到我那儿翻快件,看到新快件到了就兴奋得手脚乱舞,一看到“8-501”逮着就拿,起初我不让,他说是他家的,我可不敢惹毛了他。但是我这人还是有点责任心的,偷偷盯了两次,他真把快件拿到8幢501了,这大半年都是他拿的,我真以为他是你家老头子呢。
大半年?怎么可能,我搬进来才三个月呢。
蹊跷事。老头晃着脑袋。
我说,下次可别再让他拿了,你看,我铺车棚的地砖全给扛到五楼了,我正往下折腾呢。
看门老头连连点头,逃也似的跨上自行车,自语说,真是蹊跷事。
我也觉得事有蹊跷,要不是今儿与看门老头顶了面说了两句,怕还一直蒙在鼓里呢。我第三趟往楼下扛地砖的时候,突然一激灵,坏了,怕不是前业主把他家人落下了吧?我差点让地砖砸了脚。那流浪汉脑子不灵光,赖上我家怎么办?这锅背不得。
老婆下班回来,进了门鞋还没换好,我就迫不及待地把这事告诉她,吓得她魂不守舍,晚饭也不思量煮了。她夜里噩梦醒来,把我摇醒,说,你是一家之主,你得想想办法。我迷糊着说,也不是一两天的事,明天再说吧,事没弄清楚,别瞎想,也不一定是坏事。饶是我如此说,直到天亮,我们都未能睡安稳。大约早上五点半,窗外鸟儿叫得正欢的时候,我拨打了前业主的手机。无法接通,又是无法接通,和我预想的一样。前些天,为屋顶漏水的事我就拨打过无数遍,每次都是同一个声音——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他换掉号码是正常的,看房时,中介就介绍过了情况,他们女儿考取了上海的一所大学,在上海买了房子,准备举家迁往上海,有钱人就是任性。在我买下房子之前,他们已经卖掉了本地牌照的并不算旧的一辆轿车,手机号码再一换,似乎就与这个小城全无瓜葛了。
没办法,我必须找流浪汉问问清楚,尽管我有点怕他,平时走在路上,也与他保持三米以上距离。他跟我见过的所有流浪汉一样,有一头乱糟糟的头发,有一双小而浑浊的眼睛,有一身冬凉夏暖、破烂不堪的衣裳,我无须仔细端详,远远瞥一眼便把这些异于常人的特质尽数捕获。我在小区门口等他。为了尽快把事情搞清楚,我斗胆向老板请了半天假。可是,我左等不来,右等不来,平常不想看见倒三天两头在眼头晃荡。到了中午,我没有耐心再傻等下去了,骑了电瓶车主动出击,在小区里里外外转了两圈,鬼影子都没撞见。我不得不给看门老头留下电话号码和一包香烟,拜托他一看见人就通知我。
下午快下班的时候,我接到看门老头的电话,果断丢下电脑里胡乱设计出来的半成品,飞快地赶回去。我直接闯进传达室。看门老头说,你可来了。流浪汉怀里抱着一只小纸箱,不用看我也知道,是我家的快件。看门老头说,他抱着不放,我也没招儿。
我鼓起勇气走上前,挤出笑容说,你好。
没反应。
难道耳朵不灵?我又上前一步,大点声:你好。
没反应。
在距他一米的时候,我不敢再上前了,我说,你手上的快件是我家的。
还是没反应。
我又指指快件,再指指自己的鼻子,说,这是我的,你为什么替我拿快件?他突然抱得更紧了,眼睛圆了起来。我条件反射般退后两步。看门老头说,你别惹他了,惹毛了不好收场。
我不甘心,又问,你叫什么名字?
没反应。
你家住哪儿?
没反应。
我帮你送快件吧?
他突然发出一声怪叫。我和看门老头都像躲点燃了信子的炮仗一样往门外跑。他抱着快件从我们身侧飞奔而过,一路“哈嘿哈嘿”乱叫,像原始部落的土著人。
看他跑远了,我也用不着追上去,我敢肯定,快件会先我一步到家门口。
我靠在传达室门上,朝看门老头说,这事你就不管管?
你叫我怎么管?看门老头一脸委屈,快件没少了你的,天天有人免费帮你取,知足吧。
我无奈笑笑,别人家的他也帮?
嘿,说了你别不信,这二愣子,只认8-501,不知道哪根筋接错了。
那天沟通不成,我回去跟老婆又商量一计,走下下策——跟踪。这真不是一件光彩的事。第二天,我再次向老板请了假,我得弄明白,他到底住哪儿,有没有家人。起先我觉得跟踪这个活儿挺刺激,有点像侦探,或者像特务,后来唯一的感觉,就是觉得自己有点蠢。这事毫无技术含量,我无须隐蔽,无须斗智斗勇,因为他根本就无视我。他走得很慢,左腿微跛,像装了减震器,一弹一晃的。有时在路牙上坐会儿,有时在树上蹭背,有时绕汽车转圈,我跟着他,大半天下来,觉得自己也像个呆子,也许我在路人眼里与他无异。他做的事只有两样,走和看,走大街、走小巷、走河边,看天、看人、看汽车、看广告灯、看垃圾箱,有时从里面翻出奶茶杯或酸奶盒,吸两口,扔回去。
跟踪真是个体力活儿,比坐办公室苦多了,接近中午,我饿得前胸贴后背。他坐到台阶上,一家快餐店的大门口,一会儿对左面的空气说话,一会儿对右边的空气说话,有时会把路人吓一跳。我靠在十米外的公交站台广告栏上无所事事,我就这样跟他耗着,无精打采。我真想越过他去,在快餐店里打一份盒饭,但我忍了。就在我一忍再忍的时候,快餐店的玻璃门打开了,出来一位穿工作服的小伙儿,把他拉了进去。不可思议的一幕出现了,我隔着玻璃清楚地看见,他在角落里的一张桌子旁坐下来,小伙给他准备了一份盒饭。看他在里面狼吞虎咽,我决定采取灵活策略,为什么我就不能坐进去把午饭解决掉?
他吃完,食指抠着牙,推门而出。我不能像他一样拍拍屁股说走就走,我在收银台结了账,然后顺便问了一下收银员,那人怎么不给钱就走了?我拐着弯儿想套个话。
收银员说,能指望他给钱吗?
我说,你认识他?
认识啊。
我激动得咽了一下口水:他是哪儿人?
本地人吧。
叫什么名字?
你查户口的?
不是。我苦笑一下:随便问问,好奇嘛,这么个人。
谁去管这些呀,流浪汉而已。
我说,既然不认识,干吗给他吃,还不收钱?
收银员说,不给他吃,他坐门口,谁还进来吃?
我说,也对,就这样白吃了。
收银员说,每天一份盒饭,成本几块钱,就当日行一善,你看我们生意不一样挺好的?
我说,他天天在这吃午饭?
收银员说,经常会来,不过隔了一段时间没来,后来又来了,他还指给我们看,原来腿受伤了。
他住哪?我不死心,又多问了一句。
收银员说,谁知道呢?
他今天的饭钱我一起结了,你们都是好人。我边说边扫二维码结账。
你也是好人。收银员笑得很可爱。我要务在身,没空跟她闲聊,赶紧推门而出,要是把他跟丢了,那不成笑话了。
又跟了一程,他又转回我所在的小区,进了传达室,翻快件,没有,又出去逛了。太阳还没有落,我过家门而不入,强打精神,再跟。我就不信了,他就没一个落脚的地方?我跟着他,路上车水马龙,商场里人真多,广场舞的音乐很带劲,公园里的树真茂密。我过去从来没注意过这些,总是人走在街上,脑子里依然是设计方案。公园里的长椅似乎也很舒服,他躺下了身子。我看了一下时间,晚上八点,我在旁边的长椅上坐下来,很快听见鼾声传来。这个点,是睡觉,还是小憩?我判断了一下,应该是小憩,晚饭还没吃呢。我也躺下来,这一天太累了。
躺下后我开始思考一个问题,我是在等他醒,还是要陪他睡?思考不出答案,我快疯了。但我没疯,很快平静下来,什么都不想,管他娘的,我困了。
不知多久,一阵凉风叫醒了我,我慌忙坐起,左肩让长椅的木条压得不能动弹,想看时间,手机没电了。公园里秋虫在唱,秋风在夜色里戏弄树叶,远处的道路上偶有渣土车经过,夜一定已经深了。他却睡得静无声息,灯光穿过树叶打在他的脸上、破衣服上,像一块块癣。天气渐冷了,他穿得比我还单薄,怎么就冻不醒呢?我走过去,看不出他快醒来的迹象。他一定睡得很深,不用考虑明天早晨吃什么、穿什么,不用考虑明天设计方案能不能对上客户的胃口,我突然觉得自己真是可怜。
我对着他熟睡的身体说,说说啊,为什么替我取快件?
声音像撞到了一麻袋棉花。
倒是说说啊,为什么替我取快件?
我没指望他能回答,如果他突然爬起来接了我的话,我会吓得扭头就跑。我揉了揉肩膀,拖着灌了铅的腿往家走,肚子里咕咕直叫,到家时已近凌晨两点。
老婆说,你死哪去了?电话也打不通。
我说,跟踪流浪汉去了,不是跟你商量好的吗?
她说,你是不是疯了,跟到这么晚?
我说,收获还是有的,我发现他露宿公园,好像并没有家人。
她说,管他有没有家人,明天再说。
第二天,我上班迟到了。关于流浪汉的问题,我没来得及和老婆讨论,我连早饭都没来得及吃就出门了,路上啃了一只包子。管他呢,一个流浪汉,我盯他干吗?在接受老板关怀的时候,我豁然开朗,大不了我不网购了,他没快递可送,问题不就解决了?这招儿叫釜底抽薪。老板对我这几天的状态很不满意,精力不集中,设计的东西丢人现眼。我只说,是,是是,是是是。我挺能理解老板的,要不是客户盯得紧,他一般不太批评人。
网购还真有瘾,停止网购,起初真是难熬。这个时代如果一下子没有快件可收,人该会有多空虚啊。熬着熬着,不到一个星期,我发现淘宝上那双鞋在做活动,真是诱惑难挡。形势总会逼人作出改变,我又豁然开朗了,换个送货地址不就解决问题了?寄到单位也行。有些东西寄到单位不太方便,老婆想出一个对策,仍然寄到小区,流浪汉只认8-501,咱地址不写8-501,写81-601,小区里没有81 幢,也没有601 室,反正单子上的姓名、电话是对的,丢不了。这招儿可真高。有几次,当我从小区传达室捧走81-601 的快件,看着流浪汉在那里撅着屁股翻得起劲时,心底一种说不出的快感油然而生。
我的生活又平静如常,老板也不再对我老板着脸了。偶然遇见流浪汉在翻找快件,关我什么事呢!一小区的人,都会遇到。他跟我没关系,跟我的快件也没关系了,我总是在心里强化这一认识。至于他为什么要翻8-501 的快件,我才懒得管呢,我工作很忙,家里也有很多事等着料理。表叔帮我把车棚收拾一新,中午,我可以在车棚里睡上一觉,真是舒服。
有一次,我刚睡醒出来,准备上班去,在门口遇见一位邻居。我知道他是邻居,但我并不知道他的姓名,也不清楚是几楼的,我们在楼道里相遇会互相点头,除了“你好”,谁也没有多说过一句,我已经习惯了城市里这种只剩下礼貌用语的邻里关系。他朝我的车棚张望了一眼,然后发出“咦”的一声。
他一定很羡慕吧,我掩饰不住喜悦却又谦虚地说,简单弄了一下,利用起来嘛,中午睡个觉,挺好。
他探着头又认真看了一眼:挺不错的,清爽多了。
我说,是啊,原来简直不成样子,下不了脚。
他说,原来是挺糟糕。
我说,之前那家人,也不知道怎么搞的。
他说,你不知道啊?
我说,知道什么?
他说,那个流浪汉呀。
流浪汉……怎么了?我脑袋里“嗡”了一声。
他说,他在这里睡过两个月。
他怎么会睡这里?我背脊直冒冷汗。
他说,你不知道吧,原来501 的人家可是好心肠。
好心肠?我脱口而出。我对使用了疑问句感到非常后悔,否定别人这很不礼貌,我从不轻易否定别人,但一想到屋顶西南角的那圈“年轮”,一想到总是无法接通的电话,我还是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
是啊,好心肠,那一阵,我们一个楼道都这么说他们,你想,谁会把一个流浪汉带回家?
嗯,心肠再好,谁会把一个流浪汉带回家呢?我应和着。
你不知道啊,那流浪汉的腿被撞坏了,501 的看他可怜兮兮,把他从大街上带了回来,就住这里,那几个夜里吵得像春猫,我们楼上下都听得见,好在他腿一恢复又流浪去了。你知道吧,他以前不在这一带,自从在这里住过之后,嘿,也不知道是不是产生了感情,经常在小区里转悠。
我的脑子里猛然闪现出车棚里那张X 光片,白森森的腿骨,姓名:刘良汉。刘良汉……流浪汉?
那……谁撞了他?我转向另一个话题。
谁撞了他?谁知道呢,一个流浪汉,谁会去刨根究底?他跨上电动车朝我摆摆手说,先上班去了,回头见。
回头见。
我站在车棚门口,开始纠结于一个新的问题,到底是谁撞了他呢?白森森的腿骨,一条黑色的裂缝,X 光片成像在我脑子里,我差点忘了我也要上班。
——南京市栖霞区“老党员工作室”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