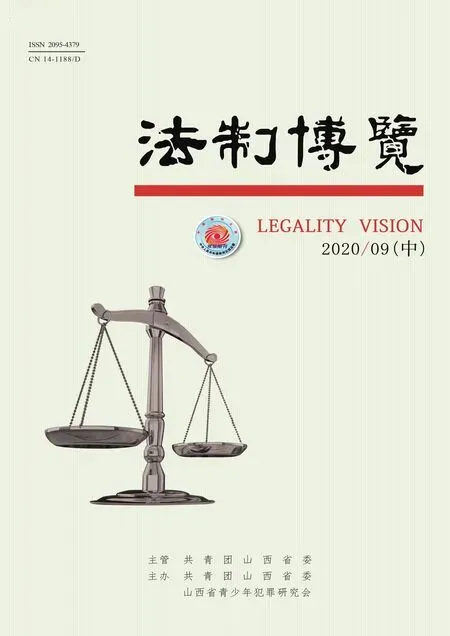从礼仪之争谈中国古代法律史上的礼与法*
赵博阳
上海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上海 200020
17、18世纪的中国发生了著名的“礼仪之争”事件。有关这场事件的过程,学界已多有叙述,本文不再赘述。笔者想要指出的是,礼仪之争的实质,其实是两大法律文明之间的冲突。这一冲突的发生,有其历史原因。不肯妥协的多明我会与方济各会会士,虽然身处中国,却未能真正理解中国礼仪的问题。他们或是将其视作道德范畴而用作附儒、合儒的手段,或是特别着眼于其迷信意味而大加鞭笞,却都没有看到礼法结合的中国古代法律文化之下礼和礼仪本身的法律属性。
“礼”是中国古代社会独有的社会现象,它的起源相当早,并且贯穿了整个古代社会。作为中国古代社会统治阶级最主要的统治手段之一,它对于维护社会结构与秩序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有关于此的学说与观念构成了传统中国文化的核心。可以说“礼”,渗透进了中国古代社会的方方面面,它调整着国家与个人、社会与个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礼”与“法”的结合,又构成了古代中国法律体系最大的特点,也塑造了独有的中华法律文化。无怪乎有学者说:“中国人的生活完全以礼为指南。”[1]本文拟从礼与法的关系、礼的法律化进程和中国古代法制史上的礼仪犯罪三个部分进行分析。
一、礼与法的关系
礼,起源于祭祀。从现有的文字记载和出土文物来看,从夏商时代起,中国古人就对祭祀极为重视,《说文解字》中讲到:“礼,履也,所谓事神致福也。”[2]后来,神权和源于父系氏族晚期的血缘家族制度结合起来,出现了礼制。西周时期,周公制定周礼,其实礼已不再局限于祭祀内容,而延伸到了调整统治阶级内部秩序、巩固宗法等级制度等范畴,逐步影响到国家、宗族、个人身份等级等诸多方面,成为了一种规范社会秩序的普遍性规范。
纵观中国古代法制史,礼的内涵相当广泛,几乎涉及国家、家庭(家族)、个人关系的各方面,起着约束规范的作用。“亲亲”、“尊尊”以及三纲五常等等,都是礼的内容,但礼的核心归结起来,是“亲亲”、“尊尊”这两条原则。换言之,就是通过规范身份等级,进而维护王权与父权。这也就是《荀子·富国》中所说的“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者皆有称者也。”通过礼的教化和规范,实现家国一体的统治方式,从而达到治理国家的目的。
中国古代的法律起源于习惯,是目前学界的共识。而礼与习惯相联,决定了中国古代社会礼与法的关系。在中国法制史上,法律最初的形式被称为“刑”,其后又称为“律”,再后来又改称为“法”。因此,可以说,中国古代最早的法律,便是以刑(刑罚)为主要内容,是统治阶级强加给民众的绝对命令和惩罚的手段。对于不遵守某种规范的人,施以刑罚,故而诞生了“出礼入刑”。
以孔子学说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在历史的进程中被确立为中国古代的正统思想。孔子本人就对周礼推崇备至,以他为代表的儒家学者们,在继承周礼的基础上,将其发扬光大,因时制宜,随时而变,不拘泥于刻板的教条主义,而是着重发挥其中的精义。《礼记》中说道:“立权度量,考文章,改正朔,易服色,殊徽号,异器械,别衣服。此其所得与民变革者也。其不可得变革者则有矣:亲亲也,尊尊也,长长也,男女有别。此其不可得与民变革者也。”[3]这段文字中所说的“不可变革者”,就是礼的要义所在。在这样的认识基础之上,孔子提出了“克己复礼”的思想。
儒家学说中有关于礼以及礼治的思想,慢慢渗透进了中国古代社会关系的方方面面,给古代社会打上了深深的烙印。儒家学者所追求的理想状态,是一种尊卑有序、长幼有别的等级社会,这被统治阶级用来作为治理的手段。法则是另一种治理国家的工具。两者成为了中国古代社会统治者的两种手段和工具,为统治阶级所服务。而礼和法所针对的对象,则是“民”——百姓是被统治的对象。
古代中国社会是从原始氏族部落一步步走来的。虽然成立了国家这样一种新的社会管理形式,但原始社会的痕迹——宗族学院关系——仍然无法抹去,并深深根植其中。儒家的礼治思想便从中萌芽并生发起来。在这样的思想中,每个人遵守礼成为理想社会的模范常态,一旦逾越了礼,就要用法这样的形式来制裁。简而言之,这就是中国古代法律的特有状态——以礼为主,礼法结合。
以礼为主,意思是礼作为中国古代社会一种普遍性的规范,涉及面之广,内容之多,渗透进了方方面面。国家的统治者,皆以礼作为法的纲(指导思想),从而来制定或者修改法律。而礼法结合,也就是说,礼和法作为服务统治阶级的两种手段和工具,相辅相成,前者是一种柔性的教化,而后者则是一种刚性的制裁措施。
二、礼的法律化进程
所谓礼的法律化,也就是指礼中一部分的原则转化成为了国家法律体系中的一部分,其目的是将礼和法中的规范意识和理念进行相合,将礼的这部分内容提升到法律的规范体系当中。
在中国古代的夏商时期,神权与宗法的思想是统治的核心。西周时期诞生了“以德配天”、“明德慎罚”的思想,这对后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及至春秋时期,奴隶制分崩瓦解,封建制得以确立,各诸侯国都开始了类似铸刑鼎这样的立法尝试,法的成文化成为历史主流。这一时期,百家争鸣,儒家提倡礼治,认为“忠孝人伦等宗法家族伦理是大经大法,是规范人们行为的准则”[4];而法家主张以法(刑)来治国,甚至要求本来应当依靠民事法律、行政法律调整的事务全部动用刑罚手段。到了汉代,在立法、法律教育、法的研究等方面,开辟了多重渠道,为礼入于法创造了有利的环境。从魏晋到隋唐,基本上是沿着这一脉络完成了礼法的结合。从现有的《唐律疏议》来看,无论是从立法的技术还是内容来看,都已经相当成熟,而礼法的结合也定型在这个时期。可以说,礼这一套规范在唐代时基本已完成了法律化,以至于后人评价唐律时,时常使用“一准乎礼”。唐代以后各朝各代的立法,基本上沿袭了唐律的道路,礼法并用、结合。
如果我们深入地了解唐律,就可以发现礼融入法的方式,前者是后者的灵魂,而后者是前者的外在表现,二者紧密结合,相辅相成。《唐律疏议·名例》中就说到:“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犹昏晓阳秋相须而成者也。”
从武德朝开始,唐代的立法活动就已开展,经历了贞观朝、永徽朝、开元朝几代才定型。在这个进程中,出现了许多“以礼改律”的情况。例如,在贞观朝前,对“谋反大逆”的规定是“谋反大逆人父子、兄弟皆处死,祖孙配没”;但到了贞观修律时,对于这一罪名的规定被修改为“谋反大逆人父子处绞,祖孙、兄弟皆配没。”这个修改的动机,主要是依据祖孙兄弟的血缘亲疏关系,调整的死刑范围。因为按照《礼记·祭统》中“孙为王父尸”的思想,祭祖可以孙列,说明了祖孙的关系比兄弟的关系要来得亲密,因此,如若祖孙配没,兄弟处死,显然于礼、于亲情不合。这是贞观朝改定这一罪名内容的原因。[5]
唐律除了有“以礼改律”这样的情况外,还有直接照搬礼典的做法。以《唐律疏议·名例律》为例,其中的“八议”制度就是对《周礼·秋官·小司寇》中“八辟”的翻版。《唐律疏议·户婚律》中“七出三不去”的规定,则是对《大戴礼记·本命》中“七去三不去”的翻版。
除了直接照搬礼典,唐律中还有对礼的原则和理念演绎的条文。例如《唐律疏议·名例律》中“矜老小及疾”一条的规定如下:“诸年七十以上、十五以下及废疾,犯流罪以下收赎;八十以上、十岁以下及笃疾,犯反逆、杀人应死者上请;盗及伤人者亦收赎;九十以上、七岁以下,虽有死罪,不加刑。”这一规范,实际上是从周礼中的“一赦曰幼弱,二赦曰老耄,三赦曰蠢愚”和《礼记》中“悼耄不刑”,“八十、九十曰耄,七年曰悼。悼与耄虽有罪,不加刑焉”演绎而来。此外,关于不孝罪的条文:“诸祖父母父母在,而子孙别籍、异财者,徒三年”、“诸子孙违犯教令及供养有缺者,徒二年”是从《礼记》“父母存,不有私财”演绎而来的。[6]
除了以上所述的特点之外,唐律在定罪量刑时也体现了礼深刻的烙印。以斗殴为例,一般人斗殴,所处的刑罚为“笞四十”,然而“诸殴缌麻兄姊”者,要被处以“杖一百”;而“大功”、“小功”的亲属关系,则要“各递加一等”;“尊属者”,还要“各加一等”;“诸殴兄姊者”,则更为严重,要处以“徒二年半”。最严重的是“殴祖父母、父母者”,要处以斩刑的极刑。由此可见,以卑犯尊的行为,随着亲属之间的亲属关系递进,唐律对其的制裁也相应地递增,这是维护礼的需求。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发现,在唐律中凡是违反礼的罪行,都要加重处罚。礼法结合,臻于唐代,也贯彻于后世的律法之中,成为中国古代社会的立法、司法原则,受到国家强制力的保证。引礼入法,礼法结合,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维持社会秩序的功能。将“亲亲”、“尊尊”的思想贯彻到国家的法律制度中,能够加强思想上的教育,人们也便于遵守,减少了民众的对抗性,一定程度上缓和了阶级矛盾。另一方面,中国古代所崇尚的价值观,诸如仁、义、忠、孝等,由礼入法,将古代社会中的人按照身份进行划分,进一步维护了封建社会的秩序。同时,国家通过法与礼两种工具,服务于统治阶级,丰富了治理国家的手段,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三、礼法结合下的礼仪犯罪
无论怎么样,礼都是抽象的观念,而“礼仪”则是礼的外在的具象的表现形式。周公在制定礼的时候,名目繁多,归纳起来大致有五种,即吉礼、凶礼、宾礼、军礼、嘉礼,总称“五礼”。当礼仪经由国家统治阶级认可后,便具有了法的特点。礼仪规范在历史的进程中不断得到发展,有关礼仪的立法也逐步成为了中国古代国家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虽然“诸法合体,民刑不分”被认为是中国古代法典编纂的特点,但中国古代法律体系中却是有民刑之分的。自两汉以来,各种法律形式逐步发展并趋于稳定,其中对违礼行为的刑事处罚规定,是礼仪犯罪属于刑事立法的体现。
律法之所以将这样的行为定性为犯罪,加以处罚,主要原因在于礼仪在中国古代社会中的重要性。它是一整套维护宗法等级制度的礼的外在体现,大到国家政治军事活动,小到个人婚丧嫁娶,事无巨细。
礼仪的首要形式就是维护秩序、巩固政权。礼仪中,以祭祀活动为最大者,也就是吉礼。祭祀活动是身份等级的象征,例如用来祭天的“圜丘”就被认为是统治阶级政权合法性的标记。历朝历代都会修建这一祭祀场所,进行盛大的祭天活动。因此,礼仪具有识别身份等级的作用。除此之外,在维护宗族伦理方面,礼仪也有着重要的功能。例如明律中规定了乡民饮酒时所要遵循的规范,是按照年龄的长幼,而非贫富来进行排序的。此外与凶礼有关的“五服”,是最能体现礼的精神的制度,乃至明律中加入了五服图。
同时,礼仪还反应了古人的一种精神寄托。历代,国家都垄断了天文历法的管理,设有专门的官员,试图据此来证实自己政权的合法性。而古人所制定的礼仪,就体现了这样的动机和目的。礼仪体现了维护封建社会价值与秩序的方式。基于这一重大作用,国家对礼作了明文规定,设置了相应的制裁方式。
国家制定了礼仪规范,并以强制力保证其实施,违反礼仪规范,就是礼仪犯罪的前提。周公制礼时期,尚无成熟的礼仪犯罪规定。两汉时期,出现了相当一部分礼仪犯罪的规定。汉律六十篇,其中《傍章律》、《越宫律》、《朝律》虽然已经亡佚,但应该是规定了一系列相关的条文,这从《汉书》、《晋书》中可以略知一二。目前关于礼仪犯罪,有据可查的律典应当是唐律。《唐律疏议·职制律》下设有六目,规定了六种违反祭祀礼仪的行为——大祀不预申期、大祀散斋吊丧、祭祀有事于园陵、庙享有丧谴充执事、大祀牺牲不如法、毁大祀丘坛。除此之外,还有乘舆服御物、监当主食有犯、主司私借服御物、匿父母夫丧这样违反礼仪的行为。这些规定散落在《唐律疏议》中的各卷中。宋代的律典基本上延续了唐律,没有什么太大变化。到了明朝,对于礼仪犯罪显示出更加大的关注,这体现在律典结构的重大变化。《大明律》按照六部进行分卷,单独设置了《礼律》一卷,集中对礼仪犯罪加以规范。
在《大明律·礼律》这一卷中,总共有条文26条,按照内容又可以分为祭祀和仪制两大部分。其中包含了违反吉礼、嘉礼、宾礼和凶礼几方面的内容。吉礼方面,主要涉及祭祀方面,包括了毁大祀丘坛、致祭祀典神祗、历代帝王陵寝、亵渎神明和禁止师巫邪术几个方面。对于祭祀活动的程序、祭祀活动参加者的行为、祭品、破坏祭祀场所的行为都作了规定。此外,对于祭祀活动的管辖,从中央还拓展到了地方,加强了对地方祭祀活动的规范。对于各地不当的祭祀活动都要处以刑罚,对忠臣烈士圣贤的墓,也加以保护。民间私自拜天、燃灯、亵渎神明的,也都是打击的对象。这是因为祭祀活动最能体现人与神的关系,是皇权专属,借助迷信来维护统治,为历代统治者所重视。嘉礼和宾礼方面,主要涉及婚冠、宴饮、宾客等方面的礼仪,《大明律·礼律》中有18个条文都与宫廷礼仪有关,主要用以调整君臣和臣子之间的关系,例如失误朝贺、奏对失序、乘舆服御物、失仪等;此外,也有和民间礼仪有关的条文,如弃亲之任、乡饮酒礼等,其所规范的冠服和饮酒方面的礼仪,也正是嘉礼和宾礼的典型。这些条文借助对礼仪的规范,加强对社会基层的管控。凶礼方面,主要涉及丧葬等,除了《大明律》律典篇首代表亲属关系的五种丧服图之外,“匿父母夫丧”条和“丧葬”条两条,是对违反凶礼的专门规定。凡是父母和丈夫去世,“匿不举哀者”,要被处以“杖六十,徒一年”的严刑。而居丧期间,如果有男女混杂,饮食酒肉的行为,家长要被处以“杖八十”的刑罚。[7]而在明代以后,清代的《大清律例》则几乎完全继承了《大明律》在礼仪犯罪方面的规定。因此,这就可以理解,发生在清代前期的中国礼仪之争的时代和法律背景了。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两种规范体系相遇并发生了激烈的碰撞。17、18世纪的西方对于中国礼仪问题的态度模糊不清,几经变更,乃至最后全盘否定,乃是由于时空、语言的阻隔以及对中国法律文化中的礼的陌生。
综上所述,在中国古代社会,国家通过立法的方式,规定和引导了各群体应当遵循的礼仪,具有法的效力。一方面,礼仪方面的立法规定引导人们的行为举止,另一方面对于违反礼仪的行为则施加制裁。礼仪犯罪本身就是中国古代法律“出礼入刑”典型。礼仪作为礼的精神的外化,作为“亲亲”、“尊尊”原则的外在体现,可以看成是一种工具和手段。在古代社会末期,明朝和清朝的律典在礼仪犯罪方面的规定变得系统,且条文数目增多,范围上也从中央拓展到地方,说明封建制度走向衰落之时,统治阶级更加需要礼仪来维护和加强专制,巩固政权。
四、结语
在中国古代社会中,礼与法的关系甚为密切,礼法结合,两者相辅相成,互为补充,影响着我国古代法制建设的历史进程。可以说,这一“思想”在中国古代具有相当强的“生命力”。对于当时的统治阶级而言,法律本身并不是目的,最终还是要维护国家的秩序,正所谓“以刑去刑,国治”[8]。在这一方面,相比法律,礼有着它不可比拟的天然优势。它能够通过提高百姓的“素质”,使他们自觉遵守规范,从而预防犯罪的发生。虽然礼是古老的,但它的一部分仍然遗留到了今日,被刻在了中华民族的基因中。因此,在当前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前提下,我们应该如何思考并重新看待礼,如何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其结合,将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