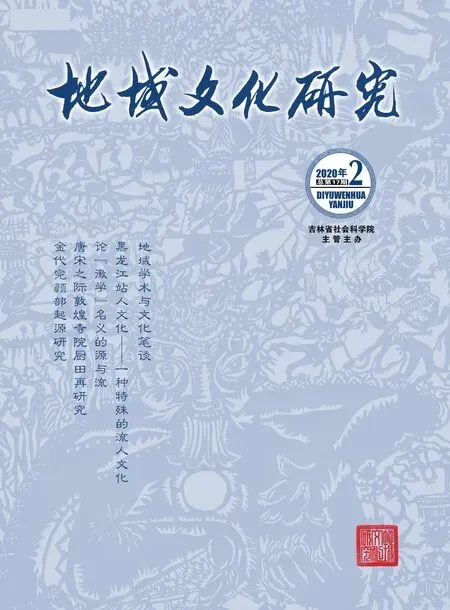河西走廊民间信仰的神礻氏类型与特点
——以张掖北武当为中心的考察
周建强
河西走廊是各民族间相互交流、交往与融合的重要区域。历史上,具有不同信仰文化的各民族间相互影响,造就了这一地带较为特殊的民间信仰①尽管学界对民间信仰的界定并不一致(参见陈勤建《当代民间信仰与民众生活》,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3年,第4 -8页),但学者从不同视角对“民间信仰”的阐释无疑深化了这一课题的研究。本文认为,民间信仰事实上就是“信仰的民间性”,这种认识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成为沟通、理解各种不同界定的前提。理解民间信仰最重要的是把握三个维度,即信仰对象(神灵或祀奉对象)的民间性、信仰力量(支持力量)的民间性与信仰归宿(去向)的民间性。从这层意义上讲,民间信仰是依靠民间力量的支持,且广泛流传于民间,又最终服务于民间的一种信仰形式与崇拜、祀奉体系,既具有一般体制化宗教的神圣性、超越性,又具有民间的自发性、善变性、实用性。本文的写作也是基于对民间信仰的这一理解而展开。形式。从河西走廊民间信仰的神礻氏类型及其在庙宇的供奉来看,虽然表现出走廊地带特有的多元性与包容性的文化风格,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多民族各种信仰文化与崇拜体系的交流与融摄,但从根本上来说,还是表现出与中原主流民间信仰传统极其一致的景象。张掖北武当位于河西走廊北面龙首山与合黎山的交汇之处,东临明清两代的山难关关隘,山内有清泉流出,地理位置十分奇特。张掖北武当肇兴于清康熙三十七年(1698)四月,原有大小庙宇27座,可惜尽数被毁。20 世纪80年代以来,在当地民众和信士的共同努力下,陆续兴建、修复各类庙宇52座之多,成为现今河西走廊最集中,最具代表性的庙宇宫观建筑群之一。一般而言,民间信仰崇祀的对象具有较强的稳定性与历史承继性,集中反映了当地民众的情感世界与精神生活方式。张掖北武当虽然肇兴于清朝,但其复兴却在当代,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当地民间信仰的历史与现状,然而,长期以来却鲜有探讨。本文拟以张掖北武当为中心,对河西走廊民间信仰的神礻氏类型与特点作一初步考察。
一、河西走廊民间信仰的神礻氏类型
民间信仰与体制化宗教关系紧密。与体制化宗教相同,民间信仰也是以祀奉对象为中心,形成的一种崇拜与信仰形式。与体制化宗教有别,民间信仰具有制度化程度低、分散性强,且与其他宗教界限模糊不清的特点。①杨清虎:《中国民间信仰学研究与述评》,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17年,第104页。民间信仰有着极大的包容性和杂糅性,是一种多元化复合型信仰形式②王守恩:《论民间信仰的神灵体系》,《世界宗教研究》2009年第4期。。河西走廊的民间信仰,特别是就其祀奉的神礻氏类型来说,兼具传统佛教神礻氏、传统道教神礻氏以及上古以来所流传的自然崇拜、鬼神崇拜、天神崇拜、祖先崇拜与英雄崇拜等多种崇拜为一体的信仰形式。从崇祀神礻氏的属性与功能来看,河西走廊民间信仰的对象可以分为天神与佛菩萨崇拜、自然与命运神崇拜、医药与健康神崇拜、仙真与人物神崇拜。
1.天神与佛菩萨崇拜
河西走廊民间信仰的天神与中国古代先民的祖灵崇拜、至上神观念、体制化宗教有关。而佛菩萨的信仰显然与佛教东渐、道教西传以及佛、道二教在河西走廊的交融有关。河西走廊民间信仰的天神主要有张掖北武当山顶最高峰无极阁祀奉的太玄圣母。作为宇宙的创生者和人类的始祖,太玄圣母在神话传说和民间信仰中,地位显赫,受到崇奉。佛母殿祀奉的是释迦牟尼与太上老君共同的母亲。玉皇阁、玉皇殿祀奉的是玉皇大帝。老祖殿祀奉的是鸿钧老祖与伏羲大帝、道德观祀奉的是女娲元君与道德天尊、王母宫祀奉的是王母娘娘、圣母殿祀奉的是黎山老母、送子娘娘殿祀奉的是送子娘娘、地藏王殿祀奉的是东岳大帝、三清殿与总神堂墙壁上所绘的云霄、碧霄、琼霄三霄娘娘。武当殿祀奉的是九天圣母(又称九天玄女或九天娘娘)、武当圣母等。此外,还有道教祀奉的是最高神灵三清尊神、救苦殿祀奉的救苦天尊以及真武大帝③按:张掖北武当供奉的真武大帝主要是明清定型后的形象,右手持有宝剑,而左脚下则有龟蛇交合的图样。另,与佛教无量寿佛相对,将真武大帝视为道教无量祖师的情形在湖北武当山也有发生,如早在元成宗大德五年(1301),武当山灵应观降笔的《武当山玄天上帝垂训》一文就曾以真武大帝的口吻说:“吾受玉帝敕命,长生治世福神。佛中即无量寿,道乃金阙化身。”(《藏外道书》,第22册,第417页)(无量祖师殿祀奉的无量祖师)。佛菩萨崇拜主要以释迦牟尼佛、弥勒佛、准提佛祖、虚空藏佛(达摩)、重兴佛祖(惠能)以及观音、文殊、普贤、地藏四大菩萨为主,兼有金光菩萨、南无大势至菩萨、千手千眼观音以及地方性的神灵仙姑菩萨。而在这些佛菩萨崇拜中,尤以地藏王菩萨、南海观音菩萨与释迦牟尼佛的信仰较为突出,特别是对地藏王和南海观音的崇奉。
2.自然与命运神崇拜
河西走廊民间信仰的自然神崇拜与中国古代先民的生产、生活密切相关,源于在当时极端低下的社会生产力条件下,人们对变化多端、神秘莫测的气候条件与自然现象的一种独特认知与反映,是古代先民自然神崇拜的承继与发展。而命运神崇拜则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它是人们对难以掌控的未来生活的紧张、迷茫与憧憬的另类反映,寄托了一定历史条件下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河西走廊民间信仰的自然神崇拜主要是龙王宫祀奉的龙王,祖师殿的星辰崇拜,如以祀奉释迦牟尼为主神的祖师殿左墙壁绘有北斗七星君,分别为第一阳明贪狼星君、第二阴精巨门星君、第三真人禄存星君、第四玄冥文曲星君、第五丹元廉贞星君、第六北极武曲星君、第七天关破军星君,右墙壁绘有南斗六司延寿星君,分别为第一天府宫司命星君、第二天相宫司禄星君、第三天梁宫延寿星君、第四天同宫益算星君、第五天枢宫度厄星君、第六天机宫上生星君。此外,观音殿的右壁上也绘有诸如龙王、牛王、马王、山神等神像;三清殿右墙壁上绘有源于中国古代先民对天、地、水自然崇拜的天官、地官、水官帝君。总神堂左墙壁甚至绘有水官禹王,表现出对禹王的崇奉。河西走廊民间信仰的命运神崇拜主要表现在对于财神、功名神与掌管生死簿神的崇拜与信仰。财神信仰方面有专门的财神殿及其他殿宇祀奉的文财神财帛星君、比干,武财神金轮如意赵公明财神及其侍从纳珍财神曹宝、招宝财神萧升,武财神关羽及其侍从手刀将军周仓与手印将军关平。功名神主要有文昌帝君及魁星点斗。掌管生死簿的神灵如北阴丰都殿祀奉的北阴大帝及其侍从牛头神,且左墙壁绘有马王真君与陆判官,右墙壁绘有牛王真君与崔判官。城隍殿祀奉的城隍、城隍娘娘及其侍从黑白无常。此外,还有地藏王殿祀奉的一殿秦广王、二殿楚江王、三殿宋帝王、六殿卞城王、七殿泰山王等十殿阎罗王。
3.医药与健康神崇拜
河西走廊民间信仰的医药与健康神不仅仅与人们对身体健康的关注有关,更重要的是与人们对疾病的担忧、恐慌以及医药治疗疾病有限性的认识有关,反映了人们对医药卫生等人类目前尚未完全认识领域的敬畏,希望借助于超人间的神秘力量减少紧张、烦躁与病痛,恢复健康。然而,从河西走廊民间信仰祀奉的医药与健康神来看,除眼光殿祀奉的佛教神礻氏眼光菩萨、滴水观音殿祀奉的滴水观音与大雄宝殿祀奉的消灾延寿药师佛外,大多是对历史上医药学家的崇奉。如药王殿以主神的形式对药王孙思邈进行崇奉。此外,药王殿左右墙壁还绘有古代医药学家如扁鹊、华佗、张仲景、李时珍等。其他一些殿也为药王孙思邈塑了神像,受到崇奉。这说明,河西走廊民间信仰医药与健康神除将极少数佛教崇奉的神礻氏作为祀奉的对象外,更重要的是还将历史上有功于民的医药人物神化,并作为崇祀的对象。而这种神化式的祀奉对象在河西走廊民间信仰当中有着广泛而重要的影响,反映了河西走廊民间信仰的人文主义基调,如当地民众普遍认为,山内涌现的神奇清泉为龙王爷所赐,具有驱魅疗疾的功效,但由于泉水所含的矿物成分不明,味道微咸,却鲜有长期直接饮用者,即便是那些神礻氏祀奉者、祈求者也往往从山下自带矿泉水引用。
4.仙真与人物神崇拜
河西走廊民间信仰的仙真与人物神主要是道教以往尊奉的著名神仙、真人以及有影响的历史人物。这与本土道教在该地区的传播、发展,历史人物的广泛影响以及历史人物在后世的神化有关。河西走廊的仙真崇拜最著名的当是万古长青丘祖洞对全真七子的崇奉,洞正中供奉丘祖,洞窟左右墙壁分别绘有丹阳真君马钰、长春真君谭处端、长生真君刘处玄、清净真君孙不二、广宁真君郝大通以及玉阳真君王处一。这种情况说明,道教全真派在清代以来对该地区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如清乾隆十一年(1746),道会司(全真派)魏阳洞、于阳海修建了紫阳宫,①(清)钟庚起:《甘州府志》,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第183页。而紫阳宫后来(1950)则成为张掖道教协会会址。1937年,张掖上龙王庙主持许合德不顾个人安危,救助红军西路军战士。1939年,道会司与道教其他派联合成立张掖县道教会,应对危难的社会时局。②张掖市志编修委员会:《张掖志》,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859页。甚至这一时期还涌现出了像全真道士李海龙、龚道人等武术名家教徒授业,发扬国术,其影响一直持续到建国初期。①金鹰等:《张掖市武术史略》,张掖市图书馆藏,1990年,第58页。此外,一些道教正一派仙真的供奉虽不及全真派一样显著,但也受到人们的崇奉。如题为正一三教扶教辅元大法师的道教创始人张道陵、神功妙济真君许逊、道教医学理论派真人葛洪、三眼灵光华光天王等则以殿堂壁画的形式进行崇奉。其他如老君殿除祀奉主神太上老君与南海观音外,还为八仙塑了神像,受到崇奉。河西走廊民间信仰人物神主要是儒家圣人孔子的神化,民间信众将孔子作为文昌帝君的侍从,与文昌一起崇奉,祈求佑护读书人考取功名。
当然,河西走廊民间信仰的神礻氏类型除以上四种外,还有少数如地方与行业神的崇拜。河西走廊民间信仰的地方与行业神崇拜主要有鲁班殿祀奉的鲁班,里城正神殿祀奉的里神、土地神与城隍神。而鲁班的崇拜与全国行业神的信仰基本是一致的,里城神合祀的情况则说明清代以来地方神,特别是乡村神灵地位的上升,甚至上升了可以与城池保护神一起享有尊祀,这也反映了清代以来乡村、城市地位在人们思想中的某种细微变化。
二、河西走廊民间信仰的特点
河西走廊民间信仰的神礻氏类型非常丰富,既有诸如远古以来的自然崇拜、神话人物崇拜,又有传统体制化宗教佛菩萨、天尊仙真的崇拜。河西走廊民间信仰是这一地区的人们认识事物的一种独特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们朴素的世界观与情感世界。从祀奉的神礻氏类型与崇拜对象的供奉来看,河西走廊民间信仰具有包容性与杂糅性、实用性与非功利性、地域性与自发性的特点。
1.包容性与杂糅性
河西走廊民间信仰的包容性是指将具有明显不同归属、类别与身份的两个至上神礻氏进行了联结与融合,包容了原来两个不同类型的信仰文化,从而创造出一个既不同于原来任何派别,又与原来神礻氏相联系的新的神礻氏。如在佛母殿祀奉的标为释迦牟尼和太上老君共同母亲的神礻氏。这种情形与佛教初传之时形成了极其鲜明的对比。魏晋时期,随着佛法东渐的不断深入,佛道二教之间的冲突也逐渐升级,道教方面提出了道先佛后、道优于佛的说法,并认为老子乘日精入国王妇人净妙口中,才有了佛。②(梁)萧子显:《南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2年,第931页。由于这一说法事关佛道优劣,甚至影响佛教在中土的发展命运,因而,此论一出随即招致了佛教方面的猛烈回击。如释慧通说,佛教所说的净光童子其实就是儒家的孔子,而迦叶则是道家学派的先驱老子,他们两人均是受佛的派遣,赴华传法的。③(梁)僧佑:《弘明集》,《大正藏》第52册,台北:财团法人佛陀教育基金会出版部,1999年,第45页。这就意味着,在佛教看来,佛先于道、又优于道。经过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的冲突与融合,佛教与道教无论是在各自义理的阐释方面,还是在社会参与方面都相互吸收,至明清时期,三教合一已成为儒释道发展的基本特征。张掖北武当塑造并崇祀释迦牟尼与太上老君共同母亲的神礻氏现象是当地对千年以来佛道之争调和的努力与见证,反映了当地民间对佛道同源的朴素认识,既有着深刻的时代烙印,是明清三教合一的时代产物,又受当地特殊的地形地貌的影响,是走廊地带各种信仰文化交流、交融的特殊反映,充分彰显了河西走廊民间信仰包容性的特点。
河西走廊民间信仰的杂糅性是指祀奉神礻氏的多样性、复合型与非纯粹性。张掖北武当除祀奉的神礻氏和神礻氏的称谓具有杂糅性的特点外,就是连同一个殿堂所供奉的神礻氏,乃至整个殿堂神圣性氛围的营造都表现出这一鲜明的特点。地藏王殿除供奉主神地藏王菩萨外,还供奉了包括十大殿阎罗王神像与值年、值月、值时、值日四大功曹画像,而十大殿阎罗王、四大功曹显然更多的是与道教信仰有关;南海观音殿的滴水观音壁画两侧却绘有武财神关公、赵公明的画像;观音殿祀奉主神观音的同时,还绘有三霄娘娘、送子娘娘;文昌宫在祀奉文昌帝君的同时,将孔子也作为帝君的侍从进行祀奉;甚至老君殿在将道教至上神太上老君作为主神祀奉的同时,还将南海观音作为与老君并列的祀奉对象进行崇奉,等等。神礻氏称谓方面,有将道教仙姑与佛教菩萨合称仙姑菩萨的现象。张掖平天仙姑信仰是当地特有的一种信仰文化,由来已久。①崔云胜认为,由于文献不足,平天仙姑信仰始于何时,已经很难稽考,但其兴盛当在明朝万历以后。(参见崔云胜《张掖平天仙姑信仰考》,《河西学院学报》2003年第1期)又,平天仙姑信仰无疑与西夏黑河桥碑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参见崔云胜《西夏黑河桥碑与黑河流域的平天仙姑信仰》,《宁夏社会科学》2006年第4期)当然,碑文还透露出在西夏国主李仁孝封敕之前,当地很有可能早就广泛流传着有关仙姑建桥的神迹故事。而将仙姑又称为菩萨的情形应该始自西夏国主李仁孝。②据西夏乾祐七年(1182)所立的《黑河建桥敕》说,西夏国主李仁孝曾敕曰:“镇夷郡境内黑水河上下,所有显隐一切水土之主,山神、水神、龙神、树神、土地诸神等,咸听朕命:昔贤觉圣光菩萨哀悯此河年年暴涨,飘荡人畜,故以大慈悲兴建此桥。……”(参见(清)钟庚起《甘州府志》,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第506页)仙姑菩萨合称则大致为清代民间的产物。在殿堂的神圣性氛围营造方面,杂糅性突出的表现在祀奉土地神与城隍神的威灵宫,却悬挂写有佛光普照字样的标志,等等。
2.实用性与非功利性
河西走廊民间信仰的实用性与非功利性看起来是一对充满矛盾、截然相反的概念,但却真实地反映了该地区民间信仰的一体两面性,表明了该地区的特殊性。河西走廊民间信仰的实用性指的是从祀奉神礻氏的功能来讲,他们大多与人们日常的生产、生活密切相关,涉及人的出生入死、身体健康、农牧业生产、房屋建造等众多领域。无论是在观音殿,还是娘娘殿,黎山老母殿都可以发现这样一种现象,即手捧婴儿的神像或神像旁边放置的婴儿鞋。③在观音像前放婴儿鞋的现象在全国比较普遍,并非独见于张掖北武当。(参见[法]逯是逑《中国民间崇拜·婚丧习俗》,高红兴据[英]甘沛澍英译本译,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1页)这说明,那些娘娘、菩萨,特别是送子娘娘、观音菩萨大多被视为与生育有关的女神形象,受到人们特别的爱戴和崇奉。此外,还有众多的地藏王信仰、玉皇大帝、十大殿阎罗王、城隍、北阴大帝及其僚属的崇拜。而这些神礻氏基本都涉及人生命的终结与来世生活的再现。可见,与人们出生与死亡相关的神礻氏成为河西走廊民间信仰主要的崇奉对象。其他如与健康有关的药王,与农牧业生产有关的水神龙王、水官禹王、山神、牛神、马神,还有行业神如鲁班等,诸如此类的神礻氏都表明河西走廊民间信仰实用性的特点,民众希望借助于对超自然、超人间神秘力量的祀奉,获得更美好的生活。当然,这只能是一种美好的愿望。
河西走廊民间信仰的非功利性是就其庙宇修建目的而言的。庙宇、殿堂的修建主要是为了满足当地及周边信众的精神需要,绝非出于收取香火钱的目的。大多殿堂虽设置了功德箱,但一般情况下,并无人看守,即便是在每逢初一、十五有人看守的特殊时节,守庙人也会提醒有上香需要的游客,支取放置在案几上的免费祭拜用品,殿堂的醒目位置时刻提醒香客注意防范烟火。河西走廊民间信仰的非功利性也反映了当地善良、淳朴的民风特点。
3.地域性与自发性
河西走廊民间信仰的地域性特点主要表现在将地方神礻氏纳入了祀奉、崇拜的范围。如在王母宫供奉王母娘娘与送子观音的同时,将地方神礻氏平天仙姑显灵黑河岸边,助解霍去病之困,战胜匈奴的神迹事件以壁画的形式进行了呈现。而这一神迹事件现见于《甘州府志》,且在当地民间有着广泛的影响。①(清)钟庚起:《甘州府志》,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第438页。另,有学者指出,刊刻于清康熙年间的《仙姑宝卷》是在仙姑传说的基础上不断丰富、发展起来的,包含着诸如发愿修桥、合黎山修道、助解霍去病之困等内容,其中助解霍去病战胜匈奴的事迹虽说发生在汉代,但实际上却反应的是明万历年间的社会现实。(参见崔云胜:《西夏黑河桥碑与黑河流域的平天仙姑信仰》,《宁夏社会科学》2006年第4期。)此外,在水神崇拜中,也有关于水官禹王的信仰。②有学者指出,中国神话系统中的抗灾英雄神话主要有抗击水灾和抗击旱灾两种,而这两种神话中的英雄人物都具有水神的性质。抗击水灾的英雄主要以鲧、禹为主。而禹作为治水英雄,也作为水神,其庙宇遍布中华大地(参见向柏松《神话与民间信仰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8页)。而禹王和张掖具有非常紧密的联系,可视为当地民众心目中的地方神礻氏。在张掖民间传说中,大禹曾经也有治弱水的事迹,甚至林则徐发配伊犁,途经张掖山丹弱水河畔时,还曾见过蝌蚪文的《禹导弱水碑》。方步和指出,张掖民间的有些说法与《禹贡》所记完全相符。而这些至少说明,大禹与张掖民众具有的一种特殊感情,因而,受到崇奉。③方步和:《张掖史略》,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02年,第43 -45页。河西走廊民间信仰自发性的特点是说民间信仰神礻氏的庙宇、殿堂修建基本上是出于民众的信仰心理与情感生活需要,是依靠民间力量自发兴建、修缮。修建过程中,民众结合当地的地形特点,巧妙地利用空间紧凑布局,随形就势,化整为零,安排神礻氏供奉。各庙宇、殿堂之间也没有隶属关系,同处一山,同为满足信众需要而服务。当然,也有学者指出,民间信仰自发性的特点还反映在其信仰内容和形式的非文本性,民间信仰的仪式活动与崇奉体系主要是依靠口耳相传、言传身教,并不像体制化宗教具有正式的文本形式。④向柏松:《民间信仰概念与特点新论》,《武陵学刊》2010年第4期。事实上,河西走廊民间信仰也具有类似的表现,有些建庙者甚至对祀奉的神礻氏并不十分了解。
总体来说,河西走廊民间信仰无论是从内容上,还是从功用上来讲,都较为丰富、庞杂,与体制化宗教风格迥异,但从这些“随意”“杂乱”当中,我们也可以发现它本身所存在的条理性及其与体制化宗教的密切关联。河西走廊民间信仰的条理化在两个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一为祀奉神礻氏的至上性,将神话神礻氏西王母⑤按:东王公、西王母(王母娘娘)在河西走廊的崇拜至迟在汉代就已经十分流行。详请参阅刘克《出土汉画所见太上老君在汉代的真形与雅号》,《宗教学研究》2017年第1期。、伏羲与女娲⑥按:伏羲、女娲作为中华人文始祖在河西走廊的崇拜至迟在魏晋时期就已经十分普遍与流行。详请参阅王晰:《高台魏晋壁画墓伏羲女娲图像解读》,《天水行政学院学报》2019年第3期。,佛教释迦牟尼、道教三清尊神始终作为重要的崇奉对象,供奉在显要的庙宇或殿堂。二为各类神礻氏均与民众的生产、生活、健康等密切相关,解决民众迫切关心的问题,但对于历史上医药学家的崇奉却再次表明,信奉人物神的纪念性。这种安排或许远未有我们一般意义上所理解的那样低级无趣。当然,河西走廊民间信仰承担着教化民众这一特殊而重要的功能。这一点我们从随处可见的劝人行善莫行恶的标语以及殿堂、庙宇贯彻落实党和国家宗教政策的行动与事例当中就能深切地感受到。
结 语
民间信仰的对象具有较强的稳定性与历史承继性,集中反映了当地民众的精神世界与社会生活方式,是这一地区人们认识事物的一种独特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们朴素的世界观与情感世界。河西走廊民间信仰祀奉的神礻氏既有远古以来的自然崇拜、神话人物崇拜,又有传统体制化宗教如佛菩萨、天尊仙真以及佛道二教在融合过程中形成的神礻氏崇拜。自然崇拜与当地的地理环境、气候条件、民间传说有关,如对于龙王、水神禹王的信仰与崇拜。神话人物崇拜与历史上民族融合、秦汉以来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以及相对稳定的社会政治环境有关,如对西王母、伏羲与女娲的信仰与崇拜。有学者在论及神话与民间信仰的关系时指出,神话产生于民间信仰,并借助于民间信仰得以传承,民间信仰是神话传承的载体。①向柏松:《神话与民间信仰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3页。显然,河西走廊民间信仰的祀奉神礻氏无疑也是神话人物在当地崇拜的重要载体。体制化宗教神礻氏的信仰与崇拜同佛法东渐、道教西传有关。而佛道二教在交融过程中形成的神礻氏崇拜则与走廊地带特殊的地形地貌以及佛道二教在走廊地带的际遇、三教合一的时代特征有关。
河西走廊民间信仰虽然具有包容性与杂糅性、实用性与非功利性、地域性与随意性的特点,但是在随意、杂乱的背后,仍有其条理化的内涵。历史上,河西走廊的北向、西向、南向三面都曾经属于游牧文化区,只有东向靠近农耕文化区,是各种文化交流与交融的重要通道,深受各种文化的影响,但是从民间信仰的神礻氏类型来看,虽然表现出走廊地带特有的多元性与包容性的文化风格,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多民族各种信仰文化与崇拜体系的交流与融摄,但从根本上来说,还是表现出与中原主流民间信仰传统极其一致的景象。民间信仰不仅仅是一种历史“遗存”,还是一种具有生命力的“活态”文化,②金泽:《当代中国民间信仰的形态建构》,《民俗研究》2018年第4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民众最朴素、最真实的情感世界与精神生活方式。③陈勤建:《当代民间信仰与民众生活》,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3年,第318页。因而,考察河西走廊民间信仰的神礻氏类型与特点不仅仅对于了解、阐释当地民众文化心理的影响因素具有积极的意义,还有助于推动民间信仰与当地社会的良性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