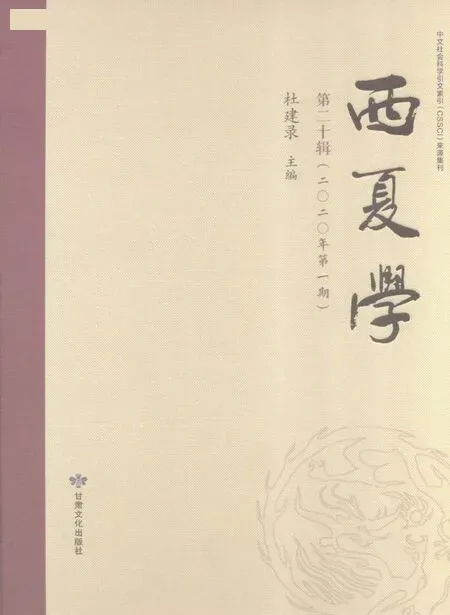瓜州榆林窟第19窟甬道西夏“大礼平定四年”题记考辨
公维章
瓜州榆林窟第19窟主室甬道北璧东起第二身女供养人像上部有一条汉文游人题记,墨书三行:
大礼平定四年四月初八日,清信重佛弟子四人
巡礼诸贤圣,迎僧康惠光、白惠登。
男弟子刘添敬、刘克敬。①张伯元:《安西榆林窟》,四川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219页。
陆离最先对该题记做过专题研究,认为该题记为大理国僧俗四人巡礼榆林窟时所留,时间为大理国安定四年(1198年)②陆离:《安西榆林窟第19窟大礼平定四年题记考》,《敦煌研究》2011年第1期。。近日陈玮亦撰文考察,认为题记中的大理国僧俗四人利用了僧人身份,由本国北上南宋西蜀,顺利穿过了金朝统治区秦州,再向西行,经过临洮、兰州等地,最后抵达河西走廊来到瓜州。时间亦为大理国安定四年③陈玮:《瓜州榆林窟题记所见大理国与西夏关系研究》,《丝绸之路研究集刊》第二辑,商务印书馆,2018年。。历史上的敦煌石窟,为当地的佛教圣地,既有大量佛教寺院,活跃着弘法的高僧大德,也吸引着大量的佛教信众来此礼佛,留下了大量的巡礼题记。这些题记,绝大多数是敦煌及其周边地区的佛教信众所题,也有少量是外地信众所题。从现存题记的内容分析,还是比较容易区分是当地信众还是外地信众所题,因为题记本身大多都表明信众的所属区域。笔者不同意陆离与陈玮的看法,认为此题记为瓜州当地信众所题写,特作考辨如下。
一、题记中的“大礼”为“大理”同名异写的可能性不大
陆离与陈玮皆认为,该题记为一则僧俗弟子四人巡礼佛教圣迹,迎请佛祖菩萨的记录,笔者认为,陆离与陈玮的解读有误。从该汉文题记可知,是“男弟子刘添敬、刘克敬”等“清信重佛弟子四人”到榆林窟巡礼“诸贤圣”,迎请高僧“康惠光、白惠登”。“康惠光、白惠登”并非“清信重佛弟子四人”中之二人,其身份是“僧”,而“清信重佛弟子”则是信佛的俗家弟子,唐宋时期的敦煌石窟俗人供养人题记大多题写“清信弟子”,僧人供养人则题“比丘沙门”,如莫高窟第196窟僧俗供养人题记①敦煌研究院编:《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文物出版社,1986年,第87—89页。,因此,“康惠光、白惠登”或是榆林窟某寺院的常住高僧,或是挂单在榆林窟某寺院的高僧。之所以只题“男弟子刘添敬、刘克敬”,或许其他二清信弟子并未随其巡礼佛窟,并且很可能其他二清信弟子为女弟子。陈玮对此则题记标点为“大礼平定四年四月八日,清信重佛弟子四人巡礼诸贤圣迎,僧康惠光、白惠登、男弟子刘添敬、刘克敬”②陈玮:《瓜州榆林窟题记所见大理国与西夏关系研究》,《丝绸之路研究集刊》第二辑,商务印书馆,2018年,第128页。。此标点表明作为僧人身份的“康惠光、白惠登”与“男弟子刘添敬、刘克敬”的身份是不一样的,怎能合称“清信重佛弟子四人”?另外,从汉语语法角度讲,“清信重佛弟子四人巡礼诸贤圣迎”有两个谓语,于语法不合。陈玮在其后文的行文中一直称“巡礼诸贤圣”,并未再称“巡礼诸贤圣迎”。因此,陈玮对此题记的标点有误。另外,陈玮认为“大理国僧俗四人在题记中自称清信重佛弟子,佛弟子在大理国写经中经常出现”③陈玮:《瓜州榆林窟题记所见大理国与西夏关系研究》,《丝绸之路研究集刊》第二辑,商务印书馆,2018年,第131页。,但所举例证中二则称“佛弟子”的身份是僧人,一则“奉佛弟子”的身份是俗人,一则“清信弟子”的身份亦为俗人,因此,佛弟子的身份有两种,一种是称“佛弟子”的僧人,一种是称“重(奉)佛弟子”的俗人,二者的身份区分是严格明显的。
关于“大礼平定四年”,陆离认为“应当与唐代西南边陲的南诏王国及其后继政权大理国有关。……‘平定’有可能为‘安定’之误”。在作此判断后,陆离认为“在大理国时期,瓜沙地区先为归义军政权领地,公元1036年西夏占领瓜、沙、肃州,此后该地区一直归属西夏管辖。所以此僧俗四人可能是先由本国北上进入蜀地,然后穿越蜀地到达秦州,再向西行,经过临洮、兰州等地,进入河西走廊,最后到达瓜州”。也有可能“是从大理国向西进入吐蕃境内,穿越青藏高原,然后再进入西夏管辖的瓜沙地区。”①陆离:《安西榆林窟第19窟大礼平定四年题记考》,《敦煌研究》2011年第1期。笔者认为,陆离所说的将榆林窟第19窟题记中的“大理”误写成“大礼”的可能性不大。因为唐代南诏称“大礼国”的时间为大中十三年(859年),而榆林窟第19窟开始修建于五代后唐时期(924—937年),北宋初年建成,其废弃的时间当在西夏占领瓜州的1036年之后,所以游人题记“大礼平定四年”当在1036年之后。大理国存在的时间为937—1254年间,陆离文中引宋人范成大笔记“《唐书》称大礼国,其国止用理字”,明确说明大理国“止用理字”,不会将“大理”误写成“大礼”。另外,云南大理国时期的石窟与经幢及佛教文献中,有不少带“大理国”字样的题记,但未见有题“大礼”者②刘长久:《南诏和大理国宗教艺术》,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年。。“大礼平定四年”为“大理安定四年”或某一未知的年号的可能性也不大,因为大理国使用汉字,1036年之后的大理国年号尽管有些不知始年或止年,但还是清楚有序的,其年号中未见有“平定”年号,而“安定”年号止于1200年,但不知始于何年③陆峻岭、林幹:《中国历代各族纪年表》,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523页。,陆离与陈玮皆将大理国安定四年定为1198年,是基于安定元年为1195年,而此年为段智兴元亨十一年,而元亨不知止年④陆峻岭、林幹:《中国历代各族纪年表》,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517页。,所以大理国“安定”年号是否行用至四年也未为可知。另外,“平定”有可能为“安定”之误的可能性亦不大,作为汉人的刘添敬、刘克敬应习汉字书写,“平”与“安”从字形、音韵皆不同,致误的可能性不大。
西夏自1036年占领瓜、沙前后,确实有四川佛教信众进入瓜、沙礼佛的记载。如莫高窟第464窟有二则“大宋”题记,具体位于该窟主室北壁西段西夏重修墙上刻有“大宋阆州阆中县锦屏见在西凉府□(贺)家寺住坐游□(礼)道沙州山□(寺)宋师父杨师父等”;南壁西段西夏重修墙上墨书“大宋□□府路合州赤水县长安乡杨□□(到)□(此)□(寺)居住□沙州……”⑤敦煌研究院编:《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文物出版社,1986年,第174—175页。据谢继胜研究,这些题记的年代都是在北宋年间,很可能是西夏据有敦煌不久,大约是1036年至1072年,至迟在北宋末年⑥谢继胜:《莫高窟第465窟壁画绘于西夏考》,《中国藏学》,2003年第2期,第71—72页。。另外,莫高窟第444窟后室龛内南后柱上,有一则墨书汉文题记:“环庆□德寨归义人范润、裴阿朵巡礼此寺,上报四恩,有三法界众生,同成佛道。辛己(巳)七月十三日范润记。”据刘玉权考证,“环庆”为环庆路的简称,“□德寨”为北宋环州通远县下辖八寨中的“洪德寨”,“辛巳”为北宋庆历元年(1041年)⑦刘玉权:《西夏时期的瓜、沙二州》,《敦煌学辑刊》第二辑,1981年。。罗华庆认为,“辛巳”并非北宋庆历元年,其从北宋“环庆路”的设置时间,考证此“辛巳”当为北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⑧罗华庆:《莫高窟第444窟龛南后柱题记考辨》,《敦煌研究》1985年第3期,第109页。。此窟题记为降夏的北宋佛教信众所留,并非北宋臣民入西夏,巡礼莫高窟后所留。
假如如陆离与陈玮所言,榆林窟第19窟题记“大礼”为“大理”之误写,则该题记表明大理国民众“男弟子刘添敬、刘克敬”等“清信重佛弟子四人”到榆林窟礼佛迎僧。大理国与西夏中间有宋、金阻隔,刘添敬等四人的身份则为使节或商人,未见史料显示大理国与西夏有外交关系,则刘添敬等四人的身份为商人。大理离瓜州的距离近2000公里,路途遥远,充满艰难险阻,不难推测,刘添敬等四人为青壮年,其到榆林窟礼佛的道路,如陆离所言,是从大理国进入四川,经陇南、兰州等地,入河西,到瓜州,或从大理国向西进入吐蕃,穿越青藏高原,沿青海祁连山南麓西行,到瓜州。笔者认为,从1036年西夏占领瓜州直至大理国灭亡的1254年,作为大理国青壮年身份的刘添敬等四人,且并非僧人身份,能够进四川,然后入陇南,到兰州,再入河西,到瓜州的可能性极小。首先,“大理国时期与内地通商,在大理国前期即约北宋时期,主要通过西川道,即自阳苴咩城出发,经姚府、会川府、建昌府,而至宋朝的黎州边境,由此进入蜀地,然后北上进入秦地(今陕西地区),再东行向北宋国都汴梁行进;大理国后期即约南宋时期,主要是通过邕州道,即自阳苴咩城出发,经善阐府,或往石城(近曲靖)折向东南,经自杞(约今贵州兴义、贞丰一带),入邕州(治所在今广西南宁附近)边境,或往特磨道(约今广南、富宁一带)而入邕州边境,这是向南宋国都临安进发的捷径”①陆离:《安西榆林窟第19窟大礼平定四年题记考》,《敦煌研究》,2011年第1期,第55页。。其次,大理国与北宋、南宋保持着朝贡关系,大理国的商队经由以上路线进入赵宋境内经商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但大理国的商队应该会受到宋朝官员的监视和管辖。据《宋会要辑稿·蕃夷四·大理国》记载,北宋徽宗政和六年(1116年)二月十五日,广州观察使、管勾押伴大理国进奉人使黄璘奏:“先奉圣旨,令于宾州(现广西宾阳一带)设局,接纳大理入贡,差官吏引伴。”②郭声波点校:《宋会要辑稿·蕃夷道释》,四川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03—204页。除了朝贡和经商,大理国的臣民进入宋境应该不会是任意、随便的。如上所述,北宋时期,四川信众可能经由秦凤路进入西夏;南宋时期,四川民众进入河西的可能性不大。笔者认为,即使是在北宋时期的1036年西夏占领瓜州直至北宋灭亡的1127年,大理国民众经四川入河西的可能性也不大,在此期间,西夏与北宋、吐蕃的战事不断,北宋、金朝与青唐、甘南、陇南的吐蕃诸部也时有战争。频繁的战争会阻断交通,更何况是大理国民众要通过西夏的敌国进入夏境。
西夏对边境管理甚严,严禁边境诸国之人进入夏境。西夏法典《天盛改旧新订律令》中有多条法律条文涉及此事。如《天盛改旧新订律令》卷一《背叛门》:“诸人往来敌界,提供密事,及为敌人侦察、隐藏等者,其人计划投降他国,则与叛逃同样承罪,家门连坐,畜物没收,当依叛逃已行法办。所捕获侦察者,皆以剑斩之。”《天盛改旧新订律令》卷四《边地巡检门》:“任大小检人者,当依数派遣确刚健人,当分队按期前往地段明显处住,若不住地段明显处,并且退避转移他处住时,失察,在所管地上敌兵步骑、盗贼入寇,多少军兵穿过,畜、人、物未归入手者,因大意,庶人依所定判断。其中有应降职、军者,当先降落职、军,所剩劳役当与官品当。放过一至十人,主管徒三个月,检人十三杖。”《天盛改旧新订律令》卷四《边地巡检门》:“检主管、检人等本人不往,放逸失于监察,使敌军、盗寇、避逃者穿过,有住滞者,依未往,本人有何住滞判断。住滞未出,则检主管徒六个月,检人徒三个月。”《天盛改旧新订律令》卷四《边地巡检门》:“大小检人在地段上住,巡检日毕,未待交接先往,新遣检人未按日来到,所管属地敌人进攻者穿越,避逃者通过,有住滞者,新检人当依有何住滞承罪,旧检人当比新检人减一等。”《天盛改旧新订律令》卷四《边地巡检门》:“与沿边异国除为差派外,西番、回鹘、鞑靼、女直相和倚持,我方大小检引导过防线迁家、养水草、射野兽来时,当回拒,勿通过防线,刺史、司人亦当检察。若不回拒,有住滞时,守更口者中检主管徒六个月,检人徒三个月。”①史金波、聂鸿音、白滨译注:《天盛改旧新定律令》,法律出版社,2000年,第116—117、199、202、203、211页。如此严苛之法律,实在是出于国家安全考虑,以免异国商人越过边防重地,探知军事布防,泄露军事机密。北宋统治者亦对西夏防备甚严,严格限制进贡的使团和商人经由北宋境内进入西夏,以防止泄露军事秘密,如《宋会要辑稿·蕃夷四·回鹘》载:“徽宗宣和三年(1121)十月八日,臣寮言:回鹘因入贡,往往散行陕西诸路,公然货易,久留不归者有之。恐习知沿边事宜,及往来经由夏国,传播不便。乞除入贡经由去处,其余州军严立法禁。从之。”②郭声波点校:《宋会要辑稿·蕃夷道释》,四川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27页。既然有这样严格的法律规定,作为大理国佛教信众身份的“男弟子刘添敬、刘克敬”等四人经由南宋的四川,然后入金朝统治区陇南,到兰州,再入河西,到瓜州的可能性不大。
陈玮文称大理国僧俗四人利用僧人身份顺利入瓜州,史实是,刘克敬等四人为俗人,到榆林窟迎请高僧,题记为刘添敬或刘克敬所写,则按陆离、陈玮所言此四人为大理国人,怎能自由穿越三国(南宋、金、西夏)进入瓜州?据《天盛改旧新定律令》载:“他国僧人及俗人等投奔来,百日期间当纳监军司,本司人当明晓其实姓名、年龄及其中僧人所晓佛法、法名、师主为谁,依次来状于管事处,应注册当注册,应予牒当予牒。若百日期间不报纳,匿卖派分为私人时,依偷盗钱价法判断。其中匿而使力受贿则徒四年。投奔者本人亦情愿自匿,则一年期间罪勿治,逾年他人报则徒二年,自报当赦罪,匿者依法判断。”③史金波、聂鸿音、白滨译注:《天盛改旧新定律令》,法律出版社,2000年,第408—409页。河西为西夏的重要统治区域,“他国僧人及俗人”进入河西后,首先要由进入地的监军司负责为其注册,上报朝廷。其在西夏境内的活动亦应受到某种程度的限制,其自由穿行的可能性不大。
陈玮认为,僧人康惠光的族属是大理国的粟特人,但所举大理国粟特人的例证犯了严重“泛粟特化”的错误,没有一例能确切证明大理国活跃着大量粟特商人。据陈玮考察,大理国时期云南与吐蕃之间的文化、经济交流甚少,榆林窟题记中的大理国僧俗四人应不是从大理国绕道吐蕃前往西夏,而是由本国北上南宋西蜀,经秦州路穿越金朝统治区经兰州来到西夏,时间是大理国安定四年,即1198年。但史实并非如此。据《金史》卷一三四《西夏传》:
(大定)十二年(1172),上谓宰臣曰:“夏国以珠玉易我丝帛,是以无用易我有用也。”乃减罢保安、兰州榷场。
仁孝深念世宗恩厚,十七年,献本国所造百头帐,上曰:“夏国贡献自有方物,可却之。”仁孝再以表上曰:“所进帐本非珍异,使人亦已到边,若不蒙包纳,则下国深诚无所展效,四方邻国以为夏国不预大朝眷爱之数,将何所安。”乃许与正旦使同来。
先是,尚书奏:“夏国与陕西边民私相越境,盗窃财畜,奸人托名榷场贸易,得以往来,恐为边患。使人入境与富商相易,亦可禁止。”于是,复罢绥德榷场,止存东胜、环州而已。仁孝表请复置兰州、保安、绥德榷场如旧,并乞使人入界相易用物。诏曰:“保安、兰州地无丝枲,惟绥德建关市以通货财。使副往来,听留都亭贸易。”章宗即位,诏曰:“夏使馆内贸易且已。”明昌二年(1191),复旧。
顷之,夏人肆牧于镇戎之境,逻卒逐之,夏人执逻卒而去。边将阿鲁带率兵诘之,夏厢官吴明契、信陵都、卜祥、徐余立等伏兵三千于涧中,阿鲁带口中流矢而死,取其弓甲而去。诏索杀阿鲁带者,夏人处以徒刑,诏索之不已,夏人乃杀明契等。
明昌四年,仁孝薨,子纯佑嗣立。承安二年(1197),复置兰州、保安榷场。①[元]脱脱等撰:《金史》卷一三四《西夏传》,中华书局,1975年,第2870—2871页。
可见西夏仁孝时期,金世宗、章宗对边地兰州的控制极严,金世宗大定十二年(1172年)停罢兰州榷场,为减少边患,严禁西夏使节入境与富商榷场贸易,直至金章宗承安二年(1197年)才恢复兰州榷场,长达25年时间。在25年中,金严禁兰州榷场贸易,并严禁使节及商人入境,远在大理国的刘添敬等僧俗四人怎会于1197年及时确知解禁兰州榷场贸易的消息?
综上所述,榆林窟第19窟的汉文题记并非大理国佛教信众所留。
二、“大礼平定四年”应为西夏纪年“天仪治平四年”
“大礼平定四年”为何代年号?查诸中国历史年表,没有“大礼平定”年号。榆林窟第19窟开凿于五代曹氏归义军曹延禄时期,为曹延禄的功德窟,所以此“大礼平定四年”应在归义军政权垮台的1036年以后。1036年以后,西夏元明清相继统治敦煌,而元明清有正史存在,年号准确,所以我们能否从西夏纪年中找到线索。西夏惠宗秉常最后一个年号为“天安礼定”,只有一年,即1086年,该年七月继位后的崇宗乾顺改年号为“天仪治平”,并且此题记中的“白惠登”应为回鹘僧,其身份应很尊贵,所以“重佛弟子”需来榆林窟迎请,这种情况发生在西夏统治时期的可能性极大。西夏人书写自己或中原王朝的年号时一般采用意译①聂鸿音:《西夏文〈过去庄严劫千佛名经〉发愿文中的两个年号》,《固原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5期,第12页。,在西夏天授礼法延祚元年至民安元年的53年时间里,“西夏王朝一共使用过十一个年号,但这些年号都是通过汉文史籍保存下来的,我们确切知道其西夏文写法的只有一个‘大安’,不知道其西夏文写法的年号有十个,即‘天授礼法延祚’……‘奲都’‘拱化’‘乾道’‘天赐礼盛国庆’‘天安礼定’‘天仪治平’”②聂鸿音:《西夏文〈过去庄严劫千佛名经〉发愿文中的两个年号》,《固原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5期,第12页。。因此,笔者认为,榆林窟第19窟的“大礼平定”为西夏纪年“天仪治平”,由于留下此题记的西夏敦煌汉人西夏文水平不高,将西夏文“天仪治平”理解为“天礼平定”,书写题记时漏掉“天”字的上边一横,写成了“大”,“大(天)礼平定四年”为公元1089年。西夏时期西夏文与汉文的对译较为复杂,据陈炳应研究,在西夏文献中,同一个西夏字,有时用义译,有时用音译;同一个汉字,使用不同的西夏字对译;同一个词,在不同文献中用字不同;同一个句子中,音义杂用等情况是较为多见的,是可以行得通的。例如,榆林窟几处题记中的西夏文“通判”二字,就与 《掌中珠》所用的字完全不同,题记用音译,《掌中珠》则用义译。何况,莫高窟297 窟题记第四行最后二字 “福果”的 “福”字,也不用义译,而用音译,与 “福圣”的 “福”字用同一个西夏字,“果”字却用的是义译。“福果”与 “福圣”的译法完全相同——一字音译,一字义译③陈炳应:《西夏文物研究》,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4—15页。。这种情况在莫高窟、榆林窟西夏文题记的夏汉对译中极为普遍,如莫高窟第444窟前室窟檐北柱上墨书西夏文两行,“第一行第一字意为‘长’,第二字意为‘安’,应是西夏崇宗‘永安’年号”;莫高窟第285窟北壁西部第一禅洞内有西夏文题记十行,“第一行第一字意为‘和睦’,第二字意为‘安康’,合为‘雍宁’年号”④王静如:《新见西夏文石刻和敦煌安西洞窟夏汉文题记考释》,原载《王国维学术研究论集》第一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现据王静如:《王静如文集》(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768页。。后文提到的北京国家图书馆收藏的西夏文印本《过去庄严劫千佛名经》的末尾西夏文发愿文中的“戊寅年中,国师白法信及后禀德岁臣智光等”的“禀德岁”为西夏毅宗谅祚“(福圣)承道年”,即为“禀承道德”之组合。
另从西夏时期敦煌石窟中的汉文游人题记书写规律来看,“大礼平定”亦应为西夏年号。莫高窟第444窟题“天赐礼盛国庆”年号,而榆林窟第15、16窟瓜州阿育王寺高僧惠聪则简题“国庆”年号;莫高窟第85窟题“大上仁庆”年号,实为西夏仁宗“人庆”年号。另从西夏元明清时期敦煌石窟中的游人题记书写规律来看,凡是敦煌地区之外的信众来此礼佛,皆书写其来源地域,如莫高窟第444窟窟门北柱西夏汉文墨书题记中有“北五台山大清凉寺僧沙□□(佛)光寺□(院)主……”,榆林窟第19窟西夏“乾祐廿四年口口日画师甘州住户高崇德”,因此,榆林窟甬道题记中的刘添敬、刘克敬应为瓜州本地人。
因此,榆林窟第19窟的“大礼平定四年”应为西夏纪年“天仪治平四年”,即1089年。
三、从西夏回鹘僧人的重要地位看题记中的 “白惠登”应为回鹘僧
回鹘是中国中古时期西北地区一支重要的少数民族力量,到归义军统治河西时期,回鹘在河西的势力日趋强大,并已普遍信奉佛教,将大量的梵、藏、汉文佛经译为回鹘文。早在德明时西夏统治者就已信奉佛教,并于1030年正式向宋求赐佛经一藏,至西夏天赐礼盛国庆四年(1073年),西夏共向宋请赐得六部大藏经。在求得大藏经的同时,西夏统治者组织力量着手翻译,由汉文译为西夏文。从1038年至1090年,西夏共译出经典八百十二部,三千五百七十九卷。在西夏大规模、长时间的译经事业中,回鹘僧人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回鹘人在从汉文经典译为回鹘语的长期实践中,积累了大量的成熟经验,西夏统治者看中的就是这一点。西夏统治者大力提倡佛教时,主要吸收中原佛教,译经时又得到回鹘僧人的帮助和支持,因此西夏早期佛教的发展受回鹘佛教影响很大。李元昊建立大夏国后,即延请回鹘僧人来西夏翻译佛经。西夏天授礼法延祚十年(1047年)二月,元昊于首都兴庆府“东一十五里役民夫建高台寺及诸浮图,俱高数十丈,贮中国所赐《大藏经》,广延回鹘僧居之,演绎经文,易为蕃字”①[清]吴广成撰,龚世俊等校证:《西夏书事校证》,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第212页。。元昊死后,西夏佛教在谅祚帝(1048—1067年在位)生母没藏氏的支持下继续发展。没藏氏亦重用回鹘僧,西夏福圣承道三年(1055年)十月,没藏氏于兴庆府建承天寺,贮宋赐《大藏经》,“延回鹘僧登座演经,没藏氏与谅祚时临听焉”②[清]吴广成撰,龚世俊等校证:《西夏书事校证》,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第236页。。
西夏元昊、谅祚父子统治时期,极为重视佛教的弘传,专门在首都建佛寺、佛塔,贮藏从北宋迎请来的大藏经——《开宝藏》,并组织回鹘高僧于寺内展开从汉文翻译成西夏文的译经活动。从西夏统治者皇太后偕皇帝常临寺听回鹘僧人“演经”一事看,当时的回鹘高僧在西夏佛教界的地位是非常高的,北京国家图书馆收藏的西夏文印本《过去庄严劫千佛名经》的末尾西夏文发愿文,对佛教在西夏的流布以及回鹘高僧翻译佛经的情况作了记述:
夏国风帝新起兴礼式德。戊寅年中,国师白法信及后禀德岁臣智光等,先后三十二人为头,令依蕃译。民安元年,五十三岁,国中先后大小三乘半满教及传中不有者,作成三百六十二帙,八百十二部,三千五百七十九卷。③史金波:《西夏佛教史略》,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66页。
据史金波研究,以上发愿文中的“风帝”指西夏王元昊,“戊寅年”是西夏天授礼法延祚元年(1038年),“五十三岁”是指从西夏天授礼法延祚元年至民安元年(1090年)。此发愿文表明,“在西夏前期从元昊时起至崇宗时止,用了五十三年的时间,译成了三千五百七十九卷西夏文佛经,共八百十二部,分装于三百六十二帙中,基本上是十卷一帙。举世闻名的汉文《大藏经》,先后经历了许多朝代,花费了近一千年的时间,共译出六千多卷,成为佛教史上的盛事。西夏仅用了半个世纪多一点的时间,就译出了三千余卷佛经,平均每年译出六七十卷。这在我国译经史上乃至世界翻译史上都是一个惊人的创举。不难想见,以这样的速度,完成如此大量的翻译工作,若没有西夏政府的极力倡导和热心扶助是无法实现的”①史金波:《西夏佛教史略》,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67—68页。。从此发愿文可以看出,从一开始,西夏译经的组织就十分成熟,这无疑得益于回鹘僧人的译经经验。
而将汉文佛经译为西夏文佛经的,是以西夏国师白法信以及后来的智光等三十二人为首的一批高僧,“智光”应是北京国家图书馆所藏西夏文《金光明最胜王经》卷首流传序中的西夏国师“白智光”,该序比较准确地记录了西夏皇帝惠宗秉常时期(1067—1086年)译经的情况:
后始奉白高大夏国盛明皇帝、母梁氏皇太后敕,渡解三藏安全国师沙门白智光,译汉为蕃。文华明,天上星星闪闪;义妙澄,海中宝光耀耀。②史金波:《西夏文〈金光明最胜王经〉序跋考》,《世界宗教研究》1983年第3期。
以上所举西夏文《过去庄严劫千佛名经》中的“禀德岁臣智光”,据聂鸿音研究,“禀德岁”应是西夏毅宗谅祚“(福圣)承道年”(1053—1056年)③聂鸿音:《西夏文〈过去庄严劫千佛名经〉发愿文中的两个年号》,《固原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5期,第12页。。
在西夏福圣承道年间,智光的身份还是“臣”,到惠宗秉常时期已升为“国师”,是西夏著名的译经僧。另外,在北京国家图书馆收藏的一件西夏文印本《现在贤劫千佛名经》卷首所附的西夏译经图中,我们可以看到西夏国师白智光在西夏早期译经中的重要地位和影响。主译人白智光以国师之尊在图中占据了中心、主导的地位。他形象高大,制约全局,皇帝、皇太后在图中只占据了左右两角的地位,这种特殊的格局,反映了白智光等人的译经活动得到了西夏皇室的支持和尊重④史金波:《西夏佛教史略》,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76—78页。。
由上可知,西夏国师白法信和国师白智光是西夏前期译经事业中两位杰出的代表,在西夏佛经翻译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据杨富学研究,白法信、白智光的民族成分是龟兹回鹘高僧⑤杨富学:《回鹘僧与〈西夏文大藏经〉的翻译》,《敦煌吐鲁番研究》第七卷,中华书局,2004年,第5期,第12页。。显示了回鹘佛僧在西夏佛教初兴时期的重要地位。
晚唐五代宋初敦煌的高僧多以法名自称,也有不少法名前冠以俗姓,西夏占领敦煌后,僧人继承了这一传统,亦为自称法名,或法名前冠以俗姓①敦煌研究院编:《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文物出版社,1986年。。榆林窟第19窟题记中的“白惠登”的民族属性为回鹘僧,殆无可疑,“康惠光”亦为法名前冠俗姓,“康”姓为中古时期敦煌粟特人的著姓,从其法名与回鹘僧“白惠登”皆为“惠”字来看,“康惠光”与“白惠登”出自同一寺院且为同门师兄弟的可能性极大。作为“清信重佛弟子”的“刘添敬”“刘克敬”于四月初八佛诞节前往榆林窟“巡礼诸贤圣”,并专门迎请僧康惠光、白惠登,可以推测康惠光为回鹘化高僧。二僧于四月初八佛诞节在榆林窟主持法会,刘添敬等四人为某佛社成员,接受其佛社的委派前往榆林窟迎请此二位回鹘高僧,指导其佛社的佛事活动,回鹘僧为西夏敦煌佛教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西夏统治者尊崇回鹘高僧,不仅促进了西夏佛教的发展,也推动了回鹘佛教的发展。西夏在建国初年就优礼回鹘僧,沙州回鹘在羁縻期内,佛事活动极为活跃,在敦煌开凿、重修了不少洞窟。在西夏重回鹘僧的大背景及不少回鹘部落散居敦煌的情况看,回鹘僧人应该在敦煌的佛教舞台上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故题记中的“康惠光”“白惠登”均应为回鹘背景的高僧。
综上所述,瓜州榆林窟第19窟主室甬道北璧汉文题记“大礼平定四年”为西夏崇宗乾顺“天仪治平四年”,在该年的四月初八佛诞节,由汉族信众刘添敬、刘克敬等四人受其所在佛社指派,前往榆林窟迎请回鹘高僧白惠登及回鹘化高僧康惠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