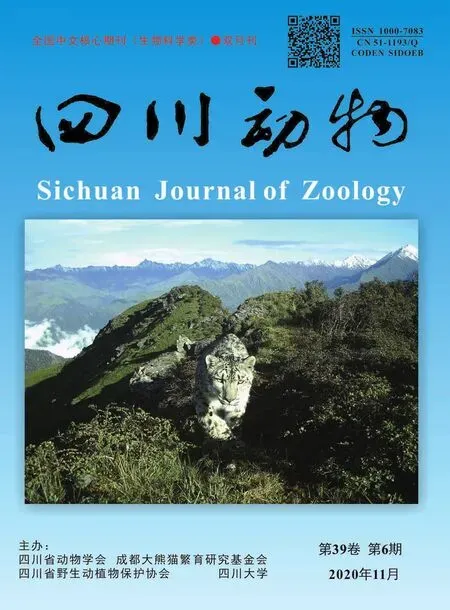雪豹生态与保护研究现状探讨
洪洋,张晋东,王玉君
(西华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四川南充637009)
雪豹Panthera uncia属我国Ⅰ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是评价生物多样性丧失的重要指示物种,具有重要的保护和科研价值。雪豹主要分布在12个境内有高山或高原的国家和地区,如中国、阿富汗、不丹、印度等(马鸣等,2013;唐卓等,2017)。
雪豹作为高海拔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维持生态系统的平衡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张荣等,2018)。然而,近几十年人类活动的不断扩张使雪豹的栖息地面积急剧下降,导致了严重的人豹冲突,部分地区牧民对雪豹的报复性捕杀愈演愈烈(Oli et al.,1994;Aryal et al.,2014a,2014b;刘浦江,韩海东,2015)。人类对雪豹的负面影响还表现在人类对雪豹食物的猎杀。相较于低海拔的肉食性动物,雪豹所能捕食的猎物种类较少,食物的丰富度很大程度上影响了雪豹的种群数量与空间分布(Oli,1993,1994;Casey,2018)。而过度的偷猎可能导致雪豹食物链的断裂,威胁其生存。除去人为干扰,雪豹的生存同样面临着气候变化带来的威胁(Aryal et al.,2016)。目前全球气温逐渐升高,雪豹被迫往更高海拔的区域转移,栖息地面积骤减,食物匮乏(Forrest et al.,2012;Pecl et al.,2017)。
基于上述原因,雪豹受到各国研究者的极大关注,并开展了一系列相关研究,以期能更好地保护雪豹。然而雪豹属猛兽,警觉性高,主要栖息在高海拔且地形崎岖的区域(Anwar et al.,2011),这给雪豹生态与保护的研究带来极大的困难,导致所获得的研究成果分散,缺乏系统性。本文对已有的雪豹生态与保护相关研究进行归纳与总结,试图了解雪豹生态与保护的研究现状,同时分析当前存在的问题,探讨今后雪豹的研究方向,以期能为今后开展雪豹系统性的研究提供参考。
1 雪豹生态与保护研究方法概述
选择正确的研究方法对研究工作的进行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目前雪豹的生态与保护研究方法大致可以整理为7种(表1)。

表1 雪豹生态与保护主要研究方法Table 1 The main research methods used in the ecology and conservation research on Panthera unica
雪豹栖息地选择与人为干扰的研究主要使用样线法获得雪豹与人类活动痕迹,以雪豹痕迹为中心建立10 m×10 m样方,调查样方内的各种生境因子(徐峰等,2006a),同时结合半结构访谈法(按照粗线条式的访谈提纲进行,访谈方式灵活多变的非正式访谈),获取当地居民对雪豹的态度,以及雪豹造成的伤害(Hussain,2000),以此达到了解雪豹如何进行栖息地选择,并在其中找到缓解人豹冲突方法的研究目的。雪豹个体识别方法可分为2类,一是通过红外相机照片,根据体表花纹特征进行识别(Jackson et al.,2006;马鸣等,2006),二是通过采集雪豹粪便、毛发等样品,利用相应的DNA分析技术进行识别(Karmacharya et al.,2011)。雪豹种群数量分布的研究在个体识别研究的基础上进行统计,再结合标志重捕分析方法(Janecka et al.,2008),即可获得栖息地内雪豹种群数量,整理之后便可明确全球范围内雪豹种群数量的分布情况。清楚了解雪豹的栖息地选择情况以及种群数量等信息后,使用遥感监测以及项圈跟踪(Mccarthy et al.,2005)、红外相机监测(唐卓等,2017)等方法,即可对雪豹的活动与空间利用模式进行研究。雪豹食源组成的研究可通过粪便残骸与粪便中的DNA进行鉴定(Anwar et al.,2011;陆琪等,2019),同时还可利用红外相机等设备,通过雪豹食物的生物量消耗来进行鉴定(Oli,1994)。通过样线法寻找雪豹粪便与毛发等样品,获得雪豹DNA后利用相应的微观技术(Karmacharya et al.,2011;周芸芸等,2014)可探究雪豹的遗传多样性。
当前雪豹生态与保护研究以野外样线调查数据为基础,在不同的研究目的下使用相应的实验方法,且有多种选择,但各种方法的使用相互重叠,设定的标准难以统一。为解决该问题,本文拟定了一条进行雪豹生态与保护系统研究的主要方法路径,希望能为今后雪豹生态与保护系统性研究(实验方法方面)提供参考(图1)。

图1 雪豹生态与保护系统研究方法路线Fig.1 Methodological road map of the ecology and conservation system research on Panthera unica
2 雪豹生态与保护研究成果概述
2.1 栖息地选择
对雪豹栖息地选择的研究表明,雪豹对栖息地植被类型的选择倾向于灌丛与高山草甸,避开森林、荒漠;对生境平坦度(徐峰等,2006a)的选择倾向于陡峭、崎岖的区域,而避开平坦、开阔的区域(徐峰等,2005,2006b;Li et al.,2013)。雪豹在海拔2 000~4 500 m均有分布,随季节的变化在不同海拔活动,当处于2 000~3 000 m时,多选择谷底;当处于3 000~4 500 m时,多选择山坡与山脊,且多利用阳坡而避开阴坡(廖炎发,1985;乔麦菊等,2017)。由此可见,当前雪豹栖息地选择的研究暂未考虑雪豹对自然生境中植被的利用情况,如灌木的基径、盖度,草本的高度、盖度等,明确雪豹对植被的利用情况,对于解释雪豹捕食时的隐蔽行为有重要作用。
随着人类活动范围的不断扩大,雪豹与人类在生态位上的重叠不断增加,二者冲突愈演愈烈(史晓昀等,2019)。面对人类活动的扩张,雪豹在一定程度上只能选择避让,因此,解决人兽冲突不仅要明确雪豹对栖息地的生境选择,还要明确人类对雪豹干扰的类型与强度。目前,栖息地中人类活动因子对雪豹影响的研究较少,仅涉及到人类报复性捕杀(Hussain,2000)、雪豹与家畜空间分布的重叠(史晓昀等,2019),而在分析与评估放牧、采药、修建道路等人为活动带来的影响,控制雪豹与人类的安全距离等方面的研究尚属空白。研究者试图通过相关保护政策来建立人类活动因子与自然生境因子之间的联系,如提出一系列的激励政策,减少人类负面干扰,改善栖息地自然生境条件,以缓解人与雪豹的冲突(Mishra et al.,2010;Li et al.,2013;Aryal et al.,2014a),以及通过雪豹的野外放归,以维持相对稳定的野外种群数量(Som&Kamal,2007;Jackson & Som,2009;Lovari et al.,2010)。
当前雪豹栖息地研究主要以保护雪豹栖息环境为目的,人为干扰方面主要以如何减少与隔断人为干扰为目的,两者以相关保护政策(如冲突分析、损失鉴定、保险赔付等)为手段建立相关联系,虽取得一定的保护成效,但并未触及到缓解人豹冲突的核心,即如何减少雪豹与人类在生态位上的重叠,因此,在今后的研究中应着重探寻如何将二者进行紧密联系,同时从雪豹生境选择与人类干扰这2个导致冲突的源头出发,减少人与雪豹生态位重叠、缓解人豹冲突。
2.2 个体识别
个体识别在野生动物保护的研究中对于估测种群数量和研究动物行为有着重要作用,因此,完善雪豹个体识别体系对于开展雪豹系统性研究显得尤为重要。学者们利用多种方法开展雪豹的个体识别研究,如Riordan(1998)利用雪豹的足迹,使用神经网络(SOM)和贝叶斯方法,成功对雪豹个体进行识别;Jackson等(2006)通过正面、侧面、倾斜面的相机配置,获得不同角度的雪豹照片,并根据雪豹前肢、身体两侧,以及尾巴背面的独特花纹成功对2003年和2004年在印度拉达克赫米斯国家公园出现的雪豹进行个体识别;马鸣等(2006)在国内首次使用红外相机技术,并结合“雪后痕迹调查”的信息成功进行雪豹个体识别。2010年后雪豹个体识别中的宏观手段逐渐减少,分子生物学手段逐渐增加,如Waits等(2010)从19只圈养雪豹中筛选出50个微卫星位点,测定每个位点的多态性,选出10个多态性最高的微卫星位点,以用于野生雪豹的个体识别;Karmacharya等(2011)利用相同的研究方法也成功对尼泊尔博克顺多国家公园和干成章嘉峰保护区的雪豹进行个体识别;Kyle等(2011)利用上述10个微卫星位点成功对吉尔吉斯共和国萨里查特-埃尔塔什地区和占哥特狩猎保护区的野生雪豹个体进行识别;周芸芸等(2014)在青藏高原的三江源自然保护区、羌塘自然保护区以及甘肃的党河南山地区,获得277份疑似雪豹粪便样品,成功扩增mtDNA cyt b基因片段190份,并确定89份来自雪豹,通过微卫星分析,确定来自48只不同的雪豹个体。
分子生物学方法的应用,如DNA条形码技术、微卫星技术,提高了个体识别的准确性,减少了误判,但如果仅使用分子生物学手段进行个体识别,也存在一些弊端,例如,雪豹的粪便样品收集较困难,且收集到的粪便样品有一部分较陈旧,而分子生物学方法无法鉴别陈旧的粪便样品。因此在今后的研究中应增加野外调查,丰富雪豹足迹、刨痕等野外痕迹样本,为利用痕迹进行个体识别提供更多参考。同时,雪豹各个角度照片的数据积累不足,如雪豹腹部的照片目前尚无记录,因此还应增加红外相机布设角度,获得更多角度的雪豹照片,利用人工智能(AI)、深度学习(赵婷婷等,2018;Hou et al.,2020)等技术,提高雪豹个体识别准确性。在保证一定准确性的条件下,解决使用分子生物学方法研究结果不全面的弊端,最后将宏观与分子生物学研究结果进行对比、印证,达到精准识别雪豹的目的。
2.3 种群数量分布
明确雪豹的种群数量分布对雪豹保护区域的规划有重要作用,但各国研究者仍未找到准确估计雪豹种群数量的方法。目前雪豹在中国主要的分布区域有新疆、青海、甘肃、四川、西藏等地,雪豹种群数量的研究集中在新疆与四川,马鸣等(2006)研究表明,在托木尔峰自然保护区边缘的木扎特谷地的250 km2范围内存有5~8只雪豹,其密度为2~3.2只/100 km2;徐峰等(2011)的研究结果显示,新疆托木尔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现存雪豹47.28~87.25只,其密度为1.99~3.47只/100 km2。雪豹在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的分布较广,彭基泰(2009)指出在青藏高原东南横断山脉甘孜地区的雪豹种群数量为400~500只,其中石渠、新龙、德格、甘孜、白玉、理塘等6县有51~78只。青海、甘肃、西藏等地的相关研究较少,Schaller等(1988)的研究表明生存于青海省与甘肃省西部边缘的雪豹种群数量达到650只。西藏境内雪豹种群数量则尚无相关报道。
巴基斯坦与尼泊尔为除中国外雪豹的主要分布区域,因此得到较多的关注,如 Hussain等(2003)估测巴尔蒂斯坦雪豹种群数量为90~120只,而整个巴基斯坦雪豹种群数量为300~420只。尼泊尔2个重要的雪豹分布区域——博克顺多国家公园和干成章嘉峰保护区的雪豹种群密度为4只/100 km2和5只/100 km2(Karmacharya et al.,2011)。除以上2国外,其余国家的报道则相对较少,如印度和蒙古国的雪豹种群数量目前仅少部分地区有文献报道,印度拉达克-赫米斯国家公园的雪豹种群数量为5只,蒙古国境内戈壁沙漠区域的雪豹种群数量为16~19只,种群密度为4.9~5.9只/100 km2。在吉尔吉斯共和国,萨里查特-埃尔塔什地区雪豹种群密度为8.7只/100 km2,占哥特狩猎保护区雪豹密度为1.0只/100 km2(Janecka et al.,2008,2011;Kyle et al.,2011)。
有关雪豹种群数量的研究在全球范围内,不同国家、地区发展不均衡。例如在我国,四川、新疆的研究较多、发展较快,西藏、青海等地研究较少、发展较慢。这种情况可能会导致不同的研究者对横跨多个国家或地区的雪豹种群进行重复计数,从而错误估计全球范围内的雪豹数量。因此,各国、各地区之间应考虑统一的研究方法,以减小各国、各地区之间研究进度的差距,提高雪豹数量估计值的准确性。
2.4 活动与空间利用模式
动物活动模式研究集中在动物的活动节律,以及影响动物活动因素的探讨(张晋东等,2015),空间利用模式是指动物对栖息地内环境资源的利用模式,影响着种群间的基因交流与生存发展(Roesnberg & Mckelvey,1999;王晓,张晋东,2019)。掌握雪豹活动与空间利用模式对于雪豹的野外保护工作的开展有重要作用。
目前关于雪豹活动与空间利用模式的研究集中在雪豹活动节律和家域范围的探索,活动节律的研究较多,且研究方法也较成熟,如唐卓等(2017)发现卧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雪豹年活动最高峰为1月,次高峰为8月,6月和7月活动最少。雪豹在夜间比白天更活跃,活动高峰为18:00—20:00,且日活动存在季节差异,夏秋季比冬春季更集中在夜间活动,与此同时,雪豹在夜间的活动受月相的影响,在月相更明亮的夜晚,雪豹的活动更频繁。Wolf和Ale(2009)研究表明,雪豹的活动模式受地形、人类活动、主要食物等栖息地条件的影响,不同地区雪豹的空间利用模式存在差异。而雪豹家域方面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仅能对雪豹的大概家域进行预测,如Mccarthy等(2005)通过标准遥测技术估测蒙古国西南部阿尔泰山雪豹的活动范围为13~141 km2,而通过项圈跟踪得出该区域雪豹活动范围为1 590~4 500 km2,上述结果差距较大,其原因在于遥测技术在估测雪豹家域范围的应用中成功率不高。研究表明,动物家域的计算受研究方法、计算模型等因素的影响(张晋东等,2013),而动物家域受季节变化、分布区域、种群数量、食性组成等因素的影响(张晋东,2012;Zhang et al.,2014),由此可见,雪豹家域的研究需考虑诸多因素,而目前雪豹家域研究的数据积累不足,难以进行区域间的对比,今后应同时在多区域开展雪豹家域研究,比较研究结果,排除影响因素带来的干扰,增强结果的准确性与可信度。除此之外,在雪豹的活动与空间利用中,野生雪豹的野外迁移、交配行为、繁殖生态、家庭关系、寿命与年龄结构等内容均未涉及,仅圈养雪豹的饲养与繁殖有少量研究(张得良,权守元,2018)。因此,今后雪豹活动与空间利用模式的研究在进一步完善雪豹活动节律与家域研究的同时,也应重视上述研究方向。
2.5 食源组成
雪豹作为唯一一种高海拔生存的大型猫科Felidae动物,其食物资源远少于其他低海拔物种,雪豹如何利用较少的资源保持其生存发展引起研究人员的关注,同时雪豹食性的研究对于其他动物在食物资源方面的利用也有一定启发作用,且研究雪豹食性对理解雪豹与同域动物间的相互作用有重大意义。目前研究发现,雪豹在不同地区食性组成不同且各地雪豹食物储量存在差异,我国雪豹的主要食物是岩羊Pseudois nayaur、旱獭Marmota spp.,包括喜马拉雅旱獭 Marmota himalayana、红旱獭Marmota caudata和灰旱獭Marmotabaibacina(Schaller et al.,1988;刘楚光等,2003;徐峰等,2007;陆琪等,2019)。巴基斯坦雪豹70%的食物来自家畜,即绵羊Ovis aries、山羊 Capra hircus、牛、牦牛Bos mutus、牛与牦牛的杂交种,30%来自野生动物(岩羊、捻角山羊Capra falconeri、鸟类)(Anwar et al.,2011)。尼泊尔雪豹的主要食物为喜马拉雅塔尔羊Hemitragus jemlahicus与岩羊,除此之外,喜马拉雅旱獭与罗伊尔鼠兔Odiotona royki也是雪豹重要的食物来源(Som,2012)。蒙古国的南戈壁地区,雪豹的主要食物为西伯利亚北山羊Capra sibirica、山羊和盘羊 Ovis ammon(Wasim et al.,2012)。Lyngdoh等(2014)分析了全球范围内雪豹猎物消耗的频率和消耗的生物量,从全球范围总结出雪豹的主要食物为西伯利亚北山羊、岩羊、喜马拉雅塔尔羊、盘羊和喜马拉雅旱獭。
当前研究大多只针对雪豹食源中的动物食源,而对植物食源研究较少,其原因在于当前研究手段的限制,红外相机监测、猎物生物量估测、DNA条形技术等方法均只能用于雪豹动物食源的研究,粪便残骸分析可对植物食源进行鉴别,但准确性有所欠缺。因此,在今后的研究应积极探索和使用新的研究方法,如稳定同位素法,此方法在其他动物食性的研究中取得显著成果,且动物食源与植物食源的研究均可使用(张璇等,2013;赵璐等,2017;Teresa et al.,2019),明确雪豹植物食源,完善雪豹食源组成,对未来雪豹救助与人工繁育等有重要作用。
2.6 遗传多样性
随着DNA提取与分析技术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研究者试图从分子生物学的角度对雪豹进行研究,了解雪豹的遗传多样性是研究雪豹生存适应和物种进化的前提。张于光等(2009)基于粪便DNA成功证明青海省都兰县的宗加乡、诺木红乡以及治多县索加乡的雪豹有着丰富的遗传多样性。周芸芸等(2014)在48只雪豹的mtDNA cyt b基因片段中检测出13个多态性位点,定义9个单倍型,其中单倍型多态性0.776,核苷酸多态性1.50%,9个单倍型的遗传距离为0.009~0.058,证明了分布在三江源保护区、羌塘保护区、甘肃党河南山地区的雪豹存在遗传多样性。
另有遗传多样性的研究也解释了一系列问题,于宁等(1996)通过构建雪豹限制性核酸内切酶图谱,并通过限制性酶谱比较金钱豹P.pardus与雪豹的mtDNA,发现两者的遗传距离为0.075 33,未到达属级分化,雪豹应当属于豹属Panthera,但因其形态、行为等特征不同于豹属其他动物,推测雪豹应为豹属中的一个有效亚属。Wei等(2009)利用设计的30个引物片段获得雪豹线粒体全基因组,长度为16 773 bp。Cho等(2013)成功报道了雪豹适应高海拔独有的遗传决定因素。
mtDNA cyt b基因片段的扩增和微卫星分析技术已经相对成熟(张于光等,2008;Karmacharya et al.,2011),Janecka等(2008)也成功设计了 1 组研究雪豹遗传多样性的线粒体DNA引物,因此,在今后的研究中应将雪豹遗传多样性的研究列为重点,探索目前尚未解决的一些问题,如雪豹的进化过程、全基因组测序等。
3 存在的问题与研究展望
关于雪豹生态与保护的研究,研究者已明确雪豹对地形、植被类型等多数自然生境因子的选择情况(Li et al.,2013;乔麦菊等,2017),个体识别的准确性也随研究方法的改进而提高,种群数量在少数国家与地区被成功估算,活动节律的研究方法也较为成熟,同时基本确定了雪豹动物食源的组成(Lyngdoh et al.,2014),遗传多样性的研究在技术上获得实践与发展,也取得了相应的研究成果(Karmacharya et al.,2011;周芸芸等,2014)。目前雪豹的生态与保护研究工作已积累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但为了今后更好地开展全面且深入的雪豹研究,建议加强以下3个方面的相关工作。
3.1 各国、各地区间需加强合作
雪豹在全球范围内主要分布于中国、巴基斯坦、尼泊尔、印度、蒙古国等国家(唐卓等,2017),在我国主要分布于四川、新疆、西藏、青海、甘肃等地(刘沿江等,2019),在地理位置上均具有连续性,但目前雪豹生态与保护的研究表现为研究者在各国、各地区分别开展研究工作,彼此之间联系不够紧密,各国、各地区均未建立持续或者定期的监测机制,方法与标准亦难以统一,导致今后很难在更大尺度上开展相应的研究工作,从而很难为更大尺度上的雪豹保护政策制定提供科学依据,因此,不同国家与不同地区之间的研究者应加强合作与交流,共同搭建研究平台,推动数据共享,以实现在更大尺度上开展雪豹生态与保护研究的目的。
3.2 人豹冲突下的保护政策研究需要加强
研究者对雪豹栖息地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栖息地的自然条件,如海拔、植被类型等,而对雪豹与人类的冲突关注较少,且不够深入,主要体现在目前雪豹的保护政策不完善,以及雪豹保护机构对牧民家畜损失的赔偿制度不完善等方面,如在我国四川邛崃山脉,存在较高的雪豹-家畜冲突风险,但目前尚未制定出有效的保护管理政策(史晓昀等,2019);在巴尔蒂斯坦,人豹冲突严重,但雪豹的保护管理政策不完善,牧民对雪豹进行报复性捕杀,使得近年来该区域的雪豹数量锐减(Hussain et al.,2003)。对此,相应的研究人员通过制定一系列的激励政策,如提高被捕家畜的赔偿额度、为家畜圈舍进行加固、加强雪豹保护的宣传工作等,试图减缓人豹冲突,同时也为后续的研究积累宝贵经验。与此同时,雪豹保护与研究目前还存在许多尚未涉及的盲点,如落后地区的贫困问题、当地居民保护意识不足、社区服务以及环保力量的扶持不足等,因此,深入了解各栖息地居民对雪豹的看法,寻找既能保护雪豹,又能保全当地居民经济利益的保护策略,从根源上解决雪豹与人类的冲突,对于未来雪豹保护工作至关重要。
3.3 应对气候变化的研究不足
目前关于气候变化对雪豹生存影响的研究较少(李小雨等,2019),对于雪豹如何应对今后气候变化的研究基本没有。近年来由于人类活动的影响,全球气候变化加剧(Forrest et al.,2012),雪豹所分布的高山生态系统植被单一,抵抗力稳定性较弱,对气候变化敏感,气候变化极有可能成为未来影响雪豹生存的重要因素,因此,研究气候变化对雪豹的影响以及探索相应的策略对于雪豹的保护工作有重大意义。
致谢:感谢佛罗里达大学生态与野生动植物系卞晓星博士,西华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侯金、罗欢在写作过程中给予的意见;西华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毛泽恩、蔡天贵在文献整理方面给予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