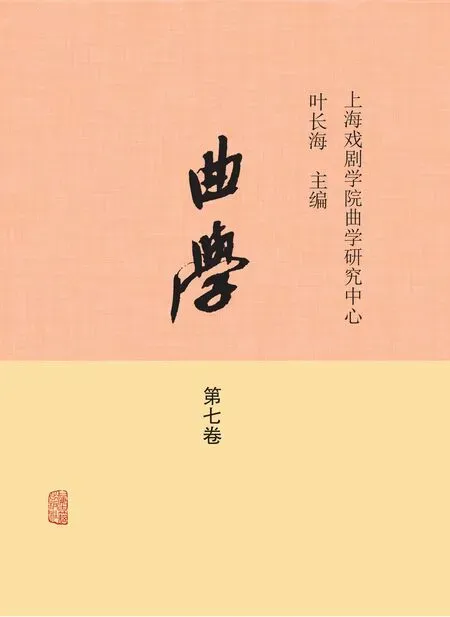纪念陈古虞教授诞辰100周年访谈录
马圣贵访谈
在校注《李玉戏曲集》的时候,陈古虞老师和陈多、上海古籍出版社的李国章,一起去北京查找资料。陈古虞老师威望高、资格老,所以就一起做这件事情。但我们交稿以后,出版社很久没有出。过了许多年,李国章又想起这事,我和陈多老师一人一半再校阅了一遍。书出版的时候,陈古虞老师已经去世了。
见过他的曲谱,但是我不懂,是《桃花扇》的曲谱,很精致,很整齐,自己搞的,非常精致,用工尺谱写的,一套,手写,很考究。这个东西恐怕没什么人会了,所以叫“绝学”。
他是教研室主任,我是副主任。上课他的特点就是一边讲历史,一边表演,能结合内容作形象化的示范教学,效果非常好。讲到《牡丹亭·春香闹学》,他会表演,所以一般人听起来会感兴趣。他原来教外语,后来去教台词。上课主要是戏曲史,还有一些戏曲专题,比如说《春香闹学》他就专题讲。他上课呢,一般不用稿子,准备得很充分。
我听过陈老师唱昆曲,我在复旦时的导师是赵景深先生,他也会唱,但是从昆曲内行来讲,恐怕还是陈古虞要内行一点。陈老师去昆剧团教戏的时候,我还跟着去过一次呢。有一次北京来了客人,陈老师还邀请了青年演员一起唱曲,我也在饭局上作陪。
马圣贵(90岁),上海戏剧学院戏文系退休副教授
根据2019年6月22访谈录音整理
郭东篱访谈
陈古虞老师是我很敬佩的一位老师,学贯中西,他本来是北京大学西洋文学系毕业的,搞莎士比亚研究。但是很有趣,从来没有看到陈古虞老师穿西装,他就迷昆曲,沦陷时候北京的昆曲艺人很多都没落了,他就盯着他们学戏,跟他们一起练功,他有兴趣嘛。昆曲老艺人们缺少文化,陈古虞是大学生,和他们熟了以后就解释唱的内容,所以老艺人们都很尊重他。俞平伯是陈古虞的老师,他家里是昆曲活动的一个据点,有演出的时候,陈老师还给他们打打杂什么的。我们山大的学生都是文工团里来的,跟老师关系都很好,陈老师一个人,经常跟我讲起这些事情。我看过陈老师演出完整的《夜奔》《思凡》,这两个戏都能演的人恐怕不多吧?在山东的时候,看他演的《夜奔》;在上海看他演出的《思凡》,化妆彩唱,一招一式非常认真。上戏还在四川路的时候,方传芸给他吹笛子。上海昆剧团演出,陈老师也看,但他从来不评论的。
陈老师的为人,值得我们学习。一解放他就要求革命,他把北大的工作辞掉了,就去了华北大学;北大的时候,讲师工资蛮高的,华北大学那时都是供给制,学生是最低的生活水平,每个月合下来所有的吃穿用大概才十来块钱。好在为了照顾原来的那些高级知识分子,以研究所研究员的名义,每个月给他们每个人补贴一百斤小米。所以陈老师后来应该是属于离休待遇,但给他办的是退休,他也不在乎,也没有去争。过了好几年后,根据中央文件才给他享受离休待遇。山东大学成立艺术系的时候,校长华岗四处物色师资,就把陈老师调到了山大。从1951年到山大,一直到“文革”以后,这么多运动,陈古虞老师都是平安度过,这也是少有的,这跟陈老师的为人有关,对学生、对同事,都是很真诚的,从来不计较个人的得失,他就一门心思搞自己喜欢的东西。所以他那时参加革命是很不容易的,牵涉到物质上的待遇呢。那时是革命的年代,他研究昆曲就是默默地,能摆脱社会的潮流,这个是很不容易。从教课上看,教戏曲史,一般大家都是从剧本啊什么的讲起,他不一样,因为他懂,所以他讲着讲着就比划起来,能从文化的角度来研究戏剧,大家都很喜欢听他的课。
陈老师的人生轨迹,跟一般知识分子不太一样。他解放前就是讲师,到退休时候还是讲师,他的学识、他的为人都是那么好,这很不公平的。但他也不在乎,也不跟人争,退休后才给他评的教授。我是他在山大艺术系的老学生,后来院系调整的时候,我是学生身份和陈老师一起来到上海的,毕业后就一直在导演系工作。所以,他退休以后,我还每年请他到导演系给进修班的学生上课。陈老师做的曲谱和昆曲研究很了不起,当时担任中国戏曲学院院长的俞琳,他的同学,来上海时去看望陈老师,看了他的曲谱等著作,很惊讶,说你这是绝学啊,我回去一定要安排申请给你出版,可惜没过几年俞琳就去世了。这些曲谱我也见过,但实事求是,我也看不懂。陈老师说元明清主要的杂剧,他都给谱了曲。陈老师身体不好,肺气肿,就爱抽香烟。医院里头住着,医生说不能抽烟,一回家他又抽。最后晚年的时候,都靠侄子一家来照顾他,他们对陈老师非常好。
再说一点,他的故事多了。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时候(按: 1986年),俞振飞想着梅兰芳的代表剧目《刺虎》,过去因为丑化起义农民什么的原因,失传好多年了,所以想着恢复这个戏,但没人教,就安排团里的一个导演秦瑞生,带着华文漪到北京的戏曲学院,说要学《刺虎》,那边的人说是陈古虞老师教的啊,就是你们上海的,所以他们就折回上海来了。我先带着秦瑞生去找陈老师,上午刚去了,下午他就带着华文漪去陈老师那里学。那时陈老师身体不好,卧床休息,他老伴管得严,不让他下床,但陈老师他来了精神啊,说着说着戏就下床了,非常认真地教了这个戏,华文漪连着去了好些天,很聪明,学得很快,很快就学会了。华文漪演出的时候,俞振飞派车去接,可陈老师自己早早就去了剧场了,其他一些昆剧团听说有《刺虎》也都派人来看。
郭东篱(91岁)上海戏剧学院导演系教授
根据2019年6月23日访问录音整理
陈古虞先生点滴记
——章基勤访谈
乙亥仲夏,一个闷热的晌午。上海戏剧学院俞永杰老师打来电话,自报家门之后,便直奔主题,说今年是陈古虞先生百年华诞,学校有个纪念活动,想找一些学生谈谈对陈先生的印象。我很奇怪,问俞老师为什么找我?因为我上的只是进修班,学业也平平,并非陈先生的高足。他说我有篇文章,曾经提到过陈先生。这话倒没错。若干年前,我曾经在《千秋遗爱》中,回忆起当年在红楼,陈先生教我们《中国戏曲史》的情景。于是,顺着这话题,我们的访谈既随意又愉快地进行。
俞老师问:“在你眼中,陈先生是怎样的一个人?”
我说:“好人!”
在俞老师来电话之前,遂昌县文广体旅局的汪旗替他联系我,告知俞老师找我是为了陈先生。我为此特地翻看了尘封多年的《中国戏曲史》课堂笔记。没想到,首页的顶格就有一行字,是对陈先生的眉批。原文如下:
陈教授年逾花甲,和蔼可亲,乐观随和,而且精通音律,能唱昆曲,乃当年昆腔票友。
我已经记不起这行字写于何时,但肯定不是初听他课的时候,因为字迹是蓝墨水,而课堂笔记的前几页是黑墨水,或许是学习中途,或许是课程学完,也有可能是结业之后。时间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随手写下的感觉,在我心中,定格了先生的形象。
俞老师问:“能举些具体的事例吗?”
我说:“可以。”
当年,陈先生给我们上课的时候,看上去已经有些苍老,属于老先生一辈。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刚刚拨乱反正,许多课程没有教材,也没有讲义,包括《中国戏曲史》,授课全凭老师肚子里的墨水,一节一节往外倒。陈先生毕竟上了年纪,有时讲着讲着,被喜欢提问的学生打断了思路,便问:“刚才老师讲到哪里了?”同学们乐了,便起哄:“不告诉你!除非你先给我们唱个曲。”陈先生就说:“好吧!”于是,他缓缓起立,伸出瘦弱但不无娇媚的兰花指,用沙哑的嗓音,咿咿呀呀唱起了“袅晴丝吹来闲庭院,摇漾春如线……”这是我们在课堂上欣赏他演唱的昆曲选段,特别开心,纷纷拍手叫好。然后,让他继续上课。
这样的场景,多次上演。
我记得1982年,学校举办过一个简朴的校庆,出过一本小册子,里面有张照片,黑白的,画面是陈先生在我们班边授课边表演昆曲,举手投足之间,神态栩栩,惟妙惟肖,学生则围成半个圆圈,边听课边观摩,互动感很强,可能是摆拍,也可能不是,我不敢肯定,但无论抓拍还是摆拍,都是珍贵的资料。谁拍的忘了。俞老师很感兴趣,说下周去学校档案室找找看。
俞老师问:“陈先生对你们的功课要求严格吗?”
我说:“还行。”
但陈先生的严格,是一种关爱式的严,不像现在的老师,用死记硬背整学生。他教的功课,也是要考试的。考前,他会告诉学生,哪些内容要考。考试也是开卷的,大家对照课堂笔记,一笔一划抄写一遍。因此,每个同学的成绩都很好。陈老师常对我们说:“考试不是目的,只是手段,让大家抄抄笔记,温故而知新,就很好了。”他对待学生,真正像对待自己的孩子。而他,就是一位慈祥和善的长者。
俞老师说:“真好!”
我说:“陈先生就是如此可爱!这也是我为什么特别喜欢《中国戏曲史》这门课的原因吧。陈先生的课,并不简单照搬别人。比如,戏曲的起源,除了介绍王国维和欧阳予倩的观点,还有他自己的研究成果,认为应该有一定的表演体制,诸如音乐等其他成分。这些,在我的课堂笔记中都有记录。”
俞老师听了很高兴,说:“找你,还真找对了!”
我和陈先生,无论在校还是结业后,并没有很深的交集,对他也没有更多的了解,却多次在文章中提起他。2016年,在《一个遂昌人眼中的汤显祖》自序中,我深情地回忆“在学校红楼的课堂上,读《中国戏曲史》;在老先生沙哑的嗓音里,听汤显祖;在昆曲柔婉的声腔中,欣赏《临川四梦》”的悠悠往事。字里行间,表达了对陈先生的深切怀念。
先生,是能让人铭记一生的人。
再说说课堂笔记吧。笔记本封面硬硬的,庄重的褐黑色,目前依然保存完好,但里面的纸张已泛黄,闻一闻,一股潮润的黄梅气息。我很奇怪,搬过多次家,居然没弄丢?莫非冥冥之中在祈盼什么,或者等待什么。我想,继续留在家里,总有一天要散佚的,找个地方去存放吧。送给母校如何?既是叶落归根,又是纪念陈古虞先生百年华诞的一件实物,我问俞老师。
俞老师表示赞同。
章基勤,遂昌县退休干部,1981年在上戏进修
本文由章基勤先生根据2019年7月8日电话访谈整理
王蓉访谈
我六舅很孝顺,在家里对父母非常孝顺。我外祖母不到五十岁就双目失明,一开始是我的母亲抱“独身主义”来伺候我外婆,但是我的几个舅舅不同意,我母亲他们兄弟姐妹由于家庭的原因,对旧的封建礼教都很憎恨,非常尊重新的文化,我的四个舅舅都是大学毕业,我五舅辅仁大学毕业,学外语,专攻莎士比亚。所以他们认为姑娘还是要出嫁,那时我母亲已经三十出头了。但是女儿出嫁后,年老的父母需要有人照顾,于是我六舅就把照顾我外婆的任务揽在了身上,其他的舅舅有的是无能为力,有的因为特殊原因。那时在沦陷区的时候,我的姨母对他们照顾很多。我六舅大学毕业后,没多少收入,几个学校讲课,非常的辛苦,后来又染上了肺结核病,所以他的身体一直不太好。但他非常勤奋,用微薄的收入奉养父母,一直到我外婆去世。我六舅是个很宽厚的人,是一个有高尚道德品质的学者,对兄弟姐妹也是极尽他的关怀。他自己很刻苦,一生都很节俭,但是对他人的爱心没有一个人不受感动,凡是同学、同事有困难的他都帮助。我四舅也很进步,我父亲介绍他在政府任职,后来他对当时国民党政府的腐败、腐朽的作风非常不满,就辞职回了农村教书,但家庭生活负担就很重,六舅也资助他。解放后四舅去世了,六舅还把侄子接到上海抚养生活,他自己没有子女,就和侄子住在一起。六舅老了以后,尤其是舅母去世后,我表弟一家对六舅的生活非常照顾,包括洗澡、看病等等,那时我们都出来了,全靠他们照顾。
院系调整的时候,六舅从山东到上海来工作,先是住在四川中路的青年会宿舍,后来住在复兴西路,他还是单身的时候,经常上我们家来,我父亲那时也资助他,他就很感恩。但不久我父亲就去世了,他觉得我父亲对他曾经有帮助,所以一直对我们母女非常关爱。我父亲原来在银行是高管,去世以后没有劳保,我们母女是生活无着。我舅舅坚持接我母女去他新婚不久的家里一起居住,一定要叫我再上学。当时我已经考上大学了,因为父亲去世就没有经济能力继续上学,就准备辍学。但是我六舅坚决一定要我完成我父亲的遗愿,叫我学医,他说一定要完成,只要有一分力量一定要叫你去读书。当时我说有能力,我可以工作养活我的母亲,而且你也刚刚成家,不要增加你的负担,而且苦了一辈子。他不肯,无论如何一定要我们去他家。我母亲也不愿意,因为他新婚嘛,我舅母也蛮好,他们觉得跟姐姐在一起也很亲近的,所以我们每个礼拜天都住在我舅舅家里,对我母亲也非常好。所以我就这样能够顺利地在上海第二医学院从一年级读到毕业。我工作后每个周末都会去看他,我调到南京后只要去上海出差,一定会去看望我六舅,他还是那么热情、那么知己、那么贴心、那么敬业。有段时期,高知有一点餐券去指定的地方可以吃得好一点,但他每次一定要带我们或者把孩子带去,他自己吃得很少。他对亲友极其热情,如果谁有困难,就帮助。他除了抽烟没有其他嗜好,把自己的积蓄全都给别人,苛己待人,就这一点工资,自己舍不得花,清廉的知识分子,思想境界高,有知识有品位,真正的知识分子,太节俭了,对人是太宽厚了,所有的亲戚他只要有能力帮助,他总归是帮助。他在做人的生活方面,实在是太苛己为人,极其艰苦朴素,总是一双布鞋、那么一套衣服,一点没有学者的派头或者架子,对人非常有礼节,非常尊重别人。生活上要求很低调,他经常去旧书店,下雨时就打一把破雨伞,也舍不得买件雨衣,但是对孩子们非常好,只要一点钱就给他们买东西。
我六舅是个非常律己的人,做什么事都是很磊落、很正派。在学术上也是非常敬业。他吸烟很厉害,这样使得他的身体每况愈下,甚至要吸氧器的时候,还是日日夜夜写作,笔耕不辍。我舅母全心全意地付出,也是鞠躬尽瘁地在照顾他,所以也是很劳累,身体也不太好,但对我舅舅关爱备至,所以他能够专心地写作。在这个过程中,他还是孜孜不倦地谱曲。他对小的也是关爱备至,放假时孩子们每个礼拜天都要去他那里,他还教我儿子昆曲的动作啊。六舅的兴趣啊,他有时跟我讲苦于没有人来关爱这个艺术,他很想把自己的一些学到的东西、看到的东西传下去,他说这是很宝贵,希望能够传给大家,可是要学的人很少,也是比较难,因此他就觉得有些遗憾。他酷爱昆曲一直到去世,死于肺气肿,呼吸衰竭,就是在医院里他还是写。最后他的遗愿是把我写的这些著作,如果你们觉得没有白费的话,交给学校,将来做教材也好,或者人家不需要,你们留着做个纪念,我一辈子也就是做这个,其他也没有兴趣,对我最大的安慰和爱好就是这个,他对事业非常刻苦。后来他生活中有些消极,但做有关昆曲的事是个安慰,就是坐在病床也一边吸氧气一边写,还把过去的稿子翻出来看,几经修改,有时还唱或读给我们听。所以这方面他太敬业了,是个了不起的学术大师,我觉得我舅舅在这方面实在是太可贵了。无论如何应该要记住这种精神,记住这么一位老师。中国文化的价值不可估量,把这些珍贵的古剧曲谱整理出来,很难,又不图名又不图利,应该弘扬这种精神。因为很少人去研究了,这种精神可嘉。对学生、对同事、对朋友他都尊重人家,他上过台词课,发音好,上海一些著名的主持人、电影明星都来请教过他,他绝对不计较,一点没有要求,丝毫无保留地教给别人。有些人不觉得他的学问的可贵,反而还一味看不起。但我舅舅还是有文人的傲骨,对文化是绝对的尊重,对中西文化结合的研究,他都有很深的造诣,但是他从来不张扬,也从来不自傲,都是很谦虚、很敬业。在艺术方面他的这些著作实在是太宝贵了,尤其现在习主席也提倡要尊重过去的文化。后来我六舅也来南京也住了一些时候,出去玩,中山陵什么的已经没有力气去了。他一生唯一的爱好和精神的寄托全是在昆曲上,对昆曲的爱好、敬业、执着,非常令人敬佩。
王蓉 陈古虞外甥女
根据2019年7月10采访录音整理
侯长治访谈
我1979年认识陈古虞老师是经过北昆的编剧时弢老师介绍,我住在龙潭湖那边,陈古虞老师住在东单的一个招待所里,我每天都去他那里。当时还有一个朋友一起去的,陈老师主要教我。我去了以后他特别高兴,我也特别高兴。陈老师说看过我演戏,1956年11月南北昆会演的时候,我跟随北昆代表团到上海,在长江剧场演出。11月8日晚上我演《火焰山》中的孙悟空,马祥麟老师演铁扇公主;我还在其他场次里侯玉山老师的《嫁妹》中演伞鬼,在马祥麟老师的《出塞》里演马童,在侯永奎老师的《探庄》里演花荣,还有《棋盘会》《对刀步战》等戏我都参加了演出,所以那时候陈古虞老师在上海就看过我的戏。我去见陈古虞老师的时候,他听我说要请他给我说说王益友先生的《夜奔》,他很高兴,满口答应。《夜奔》是光绪年间的昆弋武生钱雄的拿手戏,他传了三个弟子: 陶显庭、荣广和王益友,但却是三人三个样。荣广不知所终,王益友基本上不教弟子这个戏,陶显庭传给了侯玉山。我以前学的《夜奔》是侯玉山先生教的,王益友老师我没赶上,他是“益”字辈的老前辈了,生旦净末丑都能教,但很保守,所以那次就再跟着陈古虞老师学习了王益友老师的《夜奔》路子。他说王益友最大的特点是身上功夫好,京剧那么多武生,都没有他的功夫,他的身上非常有难度。比如说唱“急走忙逃”四个字,这本来应该是最简单的动作,但是王益友这里的身上(表演),那几步走,人家学不了,我看我老师也走不了。为什么呢?陈古虞一讲,我理解这个意思了: 这走路啊有高有平,在台上都是平的,但王益友走着走着楞就往下走,往下走再上来,有这种感觉,这就靠演员的技术了。陈古虞讲到这,我当时都愣了,我说: 哎呀陈老师您这一讲,我就理解了。这就是功夫问题,你看起来走路最容易,越是简单的越难,就是在这种地方,不光这戏,别的戏也如此。所以,陈古虞给我讲完了以后,他说: 你学了,我教给你,你的任务一定要往后传哪,不管什么情况下,你都要教学生,要发展昆曲。陈老师说的话,我到现在都记得,陈老师考虑的是昆曲事业的问题。(顾凤莉: 他呀特别听陈老师的话,因为他很佩服陈古虞老师,就打他跟陈老师认识以后,他基本上就转到教学上了。)这里还有几个动作,就是“三盖腿”,我一说你就明白了,咱们按着老的,“一刹时雾暗云迷”,陈古虞他这样来“三盖腿”(侯老师示范),这是陈老师教的,哎哟我说他要不教都要失传了,要没有了。如果现在有条件好的(演员),应该保留下来。那些天里,陈古虞老师还给我教了《别母乱箭》里的唱,这也是北昆的传统戏,他详细解说了这个戏在表演中的情感层次。陈古虞最好的就是他能把剧情讲得特别清楚,我听他讲确实受益匪浅。头一场,周遇吉见他母亲,这是一段感情;等到见夫人,这又是一段感情;再见儿子的时候,这又是一段。王益友的路子是北昆的老路子,这么讲究,有来历的,是从白永宽那时传下来的,王益友是白永宽的学生。这样三段法演下来,周遇吉诀别家人、拼死一战,观众看了都流眼泪。(顾凤莉: 像陈古虞老师这样又有实践,又有理论,真是太好了。)陈古虞老师讲了确实有好多东西,根据情节掌握表演,太棒了!
侯长治(86岁) 北方昆曲剧院武生表演艺术家
根据2019年8月22日访谈录音整理
附:
王益友在京、津、沪及河北乡间演《夜奔》时声誉最隆,他在昆弋班内弟子很多,但独不教《夜奔》。……而不可思议的是,王益友在台上演出时都不肯轻易拿出来的“掏心窝子”的好身段,却肯热心而详细地传授给业余曲友。他在曲会说戏时,每每用粉笔在地上画出步位。当时在北京大学生曲会的陈古虞,曾将包括《夜奔》在内的王氏所授身段谱一一记录下来。但由于日后陈古虞长期任教于上海戏剧学院,使我一直没有机会向他讨教。直至1979年陈教授来北京,我才终于和他会面。他毫无保留地将王益友所授的《夜奔》等戏教给我,并感慨地说:“王益友老师当年教的这些表演身段堪称精品。只可惜自己是业余曲友,无法忠实地、充分地再现出王老师的风采。如今教给你,也算是弥补了我几十年来的一大缺憾!”陈教授还叮嘱我,一定要把王益友《夜奔》的路子传下去。可惜,他还没等到亲眼看一看我整理重排出来的《夜奔》,就在数年前去世了。……又如念白“一刹时雾暗云迷”一句,我则使用了陈古虞教授记录的王益友轻易不露的“三盖腿”身段,小王桂卿先生看后尤其称赞此处边式漂亮。
摘录自侯长治《我为刘巍排〈夜奔〉》
原载《中国电视戏曲》1997年05期
阮尚志访谈
陈古虞老师是从山东文联调动到华东大学的,后来跟山东大学合并,那时的艺术系里一共只有十个老师,大家很融洽,他教台词课,我是教声乐的。我跟他熟,因为我们经常在一块,住在一块。他排过话剧,1951年春天的时候,我们排了一个秧歌剧《探亲家》,田稼写的剧本,我写的音乐,陈老师导演排戏,表演班的学生郭亚洲等演出,音乐科的同学伴奏,这是我们自己搞的创作,后来抗美援朝募捐演出的时候,这个戏还作为大轴戏演出,效果很好。他排的秧歌剧确实使用了一些戏曲的手段,比如角色的处理方法等。有次跟学生开联欢会的时候,陈老师便装表演《林冲夜奔》,没有伴奏,清唱。那个时候昆曲很少,我们还没看过其他的人演昆曲,看他演出我们也还是头一次,大家也都很有兴趣。在台词课的时候,他还教女生《尼姑思凡》,这个学生后来在上海电影厂工作过,田稼的爱人。我听过他教唱,他很懂音乐。唱武生戏《林冲夜奔》的时候是真假嗓结合用,教《思凡》时候他用的完全是假嗓唱,就是男旦的那种声音,但陈老师在生活当中没有唱旦的那种痕迹。
陈先生原来是供给制,后来也改成薪金制了,他是讲师级别。他肺里有毛病,我肺里也有毛病,我们说一起去拍片,但太贵了后来没有拍。在青岛的时候,我们一开始住在仓库里,后来搬到山大三院,厨房也有了,演剧厅也有了,条件好了很多。我们俩还一起收藏唱片,每到星期天的时候,我俩必然到旧货市场,他选了西洋的东西就给我,我选了戏曲的就给他,我们一块儿交换。我收藏了六百多张西洋音乐的,他也收藏了好几百张,他喜欢收藏梅兰芳、尚小云等人的京剧唱片,还有刘宝全的大鼓唱片,还买了一个很高档的手摇唱机。陈老师喜欢踢足球,看球赛,是个球迷。也还喜欢去看看戏,我们俩经常去唱京戏的“新四小名旦”之一的许翰英家里。在上海的时候我们也是邻居,住在复兴路上同一个宿舍里,他在一楼我在二楼。他也爱养鸟,爱听鸟叫,他也叫我养鸟,因为鸟也会“唱”,而且唱得很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