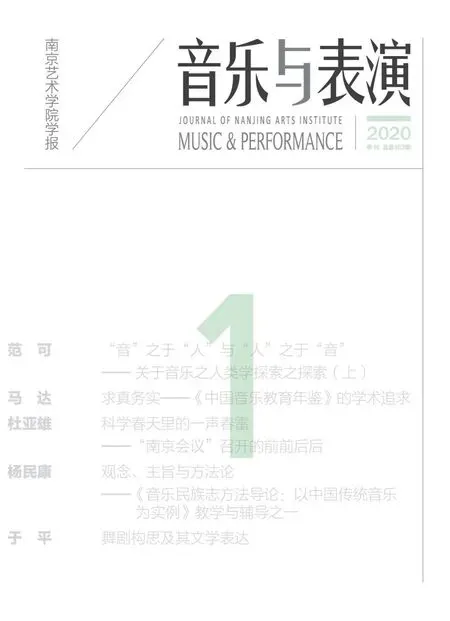“音”之于“人”与“人”之于“音”
—— 关于音乐之人类学探索之探索(上)
范 可(南京大学 社会学院人类学研究所,江苏 南京 210023)
(厦门大学 社会与人类学院,福建 厦门 361005)
缘 起
非音乐出身者谈音乐不免令人忐忑。我一直在竭索枯肠究竟该写些什么才合适。作为一位宣称为人类学家者,讨论内容自然离不开人类学,尤其是社会文化人类学。虽然音乐人类学和民族音乐学与人类学关系密切,但它们对人类学的渗入远远低于人类学对它们的渗入。如果人类学早把音乐作为自己研究的主题之一,这个世界上大概不会有民族音乐学和音乐人类学的什么事了。如此说来,音乐从未成为文化人类学研究的核心所在之一也不见得是坏事——毕竟是社会文化人类学因此而催生了民族音乐学和音乐人类学,而且后两者后来基本形成独立学科(separate discipline)。
既然已经是相对独立的学科,那么是否原先刺激其诞生的源泉就成为枯井或干涸的河床?事实显然不是这样。文化人类学者从未停歇的理论讨论,在许多方面依然对民族音乐学或者音乐人类学有着强烈的推动作用。民族音乐学与音乐人类学二者形成相对独立的学科之后,由于研究主体的不同和学者本身的主体性,在有些方面与文化人类学渐行渐远——但这可能是国外人类学界的一般情况。反观中国,情况则相反。音乐学者日益看重人类学,在民族音乐学和音乐人类学当中尤其如此。但文化人类学者的担当精神在音乐人类学和民族音乐学里似乎没那么强烈,大多数的研究依然停留在如何利用文化人类学理论来解释所面对的音乐文化现象,或是在文化人类学理论的基础上在自己的领域里寻求理论创新的阶段上。
本文题目的“人”兼指“人”和人类学,本文的“音”当然是音乐——尽管现在关于(我认为)与音乐无关的“音”也受到一些研究者的关注。[1]若非本文所论有些未必与人类学有关,或者必须绕几个弯才搭上人类学,用“音之于人类学”可能比“人类学之于音”更合适些。在本文中,我想讨论的问题是:为什么音乐在文化人类学里显得无关轻重或者相当边缘?人类学里不同的取向(approaches)是否对这种状况有所影响?同时,作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音乐在何种意义上被视为文明的象征?本文还将考察一些社会理论家对音乐的看法,通过他们的洞见,音乐能告诉我们什么?最后,笔者还将回答,人类学在哪些方面可以对音乐研究有所贡献。
一、亟待人类学深入探索的领域
在人类学领域里,对音乐的研究应该说是很不充分的。作为文化当中的一个重要部门,音乐在人类学研究中显得相当边缘。从一些美国最流行的人类学教科书来看,音乐要么不在场,要么只给予毫不起眼的篇幅。人类学迄今为止还是带有十分强烈的“他者”研究取向——所研究的对象最好是传统的简单社会。在这类社会里,音乐往往与宗教、仪式以及其他社会生活联系在一起。人们演奏音乐往往是在仪式的场合,于是音乐就具有了某种神圣意义。因而你要了解音乐往往就必须产生感同身受的神圣性,这对大部分人类学家来讲可能是难以做到的。即便研究宗教的人类学家,在他们的专著里分析和描述仪式的过程时,也只能给音乐极为有限的篇幅。①事实上,我随手从书架上抽了几本专门研究宗教或者主要研究宗教的专著,如Roy A.Rappaport 的两本著作, Ritual and Religion in Making of Humanity[M].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和Pigs for Ancestors: Ritual in the Ecology of a New Guinea People, 以及 Robert P.Weller, Unites and Diversities in Chinese Religion[M].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87和Victor Turner的The Forest of Symbols: Aspects of Mdembu Ritual[M].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67.其中,仅有魏乐博(Robert Weller)在描写的仪式场合略微提及几位道士音乐人(见该书第94页)。
众多的人类学教科书对音乐要么付之阙如,要么浅尝辄止,但音乐在人们的社会生活和文化生活中却又是如此重要。这样的反差不能不使人问个为什么。造成这种窘境的原因并不是人类学者不懂或不了解音乐。事实上,有些人类学家对音乐十分在行,不仅精于弹奏某种乐器,而且还是乐队成员,不时参与音乐会演奏。有些人甚至还会作曲。传统上,英美和其他欧洲国家的人类学者多来自教养比较好的家庭,音乐教育几乎是他们从小不可或缺的,许多人类学家在音乐上都有极好的修养。美国人类学家魏乐博(Robert Weller)就是一位大提琴演奏者,家庭里多有从事音乐的专业人士。他对我说他十分感谢他的母亲,如果不是她,他对音乐绝无可能有深刻的理解和感受。当我问他为什么不就此做些关于音乐的人类学研究呢?他回答说,他不愿意,还是让给专门接受过音乐人类学训练的学者或者音乐学者去做吧。但是,我还是发现,他在研究中也不是从来不涉及音乐,或者不使用音乐中的某些成分来写作的。几年前,他与另一位作者合著了一本书,就用了音乐上的一些技术术语作为隐喻和修辞来讨论分类和标准化的问题,也就是关于“文明”的一些问题。[2]
但是,整体而言,音乐的确不常出现在人类学著作当中。我们只能从一般人类学领域没有太多人关注的文献中看到一些——尽管这所谓的“一些”实际上也不少,但却很少看到这类文献进入人类学教科书中。②博厄斯也被认为是民族音乐学的先锋,他也写下了大量有关音乐的民族志。而我们知道,教科书的内容一定是学科的主要关怀及研究对象。因此,问题还是存在:如果不是出于人类学者对音乐的无知,那么,音乐在一般人类学中的缺位或者边缘化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对此,一位美国人类学家的文章“为什么我不是一位民族音乐学者:来自人类学的观点”透露出一些端倪。[3]
这位作者认为,由于他研究的是玻利维亚的民族和音乐认同(national and musical identity),很容易被人当作一位民族音乐学家。但他强调他不是民族音乐学家:他的学位是人类学的,而且民族音乐学和人类学二者的差别其实有着比较深的原因,可以追溯到关于音乐的意识形态、两门学科的历史和制度性结构以及训练的内容(pedagogical agendas)等。虽然这两门学科的学者的研究方法的许多方面有亲缘性,但仍不足以相互替代。“民族音乐学”的标签经常不经意地带有一些基本预设。在这一标签下,“音乐”成为研究对象,研究者被期待去“音乐地(musically)制作所研究区域的地图”。这种期待与确立一种“边界”(boundary)紧密联系。对此,人类学家会担忧文化被弱化为似乎仅与具体的地方绑缚在一起。而且一旦音乐成为研究对象,制作地图成为项目,一些重要的人类学和理论的问题也就变得不那么重要了。民族音乐学者没有这类障碍,但其学科之制度性所在(institutional affiliations)会使他们的工作超越“文化”的概念化限制。另外,民族音乐学标签往往还会意味着,研究者是个“参与着的音乐人”(a participating musician)。这一点有助于强化民族音乐学将“做音乐”(doing music)置于其他的田野参与之上,但却可能落入西方关于音乐的意识形态,如才艺、天分(giftedness)的话语窠臼中。对人类学家而言,这些概念都应经过思考而不应将之想当然地视为与生俱来的、既定的东西。
那么,如何“做音乐”呢?民族音乐学者视“音乐参与”(musical participation)如同一种特定的场域,“一种真正的参与式的参与观察”(a truly participatory participant observation)。[4]这是借助于一种特殊的鉴赏力——太多的东西你只能通过“做”方能知道。[5]当人类学家想到民族音乐学家时,总是设想他们有某种令人敬畏的要素(the awe factor)——能拨弄某种乐器,而且在民族志经验上具有与众不同的技巧和观照。然而,尽管是音乐参与是田野工作的特别领域(realm)而惠及学者,但它却有其消极的一面。所有的田野参与形式都是不同和独一无二的,但是建构出来的“音乐参与”领域却携手一种我族中心主义意识形态(ethnocentric ideology)——音乐成了自治的空间。[6]“令人敬畏的要素”与西方社会关于音乐的意识形态有关系,并在两方面影响了人类学家对于研究音乐的态度:首先,关于民族音乐学者才艺的想象;其次,设想如果不是音乐人便无法完全理解音乐。这种情况等于认为,研究音乐还是由专业人士来进行为妥。
另一种导致绝大部分人类学家在研究中不愿意接触音乐的原因可能是:传统上“他者”是人类学的研究对象。在大部分传统社会里,音乐是“嵌入”在社会生活领域里的,它并没有成为一个独立的门类(a separate sector)。在许多文化里,缺乏抽象的音乐概念,音乐总是与其他的表演形式密不可分,人类学会觉得很难将音乐独立地抽取出来进行研究。于是在文化人类学研究当中,音乐自身的作用和意义会被弱化,甚至被忽视。我想这是一种顺理成章的逻辑发展,即如果不把音乐作为一个专门的领域来对待,那就会将音乐考虑为其存在是为其他事项服务的。于是,从整体观的角度来看,对于音乐本身的探索也就没那么重要了。这应该是一些民族志里,音乐往往与其他娱乐形式,如表演、舞蹈等放在一起进行分析和描写的原因。如此一来,浅尝辄止就在所难免。
再有一种可能性并不在于研究者自己是否对音乐内行,而在于无论面对的音乐简单或者复杂,都会觉得还是有专门研究为好。许多族群的音乐听上去简单(不少民族志提及音乐都有这样的看法),反倒使人类学家产生无所适从之感,对如何深入发掘和讨论产生困惑,会觉得还是由术有专攻者来研究更靠谱些。但这倒可能是民族音乐学诞生的条件之一。
但是,这些都是人为设置的一些障碍。对音乐及其知识、技艺缺乏了解或者理解不如专业音乐人士,并不说明人类学者就完全不具备研究音乐的资格。由于人类学的旨趣所在,不同于音乐人类学或者民族音乐学,所以人类学者研究音乐一定有其独特性。换言之,人类学的研究一定不会以音乐为主体,而是更多地考虑音乐在人类生活中的意义。如人们如何通过音乐来表达情感和诉求,音乐如何表现政治或者社会的变动,音乐如何作为抗议的象征,音乐在社会分层和社会等级的再生产过程中的符号作用,以及音乐作为文化资本是如何构筑边界并影响一个人的人生,等等。传统上,大部分西方人类学者来自中产阶级及其以上阶层的家庭,而在19 世纪和20 世纪的西方国家里,有无受过音乐教育几乎是一种身份阶层和教养程度的标配。许多人类学家因此有着较高的音乐造诣,他们没有在学术上对音乐研究投入精力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二、两种旨趣及其由来
音乐在人类学中的尴尬地位可能与人类学历史上的两大取向有所联系。人类学诞生于19 世纪下半叶。两大出版物往往被认为是人类学奠定的标志,即达尔文的《物种起源》(1859)和泰勒(Edward B.Tylor)的《原始文化》(1871)。然而,在人类学最初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两种取向,一是以博物馆收藏起家的德奥民族学取向;另一是深受社会学理论影响的社会人类学取向。在理论承续上,美国人类学更多地接受德奥体系,源自德语的“文化”成为主要研究对象和关键词。在“二战”之前,美国人类学界是文化人类学与民族学两个称谓并行不悖,但在“二战”之后恢复举行的全美人类学大会上,正式将民族学改名为文化人类学。而泰勒之后的英国人类学,马林诺斯基使“文化”继续发扬光大,但为时甚短。马氏去世之后, 基本上都是深受法国社会学影响的社会人类学的一统天下。 由此正式形成文化人类学与社会人类学的两大取向。两大取向是就其研究对象和关键概念而言的。英国社会人类学的中心关怀是社会,结构是其关键概念之一。拉德克利夫-布朗甚至宣称自己不知道文化为何物。文化人类学自然是以文化为首要关注对象和基本概念术语。这样的两种取向划分与音乐的尴尬处境有何关系?囿于目力所及,在此只能略加蠡测。
人类学关注的是与人相关的现象或者问题(problem)。埃文斯-普里查德(E.E.Evans-Pritchard)在他的演讲里告诉我们,人类学的研究对象其实不是“人”,而是与人相关的各种问题或者现象。[7]不同的旨趣带来了措辞用语上的一些不同,这些不同可能会影响到是否对音乐重视或者重视的程度。社会和文化分别是社会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使用最为频繁的术语。美国人类学重点是文化而少谈社会,英国人类学则反是。美国人类学更多地接受了德意志的思想源流,这与美国早期人类学家多为德国后裔有关。有“美国人类学之父”之誉的博厄斯(Franz Boas)本身就是德国移民,他的第一代和第二代学生大多都是在家中讲德语的德国移民。而德奥民族学的一些重要作者都是博物馆的研究人员,他们的职责要求他们到海外搜寻文物。而文化在德语世界里是18 世纪浪漫主义运动之后普及的概念。文化不仅是人们生活的观念、习惯、生活方式之类,而且还成为了群体的标签。这是来自德意志古典哲学家赫尔德的理念。文化是在特定地理区域讲着同一种语言者所共享的一套生活方式、习惯和价值观,等等。所以我们很容易理解,德奥为什么称文化人类学为民族学,为什么如此倚重文化。
既然是搜寻和展陈来自欧洲之外的文物,那自然需要表明这些文物来自哪些文化或者群体。德奥系统的许多重要学者并没有从事过真正意义上的民族志田野研究,他们所依据的研究资料就是所收集的文物。这种状况不仅决定了他们为什么会以传播学派(diffusionism school)首先出现在人类学世界,而且也决定了德奥民族学注重文化甚于社会的由来。反观马林诺斯基之后的英国社会人类学,“文化”几乎被弃之如敝履。英国人类学家莱特(Susan Wright)认为,英国人类学对文化的重新重视是20世纪70 年代以后的事情。[8]在此之前,以著名的《非洲政治制度》为例,在这部结构功能主义集大成的书中,“文化”仅在无关紧要之处出现三次。[9]
针对A股长期存在停复牌乱象,监管层已经在持续发力。2016年沪深交易所分别发布《上市公司筹划重大事项停复牌业务指引》《上市公司停复牌业务备忘录》,此后沪市上市公司停牌频次逐年降低、停牌时长整体压缩,停复牌问题得到了进一步的规范。
我们都知道,无论文化取向或者社会取向的人类学或者民族学,整体观都是不可或缺的方法论基础。但文化人类学和社会人类学的整体观却有着不同的思想渊源。在哲学思想上,德奥或者美国文化人类学系统的整体观可以追溯到恩斯特·马赫(Ernst Mach)的经验批判主义。马赫是奥地利物理学家和哲学家,其重要思想之一是“整体不等于部分之和”。这一整体观念契合了德意志浪漫主义运动以降的人文地理学意义上的整体观念。马赫的整体观具有方法论意义,提供了一种独特的观照,极大地影响了德语文化圈的社会人文科学。而由于美国的文化人类学与德奥的文化理念有着渊源关系,不免受到了这种整体观的影响。
无独有偶,英国人类学里强调文化的两位前辈,即泰勒和马林诺斯基也受到德意志理念的影响。泰勒与德语世界的关系许多人类学历史的书籍都有所提及。[10]马林诺斯基虽然是波兰人,但因当时波兰分别被普鲁士、奥匈帝国和沙俄所瓜分,所以他当时是奥匈帝国的子民。他所就读的克拉科夫大学即是在普鲁士境内。今天德国人依然认为德国的第一所大学是克拉科夫大学。欧洲版图几经战乱变动甚巨,今天的波兰和俄罗斯等国都有从德国并入的领土。本文无意对此详加讨论,在此略微提及乃在于提醒读者,欧洲学者和知识分子的学术渊源的复杂性和离散性与近代欧洲的政治动荡有关系。马林诺斯基所受的训练基本是在德语世界里,这就使他的研究不仅以文化为本,而且也接受了马赫主义(Machism)的整体观。但马赫(Ernst Mach)的整体不等于部分之和的理念直接引领马林诺斯基文化功能论的出现。整体不等于部分之和的陈述说明,各部分之间存在着有机的联系,这就是所谓的“功能”。我们关注的每一个局部都必须考虑到它与其他部分之间的联系。在这样的观念的引导下,马林诺斯基把文化视为一个整体,强调各部分之间存在着谁也离不开谁的有机联系。但他的文化观却是建立在心理学需求与反应的理解模式上。在他看来,文化首先是为了满足人类的最基本的需要,也就是生理性的基本欲望即衣食住行等。唯有在基本需求得到满足之后,方有更高一级——精神性的需求。这些需求包括宗教、美、艺术,等等。[11]
英国和法国的人类学关注点是社会。其渊源来自斯宾塞(Herbert Spencer)的社会有机体论(social organism)和涂尔干(Emilie Durkheim)的社会整合论(social integration),把社会理解为生物体,各部分各司其职。这也是一种整体的观念,但讨论的议题是“社会”,因此又称社会功能论或称结构功能主义。涂尔干在他的社会分工论里充分表达了他的整合思想。斯宾塞,尤其是涂尔干的社会整合思想直接催生了以拉德克利夫-布朗为领军人物的英国结构功能主义人类学的诞生。
在这两种整体观影响之下,对音乐的重视程度会产生程度上的差别。音乐是文化的一部分,因此,文化人类学者在他们的民族志著作里,间或也会谈及音乐。博厄斯和马林诺斯基甚至都发表过他们所研究群体的音乐的专著和论文。反观社会人类学,音乐似乎不在场或者处于一种根本性的缺位状态。之所以如此,当与人们的认知习惯有关。这就是说,就逻辑而言,人们在归类上不会把音乐归属于社会,二者属于不同的逻辑范畴。社会在本质上与人类的生物本能演化有关,而文化则更多的认为是建构或者创作与再创作的过程。为了进一步理解社会与文化分岔所产生的与音乐不同程度的亲缘性,有必要就文化概念略作讨论。鉴于文化与文明是有所重叠又相互争夺的概念,而文明概念在涉及音乐时也经常作为背景或者干脆就是音乐的一种呈现,以下也略微论及文明。
三、音乐作为文化与文明的组成部分
人类学里关于文化的定义非常之多。在20 世纪50 年代早期,美国人类学家克鲁伯(Alfred Kroeber)和克拉克洪(Clyde Kluckhohn)就文化定义做了一番收集梳理,当时就已经有160 多个,现在只会更多。[12]但在众多的定义中,用得最多,最通俗易懂的却是泰勒的定义:“文化……是一个复杂的整体,其中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人作为社会成员之一,通过学习所获得的任何技巧与习惯”。其中,关键的短语在于“作为社会成员……获得”。[13]这说明,泰勒的文化定义关注的不是通过生物遗传获得的特性,而是那些人们在人生的不同阶段所获得的特性。而在每一个社会中,人们都生活在特定的文化传统中。还有一些定义是工具性的——如把文化视为人们适应环境和社会的工具箱,这样的定义在文化生态学和环境人类学中颇为常见。另外,还有把文化定义为一种内在教养积累的看法,这就是韦伯-格尔兹关于文化是人们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人们悬挂其上,为其所束缚的说法。每个人的行为都受到所处文化的规训和限制。对这种看法的理解必须回到文化的德语语境中去。英语里的“文化”来自德语,原来的意思是驯化(domestication)、培育(cultivation)。据说文化概念的出现与古罗马的雄辩家西塞罗有关,西塞罗谓文化有农耕之意。而文化所有的驯化意涵就是由此而生。驯化意味着将野生的物种转变成为我们种植和养殖的对象。所以,文化自然有教养的意思。我们都生活在一定的文化里,为其所熏陶,这就是濡化(enculturation)过程。正因为如此,文化其实是内在的或者内趋的(inward)。这是与外显(outward)的文明(civilization)相反的。文明所代表的是可视的(visible or tangible)的物质与精神的成就。这种文化第一性、文明第二性是德国古典哲学家康德的说法。康德就文化与文明之间的关系做了陈述。他认为,所谓文明是高级文化的社会体现,而文化则是人们作用于他们所处的环境,通常考虑为传统的人们所习得的行为。康德强调了文化的后天性以及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因此,文化不是普世的而是具体的。[14]
如果我们接受马林诺斯基关于文化首先满足的是人的生物性需求即衣食住行这样的基本生活欲求,那么康德所谓的高级文化的欲求也只能产生在满足基本生活欲求之后。按照马林诺斯基物质文化、精神文化、社会组织的文化构成说,精神文化——包括审美、音乐、美术之类——无疑是构成高级文化的内容。我们无法说明是否诸如美之类的问题于人类而言是否一定是客观的,但是每一个文化都有各自的看法以及与之相关的表达方式。所以我们在讨论诸如美、音乐、美术之类话题时,还是应当考虑到所在文化对它们的限制。这就是说,任何这类表述都是“文化的”(cultural)。
回到“文化”的德意志语境,那么所谓文化不啻就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意思。既然文化在字源上来自驯化,那么,所有的人都是文化的产品。可是,仅仅这样是不够的。我们都经过文化的熏陶,但这只是最起码的,使人从生物学意义上的人成为文化所基本期待的文化意义上的人而已。如果仅仅到了这一步那康德称之为文明的高级文化便无由产生。那么所谓高级文化又是从何而来?这只能到政治经济学里寻找答案了。简而言之,随着社会的复杂化,社会分工日益复杂,等级和阶级也随之而来。不同等级和阶级在社会生活的各方面自然出现了分叉。这样一来,不同阶级或者等级便会产生独具特点的文化。国家政权出现之后,那些在国家中占据上风的等级或者阶级的文化便会成为主导性文化。所谓主导就是所谓的“霸权”(hegemony),也就必然是一个社会里的高级文化。康德将此理解为文明是有道理的,因为文明得以成立往往与是否存在着国家政权、文字、城市、金属冶炼等联系在一起。
既然主导性文化代表的是统治者的文化,统治阶级本身必然会通过各种方式来建构与被统治者之间的“边界”。统治阶层人士在行为举止上一定要体现出与被统治者的不同。于是,变得“更为文明”“更有教养”就成了带有阶级区隔和烙印的过程。社会学家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用“文明”过程来称之,就此指出了文化与文明之间的关系,即文明是文化的外在表达。有“教养”的举止行为是为文明,那是发自内在的东西,但在形成文明的举止行为的一开始,却是来自外在的压力。所以文明的举止行为可谓是外在压力内化(internalization)的结果。①参见:诺贝特·埃利亚斯.文明的进程 ——文明的社会发生和心理发生的研究[M].王佩莉,袁志英,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这种结果的一种体现就是羞耻感的产生。所以,按照埃利亚斯的看法,这些内在的东西来得于生活环境。按照埃利亚斯的逻辑可知,音乐体现教养。在文明过程中,人们把听音乐会和歌剧当作一种有教养的体现,与去博物馆、画廊欣赏文物、艺术品、画作一样,体现一种高雅的品味和有闲阶级的生活方式与态度。这对生活只是为了存活的人来说,显然是一种奢侈。后来,在中产阶级兴起的过程中,举止高雅(manner)的仪态又被中产阶层人士所仿效。在这一过程中,好的教养逐渐形成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意义上的文化资本。这种教养所形成的所谓品位(taste)成为了文化资本重要的组成部分。一个人品位的好坏会对他或者她的人生产生影响,因为一旦某种品位成为特定阶层的标配,也就成为认同的维度,这就会构成个人的社会资本,这当然会对一个人的人生有所影响。①参见:Pierre Bourdieu.Distinction: 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ement of Taste[M].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4。于是,在布迪厄看来,音乐修养当然是法国中产阶层的文化资本(cultural capital)的内容之一。钢琴在19 世纪开始成为西方社会中产阶级的标配。中产阶级家庭经常会要求孩子接受音乐教育,学习弹奏钢琴或者其他乐器。 所以音乐在埃利亚斯意义上的文明语境里,具有了体现“文明”教化成果的重要意义。
传统中国其实也有这样一个过程,只不过它局限于文人士大夫的世界里。我们都知道,“抚琴”是文人士大夫的雅兴,与音乐在其他文明里一样,抚琴是一种教养的体现,是“文质彬彬”的具体行述(performativity)。它是文人的,不是一般大众的;它的演练和存在就是区隔和边界,不仅将自身与社会下层分开,而且也与其他职业群体——甚至文人群体中的不抚琴者——分开,从而在同好的文人间形成一种强烈的认同。而认同需要他者方得以确立与存在,所以琴也通过其行述过程中的仪式意义,建构起琴人与非琴人他者间的边界。琴人以“雅”自命,故而带有行为得体优雅的“雅”是为整个行述的核心所在,于是乎,琴人聚会论艺是为“雅集”,而琴也就转化为文明践行的一个过程。
四、人类学家的贡献与民族音乐学的形成
可以这么认为,民族音乐学和音乐人类学都是文化人类学的“副产品”(byproduct) ,博厄斯是这两个领域的先锋之一。在他的整个学术生涯中,博厄斯一直对音乐表现出浓厚的兴趣。通过培养他的学生对音乐的兴趣,博厄斯奠定了民族音乐学的走向。在他早年的文章中,博厄斯呼吁年轻一代的学者们对“唱和说的艺术”(vocal and verbal arts)予以足够的关注。他说,人类学家都知道,“不存在缺乏诗歌与音乐的民族(people)或者部落,但对土著生活中这部分内容的研究几乎还没起步”。对博厄斯和他的学生而言,文化相对主义的原则非常重要,尤其在艺术、音乐、宗教这样的领域。在此,主体性(subjectivity)扮演着主要角色。早先的其他考察者经常觉得他者的音乐有种“异域”的风情,而人类学家在这样的基础上来理解音乐,即音乐对生产它的社区所具有的意义。 这样的相对主义立场支持了当地人(insider)观点的正当性,人类学家反对观察者依靠自己的文化背景来解释被研究者的音乐,认为这是一种“我族中心主义”的态度。相对主义原则在音乐领域里是不可替代的。在这个领域里,许多听者天真地认为,音乐结构在某种意义上比文化的其他方面更为透明,因此外来者更为容易理解它。许多人以宗教或者语言为例,认为要理解这些如果没有第一手接触是容易进行解释的,而音乐不是这样。但博厄斯则认为这种看法有误。他认为必须要细心和移情(empathy)才能完全理解音乐,即便如一位训练有素的乐者那样,能记下所听到的旋律的结构特点——基本音阶(underlying scales)或者节奏这类传统,但包括歌曲的语言和意义以及与声音结合一起的性格、情感这类深层的意涵,也得像所在社区的成员那样,历经数年的经验方能理解。[15]
博厄斯在对因纽特人的民族志研究中,记述了他们的每日生活,根据他们所唱的歌来了解他们的各种看法。他在对他的研究所做的陈述里,把音乐和语言置于中心位置。他说:“当我学了这个民族的语言时,我能理解从他们的祖先流传下来的老歌和故事。当我如同他们当中的一员与他们一起生活时,我学了他们的习惯和各种方式,我了解到了他们关于死亡和出生、他们的餐饮食物等风俗”。[16]在紧接着的另一次的民族志研究中,鉴于都具有清晰的音阶或者相似的各个相对可期的音高间隔(intervals in pitch)之间音符关系,博厄斯将因纽特歌曲错综复杂的模式结构与东印度音乐、佐治亚的诵歌(chants),甚至古典的中国音乐做了比较。[17]除了结构平行见之于这些传统之中,他认为,对因纽特歌曲的诠释应该根植于因纽特作曲家每日的生活经验当中。歌曲是用因纽特语言来唱的,只有流畅地说这种语言的人才有可能解释语言提供的另一层象征。 博厄斯还是最先指出歌曲的意义被表演它们的环境(setting)所型塑的学者之一。[18]
除了研究过因纽特人音乐的之外,博厄斯对美洲原住民的音乐也有所研究,并形成了自己对所谓“原始音乐”(primitive music)的认识。虽然他和他的学生们收集了许多美洲原住民的音乐资料,但博厄斯依然认为:
目前我们关于原始音乐的知识尚不足以划分精准的音乐区域(definite musical areas),但足以证明其他的文化特色,我们可以了解一系列音乐区域,每一个区域都被共同的基本特质所刻画。东西伯利亚民歌狭窄曲调的界限;平原印第安人一系列下降的基调里,伴随着不断重复的母题的下落节奏;黑人音乐中轮流吟唱——就是这样的例子。[19]343-344
而人类学家所特具的比较视野使他发现, 不同地区甚至不同大陆的民间音乐有不少雷同之处(例如在墨西哥发现的一首民谣其原型是德国军歌)。博厄斯强调这是因为文化事项之传播(diffusion)和采借(adaption)的结果。[19]344
20 世纪中期,民族音乐学作为一个重要学科领域基本形成。如其名所言,这是一个研究族群音乐(ethnic music)的领域。民族音乐学的许多文化意义的层面可以在人类学所倡导的第一手经验中获得,田野工作成为了这一领域获取资料的不二法门。早期人类学家将音乐整合进他们的民族志著作,而民族音乐学者则在许多方面是反其道而行之。音乐成为研究的主要对象,尽管必须考虑到地方文化的特殊性。民族音乐学就是在这样的方法下出现的。以这样的方式投入研究人类音乐创造力的开拓者是博厄斯学生乔治·赫佐格(George Herzog),他以基于文化人类学整体观之上的民族音乐学的整体观影响了数代学者。作为民族音乐学的研究者应该不仅是人类学家,而且还是音乐人类学家,除了对音乐的描述记录之外,还得深度思考方法论的问题,甚至有关他者音乐表演经验的主体性问题。因此有学者提出“双重音乐性”(bimusicality)的说法,即至少应该谙熟两个文化的音乐传统,只有这样,才能从他者的视角理解这些传统,并建立起认识论的平台。但这是有争议的,因为作为研究对象的他者只能为他们自己发声。换言之,他们的主体性必须得经过人类学家来传达。[20]
人类学家常常把创作音乐与写小说来做比较。人类学者和小说家的工作有些相似,都是试图将不在场的事情“翻译”给“身边”的受众。由于象征的复杂本质,注定了这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人与人之间的沟通(communicating)就是“交换”(exchange)过程。如果交换的参与者从人类学视角试图解释(interpret)互动的意义时,所面临的挑战就是是否能把握住一个社会的精神实质。对此,人类学家普遍认为,象征是理解社会互动的关键。鉴于在互动过程中,交换的参与者彼此会型塑对于对方的感觉,从而影响下一步的行动,因而象征本身也就是一种行动类型。格尔兹曾经就此认为,文化是“……把意义的模式历史地传递、具身于象征。这是一个传承而来的概念体系,通过象征形式表达人们沟通、坚持和发展他们的关于生活的知识和态度”。[21]语言是最为基本的象征要素,由于每个字都有一系列的音素组成来承负一个意义,如狗、猫这类“声音”就是象征符号,它们与所指的动物没有本质的联系,否则英文不会称之为dog、cat。而当音乐成为整个事情的中心时,事情就更复杂了。说者的嗓音开始随着她或者他的声调改变时,也使所发的声音有了音乐层面的意义。泰勒(Edward Tylor)对“翻译”的局限性有过评论,他说,将“翻译”作为——但仅为——某种与声响和声调语言(tonal languages) 的叙事创造(creating a narrative)的一方面——如官话(Mandarin)和泰语——会有其特点,但这些特点可能在另一种语言的旋律流动和抒情中丢失。①“另一种语言的旋律流动和抒情”指的其实是一种语言在不同语境里的状态。[22]
现代人类学先驱马林诺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指出,人类学家必须对人们的做和说仔细考察,以描绘真实的社区生活图景。由此,他进行话语分析,或者在大量的语词基础上研究当地人的象征行动,包括语言、音乐、姿势和其他协作性活动。音乐——在这样的意义上——经常扮演影响人们每日生活中说什么以及接下来做什么的主要角色。根据他的观察,说话者从日常语言移到音乐时,话语声调发生改变。大部分巫术通过唱歌反复吟诵使之一开始就与日常表达不同。[23]这种通过音乐语调从日常语言转到激越密集的宗教性吟诵,搭起一个将巫术和神秘与神圣的宗教叙事协调起来的舞台。在此意义上,话语在修饰的同时,经常附和发生在其他地方的行为成分,或者呼应其他早先境遇的方面,从而消解掉日常语言的特点。[24]因此,通过密集重复的形式附和日常语言,反映的是音乐性吟诵对日常语言的屏蔽。音乐与日常言语的关系如此消长说明声音背后变动的权力关系。在仪式的场合,音乐成为权力中心,即便神职人员诵经时也带有音乐的色彩。传统的“读经”也是如此,其声调不同于日常语言,声调在此具有了仪式意义,在参与者与不参与者之间构筑了边界(boundary),同时也构筑参与者日常生活与“神圣的生活”(sacred life)之间的边界。这是宗教场合演奏演唱音乐所生产的意义之一。
另一位在民族音乐学和音乐人类学形成发展过程中不能不提及的人物,是美国人类学家赫斯科维茨(Melville Herskovits)。赫斯科维茨是博厄斯的嫡传弟子,美国西北大学人类学系创始人,也是美国最大的非洲裔美国人和非洲研究中心的奠基人。在他的努力下,西北大学成为美国最大的非洲和非裔研究基地。因为致力于研究非洲社会和美国黑人,赫斯科维茨对包括美国黑人知识分子在内的美国社会对非洲裔美国人的一些看法感到颇不以为然。除了对种族主义的批评之外,他还极为反对那种认为黑人已经同化而失去了原生非洲文化的说法。当时美国学术界颇为流行“寻找当代祖先”(“contemporary ancestors”),其实也就是把不同“种族”的祖先追溯到殖民化时期,这显然是把一个群体的历史斩断,为美国的同化政策张目的叙事。而当时的美国黑人学者也为美国社会无法接受非洲裔感到十分郁闷,他们变本加厉地否定非裔美国人依然还保持着一些非洲文化特质。但赫斯科维茨坚持认为,美国黑人还保持着相当部分非洲文化传承。
作为非洲研究专家,赫斯科维茨坚信一些非洲文化传承依然保持在非洲裔美国人的日常生活当中。在1941 年出版的《尼格罗的历史神话》(Myth of Negro Past)一书中,他试图解构主流社会流行的关于美国黑人的“神话”,包括他们的祖先文化的原始性,从而对人类文明无所贡献在内的种族主义谬说,以及非洲文化已经不复存在的成见。他不仅坚持非洲主义(Africanism)依然存在于美国黑人文化中,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有些非洲文化特质已经渗入了白人生活中。赫斯科维茨同意美国黑人的非洲遗存(African survivals)不如巴西黑人和加勒比黑人多,但指出这是因为美国南部人口比例,白人远多于黑人以及缺乏热带雨林和山区这类可供逃避奴隶制压迫的环境。但在南卡罗莱纳海岸和佐治亚,因为相对较为偏远,非洲遗存在当地的非洲裔当中就保留得比较多。虽然非洲祖居地的文化强烈地影响非洲裔美国人的音乐舞蹈并因此也影响了白人文化——这一事实已经在美国社会被普遍接受,但是大量的黑人民俗、巫术、民间医学等都可以追溯到非洲起源,美国黑人的社会互助组织和葬礼也是如此。他对美国黑人的福音音乐(Gospel music)和灵歌有着浓厚的兴趣,认为是美国黑人保持其非洲文化的证据。而一般人则认为,由于基督教的影响,非洲裔美国人已经“西方化”。赫斯科维茨指出,福音音乐和灵歌除了有非洲本源文化的强烈影响之外,还影响了美国黑人认同的塑造。[25]在这方面,赫斯科维茨的一个贡献就是与早先是他的学生,后来成为同事的重要的音乐人类学家——阿兰·梅里亚姆(Alan Merriam)一起,指导了一位美国黑人学生的博士论文——《美国尼格罗宗教音乐的若干特点:以福音传统为重点的民族音乐学研究》(Some Aspects of the Religious Music of The United States Negro:An Ethnomusicological Study with Special Emphasis on the Gospel Tradition)。这应该是有史以来,第一部专门研究黑人福音音乐的博士论文。值得一提的是,这部论文的主题(topic)也是来自赫斯科维茨的建议。[26]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