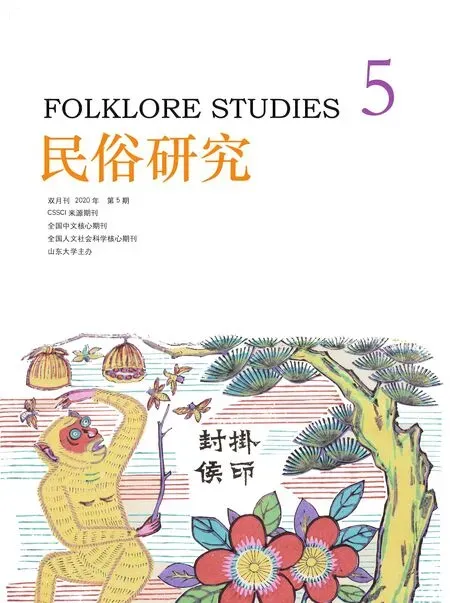从“因生而武”到“向武而生”
——鲁西南郓城县尚武风俗考察
宋晓军 李 黎
历史上动荡不安的社会环境,与较为恶劣的自然环境,是鲁西南郓城一带尚武风俗形成的主要原因。人们通过练武强身健体,期望有效地抵御风险,平安地度过危机,历经千百年积淀而形成尚武之风。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文明的进步,人们的生存状况逐渐改善,人们已经不再为了生存而搏命,但尚武之风依然强劲,并与“斗羊”“送火神”和“武戏”等民俗活动形成相互嵌套关系,为当地民众“日用而不知”。除了强身健体、休闲娱乐之外,尚武风俗还是郓城县民期待美好未来的情感寄托和精神支持,并以“武术之乡”之名成为一方水土的文化标识。
一、“因生而武”:因生存需求而尚武
在西方汉学家对于华北社会的研究中,会发现关于乡民“尚武好斗”或是“安分守己”的一些争论,或被描绘成“相信宿命的”“懒散的”“安分守己的”等等(1)[美]李丹:《理解农民中国:社会科学哲学的案例研究》,张天虹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有时候又被视为“好斗”“崇尚武力”“无法无天”的特殊群体(2)[德]狄德满:《华北的暴力和恐慌:义和团运动前夕基督教传播和社会冲突》,崔华杰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这两种截然相反的描述,其实并不矛盾:乡民要同时面对“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两种环境压力。在面对难以测度的大自然时,乡民往往充满敬畏,自知难以抗拒也很难控制,便多表现出一种温顺与服从的心态。而为了争夺地方社会中的生存资源,获取生活利益,往往就会显示出激烈的竞争意识和强烈的好斗性。(3)唐韶军、戴国斌:《生存·生活·生命:论武术教化三境界》,《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16年第5期。据《郓城县志》记载:“清末至民国二十四年,由于黄河决口,军阀混战,人民生活困苦不堪。郓城境内出现土匪30余帮,小帮近百人,大帮几千人,全县匪徒上万。”(4)山东省郓城县史志编纂委员会编:《郓城县志》,齐鲁书社,1992年,第441页。可想而知,郓城县乡民在恶劣生存环境面前,“如不‘尚武’就难以生存”(5)王学泰:《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同心出版社,2007年,第254页。。
(一)在社会动乱时期以武护身保家
在漫长的中国社会历史上,治乱相袭,其中既有较大规模的农民造反乃至改朝换代,也经常会发生局部的、小规模盗匪横行的社会动荡。历史上,郓城地区民众曾多次暴动,抗击封建暴政,也就并非偶然。北宋末年,郓城人宋江率领36名好汉曾在梁山起义,纵横十余郡,以流动作战的方式多次打败宋军,闻名远近。明末,白莲教首徐鸿儒在郓城梁家楼(现城南武安镇吕庄)一带领导教民起义,义军达10万之众,先后攻克十几座州县城池,义旗插遍山东、河北、江苏等数省,加速了明王朝的灭亡。清咸丰三年(1853),王杲勇在郓城聚众起义,联合临清宋景诗的黑旗军、菏泽郭秉钧的起义军,曾在菏泽城区一战歼灭清军千余名。清光绪三十年(1904),任清合又发动郓城、巨野、济宁等十余县屯民,反抗土地变价,强迫官府取消变价规定。(6)山东省郓城县史志编纂委员会编:《郓城县志》,齐鲁书社,1992年,第4-8页。这一系列的社会动乱,严重动摇着底层社会的生存伦理底线,乡民只能组织起来实行自我保护。非常时期,郓城农民在“他们的锄把里别着长刀”(7)[德]狄德满:《华北的暴力和恐慌:义和团运动前夕基督教传播和社会冲突》,崔华杰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04页。以自卫,也就是见怪不怪的现象。因此,也能解释在郓城武术的传统器械中,多有“劳动生产工具与武器相融合的现象”(8)唐韶军:《生存·生活·生命:论武术教化三境界》,人民体育出版社,2016年,第93页。了。
此外,在生存竞争激烈的地方社会中,往往存在着各种暴力性的派系斗争,“派系斗争是指两个竞争性且具有相似结构的社群之间的有组织暴力”(9)[德]狄德满:《华北的暴力和恐慌:义和团运动前夕基督教传播和社会冲突》,崔华杰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72页。。这种武力冲突,既可能是发生在不同家族之间冤冤相报式的循环仇杀,也可能是发生在较大村落或地域团体之间的“集体械斗”,还可能是拥有不同宗教信仰的民众之间的“教派争斗”,等等。习俗、传统、个人观念以及日常生活细节的差异与不同,都会导致多样性的衡量标准,以致在不同的群体之间造成偏见或仇恨,往往是一些日常琐事也能引发纠纷,并随着矛盾的逐渐上升与激化,最终导致暴力冲突。冲突一旦发生,就要看哪一方的武力占据优势了。要想在冲突中不至吃亏甚或幸免于难,就需要有充分的武力储备。西方天主教传教士安治泰(Johann Baptist Anzer,1851-1903)曾这样记载自己在鲁西南郓城地区的所见所闻:“(郓城县居民)个人恩怨延传至七八代。据说婴儿在出世时要攥握匕首,当长大成人后,作为担负为家人复仇的象征。”(10)转引自[德]狄德满:《华北的暴力和恐慌:义和团运动前夕基督教传播和社会冲突》,崔华杰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71页。可见,郓城地区历史上的尚武需求是如此强烈,几乎成为生存的先决性条件。特别是在传统社会中的动乱时期,不尚武即意味着没有自卫能力,在持续不断的武力冲突中命如草芥。
这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在郓城地方社会生活中,“武可以百年不用,不可一日不备”的尚武传统是如此根深蒂固。
(二)“谁的拳头硬,谁就是大哥”的生存策略
在传统社会中,越是“山高皇帝远”的偏僻地区,越是讲究“丛林法则”,很多矛盾与冲突往往最终需要“武力”解决。郓城一带广泛流行的“谁的拳头硬,谁就是大哥”“有枪就是草头王”等俗语,便是对于这段历史的集体记忆。乡村社会里这种“谁强谁有理”的集体无意识,在现实生活中就表现为对武力的崇拜,特别是对于那些一无所有、只有两膀子力气的贫民来说,可以靠力气和武艺为自己生存和发展开辟道路。练就一身好武艺,就成为他们保障个人生存、提高生活质量、体现生命意义的有效策略。(11)唐韶军:《生存·生活·生命:论武术教化三境界》,人民体育出版社,2016年,第133页。对此,郓城县体育学校校长李刚深有体会:
当年为了强身健体,村里老人请本地老拳师教我们长拳、少林拳、罗汉拳、洪拳等武功,春秋季在场院练,冬天天冷就挖地窖搭棚子在地底下练。我们一帮年轻人经过几年强练硬摔,大都练就了一身好功夫。有一次我独自一人拉地排车去河南焦作拉煤,碰上当地十几个人来找茬挑事,大有强抢豪夺的意思。一看跟他们没道理可讲,我三拳两脚就把两个领头的打翻在地,其他人一看我不是个“善茬”,就都不敢作声了。(12)访谈对象:李刚(1964年生,郓城县前周庄人,郓城县体育学校校长);访谈人:宋晓军;访谈时间:2019年5月18日;访谈地点:前周庄村。
这一现象并非偶然。在我国其他一些高山大川地区,也程度不同地存在着以武力解决矛盾纠纷的现象。如湖北麻城,“在当地百姓看来,官方通过断案来解决这类无休止的冲突是不明智的,相反,应该使用武力”(13)[美]罗威廉:《红雨:一个中国县域七个世纪的暴力史》,李里峰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39页。。即使在当今社会,对于那些处于社会关系链条之外的村民来说,当遇到欺压忍无可忍之时,往往也会在情急之下诉诸武力,付出沉重代价。
中国传统社会灾荒频发,曾被西方学者称为“饥荒的国度”(14)Walter. H. Mallory:《饥荒的中国》,吴鹏飞译,上海民智书局,1929年。(the Land of Famine)。关于水灾、旱灾、虫灾等灾难的记载,在中国历代史书中不绝于缕,“几乎到了无年不灾、无年不荒”(15)沈一民:《清南略考实》,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94页。的程度。
在这样艰难的生存环境中,人们的生存意识极易回到简单原始的“丛林法则”,只有强者才能在弱肉强食、优胜劣汰的生存环境中顽强生存下来。于是,对于强壮、力量、胆量、武力的崇尚,甚至是野蛮的以暴制暴逻辑,在许多地方社会中大行其道。郓城县地处华北平原、西临黄河,自古以来“水祸不断、旱灾频发”(16)山东省郓城县史志编纂委员会编:《郓城县志》,齐鲁书社,1992年,第4页。。在这样一种“靠天吃饭”的自然生态中,民众生活极其艰辛且不稳定。一旦遇到自然灾害,导致收成欠佳甚至是颗粒无收时,以偷窃、走私、绑架、械斗等非法方式攫取生活资源,并不少见。一位天主教传教士曾这样记录当年郓城县令人触目惊心的抢劫现象:“在田间忙于农活时,他们攻击不加提防的过路人。如果这些过路人只被留下行李而不是生命,那么应该自视为是多么的幸运了。”(17)转引自[德]狄德满:《华北的暴力和恐慌:义和团运动前夕基督教传播和社会冲突》,崔华杰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71页。
为了对抗这种防不胜防、随时可能发生的劫掠行为,人们只能时时刻刻采取防御策略,利用武力保护个人财产和人身的安全。(18)唐韶军:《维稳,保卫与调控——论武术精英在传统乡村自治中的作用》,《武术研究》2018年第12期。即使是风调雨顺之年,乡民之间也可能会因为争夺贫乏资源,如水源、土地、庄稼、牲畜、钱财等,引发矛盾冲突,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常常会演变为一场场武力争斗,甚至“成为村民的一种生活方式”(19)[美]裴宜理:《华北的叛乱与革命者:1845-1945》,池子华、刘平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89页。。而在这些武斗中,懂武术、擅长搏击术的人才就显得尤为重要。在发生武力冲突时,他们可以凭借武功击败对手,有时候甚至“不动手”,仅仅依凭长期累积起来的“隐权力”就足以震慑对方,使其知难而退,最终达到保护自身利益的目的。
(三)以武术为生计
自古至今,不论是从传统的开门授徒、看家护院、走镖护镖或获取科举功名,还是当今开办武术馆校、参加政府武术机构、担当武术教练或教师等,武术在我国始终是重要的谋生方式。武术作为一种“营生”,能够让人维持正常生活,而“靠武术吃饭”的人自古至今都大有人在。(20)唐芒果、蔡仲林:《武术从业者:武术发展研究的一个新视角》,《成都体育学院学报》2015年第1期。武术可以作为一种职业,最早见于《管子·小匡》中的“四民分业定居论”:
桓公曰:“定民之居,成民之事奈何?”管子对曰:“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民也,不可使杂处,杂处则其言哤,其事乱。是故圣王之处士必于闲燕,处农必就田壄,处士必就官府,处商必就市井。今夫士群萃而州处闲燕,则父与父言义,子与子言孝,其事君者言敬,长者言爱,幼者言弟,旦暮从事于此,以教其子弟。少而习焉,其心安焉,不见异物而迁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肃而成,其子弟之学不劳而能。夫是故士之子常为士。”(21)房玄龄注,刘绩补注,刘晓艺校点:《管子》,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144页。
管仲首次提出劳作分工的观点,并将齐国的所有从业者分为“士农工商”四种类别。“士”为四民之首,虽然包括“文士”和“武士”,但在当时主要是指军士。“士”的职业教育主要有两方面内容:一是伦理道德教育,包括“义”“孝”“悌”“敬”等;二是武术训练,包括军事知识和实战能力。由此可见,从事武术职业的武士在当时应是令人向往的职业,在可作为谋生手段的同时,又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因而至少在齐国一带极大地促进了民间尚武之风。此后,历朝历代多有“以武选士”的记载,使得尚武之风在整个传统社会中得以延续。特别是始于唐代的“武举制”,更是极大地促进了底层社会的习武热情,使得普通民众可以通过考取武举人、武进士甚或武状元改变人生命运,光宗耀祖。据《郓城县志》记载:“宋到明朝末年郓城练武人共考取武举22名,到清代武进士、武举人共72名。今县城北苏庄,曾设有古教场一处,县城外建有演武厅、官厅、点将台等专用武林比武的场所。”(22)山东省郓城县史志编纂委员会编:《郓城县志》,齐鲁书社,1992年,第551页。“武举制”在为统治阶级选拔武用人才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也给广大民众提供了一个以个人武艺技勇进身仕途的机会,这种仕宦之诱,无疑对于整个社会的尚武之风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23)[美]罗威廉:《红雨:一个中国县域七个世纪的暴力史》,李里峰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3页。
二、“向武而生”:郓城人的武术情结
“习性”(habitus)是布迪厄社会学理论中的核心概念,是“一种持续的、可转换的性情倾向系统”(24)Bernard Lahire,“From the habitus to an individual heritage of dispositions.Towards a sociology at the level of the individual”,Poetics,vol.31, no.5 (Oct. 2003), p.329.。也就是说,“习性”是以某种方式进行感觉、感知、思考和行动的倾向,这种倾向通常是人类个体以无意识的方式,把其生存的客观条件和社会经历予以“内在化”,纳入自身。(25)[法]菲利普·柯尔库夫:《新社会学》,钱翰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36页。在郓城地区,尚武便是一种“世世代代、年深月久地沉积在普通民众的意识与行为里的习惯性”(26)程歗:《文化、社会网络与集体行动:以晚清教案和义和团为中心》,巴蜀书社,2009年,第141页。。这种惯性力量,深刻影响着当地居民的日常生活,乃至传承悠久而不衰。武术可谓是郓城民生活的日常组成部分,既可习练,也是受欢迎的话题。无论是什么场合,只要谈及武术,气氛就会热烈许多。而在郓城,又好像什么事情都能和武术扯上关系,尤其是对于许多爱好武术者而言,就更是三句话不离武术。
(一)斗羊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每年“五一节”期间,郓城县城南汽车站一带都会举办斗羊比赛大会。我们曾连续三年赴现场考察,比赛场地一直设在城中“唐塔”前、“蓼儿洼”边的万人体育场上,一时间人头攒动,观者如潮。在街道两旁的水泥电线杆上,朝向四方的高音喇叭,反复播放着电视剧《水浒传》主题曲《好汉歌》,载着参赛大角绵羊的马车、拖拉机等则在体育场外的一片芦苇边上罗列成排。宽阔的体育场入口处,一个个体魄健壮、动作潇洒、斗志昂扬的斗羊人陆续进入会场,头戴遮阳大草帽,黑红的脸庞英武勃发,一只只重约100公斤的大角绵羊紧随其后。这是一种特别好斗的“抵羊”品种,毛色雪白,羊头连着横阔的前额,粗壮双角分列两边,行进中不时昂头远望或俯身嗅地,嘶鸣不已,颇有野性雄风。有的抵羊眼周围有一圈黑毛,羊角则从根部直接向外做大回旋伸展,像戏曲舞台上威风八面的武花脸。还有的羊头双角呈现出道道粗实裂纹,这是身经百战的象征。
入场仪式,是各种抵羊的形象展示,体魄多么健壮,斗志多么高昂,以及容貌威严、唯我独尊的各种架式。在这背后,是羊主人的社会资本炫耀,包括所拥有的财富、能力和地位等等。听惯了“梁山好汉”故事的郓城人,往往会给自己的羊取个响亮的名号,比如“天杀星”“豹子头”“霹雳火”“黑旋风”等等,将对梁山好汉的崇拜移情到羊身上。入场仪式结束之后,随着一声哨音,分组斗羊初赛开始。整个会场早已用彩旗分成数个圆圈,两只抵羊在“斗友”的高声吆喝声中,猛撞不已,不分胜负绝不罢休。到了决赛阶段,则采用打擂台模式,各小组的第一名参与自由角逐。在夯土而成的擂台上,擂主一手执短皮鞭,一手牵着初赛得胜的威风凛凛的羊。打擂者牵羊上场,相互拱手,各自朝相反方向领开抵羊,斗场内顿时安静下来。待裁判手中红旗一挥,主人用力一拍羊的前肩,大喝一声“嘿-哈”,两边的抵羊迅即凶狠地猛冲向对方,在临近的一刹那,突然四蹄腾空向前爆冲,双角相撞发出惊心动魄的“哐哐”之声。从第一回合相互撞击,双方拉开自然后退大约10米距离,再摆开架势连续相抵,一来一回,大约斗至七八回合,往往就有一方力怯,或头部遭到对方抵角重创,主持人便立刻终止比赛。得胜的抵羊会野性大发,迅即冲向刚刚登台的第二个参赛对手,眨眼之间即将其顶翻在地。这种戏剧性的场面每年都多次出现,场上场下顿时欢声雷动。
郓城斗羊看似是一项简单的体育运动,其实具有一定的“地位的血的洗礼”(27)Erving Goffman. Encounters: Two Studies in the Sociology of Interaction. Indianapolis: Bobbs-Merrill, 1961.p.78.的性质。就获胜者而言,此时此刻会自觉与众不同,陶醉于酣畅淋漓的成功喜悦之中。而对观众来说,置身于斗羊现场就是一种独特的情感体验,一旦自己所看好的羊获胜,也会获得一种独具慧眼的优越感。就此而言,郓城斗羊比赛即是社会表演的剧场,这一活动本身则是“一种情感爆发、地位之争和对社会具有核心意义的哲理性戏剧的综合体”(28)[美]克利福德·格尔茨:《文化的解释》,韩莉译,译林出版社,2008年,第429页。。传统的尚武之风,使得郓城人格外喜欢斗羊;而定期举行的斗羊活动本身,又进一步激发了郓城人的练武热情。
(二)送火神
正月初七“送火神”,是郓城一带乡村过年期间的神圣仪式,特别热闹。过了大年初一以后,是村民走亲戚、四处听戏的日子,青少年晚间练武,同时不忘“绑火神”。“绑火神”的材料,要选用一丈多长的高粱秸9棵,以红色麻绳捆绑,中间夹着豆秸,有的还故意塞几个鞭炮,为的是在“送火神”路上以壮声威。在“火神”的最上部,要用“秫秸瓤”(即去掉高粱籽的穗子),特别容易点燃。这一带普遍种植小麦、大豆、谷子、棉花、高粱,特别是高粱长得又高又壮,有“麦子去了头,高粱漫了牛”的俗语。秋后砍完红彤彤的高粱头,村民便将一捆捆高粱秸围成像一座座小山堆放,俗称“高梁筌”。高粱秸既解决了这一带乡村地区过冬生火、做饭、取暖等难题,还可用来扎制风筝、“兔蹦子”(29)兔蹦子,郓城一带俗语,是将高粱秸截短后扎成一种圆灯笼形,迎风则转动不已,是颇受当地孩童喜爱的传统玩具。等。“送火神”的仪式不知起源于何时,其寓意是将未来一年的灾殃驱除村外,但在郓城乡村青少年的心目中,则更像是一场展示勇武的游戏。
正月初七黄昏时分,各村十四五岁的孩子早早吃过晚饭,便扛着各式各样的“火神”,齐聚村口,相互比较品评所扎“火神”技艺的高低。天色刚刚变黑,大家纷纷点燃自家手中的“火神”,以村落为单元,在齐声呐喊中冲出村口,冲向两村之间的空旷地带。当地俗信,哪村“火神”送得远,哪村在未来一年就没有灾殃,而被对方送来“火神”的村落则有可能遭殃,因此哪个村都不允许对方“送火神”送得距离本村太近。由于这一带村际之间距离不远,此时各村之间不约而同地都相互“送火神”,多条火龙很快在野地里接近,双方开始挑衅叫骂,最后在暗影里打作一团,谓之“打火神”。双方讲究列阵配合,互有攻守,还未等分出胜负,旁边高举“火神”观战的人就难以为继了,因为火把即将散架,便索性扔向空中,火花四溅。双方在黑暗中继续乱战一阵,两村有威望者此时就会出面制止乱局,宣告“火神”升天,各自回家。第二天,两村人会在走亲戚的路上见面,但谁也不再提昨夜“送火神”酣斗之事,两村老少也从不相互记仇。而在昨夜打斗中表现勇武的青少年,则被视为村落英雄,甚至被赞誉为“活李逵”“燕青再世”或“好汉武二郎”等等,与梁山好汉相提并论,成为全村老少未来好长一段时间的谈资。
“送火神”仪式起源的原初动机也许是民间信仰,但其延续至今,依旧昌盛不衰,却在于它满足了人们更多的精神需求。其中,练武者的广泛参与以及丰富的武术元素的融入,使得“送火神”仪式具有了更多的“地方性知识”。首先,按照传统信仰,该仪式既要把“灾殃”驱逐到本村以外,同时又要防范邻村将“灾殃”驱至本村为害,村际之间发生冲突和武斗就在所难免。在这一仪式活动过程中,本村习武的年轻人特别是武功高强者,往往会成为村民依赖和安全保障,并被视为村落英雄。其次,在这种有攻有守的村落集体行动中,村民紧密团结,一致对外,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本村的凝聚力。再次,“送火神”仪式发展到后来,逐渐衍变为一种娱乐性很强的“社会戏剧”,从最初扎制“火神”时对易燃易爆材质的添加,到两村村民相遇时较为夸张的花腔叫骂,再到黑暗里短暂的冲突与权威者及时出面制止,象征与表演的意味十足。遍行各村的尚武之风,特别是武林高手在这一带的普遍存在,则是这一“社会戏剧”具有极强感染力的基本保障。
(三)武戏
郓城县是远近闻名的“戏窝子”,长期流行山东梆子戏、柳子戏、两夹弦、大平调、四平调、枣梆等诸多剧种。戏曲音乐伴奏有“文场”“武场”之分,武场包括鼓、锣、镲等打击乐器,用以控制舞台演出节奏,文场则以管弦乐为主,演奏出声韵旋律。当地每逢庙会必唱大戏,各剧种名角辈出,声名远扬,以至于流行着“扒了屋子卖了地,一心要听×××的戏”之类的谣谚。在郓城乡村,最受欢迎的还是武戏。武功是武戏的主要表现形式,因而习练武功是当地戏曲演员每天必有的基本功课。当地有一句俗语“好手打不过赖戏子”,便是夸赞武戏演员的武功之高强。不少演员从小就开始练“童子功”,并长年坚持,以“曲不离口,拳不离手”“台上三分钟,台下十年功”等行规俗谚自励。郓城一带的戏曲武功训练自成系统,“基功”包括走台步、跑圆场等,“技巧”包括拿顶、下腰、压腿、踢腿、虎跳、飞脚、旋子、前后空翻等;“把子功”则包括剑、单刀、双刀、双锏、双锤、单枪、双枪大刀、棍、戟、打出手、徒手格斗等,并各有单练和对练套路。
武戏中最常见的是“长靠戏”和“短打戏”。长靠戏即指表现武将骑在马上的戏,如《挑花车》《古城会》等。短打戏则是表现绿林好汉对打的戏,如《武松打店》《白水滩》等。此外,武戏中还有名为“打出手”的一种特别讲究武功表演的一种,直接将武术功法搬上舞台,注重炫技效果,很受欢迎,一些著名演员往往能“一招鲜,吃遍天”。有的乡村舞台演出,演员直接使用武术中的真刀真枪对打,枪刀相击火花飞舞,再加上兵器碰撞所特有的声音,观众看得如醉如痴。事实上,老一代郓城武戏演员多是当地武林高手。清末,郓城县石垓村著名武生演员史如秀驻留济南演戏,看到知府悬赏白银两千捉拿一个无恶不作的飞贼,便主动领受任务。他运用轻功进入飞贼卧室,眼疾手快,先将其短刀踢飞,再将其胳膊卸脱臼,降服后扭送官府。史如秀为民除害,却不领受封赏,被赞为义士。
在郓城传统武戏演出中,以水浒戏最受欢迎,如“武松打虎”“武松打店”“醉打蒋门神”“血溅鸳鸯楼”“三打朱家庄”“燕青打擂”“时迁盗甲”等。当地传统武术套路与武戏表演有着密切的互动关系:多种拳法中都有的“打虎式”,据说是受到了武戏中武松打虎动作的影响;在“醉打蒋门神”的武戏中,武松与蒋门神对打时主要采用当地流行的“醉拳”套路;“燕青打擂”中武生扮演的“浪子”燕青,与擂主任原在擂台上对打,则采用多种武术抱摔的动作,如燕青一个潇洒漂亮的“前扑”上场,拧两圈如云中燕子飘飞的“旋子”后突然静止,立地作一个“鹞子翻身”亮相,而武花脸任原求胜心切,几个照面对打扑空,自乱脚步,被燕青随机近身双手抓起,使出“鹁鸽旋”将其扔下擂台。上述一连串动作,显示出武功绝技与武戏表演的相互补充,达到了绝妙的艺术效果。
地方戏曲,是对中国传统乡村生活影响最大的一种教育途径和娱乐形式。(30)张鸣、徐蕾:《“拳民”与教民:世纪之交的民众心态解读》,九洲图书出版社,1998年,第117页。而在郓城地区,广泛流传的梁山好汉故事则对此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特别是壮怀激烈、武打精彩的武戏,潜移默化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形成了与传统尚武之风的同构。
三、结 语
张士闪曾在论及村落民俗传统时提出:
很多民俗传统一开始都是作为事件应激之文化调适而出现的,如村落形成之初的生存所需、灾乱年头的秩序维持、太平时期对发展机遇的捕捉等。这种因事件应激而形成的文化调适,不会随事件的结束而彻底消失,而是逐渐沉淀、扩散于村落日常生活中,作为社会经验而有所传递,并有可能在后发事件中被选择性、创造性地运用,由此磨合为一种社区行为模式。(31)张士闪:《当代村落民俗志书写中学者与民众的视域融合》,《民俗研究》2019年第1期。
鲁西南郓城地区尚武之风的形成正是如此。自古以来,郓城一带“民风强悍”,“年轻人自然而然地变得精通武术”(32)[德]狄德满:《华北的暴力和恐慌:义和团运动前夕基督教传播和社会冲突》,崔华杰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68页。,而在1992年被评为首批全国“武术之乡”,亦可谓名至实归,是对其深厚武术传统的高度认可。在郓城县,尚武风俗与斗羊、送火神、武戏表演等诸多民俗活动形成了密切的互动关系,在地方社会生活中发挥着不可低估的作用。这一尚武之风之所以根深蒂固,是因为在经过了“世世代代、年深月久地沉积”(33)程歗:《文化、社会网络与集体行动:以晚清教案和义和团为中心》,巴蜀书社,2009年,第141页。之后,已经深蕴于普通民众的意识与行为之中,成为布迪厄所谓的一种生活“惯习”(34)[法]皮埃尔·布迪厄、[美]华康德:《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李猛、李康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第15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