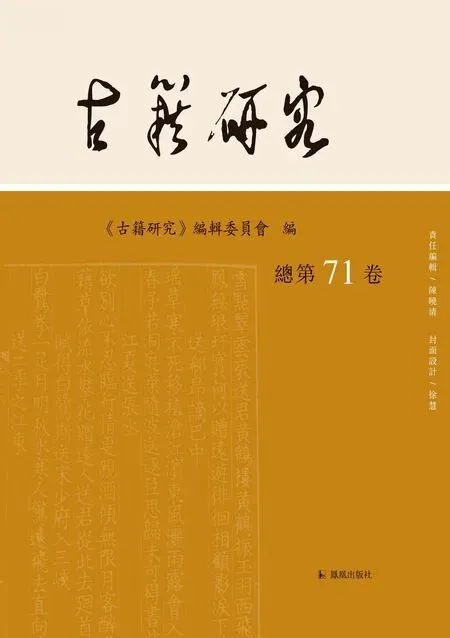論《離騷》的“女嬃”與清華簡的“有嬃女”*
侯瑞華
關鍵詞:《離騷》;女嬃;清華簡
《離騷》:“女嬃之嬋媛兮,申申其罵予。”(1)(漢)王逸著,黄靈庚校點:《楚辭章句》,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第15頁。按:“罵”一作“詈”。
對於“女嬃”一語,衆説紛紜。根據學者最新的梳理,“有關女嬃身份的各種解讀共有七大類二十餘種”(2)曾廣麗:《文獻與義理視野下的女嬃研究》,《三峽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9年第2期,第22頁。。細繹以往諸説,雖然所得結論各異,但各家所據以立説之材料則相差無幾。下面我們先將傳世文獻中的相關材料按照内容分組,逐一進行考辨。
第一組文獻:
(1) 王逸《楚辭章句》:“女嬃,屈原姊也。”(3)《楚辭章句》,第16頁。《楚辭·九歌·湘君》:“女嬋媛兮爲太息”,王逸注云:“女謂女嬃,屈原姊也。”(4)《楚辭章句》,第48頁。
王逸之説在後世影響甚大,但是從文義、辭氣出發,前人多有疑“女嬃”非屈原之姊。姜亮夫先生在《楚辭通故》中曾有詳辨,其説謂:
一則以“鮌婞直”而至於大過爲此,則以婞直爲戒也。“博謇而好修”,“獨有姱節”,則以博謇、好修、姱節爲戒也。“世並舉而好朋兮,夫何煢獨而不予聽。”則不必煢獨,與世爲朋也。原若有姊,則期其弟爲壬佞,爲不修,爲無姱節,爲結黨以自營,爲判離不服,此無識尾瑣婦人之言,使原有此不明大義之姊,原又豈忍彰之“報章”,騰諸口説,以爲快哉。且下文總結時,有閨中邃遠之詞,何得以閨中指斥姊氏,本節冒語有申申詈予之語,何得以詈語言及姊氏,且嬋媛一詞,王訓牽引,以今語譯之,有面柔體柔,婉轉作媚之義(《九歌》“女嬋媛兮爲余太息。”亦此義,王逸注亦以指原姊女嬃),又安能以此等絶不莊嚴之詞,形及同懷。則就詞氣論之,此不宜爲姊氏,而當爲小妻。(5)姜亮夫:《姜亮夫全集》二《楚辭通故》第二輯,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75—176頁。
儘管對“女嬃”的身份仍多争議,但後人對王逸之説多不采信。
(2) 酈道元《水經注·江水》“又東過秭歸縣之南”下注引袁山松云:“屈原有賢姊,聞屈原放逐,亦來歸,喻令自寬。全鄉人冀其見從,因名曰秭歸。即《離騷》所謂女嬃嬋媛以詈余也。……縣東北數十里有屈原舊田宅……宅之東北六十里有女嬃廟,擣衣石猶存。”(6)陳橋驛:《水經注校證》,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第791頁。
此説明代汪瑗、李陳玉等已經辨之甚詳,如李陳玉《楚詞箋注》云:
從來詮者,謂女嬃爲屈原姊,不知何所根據,蓋起於袁崧之誤。袁崧因夔州秭歸縣有屈原舊田宅在,遂謂秭歸以屈原姊得名,不知秭歸之地,志稱歸鄉,原歸子國。舜典樂官夔封於此,故郡名曰夔州。《樂》緯曰:昔歸典吁聲律。然則歸即夔,後人乃讀爲歸來之歸。宋忠曰:歸即夔,歸鄉蓋夔鄉矣。酈道元好奇而不能辨,遂兩志之《水經注》,故世互相沿習。(7)轉引自崔富章、李大明主編:《楚辭集校集釋》,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302頁。
可知《水經注》之説實不可信據。
第二組文獻:
(3) 文獻中有星名“須女”。
作爲星名的“須女”在較早的傳世文獻中一般稱爲“婺女”,如《左傳·昭公十年》:“有星出于婺女”(8)《十三經注疏》整理委員會整理:《春秋左傳正義》,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第1469頁。,《禮記·月令》:“季冬之月,日在婺女。”(9)《十三經注疏》整理委員會整理:《禮記正義》,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第651頁。之後則似乎並行互用。如睡虎地秦簡《日書》甲種六見“須女”一詞,如簡77“須女,祠、賈市、取妻,吉。”相同的内容,睡虎地《日書》乙種簡105作“婺女”。(10)陳偉:《秦簡牘合集.釋文注釋修訂本》(壹、貳),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16年,第364、497頁。《淮南子·時則訓》:“旦婺女中”,高誘注云:“婺女一曰須女。”《淮南子·天文訓》:“北方曰玄天,其星須女、虚、危、營室。”(11)張雙棣:《淮南子校釋》(增訂本),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年,第559、295頁。《史記·天官書》:“婺女,其北織女。織女,天女孫也。”張守節《正義》云:“須女四星,亦婺女,天少府也。南斗、牽牛、須女皆爲星紀,於辰在丑,越之分野,而斗牛爲吴之分野也。須女,賤妾之稱,婦織之卑者,主布帛裁製嫁娶。”(12)(漢)司馬遷:《史記》,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第1558—1559頁。
上引張守節的《正義》一段常被用來證成《離騷》“女嬃”是侍妾或賤妾之説,然而作爲星宿的“須女”是否與“女嬃”有關是很成問題的。
首先,對於須女的得名,文獻中實際上已有解釋。《史記·律書》:“東至于須女。言萬物變動其所,陰陽氣未相離,尚相胥[如]也,故曰須女。”(據張文虎説:“‘如’字疑衍,胥、須義通”)(13)[日]瀧川資言著,楊海峥整理:《史記會注考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1422頁。則須女之須,從語源上來説是來自“胥”。“須”與“胥”音義皆近,《史記·趙世家》:“太后盛氣而胥之。”裴駰《集解》“胥猶須也”(14)《史記》,第2184頁。,可以爲證。
其次,“須女”一名“婺女”,且女宿又有“織女”,可知“X+女”是其構詞方式,文獻中也並未見到“須女”倒文作“女須”的。
至於張守節之説“須女,賤妾之稱”,未詳何據,且與《史記·律書》所言不合。不過從“婦織之卑者”一語推測,張説應是以天文比擬而論。《説文》“嬃”字下朱駿聲《説文通訓定聲》云:“按天文北方宿女四星亦曰須女,光微小。天市垣、織女三星明大,故織女爲貴,須女爲賤。”(15)轉引自丁福保編:《説文解字詁林》,北京:中華書局,2014年,第12095頁。織女三星明亮,且如《史記·天官書》所言是“天女孫也”,而且又象徵紡織;“須女”光微小,相比之下,正可以説是“婦織之卑者”。
根據以上三點,可以首先排除作爲星名的“須女”與“女嬃”的關係。
第三組文獻:
(4) 《周易·歸妹》:“六三:歸妹以須,反歸以娣。”《釋文》“以須”下云:“如字,待也。鄭云:‘有才智之稱’。荀、陸作‘嬬’。陸云:‘妾也’。”(16)(唐)陸德明:《經典釋文》,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第29頁。
(5) 《鄭志》答冷剛云:“須,才智之稱,故屈原之姊以爲名。”(17)“姊”原作“妹”,阮元《校勘記》云:“‘姊’誤‘妹’,下同,是也。”孫詒讓《十三經注疏校勘記》云:“《周禮·天官·叙官》疏引《易》注亦作‘姊’。”參見《十三經注疏》整理委員會整理:《毛詩正義》,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第1009頁。(《詩經·小雅·桑扈》“君子樂胥”句《正義》引)
前人多已指出,鄭玄的解釋是將“須”破讀爲“諝”,如《説文》“嬃”字下段注云:“按鄭意,須與諝、胥同音通用,諝者,有才智也。”(18)(清)段玉裁:《説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617頁。
馬王堆帛書本此句作“歸妹以嬬”(19)于豪亮:《馬王堆帛書〈周易〉釋文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33頁。,與荀、陸本相同。從破讀方向上看,鄭玄的解釋應該是有問題的。結合初九爻辭作“歸妹以娣”,可知今本的“須”字亦不當如字讀,而應讀爲“嬃”。而根據初九爻辭以及“歸妹以須,反歸以娣”對文,則“嬃”當與“娣”相對,指姊姊。陳鼓應、趙建偉《周易今注今譯》解釋説:“古時女子出嫁,例以侄娣爲媵(陪嫁),今以姊姊爲媵,是爲‘未當’(《小象》語),故被遣歸而仍以娣爲媵。”(20)陳鼓應、趙建偉:《周易今注今譯》,北京:中華書局,2015年,第477頁。其説可從。
至於《釋文》所引訓“妾”之説,與上説也並無矛盾。以“嬬”字而論,《説文》云:“弱也。一曰下妻也。从女,需聲。”(21)(漢)許慎:《説文解字》,北京:中華書局,1963年,第264頁。下妻即是妾,正妻以外的媵女嫁到夫家自然是妾,“歸妹以娣”、“歸妹以嬃/嬬”中的“娣”與“嬃/嬬”正是這種身份。從文義出發“嬬”可以理解爲“妾”,但從詞義出發,“歸妹以須”的“須”則應以訓“姊”爲是。
第四組文獻:
(7) 吕后的妹妹名吕須(又作“嬃”)《史記·樊酈滕灌列傳》:“噲以吕后女弟吕須爲婦”(23)《史記》,第3205頁。,《漢書·高后紀》“(吕禄)過其姑吕嬃”(24)(漢)班固:《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第101頁。。
(8) 《漢書·武五子傳》:“始,昭帝時,胥見上年少無子,有覬欲心。而楚地巫鬼,胥迎女巫李女須,使下神祝詛。” 颜师古注曰:“女嬃者, 巫之名也。”(25)《漢書》,第2760—2761頁。

賈逵之説似與《周易》“歸妹以須”相合,但是與吕后之妹名嬃這點矛盾。面對這個問題,《楚辭》學者的解釋是:
張鳳翼云:
恐嬃者女人通稱,未必原姊,不過如室人交遍責我之謂耳。(26)《楚辭集校集釋》,第301頁。
張雲璈亦據吕后之妹名嬃,認爲:
是妹亦可稱嬃,則知嬃乃女之通稱,不必專屬姊妹。(27)《楚辭集校集釋》,第303頁。
《説文》學者對此也有不謀而合的論斷。《説文》所引的“楚人謂姊爲嬃”一句,傅雲龍《説文古語考補正》云:
嬃之本義爲女字。“楚人”上無“一曰”字,則“姊”當作“女”。《集韻》、洪興祖《楚辭補注》引《説文》“楚人謂女爲嬃”,作“女”可据以訂正古語,云“嬃”不專屬“姊”。(28)《説文解字詁林》,第12095—12096頁。
《楚辭》學者從文義出發,《説文》學者則找到了版本上的證據。即以《周易·歸妹》的辭例而論,也有學者據“吕嬃”之名立説。如李鏡池《周易通義》云:
須:借爲嬃,亦即女弟。須與娣對文,用换辭法避免重複。《史記·高后紀》:“太后女弟吕嬃。”以嬃爲名,意謂吕妹妹。(29)李鏡池:《周易通義》,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第108頁。
可見“嬃”字很難明確究竟是稱“姊”還是稱“妹”,並且很有可能就是女性的通稱。
此外,第(8)條材料過去常被人引爲證明《離騷》的“女嬃”是女巫,然而此中只是女巫名叫李女須,並不是説凡是女嬃就是女巫。况且顔師古的注釋已經説得很明白了,“女嬃者, 巫之名也”,是説這個女巫的名字是“女嬃”。游國恩先生指出:“蓋巫者名須,名須者不必皆爲巫者也。吕后之妹亦名嬃,豈亦巫者乎?”(30)游國恩主編:《離騷纂義》,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第189頁。
至此,各家據以立説的傳世文獻梳理完畢。總結以上的論據和論點,我們能够知道:“嬃”是女字,可以作爲人名。此外,“嬃”也很可能是女性的通稱。而且這兩者也可以同時成立。如吕后字娥姁(《史記·外戚世家》),其姊名長姁(《史記·惠景間侯者年表》),而“姁”字《説文》云:“嫗也。”徐灏《説文段注箋》云:“姁蓋即嫗之異文。”“嫗”即爲婦女通稱,如桓寬《鹽鐵論·毁學》:“趙女不擇醜好,鄭嫗不擇遠近。”秦漢女性又多以“姬”爲名字,如人們熟悉的“蔡文姬”。《詩經·陳風·東門之池》:“彼美淑姬”,孔穎達疏云:“美女而謂之姬者,以黄帝姓姬,炎帝姓姜,二姓之後子孫昌盛,其家之女美者尤多,遂以姬姜爲婦人之美稱。成九年《左傳》引逸詩云:‘雖有姬姜,無棄憔悴’,是以姬姜爲婦人美稱也。”(31)《毛詩正義》,第521頁。《史記·貨殖列傳》:“今夫趙女鄭姬。”足證“姬”亦爲婦女通稱,且可以爲女性名字。
“嬃”可能是女性通稱,則“女嬃”一詞就與“婦女”一詞同例。游國恩先生即持此説,認爲“女嬃爲楚人婦女之通稱”。那麽“女嬃”的涵義是否僅此而止?下面我們根據出土文獻的材料,進一步分析“女嬃”的問題。
既然“嬃”和“女嬃”在漢代作爲人名出現,我們可以從人名的角度切入這個問題。“嬃”字亦見於秦漢私印的印文中(32)以下所引漢印文字如無特殊説明,皆引自李鵬輝:《漢印文字資料整理與相關問題研究》,安徽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7年。,如:
秦印:新嬃
漢印:趙嬃、侯嬃、妾女嬃、趙穉嬃(33)羅福頤:《漢印文字徵補遺》,北京:文物出版社,1982年,第165頁。
此外,漢代私印中有一些雙面穿帶印,其正反二面分别是其人的姓名與姓字:
韓嬃之印—韓少孺
酈到—酈少嬃
在以上這些人名中,唯一能够確定其爲女性之名的只有“妾女嬃”。漢代的私印中往往使用謙稱,一般男性在名前加“臣”,女性在名前加“妾”,因此該印的主人是女性並且以“女嬃”爲名。這就和《漢書·武五子傳》所載女巫李女須的名字相合。這樣我們就更加確定“女嬃”可以作爲女性的名字,也能够反證“女嬃”並非巫女之稱。
而對於“妾女嬃”以外的私印,儘管不能確定這些名“嬃”者的性别,但是通過上面這些名、字的關係,我們仍然能够對這些名字中“嬃”的含義有所了解。首先,韓嬃名嬃字少孺,而少孺乃是漢代習見的字。如枚乘之子枚皋,《漢書·賈鄒枚路傳》載:“皋字少孺。”從漢印中亦可知漢人常以“少孺”爲字:


孺本來是幼小孩童之意,少孺即是此義。以“穉孺”一名而論,穉乃幼稚之意,與“孺”意近。《世説新語·德行》:“至,便問徐孺子所在,欲先看之。”劉孝標注云:“謝承《後漢書》曰:‘徐稚字孺子’。”(36)余嘉錫:《世説新語箋疏》,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第1頁。從名字相應的角度上看,“韓嬃之印—韓少孺”“曹小—曹少孺”都是名字意義相近的例子。秦漢時人往往以幼兒義的孺、稚、嬰、兒等作爲名、字,且男女通行。如先秦有“程嬰”“晏嬰”“田嬰”,漢代有“項嬰”“灌嬰”“夏侯嬰”“韓嬰”“竇嬰”等等。《急就篇》中載常見人名,其中有“田細兒”。“細兒”自然就是小兒,《列女傳·節義》:“友娣者,郃陽邑任延壽之妻也,字季兒”,又《漢書·衛青霍去病傳》:“衛媪長女君孺,次女少兒”,江蘇盱眙大雲山西漢江都王陵北區陪葬墓M12出土一方雙面穿帶銅印(37)南京博物院、盱眙縣文廣新局:《江蘇盱眙縣大雲山西漢江都王陵北區陪葬墓》,《考古》2014年第3期,第34頁。,一面印文爲“妾勝適印”,一面印文爲“淳于嬰兒”,墓主人是江都王劉非的嬪妃,則此人名爲勝適,字嬰兒。蘇鶚《蘇氏演義》卷上云:“兒者,嬬也。謂嬰兒嬬嬬然,輸輸然,幼弱之象也。亦曰孺子,與嬬同義。”(38)(唐)蘇鶚著,吴企明校點:《蘇氏演義》,北京:中華書局,2012年,第19頁。
不僅如此,古人常以“孺”“兒”等稱呼女子。“孺”字《説文》訓“乳”,本爲孩童之意。對於女子稱“孺”,章太炎先生有過這樣的解釋:“《左傳》‘南孺子’,《禮記》有‘孺人’,漢宫有‘孺人’。蓋本訓乳子,因古人視女子甚小,故引申稱婦爲孺,猶稱小童也。”(39)章太炎:《章太炎説文解字授課筆記》,北京:中華書局,2010年,第610頁。説明古人通常將女子視作幼弱、幼小。此外,文獻中的“女兒”一詞亦可爲證。“女兒”猶言婦女,如《史記·張耳陳餘列傳》:“今女兒乃不爲將軍下車”,其中的“女兒”指趙王姊。又《漢書·地理志》載:“襄公淫亂,姑姊妹不嫁,於是令國中民家長女不得嫁,名曰‘巫兒’,爲家主祠。”巫兒即是巫女。後世婦女仍多以“兒”稱。
人名中的“嬃”與“孺”“稚”“嬰”“兒”等意義相近;而且“嬃”既與“嬬”相通,《集韻·虞韻》:“嬬,婦人弱也。”《説文》:“嬬,弱也。”段注云:“嬬之言濡也。濡、柔也。”(40)《説文解字注》,第624頁。因此“嬃”應該有幼弱、幼小的涵義。

“嬿”,段注云:“毛詩‘燕婉之求’,傳曰:‘燕,安。婉,順也。’韓詩作‘嬿婉’,‘嬿婉,好皃。’見《西京賦》注。”(43)《説文解字注》,第617頁。
“婀娜”又作“妸娜”,是轻盈柔美貌。
“婕嬩”即文獻中的“婕妤”(“嬩”下徐鍇云:“古婕妤字也”),而《史記·外戚世家》:“幸夫人尹婕妤”,《索隱》:“一云:美好也。”(44)《史記》,第2391頁。
《詩經·陳風·月出》:“佼人僚兮”,毛傳云:“僚,好貌。”《釋文》云:“僚,本亦作嫽。”(45)《毛詩正義》,第528—529頁。
“孁”字見於西周金文,“孁(靈)冬(終)”(《集成》9433)“靈終”即“令終”,是善終之意。可見“孁”大概也是善好之意。
“姶”字見於漢印人名“乘馬姶-乘馬少娃”,《方言》:“娃,美也。”《廣雅·釋詁一》:“娃,好也。”如果名字相應的話,那麽“姶”應該也有美好意。
其次,幼小與美好意義相因在《楚辭》中是有實際例證的,《楚辭·九歌·少司命》:“竦長劍兮擁幼艾”,洪興祖《楚辭補注》云:“《孟子》曰:‘知好色則慕少艾’,説者曰:‘艾,美好也。’《戰國策》云:‘今爲天下之工或非也,乃與幼艾。’又:‘齊王有七孺子’,注云:‘孺子,謂幼艾,美女也。’《離騷》以美女喻賢臣,此言人君當遏惡揚善,佑賢輔德也。”(46)(宋)洪興祖著,白化文等校點:《楚辭補注》,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第73頁。古人將幼艾、孺子、美女這些詞互相訓釋,可見幼小與美好二義相因。特别是聯繫上文“嬃”與“孺”的密切關係,而“孺子”又指美女,“嬃”有美好、美麗的意思自然是可以理解的。
準此,“嬃”字除了幼小之外,還應該有美好的意義。姜亮夫先生《楚辭通故》云:
按此須,蓋即漢人所用之娵字。《七諫·怨世》云:“親讒諛而疏賢聖兮,訟謂閭娵爲醜惡。”王注云:“閭娵,好女也。”《補注》引《荀子·佹詩》“閭娵(今本或誤姝,聲近字也。)子奢,莫知媒兮”。韋昭注梁王魏瞿之美女娵,音鄒。《集韻》音須。又《哀時命》“隴廉與孟娵同宫”。王逸注“孟娵,好女也”。洪補音須,又音鄒,是須當即娵之異文…… 魏王美女曰閭娵,則吕后弱妹亦得吕須,廣陵厲王有女巫曰李女須,此用須字名女娟美幼小者,後人名人女曰娙、曰娥、曰娟、曰秀而已……則女嬃者,戰代以來婦女幼小娟好者之詞耳。(47)《姜亮夫全集》二《楚辭通故》第二輯,第176頁。
從出土文獻來看,姜説把“嬃”與“娵”視爲一字是有問題的,但是他對“嬃”字詞義的把握則十分準確。北大漢簡《蒼頡篇》魚部有“盨娶褭嬽”一句。“盨”當讀爲“嬃”;“娶”字整理者以爲嫁娶之娶,但是出土文獻中往往以“取”記録嫁娶之“娶”。簡文“娶”字實即上引漢人所用之“娵”,乃訓美女。簡文中的“褭”“嬽”二字整理者分别注云:
《淮南子·原道訓》“馳要褭”,高誘注:“褭,橈弱之弱。”又《文選》陸機《擬魏太子鄴中集詩》“白楊信褭褭”,李善注曰:“褭褭,風摇木貌。”故“褭褭”即柔弱、輕盈而摇曳之貌。褭,泥母宵部字,同音字有“嬈”“嫋”,亦均輕盈柔美貌。
《説文》:“嬽,好也。”《玉篇》:“嬽,美女也。”《漢書·司馬相如傳》之《上林賦》有“柔橈嬽嬽”句,《史記·司馬相如列傳》作“柔橈嬛嬛”,索隱引郭璞曰:“柔橈嬛嬛,皆骨體耎弱長艷皃也。”(48)《北京大學藏西漢竹書》壹,第101頁。
則簡文的“娵褭嬽”三字皆是柔弱美麗之意,“嬃”字自應與其義近。
所以,作爲女性人名的“嬃”應該兼有幼弱與美好二義,而且“女嬃”很可能如姜亮夫先生所云,是“戰代以來婦女幼小娟好之詞”。
清華簡第九輯新刊佈的《禱辭》爲我們檢驗以上論斷,確定“嬃”的詞義,提供了新的材料。《禱辭》的内容是爲禱祠地祇的告事求福之辭,其中簡21—22提到了獻祭的物品(釋文用寬式):
皋!告爾君夫、君婦、某邑之社:使四方之民人遷著於邑之於處,吾使君鬯食,且獻乘黄馬與二有嬃女。乘黄馬未駕車,二有嬃女未有夫。(49)黄德寬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玖),上海:中西書局,2019年,第183頁。
祭品是“乘黄馬”與“二有嬃女”,並且承諾祭品的品質很高:“乘黄馬未駕車”、“二有嬃女未有夫。”
根據簡文所言的“二有嬃女未有夫”,説明“有嬃女”是可以有夫、可以無夫的。以往一些説法認爲“嬃”指小妻或者媵妾,自然和簡文相矛盾,所以這種説法不能成立。
“乘黄馬”與“二有嬃女”的結構一致,“乘”與“二”是量詞,“黄”和“有嬃”是修飾成分,“馬”和“女”是被修飾的中心語。整理者已經指出:“黄爲馬之上色”(50)《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玖),第188頁。,則“嬃”也一定不會是賤稱,而應該是對女性的某種美好特質的形容。
討論至此,同樣與獻祭有關的一個故事不能不引起我們的注意。《史記·滑稽列傳》:“巫行視小家女好者,云是當爲河伯婦”、“西門豹曰:‘呼河伯婦來,視其好醜。’即將女出帷中,來至前。豹視之,顧謂三老、巫祝、父老曰:‘是女子不好,煩大巫嫗爲入報河伯,得更求好女,后日送之。’”(51)《史記》,第3872—3873頁。故事中爲河伯娶婦的情節,實質上也是一種對於神靈的獻祭,而且祭品同樣有女子。值得注意的是,故事中特别提到了“視其好醜”以及“是女子不好”。衆所周知,“好”是指女子貌美,可見作爲祭品向神靈獻祭的女子需要滿足一個條件,就是貌美。回過頭來看清華簡《禱辭》的辭例,則“二有嬃女”自然也是指兩個容貌美麗的女子。因此,前文“嬃”作爲人名具有“幼弱”與“美好”二義的論斷進一步得到了清華簡《禱辭》辭例的證實。
需要説明的是簡文中“有嬃女”的結構。簡文中以女子與車馬獻祭的句子還有下面兩處的描述:
很顯然,簡文的“淳女”與“兩女”以及我們上面所討論的“二有嬃女”所指相同。對於“(淳)女”一詞,整理者注釋云:“,讀爲‘淳’,可訓‘清白’。《玉篇》:‘淳,清也。’淳女,即後文未有夫之女。”(54)《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玖),第188頁。整理者應該是基於“女”與“美馬”對文,所以將“”理解爲形容詞。但是例(2)的“兩女”與“美車馬”却不都是形容詞。况且“淳”當清白講恐怕出現得比較晚。將全篇的“女”“兩女”“二有嬃女”綜合起來看,“”應該也是量詞。“”字从木、聲,讀爲“淳”自然可通。不過“”聲字在出土文獻中還有一個重要的通假,就是讀爲“純”。朱德熙先生的名文《説“屯(純)、鎮、衠”》曾詳細討論了總括副詞“純”字的源流,並且指出:
用爲總括詞的“屯”除了寫作“純”字以外,還有寫作“淳”的。……“淳”和“純”古音同聲同部,可以相通。《周禮·天官·内宰》:“出其度量淳制”,鄭注“故書淳爲敦,杜子春讀敦爲純”;又《地官·質人》“壹其淳制”,鄭注“杜子春云淳當爲純”,並可證。(55)《朱德熙古文字論集》,北京:中華書局,1995年,第175頁。
尤其是朱先生指出了“純”的一種用法是指一對。“殷人稱卜骨或背甲一對爲‘一屯(純)’。卜骨一屯指牛之左右肩胛骨各一塊。背甲一屯指背甲從中間剖開後的左半和右半。”(56)《朱德熙古文字論集》,第178頁。他引用《儀禮·鄉射禮》“二算爲純”,鄭玄注:“純猶全也,耦陰陽”來説明這種用法。此外,《大戴禮記·投壺》:“二算爲純,一純以取一算爲奇”,孔廣森《補注》云:“凡物耦曰純。”(57)(清)孔廣森著,王豐先校點:《大戴禮記補注》,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第232頁。都可以證明“純”是一對的意思。我們認爲《禱辭》簡15的“女”當讀爲“純女”,就是他處簡文的“兩女”、“二有嬃女”。(58)李守奎師在看過本文後指示筆者,“二有嬃女”的“有”可能讀爲“友”,也是指一對。見李天虹:《楚國銅器與竹簡文字研究》,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12年,第189頁。不過考慮到“兩女”與“純女”的結構,而且“二有(友)”兩個量詞並列似乎少見,故本文仍以“有”爲助詞。
我們知道,楚地墓葬中往往陪葬以木俑。而女性形象的木俑更是常以成對出現,如江陵馬山楚墓出土有4件彩繪着衣女木俑(59)湖北省荆州地區博物館:《江陵馬山一號楚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80頁。,曹家崗楚墓出土2件女性面俑(60)黄岡市博物館、黄州區博物館:《湖北黄岡兩座中型楚墓》,《考古學報》2000年第2期,第268頁。等等。不少墓葬同出的遣册中還有相應的記載,如湖北雲夢西漢墓M1木牘載“女子禺(偶)人四”(61)陳振裕:《雲夢西漢墓出土木方初釋》,《文物》1973年第9期,第37頁。,長沙馬王堆M3遣册簡43“美人四人,其二人仇(裘)服,二蹇(褰)”。簡44“美人四人,其二人楚服,二人漢服”。(62)湖南省博物館、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長沙馬王堆二、三號漢墓》第一卷“田野發掘報告”,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年,第50頁。湖北江陵鳳凰山M168簡6“美人女子十人”(63)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江陵鳳凰山西漢簡牘》,北京:中華書局,2012年,第184頁。等等,可見楚人有以成對美人殉祭的習慣。也可以從側面證明《禱辭》的“純”是指一對。
既然“純”“兩”“二”都是量詞,那麽“有嬃女”應該是一個獨立的名詞性結構。“有”應該是一個助詞,放在單音節形容詞之前。《詩經》中常見其例,前人多稱爲“狀物之詞”。《詩經·小雅·何草不黄》:“有棧之車”,孔穎達疏云:“有棧是車狀,非士所乘之棧車也。”(64)《毛詩正義》,第1113頁。《詩經·周頌·載芟》:“有厭其傑”,毛傳云:“言傑苗厭然特美也。”(65)《毛詩正義》,第1597頁。“嬃”是形容女子柔弱嬌美之詞,“有嬃女”即“有嬃之女”,相當於《何草不黄》的“有棧之車”,指柔弱嬌美的美女。
結合以上論述,我筆認爲《離騷》的“女嬃”是指柔弱嬌美的美女。與“女嬃”構詞類似的有“女好”,見《荀子·賦》:“此夫身女好而頭馬首者與。”梁啓雄《荀子簡釋》云:“《方言》:‘凡美色或謂之好’,女好即女媄。此言蠶身似女媄,蠶頭似馬首。”(66)梁啓雄:《荀子簡釋》,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第359頁。這類形容女性的詞往往既是形容詞又是名詞,如《方言》:“娥,好也”、“秦晋之間美貌謂之娥”、“娃,美也”(67)(漢)揚雄:《方言》,北京:中華書局,2016年,第1、18頁。,也同樣可以作爲名詞指美女,還常常作爲女性名字,如吕后字娥姁。幼弱嬌美的美女《楚辭》中還有“姱女”,見於《九歌·禮魂》:“姱女倡兮容與”,王逸注云:“姱,好貌也。謂使童稚好女先倡而舞。”(68)《楚辭章句》,第65—66頁。
而對於爲何此處以“女嬃”這樣的美女來設辭立言,前人從文義和辭氣上已有很多論述,如清人施愚山云:“屈所謂女嬃,明從上文美生端。”(69)《姜亮夫全集》二《楚辭通故》,第177頁。又游國恩先生在《離騷纂義》中指出:“此處必以女嬃爲言者,因屈子嘗托美人以自喻,故假設有人責勸之亦當托爲女性,此亦猶上文嫉余蛾眉者之必爲衆女也。”(70)《離騷纂義》,第189頁。其説於修辭文情都十分融洽,更可從側面説明“女嬃”一語乃是指一柔弱嬌美之美女。